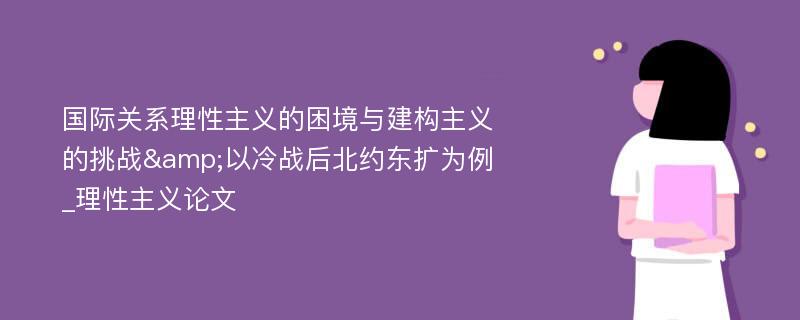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建构主义的挑战——以冷战后的北约东扩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为例论文,战后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60—66
冷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扩大是国际关系学界较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不仅有大量的学者从政策层面进行分析,同时也有大量的国际关系学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尤其是冷战结束前后,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北约未来的预测与现实国际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偏差,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没有预测到冷战后的北约会以一种相当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进行反思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效用。如罗伯特·劳赫豪斯(Robert W.Rauchhaus)大声质疑说,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没有预测到北约的扩大?① 因此,围绕冷战后北约的扩大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几大流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扩大预测的失效
冷战结束前后,一大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对北约的未来进行预测,主要包括现实主义的“消亡”论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存在”论。冈瑟·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与莱茵哈德·沃尔夫(Reinhard Wolf)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种角度对北约的未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新现实主义认为,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同盟的凝聚力将会下降,北约停止作为一个有效的同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则宣称北约高度的制度化将保证其以某种形式得以生存。同盟或者以目前的形式继续下去,或者在成员国之间通过合作性安排来适应新的安全环境。从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北约的消亡可能性最大,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预测是北约或者继续存在或者发生深刻的转变。② 但是,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没有预测到冷战后的北约会以一种相当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
早在冷战结束前,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对北约的前途就持一种较为悲观的态度,认为北约的消亡是必然的。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就断定,苏联威胁的下降将鼓励西方同盟为遏制一个直接的军事挑战付出较少的代价,西方对于威胁认识持续性地减小将最终导致北约的消亡。③ 他说:“没有明晰和现实的威胁,无论是欧洲的政治家还是美国的纳税人都不可能支持美国在欧洲大规模的军事存在。虽然北约复杂而详尽的制度性结构将会减缓其解体的速度,但只有苏联威胁的复兴才可能使北约留存并维持既有的模式。”④ 同样,就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ier)就预测说,没有苏联的威胁,北约将中止作为一个有效的同盟出现。苏联的威胁把北约国家绑在一起,这一进攻性威胁消失后,美国有可能放弃欧洲大陆,北约这一防御性同盟也将解体。⑤ 1990年,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也预测说,欧洲所发生的剧变将导致一个多极世界的出现,其中,北约和华约将会崩溃或发生急剧的变化。⑥ 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 N.Waltz)1990年也写道,北约正在走向消亡,现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机构还将存在多长时间,即使它的名称还会暂时得到保留。⑦
与现实主义对北约的态度相比,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北约的未来没有太多的悲观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北约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同盟,主要是因为:第一,北约高度的制度化;第二,北约不仅仅要在军事上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进行威慑,还存在其他的目标,如促进成员国安全、防止成员国之间的安全竞争。苏联的解体使北约的一项主要任务消失了,但是其他的任务还继续存在,如抑制德国、使美国仍保留政治与军事存在,以及应对冷战后出现的新威胁。⑧ 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 A.Wallander)认为,北约需要被理解为一个安全管理机构,它不仅仅用来应对外在威胁,而且也用来处理成员国之间相互不信任、误解等问题。北约不仅仅是一个同盟,北大西洋理事会以及北约的其他机构在推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在处理彼此不信任问题上,都发挥着关键作用。⑨
因此,在对待冷战后的北约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学者主张:第一,利用北约已有的规范与程序来处理新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组织;第二,改变北约,在进行必要的改革后再来处理问题;第三,利用现有机制加强同其他行为体、国家及非国家的联系,寻找制度目标。⑩ 制度学派以制度为工具来分析北约的最大贡献是,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制度的北约能够在面对变化了的环境下持续地生存下去,主要是由于制度属性的作用。冷战的结束没有带来北约的消失,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预测北约在冷战后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对北约的扩大作出准确的预测,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国际政治的偏差使得人们对其理论的效用提出了质疑。
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辩论
尽管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北约扩大问题上的预测失效,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是其理论本身的失误,相反,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试图论证各自观点的正确性。(11)
北约作为一个冷战时期的传统的军事同盟,其在冷战后的继续生存、改革以及扩大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者极大的兴趣:同盟何以形成?同盟何以持续发展下去?同盟何以扩大规模等?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同盟是对威胁能力的一种反映,实力分配的变化决定同盟的命运。同盟的凝聚力依赖于成员对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对手所造成的威胁决定同盟的凝聚力。例如,沃尔特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同盟会瓦解以及为什么有的同盟面对困境会继续生存下来的问题,尤其是,在原有的合理性消失后,为什么有的同盟会继续生存下来?沃尔特精辟地指出,影响北约的继续生存与扩大,最大的因素是霸权国的领导地位。(12) 因此,从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出发,在欧洲安全均势以及北约外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北约的消亡是符合其理论的必然路径。
然而,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不断向防区外扩张。针对这一情况,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正是制度的力量保障北约的继续存在并得以扩大。制度被创造出来是因为国家认为制度符合他们的利益,制度应该得以延续,只要,而且仅仅只要其成员有动机来维护他们就行。当国家在一种稳定的制度下进行合作时,会较少关注相对收益。因此,尽管外在的威胁已经消失,但是北约的制度性因素还存在,北约扩大反映了北约制度性力量的存在。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联盟是一种制度,其持续的时间及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特点,制度难以建立,而一旦建立,它的运行就有一种自发性,较少依赖联盟内成员国的意志。北约在冷战后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这证明了国际机制的重要性。(13) 亚历山大·格修(Alexander Gheciu)也认为,北约远远不是一种地缘战略安排用来应对苏联的威胁,北约是一种制度,它把内在的安全逻辑和外在的安全逻辑结合在一起。北约的创造者不仅要对潜在的地缘战略挑战作出反映,而且还要创立集体的西方认同,保护欧洲大西洋地区的自由主义规范。(14) 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对北约的制度框架大加赞赏。他说,北约本身是一个政治法律框架,有完美的政治协商、军事运作模式,程序完备,有一体化的军事结构。(15)
但新现实主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制度与相对收益的观点,指出北约的扩大并不是制度的力量,而是大国主导下的扩张。新现实主义认为,即使是在稳定的状态下合作,国家也会关注相对收益。国家寻求维持其独立并努力避免卷入国际组织,当收益不平衡地进行分配时,即使是强大的国际制度也必然崩溃。(16) 制度作用的强弱依赖于国家的意图,强大的国家利用制度,制度的作用就大。(17)
从上述理论出发,沃尔兹明确指出,冷战后北约的继续生存与扩张是美国所推动的产物,他说:“北约之所以继续生存下来并向东扩大,完全是美国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是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北约在冷战后的留存和扩大并不是制度的特点,而是美国使之如此。国际机制由大国创立,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国际利益。”(18)
总之,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相互辩论不仅反映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国际政治之间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双方试图努力论证各自理论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下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面对理性主义的困境,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方法论开始介入北约问题的研究并挑战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方法论。
三、理性主义的困境与建构主义的挑战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其结盟理论密切相关。在理性主义看来,不结盟或结成小的同盟是理性的行为。因此,同盟的扩大,尤其是在促使同盟形成的合理性不复存在的背景下实现扩大是不现实的。新现实主义认为,一般来说,国家不会选择结盟。因为结盟会减少行动的自由,并且还要承担被欺骗的风险。只有在一个国家不能维护其安全、不能保护他们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时才会选择结盟。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为,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少数几个成员结盟优于许多成员结盟。一般来说,国际组织的规模越大,新成员的贡献就越小,从合作中获得利益的分配就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就越大,管理成本以及达成一致的成本就越高。(19) 因此,从理性主义的同盟理论出发,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不可能预测到北约的扩大。新现实主义理论不仅不能预测到北约的扩大,相反,从其同盟理论出发还预测冷战终结后其结果是北约趋于瓦解。即使北约继续得以生存,本身也没有必要扩大。(20) 新自由主义预测,由于制度的作用北约将继续生存下来,但它不能预测到北约所发生的深刻转型,尤其是北约的扩大。
因此,在主流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视角挑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建构主义从国际关系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并以其主要的核心概念,如规范、认同与文化来分析世界政治。在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有效预测并分析北约及其扩大的情况下,建构主义从国际社会化、安全文化的视角对北约的扩大、北约的未来以及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开始挑战理性主义范式。建构主义拒绝理性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前提,并对理性主义所给定的一种稳定的成员认同、利益和偏好提出疑问。建构主义批驳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第一,国际无政府状态不是永恒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第二,国家利益不是提前给定的,也不是不变的,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是共有观念建构的产物。
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认为安全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是通过“捍卫”而实现的相比,建构主义的安全观是建立在行为体的规范与认同基础之上的,认为安全利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被认识的过程。如在温特看来,国家利益是指国家一社会复合体的再造要求或安全要求,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21) 温特反对理性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首先给定论,认为国家利益是认同的产物,认同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同样,卡赞斯坦也认为,安全利益是行为体对文化因素作出反映后而定义的,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过程形成的,是“定义”的而不是“捍卫”的。(22)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北约既不是像新现实主义那样所理解为一种结盟的形式,也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理解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国际组织,而是被视为一个具有价值观与规范的国际共同体的组织。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论来分析北约及其扩大,如弗兰克·施默芬宁(Frank Schimmelfennig)、亚历山大·格瑟(Alexander Gheciu)、彼德·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基思·克劳斯(Keith Krause)、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罗伯特·鲁宾斯坦(Robert Rubinstein)等。(23)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介入为分析北约扩大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研究视角。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国际社会化理论是北约问题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针对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北约以及北约的扩大,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北约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国际性的社会化过程,亦即北约将自身的行为规范、价值观通过社会建构的过程使中东欧国家得以接受,中东欧国家通过学习北约的规范与价值观并内生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对北约的认同并得到北约的认可。施默芬宁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分享共同体的价值观和规范,它就可能被一个国际组织接受为成员。内在化的过程越快,它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也就越早。(24)
对北约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社会化互动研究的西方学者主要有弗兰克·施默芬宁与亚历山大·格瑟等。弗兰克·施默芬宁把一个国际组织的扩大视为一个国际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就是社会行为体把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内在化。通过这种方法,行为体获得了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从国家层面上看,内在化是指把一个国际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嵌入国内决策的过程。从制度层面上看,成功的内在化是把基本的共同体规范一体化于国家的宪法,并演变为稳定的国内法律。成功的内在化要求把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有效地嵌入国内制度与国内事务并决定国家的行为。弗兰克·施默芬宁还认为,国际社会化的方法为解释北约扩大提供了答案:第一,中东欧国家想努力成为北约成员国是因为他们想分享西方共同体的价值观或规范,寻求一种认同并得到西方的认可;第二,北约决定扩大是因为要加强自由民主的规范和多边主义,在中东欧国家营造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规范基础上的稳定的和平。(25)
同样,亚历山大·格瑟也认为,社会化是一个吸收新成员融入共同体或社会群体并吸取规范和原则的过程。在他看来,成功的社会化其结果在于采纳新的规范,重新定义认同和利益,并与那些规范相一致。为了把一个行为体变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必须成为一个行为体认同的内在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化中,一个国际共同体及其组织把他们的基本规范与价值观“教”给一个国家或社会。国家与共同体以及组织的关系依赖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认同与利益建立在共同体的价值观与规范的基础上。为了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国家不得不接受共同体的“授课”,即内在化他们的价值观、规范和实践。他们也不得不经过一个试用的阶段,共同体要对这些申请国进行评估,看他们是否内在化共同体的认同或者是简单地适应它。获得完全的成员国资格的标准是社会化过程有充分的进展,而且共同体认为,这些申请国是他们中的一员。(26)
除了国际社会化的核心概念外,建构主义关于安全文化的核心概念也为解释北约扩大提供了极好的视角。北约的扩大就是北约安全文化以及规范与认同的扩大。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安全文化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行为体与社会关系的不断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逐渐确定其行为规范、集体认同与安全利益。(27)
冷战结束以来,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加。许多西方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安全问题,其中以彼德·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为代表,形成了安全文化这一核心概念以及相应的安全文化理论。卡赞斯坦认为,安全是规范、文化与认同的结合。国家安全文化通过规范、文化及认同得以表现出来。规范为有着特定认同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描绘了一个共同的期望,不同的规范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不同的安全文化具有不同的规范与认同,因而对安全利益的认识也大不一样。(28) 除彼得·卡赞斯坦外,西方学者,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基思·克劳斯(Keith Krause)、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罗伯特·鲁宾斯坦(Robert Rubinstein)等都在这一领域有较为突出的贡献。如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基思·克劳斯认为,冷战后的一个共识正在出现,那就是文化在形成国际政治行为,以在塑造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思认为,有三种文化共同塑造了安全文化,即外交文化、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外交文化是国家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互动中的行为规则,包括特定的程序与约定;政治文化是描述国内政治制度或安排的区别,揭示不同政治辩论的社会基础;而战略文化则是建立在军事机制基础上的一整套规范与态度,如关于战争的政治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最有效的运行方法。三种文化之间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也具有共同的特点,其中心部分就是安全文化。(29)
尽管建构主义流派的理论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运用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对实际问题进行剖析,如对冷战时期形成的北约的研究就是一例。建构主义把北约更多视为一种制度而不是一个同盟。但是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的是,他们关注的是国际制度怎样有助于形成规范,并改变国家的偏好。(30)
在卡赞斯坦的笔下,北约代表了一种安全文化,其内涵是:北约“代表了基于共同价值观及对自由民主的集体认同之上的跨大西洋的安全共同体”,北约“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民主国家不仅不相互打仗,还可能发展一种集体认同,使合作变得容易,为特定目的而产生合作的制度。这些制度的特点是民主的规范、决策原则,其中,……规范与原则的实施加强了共同体的意识及主体的集体认同”。(31) 温特也从非竞争性及团结一致的角度解释了“安全共同体”及“集体安全”这两种国际关系领域的现象。在温特看来,北约这样一个“功能良好的集体安全体系”就是一个多元的安全共同体,“这种结构没有一个单独的元首,但是仍然能够实施制度性集体行动”。(32)
总之,建构主义的国际社会化理论与安全文化理论认为,行为体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之中,不同的行为体在这种关系与环境中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形成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定位。社会化导致行为体接受共同体的规范与原则,并内生为自身的规范与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共同体相一致的安全文化。建构主义的理论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出现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面对现实国际政治发展时所遭遇的理论困境。
注释:
① Robert W.Rauchhaus(ed.),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Frank Cass,2001,p.9.
②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Neorealism,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nd the Future of NATO,”in Security Studies,Vol 3,No.1,Autumn 1993,pp.26—28.
③ Stephen M.Walt,“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What Lies Ahead?”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3,nol,Summer/Fall 1989,pp.8—9.
④ 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⑤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15:5—56,1990.
⑥ Glenn 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m First Cu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No.1,Spring/Summer 1990,p.121.
⑦ Kenneth Waltz's Statement at a U.S.Senate Hearing in November 1990,quoted in Risse-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p.363.
⑧ Robert W.Rauchhaus(ed.),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Frank Cass,2001,pp.6—14.
⑨ Wallander and Keohane,Risk,Threat,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⑩ Robert B.McCalla,“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0,3,Summer 1996,p.464.
(11)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Neorealism,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nd the Future of NATO,”in Security Studies,Vol.3,No.1,Autumn 1993;Celeste A.Wallander,“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NATO after the Cold War,”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4,4,Autumn 2000,pp.705—735;Charles L.Glaser,“Why NATO is Still Best,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1(Summer,1993),pp.5—50;Richard Rupp,“NATO 1949 and NATO 2000:From Collective Defense toward Collective Security,”edited by Ted Galen Carpenter,NATO Enter the 21st Century,Frank Cass Publishers,2001,etc.
(12) Stephen M.Walt,“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 1997,pp.164—168.
(13) Keohane,Robert,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Colo.:Westview,1989.
(14) Alexander Gheciu,NATO in the “New Europe,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32.
(15) David C Gompert and F.Stephen Larrabee,America and Europe,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83.
(16)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Neorealism,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nd the Future of NATO,”in Security Studies,Vol.3,No.1,Autumn 1993,p.11.
(17) Kenneth N.Waltz,“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NATO Expansion,The Debate over NATO Enlargement,”Conference Papers,March9—10,199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8) Kenneth N.Waltz,“Structu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2000,pp.5—41.
(19) 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Stephen M.Walt,“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 1997,pp.156—79;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assachusetts: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9.
(20)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5—56,1990;Stephen M.Walt,“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What Lies Ahead?”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3,No.1,Summer/Fall 1989,pp.8—9;“Kenneth Waltz's Statement at a U.S.Senate Hearing in November 1990,”quoted in Risse-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p.363;Glenn 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m First Cu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No.1,Spring/Summer 1990,p.121.
(21)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293—294页。
(22) 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2—5.
(23) Frank Schimmelfennig,“NATO Enlargement: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Security Studies,Vol.8,No.2/3,Winter 1998/99-Spring 1999;Alexander Gheciu,NATO in the “New Europe,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Keith R.Krause(ed.),Culture and Security,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Frank Cass Publishers,1999,etc.
(24) Frank Schimmelfennig,NATO Enlargement: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Security Studies,Vol.8,No.2/3,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25) Frank Schimmelfennig,“NATO Enlargement: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Security Studies,Volume 8,Number 2/3,Winter 1998/99-Spring 1999.,pp.198—199.
(26) Alexander Gheciu,NATO in the“New Europe,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0.
(27) 彼德·卡赞斯坦著:《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言。
(28) Peter J.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2—5.
(29) Keith R.Krause(ed.),Culture and Security,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Frank Cass Publishers,1999.
(30) Robert W.Rauchhaus(ed.),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Frank Cass,2001,p.17.
(31) 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395—397.
(32)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261页。
标签:理性主义论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建构主义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新现实主义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北约东扩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同盟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