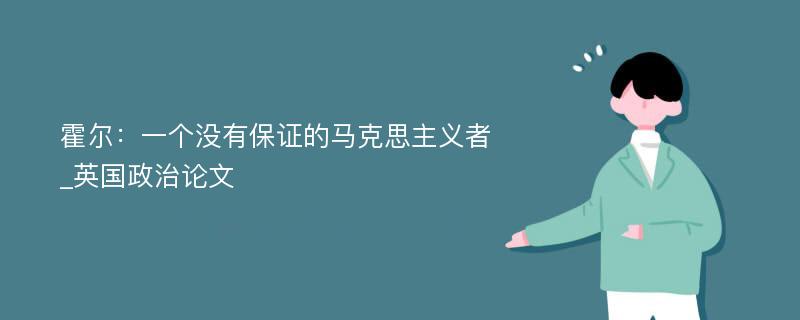
霍尔:“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尔论文,不作论文,马克思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2月10日深夜,我从英伦友人处惊闻斯图亚特·霍尔去世的消息,顿时睡意全无,旋即点开了电脑里保存的纪录片《斯图亚特·霍尔计划》(The Stuart Hall Project)。其间,我一边体悟霍尔作为“熟悉的陌生人”的璀璨传奇的一生,以及他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多元文化主义”、“接合理论”等理论遗产,一边回忆自己的“无霍尔不成课”的英伦问学经历。 1932年,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出生在英国前殖民地牙买加首府金斯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加勒比移民潮期间,霍尔作为1951年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乘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帝国风潮号”(The Empire Windrush)客轮来到了英国,以牛津大学为起点开始了他在英国作为“熟悉的陌生人”的生活。自此以降的六十余年里,霍尔先后基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大学社会学系等平台,积极地穿梭在社会运动、公众讨论和学术研究之间,有效地开启了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先河,结构性地影响了英国新左政治、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社会学研究等领域,获得了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美誉。促成这一切发生的关键之一,是霍尔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资源核心的坚持。虽然我们必须知道,他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拥趸,而一如他的论文《意识形态问题: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所暗示的①,是一位“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决定论和还原论,强调理论开放性,主张不断理论化,以期保持理论思考与现实介入的良性互动。 创建新左派 登陆不列颠之后不久,霍尔便开始了证明他是“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中见诸他与 E.P.汤普森等人合力创建英国新左派(The New Left)。受成长环境的影响,霍尔从小就有反帝国主义情结,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受其影响,只不过当时他尚未把自己视为欧洲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问学于牛津大学期间,霍尔加入了利维斯派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间的联盟,深刻地认识到了“可供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太机械化,带有过多的还原主义色彩”,于是“强烈批判斯大林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还是一种政治形式”。②随着其政治关切从第三世界殖民问题转移至冷战情势下的英国政治,霍尔开始了与牛津左翼更频繁的接触,不但积极参与讨论“把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应用于当代资本主义是否合适”,而且日益关注“随着保守主义的复兴,工党和左翼的未来是什么?福利国家和战后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什么?在早期‘富裕’的10年中,文化的改变对英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③最终,1956年事件——苏共二十大、苏军入侵匈牙利、苏伊士运河危机——戏剧性地把霍尔的这些关切集中了起来,促成了他决定移民英国,帮助他确定了政治家园:“马克思主义拉着他,对抗布达佩斯的坦克。” 即是说,1956年事件让霍尔看到了支配着20世纪50年代政治生活的西方帝国主义与东方斯大林主义的暴力与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他对英国政治与文化的永久幻想。一如霍尔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所言:“‘匈牙利事件’之后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心怀俄罗斯革命退变为斯大林主义由二十世纪左派所表征的悲剧意识。‘匈牙利事件’终结了某种社会主义‘清白’。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危机’表明了错误之巨大:相信在一些前殖民地降下联合王国旗必然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或福利国家的实际好处、物质富足的扩大意味着不平等与剥削的终结。因此,匈牙利事件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具有阀限作用的’、划定边界的经历。它们象征着政治冰河时代(Ice Age)的结束。”④匈牙利事件与苏伊士运河危机虽然持续时间并不长,但对英国左翼社会力量的影响却是深远甚至灾难性的。正如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所言,匈牙利事件之后,“英国社会主义分子已经不可能盲目地相信史达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教条,甚至必须根本地质疑苏联革命以降的历史大悲剧。另一方面,苏伊士事件也使左翼分子觉醒到殖民主义并未终结,福利国家的出现更不代表剥削的消失”。⑤英共党员因此艰难地徘徊在去与留之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英共党员在力图改变英共方针失败后,选择了退出英共、在党外继续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策略。换言之,英国左翼社会力量基于1956年事件定下的政治边际与界限,同时拒斥了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做出了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寻求第三度政治空间的抉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霍尔等人在巴黎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协会筹备大会期间,自觉接受了法国抵抗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致力于开辟欧洲政治“第三条道路”的克劳德·布尔代(Claude Bourdet)的启发,回国后开始自称“新左派”。⑥ 当然,霍尔对英国新左派的贡献并不仅仅限于为之命名,更重要的是他作为英国新左派刊物《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第一任主编的努力,尤其是在调和《新左评论》前身《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与《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的过程中。《新理性者》的编辑包括E.P.汤普森夫妇、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等人;他们因苏共二十大而痛苦,虽然无意凭一时冲动与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共产主义传统决裂,但坚持要重新发现、重新确定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共产主义传统。《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包括霍尔、加布里埃尔·皮尔逊(Gabriel Pearson)、拉尔夫·萨缪尔(Ralph Samuel)等人;这支以移民为主的编辑队伍均为牛津大学“科尔小组”(Cole Group)成员,反对工党政府在工业国有化等问题上的保守态度,希望与党派组织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虽然同为1956年事件的产物,《新理性者》与《大学与左派评论》显著不同:前者体现反法西斯运动的共产主义传统,联系着约克郡、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工人阶级文化,具有古典性;而后者体现牛桥(Oxbridge)的中产阶级激进主义传统,联系着大都市文化,具有现代性。用霍尔的话来讲,《新理性者》属于“共产主义人道主义”传统,而《大学与左派评论》则属于“无党派社会主义”传统;两种传统之间的区别“并非年龄而是形塑的区别——政治代际的问题,二战于其间构成了象征性的分界线”。⑦尽管如此,因为在倡导民主、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上的一致性,“为社会主义开拓道路,像旧时的传教士一样,宛若燃烧的火焰照亮我们社会的黑暗角落”⑧,加之工党在1959年大选中的败北、办刊经费紧张等因素,《新理性者》与《大学与左派评论》在1960年合并为《新左评论》,霍尔“鲁莽地”担任了第一任主编。 主持《新左评论》伊始,霍尔基于理论的贫乏制约着英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认知,提出了新左运动致力于教育、分析与宣传社会主义,以及阐释霸权等概念的主张,“我们意在介入英国政治生活,发展预示着社会主义本身的一种自发组织的参与式政治实践”⑨,实现了《新左评论》与新左运动的任务分工:前者旨在实现知识分子与工人真正对话,后者致力于制造社会主义者——“我们现在处于宣传阶段……新左派……必须通过为社会主义工作开拓出一条通往未来之路”。⑩于是,《新左评论》成为了英国新左运动的喉舌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另一中心,外在于英国共产党及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其间获得发展。“《新左评论》点燃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复兴,使自己一方面成为了西方主要左翼论坛之一,另一方面成为了社会主义理论重建领域的知名出版机构。”(11)另外,作为主编的霍尔在关于英国社会文化变化的论争中,拒绝了要么否认变化要么颂扬变化的态度,选择了把文化分析和文化政治当作政治学核心问题的“第三种”描述。对自己的这一“不作保证”的实践,霍尔给出了如下解释:第一,只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变迁才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第二,文化维度绝不是社会的一种次要维度,而是一种本质维度;第三,任何能够用于重新描述社会主义的语言,都必须挪用文化话语。(12)所以,倘若认为霍尔参与创建的新左派构成了英国社会左翼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么他主持的《新左评论》则势必为即将显影的英国文化研究介入政治奠定基础。 形塑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 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为了继续其发轫之作《文化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又译《识字的用途》)所开启和代表的工作,在宣布成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以下简称伯明翰中心)的同时,邀请同样拥有左翼背景、感兴趣于媒体与电影研究、颇为文化主义的霍尔作为研究员加入伯明翰中心。1968年,霍尔接替霍加特领导伯明翰中心,开启了伯明翰中心发展史上的霍尔时代。霍尔引领伯明翰中心承继了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宗旨,继续致力于霍加特时代的阶级史、大众文化史、大众记忆等范畴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基于“不作保证”的策略将伯明翰中心的关注焦点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转移到了媒体,“在霍尔的领导下,通过对文本中表意系统的分析,媒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考察”。(13)此外,霍尔也鼓励伯明翰中心开展日常生活历史的人种志研究,见诸对各种青少年亚文化的聚焦,包括它们的建构、它们与母文化和支配性文化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抵制与融合,尤其是在都市青年亚文化这一不曾为霍加特所关注的文化场域中生成意义、制造愉悦的仪式和实践。伯明翰中心在亚文化研究上的成功让女性主义研究大受启发;亚文化研究策略被用于考察女性文化从属地位,重新思考女性与电视之间的关系。1979年,霍尔应邀到开放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伯明翰中心进入“后霍尔时代”,其关注焦点再次转移——文本分析让位于历史,作为伯明翰中心标志性研究之一的人种志研究被边缘化。在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中,直接联系着霍尔的这种非连续性始终存在,因此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的历史更多地联系着霍尔,“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即文化研究的同义词”(14),虽然霍加特创造了作为一个术语的文化研究,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创建了伯明翰中心。其间的原因言人人殊,比如霍尔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更大、霍尔领导伯明翰中心的时间更长,但想必不会有人质疑的是,霍尔时代的伯明翰中心并不鼓励学生以学习理论或攻读学位为首要目的,悖论地通过工作坊或研讨小组等非正式教学方式,培养了文化研究领域的很多代表人物,包括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等等。这些当年求学于伯明翰中心、日后紧密团结在它周围的学者,与霍尔等伯明翰中心的讲师们构成了无人能出其右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其间霍尔不但发起、创办了内部刊物《文化研究工作论文》,而且让伯明翰中心与新左书局即后来的韦尔索出版社、与哈钦森出版集团建立了稳定的外部联系,为伯明翰中心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可靠的传播基地,有效地推动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浮现与播散。 由于坚信“马克思并未提出社会思想如何运作的一般性解释”,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沿着其预定的路线愉快地前进,遵循既定议程”(15),霍尔指导伯明翰中心引进了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诸多欧陆理论;伯明翰中心随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理论时代,先后经历了体现差异中的同一性的语言学转向、葛兰西转向、“后学”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显影过程亦可谓霍尔时代的文化研究理论化过程,其重要能指一方面是霍尔的以“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为代表的诸多著述,另一方面是直接联系着霍尔的一系列伯明翰中心集体成果,比如《论意识形态》(1978)、《治理危机:行凶抢劫、国家与法治》(1978)、《妇女发言:妇女从属地位面面观》(1978)、《工人阶级文化:历史与理论研究》(1979)、《亚文化:风格的意义》(1979)、《文化、媒体、语言:文化研究工作论文,1972—1979》(1980)、《帝国还击: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种族与种族主义》(1982)、《创造历史:历史书写研究与政治》(1982),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伯明翰中心日益体制化、文化研究日益学科化的霍尔时代(以及后霍尔时代),伯明翰中心不但通过师承关系的传递团结了一些人,开展了诸多集体性智识项目,而且将其考察的维度从原有的阶级拓展到了性别和种族,呈现出霍尔所谓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激进异质性”。作为霍加特时代与霍尔时代及后霍尔时代之间的一种别样的“非连续性”,“激进异质性”表征的是伯明翰中心的一种学术传统,伯明翰中心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一种学术传统,让伯明翰中心显在地有别于其他类似机构的一种学术传统。所以,伯明翰中心从霍加特时代进入霍尔时代及后霍尔时代的过程,既是它从经验主义时代进入理论时代的过程,也可谓正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显影抑或浮现的过程,虽然霍尔曾经强调:“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派。”(16)倘若认为霍加特时代的伯明翰中心尚与传统的英国文学研究有着某种纠缠,霍尔时代及后霍尔时代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则已然超越以马修·阿诺德、F.R.利维斯为代表的保守或传统精英主义思想对后工业、后现代文化的怀旧式简单抗拒,走出了对传统高雅文化的简单颂扬,而且通过挪用结构主义等“新”理论解读新的社会现实,同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建构接合理论 霍尔的“不作保证”的另一个著名实践,是他通过对还原论的重新理论化,发现了曾经被还原论遮蔽、现在急需填补的理论空间。“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初,文化理论家的工作,尤其是斯图亚特·霍尔的工作,通过关注还原论概念令其费解之物打开了那个空间。好像出现了一个理论空白,一个勉力被填补的空间。”(17)霍尔不但为此设计了“生产模型”、“关系组合”等概念,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在葛兰西转向中发现了后马克思主义者恩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ou),引导伯明翰中心走向了接合理论。一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所告诉我们的,拉克劳认为,还原论,尤其是阶级还原论,已然同时在理论与政治上失效,无力解释阶级话语中的实际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发展出一种消除阶级还原论的最后残迹的意识形态实践的严格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18)于是,基于批判性地吸收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意识形态理论、有效地挪用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拉克劳提出了自己的接合系谱学:接合概念深植于欧洲哲学传统,但需要重构,一如他对柏拉图洞穴隐喻的解读:“常识话语,即意见呈现为一个误导性接合的体系,概念于其间似乎并非由内在逻辑关系所联系,而是仅仅被习俗与意见已然在它们之间确立的内涵的或引发共鸣的联系绑在一起。”(19)接合即是“概念之间的联系”。洞穴隐喻意在“解接合”(disarticulate)(误导性的)联系,“再接合”(re-articulate)它们真实的(必然的)联系,即是说,摆脱意见走向知识的过程即是切断原有的接合重建真正接合的过程;从“解接合”到“再接合”的双重运动联系着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范式。作为一种“重构”,拉克劳把这一范式修订如下:“第一,并不是每一个概念都与其他概念有必然性联系,仅仅从一种关系出发构建一个体系的总体性是不可能的……第二,不同的概念结构间不可能建立必然的关系,而只能构造出接合的可能性条件。第三,任何对具体的接近都以更复杂的概念接合为前提条件,而不仅仅是对简单的概念全体逻辑特性的揭示。”(20)所以,对任何具体情势或现象的分析都必须探究复杂的、多重的、理论上抽象的非必然性联系;一如拉克劳对支配阶级的霸权行使过程的分析所证明的,获得支配地位的阶级总能将非阶级矛盾的话语接合进自己的话语,因而总能吸纳从属阶级的话语内容。即是说,虽然没有任何话语有着一种本质性的阶级内涵,但话语中的意义总是在内涵上联系着不同的阶级利益与特征。就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而言,其内涵可以由革命性的反抗、对剥削阶级的仇恨组成,但也可能接合进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享受与革命热情的消退。(21) 不难发现,拉克劳的接合概念体现的是一种非还原论或本质论的阶级观,对实践与意识形态元素之非必然对应关系的主张,对作为冲突性意识形态结构的常识的批评,以及对霸权乃一种话语接合过程的坚持。正因如此,拉克劳成为了霍尔形塑接合理论时的首选资源:“接合理论是由恩尼斯特·拉克劳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其间他的观点是,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内涵并无必然的归属性……他用接合概念来与夹杂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中的必然论和还原论逻辑决裂。”(22)“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内涵并无必然的归属性”这一观点所暗示的,是意识形态要素并非一定具有阶级属性,其中的一些要素是非阶级的或中性的;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并非是由主体在生产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给定的,而是取决于意识形态各要素的连接方式——接合。即是说,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非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为意识形态要素的接合所建构的;接合在打造由多种要素组成的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同时,赋予意识形态“自治”。这无疑是拉克劳对马克思主义还原论的一种颠覆,而霍尔正是从这里受到了启发,一如他在讨论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时所言:意识形态“不可能是一种历史或政治力量被简单地还原为一个一致的阶级……唯有通过作为一致化的意识形态之内的集体主题的形构,它才成为一种一致的力量。直到它开始拥有某种解释一种共享的集体情势的概念形式,它才变为一个阶级或一种一致的社会力量。即使到这时,决定其地位与同一性的东西也绝非我们可以还原为我们过去常常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所意指的术语”。(23) 然而,霍尔对拉克劳的观点也不乏拒绝,尤其是在拉克劳从意识形态批评滑向单纯的话语境地的时候。在霍尔看来,按照“实践皆话语”的逻辑,难免会出现“将所有实践概念化为仅仅是话语而已,将所有历史行动者概念化为话语建构的主体性,大谈位置性却绝口不提社会实际位置,仅仅看到具体个体被询唤到不同主体位置性的方式”。(24)在这里,霍尔看到了自己和拉克劳的分歧——他认为“世界、社会实践是语言,而我想说社会像语言一样运作”,直言不讳地对拉克劳提出了批评:“我想说,彻底的话语立场是一种向上的还原论,而不像经济主义那样是向下的还原论。情况似乎是,在反对一种幼稚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X像Y一样运作的比喻被化约为了X=Y。”(25)当然,就对“实践皆话语”的批评而言,拉克劳并非霍尔仅有的批评对象;阿尔都塞同样遭到了他一针见血的批评。讨论意义、表征与实践的关系时,霍尔虽然承认一切实践及其意义密切联系着其表征与话语,但拒绝把一切实践还原或化约为话语:“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一切实践都带有意识形态的痕迹,或者被意识形态铭写,一切实践便仅仅是意识形态。那些以制造意识形态表征为主要目标的实践是有特殊性的。”(26) 在他对还原论、“实践皆话语”等观点的批评中,在他对实践特殊性的强调中,霍尔开始了其接合理论形塑之旅,见诸他的不同论述。在发表于1980年的《支配结构中的种族、接合与社会》一文中,霍尔第一次对作为一个概念的接合做出了阐释:“这种联合或接合所形成的同一性始终、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一个万物于其间一如通过相似性那样通过差异性,彼此相关的结构。”(27)霍尔在此间对接合概念的阐释标志着他的接合理论的萌芽,但仅仅指出了接合理论的部分内涵。他对接合概念的系统理论化与阐释主要发生在数年之后。在发表于1985年的《意指、表征、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论争》一文中,霍尔指出:“我用‘接合’一词来表示一种连接或者联系,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未必是给定的……而是要求出现在特定存在情势之中。它必须通过特定过程积极地维系,也并非是永恒的,而是必须被不断更新;它在某些环境下可能消失或瓦解,导致旧的联系被消解、新的联系——再接合——被打造。”(28)很显然,霍尔已然在此间提升了对接合概念的理论化程度,但他对之最详尽的阐释,却见诸这一年晚些时候的一次访谈:“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让两个不同的元素统一起来。环扣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必需的。你不得不追问,在什么情势下可以打造或产生出一种关联?因此,一种话语的所谓‘同一性’实际上是不同的、独特的元素接合,这些元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接合,因为它们丝毫没有必然的‘归属性’。至关重要的‘同一性’是被接合的话语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一种环扣,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但不一定必须借助被接合的话语与社会力量连接起来。因此,接合理论既是理解意识形态元素何以在一定情势下逐渐连接在某一话语之内的方式,也是追问它们何以在某一关键时刻与特定政治主体接合或不接合的方式。”(29) 此间的霍尔不但向我们阐释了接合概念的丰富内涵,比如接合、解接合、再接合、意识形态、要素、一定条件、遇合、差异性、同一性,等等,而且以“接合—解接合—再接合”的动态发展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接合的非必然性、非持久性、暂时性、动态性、未完成性等特征,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促成了接合概念的理论地位,即著名的“接合理论”。当然,霍尔形塑接合理论的成功并非仅仅在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传统、对还原论与本质论的持续批评,同时也联系着霍尔对“关键时刻”的把握。霍尔勉力建构接合理论可谓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关乎撒切尔夫人当政以降已然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英国社会文化现实对理论阐释的渴求。撒切尔夫人的英国福利制度改革显然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为何却赢得了后者的认同与支持?霍尔发现,撒切尔夫人成功的秘诀在于一种独特形式的领导权——“威权平民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它强调“对一种基于法律、秩序和家庭价值的新的平民道德的需求”,并且“通过将受欢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界定为包含所有人,它也变成了一种道德力量”。(30)撒切尔夫人时常与工人阶级一起抱怨官僚政府,不断重复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为富人服务,而且也为普通人服务,即普通人同样能够成为股东与投资人。但一如其如下修辞所证明的,“在公司里不要跟我谈什么‘他们’和‘我们’”,“大家在公司里都是‘我们’。你活下去就是公司活下去,你成功就是公司成功——大家齐心。未来在于合作而不是对抗”(31),在与左派的斗争中,撒切尔夫人仅仅旨在借助赢得大众的认同重建政权。通过这样的一种威权平民主义实践,“其中平民被威权化即综合和超越,而威权被平民化即被普遍化、道德化、常识化和自然化”,威权平民主义便成为了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性意识形态的实践,不再关乎经济的枯荣。(32) 面对撒切尔主义的胜利、右翼势力的复兴、广泛的保守政策的回归、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衰退、声誉日隆的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颠覆,尤其是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的质疑,霍尔主张左派从撒切尔主义的胜利中吸取教训,放弃过时的还原论、本质论。为此,霍尔“解接合”了撒切尔夫人所喜欢的一些概念,“再接合”了作为一个概念的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一,意识形态不是专属于或天然地联系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第二,……意识形态计划……可以发挥出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可以改变社会……第三,这种改变的发生并不必然地受制于或紧密地相关于经济力量。”(33) 霍尔的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56~1964年为第一个阶段,此时的霍尔深受雷蒙·威廉斯、霍加特及E.P.汤普森的影响;1964~1978年为第二阶段,此时的霍尔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及各种符号学理论;1979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此时的霍尔主要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活跃在多个理论前沿。从这里可以看出,霍尔并不生产理论,而是积极运用理论,以及为此像“喜鹊”那样,“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么东西都抓到自己的窝里”(34),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霍尔始终在勉力保持自己作为一位“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挪用潮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理论?我们是否可以始于霍尔研究?毕竟一如评论家所言:“霍尔是伯明翰70年代的顶尖人物,他的名声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书,而是在于文章和文集的序言,它们交织在热火朝天的争论中间,引导伯明翰工程走过了五花八门的理论地雷阵。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发现这类文章鼓舞人心,富有挑战性,在多姿多彩的伯明翰著述中,是我们的阅读首选。”(35) 毋庸置疑,霍尔的离世意味着霍尔的时代已然结束,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一个霍尔研究的时代即将来临,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任何人为英国思想左派著书立说,都始于四处寻找某位能够连接其诸多倾向与阶段的代表性虚构人物,发现自己在不由自主地重塑斯图亚特·霍尔”。(36)联系到“倘若有人与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特别研究领域的发展最相等同,那这个人就是斯图亚特·霍尔”(37),我们有理由相信,霍尔研究将会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 注释: ①Stuart 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p.25-46.原文见:“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Betty Matthews,ed.,Marx:A Hundred Years on,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83. ②斯图亚特·霍尔:《第一代新左派的生平与时代》,王晓曼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11期,第86页。 ③斯图亚特·霍尔:《第一代新左派的生平与时代》,第87页。 ④Stuart Hall,“The First New Left”,in Robin Archer et al.(eds.),Out of Apathy,London:Verso,1989:p.13. ⑤陈光兴:《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思想文综》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⑥Stuart Hall,“The First New Left”,in Robin Archer et al.(eds.),Out of Apathy,pp.14-5. ⑦Stuart Hall,“The First New Left”,in Robin Archer et al.(eds.),Out of Apathy,p.15,p.22. ⑧Editorial of New Left Review,no.1. ⑨Stuart Hall,“The First New Left”,in Robin Archer et al.(eds.),Out of Apathy,p.31. ⑩Editorial of New Left Review,no.1. (11)Lin Chun,The British New Lef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3:p.16. (12)斯图亚特·霍尔:《第一代新左派的生平与时代》,第90页。 (13)Graeme Turner,British Culti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2003:p.64. (14)Helen Davis,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London:Sage,2004:p.1. (15)Stuart 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27,p.26. (16)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149. (17)Jennifer Daryl Slack,“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117. (18)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LB,1977:p.142. (19)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p.7. (20)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p.10. (21)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p.161. (22)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142. (23)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p.144. (24)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p.146. (25)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p.146. (26)Stuart Hall,“Signification,Representation,Ideology: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vol.2,no.2,1985:p.103. (27)Stuart Hall,“Race,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Sociological Theories:Race and Colonialism,Paris:UNESCO,1980:p.325. (28)Stuart Hall,“Signification,Representation,Ideology: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vol.2,no.2,1985:pp.113-4. (29)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p.141-2. (30)Angela McRobbie,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p.24. (31)Stuart Hall,The Hard Road to Renewal: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8:p.49. (32)金惠敏:《霍尔的文章,麦克罗比的眼睛——霍尔文化研究三大主题的评议》,《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第233页。 (33)Angela McRobbie,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p.26. (34)金惠敏:《积极受众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87页。 (35)约翰·道克尔:《一种正统观念的开花》,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6页。 (36)Terry Eagleton,“The Hippest”,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18,no.5,7 march,1996:pp.3-5. (37)Chris Barker,Th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4,p.82.标签:英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霍尔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还原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