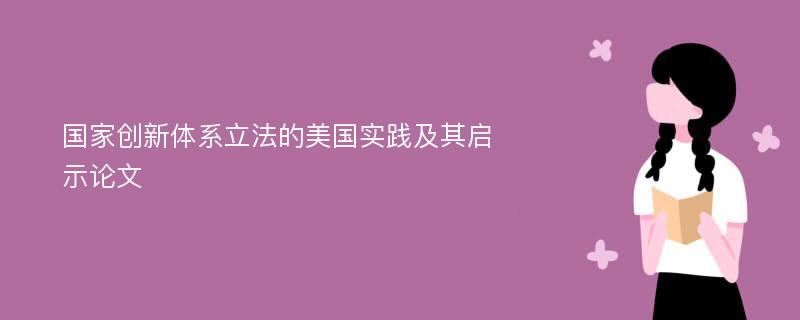
国家创新体系立法的美国实践及其启示
周海源
(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1620)
摘 要 :美国在国家创新体系方面制定了《全国合作研究与生产法》《美国竞争再授权法案》等多部法律。2017年6月1日由美国总统签署生效的《创新与竞争力法案》是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立法的集大成者,该法案在基础研究、行政减负、STEM教育、公民科学、成果转化等方面创设了一系列新制度。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立法应借鉴美国经验,遵循以法治引领创新体系建设的立法思路,构建以“研发-转化”保障为核心,覆盖人才、金融、环境等内容的综合性法律体系,强化政府激励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创新引领和保障作用。
关键词 :国家创新体系;创新与竞争力法案;立法思路;法律体系;立法内容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最终需要回到法治轨道内,以立法形式搭建其基本构架,这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必然要求。当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我国的科技法体系呈现一定的滞后性,1996制定2007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和2015年修正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都无法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创新资源的聚集和辐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区域协同创新、科技金融融合等提供充足保障。其缘由在于上述立法没有涉及创新的全部要素和过程,未形成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法律框架。而在科技与法治建设方面同时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则在国家创新体系立法方面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立法工作的推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立法历程
所谓国家创新体系,即是指“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1]”。国家创新体系建构的核心在于搭建保障创新要素在创新主体之间交换的网络[2]。据此,国家创新体系立法即是指着力于通过创新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建设有效揉合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创新资源在创新主体间有效流动的相关立法。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立法的核心在于其体系性思维,即融合已有的科创激励制度和措施,将所有创新资源统一于同一系统当中,其在内容与措施上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是实施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例如,2007年《美国竞争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2017年《创新与竞争力法案》也强化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其二是着力于促进创新主体与创新要素的高度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任务在于促进设施、经费、成果等创新资源在企业、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创新行为主体间的流动。例如,2010年《美国竞争再授权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通过技术创新项目帮助美国企业、高校和其他机构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研究,这项措施旨在强化创新主体间的联系,促进创新资源在创新主体间的流通。其三是从创新流程保障延伸至创新环境保障。创新流程大致包括科研主体的设立与运行、经费投入、研发、转化等过程,国家创新体系立法则超出了对上述创新流程的保障,延伸至对创新环境进行保障,如2017年《创新与竞争力法案》在融资、法治环境、公民科学等方面设置了诸多保障措施,强化对创新环境的保障。
2.2.1.3 AML患者首次CR 后12个月 此阶段35份标本,MRD阳性5例,复发2例,分别在MRD阳性后1、10个月复发;MRD阴性30例,复发7例,分别在MRD阴性后1、3、4、5、6、12、15个月复发。两组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86)。MRD阳性组及阴性组的中位RFS分别为5.0个月(4~10个月)、25.0个月(1~35个月),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
需要说明的是,相较于传统科技立法而言,国家创新体系立法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已有创新法治保障的原则、内容和措施的升华和融合。也就是说,在美国的法制体系尤其是科技法体系中,“国家创新体系立法”应作以下定位:一方面,国家创新体系立法本质上属于科技法体系的范畴,其同样需要围绕科研主体、科研经费、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等内容展开,也需要借助项目设置、经费扶持、校企联合等措施促进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国家创新体系立法又秉持体系化的立法思路,既要将企业、研究机构、政府部门、教育培训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融合于同一系统之中,使科技资源通过创新体系在科技创新的全部过程中自由流程;同时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法律制度不仅面向研发、转化等创新过程,还需面向中介、人才、金融等外围要素,将其融合进创新体系当中。因此,国家创新体系立法应是美国科技立法的最新发展阶段,是已有科技法机制和措施的体系化建构和升华。遵循这一思路,美国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制定了多部法律。
在文化从属于语言教学的现状下,文化教学的内容不够深入,也不丰富。因此,丰富文化教学的内容也是满足跨文化交际需要的重要部分。
其一是1993年制定的《全国合作研究与生产法》。《全国合作研究与生产法》实际上是1984年《国家研究合作法》的修正版。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产业组织经济学学派——芝加哥学派认为美国源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反托拉斯政策阻碍了技术创新。在此种思潮影响下,美国政府制定的《国家研究合作法》明确规定对企业合作从事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活动适用合理原则而非本身违法原则,即企业间的技术合作有合理理由,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就算合作行为使企业所占份额达到可能形成垄断的状态,也不认为其构成垄断。《全国合作研究与生产法》则对《国家研究合作法》进行了补充,其明确了合作的范围,具体包括理论研究和实验、工程设计和开发测试、技术应用的实验性生产和测试、产品生产、研发信息交换等[3]。
该法案首先是肯定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创新团队项目(I-Corps)在成果转化方面的作用。I-Corps是由科研机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建立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其任务在于确定和探索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的创新能力和商业潜力并提供创业补助和商业化的教育、培训和指导。该法案提出,I-Corps提供的教育和培训应当向其他基金会资助的研究人员开放。同时,该法案还鼓励I-Corps项目实施扩张,规定项目主管应当鼓励发展和扩大I-Corps和其他侧重于职业发展的培训项目;寻求与其他联邦科学机构签订协议以确保由该机构资助的研究人员、学生和机构有资格参加I-Corps项目;协助该机构设计和实施与I-Corps项目类似的项目等。
其三是2007年《美国竞争法案》和2010年《美国竞争再授权法案》。《美国竞争法案》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持美国在基础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是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在基础研究方面,该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国家技术与标准局执行新的“技术创新计划”[5],该计划的主要内容为,在国家重点领域实施基础科学研究资助,同时增加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科研经费预算;在人才培养方面,则实施了数项新的人才培养计划,或扩大原有计划项目的覆盖范围,包括罗伯特·诺伊斯教师奖学金计划、国家实验室举办的暑期学院的培训和教育计划等。2010年《美国竞争再授权法案》则是2007年《美国竞争法案》的修正版,其要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通过技术创新项目帮助美国企业、高校和其他机构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研究,并规定联邦政府在未来10年内给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财政预算金额应增长一倍[6]。
其五是2011年《发明法案》和2014年《创新法案》。《发明法案》确立了发明人先申请制的专利取得制度;扩大了专利受让人、第三方的权利范围,如赋予专利受让人申请专利的权利;同时调整了专利申请条件,禁止人体器官和税务策略申请专利。2014年《创新法案》主要对专利诉讼规则进行修订。在该法案出台之前,美国创新企业饱受“专利蟑螂”之害。“专利蟑螂”不从事科研和生产经营活动,主要通过诉讼方式向使用可能与其专利相关的企业寻找侵权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2014年《创新法案》增加了原告在诉讼中的义务,如原告在诉讼中需要提供诸多“必要细节”,包括受到侵害的专利权、侵权工具的具体情况等,同时规定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7],据此扼制专利领域的恶意诉讼。
其四是2009年《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是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出台的立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减税与政府投资促进就业,并以科技创新引领关键产业的发展,因此该法案实际上是一项总额为7870亿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包括对关键领域的科研活动予以巨额资金扶助。该法案涉及科学研究的支出有两部分,一是712亿美元对健康、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预算内支出,主要用于医疗投入、医疗技术投入以及教育科研投入;二是507亿美元能源与水资源发展的预算内支出,用以支持绿色能源产业的研发、成果转化等活动。
二、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立法的最新法案
(一)立法背景
《创新与竞争力法案》的制定源于美国对其在科技领域内的竞争力下降的担忧。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创新引领能力面临巨大压力,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是在科研投入方面,美国科研经费支出占全世界科研经费支出比例不断下降。近年来,美国科研经费投入额虽有所上升,于2013年达到4570亿美元,但其在全世界科研经费总量中所占比例从2001年的37%下降到2013年的27%;同期中国占比从2.2%上升到20%,达到了3370亿美元。其二是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存在障碍。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美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死亡峡谷”,表现为美国缺乏将其原创性研究成果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的意识,产业、政府和学界在成果转化和创新激励方面的合作有待深化。其三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方面,美国学生已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学生。在2015年,美国仅有38%的高中毕业生具备接受大学培训计划的能力,能够接受大学程度的数学教育的学生比例则为42%。与此同时,从2012-2022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内的需求人数预计增长13%,接受过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工人已不能满足美国产业发展的要求,预计2012-2022年,软件和应用程序方面的人员缺口高达20万;移动应用程序、数据科学和制造业等领域也存在较为严重的人才短缺[注] 详见美国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报告: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ternet: Trade secrets: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market acccess inforeign markets. 。
(二)主要内容
美国《创新与竞争力法案》于2016年12月10日由国会正式通过,2017年6月1日获得美国总统签署,正式生效。该法案共有6章50条,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创新体系建设改善美国科研环境并提升其竞争力。
3.人才培养
1.创新投入
基础研究的强化是该法案最为重要的内容,在该法案的50个条文中,基础研究一章共有17个条文,主要内容有:一是将美国科学基金会提升资助透明度和明确使用资金义务的措施予以法典化,更新了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实验性项目计划以激励竞争性研究。如该法案第102节即规定,基金会应致力于提高资助的透明度和明确问责制,基金会主任应定期发布和更新适用于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其他基金会绩效评估参与者的政策,并通过价值评估程序强调科学研究产出的透明度和责任;每一项受资助的项目都应当证明其支出是合理的。二是在科研投入分配方面,该法案注意到科研经费流向的地区不平衡,即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仍然高度集中,有28个州和司法辖区仅获得了全国科学基金会研究经费的12%。针对这一问题,《创新与竞争力法案》提出,主管部门应协调EPSCoR项目和联邦实施的其他类似EPSCoR的项目间关系,据此提高由联邦提供的科研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增强EPSCoR资助的研究人员与其他机构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向青年研究人员提供使用联邦设施的机会。法案同时要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就网络安全的特定领域展开研究;该法案还明确了部分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有义务提出建议以改善实验室的科研规划。
5.成果转化
该法案第201节指出,研究人员大致需要花费42%的时间从事申请拨款或撰写满足要求的报告等行政任务。因此,该法案在第201节(d)款规定,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主任应配合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建立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其任务是减少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的行政负担,同时通过提升联邦政府资助活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保护公共利益;该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包括:定期审查适用于联邦资助的研究人员的行政法规,梳理并提交可能被淘汰、简化或改进的规章或流程;提出减轻高等教育机构监管负担的建议;对联邦科学机构的拨款申请文件进行全面审查,设计简便、统一的文书格式供研究机构使用。
解析:0.1mol金属钠与水完全反应,产生0.05molH2,同时产生0.1molNaOH,铝箔又与NaOH反应也产生H2,所以产生的H2大于0.05mol,本题答案应为C。
相较而言,中国不管是在科学技术层面、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层面还是在科技法治建设方面都处于追赶期。我国科技工作的推进,则不仅需要学习美国技术和制度,也需要借鉴制度背后先进的立法思路。实际上,李克强总理于2017年8月23日在科技部考察时也提出,要切实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最终要落实到法治保障上,一方面,创新体系建设涉及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这需要改革部门获得法律的授权,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另一方面,建设的成果也需要以法律的形式体现,这也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题中之义。“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之双轮,是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两翼。法治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路径[9]。”因此,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背景下,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双轮驱动应当以法治手段为保障和促进力量,通过对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科技法律制度的完善为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创新提供指引和保障。
针对软件、应用程序、数据科学和制造业等领域存在巨大人才缺口的问题,美国《创新与竞争力法案》重申了STEM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系列改革措施:一是改革罗伯特·诺伊斯教师奖学金计划,要求项目主管提高留在STEM教学行业的人员获得奖励的比例,建立更为完备的信息收集系统以收集、跟踪和分析接受奖学金的个人的职业走向;开展试点项目提升留任STEM教师的比例。二是吸收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法案》的内容,规定基金会主管、教育部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局长应当共同建立一个咨询小组,负责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的STEM教育委员会提出有关STEM教育方面的建议。三是增加了STEM教育委员会的职能,除原法案规定的协调管理STEM教育工作职能外,新增了协调STEM教育咨询小组工作的职能。同时发展了STEM学徒制,优先为企业尤其是小企业提供学徒。
4.公民科学
《创新与竞争力法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科技创新:一是奖励项目。该法案规定,竞争奖项应当在可公开访问的政府网站上发布公告,公告内容包括主题、参选的资格规则、注册程序、奖励形式和额度等,同时明确了参评项目的产权归属,即未经参赛者书面同意,联邦政府不得对参评奖励项目所开发的知识产权获得利益。二是民众参与。该法案规定,每个联邦科学机构的负责人,或者多个联邦科学机构的负责人,可以利用众包和公民科学来开展项目,以完成联邦科学机构的任务或联邦科学机构的联合任务。同时,为了鼓励公众参与,该法案还规定,联邦科学机构应当在适当情况下,将公民科学项目的数据提供给公众使用。
2.行政减负
分油机仿真面板的系统架构见图2,由上位机PC监视器和CAN总线系统上挂接的多个分油机分布式仿真节点组成,因为PC监视器本身不支持CAN通信,通过32IO8AO通用板卡将数据流转发并经以太网与上位机数据通信。
其二是2000年的《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的立法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美国国会认为,《拜杜法案》的出台确实促进了成果转化,但联邦科研机构科技成果沉冗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该法案的立法目的在于促进联邦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的进一步转化,并强化联邦科研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为达成这一目的,该法案授予联邦机构对其所有的专利实施许可的权限,同时明确了联邦实验室报告成果转化的义务[4]。
三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立法对中国的启示
(一)以法治引领创新体系建设的立法思路
美国《创新与竞争力法案》的制定体现了以法治引领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路。纵观美国科技发展的历程,创新体系与科技创新具有紧密不可分的关系,科技创新往往需要以创新体系建设为前提,如其《拜杜法案》改革了职务科技成果的归属和管理关系,带来了美国科研成果的爆发式增长[8]。当然,不管是《拜杜法案》抑或是《创新与竞争力法案》的制定也都体现了体系建设与法治创新统一的思维。具体而言,《创新与竞争力法案》实际上也包含了系列创新体系的建设和改革举措,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该法案第一章规定的基础研究投入和第二章所规定的行政减负措施。除此之外,该法案还在EPSCoR项目、STEM教育、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而这些改革以立法的方式推进,这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对科技法治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以立法形式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也能够使改革和建设的成果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化,最终实现体制改革与法律创新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在肯定美国在科技领域具有悬殊领先优势的同时,表达了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科技发展的担忧,美国国会据此迅速制定了该法案。该法案在美国国会两院表决中均无一反对票,表明在阶层、族群分立、两院和两党牵掣颇多的美国,以法治建设推动和保障创新体系建设依然获得了高度的共识。
这是本节复习课的最后一道例题,处理完问(1)距下课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之后对问(2),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展示、交流.学生自主提出5个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又有4个新问题被提出.在解决的过程中,教师又引领学生深入研究.前两个问题解决后,发现最值取得时,四边形PAOB恰是正方形,顺势教师提出可以研究四边形PAOB何时为正方形;∠APB的最大值求出是90°时,教师又提出若∠APB=60°,那么点P的横坐标的范围如何等等,问题不断衍生,探究永不停止,从而让思维的教学更具穿透力、延展力.
(二)全面性的创新保障法律体系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立法尤其是其《创新与竞争力法案》的制定,充分展现了其在国家创新体系立法方面所形成的以“研发——转化”为核心,辐射人才、金融、环境等要素的全面性创新保障法律体系。
一方面,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立法以研发和转化保障为核心,《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技术创新法》和《联邦技术转让法》等,构成了美国科技法的核心[10]。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立法也超越了研发和成果转化保障的局限,而将科技立法延伸至人才、金融、环境等创新要素,形成了全面性的创新保障立法。如美国的《创新与竞争力法案》并不限于对已有的研发与成果转化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其设定了诸多的利益诱导性条款,也明确了美国科学基金会等主体在促进科技资源均衡分配、发展STEM教育、调动公民参与等方面的职责和制度,涉及人才、金融、环境等创新要素,总体上属于综合保障型的立法。此种特征在《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美国竞争再授权法案》《全国合作研究与生产法》等立法中也得以充分展现。实际上,法国制定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法》和以色列制定的《产业创新促进法》同样涉及对上文所述的多种创新要素的综合保障。
本文结合仿真工具Matlab,实现高阶累积量算法识别6种通信调制信号。图2为识别2ASK、4ASK、2FSK、4FSK、2PSK、4PSK信号的识别率仿真图。图中每一种调制信号识别率曲线都用不同形状表示。
4)省级基础测绘的DEM数据是正射影像纠正和多尺度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生产的基础数据,主要用于遥感影像的正射纠正处理、精细化DEM生产。
就美国而言,其面临科研投入占比下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畅、技术人才队伍后备不足等问题,研发与转化保障立法如《国家科学基金会法》《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重点法》等的修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并无助益,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制定《创新与竞争力法案》的原因。就我国而言,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面临创新主体、技术、人才、资本、环境等多方面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全面保障问题,现有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主要面向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可能无法全面涉及和综合考量上述问题。因此,我国有必要参照美国经验,结合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实际需要,制定体系化的综合性立法。实际上,在此方面,地方层面已进行有益尝试,湖北、广东和辽宁三省已制定自主创新促进条例,上海市也紧锣密鼓地进行《上海市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的立法论证工作,形成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草案)则设置了“创新主体建设”“区域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创业环境建设”“法治环境建设”等章节,实现了对创新要素的全面保障和创新体系的全面规范,形成了以研发与成果转化为核心、涉及各项创新要素的综合性保障立法。在地方立法经验进一步成熟的基础上,国家层面即有必要针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面临的金融、人才等方面问题制定一部综合性激励型立法。
(三)突出政府激励的立法内容
美国在经济上崇尚自由主义,但在科技创新领域,其自由主义立场有所退缩,提倡政府强有力的激励,据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立法上也形成了政府激励为主线的内容体系。如《创新与竞争力法案》强化了政府的激励作用,其附带了2017-2018年度的预算案,议员Gardner和Peters还专门提出修改意见,将预算额度提升4%,国会最终通过了预算案及议员的修改意见。另外,在成果研发与转化的融合方面,该法案主要通过设立政府资助项目(I-Corps项目)的方式推动成果转化。在该法案制定前,密歇根大学等七所高校和机构是实施I-Corps项目的节点,法案则将该项目扩展到了其他联邦机构。而该法案的人才培养计划实际上也是政府扶持项目。据此,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11]。
就我国而言,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此项原则体现于科技创新当中,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对科技产业的投入与激励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高速发展及对美国形成的压力,应该说政府激励的作用功不可没。当然,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即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作用应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尤其是创新主体的成长、成果转化项目的开展等需要大量的资助支持,这就需要以强有力的政府扶持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背景下,政府激励更应当超越研发和成果转化投入的局限,一方面需要将其扶持的触手向人才、金融、园区等领域延伸,形成由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创新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进一步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调动银行、保险企业、风险投资企业、创客中心、孵化器等主体参与到创新保障和服务当中。
当然,与政府调控相对应的是调控权力与手段的合法性、规范性问题。就美国而言,其《创新与竞争力法案》一方面授予美国各级行政部门广泛的职权,另一方面也通过行政减负、反垄断规制的缓和等方式减少和规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就我国而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一方面面临授权问题,即各政府部门的推进性措施应有法律授权;另一方面也面临限权问题,即政府权力的行使应以尊重市场规律和科研规律为前提[12]。以上问题的核心实际上都触及了政府权力的规范化问题。以某市科委为例,其享有的84项职权高达36项职权无规章以上的法律依据,占比为42.9%。这就要求中国借鉴美国创新体系立法的精神,结合科技管理实践明确政府部门在制定和实施科技发展规划、评审与颁发科学技术奖项、引进和评价科创人才、实施科研项目扶持等方面的职权,并规定职权的行使程序和方式等,从而确保政府部门职权的配备更加符合科技行政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13]。
从机制上保证审计组长责权利相统一,把审计组长负责制逐步落到实处。不仅要赋予审计组长一定的用人权、分工权和检查复核权,还要建立审计组长奖惩制度、定期督导、考核评价机制,构建完善的审核把关体系,不断提高审计工作整体水平。此外,上级审计部门要关心、支持和信任审计组长的工作,及时进行指导管理、排忧解难,对审计组长既不要事事干预,也不要撒手不管,关键时刻及时提醒,维护审计组长的威信,为审计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参考文献 :
[1] Chris Freeman.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9 (1): 5-24.
[2] 沈桂龙.美国创新体系:基本框架、主要特征与经验启示[J].社会科学,2015(8): 3-13.
[3] 赵 歆.科技政策视角下的竞争与创新——美国科技政策立法对合作创新的反托拉斯规制[J].科技管理研究,2012(5): 10-13.
[4] 黄武双.美国技术创新与技术转让激励政策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275-276.
[5] 刘 艳.论政府主导下的美国科技创新体系[J].前沿,2015(5): 18-22.
[6] 赵文慧, 聂爱轩.美国应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标准化战略与组织转型方法[J].中国标准化,2016(4): 60-67.
[7] 易继明.美国《创新法案》评析[J].环球法律评论, 2014(4): 146-166.
[8] 单美玉, 李彩霞, 王戴尊, 等.《拜杜法案》对美国大学基础研究的影响[J].技术与创新管理, 2014(6): 576-579.
[9] 石佑启, 刘茂盛.论创新驱动发展的法治支撑[J].学术研究, 2016(1): 51-58.
[10] 董 昕.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区域经济评论, 2016(6): 38-45.
[11] 刘 艳.论政府主导下的美国科技创新体系[J].前沿, 2015(5): 18-22.
[12] 周海源.从政府职责到科研权利:科技法虚置化的成因与出路[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 68-75.
[13] 周海源.从照搬到转化:地方科技进步条例修改的上海经验[J].科技管理研究,2017(13): 42-46.
American Practice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Legisl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ZHOU Hai-yuan
(Research Center on Rule -by -Law Strategy in China ,ECUPL ,Shanghai 201620,China )
Abstract : The US has formulated the multiple laws such as National Cooperation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Law and the US Competition Reauthorization Act in terms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June 1, 2017, is a master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legislation, which was created a series of new systems in basic research, administrative burden reduction, STEM education, citizen sc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sults. China’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legislation should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 the legislative ideas of leading the system innovation with the rule of law, and build a comprehensive legal system that covers the cor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transformation” and covers talents, finance, environment, etc., and strengthen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government. encourage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legislative thinking; legal system; legislative content
收稿日期 :2018-08-21
修回日期: 2019-01-28
基金项目 :上海市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上海策略”(18692103700)。
作者简介 :周海源(1985-),男,广西玉林人,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科技行政法。
中图分类号 :D93/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19)03-0013-07
(本文责编 :辛 城 )
标签:国家创新体系论文; 创新与竞争力法案论文; 立法思路论文; 法律体系论文; 立法内容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