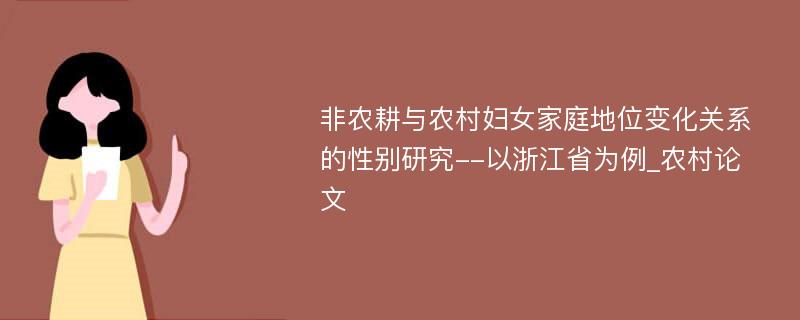
非农化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性别考察——以浙江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为例论文,化与论文,非农论文,农村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般认为,与非农化相伴随,中国农村妇女家庭地位是不断提高的。但将这一地位分解成农村妇女作为个体在家庭内权益总格局中的地位、作为代际成员在家庭代际权益格局中的地位、作为配偶在婚姻权益格局中的地位这三个定位点,以非农化进程为背景,通过对非农化程度较高的浙江省农村的调查[①],我们发现,这一提高存在着定位点之间的不均衡性。而进一步引入男性相关数据比较的结果显示,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这一提高更多地是以家庭内总体利益的削减和上代(包括女性上代)地位的下移为实现途径的:且不说这一削减和对上代的蚕食实际上是一种两性合作(包括作为个体的合作和作为同侪下一代的合作),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无性别行为,并且男性在其中获利更多,事实上,就男性总体而言,他们为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而付出的代价是较小的。说得更透彻一点,无论是前三十余年还是近十几年,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实质上是女人作为家庭成员与男人一起瓜分了家庭共同体的“蛋糕”,作为下代与男人一起抢占了上代(包括女性上代)“阳光下的地盘”,而作为女性的女人其实并未从作为男性的男人的“汤锅”里“舀出”更多的“肉汤”。对此,人们往往是忽略的。
以本研究所获调查数据为基础的进一步论证如下。
二
在家庭权益格局中的地位上,1、就当家人而言,女性当家人近一两年的比例与五十年代相比有较大下降;与1985年前相比,微有上升。进一步分析当家人性别/代际的年代分层,可以看出女性当家人比例的下降主要在于家中辈份最高的女性作为当家人的减少(五十年代占18.6%,近一两年占11.17%),而男性比例有较大上升则主要在于家中第二代男性和第三代男性所占比例的上升(前者在五十年代占22.1%,近一两年占30.5%;后者在五十年代占0.3%,近一两年占15.1%)。减去从男性家中辈份最高者当家人减少中获得的比例,男性当家人增长的比例几乎等于家中辈份最高的女性作为当家人减少的比例,这极其典型地表明,在对于上代权益共同的蚕食中,男性下代的获利更多。
2、就家庭事务的分工而言,从家务操持者来看,四十余年来,传统的家务劳动完全由女性操持的局面已有较大改变(两性中谁有空谁干家务的家庭在五十年代为4.7%,在近一两年为20%)但女性作为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尚未发生质的变化:家务大部由女性干的家庭占50.3%,完全由女性干的家庭占26.7%。至于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四十余年来,传统的模式日趋模糊——无固定分工的,从44.1%增至63.9%。这表明,在家庭事务的分工方面,具体家务劳动中的性别隔离已极大地被打破了,但“女主内”的规则依然存在。
进一步从两性对家庭经济的支撑看,四十余年来,女性收入在家庭经济收入增长中的作用显然不断加强:与五十年代相比,女性中不支撑家庭经济者从34.2%降至6.5%,而收入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例在1/3、1/2至3/4以上者的比例分别上升了25.9、30.8、6.5个百分点,但相比之下,今天男性的收入仍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近一两年其收入占家庭总收入51%及以上的男性占男性总数的51.4%,女性占女性总数的12.3%,这表明养家仍更多地是属于男性的责任,“主外”仍更多地是男性的行为规范。而这恰恰不仅是家庭权利格局中男性得以高于女性的主要基础,亦是家庭资源配置中男女不平等的一个结果。
3、本研究的调查问卷设置了生育目的一问,而回答者(N=217)选择答案中在“传宗接代”(31.8%)、“养儿防老”(55.8%)上的强烈倾向明晰地表明男性权利与义务的强于女性——在一个仍以父系单系为主传嗣和以男性亲属反哺为赡养模式的社会中,无论是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显然更多地是属于男人的权利和义务。更发人深思的是“养儿防老”——儿子在赡养过程中作用的强大在1985年前的达到高峰后(83.1%)在近一两年中的回落(55.8%)。与1985年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和发展,九十年代以后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扩大及外出打工经商者速增相联系,我们可以看出小农经济——社会结构中,儿子对于农户的重要意义。
4、就家庭中的消费导向而言,四十余年中,家庭生活需求的比例持续下降:五十年代占98.6%,1985年前占84%,近一两年占72.8%;妻子的需求则呈削减中的增长态:五十年代占0.5%,1985年前占8%,在近一两年占5.7%。相比之下,丈夫和孩子的需求倒是线性增长的:前者五十年代无,1985年前占5.4%,近一两年占6.4%;后者五十年代占0.5%,1985年前占0.7%,近一两年占6.7%。于是,到了近一两年,妻子的消费地位在经历了四十年左右的略高于丈夫和较高于孩子后,终于降到了丈夫乃至孩子之后,居最末位。这又一次证实了本研究提出的女性地位提高是以家庭总体利益而不是男性利益的削减为途径,男人甚至在这一削减中获利更多的观点。
5、就闲暇活动而言,四十余年来女性中无空闲时间者的减少不多(从21.6%降至17.3%),而近一两年来,其闲暇活动大多也是在自己家中进行的,与在五十年代和1985年前大多为户外活动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与男性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男性的闲暇活动在近一两年也出现了户内化的倾向,但其仍有比女性更多的户外活动与社会交往。此外,在无闲暇时间者中,男性的比例直线大幅度下降,两性间的差距也是呈减少中的增长态:五十年代相差2.7个百分点,1985年前相差11.2个百分点,在近一两年相差6.7个百分点。这在表明了女性闲暇度小于男性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农户家庭生产功能的强化更多地给女性而不是男性带来的生活压力,以及近几年来非农化的深入在减轻这一压力中的作用。
6、就交往和支持网络看,首先,四十余年来女性的烦恼倾诉者中家中老人、父母的比例减少了,(前者从6.1%降至1.5%,后者从50%降至44%),而配偶有了很大的增长(从8.5%增至30.9%),孩子、兄弟姐妹、邻居有了较大增长(分别为7.6%、9.1%、5%),朋友、同事、村干部或单位领导略有增长(分别为2.2%、1%、2.9%)。这表明,配偶已取代了上代在农村女性人生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血缘的支持已更多地表现为下代和同辈的支持。不过,数据表明近一两年来,女性向配偶诉说烦恼的减少了(从35.1%降至30.9%),其减少比例更多地是进入对孩子的倾诉和对兄弟姐妹的倾诉中。这为我们从访谈中得知的由于近几年男性更多地外出做工经商,更多地固守家中的女性不得不转而向血缘网络中的孩子和兄弟姐妹寻求精神慰藉和支持的事实提供了数据依据。
其次,四十余年来作为女性日常交往最多者,家中人的比例较大减少(从57.5%降至40.7%);呈波浪型增长态的为亲戚、邻居和朋友;同事和村干部或单位领导则逐年有微弱的增长;女性日常困难求助者中,家中人的比例逐年减少(从32.6%降至12.4%);呈波浪型增长态的为亲戚、邻居和朋友;同事及村干部或单位领导的增减幅度不太大;遇到矛盾时的求助者中,家中人的比例在1985年前大幅度下降后(从36%降到9.4%)在近一两年又略有回升(10.3%);亲戚的比例在1985年前大幅度上升后,在近一两年仍保持相近的水平;邻居的比例略增,但在近一两年中却是下降的;朋友和同事的比例在1985年前下降后,在近一两年中又有所上升;村干部或单位领导的比例在1985年前大增,但在近一两年却有所下降。综而述之,四十余年来,亲戚和家中人作为女性交往和支持首选对象的身份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女性交往和支持网络仍更是亲属血缘型的。尽管,在近几年,这一内倾的血缘亲属网络已有所疏松和开放。
相比之下,尽管血缘亲情在男性交往和支持网络中也仍是强大的,但就其发展趋势来看,在四十余年,尤其是近一两年中,男性的交往和求助更多地是外倾的,朋友甚至已成为男性交往和求助的首选或次选对象——与女性相比,可以说友缘和业缘已相当程度地替代了血缘在男性交往和支持网络中发挥着作用。而从烦恼的倾诉对象看,姻缘对于男性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并甚于女性:四十余年来配偶在男性烦恼倾诉者中所占的比例呈直线上升(五十年代占9%,1985年占34.6%,近一两年占35.5%);在近一两年,作为首选对象亦比女性多出4.6个百分点。这表明,较之女性,男性从配偶处寻求精神慰藉的需求更强,其需求的实现也更多。由此,两性相比,如果说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和变化,男性的交往和支持网络已从单一的血缘亲属型向综合性的血缘——友缘——姻缘转化的话,那么,女性的交往和支持网络则更多地是从单一的血缘亲属型向综合型的血缘——姻缘转变:女性仍更多地处于“内”,交于“内”、主于“内”,更多地仍是“内人”。
在代际权益格局中的地位上,1、就婚姻决定权而言,女性个体权利的增长呈现出线性发展的特征。其中,以1985年为界,在此之前更多地是当家人意愿的削减(婚姻完全由当家人作主的五十年代占18.3%,1985年前占5.9%,近一两年无),在此之后是个体意愿的增长(婚姻为自己作主,征得当家人同意的五十年代占12.5%,1985年占33.2%,近一两年占72.2%;完全由自己作主的五十年代占2.5%,1985年前占5.9%,近一两年占8.3%)。而进一步与男性比较,虽然在当家人绝对权力的失落和当事人绝对权力的增长上两性有大致相近的变化曲线,但在半自主婚上,男性自我权力的增长却表现出强于女性的倾向:在“自己作主,征得当家人同意”上,1985年前与五十年代相比,男性比女性多增长4.3个百分点,1985年前与近一两年相比,男性比女性多增长8.5个百分点。因此,就总体而言,不能不说男性对于婚姻自主权的获得是更多的。
2、就自我收入支配权而言,四十余年来,与家长控制的减弱相对应(自我收入全部交给当家人的女性五十年代占89.3%,1985年前占61.2%,近一两年占47%),女性的这一权利逐年有较大增长,其中,绝对自我支配权的扩展更多地是在近十年中出现的(自我收入全部由自己支配的女性五十年代占7.9%,1985年前占15.7%,近一两年占28.3%)。与男性相比,其自我收入支配权的实现在四十余年中也是不断递增的,并且,拥有的绝对支配权更多。与五十年代相比,近一两年来收入全部由自己支配的男性的增长比例比女性多4.3个百分点。当然,分层来看,近十年中女性对于收入支配权的获得是比男性略多一些的。这表明,就整个非农化过程而言,在父权和家庭利益的减弱中,男性较之女性获益更多;随着非农化的深入,在某些方面已出现了有利于女性的转机。
3、就孩子对于家长的服从而言,四十余年来男孩/女孩之间的差异显然增大了(男孩更服从家长的五十年代占10.1%,1985年前占16.4%,近一两年占16.2%。女孩更服从家长的五十年代占25.6%,1985年前占29.6%,近一两年占32.7%)。女孩中的服从不仅增长比例更大,并且其增长是呈直线的。而进一步从孩子的服从者看,四十余年来,其对母亲的服从呈减少中的增长态(五十年代占30.4%,1985年前占42.9%,近一两年占36%);对父亲的服从一直在减弱(五十年代占42.3%,1985年前占37.1%,近一两年占34.6%);对家中老人的服从在经过了前三十余年间下降后(五十年代占8.3%,1985年前占1.8%),在近一两年又有所回升(2.6%);对老师的服从在近十几年有较大增长(五十年代占18.5%,1985年前占17.9%,近一两年占24.6%)。从比例分析看,服从父亲者和服从老人者减少的比例在前三十余年间大致是转移到了对母亲的服从上,这表明,女性作为母亲的权力的增强在前三十年年间基本上是以男性作为父亲的权力的减弱和上代(包括男性和女性)老人权力的减弱为途径的。但在近十几年中,对母亲服从的减少更多地转移到对老师的服从上表明,不仅父权不再进行向母权的移交,甚至由于年轻母亲(1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基本上为中青年者)们更多地投身社会劳动和社会工作,其母权也有较大幅度下降。通过此,我们看到了与非农化扩展相伴随的家庭对孩子管理教育功能的外移,以及更为深层次的家长权力(包括父权和母权)的被替代。
4、就受教育权而言,应该说四十余年来农村孩子的获得有了很大的增加。但与男孩相比,女孩子文化水平的提高却是不足的:不仅男孩的学历构成已由五十年代的小学——初中转型为近一两年的初中——高中,而女孩的学历构成仅是由文盲——小学转型为小学——初中,并且,四十余年来,男孩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增加了1.8个百分点,高中(中专)者增加了18.3个百分点,而在女孩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仅增加了0.4个百分点,高中(中专)者增加了16.9个百分点。可见,在高中(中专)及以上的发展中,女孩是不如男孩的。
5、就对孩子未来职业选择的注重而言,四十余年来,虽然无论是对男孩还是对女孩,表示无所谓的家长均增加了,但两性相比,不仅对女孩未来职业选择持无所谓态度的家长仍然更多(对男孩未来职业无所谓的家长五十年代占6.9%,1985年前占7.7%,近一两年占11.2%;对女孩未来职业无所谓的家长五十年代占10.7%,1985年前占12.4%,近一两年占16.2%),并且,其比例增长也更快。这一“望子成龙”高于“望女成凤”的事实不能不说是今天即使非农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农村家庭也仍存在某种传统的两性权益不平等格局的又一明证。
夫妻打闹及和解形式典型地反映农村家庭婚姻权益中的性别格局——就妇女而言,便是其作为妻子在婚姻中的地位。在本调查对象中,夫妻发生打闹时,总体上是夫打骂妻而非妻打骂夫的现象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和解形式看,丈夫的让步仍是主要的,且逐年增长,而妻子的让步在前三十余年中有了一定增长后,在近一两年又是下降趋势:在有夫妻打骂的家庭中,打骂后丈夫先让步的五十年代占47.7%,1985年前占45.3%,近一两年占49.4%;妻子先让步的在五十年代占1.5%,1985年前占8.4%,近一两年占4.9%。中国农村社会向有丈夫更多地虐妻和虐妻后更多地让步和解的传统,这无疑是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高女低性别权益格局的折射——丈夫以对妻子的暴力和一定限度的退让显示了自己作为男人的力量和气量。这一传统的至今犹明显存在表明,虽然作为妻子的女性的家庭潜在权力有所上升,但在总体上,夫权仍然是强盛的。
本研究对于浙江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化的性别考察实际上是以浙江省农村的非农化进程[②]为背景断代的,因此,上述所谓浙江省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即是与非农化进程相伴随的浙江省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变化。这一变化无疑是有利于妇女的生存与发展的,而它更多地是在近十年来得以扩展和深化的事实表明非农化扩张性动力在家庭传统性别利益格局变化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看,非农化在前三十余年主要是一种政治——经济变革的过程,在近十几年,主要是一种经济变革的过程。所以,就总体而言,四十余年来与非农化相伴随的农村家庭中传统性别权益格局的变化是经济加上政治力冲击和渗透的结果;而农村家庭中传统性别权益格局至今尚未本质性地实现男女平等的现状则不仅表明家庭中性别权益格局的构建和运行有着自己的规律,纯经济和政治的力量难以冲击和渗入至每一个层面,更提示我们,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消费品,即使是家庭中的男女平等也需要有更复杂的生产机制,仅仅依靠经济和政治的驱动和扩张是远远不够的。
三
从人力资源角度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时代:生殖力时代、体力时代、智能时代,由于推进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不同,在这三个时代,被社会依靠并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人力资源的载体也大相径庭。就性别而言,在生殖力时代,生殖力是人力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而女人更多地拥有或者说是被认为拥有生殖力,女人也就成为高居于另一性别——男人之上的“女神”。在体力时代,个体体力是人力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男人得以以更多地拥有强壮充沛尤其是能无间隔使用的个体体力取代女人,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自十八世纪末开始,随着蒸汽机的长鸣,人类进入了智能时代。在这一时代,个体智能成为人力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而正由于就整体而言,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无太大的强弱差距,性别在两性价值定位中的决定性意义也就减弱了。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各种机械和人工智能日益实施着对人类体力的替代,体力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再是绝对重要的,男性便再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向另一性别——女性“称雄”。这一由于智能对体力的蚕食和替代,男人在世界范围内遭到的历史性的失败,就是今天即使浙江的农村妇女也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大背景,就是今天即使浙江的农村妇女也受到了影响和作用的性别文化的转型。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中国四十余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非农化的最伟大之处是在解放生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智能时代引入了农村,播撒和催发了新的两性权益划分规则。
进一步看,体力在今天农村生活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换句话说,即使在非农化程度较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所展开的浙江农村,个体体力也仍是人力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体力社会性别价值定位的准则就依然具有某种刚性,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以及社会家庭生活中的某些性别隔离便仍然能规范两性的意识和行为,直至最大程度地决定了两性的力量、作用、地位对比结构。在体力社会的框架中成长起智能社会的秩序,在农业社会的结构中建树着工业社会的机制,在传统的性别权益格局中扩展着现代的性别价值定位准则,这,就是今天浙江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化的规定性及内涵。
而正因为智能因素的成长还未能根本动摇体力社会的构架,农村仍更多地属于农业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因此,我们在欢庆女性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首先,整个农村的社会——家庭环境还是更倾向于有利于男性而不是女性的发展,非农化过程给予男性和男性自己获取的好处较之女性的更多。
其次,男性不仅仍更多地居于“高者”、“优者”、“强者”、“主者”的位置,并且,更固执地维持着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性别规范,女性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改善,由此受到来自另一性别——男性的制约。
第三,虽然已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显示出与传统相背的性别规范选择,但大多数女性仍持有传统的性别定位标准,以及对自己在家庭中享有的权利和所处的地位表示满意[③]的事实明晰地表明,更多地受着传统性别价值观的左右,大多数农村女性还未充分意识到家庭或婚姻的性别权益格局中的不平等状况,其抗争力也不强,两性间由此维持着传统意义上的“相安无事”。
第四,当女性与男性联合向家庭强权或上代强权进行抗争,对家庭利益或上代利益实施蚕食时,女性往往能有所成功乃至大获成功的,虽然两性相比,男性的获利更多些。但当女性纯粹以女性的身份与男性进行抗争或实施蚕食时,女性的成功却是微弱的。考虑到事实上上代女性(包括母权)权益也在衰落,比较工业化导致的全球个体主体价值增强和下代权益扩展的时代潮流,不能不说,今天农村妇女婚姻家庭地位的提高是一种以家庭成员个体和下代身份获得的“顺手牵羊”式的成功,决非是纯粹的女性的胜利。
很难说今天在非农化程度较高地区存在着的这一体力社会性别规范辅之以智能社会性别规范的状况不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是否也可以说是以经济冲击波为主的非农化进程对于农村社会传统结构——功能构架冲击的尚不充分和有力?从中国妇女地位提高的历程来看,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这三种力量的推动是极其重要的。而当近十几年来中国由政治化社会日益向世俗化社会转型时,经济和文化价值的推动力量就更是至关重要的了。只是,非农化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经济力量而存在、发展、扩张的。虽然它能引发、推进文化价值的变化,但毕竟不是直接的文化价值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文化价值造成了性别等级并决定着性别间的利益分配。当新的文化价值还不足以对旧的文化价值进行摧毁性冲击时,即使已有人不满意被指派的性别角色,已有人不满足被指定的性别地位,仅依靠经济的动力也是难以完成对性别规范的转型的。此外,即使是非农化本身,迄今为止在中国的发展亦是不充分的,包括在非农化程度较高的浙江农村。于是,在性别格局上,尽管与非农化相伴随,两性的地位对比确实发生了较大的、有利于女性的变化,但就总体而言,男女不平等仍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看来,为使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有一个质的飞跃,加速非农化进程,扩展新的文化价值的力量已势在必行。
注释:
[①]本研究的调查采用了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和个别访谈、观察等方法。其中,问卷调查所采用的问卷是自行设计的,设置了涉及家庭权益格局、代际权益格局、婚姻权益格局三个方面的共40个典型问题,其实施和数据处理委托浙江省统计局农村调查队住户处进行。问卷调查的具体实施方法为,以代表性和可能性为原则,根据非农化水平,先选取了非农化程度较高的余杭市(县级市)、非农化程度一般的嵊县和非农化程度较低的缙云县(市),然后根据样本量的要求,以人均纯收入为排队标识,以人口为辅助资料,采用随机起点、对称等距的原则,采用县(市)抽乡镇、乡(镇)抽村、村抽户的三阶段抽样方法,抽取了各100份共300份的样本。各县(市)的100个样本均分布在10个乡(镇)中的10个村中,抽样误差控制在3%以内,概率度a=0.05(把握程度为95.54%)问卷调查时间为1995年5月—8月。问卷调查形式为乡统计员牵头、辅助调查员进入样本户访问其曾有婚姻史的一位成员,帮助填写。问卷共发放350份,收回300份,回收率为87.1%,有效率为100%。
问卷回答者中,男性占53.7%,女性占46.3%;年龄分布为35岁以下占13.3%,35—45岁占31.0%,46—55岁占36.7%,56—65岁占13.3%,65岁以上占5.7%;平均年龄46.12岁,其中男性46.52岁,女性45.7岁;中位数年龄46岁,其中男性46岁,女性44岁;最小年龄24岁,最大年龄86岁;文化程度分布为大专及以上无,高中及中专占4.4%,初中占33.3%,小学占49%,文盲及半文盲占13.4%;主要收入来源分布为农业的占8.1%,乡镇村企业工资的占28.5%,个体劳动的占52.4%,股金或股息的占0.3%,亲属资助的占1.3%,副业手工业等其它的占6.7%,无经济收入的占2.7%。
[②]在1949年以后,浙江农村基本上仍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但制丝、纺织、农机具修理等非农行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据1978年统计,该年农村98.72亿元的社会总产值中,农林牧渔业产值占66.56%,非农产业产值占37.43%;1465.2万农村劳动力中,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占86.74%,非农行业劳动力占11.21%。从八十年代开始,以乡村两级工业企业为龙头,浙江农村家庭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出现了全面发展,农村劳动力也大批转入非农产业。至1985年,农村非农行业产值增至270.04亿元,在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60.8%;非农行业中的劳动力达到564.7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3%。
通过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更深入的发展,至九十年代,浙江省农村非农产业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非农化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据1994年统计,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只占12.6%,非农行业总产值占至87.4%;农村总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占56.5%,非农行业劳动力占43.3%,外出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劳动力占10.7%。农民收入来源也日益扩展。199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林牧渔业等的收入只占30%,另外70%则来自乡镇企业工资、个体手工或商业劳动等非农劳动,而收入形态中,贷币收入已占到收入比重的91.1%。可以说,作为非农化程度较高省份,浙江省农村的非农化过程具有典型意义。
[③]参见王金玲:《浙江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性别比较》,载《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