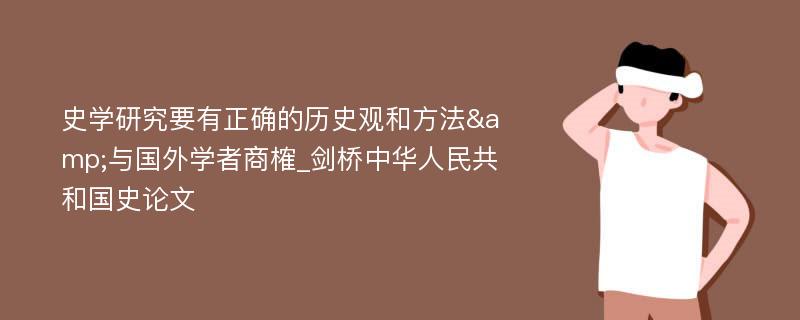
史学研究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同外国学者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历史观论文,史学论文,学者论文,正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拜读了著名的美国史学专家麦克发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后,感慨颇深的一点是,作为史学工作者,在对中外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或者仅仅是其中的某一局部、某一片断进行研究,并要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描述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论时,必须具备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完全地把握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是十分困难的,包括笔者本人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缺少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则历史就常常会被扭曲、变形,以至离历史的真实相距甚远。所以,努力地去把握,或自觉不自觉地把握与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则是一切史学研究获得良好成果所必需的。尤其是撰述千古流传的史书巨著,这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它直接关系到撰著的好坏、成功与失败。所以,在史学研究工作者面前,或在史书的撰写者面前,随时随地、也可以说时时刻刻都要迎接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挑战,有时这种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某些作者,曾正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严肃地坦诚地提到这个问题。在我们读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4卷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所撰写的《书目介绍 政治挂帅:略论1949年后的中国研究》时,曾发现,作者深刻地指出:“原始资料的不连贯性,构成中国研究的一个基本方面,向方法论和分析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第6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说明,在撰写这部史书时,作者感受到一种挑战,并体察到这是向史学研究工作者或撰写者所运用的方法论的挑战,这种感受或者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从整段话的完整性要求来看,还需要做什么补充的话,我想,是否再补充两点会使这一论述更为丰满:
第一,研究工作者的方法论和历史观是统一的。没有孤立的方法论,方法论与历史观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即观察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每个人也都有他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就是运用他的世界观来观察历史所得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所以,历史观和方法论从本质上看是不可分的,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没有孤立于历史观之外的方法论。所以,在上述引文中,作者的提法如果是“向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挑战”,而不仅仅是“向方法论和分析”的挑战,似更完整些。
第二,不完全是资料的问题。作者认为向方法论提出的挑战主要来自对中国研究方面的“原始资料的不连贯性”。第一手研究资料不充分,各个时期资料的公布和占有不均衡,以及原始资料之间缺乏关键环节的连续性等等,这些在历史研究中都是会经常碰到的,是必须千方百计努力克服的困难。但对方法论而言,这种“原始资料的不连贯性”则不是最主要的矛盾。其实,占有再浩繁、再具有“连贯性”的资料,也还有一个向史学研究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挑战问题。原因是,在浩繁的、连贯的历史资料面前,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都需要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艰苦研究过程,否则就不能把握历史发展过程、本质及其规律性。所以,每位史学工作者,不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不论是研究中国史还是研究外国史,都应该力求把握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便达到自己所预想的研究境界和取得应有的研究成果。
那么,史学研究中具有成效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要点有哪些呢?
厚厚的两大本史书巨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以说是西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诸多学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它的主编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参加撰写各篇章的有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校的专家、教授,还有伦敦大学、悉尼大学、日本大学、香港大学等的专家、教授。都是一些学术造诣很深,政治上有独立见地,史料学研究谙熟的学者。然而,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有各自的生活、工作环境和学术历程,要求他们有统一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而提笔对于摆在面前的巨著书写评论的中国学者,当然也能依据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的指导思想,诚然,这也成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但作为同上述各国资深学者、专家的学术探讨、问题商榷、著作分析,我们不能要求国际学界朋友们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正如国际上有的学界朋友信奉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而不能要求我们也同样信奉实用主义,并以其为治学指导原则一样。历史观和方法论存在分歧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逝的。强求一致,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不过也正因为有分歧,方使交流和商榷成为必要的,对于加强学术界的沟通是有益的。
因此,我想就我们和国际学界朋友可以沟通、可以达到共识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某些要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史学工作者写历史真实、还历史本来面貌。
写真实,记真实,论述真实,这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起码的求实态度。因为,昨天对于今天来说就是历史。昨天以前,有无数的真人真事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沿着历史的轨道或超速飞跃或步履蹒跚地行驶着。而历史事件又是十分复杂、犬牙交错的。人们所追求的是“以史为镜”。若离开历史真实,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离开历史本来面目的研究和撰著,不仅被诚实和正直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是不可取的,而且其最终结果,没有不失败的。
关于书写历史,必须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在这一观点上,我们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地位很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的看法十分接近。在费正清和丹尼斯·特威切特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所撰写的《总编辑库》中,曾谈到认识的事实基础问题:“由于现代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从历史上认识世界就愈发变得必要,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复杂了。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资料激增,认识也在提高。仅仅总结已知的事件就令人生畏,然而,对于历史的思考来说,认识的事实基础越来越必不可少。”(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卷,《总辑程序》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说明,在主导编辑看来,史学家认识历史、思考历史、对历史作出理性的判断,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这无疑是合理的正确的。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正确地批评了那种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而不顾实际的研究中国历史的错误倾向。例如,有人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作辩护,说正是西方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费正清教授批评说:
“我们自我欺骗的程度是不难看出的。在今天,谁在一眼之下都不会支持这样的论点:即蹂躏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实例不是使中国的改革家看到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优点了吗?……
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第14-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作者是在“中国统一的成就”的标题下面谈到上述观点的。他不同意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说明中国过去和现在这样的统一大国的形成与存在的。很明显在这里作者是赞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说明中国,而不主张生搬硬套西方的名词术语。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也是我们之间能够取得共识的研究标准。
第二,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客观地观察、书写历史。
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要做到尊重“认识的事实基础”,首要是能够排除主体感情和利害关系等因素的干扰和扭曲。
作为史学家,即书写历史的主体,都是有感情的具体的人。有人提出“抛开感情的因素书写历史”。这种要求不能认为不合理,但要百分之百的真正做到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提出这种要求可以促使史学家更加冷静、客观、自制,努力不使这种感情因素干扰史学研究,更不能偏离历史真实的轨道。出自某种个人偏爱和利害得失去书写历史,势必持偏执之词而歪曲历史。当然,刚直不阿的史学家,怀着满腔的怒火,揭露社会的罪恶,写出流传千古的杰作,也屡见不鲜。中国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书写《史记》就是一个范例。不过这是一种忧国忧民、以社稷为重的站在人民立场的感情。它同以个人利害为出发,或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为重的狭隘的个人感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对“感情”也还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史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是要排除那些干扰客观地认识历史真实的“感情”。比如,某些人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由于对共产党有偏见,感情上不接受或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他肯定不会客观地书写这段历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二位教授所撰写的第14卷序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力量和意图构成了这两卷的总布局。与帝国和民国时期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没有一个生活的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地区不受中央当局坚决使中国革命化这一努力的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写完两卷本巨著,主编麦克法夸尔在15卷的《后记》中又写到:“本卷中的主要论述截止于80年代初期,以便提供一些历史背景。80年代初期是充满希望的岁月,人们真正感到在邓的领导下,已有了新的开端。中国人民开始显示,他们愿意,也能够利用新的自由来改善自己的命运。”(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卷,第928页。)这一方面说明国际学界朋友,对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友好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该书的主编力主撰史的客观性。与此同时,该书还在有关部分批评了某些国际学者撰写的史书由于感情的偏颇,而出现的对历史的扭曲。例如书中指出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可谢·泽罗克霍夫契夫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微》(德文版名称)一书中“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卷,第972页。)针对这种现象,该书提倡“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卷,第972页。)确实如此,以着不友好的感情,很难客观地书写中国的历史。主观的歪曲史实的攻击之词,又能够为严肃的有意义的史学研究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抱着要求客观地观察历史的愿望去进行研究,虽然也很难一次就穷尽史实,但总会愈研究离历史的本来面目愈接近。
第三,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从发展变化上观察和书写历史。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会在哪一个阶段停滞不动,相反地,永远是处在变动之中。“生生不息,变化不已”。这种变动,尽管千变万化,曲曲折折;有时急骤,有时缓慢;有时表现为前进的运动,有时表现为后退的运动,但从总体上看历史从来没有停止,也没有循环,而总是不断地发展和前进着。同样,历史上的人物以及所发生的事件,或历史上人与人的关系、历史事件的联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如此,历史本身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客观地如实地从变化发展上观察、认识与书写历史。这也可以说是历史科学这门学科客观存在的质的规定性。有关上述观点,我们不清楚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和撰稿者在认识上、在理论上有多大程度上的共识,恐怕很难彼此完全一致。然而,由于受到历史科学的质的规定性的客观导引,却能够在方法论上表现出很多共同性。例如我们看到该书的许多部分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书写这种历史进程的变化,也许是在“跟着历史走”。尽管有的史料不够真实和准确,论述不够客观,但他们总是在写变化。而且他们是在分阶段地认识与书写这种变化。正如该书主导编辑费正清在14卷第1章所说的:“我们对现代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了解已经通过一系列很有特征的阶段而有了发展。对这几个阶段的简单的回顾,就是阅读这段论述人民共和国最初16年(1949-1956)的《剑桥中国史》的最佳入门。”(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不仅注意了历史的变化,而且还注意到西方和中国学者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互相影响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他们认为:
“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总编辑序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当然是中国史学界乐于看到的一种应予肯定的好趋势。
在该书的某些部分中,还正确地指责了那些不从变化发展上书写历史人物与事件所产生的谬误。有的作者指出:“当代中国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扰动和变化的领域;当学者结合关于过去事态发展的最新资料进行研究时,就需要不断地修改他们的解释。虽则大多数分析家对资料问题的态度是谨慎的,这个领域偶尔也发生弊端。……例如,研究者在1966-1970年得到的文献,说明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不断增长的冲突和他们在1965-1966年关系破裂的原因。有的分析家孤立地抓住这个材料而忽视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个巨人之间长期合作的记录,着手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描绘成敌对的。”(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第612-6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从这种批评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主张史学家应“描绘”出历史的变化。不过,这种历史变化的“描绘”应该是符合客观的实际状况,科学地估量其发展变化程度,而不能主观地任意夸大或作过分的估量。这样的看法,我们也是赞成的。
第四,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充分地认识和书写出历史的曲折。
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作为一种变化发展过程,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前进的运动。然而,这种前进不是笔直的,平顺的,而是曲曲折折,起起伏伏,有前进,也有后退,复杂多变,呈现出一种波浪式的状态。有谁能找出世界上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道路是笔直的,或者始终在一个水平线上发展?没有这样的客观存在,也没有这样的历史记录。那么只能是“踏破铁鞋”,也寻觅不到这样的“净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承认“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总编辑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承认中国历史的发展“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而新中国进行的改革和建设将是“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试验。”(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既然是“试验”,而且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那么曲折和挫折的不可避免性,也是客观存在的。该书的一些撰写者确实是在努力书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的复杂与曲折。这是很好的。当然,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比如,有些撰写者对这种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描述得不够准确,作了某些缺乏事实依据的主观推测,甚至苛意的评说。应该说在研究别国历史时,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这些现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总要反复研究,慎下结论为好。
第五,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史学工作者能够严肃地去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
历史的发展变化原因是什么?这是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变化都不可能是凭空而起的,都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而且这些原因是现实的、客观的。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某种神秘力量制造的发展变化。那种认为历史的变化发展来自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什么“天命”、“鬼神”、“上帝”等等,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这种愚昧和妄想,是不应进入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视野之内的。
当然,要准确、无误地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很不容易的。具体来说,找出某种历史事件的发生、演变、以及历史人物行为和思想变化的原因,没有对大量史实的认真搜集和占有,没有科学的分析头脑,没有艰苦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对于新中国历史的发展的原因,一般说是重视的,并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大胆的探索。但就其实际结果而言,有些对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事件、人物的思想行为的变化原因,作了比较好的探索和论述;有些则论述得不恰当,甚至失真;有的还只是罗列了很多现象,而不分主次,真伪混淆;有的没有摸到历史事件、人物思想行为演变的真正原因,似在进行主观的猜测;当然,也有坦诚地声明这件事的原因还不清楚等等。
作为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我们是和这段历史一起走过去的。这样一来,一方面,作为亲历者,我们不难发现上面所谈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成功和失误之处。因为,许多历史事件,对于我们来说不仅身临其境,而且至今回顾起来还历历在目;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真正把握各种事变的深层次的内因与外因,对于我们这些只从一个小局部亲历事件的人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件。这中间有个人生活条件的局限,有接触环境与视野的局限,有个人认识的局限,以及资料占有的局限等等。由此领悟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国际学界朋友(这里已排除了那种仅以史学为掩护而别有企图的,严格说不能被认为是史学家的个别人)在研究中国历史、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确切原因时,有论述不当之处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历史变化多端,“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而广泛”(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总编辑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新中国也不例外。要真正写出新中国的变化发展,探索其真实原因,即各种历史事件处于多方面联系中的内因与外因,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任何事物变化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原因,偶然原因,以及各种原因又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存在的,因为整个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面对这种普遍联系的图景,去寻找历史链条的某一环节的真实原因,必须要有全方位、多层次的观点。这是要付出艰苦努力的。
在探索历史的变化、发展及其原因时,有一个规律性的问题,既是观点问题,也是方法问题,即“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是不应予以忽视的。如果由于批评新中国的领导者所提倡的“斗争哲学”带来的危害,而根本否定上面讲的观点与方法,就意味着没有办法找寻到历史事变的根本原因。
总之,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向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有正确的历史观、方法论意味着对科学世界观的把握,也意味着开启了取得辉煌的研究成果之门。诚然,对它的完全把握是异常困难的,要求中外史学工作者都全面无误地把握和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现实的,也肯定会有许多西方学者不会赞成。然而,全面把握的要求,是应当提出的,也是我们应共同力主和努力提倡的。“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有了较高的要求,以及艰苦的努力,即使达不到本来的要求,也还会取得较好的成果。更多的把握,会有更多的成功;部分的把握,会有部分的成功;对其把握,哪怕有一点点自觉的意识和努力,也会有某些优秀成果作为回报。相反地,完全背离和在某些方面背离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其研究的结果,势必导致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扭曲和背离。那么,带给社会的不能不是被列入否定性的产品,对于个人的艰辛努力及所付出的代价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标签: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科学论文; 费正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