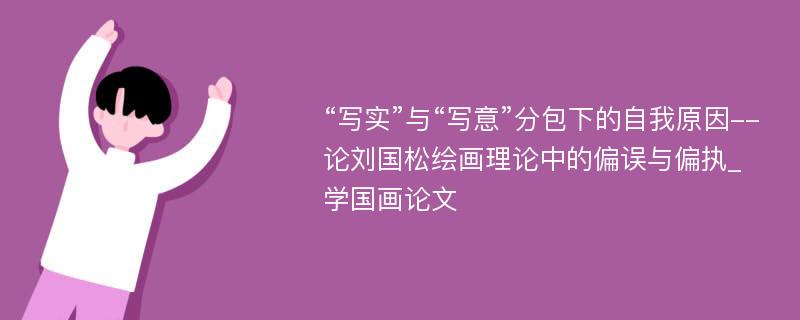
“写实”与“写意”分判之下的自我理由——论刘国松绘画理论中的错误与偏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意论文,偏执论文,错误论文,理由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郎绍君先生在《类型与流派》一文中将20世纪的中国画分为三大类型和九个流派①。三大类型分别是“传统型”“泛传统型”和“非传统型”。其对于20世纪中国画的考察主要基于大陆范围而不涉及我国台湾的画坛,以其三大类型的划分来看,刘国松的画作则应该归于非传统型。其自身的定位是“中国的现代绘画”②,更为确切地说其创作实践主要是“现代水墨画”(《刘国松谈艺录》第61页)。本文无意于对其绘画实践作出分析与评判,而在于对其指导实践的绘画理论进行适当的论辩,以对支持其实践的理论合法性作出适当的论定。
一、写实、反写实
1.对传统中国画“写实”的错误判定
“写实”作为绘画理论用语并非中国本有,而是随着西方艺术理论的引入才被使用的。“写实”一词来自于日语,在旧日语中realism被译成“写实主义”,同样为中文旧译所沿用,而在现代日语中则是以片假名形式的音读外来语,现代汉语则译为“现实主义”。“写实”一词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出现了三次,均是将其与“理想”对举③,则“写实”即“现实”。
在西方绘画中现实主义的表现是与再现理论相一致的,这是西方古典绘画的重要特征。西方古典绘画对现实的模仿是与认知的功能结合在一起的,在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中,对象是被客观认知的,而绘画就是手段之一,如达·芬奇所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觉。”“对作品进行简化的人,对知识和爱好都有害处,因为对一件东西的爱好是由知识产生的,知识愈准确,爱好也就愈强烈。要达到这准确,就必须对所应爱好的事物全体所由组成的每一个部分都有透彻的知识。”④他又说:“鄙视绘画的人,既不爱哲学,也不爱自然,绘画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的模仿者。如果你藐视绘画,你势必藐视了一种深奥的发明,它以精深而富于哲理的态度专门研究各种被明暗所构成的形态(例如海洋、陆地、植物、动物、花草等等)。绘画的确是一门科学,并且是自然的合法的女儿,因为它是从自然产生的。为了更确切起见,我们应当称它为自然的孙儿,因为一切可见的事物一概由自然生养,这些自然的儿女又生育了绘画,所以我们可以公正地称绘画为自然的孙儿和上帝的家属。”⑤当绘画被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时就发现了其中焦点透视、光影变化规律以及色彩变化规律。
中国画与西方绘画不同,它的本质是“象”。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谓:“江南绝笔,徐熙、唐希雅二人而已。极乎神而尽乎微,资于假而迫于真,象生意端,形造笔下。”⑥“象生意端,形造笔下”是中国画的基本原理,笔下之“形”是为了充分呈现心中之“象”。明祝允明言:“盖古之作者,师模化机,取象形器,而以寓其无言之妙。”⑦《周易·系辞上》:“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有形的世界是“器”的世界,而对于人来说要通过这个有形的世界达到对“道”的领悟,而“象”则是人用智慧与这个器世界照面之所得,即易之“观物取象”,象中既有对器的观感同时又含由观感而得到的对道的领悟,故象是道器的连结,而具体的象则是具体画家独特观感的结果,又标示着画家之心,所谓“无言之妙”即显示着画家对宇宙及自我的整体深入体验。画中得到表现的象是内心超越特定时空的取象显现,因此在中国画中就不可能存在焦点透视、光影变化规律以及色彩变化规律的探求。刘国松认为:
远如曹不兴墨污改蝇一类的故事不说,就拿流传下来而且大家所熟悉的古画来看,韩干的《牧马图》、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以及家喻户晓的《清明上河图》,哪一张不极尽写实之能事。讲光影,讲透视,我想西洋的油彩写实风景也不会超过南宋阎次平的《四乐图》了吧!(《刘国松谈艺录》第13页)
这种认识完全是主观的臆断。他又说:
模仿自然的论调,早在唐代,王维已说过“师法在自然”了。这种模仿自然的绘画观念,一直到两宋画院里徽宗皇帝对“晴夏月季”与“孔雀升墩”的写实精神的要求而达到高潮。(《刘国松谈艺录》第20页)
在中国画史中宋代的绘画表现以工细为主要特征,但在其时的艺术理论中从来就没有“模仿自然的论调”,而刘国松所谓的“写实精神”的内涵是从西画理论中移用过来的,并不适合于中国画。
2.“反写实”的臆断
刘国松对中国画史的论述中多次提到“反写实”:
这种反写实的精神,并非泛泛的偶然论调,乃是经常挂在画家的口头上,存在画家的心里的。其实,还不仅仅如此,甚至有点故意地走极端的意味。例如王维画雪中芭蕉,苏东坡画无节竹子,又画所谓朱竹。芭蕉哪里能长在雪中,竹子怎会没节?竹子的颜色应该是常青的,如果不设色,用水墨也算罢了。既然设色,而却又用红色,这不都是故意与现实采取相反的态度吗?然而中国人在这些地方,不但不加指责,反加赞美。(《刘国松谈艺录》第23页)
这种“理”的论调,正是中国画中形而上学的核心,也是打开中国画里反写实精神的惟一锁匙。因此,中国绘画一直是不贵形似而贵理的了,如果画家得到这种理之后,画的一切其他问题都变成了次要的事。(《刘国松谈艺录》第24页)
所谓“反写实”必须是有“写实”在,人们不满足于此才会出现“反写实”,这恰恰是西方绘画史的现象。西方绘画在其古典时期以写实为特征,而二十世纪发展的现代艺术则走向相反的方向,这是由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所决定的,绘画的表现由客观转向主观的结果。然而,作为“象”的中国画始终是主客相遇之际的所得,主客从来没有分离过,故而没有“写实”与“反写实”的现象存在。雪中芭蕉、朱竹都是融主客的“象”。“理”确实是中国绘画表现的重要内容,其内涵是多层次的,但是中国画从来没有出现表达纯粹观念的艺术,因为纯粹的观念是主观的,而理作为形而上的内涵是寓于形而下器世界之中的,因此对其表达不离于物。
二、变形、写意、抽象
1.“变形——写意”的非匹配性
在刘国松的理论中“变形”是极为重要的,并常常将其等同于“写意”:
我认为无论中国或西洋美术史的发展,都是走着同一条道路,那就是由工笔(写实)经过写意(变形)而走向抽象意境的自由表现。换句话说,整个的美术史,也就是艺术家为了争取表现自由的奋斗历史。(《刘国松谈艺录》第15页)
因此,上自唐之王洽、张璪,宋之石恪、梁楷、法常、米芾,元之倪瓒、方方壶,明之石涛、八大,清之扬州画派以及民国以来之齐白石,都是激烈地反对形似,反对抄袭自然,主张变形,主张简笔画者,强调“笔”与“墨”的趣味,也确立了“笔”与“墨”的价值。(《刘国松谈艺录》第20页)
一部美术史也就是一部艺术家挣脱形象束缚的奋斗史。所以,在早期的时候,画家都是在尽量地模仿,等到他感到“像”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束缚太大,甚至感到它阻碍着画家去表现自己,就开始变形。这种变形,国画称之为写意。因为要写“意”,便需要打破自然形象,也说明那些形象不重要而那个要表现的“意”或“我”才重要。等到那些形象完全不需要时,绘画就能直接地自由地去表现了,到了这个阶段,“意”或“我”就是“抽象”了。(《刘国松谈艺录》第100页)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工笔与写意的关系问题。就画面具体表现来说,与工笔相对的应该是意笔,清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言:“工笔如楷书,但求端正不难,难于笔活。”“意笔如草书,其流走雄壮,不难于有力,而难于静定。”⑧这自然是指不同的用笔方法及相应的线条形态。将工笔与写意对举则是由具体的用笔转而对整体表现形态的分别。在古代画论中则往往将形似与写意对举。元汤垕《古今画鉴》谓文与可:“墨花凡见十四卷,大抵写意,不求形似。”⑨又谓:“若观山水墨竹梅兰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戏翰墨,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观天真,次观意趣,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之。”(10)清方熏《山静居画论》云:“世以画蔬果虫鱼,随手点簇者,谓之写意;细笔勾染者,谓之写生。以为意乃随意为之,生乃像生而肖物,不知古人写生,即写是物之生意,初非两称之也。工细点簇,画法虽殊,物理一也。”(11)写意更多的是表达画者内心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内涵的展现在一定程度上与物象形体表现的具体性相冲突,在这个时候则需要对物象之形作一定的调整,尤其是文人画家的特定追求显得比较突出。当写意的表现落实在具体的笔墨上时由于其对物之形的遵循有所疏离便会带来新的问题,即画之象中物的因素减弱而使象本身受到伤害,则会伤及画的本体,故方薰强调“画法虽殊,物理一也”,在写意的同时必须对“物理”保持必要的关照。对此清恽寿平也表达了同样要求:“宋人谓:能到古人不用心处。又曰:写意画两语最微,而又最能误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处;不知如何用意,乃为写意。”(12)“不知如何用心”与“不知如何用意”即不要人为地刻意用心与用意,一切听从当下的自然表达需要。
写意与形似对举,在写意的表现中会突破物象表面的形似,则物象形态会有所改变,甚至有巨大的改变。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种物形的变化,但是中国画传统中物的形态变化与西方现代绘画中的“变形”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西方现代绘画中物形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到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表达物质形体在特殊时空状态下的形变,另一种情况则是对理性的反叛,依据个人的感性要求对客观物作非理性的肢解与重组。这是以“形”为对象的主动改变,是主动用心、用意的“变形”。而中国画中物象的形体变化是象的要求,西方绘画物在先而中国画则象在先。“象生意端”,由“意”到“象”是整体的生态转换,因此不妨称之为“形变”。在西方绘画中对现实物在形态上的主动变化必然是对再现的违背,是由客观走向主观,刘国松将“变形”等同于写意的时候,写意就是在写实之后出现的变化,两者是有时间先后的。而中国画的写意只是象形态上的变异,而作为象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因此在中国画中工笔与写意是并行共存的,不是发展的先后关系。而“形变”在工笔及意笔表现类型中同时、同理地存在着。“一部美术史也就是一部艺术家挣脱形象束缚的奋斗史”只适用于西画,在中国画中只是“形”与“意”的侧重程度不同而已。
2.所谓“抽象”
抽象是与具象是相对的一对范畴,法国美术史论家米歇尔·瑟福是这样来界定抽象绘画的:“我们称一幅画为抽象,主要是我们在这幅画中无法辨认出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客观真实。换句话说,一幅画之所以被称为抽象,乃在于我们在欣赏并以与表现无关的衡量标准来评论这幅画的时候,不得不认为任何可以认识的和可以解释的真实性是不存在的。由此引申:任何自然的真实性,不论它向前发展转变到何等程度,它总是具象的;然而,在作品中任何为具象服务的出发点(联想和暗示)都不存在,这种转变为我们的肉眼所不能加以辨认,那么我们就称这幅画为抽象的。”(13)
刘国松对抽象极为推崇:
艺术中的形式,色彩的对比和谐、线形的飞动处理、数量的比例安排,以及音律的节奏、舞蹈的姿态,都是抽象的点线面体或音色等的交织结构,以网罩万物形象及心情绪感,犹如面纱垂罩佳人之面,使人在摇曳荡漾、似真似幻中窥探真理,引人无穷之思。绘画形式的作用是组织、集合、配置,换句话说,就是构图:它使片情孤境自织成一内在自足的境界,无求于外而自成一意义丰满的小宇宙。但形式最后与最深的作用,就是它不只是化实象为空灵,引人精神飞越,超入幻美,而尤在它能进一步引人“由幻即真”,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世界上惟有最抽象的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书法,以及建筑、平剧脸谱、钟鼎彝器的形态与花纹,乃至现代绘画……才最能表现人类不可言不可状的心灵感受与生命的律动。(《刘国松谈艺录》第92、93页)
刘国松所强调的是艺术中的形式因素及其构成,并非是完全的抽象艺术,只是其中的抽象因素。其将音乐、舞蹈、书法,以及建筑、平剧脸谱、钟鼎彝器的形态与花纹归于抽象艺术的论断也是极为武断的。其对抽象的推崇自有理论依据:
一部美术史也就是一部艺术家挣脱形象束缚的奋斗史。所以,在早期的时候,画家都是在尽量地模仿,等到他感到“像”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束缚太大,甚至感到它阻碍着画家去表现自己,就开始变形。这种变形,国画称之为写意。因为要写“意”,便需要打破自然形象,也说明那些形象不重要而那个要表现的“意”或“我”才重要。等到那些形象完全不需要时,绘画就能直接地自由地去表现了,到了这个阶段,“意”或“我”就是“抽象”了。譬如说意境,它的难以用某种固定的事物表达,就说明那是抽象的。等到绘画不用自然的形象表现意境,而自由地随意造个新形象以适于表现,这绘画就没有多少束缚了。所以,画家是由模仿而走向抽象的。(《刘国松谈艺录》第100页)
在上面的阐述中刘国松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绘画态度:“意”或“我”是最重要的,而这个“意”是属“我”的意,他在艺术中要表达的归根结底是个人的“我”。他是这样来解释国画传统的:
国画传统尤其以性为主,心即学养情思,性即个性性灵,国画所注重的个人面目,其实就是个人的个性表现,所以无个性即无个人,无个人即失国画的传统精神。国画的发展,一向以自然为本,藉自然发挥自己的性灵个性、学养情思,进而冲破自然,不为物囿,自然而然地写成了半抽象的画。(《刘国松谈艺录》第29页)
其面对传统只是看到画家之间的异处,而没有看到画家们对深度与高度的共同追求,对于格调的强调是古代画家追求文化深度的重要体现,而对形而上之“道”的领悟与表现才是中国画代代相承的核心目标,而对道的追求是不能脱离这个世界的,是在这个世界整体之中的,那么我们的画就不能离开物。金观涛、司徒立指出:在西方19世纪之前,表达公共价值和人们的普遍感情是画家的使命,无论新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或写实主义,其关心对象和普遍价值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都力图表现那个时代的公有现实。自从“印象派”把风景理解为感觉分析并以此为绘画题材后,绘画所表现的内容才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变化。“表现主义”注重布尔乔亚细腻的个人生活,“野兽派”力图画出内心狂野的激情,抽象绘画则把人的主观概念呈现在画布之上,这些现代主义的每一步进展,都与否定公有现实并主张表达个人独特的感情连在一起。正如文化中的现代性是用个人自主性解构统一意识形态一样,把现代艺术的本质定义为否定公有现实而崇尚个人的特殊感受已被人们普遍接受。(14)
此论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艺术(抽象绘画)的本质是:否定公有现实而崇尚个人的特殊感受,而刘国松抽象追求的结果也正是这个。这是剥离了民族文化积淀之基因的个人化追求,这种剥离实际上就是剥离了中国画本体的文化规定性,事实上离开了中国画根脉的绘画实践必将归于“非传统型”。
三、创造、反叛、新皴法
1.创造
刘国松高举着革新的旗帜,宣扬着他的创造观:
艺术需要创造,这不但是本质,也是永远不变易的真理;中国绘画需要创新,这是中国画家一致的愿望、共同的目标。但由于对传统与创新的认识上的差异,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明二者强烈的对立,甚至水火不容。(《刘国松谈艺录》第48页)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进步,都是由于一代一代的人民,不停地对上一代或古人的理论与做法发生怀疑,产生疑问与新的想法,才会有新的创造与发明,社会才会不停地进步。
中国绘画几百年来没有突破、没有发展,就是因为画家对古人的理论(如方法论)视为金科玉律,对前辈的表现方法(如皴法)没有疑问,都认为理所当然。久而久之变成了教条主义,阻碍了中国画的正常发展。我辈画家如欲振兴中国绘画,必须要从基本的认识做起,进而发生疑问,产生新的理论与创造。(《刘国松谈艺录》第49页)
创造对于中国画的发展来说无疑是必须的,但是艺术的发展不能唯创造,刘国松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进步,都是由于一代一代的人民,不停地对上一代或古人的理论与做法发生怀疑,产生疑问与新的想法,才会有新的创造与发明,社会才会不停地进步”是典型的西方思想中的“进步论”,只有不断地彻底否定与重建才是发展,唯“进步”的变革是目标,这种思想本自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状况,西方不少人士以之用于人文科学及艺术领域导致了主动地变革和创新,但同时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人们对此正处于反思中。进步论的产生是基于西方文化的自我特性,其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化与艺术。
2.反叛
在西方进步论思想之下必然地带来反叛思想,而这种思想也被刘国松用在绘画理论中:
一个有创造和深彻了悟文化艺术的人,绝不会甘愿接受前人替他铸定的形式与格法。保守者常称我等为“艺术的叛徒”,其实,艺术的目的在求创造、在求表现自我,绝不在求破坏或表现反叛。创造必与已有的不同,自我必与他人相异,艺术只求异于大众,不谈反叛,如果一定要说我们背叛的话,那我们也许遵守了艺术的创造,而背叛了形式的抄袭,而那些所谓传统大师们,却愿意遵守先人固定的形式而去背叛创造,如说背叛的话,到底谁是艺术的叛徒呢?(《刘国松谈艺录》第45、46页)
“反叛”本是现代精神的一部分,其本质是反对一切既成的形式,其目的是创造一些世上所没有的,用以丰富人类精神的世界。可是不幸的很,那些自认了解现代精神而已攫取到现代精神的青年画家,他们所“反叛”的是过去中国的,或者西洋旧的,但却不反叛西洋新的流行的风貌。其实,西洋现代最流行的也同样是“既成”的,也应该归于反叛之列,并非将西洋最新的形式搬来就可成为中国最新的、个人最新的了。如果把这种模仿视为学习的过程,尚无可厚非,如果这样就奢谈创造,那就未免有些过早了。因为,凡是创造必定是新的,凡是新的必定是过去中外所没有的。说得再明显一点,现代精神是建筑在反叛的、创造的与个人特质显现的基础上,以为模仿西洋现代绘画的形式即是获得了现代精神是错误的。相反的,却是违反了现代精神的本质的。反叛首在反叛一切既有的“形式”,不论东西。(《刘国松谈艺录》第47页)
刘国松对于个人创造的论述与马蒂斯所说的“我相信,艺术家个性的发展及充分肯定它的权利是通过同其他个性斗争才能获得的”(15)是一致的,“同其他个性斗争”是同古往今来的所有个性艺术家斗争,这是以画家个人为中心的奋斗。反叛意味着割断与他人的关联,这种西方式的个人创造与重师承、重积淀的中国画传统完全背离,其核心就是对传统文化基因的剥离。
3.新皴法
那么刘国松所谓的创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的论述:
如果你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像科学家一样,不停地在画室做实验,探索、发明并创造出一种或多种适合你自己的需要与表现的新技法,然后紧抓住它,再重复地锻炼、重复地练习,等到你这独特的技巧愈练愈精,达到成熟完美时,你就可以挥洒自如,你个人的独创画风也已建立完成。这时你的个人建筑就开始露出地面,将来你到底能建多高,就要看你的思想观念是否纯、专,独创的技法根基打得多么深,个人独特的画风有多么强,自己方面的修养有多么精了。千万快不得,更不可急功近利地求速成,否则你个人的艺术大楼,就建不高,而且还容易倒塌。(《刘国松谈艺录》第78页)
我和我的学生们不停实验的结果,共同创造了许多新的皴法,有的已定名,有的还未命名,都在这次“刘国松研究展”中同时公之于世,引起了观众热烈的欢迎与讨论,也引起了保守人士的震惊。六百年来,我们对公式化的文人画首先作出了突破性的发展。新的创造性浪潮,又滚滚而来。(《刘国松谈艺录》第50、51页)
刘国松在反叛之后所建立的主要就是在画面形态上通过实验的方法找到别人没有用过的新皴法。他说:
所以说,“笔墨”就是一切绘画的元素“点、线、面、色彩”;“皴”就是北方人冬天所说的“脸上皴了”,查查字典,“皴”就是“肌理”。如果大家思想能搞通这一点,中国画就再也不会受明清封建文人的家法所限制规范了,立刻变得海阔天空,任你遨游飞翔了。画家们就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表现工具、材料和技法。即使不是用笔而是用其他方法制作出的点和线好的话,也叫做用笔好。如果这些点和线又是用笔“写”不出来,又和传统的点线完全不同,这不就丰富了国画的表现方法,也拓宽了国画的表现领域吗?那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有大批中青年画家加入此一创新的行列,互相观摩竞争,一定会力争上游出人头地的。除了他们的胆识会比传统的画家强之外,如果在个人学养、胸襟和格调上再加以好好培养,最后才气高的一定会脱颖而出,人数多的话,再假以时日,中国画的另一高峰,是指日可待的。(《刘国松谈艺录》第61、62页)
传统中国画是通过笔墨来展现画家对世界的领悟以及表达个人心绪的,其之所以能够胜任是因为在手的挥运之下笔墨与画者的内心直接对应而无间隔(这是需要严格训练的),并且笔墨自身作为生命状态而存在,古人对于笔墨、筋骨血肉、神的要求与审美体现了中国人对宇宙世界生命性的根本理解。当笔墨成为画面形式因素而皴法成为肌理的时候,画面只剩下纯粹视觉了,而这种视觉形式与画者内心的精神对应在画面的经营中反而疏远而变异了。刘国松说:
林风眠、刘海粟与徐悲鸿等虽然也各自提出“改良国画”的论调,但只有徐悲鸿接受了法国写实派的观点,提倡写实的论调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于是徐派在大陆一枝独秀,而刘、林二人则被打成右派,三十年不许画画。所幸者,台湾与海外还有一些从事中国绘画创作的有胆识的画家,有鉴于此,不停地努力、探索、反省、试验、再探索,希望把具象的传统写意画与抽象的西方现代画糅合在一起,希望将造形的绘画与表意的草书融会成一体,创造出一种或多种崭新的绘画形式与风格。(《刘国松谈艺录》第59页)
他所谓的“把具象的传统写意画与抽象的西方现代画糅合在一起”的目标实际上是用西方现代绘画的理念改造中国画。因为刘国松绘画理论的基本立足点是西方的,他对中国画的观点和认识是以西画的历史和标准而形成的,其理论中的错误来自于对传统绘画血脉的全然无知,其实践追求是在这种无知下的个人偏执,这种偏执使其绘画重在技法层面的新异探索,尽管其也强调作品的精神性内涵,但只是降为个人的私情。如若视其为画之别调则也无可厚非,但作为传统绘画的发展来对待则是南辕北辙之行。
注释:
①此文见于郎绍君文集《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8月。文中将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分为“传统型”“泛传统型”和“非传统型”三类,其对于三大类型分别有具体表述,传统型:“其特点是坚持传统绘画最基本的语言方式——笔墨方法。笔墨方法不仅包括写意画的笔法墨法,也包括工笔画的‘骨法用笔’以及相关的晕染法。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吴湖帆、贺天健、陆俨少、李可染、傅抱石以及晚近许多中青年画家,都属此类型。他们也有人适当吸收西画因素(如李可染),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语言方式的民族特色。它是传统的,古典的,但又有新意,绝非对古人的重复。”泛传统型:“指古典中国画的变异形态,如高剑父、高奇峰的‘调和中西’之作,徐悲鸿、蒋兆和式加入了素描因素的人物画,林风眠以水墨为主的仕女与花鸟,陶冷月的月景山水,吴冠中的部分彩墨风景,及当下中青年画家同一倾向的作品。它们强调‘现代性’与‘转型’,广泛地借鉴西方绘画,移步换形,突破传统媒材与笔墨方法的限制,手段更加自由,面貌愈趋多样。”非传统型:“指中国画变异的极端形式。它介于中国画与非中国画之间,是一种边缘形态。它们保留或部分保留着传统中国画的材料工具,但作画观念、技巧规则和风格面貌大都取借于西方,与传统中国画的联系已微乎其微。某些作品已跨出中国画边界,大略混同于水彩画、水粉画、丙烯画或综合材料画。它们大多抛弃了笔墨方法,或代之以其他画种(如油画)的技巧方法,或变为不拘一格的综合制作方法,或只把水墨媒材从笔墨传统中分离出来,将它‘还原为单纯的材料’而随意用之。”
②李君毅.刘国松谈艺录[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2:145.本文引用的刘国松绘画论述原文均本于此,后不再另注,仅在引文后标注页码。
③“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民国十六年《王忠悫公遗书》本)
④[意]达·芬奇.朱光潜,译.笔记:卷一[M]//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58-159.
⑤[意]达·芬奇.戴勉,编译.画论[M]//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62页。
⑥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456.
⑦祝允明.枝山文集:卷一 吕纪画花鸟记[M]//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7.
⑧于安澜.画论丛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573-574.
⑨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900.
(10)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903.
(11)于安澜.画论丛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448.
(12)恽寿平.南田画跋[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983-984.
(13)[法]米歇尔·瑟福.抽象绘画史[M].王昭仁,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7.
(14)金观涛,司徒立.具象表现绘画研究[M]//司徒立,金观涛.当代艺术危机与具象表现绘画.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53.
(15)杰克·德·弗拉姆.马蒂斯论艺术[M].欧阳英,译.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7:11.
标签:学国画论文; 刘国松论文; 国画大师论文; 国画写意论文; 艺术论文; 个人形象论文; 美术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化论文; 谈艺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