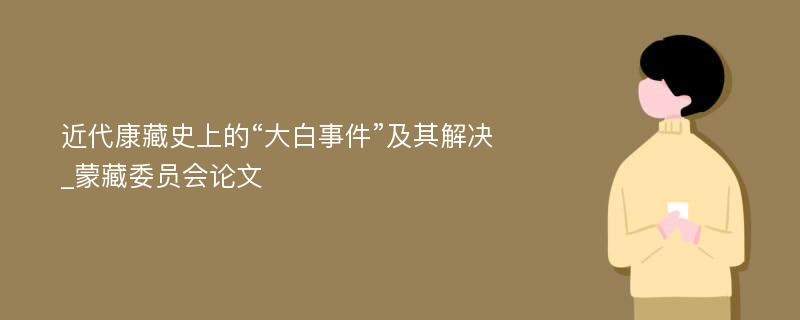
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白论文,史上论文,近代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8)02-0020-06
在近代史上,如同“民七事件”升级为“第二次康藏纠纷”一样,在民国中期的1930年,在西康地区发生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大白事件”,并升级为“第三次康藏纠纷”。事件发生后,发生纠纷的双方——大金寺(当时文献又译写为“大节寺”、“达结寺”、“大吉寺”、“大经寺”、“达金寺”)、白利村(当时文献又译写为“白日寺”、“白茹寺”、“碧利寺”)各执一词,互相指责,致使卷入事件的康与藏、中央与地方等各方面越来越多,一直到了1940年,这一历时久、涉及多、过程复杂的纠纷事件,才最终得以解决。关于“大白事件”及所引起的所谓第三次“康藏纠纷”,最新的研究成果请参看周伟洲先生的大作《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1-10页),该文对“康藏纠纷”的历史根源、性质及其影响提出了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本文拟重从民族关系的视角进行一番论述。
一、“大白事件”的发生
(一)大金寺及其亲藏传统
大金寺位于甘孜县西部的绒坎岔,距县署约50里,在白利村西约30里,是一座格鲁派大寺,在康北以富裕、势众著称,寺中僧人善于经商,办有“桑都昌”商号,该商号的分支机构遍布拉萨、康定以及印度噶伦堡。大金寺部分喇嘛投靠十三世达赖(1876-1933)后,在拉萨做生意,请求免税,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批准[1](p1452),势力更加发展壮大,喇嘛益加骄横,有恃无恐。
大金寺向有亲藏传统:光绪三十五年(1909),赵尔丰在率军平定德格土司争袭的军事行动中,由于大金寺“拒绝官军驻扎”[2](p509),致使昂翁降白仁青一行人得以从绒坎岔以南打火沟逃往邓柯、杂曲卡一带;民国六年(1917),“有乡城挂[即娃]八百骑,远道来抢大金,寺僧闭门拒守,激战三日”,并向当地边军“乞援”,边军坐视不救,“寺僧由是大恨”[3](P456-457);次年,在藏军东攻的战争中,“寺僧因记旧仇,私通藏军,确曾戎装助战,所以能攻陷喀坪桥,汉军大遭挫折”,因此,大金寺“不畏汉官,益与藏军结纳也”,“大金寺实暗助藏番”[4](P420),是当时的共识。1928年冬,九世班禅大师驻川办事处所出版的《藏民声泪》说:“西康北路之大节喇嘛寺,共有喇嘛七百余人,殿宇宽宏,寺产富庶,为全康各寺之冠,……又每人必备快枪良马,以资防卫,偶一集合,俨成劲旅,近年受达赖指使,屡次驱逐川军,极得达赖嘉奖。今春,达赖复行笼络手段,遣特派员到康,赍该寺金佛二尊,绣像一轴,以及其他珍贵什物,该寺喇嘛,为其所感,是奏乐排队,欢迎特派员云”。[5](P53)
(二)“大白事件”的爆发
在康北,白利土司是很有影响的地方势力,其核心在甘孜县一带。在20世纪以来,白利土司“辖有喇嘛寺三:一曰春则,二曰白利,三曰亚拉”[3](P491),其中,雅让寺(属萨迦派,当时文献又译写为“亚拉寺”)系白利土司家庙。当地政务向由白利土司与雅让寺活佛共管。
1927年,白利土司去世,其女袭任。袭任的白利女土司性情刚烈,与雅让寺二世智古活佛不和,而雅让寺二世智古活佛降生于大金寺附近之“林葱乡桑都家,此家即属于大金喇嘛寺管辖”[4](P428),素与大金寺关系密切。此后双方矛盾日益加剧,智古活佛遂于1930年初迁往大金寺,并将此前白利土司拨给服役的15户差民转赠给了大金寺,引起白利女土司和民众的反对,为争夺15户差民,白利女土司逐渐与大金寺发生纠纷,实际只是很少的寺产之争。
当时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属下的川康边防军(下称“康军”)无心无力使事态扩大,希望息事宁人。故而康军旅长马驌派遣了参谋朱宪文“驰往开谕”,谋求前往解决大金、白利之纠纷。而金沙江西岸的十三世达赖及西藏地方政府想乘中原战乱恢复大西藏的迷梦,派了两个代本的兵力越过金沙江,从德格打过来支持大金寺,妄图占领康区。
1930年6月18日黎明,大金寺仗着人多势众、武器装备精良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纵容,在管家桑领德甲、真真的率领下,出动僧兵,“率队猛攻,开枪轰击,将白利高地占领,焚毁民房数十间,继又占领白利村全部,掳去男女数十人,缴去快枪及九子枪共二百余支”[4](P431)。武力攻占了白利村后,僧兵们到处抢劫烧杀,无所不为。白利土司及其随逃人员逃至甘孜县后,先后上报甘孜县、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等部门[3](P1),要求主持公道。甘孜县知县韩又琦闻报,处理无措,只有请康军前来防范。康军旅长马驌商议后,派遣了军法官马昌骥、团长马成龙,会同道孚县灵雀寺、炉霍县寿灵寺的高僧以及甘孜孔撒土司、朱倭头人,前往调解纠纷。大金寺依仗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尤其是驻扎德格的藏军德墨代本的纵容收及三百支步枪的支援,蛮横无理,拒不接受调处。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驻川办事处均多次致电川防边防总指挥刘文辉、蒙藏委员会等部门,献策派人,积极调解,一度还曾引起过一场误会[3](P6-15)。
8月30日,康军派出的前沿侦察排长李哲生在值勒巡逻时,被藏军游骑开枪打死,致起战端。此即近代康藏史上有名的“大白事件”或“大白之争”,又名“大金寺事件”、“大金事件”、“达结(大金)白利事件”、“达结、白茹事件”、“达白事件”①,简称“达白案”[3](P200)。因大白寺地处西康甘孜县,故又称“甘案”[4](P433)。
事件发生后,康军大愤,当即炮轰雅拉寺、大金寺的防御工事。大金寺则组织僧兵并联合琼让代本部藏军,包围了康军连长章镇中部。旅长马驌闻报,派遣马成龙率部与大金寺作战。激战一个多月,克复白利村,并占领了寺旁的伸科、荡古,包围了大金寺。在这过程中,大金寺求救于西藏地方政府,十三世达赖致电蒙藏委员会,请求南京国民政府速电西康撤兵。康军亦由刘文辉转电呈南京国民政府,说明事由。南京国民政府闻报,迭令双方停火,不希望战事加剧,这样反而给了大金寺以喘息之机。英帝国主义见有机可乘,乃秘密向藏军提供大批军火、唆使藏军卷入大金寺事件。于是,藏军袒护大金寺一方,介入事件,导致藏军、康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故而大金寺事件扩大化为第三次康藏纠纷。所谓“康藏纠纷”,指发生于中国内部西藏地方与西康地区之间的矛盾与纠葛。
南京国民政府见藏军、康军双方各执一词,难于调解,乃于1930年12月17日下令派员前往西康实地调查处理,由此,国民政府长达十年的“大金事件”调解揭开了序幕,直到1940年5月事件才最终完全解决。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行政院、蒙藏委员会以及唐柯三等特派专员、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诺那活佛(1866-1936)、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汉名王天华,1904-1946)、蒙藏委员会“康藏调查员”刘曼卿、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及西康政务委员会之外,青海省政府以及“西康特区汉夷全体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西康总商会”、“西康旅京同乡国防救亡会”、“西康民众驻京代表”马泽昭等西康民众个人和团体,在处理和交涉康藏纠纷事件中,各自发挥了一定的作用②。
(三)事态的扩大及唐柯三调解无效
冲突爆发后,藏军从各地调动兵力,如从贡觉、察雅等地“调来民兵百余人增防,俱系快枪”[4](P439),大举进攻巴塘、盐井等地,康军败退。
1931年2月,德墨、克米两个代本所率的藏军,趁国民政府电告康军停止进攻之机,于9日在甘孜间夜突袭康军,康军失利,溃退至炉霍一带,藏军获胜,兵分二路,一路进逼炉霍朱倭,朱倭土司因与炉霍县政府不睦而投靠藏军;一路沿硅袭江而下,直指瞻化(新龙)。5月,藏军攻占瞻化和理塘县的穹坝、霞坝两地等甘孜藏区的腹心地带,俘获瞻化县知县张楷等三十余人,送至昌都关押。藏康两军形成了在炉霍朱倭、瞻化一线军事对峙的局面。
1931年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决定委派孙绳武、刘赞廷为赴康调解“专门委员”,旋因孙绳武未能成行,春季,蒙藏委员会另行派遣委员兼总务处长唐柯三,作为“国民政府特派调查康藏事宜专员”,前往西康调解康藏纠纷。4月3日,唐柯三从南京出发,一路商议、停顿。6月11日,唐柯三抵达康定,接获蒙藏委员会电告,知琼让已在甘孜县等候谈判。7月8日,唐柯三抵达炉霍县,即致函昌都总管噶伦阿沛,要求“迅即撤退甘、瞻藏军,送回张知事等”,为了“中藏亲善之进行”,“盼早日来甘,商洽一切”[4](P445),唐柯三又派交涉委员刘赞廷前往甘孜。昌都总管复函,云“已派琼让代本先行接洽商筹一切”,“不日即拟前来相会”,又称“将张知县及其眷属等由昌遣回”[4](P445-446)。此函由刘赞廷派人送出后,唐柯三与昌都总管和琼让又多次函商,由于唐柯三坚持藏军退回原防再予调解的原则,琼让等人“借词延宕,始终不肯履行退回原防之约言”,一再更换会谈代表及地点,故而“交涉月余,只允到德格为止,而甘、瞻之兵仍不撤退”[4](P447)。
唐柯三以终无效果,曾经于8月27日致电蒙藏委员会,建议“饬川省速拣精兵数营出关,并利用民兵表示收复决心,再饬滇、青两省武装警告藏军,或不战自退”[3](P179),但此时接连发生军阀石友三之叛、“九一八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忙于东部的外忧内叛,无力西顾。蒙藏委员会指示唐柯三迅速了解“甘案”,息争御侮;而此时,藏军主动释放了拘押的瞻化县知县张楷等三十余人。在这一背景下,11月6日,唐柯三自认为“秉承中央意旨”,“委曲求全”,与藏军代本琼让订立和好条件八款,这就是康藏间的又一起停战协定——“唐琼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有,藏军暂时驻守甘孜、瞻对,并将对俘之川兵放回,川省赔偿藏洋二万元作为补偿。
消息传开,川省、西康大哗,康地民众及旅京康籍学生指责唐柯三迁延半载,草结甘案,昏庸无能,是“割地专使”③,而11月13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亦在电文中对此协定表示“闻之至深骇愕”,多个条款“均属出人意外”,并“电唐(柯三)声明不便赞同,并电东府不得列名签字”[4](P446)。由于川康失望与哗然,兼之,12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改组,石青阳任委员长,于26日电唐柯三“暂勿签字”[3](P240)。藏军也拒绝退还穹霞、朱倭,于是“唐琼协定”形同废纸。
1932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怂恿及唆使下,态度忽转强硬,变本加厉,藏军旋即扩充前线兵力。当时驻康之藏军共七个代本的兵力,四千余人,统归于昌都总管,以琼让、崔科代本部战斗力较强[6](P64-65)。而刘文辉于1931年10月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来,正处于一生的巅峰时期,因而力主武力收复失地。当(1932)年2月,康定的康军哗变,旅长马驌被戕,刘文辉调遣余松琳旅入康平息,驻康的康军实力得以增强。当月28日,经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电告刘文辉“酌派队伍前往西康,维持现状”,并要刘转告唐柯三“暂驻炉城,商承刘总指挥文辉,妥为交涉”[4](P447)。不久,唐柯三为母病请假回京得准后,于4月底启程返内地。唐柯三奉命调处失败,3月2日,国民政府责成刘文辉处理甘案。在1932年8月,刘文辉与刘湘“二刘之战”爆发前,按照刘文辉自己的话说是:“1924年至1932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极盛时代”[7](P3-4),正处于人生政治生涯巅峰的刘文辉得到了中央的同意,迅即调遣康军,积极备战。
二、康藏边界的确定与大白事件的解决
(一)“康藏冈拖暂行停战协议”的签订与康藏界务
在刘文辉调遣康军备战的同时,藏军也在代本厦苏的率领下,有意进攻康军,并分兵向“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马步芳的驻军进攻,开始同时进攻康、青二军。当年3月24日,借口解决青海玉树所属的噶丹寺和得塞召寺发生的土地纠纷,一千多名藏军大举进入青海,占领大小苏尔莽、春科等地。3月30日,康军余松琳旅部下的团长邓驌(或作“邓骏”、“邓骧”)率部进攻藏军,收复朱倭的雄鸡关。4月4日,在青海的藏军不断取得军事胜利,进占囊谦。同月7日,康军收复了甘孜,前锋直指瞻化,战事扩大。
起初,藏军进攻连连得胜,进而围困结古(今玉树)青军,在通天河一带与马步芳部马良臣旅骑兵发生激战。7月,青军反攻,大败藏军,9月初收复了大小苏尔莽、囊谦。之后,青军进而控制了石渠、邓柯等县城。10月1日,“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马步芳,联名致电中央各部门,称“西藏系中国领土,藏人系中国国民,内部鹬蚌之争,徒授外人以渔翁之利”,要求“中央速电达赖确定康藏界限,早日息兵,以安边圉”[3](P298),并做出了青、康联手进军昌都的姿态。
同时,刘文辉部康军亦步步前进。此时康区各地有人枪的实力派,已经公开或暗中被收编、委任为刘文辉部的营长、队长诸职。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以国民党西康党务特派员的身份自称“西康省防军司令”,于1932年2月发动“巴安事件”后,驱逐了刘文辉驻扎于巴安(巴塘)的康军,率领一支康南民兵,既不服从刘文辉驻的康军,又不听从藏军之命令,活动于藏军区域,他们在藏军地盘迂回侧击,给藏军造成了很大麻烦,“使敌无瑕整顿”[3](P261),加速了藏军的溃败,故康军连连取胜。4月底康军克复炉霍,5月,康军克复瞻化。此时,藏军防守甘孜的部队,大多是临时征雇甘孜孔撒、麻书土司之百姓,在康军进攻前夕,大多解散,大金寺僧人亦焚其寺西逃,康军大举反攻,占领了大金寺并再次放火焚烧。7月,康军克复德格,并直接抵达金沙江边的冈拖一带(又写作“岗拖”)。青、康两军两路进攻,奋力反攻藏军,藏军不支,节节败退,溃逃至金沙江西岸,这样,康军得以收复从“民七事件”(1918)以来被藏军占领的德格、白玉、邓柯、石渠等4县,出现了康、藏两军以金沙江为界隔江对峙的局面。
鉴于藏军已呈败局,无力再战;兼之汉康藏各族人民对于藏军把“康区视为致富的机会”而肆意盘剥[8](P181),以及对连年的战争造成的无穷灾害更是深恶痛绝,西藏地方政府只得接受和解,故十三世达赖于7月命令昌都总管派代本琼让前来与康军议和。8月,英国政府向中央政府外交部发出照会,要求康藏双方停战,并提出了一个决议。
9月18日,蒋介石召集川、滇、青、陕、甘五省及蒙藏委员会、外交部、军政部代表,在南京举行“西防会议”,决定康藏停战。而国民党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先后致电蒋介石、刘文辉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建议长驱直入,“最低限度,务恢复民七年(1918年)以前西康范围,俾能完整建省,并调解班、达纠纷,送班回藏”[4](P459)。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及刘文辉、刘湘“二刘之战”已经爆发,蒋介石复电不必多事。由于刘文辉的康军急于与刘湘军队争夺在四川一带的利益,也同意在康区停战[9](P164),放弃了进军昌都。
1932年10月初,川康边防总指挥部派出交涉委员姜郁文、交涉专员邓驌前往德格属下的冈拖(今属昌都江达县)地方,与藏方交涉专员藏军代本琼让(一译“却让”)、交涉委员吉卜议定停战条件。8日,在冈拖东岸的议场,康藏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即“冈拖暂行停战协议”,共六条,规定[10]:主要有:1、康藏双方接受议和协定,弃嫌修好,所有“汉藏悬案听候中央及达赖解决”;2、康军以金沙江上下流东岸为最前防线,藏军以金沙江上下流西岸为最前防线,双方军队,不得再逾前方一步;3、“自中历(1932年)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八日止,双方作战部队,各将先头部队撤退”,“双方各处驻军不得超过二百人,并各派员互相监视撤兵”。此外,协议还对恢复双方商民往来、交通、保护喇嘛僧侣等作了明确规定。
至此,双方达成岗拖协定,康藏双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但是对于引发军事冲突的大白事件如何处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
1933年春,藏军小股部队曾从昌都出发,分兵三路袭击青海玉树,欲夺回春科等地,遭到了青海防军的反击,无果而返。这以后,青藏双方决定议和。6月15日,藏方代表代本索康苏巴、孜仲多吉与青方代表海南玉树宣慰使马驯、李正楷,在交界处的囊谦德扎宫签订了停战、和平协议八款,主要内容是,藏军先退兵,十四日后青海方面亦撤军,所有俘获藏方军民,亦无条件释放;保护双方的商民、寺院;若藏军犯青,则由“藏方昌都、巴(八)宿、类乌齐二十六族头目人等担保”;青海军队犯藏,则由“玉树二十五族头目人等担保”;此后双方各守其地,“和睦如前,西陲国防巩固,国家幸甚,边民幸甚”④。康区、青藏和议既成,康、青、藏三方气氛进一步好转。通过康藏冈拖协议、青藏协议,康青藏三方的纠纷基本平息,青藏维持原状,康藏则以金沙江为界,三地人民之间的正常经济、商贸与文化交流得以恢复。
(二)大白事件的解决
1933年秋,刘文辉兵败于“二刘之战”,率二十四军余部退据雅安一隅,只好全力经营西康。为了站稳脚跟,拓展势力,刘文辉极希望尽早彻底解决大白事件。当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康藏两方一度因甘孜大金寺僧人引发问题而重起纠纷,次年初,康藏两军在邓柯、石渠等地发生了小冲突。
1934年1月底,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热振呼图克图出任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心向祖国,以民族团结为重,由此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出现了“民国以来最为好之局面”[11](P164),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也拟定了恢复大金寺的“善后办法”,这让大白事件的彻底解决成为可能。
当年(1934)5月17日,川康边防指挥部派出的交涉善后坐办、德格县县长姜郁文与西藏三大寺及噶厦代表觉吾向让,针对“上年”即1932年协议对于“安置达结(即大金寺)尚未办结”的现实,“由双方协议”了相关的“安置办法”并正式签订,这就是康藏之间的又一“协议”,即《康藏和好条件十二条》[12]。主要内容是:“达结(即大金寺)未安置前,双方为免误会”而军队各自后撤;“达结寺应委堪布”,由该寺公推取得康方同意后再由藏方达赖喇嘛委任,并由康方“加状委任,只管寺中教务,不能干涉行政及其他事务”;大金寺应该“谨守黄教清规。西康政府对于该寺,与康定各寺,同等待遇,同样管辖”;“自由耕种”“所有土地”并且“按亩纳粮,照章支应乌拉”;西康政府对于大金寺僧民“不咎既往,概许自新,奉公守法,与康民一体待遇。唯不得干犯法纪”等。此外,《康藏和好条件十二条》还对康藏双方“派员督率修复”大金寺、寺中存留枪支数量等做了规定。但是,由于“汉藏文字发生误会”,大金寺僧人代表“乘夜遁逃,复在德格县所属松林口地面,抢劫甘商大宗货物,事态扩大。当时虽仍与藏方不断交涉,因牵涉过多,一时遽难就范”[4](P455);兼之大金寺僧人抢劫并焚毁邓柯县保正泽旺彭措(一译泽翁彭错)官寨,更使大白事件趋于复杂。
1935年1月9日,藏军代本崔科(或译“出科”)与德格县长邱丽生,在德格议定了《安置大金寺僧规约》八条。对于“大金寺庙大殿”的重修、土地的“发还”、僧人的回寺、堪布的推选及任命等问题达成了共识[3](P386-387),满足了大金寺的愿望,进一步缓和了康藏之间的气氛。同年,长征的红军经过西康,诺那活佛所率武装、康军均曾与红军交战,正在解决中的大白事件由此再次暂时停顿。
1936年初,大金寺僧人代表亚鲁大阶、格松德朱、尼玛慈仁等人抵京,向中央政府陈述请求,说明恢复大金寺是“关系数千僧众之安置,为汉藏团结、边防安宁以及整个西陲佛教之安定”的大事[3](P392),获得财政部拨给修葺大金寺补助资金2万元。而同年,“西康建省委员会”移康办公,筹建“西康省”,“为辑睦康藏、安定地方起见,对于此案(‘甘案’,即大白事件)极端重视”[4](P455),并正式着手修葺大金寺。由于尚有为数不少的大金寺僧人滞留于金沙江西岸的昌都一带,所以,西康方面一再向藏方提出请求。至次年1月,返回甘孜的大金寺僧人已有二百余人,刘文辉并“致电昌都札萨索康札萨喇嘛,请其转知流散河西之大金寺僧早行返寺”[3](P398)。
1938年10月21日,刘文辉委派的24军815团团长兼“西康建省委员会特派调解甘案专员”章镇中,从甘孜出发前往康藏前线地区。10月底,章镇中抵达德格县。11月9日,章镇中会同德格县长兼“康藏交涉坐办”范昌元,与大金寺、西藏地方代表汪钦以及西康土司、头人“开始会议”,商量协议“规约办法”,“不意第一次对照规约藏汉文字颇多错讹,彼此争执,莫衷一是。经电陈明,请加修改”,刘文辉予以“指示,另订办法”,“逐日议案”,“反复协商,讨论不欠求详,折衷务得其当”,“历时两月,始告完成”。12月30日,康藏双方就达成的“安置良善大金寺僧规约详细办法”七条,在共同认可后,“当场公布,签字结束”[4](P455)。“办法”主要内容是:第一,“修复大金寺”,由甘孜县政府代雇民众150人,每人每月发给工资藏洋11元;第二,以前划入白利土司的朱倭、林葱、骨老隆三村,“一律收归县府直接管辖,专设一区,由县长兼任区长”,对于“该区内一切政务”,大金寺、白利土司“一律不得干预”;第三,“藏方发给大金寺枪弹,由藏方悉数收回”,“倘有隐匿不缴者,查出枪弹一律没收。大金寺僧回籍渡河(指金沙江)时,由康藏双方代表监视检查,并实行登记人枪子弹数目”;第四,规定“大金寺及大金寺僧与其他各方面之手续,候大金僧返寺后,依合法方式解决”[4](P453-454)。在孔撒、白利、朱倭等土司,甘孜等寺代表监督具结情况下,共同签字,保证弃嫌修好,大金寺代表亦表示永不滋事,若有违犯,愿受地方官府依法治罪⑤。
1939年1月2日,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所派代表索康·旺钦格勒,与西康省政府方面的章镇中、范昌元又议定《安置大金善良寺僧详细办法》七条[13],事后,西康省政府报呈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称:岗拖停战条件后,“民七部分失地得以收复矣。关于安置大金僧民,因事体繁重,与藏方往复磋商,未有结果”。而从“安置良善大金寺僧规约详细办法”签订以后,所有大金寺僧众“遵守规约”,从昌都渡江返回甘孜原寺;“藏方因本案已告结束,表示满意,原驻金沙江两岸藏军除少数维持交通外,余皆撤回昌都;我军(指康军)亦撤回甘孜,双方相见以诚,从敦旧好”[4](P454-455)。
至此,由“大白事件”引发的第三次康藏纠纷,在康藏双方发生多次军事冲突,经由中央政府专员及多方调解,和双方多次谈判和反复交涉,在历经十年之后,终于宣告顺利圆满地解决。康藏双方的人员往来、民族关系得以恢复正常。当时中央社记者刘尊祺,为此事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康藏关系新纪元》的评论文章。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以金沙江为界,康藏双方人员往来、民族关系正常进行,未再发生纠纷。
三、余论
“大白事件”,本是西康地区世俗势力、宗教势力的利益之争,属于地方事务,不幸导致康军与西康辖境内藏军发生武装冲突,随之升级为“第三次康藏纠纷”。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藏军发动了第二次东攻,并且还与青海马步芳部发生战斗,使这次纠纷,演化为三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且中间小冲突不断;随着1932年“巴安事件”、1935年“诺那事件”与红军入康、1935年大金寺僧人“在德格县所属松林口地面,抢劫甘商大宗货物”以及抢劫并焚毁邓柯县保正泽旺彭措(一译泽翁彭错)官寨等,更使大白事件趋于复杂。
其间,英帝国主义出于英印及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怂恿西藏地方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势力,对抗毗邻各省区,如驻亚东的英国商务委员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就直言不讳:每到汉藏发生争执时,我总是乘机挑拨汉藏关系[14](P36)。在这一背景下,英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不断增加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援助,如锡金政治长官古德(Basil Gould)坦白地说:“自从德格被汉人占据以后,对东藏军队的供应变得非常困难了”[15]。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又欲以调解人的幌子出面干涉,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回复以“康藏战事为中国内政问题,无接受斡旋之必要”的同时,也向十三世达赖表明:“汉藏问题纯属内部事务,现为国民政府时期,绝不允许他人插手干涉”,“内部事务,可经内部协调逐步解决”[3](p303-309),向贡觉仲尼表明,“西藏为五族共和之一,无异一家骨肉”,“万勿轻信他人挑拨谣言,趋走极端,徒授帝国主义者侵略之机会也”[3](P283),并安抚说“素稔达赖佛爷(十三世达赖)深明大义,必能仰体政府扶植边民主张和平至意,有以解除康藏人民之痛苦也”[3](P68),维护了主权不容外来势力干涉原则的同时,顾及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
经过中央政府多次调解,各方势力不断介入与努力,康藏双方多次谈判和反复交涉,历经十载,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宣告结束。可谓“以大金白利争产细故,酿成重大纠纷,康藏因而失和,国家亦受其累”,康藏数年的军事冲突,“耗帑巨万,而人民之损失,官兵之伤亡,更无论矣”[4](P455),对于康藏双方人员的往来、民族关系之间的正常交往,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在康区等民族地区,任何事件都应从快解决,化解矛盾,否则小事变大,时间越久则解决难度越大。由此,也证明了“民族、宗教无小事”论断的合理无误。
在这一历时久、涉及多、过程复杂的康藏纠纷事件的解决中,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达赖喇嘛及西藏驻京办事处、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青海省政府、西康政务委员会、西康民众团体、中央特派专员等,均有所贡献,可以说,各方面的相互了解也在客观上得以加深,康藏、藏汉民族感情自然亦得到了强化。
审稿 顾祖成
注释:
①如1931年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致蒙藏委员会电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②见《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及《康藏纠纷档案选编》的相关部分,有各方运动和平电文;报告大金、白利发生纠葛经过情形文件;有关藏军与川康边防军、青海军队交战情形文件等。
③《康藏纠纷档案选编》,第209页;《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第447页。唐柯三归来后,在《西康日记》(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4年版)中对自己的调解行为予以了辩解。
④关于青海西藏停战和议条文内容,可参见方范九:《青海玉树二十五族之过去与现在》,《新青海》第1卷第3期,1935年。以及刘绍塘:《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02页;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9页;《康藏纠纷档案远编》。
⑤1938年10月,路过德格县的汉僧邢肃芝(法号碧松、藏名洛桑珍珠)在这次会谈开幕日拍摄了唯一一张照片。见邢肃芝口述、张健飞等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96、98-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