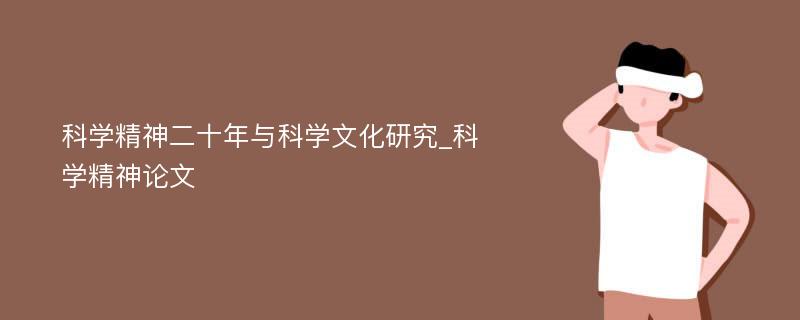
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研究二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科学文化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2)01-0088-07
从1980-1981学年作硕士论文“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1]起,我或多或少地研读了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的科学哲学著作,对他们关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的论述略知一二。也许在当时,我就不知不觉地在心里埋下了日后研究它们的种子。
翻译R.K.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2]一文,是我关注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问题的肇始,其时乃1982年春。该文揭示了科学的四条精神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这是中国学人常常引用的观点和文献。1984年9月完成的《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3],集中展现了作为二十世纪科学代言人的爱因斯坦的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审美精神(美学精神)。其后两年间,我先后在《北京科技报》发表了数篇介绍性和评论性的短文[4]——<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探索的动机>、<科学创造的心理机制>、<科学本身的三类功能>、<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上、下)>其中都涉及到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这一主题。
1985年完成的《科学的革命》[5]是一部科学哲学和元科学研究书稿。由于该书一时难以出版,其中两章分别以<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6]、<科学革命的实质和科学进步的图像>[7]为题于翌年面世。前者论述了实验(含观察)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各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促成了科学的“自己运动”,并讨论了内部运动作用的机制和科学家的探索动机。后者指出,科学革命是科学观念——科学理论的基础或框架——急剧而根本的改造,其改造形式有彻底取代、旧名新意、合理推广、辩证综合。包容蕴涵、标新立异,并描绘了科学发展的“进化—革命”图像。其间,我还发表了<评爱因斯坦的科学观>[8]。这些论著都属于科学文化研究的范畴。
1987年问世的两篇论文径直进入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的堂奥。<科学家的科学良心>[9]揭示了科学的本性和真善美架构;科学之真表现为它的客观性、自主性、继承性、怀疑性;科学之善表现为它的公有性、人道性、公正性、宽容性;科学之美表现为它的独创性、统一性、和谐性、简单性。同时探讨了科学家内心对科学研究中的各种涉及到伦理道德方面的是非的正确认识,亦即科学家的科学良心。该文后来以“科学与精神文明建设”成为《科学的革命》的第十二章。<科学解释的历史变迁>[10]依次论述了古代的拟人说、近代的机械说、现代的嵌入说解释;文章评论说:“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本来具有天然的同盟关系。但是,在拟人说解释中,人与自然的同盟是以扭曲的形态出现的,实际上是用神性排斥人性,造成科学与人性的分离。机械说解释虽然削弱或驱除了科学中的神性,但同样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同盟,进而形成了两个世界、两类科学、两种文化。现代科学和嵌入说解释正在把二者统一起来,建立人和自然的新同盟,沟通人与自然通信的渠道,从而使科学具有人性,人性具有科学性。”
1988年初发表的颇有影响的短文,明确揭示了科学的怀疑、平权、多元特征,并以此为根据主张打破一贯正确、惟我独优、一元化的旧思维定规,采取怀疑批判、科学平权、多元化的新思维方式。[11]是年面世的两篇重要论文是<关于科学发现的几个问题>[12]和<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为什么发端于德国?>[13]。前者讨论了科学发现的起点、逻辑、心理机制,科学美、科学启迪与科学发现,科学革新家的精神气质等问题;后者讨论了十九世纪德国科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科学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伦琴、普朗克、爱因斯坦是如何成为科学革新家的。此外,我在当年还发表了<创造性科学思维中的意象>、<在哲学与科学之间>二文[14]。
1989年3月24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在北京召开了“民主、科学与中国现代化”专题学术研讨会,我为会议提交了<把民主何科学精神变为国民的自觉意识>的短论[15]。该文明确指出:“科学精神集中体现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的精神气质(ethos)之中,其首要者乃是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借用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话来说,科学的理性精神的精髓‘并非在于它对原则问题毫无异议,而在于从来不是毫无异议;不在于固守驰名天下的公理,而在于不把任何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科学的实证精神也许集中体现在这样的观点上:科学力图按照宇宙的尺度而不是按照人的尺度来看待世界。……因此,以理性为先导、以实证为根基的科学是一个‘三无’世界——无偶像、无禁区、无顶峰。要知道,任何社会的最大危险莫过于盲目自信,而以理性和实证珠联璧合的科学怀疑精神正是盲目轻信的有效解毒剂,这才是科学之价值的深层意蕴。”文章还表明,纯粹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地看待科学,“无异于现代的货物崇拜(cargo cult),它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追求真知、追求智慧(wisdom)的科学形象,泯灭了科学精神的弘扬”。
翻译《科学的智慧》[16]激发了我集中研究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的热情。在1989年4月7日撰写的译者序<什么是科学?>[17]中,我点明:“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身居权力顶峰和知识山巅的权威人士和知识精英,也往往只注意到科学对社会的‘形而下’(或曰‘器物层次’)的作用,而低估乃至忽视它的‘形而上’(或曰‘观念层次’)的作用。于是,人们把科学简单地等同于技术,把科学看作是装着精巧戏法的盒子,能变换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强调:“人们长期以来把科学的社会功能仅仅局限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福利方面,至多只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客观的、严密的静态知识体系,而很少看到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的精神气质——言以蔽之曰科学的智慧——对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作用,对于提高社会精神文明和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的作用。”在传达了布朗教授的新颖见解——科学是智慧而不是知识,科学最有价值的“用处”就是获得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而且人种的‘永存”也取决于智慧的获得——之后,我随即指出:“可以设想,随着‘科学即智慧’的思想深入人心,肯定会对社会的精神生活、人的现代化、人才教育和培养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此外,我也揭示出,功利主义的泛滥,“使得不能‘立竿见影’地获取‘经济效益’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受到某种歧视和冷遇”。
1989年夏至1990年春的十个月时间,我专心致志地研究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课题,其成果在日后两三年陆续发表。1990年5月,我为《科学论译丛》之一的《科学方法讲座》[18]写了题为<应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的代总序,该文的摘要首次在10月23日的《科技日报》与读者见面,后来全文被数次转载[19]。该文表明:“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科学精神恰恰也与之对应地体现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气质这样三个方面上。”文章接着论述了科学精神的各个方面:“科学思想是科学知识体系的精髓或精华之所在。大凡科学思想都具有革命性:它能扩大人们的视野,开阔人们的胸怀,启迪人们的心智。它是愚昧的天敌,教条的对头,迷信的克星。科学思想同时也为人们观察和分析问题提供了基点和视角——此即所谓“科学的透视”,……这是科学思想革命性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革故和鼎新。……科学思想的革命性还表现在它的自我批判方面。与艺术不同,科学在某种程度总是毁灭自己的过去。自我批判是科学的生命,自我批判不是科学没落的征兆,而是科学进步的标志之一。自我批判终止之日,就是科学发展停滞之时。”“科学的统一不在于它的材料,而在于它的方法。科学精神也集中地通过科学研究活动中所运用的方法体现出来。……科学的三大类方法即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显示了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审美精神,它能够潜移默化地使人们树立求实、尚理、爱美的思想情操。尤其是,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的鲜明标识.是科学的精神价值最根本的构成要素。”至于作为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和道德理想的科学精神气质,它“不仅是维护科学共同体稳定秩序的基石和科学发展的保证,而且也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的大目标是相通的或一致的。”文章顺便批驳了当时在中国刚刚露头的反科学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反科学思潮没有看到科学的深层涵义即科学精神,这便为商品社会中极端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科学精神正是上述各种极端‘主义’的有效‘解毒剂’。”文章最后强调:“科学精神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体,科学的精神价值是无法用数量衡量的最高意义上的价值。只有使科学精神变为国民的自觉意识,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才不会仅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也是人的现代化。”
我在1990年代伊始发表的比较重要的论文中,<关于科学和价值的几个问题>[20]点明了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值得探讨的三个方面:科学的价值,科学与社会价值观念的互动,科学中的价值。论文着力探讨了后者。关于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价值,主要包含在科学基础、科学陈述和科学解释之中;而且,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也体现了真善美价值——这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关于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价值,集中渗透在探索的动机、活动的目的、方法的认定、事实的选择、体系的建构、理论的评价之中。关于科学社会建制中的价值,在维护科学的自主性、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对研究后果的认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均衡、科学资源的分配与调整、科学发现的传播、控制科学的“误传”、科学成果的承认和科学荣誉的分配、对科学界分层的因势利导之中明显体现出来。论文最后提出了科学价值即是人的价值的命题:“科学共同体具有直接的共同目标——探索真理。它必须促使单个科学家是独立的,促使科学家群体是宽容的。从这些基本前提——它们形成了最初的价值——逐步得出一系列价值:异议、思想和言论自由、公正、人的尊严和自重。这就是科学所塑造的人的价值,而且有这种价值的人,又大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而使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科学和人正是在这种张力和互动中丰富起来、完善起来的。”<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21]论述了我稍后命名为“哲人科学家”——他们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的小群体的定义、特点和作用。我明确指出他们是人类思想史上路标的设置者,沟通科学与哲学的桥梁,科学家和哲学家联盟的纽带,两种文化的承载者和缔造者,科学的人文主义者。我在文末提醒读者注意:“当前,科学的扩张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加强了,每一门科学的分支都变得非常众多、非常狭窄、非常专门、非常深奥,对于仅有有限融合贯通能力的科学家来说,要对科学的全貌(更不必说对整个人类文化了)有大略了解也是相当困难的。而没有这样的了解,不仅真正的科学精神会受到损害,而且也会使科学家本人丧失广阔的眼界,沦为一个匠人的水平。”<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22]对该思潮作了简要的解剖,并提出了反对它的五条理由,这是国内较早抨击反科学主义的文章。
我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较多。<科学价值中性的神话>[23]列举了科学价值中性论的三个含义(科学不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科学成果在价值上是中性的,科学认识是价值中性的),并对其分别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评。科学之所以渗透价值,其原因主要在于,科学是人的科学、历史中的科学,而不是超人的、超历史的,它必然要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作为科学认识主体的科学家是有血有肉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他们必然有选择、有偏爱。该文在讨论了科学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后认为:“科学并不是价值中性的,而是包含着价值判断和价值因素。但是,这种价值联系并没有动摇科学客观性的基石,它仅仅是科学的一个从属的组成要素而已。而且,科学的这种价值相关性并不是科学的缺点,毋宁说它是科学的深远意义之所在,因为它作为一条有机的纽带,把科学与整个人类文化联系起来了。”<论科学的精神价值>[24]首先指明,科学的真谛在于,它是人类精神的成就而非物质技术的成品,是人类文化的最独特的果实。接着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科学的精神价值: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具有信念价值、解释价值、预见价值、认识价值、增值价值、审美价值;科学作为研究活动,其精神价值在这种活动的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中充分体现出来,特别是三大类科学方法所蕴涵的精神价值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科学作为社会建制,其固有的精神气质内化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外化为公众的科学的心智框架,从而直接有助于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科学的新浪漫主义批评家的最大误区恰恰在于,他们忽视、漠视乃至无视科学的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25]是我向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完稿于1989年10月。该文从语言哲学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了科学革命的深层结构和科学发展的内隐真相,严密地论证了下述观点:科学革命是科学“词典”的重新编纂,导致科学革命的科学发明实质上是“语言游戏”,科学革命促使科学共同体的“生活形式”(日常生活形式和超体生活形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是年发表的几篇短论中,<专家政治得失谈>[26]认为专家政治(技治主义)虽然优于官僚政治,但也有重大缺陷: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社会工程)知之不多或一窍不通,易于滋长重物不重人的倾向,打上了机械决定论的烙印。未来的最理想的政治模式应是通才政治。<科学和伦理>[27]论述了二者的关系:科学对伦理规范的评价和决定不能起直接作用,但间接影响却是相当大的。尤其是,能够通过激发人的天然存在的情感或使人产生新的情感,逐渐形成一种职业性的感情心理,从而使人的灵魂得到更新,使社会的伦理规范日臻完善。只要科学和伦理处于前进之中,他们二者之间肯定会相互适应。<基础研究及其社会意义>[28]在简要论述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区别后,着力阐明基础研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方面的意义。文章最后强调指出:“如果说在控制应用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科学对社会所负的责任的话,那么在控制基础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社会对科学所负的责任。要求所有的研究都应该与我们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这种流行的要求表面看来是公正的、善良的、无害的,实际上对科学进展来说却是最大的危险之一,从而对于社会需要的长期满足来说也是最大的危险。”
接着的两年,我就该课题发表的文章不多。<科学理论的价值评价>[29]在讨论了事实评价面临的七大困难(由不充分决定、逻辑困境和事实评价的现实困难引起)之后,重点论述了价值评价——社会价值评价、个人价值评价、理智价值评价——的必要性和八大特点,以及彭加勒、爱因斯坦、邦格、库恩、雷斯彻的理智价值评价标准。最后,分析了对科学客观性的各种“拯救”,同时批评了所谓的客观主义和神目观:“总之,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客观性,而不是在人类之外的所谓客观性(这样的客观性根本不存在,因为客观性是相对于主观性而言的)或客观主义。客观性使科学真正成为科学,而客观主义则使科学非人化和非人性化,从而实际上取消了科学。要知道,没有人就没有客观性,即使以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也是人为的和为人的。”在<爱因斯坦的科学信念>、<爱因斯坦的科学创造个性>和<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30]中,我从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的主将爱因斯坦身上看到了现代科学的深邃的精神气质、丰厚的文化意蕴以及与人类文化的其他分支的关联。
从1993年初到1998年初的五年间,我连续为傅伟勋、政通教授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撰写了五部专著——《彭加勒》、《马赫》、《迪昂》、《爱因斯坦》、《皮尔逊》[31]。这五位伟大人物都是哲人科学家,是科学精神的化身和科学文化的代表。在《彭加勒》中,我论述了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和综合实在论的丰厚圆融的观念多元性和文化包容性,特别是在他的科学方法和发明心理学中所表露出来的美的旋律和创造的神韵。在《马赫》中,我从科学文化的视野揭示了马赫经验论的丰赡的哲学内涵和绝妙的思想张力,以及思维经济原理的深远意蕴、微妙真谛和精神实质——科学的目的、方法论的原则、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反形而上学的武器、知识(认知)的生物经济学。同时,我也阐释了马赫的社会哲学、人文关怀和社会实践。在此基础上,发掘出哲人科学家马赫和马赫思想的精神气质——启蒙和自由、怀疑和批判、历史和实践、兼融和宽容、谦逊和进取。在《迪昂》中,我描绘了迪昂在坎坷中走向逻辑永恒的人生历程,在科学与宗教、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显现的鲜明的人性和个性,即帕斯卡所说的“精神的伟大”(思想)和“智慧的伟大”(仁爱)。尤其是,探讨了迪昂的颇有文化意义的科学史观、编史学纲领、科学史的价值(认知价值、方法价值、教学价值、平衡价值)、对人类精神的壮丽探险。我在书中这样写到:“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时,科学、哲学、宗教、历史之间的关系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探究,迪昂及其著作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范例和思想源泉。未来的新世纪是一个科学文化人文化、人文文化科学化以及两种文化融会的时代,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于一体的迪昂无疑会再度复活,为人们所青睐。”皮尔逊是一位集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精通或研究的科目和领域令人眼花缭乱。在《皮尔逊》中,我再现了他作为两种文化承载者和缔造者的形象。在该书“后记”中,我还这样写到:“说起来也是令国人难堪的:五四运动至今已八十年了,但是先贤和先哲们当时从西方请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却始终未能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和国人的意识里生根。时至今日,上自国家巨头,下至平民百姓,几乎都把科学视为‘财神爷’,把民主主义视为民本主义(‘民惟邦本’)。作为一种文化和智慧的科学就这样被消解为发财致富的工具,科学之道沦落为技术之用——这实在无异于买椟还珠。”
爱因斯坦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典范。在《爱因斯坦》中,我除了展示作为科学家和思想家的爱因斯坦之外,着力刻画了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爱因斯坦。从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的意义在于:他的科学贡献大大变革了人们的时空观和世界观;他的具有独特而微妙的多元张力的科学哲学,他的包罗万象且洞察明澈的社会哲学,他的对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充满明睿洞见的人生哲学,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注入了崭新的因子和酵素。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成为追求真善美的使徒,显示出独立的人格、仁爱的人性、高洁的人品。在这里,我只想提及一下爱因斯坦科学工作中的最富有文化意义的科学美和宇宙宗教感情。爱因斯坦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科学的艺术家,具有根深蒂固的臻美情结,他的科学理论本质上在于其艺术性,他的科学方法的最鲜活之处在于臻美取向和审美判断。对美的追求不仅是他进行科学探索的动机和动力之源,也是他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之一——准美学方法,这一科学方法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科学创造的全过程(提出问题、发明原理、评价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展现出美仑美奂的观念之美和结构之美——对称美和奇异美的天衣无缝的结合。爱因斯坦具有强烈的宇宙宗教感情,宇宙宗教不仅是他的科学探索的最强有力的动力和最高尚的动机,而且也形成他的“宇宙宗教思维方式”。宇宙宗教思维“能透过现象与实在神交,直接导致灵感和顿悟,从而触动直觉和理性,综合而成为科学的卓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与此同时,这种思维方式所运用的心理意象和隐喻、象征、类比、模型,径直导致新的科学观念的诞生。”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杂交的奇葩,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这里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在此期间,我除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评图奥梅拉的科学观>、<评皮尔逊的科学观>、<论科学中的语言翻译>[32]外,也密切涉及到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主题。在1995年2月14日为《科学巨星丛书》写的总序[33]中,我指明:“科学的研究进路和规范结构或明里约束强制,或暗中潜移默化,从而逐渐滋养和塑造了科学家的‘生活形式’乃至‘集体无意识’,使他们在总体上形成卓尔不群的美德和超凡脱俗的品格。”在这里,我明确倡导“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理解科学价值”。紧随其后的<对科学的人文理解>、<发掘科学的深层底蕴>、<科学家: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者>[34]进一步重申了我的观点。接着,在<科学精神与人的价值>[35]的短文中,我把科学精神定义为“科学的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把人文精神定义为“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最高展现”。在简要分析之后,我得出结论:“科学和人文尽管在关注的对象上乍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和深层底蕴上则是相通的和互补的。……科学价值在某种意义即是人的价值,科学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文精神。”我揭示了两种文化被人为地割裂的原因:“这里既有所谓的科学主义的偏激,也有人文主义的偏见;尤其是社会和公众片面地看重和强调科学的技术应用、经济效益和功利价值,而忽视或漠视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其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非水火不相容,冰炭难同炉,它们早就在优秀的哲人科学家身上得到双重完美的体现。”反观国内,“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发源地,也未直接经受科学革命和科学文化的洗礼,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没有西方科学精神以及民主、自由精神的融会,中国新文化的重建就难以成功。因此,国粹派和后现代派的合流在中国滋生的一小股反科学主义思潮,是不明智的和不合时宜的,在学理上也是难以立足的。”我在《中国科学哲学论丛》的总序中也强调,要加深“国人对于作为一种智慧和文化的科学的再认识,加快科学精神注入国人的意识乃至潜意识,加速科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补苴和改造,重建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新人格。”[36]至于访谈录<探索科学的人文底蕴——访李醒民研究员>[37],则是对我在1989-1990年间十个月研究成果的小结。
步入二十一世纪,我发表了<五四先哲对科学的多维透视>[38]。五四先哲“对科学的内涵、外延和特质的认知,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全面审视:强调其精神价值,对科学精神的深入剖析,对科学方法的重视与探究,对科学文化意蕴和文化影响的探索,对反科学思潮的辩驳”,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由于五四先哲能与当时西方的先进科学思潮‘接轨’,尤其是从世纪之交科学哲学和科学观的高峰(批判学派)那里汲取了思想营养,因而他们的见解在当时是相当‘现代化’的。”反观今日之域中,科学被许多人仅仅当作工具,“从而消解了科学的本真,泯灭了科学精神。”对这个问题的更为详尽的阐述,则发表在长篇论文<“五四”先哲的睿智: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上、下)>[39]之中。
人贵有自知之明。老实讲,我对科学精神乃至科学文化的研究用时不多,取得的成果也是初步的。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99年春翻译完批判学派五位代表人物的七本科学哲学名著后,立即捡起十年前临时终止的课题,全力以赴地研读有关科学元探或元科学研究(sciencestudies)——这是比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更加广泛的论题——的外文论著。迄今已翻阅了百余种书籍和论文(恕我孤陋寡闻,说实在的,国外不但没有直奔主题的关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的专著,甚至也没有这样的论文,有关的论著往往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记下了120多万字的翻译资料。尽管如此,我心中仍是一团混沌,还没有一个明晰的构想和妥当的框架。我打算再研读一段时间,把记下的资料从头到尾细看一遍,列出索引,拟好提纲,再动笔撰写。眼下实在是心中无数。我“羡慕”有些人真有能耐,一本书也不读,一点资料也不记,就能把课题申请表填得天花乱坠,赢得基金会主管的青睐,把大把大把的钞票装进腰包后,最终却拿不出一点象样的东西来。
二十年的研究炼狱,不仅出了一批学术成果,而且也磨炼了我的精神和意志,塑造了我的人格和生活形式。对于学术研究中的酸甜苦辣,我有以下感触和切身体会:
一、学术研究是一个必须下苦功夫的行当,来不得半点机巧和浮躁。要在一两个问题或领域有所建树或取得突破,十年磨一剑似乎还嫌不够,往往得摊上二十年、三十年乃至整个一生的工夫。四面出击,八方奔走,大轰大嗡,恣意爆炒,除了浪得“各领风骚三五天”的虚名外,对于学术进展和文化积累而言实在于事无补。
二、学术研究无热点。在真正的学人看来,学术无所谓阴晴冷热,研究无所谓轻重缓急。你看准一个题目,认为它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就稳坐钓鱼台,埋头做下去,“香茗一杯思絮远,任尔东南西北风”,肯定迟早会有收获和突破。所谓的“学术热点”,往往是一些假问题。即使真正的学术问题,一旦被人为地炒成“热点”,那就必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顿失其应有的学术意义,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学人还是暂时远离或保持沉默为好。至于那些追逐热点者,自然会捞到不少浮名和实惠——对于热中于此道的人来说,这正是他们的目的和归宿——但却不能把学术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
三、学术研究不是宣传。针对某些问题或某种现实,学人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配合普及者做点宣传是有意义的,也是学人应尽的社会责任。但是,学人应有广阔的视野,而且必须把宣传建立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否则宣传只能是人云亦云,老生常谈,也无法为普及者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和思维空间。以近年在社会上大力宣传科学精神为例。作为学人,应该看到,这决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一两个具体问题,而是为了提高国人的科学文化素养,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加速思想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是比物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更为根本的现代化。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相当一批学人既不研读国外的有关文献,也不汲取五四先哲的思想遗产,仅凭一点观感、随想乃至道听途就,就四处抛头露面,恣意夸夸其谈。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有失学人的水准。比如说,在“新世纪初”由“我国学者”撰写且即刻出版的《论科学精神》一书,并不像封面自诩的那样“深入系统”,其整体的学术水平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四、学术研究有苦也有乐。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且有点清贫的事业,要作出像样的成果,非全身心投入不可,而且要连续地投入;此行当也不可能涌现腰缠万贯的富翁或大款。入此门者务必要有心理准备,否则还是及早改换门庭为好。不过,苦中也有乐,正所谓“痛并快乐着”。这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当你遨游在思想的海洋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之时,你能不心旷神怡,羽化登仙?其二是,当你的研究成果问世之时,望着散发油墨香的新著(尤其是它是一部新意迭出、文采斐然的新著),你能不感到苦尽甘来,乐在其中?其三是,当你在学术研究中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进入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境界时,你能不如醉如痴,乐此不疲?此时,学术研究已成为你的最心爱的精神憩园和最惬意的安身立命之所——对学人而言,这就足够了!
〔作者附记:此文完成后一月有余,我的第一本论文集《科学的精神与价值》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10月出版,全书共522页,包含上述参考文献中的部分论文〕
〔收稿日期〕2001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