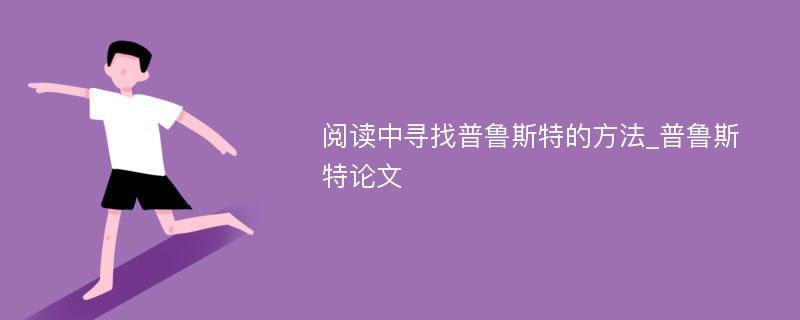
寻觅普鲁斯特的方法——论阅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特论文,普鲁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作品的阅读,按照普鲁斯特的说法,是“以死者或不在场的人为对象”(注:马塞尔·普鲁斯特《阅读的日子》,选自《阅读的日子》,10/18丛书,1993年,第48页。)的活动,它的意义究竟何在?这项苛求的活动向我们索取作为生者最为宝贵的财富:我们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我们全身心的投入。我们同人物一道欢笑或哭泣。有时我们也会为那些夺去了我们许多宝贵时间却未能提供所期待的快感的作品而感到失望与恼怒。然而我们知道,在此应责备的不应是他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对作品的选择。不幸的是,不经过细致入微的阅读,我们无法知道一部作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无论如何,在这一极其耗时耗力的活动中,没有任何确定无误的报酬与收获可以期待。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我们是否能够使死者起死回生。如何才能使这一看似徒劳的活动成为有益有利的经历?
且让我们换一种乐观些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一部文学作品也许是一件特殊的物品——一座希望之墓。它具有物的特性,文学世界不是抽象的,而是生动可感的;它是一座希望之墓,因为对某些人,它不再是个死者的居所,而成为一扇门或一道门槛,它把人引向他方,引向他的内在世界,并由他来实现使死者复活的奇迹。也许对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一部独特的作品,就像马德兰点心对于马塞尔生活中某一时刻是意味深长的一样。在他与马德兰点心之间存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神秘关系。正是这普普通通的点心引起了他的不自觉的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整部作品。而这部对我们意味深长的作品,也将把我们引向文学与生活的秘密,引向我们自己的文字生涯。它将使人们豁然开朗,处处遇到自己所熟悉的思想,文学的大门奇迹般地向我们敞开了。然而这部作品究竟在哪里?那不寻常的相遇何时发生?
在《论福楼拜的“风格”》(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选自《驳圣伯夫,以及仿作与杂文,论文及评论》,伽里玛出版社,1971年,第595-596页。)(1920)一文中,普鲁斯特写道:“我感到我们不再懂得阅读。”是否存在一种有效的阅读方法?普鲁斯特这位伟大的读者与作家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答案。这里我想通过他对福楼拜这位他并不十分喜爱的作家的阅读理出他的阅读方法。
普鲁斯特在文章的开头指出:“鉴于一些在此无法充分展开的原因,我相信只有隐喻能够赋予风格某种永恒的东西,而在全部福楼拜的作品中可能没有一个美丽的隐喻。”接下去他继续说道:“隐喻并非风格的全部。”因此如果在福楼拜的作品中没有普鲁斯特所看重的隐喻,我们仍然能够欣赏构成福楼拜风格的其它成份。这便是对普鲁斯特而言阅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辨别出一位作家的独特性与独创性。
在一篇题为《关于文学与批评的笔记》(注:马塞尔·普鲁斯特《关于文学与批评的笔记》,同②,第303页。)的文章中,普鲁斯特这样声称:“当我阅读一位作家时,我很快辨认出话语之下那使一位作家不同于另一位作家的歌子的曲调……”但如何辨别每位作家的独创性,通过直觉——一种先天的善于在瞬间把握隐蔽的内在关系的敏感?通过模仿——去写一些自觉的仿作?还是通过思辨——对作品进行细节分析并归纳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而这一切是否构成了阅读的最终目的?这是我们要在本文中一一澄清的。
对于普鲁斯特而言,是什么构成了福楼拜的独创性与独特性?他把它概括为“一种语法的美”(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选自《驳圣伯夫,以及仿作与杂文,论文及评论》,伽里玛出版社,1971年,第587页。),并称福楼拜为“一位语法天才”(注:《关于福楼拜的补充之言》,同②,第299页。)。更确切地说,这种语法的美来源于“对动词时态、介词、副词的新用法”(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选自《驳圣伯夫,以及仿作与杂文,论文及评论》,伽里玛出版社,1971年,第589页。)。在普鲁斯特看来,这是一场根本性的革新,它在《情感教育》中得以完成。普鲁斯特不止一次提到《包法利夫人》一书的最后一句话“他刚得到十字勋章”,认为这还不是真正的福楼拜的语言,因为它仍流露出某种直接的抒情与嘲讽的东西,而这正是福楼拜在其创作发展中所要消除的。实际上作者借此表达了对资产者社会中实用主义的胜利和缺乏诗意的现实的苦涩的嘲讽。如果我们回首作者的早期创作,比如在1945年版的《情感教育》中,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表达艺术家的自我欣赏及与社会的格格不入。他也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随后,在福楼拜的作品中,作者不再通过人物或叙述者直接或间接的话语来表达他对实用主义及缺乏诗意的现实的无情嘲讽,而是把他的愤世嫉俗转化成对小说艺术的刻意追求,通过热情而勤奋的工作以达到美好的风格——那转化了的与作为材料的语言融为一体的智慧。在普鲁斯特看来,这便是福楼拜的独创性之所在。他这样说道:“这一精力的转换,由此思想者让位于缓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不正是作家走向风格的最初的努力吗?”(注:马塞尔·普鲁斯特《关于风格的评论》,同①,第167-168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作为个人的福楼拜向作为小说家的福楼拜的转化。或者说,从生活向艺术的转化——个人的直抒胸臆或冷嘲热讽让位于小说家对作品的营造。思想者的隐退也许是福楼拜的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由此福楼拜的风格得以确立。
让我们回到属于福楼拜的语法的美和他的根本性的革新上来。表面看来,这不过涉及到语言的一些纯技术性的方面,动词时态、介词与副词的用法。普鲁斯特列举出一些“一位出色的小学生都能更正的错误”。然而正是由于这番技术上的创新,福楼拜完成了一场“可能同康德把人对世界的认识的中心移入心灵同样伟大的革新”(注:《关于福楼拜的补充之言》,同②,第299页。)。由于其独树一帜的用词法,“那直至福楼拜一直作为动作的变成了印象”(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选自《驳圣伯夫,以及仿作与杂文,论文及评论》,伽里玛出版社,1971年,第588页。),并且“这些语法上的离奇用法”揭示出“一种新的眼光”(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选自《驳圣伯夫,以及仿作与杂文,论文及评论》,伽里玛出版社,1971年,第592页。)。
如何理解“动作变成了印象”?这一“新的眼光”由何构成?在福楼拜的小说中,普鲁斯特注意到未完成过去时常被用来表现人物,而简单过去时则被用来表现事物。然而习惯上,未完成过去时表明事物的状态,简单过去时表明人物的动作。这便是福楼拜在小说中实现的关于人与事物的现实的根本倒置。仿佛人不再行动,而事物自动,并且人的精神承受事物的涌现及其影响。普鲁斯特十分重视事物的这种自发性的显现:
事物并非作为故事的附属品而存在,而存在于它们显现的现实中;它们常常是句子的主语,因为人物并不前来干预,反而承受其眼光……甚至于当被再现的对象是人物时,由于他是作为物品而被认知的,那显现的被描述为正在显现的,而不是作为意识的产物。(注:《关于福楼拜的补充之言》,同②,第299页。)
福楼拜打破了传统的以人物动作为主体的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因果链条。正是由于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动作的原因无从得知,而使动作成为印象,“因为正是推理在事后赋予所有视觉现象以外在原因,然而在我们得到的第一印象中,这一原因并不包含在其中”(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选自《驳圣伯夫,以及仿作与杂文,论文及评论》,伽里玛出版社,1971年,第588-589页。)。普鲁斯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包法利夫人想到火边取暖。书中这样写道:‘包法利夫人(作者不曾在任何地方讲过她感到冷)走近壁炉……’”(注:《关于福楼拜的补充之言》,同②,第300页。)由于取消了人物动作的原因,作者使世界在偶然性中自由地显现。在这一描写中,与其说作者想以此来表现女主人公因怕冷而想要取暖,不如说作者通过某个人物的眼睛来描述他所看到的女主人公——作者并不想揭示女主人公的内在感觉。又如在查理初访胡奥农场的一幕中,读者通过查理的视线逐渐深入农场的内部。小说家及读者不再是人物动作的超级目睹者,而是同人物一道前行,并见其所见。这显示了福楼拜的一种新的眼光。使他读者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读者的视线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小说家把视角分配并交给了人物,以使读者通过人物的眼睛来发现世界。他的小说由此实现了从再现(无所不在的叙述者的唯一视角)到显现(意象通过人物视线而涌现)的过渡,也即从动作到印象的过渡。
普鲁斯特对福楼拜作品的分析(1910和1920),与他针对后者的风格所做的模仿之作(1908)密切相关,或更确切地说是以其仿作为基础的。围绕福楼拜的创作,普鲁斯特写过两篇仿作。其一是对福楼拜风格的直接模仿,题为《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勒穆瓦纳事件》;另一篇则是模仿圣伯夫风格而写的对他本人的上述仿作的批评,题为《圣伯夫发表在‘立宪党人’专栏里的对居斯塔夫·福楼拜关于勒穆瓦纳事件的小说的批评》。模仿的工作显然介于阅读与独具个性的创作之间。它要求对他人的风格的深刻的了解:不只是被模仿者的精神状态与趣味,还有他的语调与表达方式。在仿作之中,他人的声音无疑应占主导地位,换言之,“我”努力从精神与风格上成为他人。也许仿作是创作的必经之途。按照普鲁斯特的看法,作家总是以有意或无意的仿作开始其文学生涯的,然而有些人最终超越了这一阶段,另一些人则一辈子都在不自觉与不自知地从事仿作。
在针对福楼拜的仿作中,作品的题材是平庸的,没有任何精神性或神奇性。普鲁斯特在一篇涉及到罗曼·罗兰的写作风格的文章中指出,作品的精神性不在于题材本身是否高雅,如主要人物是否是艺术家或音乐家,而在于作家对题材的处理。简单说来,精神性同如何写作而非写什么直接相关。就像《包法利夫人》,普鲁斯特仿作的题材得自当时的一宗社会新闻:一个骗子声称发现了制造钻石的秘密。仿作中三种动词时态占主导地位:未完成过去时、简单过去时(普鲁斯特称之为完成时)以及现在分词式。这与他后来在《关于福楼拜的补充之言》一文所进行的分析相呼应:
一种延续的状态要求未完成过去时,然后它终止以让位给一个新的动作,这要求完成时,而完成时之前常有一个分词句以表示动作的开端,或者作为动作的原因,或者为了向我们显示陀螺的不同侧面。(注:《关于福楼拜的补充之言》,同②,第300-301页。)。
证如一位法国作家所言,动词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灵魂,因为动词通过其时态变化负载着语言的时间性。而时间性则与人类的历史和个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对时间的意识往往同对死亡的恐惧与对永恒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在语言、时间、死亡之间存在着十分内在与复杂的关系。也许是由于法语的独特性,法国作家对动词的时态格外敏感。在此,普鲁斯特借助福楼拜所常用的三种动词形态以构成这篇仿作的骨架。可以说,掌握了一位作家对动词的特殊用法便掌握了他的创作风格中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普鲁斯特以丰富的细节充实其仿作。如果我们熟悉福楼拜的作品,就不难发现仿作中的某些成份直接取自福楼拜的作品,另一些则是普鲁斯特本人借题发挥的巧妙组合。例如文章的头两个短句“热浪变得令人窒息,钟声敲响了”,可以说直接得自福楼拜的作品。在《情感教育》中有很多处对令人窒息的热浪的描写;而在《一颗简单的心》中,则有“钟声敲响了”的句子。在仿作中,有对法庭主持人的细致描写,他那狠亵的、不伦不类的相貌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包法利夫人》中查理那顶丑陋的帽子,如同某种“装饰性的和庸俗的东西”。仿作中的那位黑人无疑是对福楼拜小说中数位黑人女性角色的滑稽模仿,例如《情感教育》中阿尔诺夫人孩子的保姆。而仿作中这位黑人把柑桔分给周围人的行为则令人想起阿尔诺先生在船上“把雪茄分给周围所有的人”的作法。仿作中那只“停落在一位夫人的小帽子上的鹦鹉”则令人想起《一颗简单的心》中的那位女仆的鹦鹉。仿作中那位律师的“谦卑态度”无疑是对《包法利夫人》农业促进会一幕中那位参议员对“政府、君主、国王”的卑微态度的模仿。《修士圣于连的传奇》中写到过“从洞里钻出一只小白鼠”,在仿作中则演变成“每个洞里有只老鼠”。仿作最后一段中众人对财富的幻想很可能得自《情感教育》开头处船上的人们对岸上房产的向往:“不只一人渴望自己是其所有者”等等。我相信,我们越是熟悉福楼拜的作品,这类有趣的呼应便越加俯拾即是。
由此不难看出,普鲁斯特对福楼拜的阅读十分细致、精心,并极其重视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仿作的基本素材,正是对这些细节的重新组织与安排带来了仿作中无处不成的嘲讽与幽默的语调,而这语调一方面夸张了原作者的风格,另一方面又透露出模仿者本人的幽默以及模仿行为本身给他带来的精神快感,这是理解以及赋予理解以生动的语言形式所带来的快感,这种快感无疑是对单纯的阅读的快感的超越。
在模仿圣伯夫风格的仿作中,那所谓的圣伯夫对福楼拜作品的批评主要围绕着作品之外的某些现象进行。如他的选材,他的出身以及他父亲的职业,而其它部分则针对所谓的福楼拜所犯的观察错误。这是因为圣伯夫不理解福楼拜小说中“行为变成印象”这一特点,他仍固执地寻找人物行为的逻辑性与因果关系。当他找不到这种关系,他便认为描写不真实。普鲁斯特也嘲讽了圣伯夫以老朋友的口吻谈论诗人与艺术家的做法。圣伯夫曾用过“好心的耐瓦尔”这一说法,在仿作中则变成了福楼拜“这位可爱的儿子”。然而当福楼拜或其他诗人、小说家创作之时,他们是作为创作者而非生活中的某个人而工作的。用普鲁斯特的话来说,作品是由另一个自我创作的。事实上,普鲁斯特所针对的,尤其是圣伯夫文学批评中对那些与他同时代的真正伟大作家的独创性的漠视。他似乎只看到他们作品中的缺点。他的阅读方法是不足取的。因为那是一种毫无建树的阅读。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批评家圣伯夫的模仿之作中,作为圣伯夫的批评对象的作品也是普鲁斯特本人的仿作。因此可以说在这篇仿作中普鲁斯特以三重身分出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风格与声音。在此区分这三位作家不同的精神特质与语调便成为一件十分有趣而复杂的工作。当然这并非本文所要追问与解决的。
普鲁斯特对福楼拜作品中动词的关注,同他本人对时间的敏感不无关系。他也曾指出,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时间的推移“具有一种主动的与文献性的特征”,而福楼拜却“为之谱曲”(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选自《驳圣伯夫,以及仿作与杂文,论文及评论》,伽里玛出版社,1971年,第595-596页。)。时间无疑是普鲁斯特小说中的重要主题。正是时间的推移以及人物在不同年代的迥然不同的表演使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许多人物拥有了立体感。而这一立体感又反过来揭示了时间所造成的人生的沧桑之变。在他的小说中,印象这一唯一的个人性的得自人的感官的东西是与由理智获得的现成的知识相对立的,因为现成的知识是不属于个人的。只有通过追踪那稍纵即逝的印象的遗迹,我们才能达到深层的真实的自我。比之于那些看似坚实的现成的知识,在我们与周围世界接触的某些瞬间产生的印象显得十分微不足道并且难以把握。然而正是在茶水中蘸过的马德兰点心的味道以及其它一些触发了马塞尔的不自觉的回忆的微妙的感官印象把他引向对逝去了的时间之大厦的重建。眼光也是他的小说中的重要主题。普鲁斯特曾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他的一个人物——画家埃尔斯蒂尔的眼光,当他画海与城市时,“他懂得让眼睛习惯于不去分辨陆地与海洋之间固定的界线与绝对的分界”。这种一反常规的眼光却揭示了某种十分真实的东西,使人们看见了他们平时不曾注意到的东西。经过漫长的在文字中的求索,马塞尔最终发现的,不外乎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眼光。
这对时间,印象与眼光的兴趣源于作家普鲁斯特还是读者普鲁斯特?是阅读启发了他还是他在别人的作品中看见了他自己?这一追问把我们引向读者普鲁斯特与作家普鲁斯特之间的关系,更明确地说,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在普鲁斯特看来,在阅读中我们首先辨别出一位作家特有的节奏,然后听凭这一节奏深入我们内心,甚至完全被它占据:“应该……写一篇有意的模仿之作,以便在此之后重新变得具有独创性,不至于一辈子进行无意的模仿”(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选自《驳圣伯夫,以及仿作与杂文,论文及评论》,伽里玛出版社,1971年,第549页。)。有意的模仿与无意的模仿有着本质的区别。有意的仿作是一种把偶像崇拜推至极点的手段,然而它又是一味解毒剂——通过暂时地彻底地成为他人而为最终超越他人成为自己做准备。因此阅读和仿作的最终结果应是我们写作自己的作品,只有写作才能作为我们阅读他人作品的收获,只有写作帮助我们发现自身的秘密,并使我们的阅读深入下去。对普鲁斯特而言,阅读远非一种单纯的令人愉悦的审美活动,它是一种启示,一种把人引向真正的生活的契机。普鲁斯特曾嘲笑那些所谓的文艺爱好者,他们在对他人作品的喝彩声中消磨了一生的时间——激情随着喝彩而消散,他认为这样的生活是不足取的。而真正圆满的生活来自文学(创作),只有写作才能作为阅读的总结与归宿,只有写作赋予人生以意义。作品不是在闲聊与激情勃发中而是在沉默与孤独中诞生的,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通过两个人物马塞尔与斯万的关系形象地揭示了这一道理。二者在性情、趣味与生活经历上十分相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塞尔是斯万的副本,而斯万是他的启蒙者和先驱。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审美家斯万的一生消磨于对艺术品的欣赏与收藏,消磨于上流社会贵妇们的沙龙,消磨于与奥黛特的不幸的爱情和婚姻(他的这段爱情可以说是由他对艺术的爱引发的的),而小说的叙述者马塞尔虽然也曾和斯万一样爱艺术,也曾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也曾如痴如醉地爱过(不只一个女性)并几乎同阿尔贝蒂娜结婚,但正是由于他放弃了对人世幸福的追求而与文字结合,他最终成为了小说家。
如果我们把阅读看作写作的必不可少的阶段,看作对写作的诱发与激励,看作认识他人与我们自身的独特性的契机,那么我们便能够从阅读中吸取最好的养分,无论是好书还是劣书,正如普鲁斯特所言:
一本书即使不是一面反映强有力的个性的镜子,它仍是一面反映精神的离奇的缺陷的镜子。俯身于一本弗洛芒丹或一本缪塞的书,我们会在前者的深处发现某种优雅中的短促与无聊,而在后者的深处发现雄辩中的空虚。(注:马塞尔·普鲁斯特《阅读的日子》,选自《阅读的日子》,10/18从书,1993年,第51页。)
这便是普鲁斯特的阅读的独到之处。他试图深入到每一位作家作品的核心,以发现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一种不同于所有其它作品的独一无二的特质。而正是在对诸多作家个性的认知中,作为读者的普鲁斯特渐渐实现了对其自我的认识。
让我们再次回到他对福楼拜的阅读上来。他不但分析了福楼拜在语法上的独特性,并归纳总结出一整套新的美学原则,而且他的分析和总结是建立在精细的阅读与充满直感与巧智的仿作之上的。对一般人而言,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可能是明晰与易于理解的,然而在此之前他所做的仿作和细节研究则可能鲜为人知。更为重要的是,随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继续思考与发展那些既存在于他所读的作品中又存于他的思想中的共同问题。况且,在普鲁斯特看来,他人的作品不可能透彻地回答那属于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真理,真理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注:马塞尔·普鲁斯特《阅读的日子》,选自《阅读的日子》,10/18丛书,1993年,第37页。)当我们阅读普鲁斯特的作品时,我们会发现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展他人的思想与创作,他不断同文学史上重要的和不甚重要的作家进行对话。的确,《追忆逝水年华》如同一部由文学家书写的法国文学史。无怪乎乔治·布莱在他的《人类时间之研究》中指出,普鲁斯特的作品如同“一只共鸣箱,在其中不仅可以分辨出个人存在的每一阶段以及一位独特的天才的超越时间的特质,同时通过它,可以追溯到法兰西思想的每一阶段,直至其起源”。写作对于他而言是他的阅读的继续。
普鲁斯特阅读的书目是广泛的,这其中不但包括他一向深爱的作家,如拉辛、圣西蒙(散文与回忆录作家)、夏多布里昂、纳瓦尔、巴尔扎克、波德莱尔、拉斯金等,还包括与他兴趣不甚相同的作家,如圣伯夫、缪塞、福楼拜、马拉美。普鲁斯特在他的作品中曾明确指出他在延续一系列他所喜爱的前人的创作,或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再创造。阅读不只是一个接受来自多方面影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入细致的阅读达到对自我的认识,认识的中心在自我之中。阅读如同一面魔镜,在里面我们不但能够看到他人所看到的独特的世界,也能看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然而,认识自我并非阅读的最终目的。
“我们的精神不会得到满足,如果它没能赋予它无意中创造出来的东西以明晰的分析,或者赋予它曾耐心分析过的东西以生动的再创造”。(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选自《驳圣伯夫,以及仿作与杂文,论文及评论》,伽里玛出版社,1971年,第595-596页。)因此,一种良好的阅读,或者说,一种有效而起死回生的阅读应包括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他人的节奏的模仿,写一些有意的仿作。在此,印象和直觉起主导作用。第二阶段则是以理智为向导对他人的作品进行明晰的分析以达到更高层次的认识。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创作自己的作品,也即对我们所热爱的大师的作品的再创造。只有这一阶段才是一个综合的阶段,一个凝神收聚的阶段。在此直觉与理智均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说我们从印象出发,那么所要达到的则是对人之秘密的揭示。对普鲁斯特而言,揭示真理与某些普遍规律比发现自我更为重要。然而对人的认识又永远离不开认识的主体——人的自我。有意味的是,普鲁斯特死后才被发现的小说《让·桑德》(1895-1899)是用更为传统的第三人称写的,但这并不排除这部作品的自传性质;相反,1908年开始一直写到去世的《追忆逝水年华》虽用的是第一人称,我们却不能视叙述者马塞尔为普鲁斯特本人。也许只有在超越了自我而把视线投向某种更为深层、更为普遍的东西,投向人的极限时,只有在把写作当成独特的个人对文学本身、对时代以及对那独一无二的作品的要求作出的回答时,我们才有可能写出不朽的杰作。
总之,阅读与写作是密不可分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阅读与写作不过是文字生涯的两个方面。但只有写作才能成为阅读与人生的归宿。诗人(广义的)死亡而常人在默默无闻中消失。对后人而言,作为常人的普鲁斯特渐渐会被遗忘;然而作为诗人,他的名字却永远与20世纪的不朽之作《追忆逝水年华》结合在一起。
也许,普鲁斯特对福楼拜、圣伯夫以及其他作家作品的阅读与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个人的特色,然而他那由阅读、模仿、分析他人的作品直到最后创作出自己的作品的道路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有价值的参考。
标签:普鲁斯特论文; 文学论文; 包法利夫人论文; 艺术论文; 追忆逝水年华论文; 小说论文; 福楼拜论文; 情感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