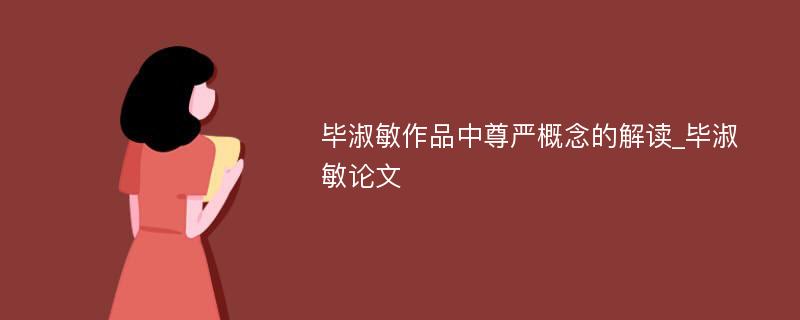
毕淑敏作品中尊严观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尊严论文,作品论文,毕淑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1)02-0049-04
一
毕淑敏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成就斐然、引人注目的一位中年女作家。大凡一个优秀的作 家,除了会给读者编讲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外,总还能给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带来一些启 人心扉的东西。毕淑敏说:“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只不过他们的思想是 用优美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缜密的神经颤动、精彩的语言包装 过的,犹如一发发糖衣炮弹。……你在不知不觉中已明了作家对世界的把握。”[1][37 2]毕淑敏在呈现人间万象的同时,也给了人们一些新颖独到的思想。比如引人关注的《 素面朝天》,作家在涂脂抹粉成时尚的潮流中,却别树一帜,以此为契机,呼唤真实, 反对虚假,崇尚自然,摒弃伪装。无论此议是否得当,总让人思想有所触动,显示了作 家在理念上的独特性。在本文中,笔者将就毕淑敏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尊严 观”加以评论。
纵观毕淑敏的作品,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作家对于尊严问题的关注。她作品中的人物, 很多都与尊严有关,他们的行为都在追求和保持着某种尊严,他们的心态都以尊严的得 失沉浮而喜怒哀乐,在毕淑敏直抒胸臆的散文作品中,尊严更是经常谈论的主题。作家 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忽视尊严,“不要以为普通的小人物就没有尊严。不要认为女人的 尊严感天生就薄弱于男人或人类的平均值。不要以为曾经失去过尊严的人就一定不再珍 惜尊严。”[1][364]“尊严”成为毕淑敏作品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语之一。
如小说《一厘米》中,年轻母亲陶影是一位讲究尊严的人,特别是在儿子面前她要求 自己成为一个“完美而无可挑剔的母亲”。有一次她带儿子去公园游览,在购买门票时 ,因丈量身高的“免票线”不准,相差一厘米,她被管门人误认作是企图逃票者,致使 她的儿子都对她的人格发生了怀疑,她感到这是对她的尊严的最大侮辱。后来公园负责 人弄清原委后,要给她以经济利益的赔偿时,她不为所动,而只是提出要求把事情真相 告诉她的儿子,以求挽回她在儿子面前的尊严。
再如,《女人之约》中的普通女工郁容秋,也是一位渴望尊严的人。她由于生活上一 度作风不检点,而被人戏称为“大篷车”,得不到人们的尊重,这使她很痛苦。为了重 新获得尊严,她在工厂被“三角债”套牢面临困境、大家的工资都发不出的时候,主动 应聘充当“讨债人”,使用种种手段,终于将工厂的债权讨回。对此功劳,她并不要求 高额的奖励金,她唯一企求的报酬是希望工厂的厂长能够当着全厂职工的面给自己鞠上 一躬,还她以尊严。
活着的人需要尊严,濒临死亡的人也同样需要尊严。《预约死亡》将“临终”与“关 怀”联系起来,恰是社会给“临终”以尊严的一种努力。作品表现了病人在临终前对自 尊的执著和渴望,赞扬了在这样的医院中给病人以关爱和照顾的医生护士和年轻的志愿 者,是他们在用爱心和行动帮助那些无法自理的病人实现自己的尊严。
如果说上述作品中的人物都渴望尊严、以得到尊严为荣的话,那么长篇小说《红处方 》则从另一面展示了丧失尊严的可怕与可悲。“鸦片使人回到无拘无束的兽性”。在吸 毒者中,充满了人类的弱点与迷误,到处是污言秽语,粗野放肆。而作品所赞扬的从事 戒毒工作的医务人员,恰恰是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使吸毒者过上正常的生活、重新找 回失去的人的尊严。
作家在创作中执著地、深切地关注人的尊严这一问题,尊严对人如此重要,那么尊严 的实质是什么?在毕淑敏的作品中,对尊严的追问,可以其两点概括:
第一,尊严是有别于物质享受的精神满足,它不是对金钱物质之类初级层次的追逐, 而是一种因自身完善而心灵愉悦的高层次需求;第二,尊严与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我行 我素、无视社会和他人的极端利己主义不同,尊严注重的是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 注重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在当今物欲横流、私心膨胀的社会,毕淑敏大力倡导尊严是有 其现实意义的。它是对金钱至上主义的一种超越,是对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拨正。无怪 乎毕淑敏的作品受到人们的欢迎,它就尤如荡涤浊世的清泉,让人们深思,给人们启迪 。
二
人人都要有尊严,那么,个人尊严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这是毕淑敏在创作中不断 探究的问题。有的人以身份显赫、地位高贵来作为尊严的资本,有的人企图用金钱来“ 买”到自己的尊严,他们不从自身内在修养下功夫,或为他人、社会做一点好事,而只 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去“博取”他人对自己的夸耀和羡慕,在毕淑敏的作品中人们读到 了这种种的“尊严世相”。
《送你一条红地毯》中的老干部夫妇可以说是“身份尊严”的代表,无论他们走到哪 里,到处是尊敬仰慕的目光,这里面固然有老百姓对他们所作贡献的感激,但不可否认 的是在其中也含有对他们权势的逢迎。在以往讲究身份地位的时代,他们确实享有许多 特权,比如,在户口制度森严、城乡差别严重的年代,由于他们的过问,一个拖儿带女 的乡下寡妇就被迁到了城里,还让一位年轻的军官娶了她,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预约财富》中的那位住在高干病房的老者曹畏三也是威仪凛凛,呈现出一幅威严的吓 人样。他约见来人,自然是身份地位比他低的人,来到以后,他仍然顾自“趿着软底拖 鞋,缓缓蹁着方步,很有规律地在地毯上走动着”,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功课,完全无 视别人的存在,“这是一种融入血液中的尊严的气势”,事后他也不说“让你们久等了 ”的客气话,“老爷子毫不感到内疚,让别人等着他,是他一生中最常做的事之一”。
应当指出的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其实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社会等级系统中的一定 位置,都有自己相应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这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评价,凭此而获 得尊严也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当总统要比当平民显耀,当元帅要比当士兵威风。 事实上,正是社会等级系统的这种作用,才促使每个人积极努力,从而充分发挥出每一 个人的最大潜能,以获取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良好评价。
然而,仅凭身份来建立尊严,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尊严。在毕淑敏的文学作品中,对 此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身份尊严虽然包含着社会的评价与肯定 ,但也掺杂着某些人对身份、权势的羡慕与巴结。而一旦人的身份地位改变、权势丧失 ,他们的尊严便会顿时荡然无存,另一方面,身份尊严也容易走向异化,借自己的身份 藐视比自己身份低的人,——如毕淑敏作品中的老者曹畏三,这最终只能是失去尊严。 正因为作家毕淑敏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她在作品中对这类人是语含讥评的。
如果说在五六十年代,个人身份与权势结合体现着一种社会评价的话,那么在八九十 年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万能主义受到冲击,社会评价系统不再是孤峰一座, 社会评价标准也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于是昔日的“身份尊严”不再风光独领,而凭借金 钱以获取尊严的人物走上台来。
毕淑敏显然注意到了社会的这种变化,她笔下的小说人物张文便是这样一种人。张文 是“金钱尊严”的代表。他母亲是农村妇女,他小时受继父欺凌,长大以后曾是一名养 路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当他抓住机遇发了大财以后,他渴望通过金钱得到更多的 尊严,决心通过经济实力与“身份尊严”来一番较量。于是他不惜用高额的价钱去买一 件老干部的旧军礼服,不惜以高额的工资雇副县长老干部的女儿给自己做事。在这里, “旧军礼服”极具隐喻意义。这件“旧军礼服”是老干部甘振远五十年代军队授衔时穿 的礼服,当年他曾“穿着这套礼服,站在天安门侧的朱红色观礼台上”。这套衣服无疑 是和功勋、骄傲、权势、威严连在一起的。对于老干部甘振远来说,脱下这套礼服,显 示着权力尊严的丧失,“他感到撕心裂胆的痛苦,觉得被扒掉了一层皮。”而对于八十 年代的年轻富商张文来说,他要买这套军礼服,恰是要用“金钱尊严”替代权力尊严或 身份尊严。
然而,在作家看来,金钱尊严与身份尊严实际上是一样的,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尊严, 它们都是借助于身外之物而建立的,貌似的尊严,犹如沙滩上的城堡,外表张扬而内在 空虚。一旦脱尽外装,便失去所有。作家借小说人物之口表明了这样的理念:世界上有 比金钱更为强大的东西,这更为强大的东西,当是人格的力量。
在一个讲究自由平等和人权的现代社会,人的尊严主要来自于一种人格力量,来自于 社会对个人的正确评价。一个人可以没有可恃炫耀的身份地位,也可以没有可资显摆的 金钱,但如果他具有良好的品质、能力、修养,从而感到内心充实、安详和愉悦时,可 以说他是有尊严的,当然,当他因良好素质导致德行而使大众受惠时,他获得大众的称 赞,社会给予他肯定,这时他是值得人们敬重的。如此说来,对任何人来说,尊严既是 一种个人的良好品质和情操的体现,也是一种社会对个人的褒奖。
三
正是因为尊严涉及到社会对个人的评价,而社会作为一种独立于个人的存在,其本身 是复杂的,它有其自身的运行惯性,并不总是能够代表合理、完善和先进,在某些时候 甚至也会表现出某种劣性,所以这种评价远非总是正确的。
比如,当有人作出了某种成绩时,他不一定能得到夸奖,得到的倒可能是嫉妒。如毕 淑敏的散文《被老师读作文的时候》中的那个小学生,作文写得不错,经常被老师当作 范文当堂诵读,但小小年纪的她敏锐地感到了同学们的疏远和讥讽。
又如,在散文《请给烤乳猪打包》中,一钵昂贵的、只在豪华宴席上露了露面而未被 乱箸点过的烤乳猪,本是打了包应该带回家的,可最终还是被丢进了垃圾箱,因为谁都 要面子,怕丢人。
更可怕的是,在小说《阿里》中,一个边防女兵,只因与自己的男朋友夜间外出,竟 被人误认为是“关系不正常”、“企图偷越国境”,在这样的外界压力下,年轻的女兵 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竟然跳井自杀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生 命就这样夭折了。毕淑敏这样的故事似乎并不让人感觉新鲜,有多少人受到社会不公平 对待,有多少磊落之人的超凡脱俗之举不能被社会所认同,对这样的故事,过去人们的 视点总是停留在对社会黑暗面的批评上,谴责散布流言蜚语搞阴谋诡计的人,感叹社会 上大多数人的无知、愚蠢、盲从,甚至为虎作伥,但对这些悲剧的主角、这些视尊严为 生命的人,却只有廉价的同情,而缺乏理性的指引。
作为当今社会,应该对尊严问题有新的认识和态度。令人欣喜的是读者在毕淑敏的作 品中看到了这种新的尊严理念。
人的存在是人的尊严的前提,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是最可贵的,要珍惜生 命,热爱生命。毕淑敏在《那座山,虎啸龙吟》中讲她自己这样一段经历。她17岁那年 随部队攀越6000多米的高山,山高路陡、筋疲力尽之时一个老兵让她揪着马尾巴走以防 危险,起初她甚觉有失尊严,因为她想,“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 比死还让人难堪?”但后来她还是理智战胜了面子,“我伸出手,揪住马尾巴……”。 这事固然很小,但它的蕴意是极为深邃的。诚如作家所说,“我们常常过多地把眼睛注 视着别人,而自己则在不知不觉中失落着最宝贵的东西。”[1][22]“我明白日常生活 的核心,其实是如何善待每人仅此一次的生命。”[2][202]
其次,毕淑敏作为一个强调以人为本的作家,她呈请人们“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 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2][78]她要求人们不要在劳累中将自己忘记, “请从这一分钟开始,享受生活”。坦坦荡荡地自利,不该得到社会非议,极端地自私 自利,甚至还要损人以自利,表面上却要声称不自利,这是虚伪的尊严。尊严,“它的 本质是一种对自己的珍惜和对他人的尊重。”[2][58]然而,“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 是——‘我不重要’”。现在,“我终于大声对世界这样宣布……我很重要……我们每 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 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3]
再次,作者认为,人们还必须有一种自尊之心。既然社会也有它的恶劣的一面,人们 为什么要无条件地屈就于它?在毕淑敏看来,这是“一种最积极、最勇敢的生活态度。 ”[1][229]有尊严的现代人应是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既不趋炎附势,盲从权威,也不 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洁身自好只求心灵的快慰,为他人为社会做善事好事也是为了得 到自己精神的升华,而决非贪图别人的吹捧,媚俗而讨好只能换来一时的虚荣。即便是 暂时不被社会理解也无妨,因为“自尊,便是自己尊重自己,只要自己不倒,别人可以 把你按倒在地上,却不能阻止你满面尘灰遍体伤痕地站起来。”“真正的自尊是建立在 不断完善自己的地基之上”的。[1][51]“他人的评判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 对自己的评判,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剥夺的权力。”[4]象《女人之约》中的那个竭力想 要别人一句好话而不能如愿的郁容秋,她的悲剧结局和可怜之处就在于她只知乞怜而不 懂真正的自尊。毕淑敏塑造的这个渴望尊严而不得的人物留给读者的是意味深长的思索 。
四
表现人的尊严观念和行为,弘扬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情操,这历来是文学作品中不少 作家写作的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些珍重人格尊严、始终坚守道德信念的文学形象 不胜枚举,东晋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罢仕归田,大唐李白高唱“安能摧眉折 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潇洒江湖。在他们的心目中,作为精神追求的尊严大大 高于物质享受。更有古代圣贤视人的道德情操高于生命。孟子说:“一箪食,一豆羹, 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5] 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所反映出来的尊严观念,通过文学作品一代 又一代地传递,成为一种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的积淀。
应当说,人的尊严是人高于动物的内在规定性,是人的人格的确证。只有人才追求生 命的意义,才如此看重精神世界的价值。因此,当年毕淑敏通过文学作品来呼唤尊严的 时候,她笔下的人物既汇入了传统文学道德追求的主流,又与时下某些作品放纵物欲、 逃离精神的倾向相左。但是,如果仅此而已,毕淑敏作品中所体现的尊严观在文学层面 上也只是继承和延续,还没有突破和创新,而毕淑敏作品中所体现的尊严观的价值,恰 恰是在弘扬人的精神追求的同时,注意到了对尊严观赖以存在的基础、即生命本身的观 照。
《补天石》、《阿里》、《昆仑殇》等都是描写高原军人特别是女兵生活的小说。在 这些作品中,有爱国的激情,有军人的尊严,更有不可阻挡的生命、青春和爱情的涌动 。作家写道,姑娘们长大了,你不能阻止自然规律发生作用。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 自然规律只能服从于铁的纪律,把活泼的生命禁锢在军规之下,这需要权威,更需要自 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如果说在这里作家揭示了生命与尊严的矛盾,表现了作家对 生命的关怀的话,那么在《昆仑殇》中因某些错误的决定而造成军人重大伤亡的时候, 作家则借一号指挥员在墓地的心理描写,对鲜活生命的消失表示了极大的悲悯:“一号 孤零零地站在墓地,感到难以自制的悲哀。不要登报,不要升迁,不要和呢军帽比高低 ,只求这高耸的土丘填回去、填回坑去,让地面重新冻结得钢铁一样坚硬……。”[12]
易经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对生命的珍惜是人对自身认识深化的表现,社会 对生命的尊重更是社会走向进步与文明的标志。为了道德尊严轻易地放弃生命的故事只 当发生在古代和非常的年代。在今天,当尊严与生命发生冲突的时候,现代人会作出理 性的选择,社会也会对现代人的选择作出理性的评价。这或许正是毕淑敏的文学创作上 别具深意的地方。
除此而外,毕淑敏作为一个由拿手术刀而转向文学的作家,她的从医的经历和背景, 也使她更多地具有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目光,对人的生命本体有实在的认识和更细微的 把握。生命的开始,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崭新而伟大的,生命的终结,对每一个人来 说,也都是“重于泰山”的。
这也正是毕淑敏作为作家特别地关注生命与尊严的个人原因。
收稿日期:2000-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