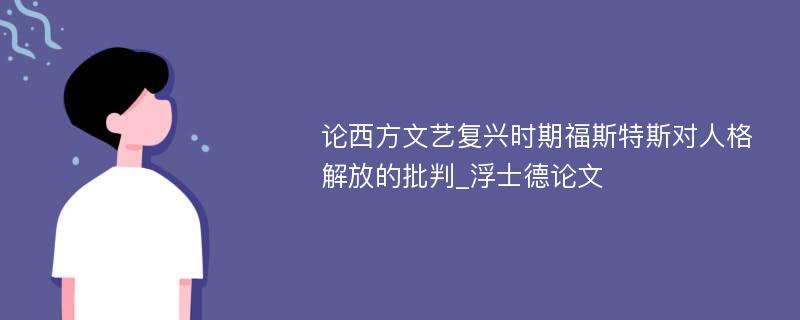
《浮士德》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解放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浮士德论文,文艺复兴时期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一般地被西方思想家、哲学家评价为具有超时代的伟大意义和永恒价值的巨著。席勒是属于十九世纪的,而歌德则是超越十九世纪而属于此后一切时代的:他的《浮士德》一书,尤其如此。然而《浮士德》体现的基本思想到底是什么?何以它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永恒价值?我国艺术界一些知名人士认为,《浮士德》刻画了浮士德那样一个自强不息、永无个人满足的不断进取形象。如果是这样,《浮士德》那种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便无从成立。本文想就《浮士德》的基本思想,提出我们自己的一点粗浅想法。
一、上帝与魔鬼的对立:邪不胜正
上帝与魔鬼的对立,是西方宗教——基督教思想中两个基本对立面,在这个对立面中的“上帝”,无非是人性之善的幻想对象化,而在这对立面中的“魔鬼”,则是人性之善的对立物
非性之恶的幻想对象化。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历史而言,非性之恶可以逞一时之强,气焰嚣张,大有踏平上帝的人世间伦理秩序,代之以魔鬼世界之势。但到后来,它却还要失败,而让位于上帝那人世间伦理秩序的朗朗乾坤。这种上帝与魔鬼的对立和斗争,实质上便是人们灵魂深处性与非性的对立和斗争:人们不是本于人性善的伦理秩序而行动,便是本于非性之恶的一己之私而行动。人本于人性善的伦理秩序而行动,这是人性善对非性恶的否定;人本于非性恶的一己之私而行动,这是非性恶对人性善的否定。在这两种否定的共存、共在中,有一条永恒不移的必然法则——邪不能胜正。这一见诸人世间的善恶对立和斗争的实质,便是见诸幻想天国中的上帝与魔鬼对立斗争的实质。
歌德深明此理,他非常明确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邪不胜正,这是贯通整个《浮士德》一书的基本原则。歌德根据传统流行的有关“浮士德”的传说,妙笔生花地写成《浮士德》这一伟大诗剧。
在《浮士德》一开始的“天上序幕”中,便揭开了这一正邪斗争实质的发源。在那里,上帝与魔鬼靡非斯特,有如下一段对话:
靡非斯特:在那儿我总不能欢喜。人类的苦状使我哀怜,连我也不肯把苦人作践。
天帝:你知道那位浮士德么?
靡非斯特:是那位博士?
天帝:我的下使!
靡非斯特:无疑!这位大愚又别外有趣。他不用尘世上的浆斗稻梁,他只是发酵着驰鹜远方,他一半也自知他的诞妄;他在景仰着上界的明星,又想穷极着下界的欢狂,无论是在人间或在天上,没一样可满足他的心肠。
天帝:他虽然还困顿在那迷津,我不久要把他引入清澄。树木正繁枝,便是位园丁,也知来年的花果收成。
靡非斯特:你肯打赌么?我说你会输,你假如许可我时,我要把他引入魔路。
天帝:只要他生在世上,我听随你去作摆布。人在努力时,难离错误。
靡非斯特:我感谢你哟,上帝;我从不想和死尸游戏。我最爱的是丰颊新鲜,对尸骸我是闭门不见;尤如那猫儿不吃死鼠。
(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44 46页)
在这段上帝与魔鬼靡非斯特的对话中,充满了人性善与非性恶、特别是后者的本质规定。
穷人或苦人无力为恶,因而其非性恶一面便很少出而这样或那样以邪路对人进行诱惑。这便是魔鬼靡非斯特的“连我也不肯把苦人作践”的本质。当然这是相对的。
只有对那些充满生命活力而有条件为恶的人,其非性恶一面才常常出而这样或那样以邪路对他们进行诱惑。但当他们走向邪路之后,最终落入山穷水尽的恶果中时,便不见其非性之恶一面出而对其出谋划策的影子,只能与绝望相伴随。这便是魔鬼靡非斯特“从不想和死尸游戏”而“闭门不见”,却只喜欢“丰颊新鲜”的本质。
魔鬼靡非斯特对浮士德的看法,正好表明他是个徘徊于正邪之间的人:他有善基在景仰“上界的明星”而渴望高尚,又在“想穷极着下界的欢狂”而渴望非性恶的卑下无耻。因此,它在前者中又渴望后者,因而感到不满足;他在后者中又渴望前者,因而也感到不满足。这便是浮士德的迷津,是他“无论在人间或天上,没一样可满足他的心肠”的本质。
非性恶是人性善不可分割的对立物。本来人之为人理应体现的是人性善对非性恶的否定,但在人生的征途中,欲望不断向上浮动,难免使人摆动于二者之间,产生浮士德式无所归依的苦恼,以至于听命于非性恶而去实现它对人性善的否定。作为人性善天然精英负荷者上帝的下使,尚且如此,何况常人。此即上帝所谓“人在努力时,难离错误”的本质。
但中国古人云:“修道之谓教”。在人性善的伦理秩序的教养下,人总是要走向正道的,少数不肯向善、甘心为恶者,将自食其果,起不了什么大的风浪,因为凡人皆有人性善的善基
邪不胜正。此即上帝所谓浮士德“虽然还困顿在那迷津,”但他会象园丁那样,“把他引入清澄”,以期“花果收成”而敢于与魔鬼靡非斯特打赌的本质。
但“邪不胜正”的基本原则,在《浮士德》全书中,却以西方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而使它具体化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原则。此为《浮士德》的核心。这便是歌德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解放的批判。
二、歌德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解放的批判
《浮士德》全书的具体核心思想,是以“邪不胜正”为逻辑基础而导向一个伟大历史原则的,是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解放片面性的深刻批判。
所谓西方文艺复兴,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文艺复兴,是指西方自十三、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新兴思潮而言;广义的文艺复兴,是指这个新兴思潮的发起及其延续、发展直到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结局为止的整个历史时期。歌德以其《浮士德》所体现的批判,是针对广义的文艺复兴而发的。鼓吹抽象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是这整个历史时期的核心历史内容。
歌德是当时德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所谓“狂飙浪漫思潮”的著名领袖之一,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正是从这浪漫文艺思潮及其影响所及的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出现了歌德、黑格尔等人对广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兴思潮片面性的划时代的伟大批判。前者是以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进行的,后者是以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形式进行的。这种批判,既是否定也是保存,使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伦精神,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便开始冷静沉着地纳入正轨的合理性,达到了高度而全面性的自觉。没有这种转变和自觉,便难有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谈到东方日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我们可以说,它在一开始便既学习西方,也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相结合,而原本就基本上存在于它的合理伦理精神之中。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勃起,便产生了不同于封建制度那种等级从属人格的一代新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和的无形规律制约中,显得是一些除了自己的理性命令之外再无其任何制约性的个性自由人格。所谓“个性解放”,便是这一代新人的内心呼声的集中体现。由于这些新人只见到自己为一些有理性的个体自由人格的现象,所以他们所谓“个性解放”,便是一个在其我思、我想的理性命令中,我行我素地去追求个人幸福的片面个性解放。它抓住了个人幸福的社会内容,而抛弃了它实际存在其中的社会伦理——道德制约性。这种片面个性解放的逻辑内容,便是这些个体自由人格现象企求的抽象自由平等——人无差等的自由平等。实质上他们这种自由平等的具体合理性也只能在于:它必须内在包含着人们在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和的规律制约中,各尽其所能为,各得其所应得,而不是其所不应得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环节在内。单纯我行我素的片面个性解放与其逻辑内容——抽象无差等的自由平等相统一,这本身便是一种违背人性善历史规律的历史性非性之恶。我们不是说,这种新兴思潮,不讲其资本主义一代新人的社会伦理——道德,但它却想将此奠基于这历史性非性之恶上,这实质等于无伦理、无道德,让人将自己的灵魂交给这历史性非性之恶去支配。从西方的宗教思想上看,此亦即让人背叛上帝,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魔鬼去支配,以求人世间人欲之利的高度满足。这种新兴思潮所鼓吹的片面个性解放和抽象自由平等的实践,必然导向到处都是侵犯人权的恶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如果让位于这种片面新兴思潮来统治,它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也不会有今天的繁荣。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浮士德》的主人翁——浮士德,实质上是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及其一代新人的集中代表。他与魔鬼靡非斯特定立契约,答应对方如果能使他在人世间达到心满意足的境界,他的灵魂便归对方所有。这就是说,西方封建社会及其社会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已归没落,而让位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尚还是个历史性非性之恶的片面个性解放新兴思潮,如果它真能使资本主义一代新人在生活中达到其心满意足的境界,它便理应是他们灵魂的主宰原则,而同时也是新兴资本主义发展、昌盛的主宰原则。但这是不可能的。
所谓浮士德随同靡非斯特走出中世纪的书斋,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一代新人的问世。他们为了实现其时时增长的欲望而听命于靡非斯特,就是说这一代新人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世界观,在其抽象否定传统的我行我素的片面性中,本质上是非性之恶的。既然浮士德只是新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一代新人的代表,当然还有他与其他新人乃至那和新兴思潮相结合的封建贵族、国王的相关者存在。于是由此便开始了以浮士德听命其非性之恶的化身——靡非斯特种种策划为主题的一系列恶行和瞎胡闹。这些微妙奇特的场面,在这里不必一一缕述。
浮士德在不择手段,一心一意去追求“穷极着下界的欢狂”的过程中,欲望发展到高峰而得到满足时,他便不禁喊出了“你真美呀,请留一下!”,虽然这时已双目成盲,变成快要倒下去长逝的人了。按照它与魔鬼靡非斯特所订立的契约,一旦他心意满足,他就不得不为靡非斯特所有。但天上“光明的圣母”及其一些天使们却将他抢救了去,出现了浮士德的天界复生。
所谓浮士德快要逝去而为魔鬼靡非斯特所有,就是说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一代新人,已将失去其本真历史合理性和意义,名存实亡,而将变成非人伦社会的魔界和一些无法无天的人魔。
所谓行将死去的浮士德为“光明的圣母”及其天使们所抢救,就是说历史之邪不胜历史之正:人性善的历史真实,总是要突破几乎即为魔界和人魔的非性恶历史假象,而纳新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一代新人于新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规道之上——“修道之谓教”的社会教养,必须要以从道德上树立人的人格为先。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实质上是要求一种新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包括法律在内)和与此相统一的新人格,而不是使人们变成一些非性之恶的人魔。
所谓浮士德的天界复生,就是说新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一代新人,在其固有此种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规道上,走向其本真历史合理性和真实王国中去。
所谓“光明圣母”及其天使们,无非是人性善及其历史真实不能为其对立面所压倒的、正必胜邪的孕育力量而已。
在《浮士德》书中的靡非斯特和一些魔女们,能够想怎样就怎样,要什么有什么,这无非是象征:非性恶的人格化,是人非人。人非人者在其非性恶中成了气候,便是一些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下的,呼风有风、唤雨有雨的大魔头而已。但他们实质上却是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纳人为制造出的小仔仔蒙古鲁士,他只能装在玻璃瓶中去见天。结果,便在放恣情欲中,一旦好玻璃瓶弄破了,他便要在一片火光中化为灰烬。这是必然的,蒙古鲁士便最终以此种命运而告终——邪不胜正。靡非斯特想占有浮士德灵魂的妄念,终于变成泡影,同时他之为邪也为正所否定。浮士德的中世纪书斋和瓦格纳在其中焦头烂额地制造“人造人”,是象征着资本主义及其一代新人,在西方封建制度中的人的孕育。
于是,《浮士德》便实现了这样一个邪不胜正的伟大历史原则: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一代新人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也需要成立在人尽其为而物尽其材,使得人各得其所应得,不得其所不应得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之一定历史形成的制约中,而要以树立人们与此相统一的道德人格为先——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解放片面性的非性之恶的历史形式,必然要让位于这个人性善的历史形式。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歌德《浮士德》的以其邪不胜正基本原则为基石的核心思想。同时,这也是贯通《浮士德》全书的基本思想。
标签:浮士德论文; 文艺复兴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人性论文; 歌德论文; 经济论文; 魔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