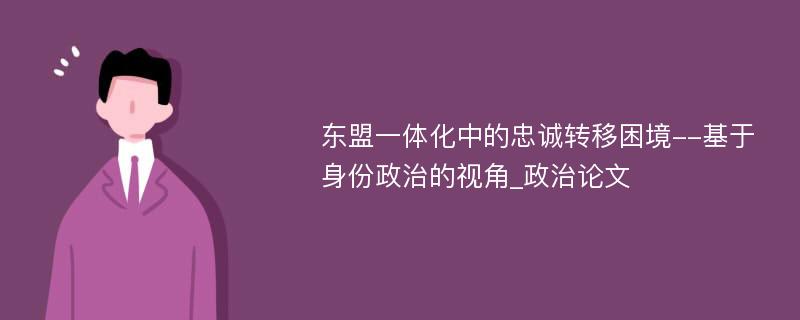
论东盟一体化中效忠转移的困境——从认同政治的视角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视角论文,困境论文,政治论文,一体化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3)06-0046-10
修订日期:2013-05-20。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自1967年成立以来,已经历了40余年的发展历程。2008年12月,《东盟宪章》正式生效,该宪章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建立“东盟共同体”的战略目标。①当前,加快共同体建设已成为东盟各国的基本共识。2012年11月,第21届东盟首脑会议将2015年12月31日设为建立“东盟共同体”的最后期限。东盟一体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但要建成真正的区域共同体,前景并非完全乐观。新功能主义把一体化进程划分为学习、外溢和效忠转移(loyalty transferring)三个递进的阶段,认为外溢效应将导致效忠转移,从而实现新政治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但实际上,物质层面的制度化并非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变迁的充分条件。作为新兴民族国家,东盟各国的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思想方兴未艾,同时,一体化进程所建构的地区认同和地区主义理念也正在缓慢发展,而这两者是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的。由于这种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东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效忠转移,并非像新功能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能够一气呵成并将一劳永逸。效忠转移的困境,随着东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将成为东盟各国终须克服的难题。
一、认同的冲突:一体化进程中效忠转移的困境
一体化(Integration),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个具有纵向与横向双重普遍性的现象。②从纵向历时态的视角看,人类历史是一部不断由分散走向整合的历史:从基于血缘联系的氏族、部落发展到基于地缘联系的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进而经历长期的交往与融合演进出更为广泛的共同体——民族,并以此为基础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直到出现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从横向共时态的视角看,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一体化进程通常具有超越地域界限的普遍性:以“二战”之后出现的地区一体化为例,五大洲相继出现一系列以一体化为宗旨、以地域联系为纽带的国际组织,地区整合趋势日渐遍布全球。东盟的一体化进程,也是这一世界历史普遍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国内外学界对东盟一体化的研究多关注经济和政治领域,社会认同维度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认同的冲突已构成东盟一体化进程中效忠转移的困境,使区域共同体的构建面临着社会心理层面的现实挑战。
1.1 新功能主义的一体化逻辑
在一体化研究中,以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是当前学界两大主流理论范式之一。③哈斯将一体化界定为国内层次的政治行为体,“将它们的效忠、期望和政治活动转移到一个其机制拥有或要求拥有高于现存国家管辖权的新的中心的过程”,并认为一体化进程的结果是“产生一个高于现存政治实体的新的政治共同体”。④简言之,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一体化进程将使民族国家被更高的共同体所取代。
在新功能主义学派看来,这一新政治共同体赖以形成的有效路径,包含学习、外溢、效忠转移三个相互衔接的动态发展阶段。一体化参与者通过不断的学习,使原有的利益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并产生新的规则,进而为外溢的实现创造动力。外溢(包括功能外溢、政治外溢和地理外溢)在本质上是一体化在范围与层次上的加深。一体化进程中日渐密切的经济交往将会产生重要的政治效能,它会产生对超国家规制的功能性需求,而这种功能性需求最终将导致政治外溢,各国政治精英在超国家规制的现实效应之下产生利益与期望的趋同。换言之,一体化以其本身的重要性构成压力,形成在超国家层次实施政治控制的客观需要,最终导致超国家机构的诞生。在一体化的动态发展中,这种外溢效应最终将导致效忠转移,使群体忠诚归属由民族国家向超国家机构转化,从而实现新政治共同体的最终形成。
新功能主义强调,一体化发展的动因在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认为一体化的动力不仅在于(旧功能主义所主张的)技术官僚的自主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功能性外溢,还在于行为者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实现。具有一体化意愿的行为者,特别是政治经济领域的精英力量及其主导的超国家谋划,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精英主导的具有一体化导向性的国家间互动,是由国家向超国家共同体演进的内在动因。
同时,新功能主义认为,超国家机制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力量,超国家性的中心机构是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强调外溢机制可以使一体化实现从技术性部门向政治性部门的溢出,最终建立区域范围的制度化的超国家机制。新功能主义主张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需要超国家机制作为其动力机制,认为随着自身程度的加深和范围的扩大,区域一体化的运行将会在超国家层次和国家层次同步展开。代表一体化参与国共同利益的超国家机制,能够协调相互间的利益冲突,进而促使政治精英和国内民众将政治忠诚转到地区层次上,实现从民族国家向更高层次的地区共同体的进化。
1.2 效忠转移:一体化中的认同政治
效忠观念是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的核心要素之一,效忠归属甚至被哈斯视为界定政治共同体的标尺。按照新功能主义的观点,在一体化进程中,以政治外溢为基本机制,国家政治精英利益与行为的重新定位将会最终改变传统的国家中心信仰体系,减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预期,增加对超国家权威结构的忠诚与预期,⑤从而最终实现效忠归属的转移。简言之,“人们会因为跨国机制比民族国家政府能更好地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把他们对民族国家的效忠转移到跨国机制上”⑥。这种效忠转移,正是一体化中新共同体最终形成的根本标志。
效忠转移问题的核心在于效忠归属的对象与客体,它在本质上源自施动者的认同感归属。一体化中的认同(identity),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确认。认同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现象。在横向上,它包含了语言、宗教、种族、民族以及对过去历史的认识等一系列人类特征;⑦在纵向上,它集合了家庭认同、地方认同、国家认同、超国家认同等多种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正如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曾指出的,我们都是多重认同的人。⑧每一个个体都处于一定的认同框架之内,这些特定的认同框架通过集体或集团与更大范围的认同联系起来。在一体化中,认同是连接区域结构和个体行为的关键概念。一体化所涉及的认同主要是地区认同和民族认同。效忠转移问题在本质上指的是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认同,其核心内容是以地区认同为主的认同框架取代以民族认同为主的认同框架。就东盟一体化而言,效忠转移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东盟共同体为归属的地区认同和以东盟各民族国家为归属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地区认同(regional identity)是“若干地理上接近并相互依存的国家在观念上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认同以及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意识”。⑨它是一体化与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集体认同重叠而产生的一种认同形式,是在一体化组织内部形成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其核心意涵是以地区为特定忠诚对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现代国际体系中最基本的认同归属形式。民族认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认同指对特定民族国家的认同,又称国家认同⑩;狭义的民族认同则特指族群认同。本文中的民族认同概念系取其广义。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11)它在本质上是对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承认与效忠。这种认同,是基于共有历史和共同未来而产生的集体归属感和共同使命感。这二者的关系,是效忠归属的系统层次与单元层次间的关系。
1.3 认同冲突:新功能主义的理论疏漏
尽管认同结构可以存在多元性的特征,但主导性认同是唯一的。主导性认同决定着认同主体的效忠归属,因而效忠归属也具有单一性。在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和地区共同体作为社会认同与效忠归属的对象,是存在对立性的。客体的对立性使效忠的归属存在两难情境,使地区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这种认同的冲突,是新功能主义所未予以足够关注的。
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一旦一体化机制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效忠转移就会成为顺理成章、自然发生的事。(12)但新功能主义在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中,对于外溢效应将导致效忠转移的论断并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事实上,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与效忠归属与对地区共同体的认同与效忠归属,在认同主体观念世界中只能由其中一种主导而难以平等共存。
在现阶段,民族认同是一种“强势认同”,具有高度排他性与极端性;而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区认同是一种“弱势认同”,由于历史深度的匮乏和集体记忆的缺失,难以激起以政治效忠为导向的大众情感。加之地区认同和已有的民族认同之间在内容上固有的对立性,使得一体化进程中主导型认同归属的转换以及与此同步的效忠转移,并非像新功能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可以轻易实现。
在一体化领域,认同之间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东南亚地区尤其突出。当代东盟各国(除泰国之外),皆为“二战”后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由殖民地独立而形成的新国家,作为民族国家而存在的历史相对短暂,各国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思想方兴未艾,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观念相当强烈,远不能与有着悠久的民族国家历史,主权观念逐渐淡化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相比。(13)当前东盟许多国家内部都存在部族、民族和宗教冲突,民族国家建设依旧任重道远,民族认同仍在建构进程之中。同时,1967年以来,东盟一体化进程所建构的东南亚地区认同和地区主义理念也正在缓慢发展,并且得到了东盟国家政治精英超国家谋划之下的刻意培养,有着不可轻视的发展空间和前景。民族认同和地区认同两者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随着地区共同体的构建,这种认同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东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现阶段,东盟民族认同和地区认同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强势的民族认同对于弱势的地区认同发展的抵触和压制。这在东盟共同体构建进程中有着普遍的体现。以中南半岛的柬埔寨和泰国为例,尽管两国政府都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并按照《万象行动纲领》等相关国际协议的共识推进地区认同的构建,但由于两种不同类型认同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在民族认同之下双方各自民族利益的驱使下,两国由于柏威夏寺领土争议,近年来多次爆发边境冲突和危机。2011年2月,两国在柏威夏寺地带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导致柬泰两国双边关系的危机,对东盟一体化进程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认同的冲突阻碍了东盟共同体的构建和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效忠转移陷入理论和现实上的双重困境。
二、困境的缘起:东盟一体化中的双重认同建构
认同的冲突使新功能主义所预期的效忠转移陷入困境,而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现实后果。东南亚次国家行为体地区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从根本上说源自一体化进程中身份认同的双重建构。东盟的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建构了地区认同,推动了地区主义观念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向建构了东盟各国内部的民族认同,促进了民族主义理念的强化。正是东盟一体化中的这种双重建构效应,使得民族认同与地区认同之间隐藏的结构性矛盾得以显现。
2.1 地区认同的发展:交往与规制的共同建构
东盟地区认同是在东盟内部形成的超越民族国家的一种共同体意识,它作为一种群体性社会认同,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经历了一个“被唤醒、被改造和逐步强化的过程”(14)。这种建构进程的主要模式有二:一是交往行为的推动作用,二是区域规制的强化作用。
(1)交往行为的建构
东盟地区认同的建构首先是区域内交往行为的现实效应。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以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交往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Approach)可资借鉴。交往沟通理论以“共同体意识”作为地区集体认同的等价概念。这一理论强调交往对于区域性集体认同的建构作用,它揭示出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是国家间交往沟通的一种机能,认为相互交流的网络的构建是通向超国家共同体的基本路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如果两国之间存在的互动越多,那么对这两国来说相互间的重要性就越大。(15)这对地区认同这种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是有利的。同时,交往互动还可以获益的观念有利于国家间信任的形成,而信任感的存在又将反过来促进国家之间的进一步交往互动。
通过东盟区域内行为体(包括国家、团体和个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区域性规范、规则和价值等社会观念实现在区域内的社会化,进而建构了行为体对于本区域的认同。行为体通过社会学习,能够逐步内化这种地区认同以及它所包含的规范内涵。此外,促使地区认同形成的社会互动不仅包括区域组织内部的互动(行为体之间,行为体和制度之间),还包括区域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和区域外部的社会互动,即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套逻辑机制之下,地区认同最终得以形成和发展。
交往行为对东盟地区认同的建构效应是通过两个中介变量产生作用的。一方面,它增强了东盟组织内部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依存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认知。交往行为在客观层面加强了东南亚区域内行为体相互依存的程度,在主观层面推进了他们对于相互依存状况的认知。另一方面,它强化了区域内个体间的共同命运。行为体具有共同命运是指他们的每个人的生存、健康、幸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16)交往行为使东南亚区域内个体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使群体状况对个体状况的影响增强,增强了共同命运的客观基础和个体对于群体共同命运的主观认知,从而促进了地区认同的发展。
(2)区域规制的建构
东盟地区认同的建构同时还是区域规制运行的现实效应。一体化实践导致对实现共同行动的区域规制的需求。区域规制对社会认同具有塑造作用,它从多方面影响着行为者认同感的形态。区域规制作为一种合作性的地区安排,能够提供民族国家之间沟通彼此信息、增进相互理解的机会,并促进一体化组织内部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的发展,同时,它也会导致对民族国家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并要求超国家层次上的政治控制和责任承担,使超国家机制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权重增加。由于区域性规制的这一系列政治效能,最终使地区认同作用得以在纵向上深入和横向上扩展。具体来说,区域规制对东盟地区认同的建构效应主要是通过两个中介变量产生作用的。
首先,它增强了作为地区认同基础的区域同质性。作为区域内各民族国家共同的制度化框架,区域规制是地区共同特性的特殊体现形式,它约束区域内各民族国家的行为并导致其趋同。区域规制所造就的共同行为取向,能够使东盟组织内部各成员国形成针对区域外行为体的较为一致的政策倾向。通过区域内各行为体有别于外部地区的共同政策和行为取向,区域规制使东南亚地区的同质性在原生性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了建构性因素,拓展了区域同质性的内涵和外延。
其次,它强化了作为集体认同主变量之一的“自我约束”。这一进程是通过区域规制中的规范因素实现的。东盟方式的基本程序规范和行为规范,是其成员国之间交往所遵循和依赖的主要行为准则和处理方式。以区域规制来规避和调解国际争端、处理国际安全问题的东盟方式,已成为东盟各成员国的基本行为模式。规范对地区认同的建构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从同一性的角度论述过学习与认同的关系,认为认同(同一性)的形成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17)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价值与规范的构造过程,它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外部结构向内部结构的转变(内化),即把规范和规则变成主体内在的东西,影响和改变其观点以及思想的基本模式。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区域规制对地区认同的建构作用才得以运行。
2.2民族认同的强化:理念与行为的相互建构
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认同形成于长期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之中。去殖民化之后至一体化起步之前,东南亚地缘政治环境以对立和冲突为主要特征。一方面,国际体系层次的大国对抗严重渗透到东南亚地区安全结构之中。由于地缘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东南亚沦为美、苏等大国之间战略博弈的舞台。苏联在越南,美国在菲律宾和泰国,都设有军事基地。外部强国在这一地区展开势力角逐,影响了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另一方面,区域内国家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对抗或冲突现象。如苏加诺执政时期,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马来西亚同菲律宾之间的沙巴争端等。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为解决区域内国家间的矛盾与争端,避免地区外大国的控制,部分东南亚国家开始加强相互间的交往沟通,启动了区域合作的初步尝试。1961年,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联合组建的东南亚联盟;1963年,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组建的马菲林多联盟(MPHILINDO)等,(18)都是这一尝试的产物。在这些早期区域合作组织相继失败之后,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式成立,东南亚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开始步入正轨。
通过对这一历史的分析可以发现,东盟的一体化起源并非是超国家谋划的产物,而是各民族国家出于民族认同的自群体偏向,在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理念指导下,采取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手段来维护本国的现实和长远利益。
民族认同推动了东盟一体化的起步和发展,而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间政治博弈,反过来又推动了东盟各国民族认同的强化。东盟各国民族认同的巩固和强化,是国家间互动进程中认同理念与对外行为相互建构的结果。这一互构进程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认同理念对民族主义行为的建构,二是民族主义行为对民族认同理念的建构。
(1)理念建构行为
民族国家的行为遵循适当性逻辑,而适当性逻辑与主体的认同观念密切相关。认同因素是行为者利益判定和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影响着行为者对行为动机和行为后果的判断,影响着对成本与收益的评估,进而影响着行为者对于可行性方案的评价与选择。民族认同理念决定了民族国家的行为。认同理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以利益为中介变量的。利益、认同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式是:认同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19)
首先,民族认同理念建构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利益包含了客观需要与主观认知两个层面的属性,作为一种认知观念的行为者利益,是由其本身的认同决定的。群体利益的形成是以社会认同的定位为基础的,它取决于自群体与外群体所形成的认同关系的特定结构。
其次,民族国家的利益决定了其对外行为。民族国家的行为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本民族的利益为核心宗旨,维护和追求本民族的整体利益,认为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本民族利益具有至上性。东盟国家民族主义导向的国家政策实践,正是以此种理念为思想底蕴的。
(2)行为建构理念
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 Anderson)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认同是在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中构建的,而不是预先给定的。(20)建构主义理论也认为,作为观念性社会实践的集体认同,是在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观念与施动者行为是一种互构的关系。从此种意义上讲,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不但东盟各国的民族认同理念建构了民族主义政策行为,而且东南亚区域内的民族主义政策行为也同时建构了东盟各国的民族认同理念。
民族国家的对外行为,其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作用是通过自我身份认同的反向建构实现的。群体性社会认同并非完全是基于行为体内在属性的内生身份,它同时还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因而也需要来自外部的反向身份,以之为与自群体相对的外群体,从而以竞争性行为来巩固自我的身份认同。社会心理学中社会认同理论将认同所引起的给内群体较多资源以及正向的评价的现象称为自群体偏向,而对外群体成员则分配较少资源并给予负向的评价这种现象称为外群体偏见。(21)个体忠诚于自己所归属的群体,并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中体会群体间差异。对于民族认同而言,这种建构进程是以本民族国家为自群体,以其他国家为外群体的。东盟一体化进程中,各民族国家在通过自利的民族主义行为,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强化了自身的民族认同。
三、困境的消解:东盟认同冲突弱化的路径模拟
在东盟一体化的未来进程中,以认同冲突为外在表现的效忠转移在现实层面的困境,是地区共同体形成所必须逾越的障碍。实际上,如果把政治外溢看成一种历史进程,那么,其实际意涵就包含了时间维度上的长期性,由此也可以认定效忠转移在现实层面的必然性。因而,虽然困境的产生是客观历史进程的产物,但是其消解也是可预见的。一体化进程中东南亚地区的系统渐变将从结构性路径和功能性路径两个方面推进区域内认同观念的演变,逐渐弱化地区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使效忠转移最终成为可能。但这一进程绝非短时期内所能实现,而须以布罗代尔式的长时段的视野进行体察。同时须指出的是,本文并非以政策实践为指向的对策研究,而是对一体化特定发展轨迹规范性的探讨,是对东盟未来长时段历史演进的一种学理审视。
3.1 结构性路径:地区结构演进推动观念嬗变
东盟一体化是一个地区结构持续演变的进程。东盟的地区结构,并非单一维度的政治结构,而是多领域、多层次的复合结构,包含安全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三个层次。地区结构的这三个层次在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中不断演进,将推动区域内认同观念的缓慢嬗变,促进地区认同的发展,同时逐渐消融民族主义坚硬的认同内核,最终为效忠转移困境的消解创造可能性空间。
(1)安全结构
安全结构是地区结构的首要内容。东南亚地区在一体化起步之前的阶段,实际上是处于安全困境之中的。为消解这种地区安全困境,部分东南亚国家开始搁置争议,谋求构建以合作安全为基本理念的地区性安全制度。经过46年的发展,东盟已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自1967年成立以来,东盟成员国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地区内部的和平与安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在东盟未来的一体化进程中,地区安全结构将进一步演变,实现由当前的安全复合体(security complex)向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的进化。随着安全共同体在可预见未来的建成,东盟各国在安全问题上将朝向多伊奇所界定的“共同体的成员真正确信彼此间不以武力相害,而是以其他的方式解决争端”(22)的状态过渡,各成员国避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东盟地区规范将深度内化,形成一个国家间安全互助的实体。
(2)经济结构
经济领域是一体化进程的基础性内容。在东盟一体化中,由于东盟国家经济相似性高,互补性弱,东盟一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额甚至小于其各自与中、日等国的贸易额。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影响到东盟地区认同的发展。不过,“东盟各国的经济合作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蓬勃发展。无论从贸易总量上还是从贸易的微观结构上,合作水平都不断上升”(23)。特别是2003年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签署的《东盟第二协调一致宣言》,提出了构建“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战略规划,东南亚经济结构朝向新的方向发展。2009年2月,东盟各国签署了《东盟全面投资协定》、《东盟货物贸易协定》以及落实东盟服务贸易框架协定,为东盟在2015年前实现投资、货物、服务以及人员的自由流动奠定了基础。2010年10月,第17次东盟首脑会议又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东南亚地区经济结构正朝向区域经济共同体方向稳步发展。
(3)文化结构
一体化起步之前的东南亚地区文化结构,以多元化为主要特征。它同时受到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东南亚的文化结构并非静态的结构,而是处于持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外来文化与东南亚本土文化(indigenous culture)长期接触、交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同时,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使东南亚在固有的多元的文化结构之上形成了自己的当代地区文化,与传统社会文化相互作用,构成了本区域多元一体的新的社会文化结构。在一体化进程之中,东盟各国政治精英致力于构建东南亚社会文化共同体,主张“培育人才,促进东盟学者、作家、艺术家、媒体从业者相互交往,保护和推广东盟多元文化遗产,培养地区认同和东盟意识”(24),从而使“东盟公民通过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的共同体意识相互交往,通过共同的地区认同结合在一起”(25)。
3.2功能性路径:国家权威转移带动认同外溢
(1)权威转移增强一体化的政治效能
一体化进程会使地区公共生活发生系统嬗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治领域公共权威由民族国家向超国家共同体的渐进性转移。这种政治权威的转移是民族国家权力流散的必然结果。权力流散理论是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通过对当代全球政治经济领域进行系统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它揭示了国家权威的衰落和非国家权威兴起的现实状态与必然趋势,指出了权力正在由国家向非国家权威流散。(26)但斯特兰奇在非国家权威中更多地关注了国内层次的次国家行为体,而未对作为国际体系子系统的地区性超国家行为体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由于一体化进程的现实效应,区域组织特别是作为其后期形态的地区共同体,更是国家权力流散和权威转移的主要对象。这种政治权威的转移是通过两个步骤实现的:
首先是职能让渡。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一体化的发展“意味着国家职能与职权进一步向一体化组织的转移或让渡”(27)。在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内各国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相互依赖的不断增强,以及地区性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问题日益突出,迫使各国加强的区域合作与协调,以控制和消除共同威胁,维护共同利益。这就使得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职能逐步地、缓慢地向超国家行为体让渡,从而造成民族国家功能上的空心化,使区域组织的功能不断增强、权限不断增大。随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这种职能让渡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其次是主权转移。国家职能的让渡最终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主权转移。在一体化进程中,各民族国家的部分主权逐步向共同的超国家共同体转移,“转移出来的某种主权有可能形成一种超民族国家性质的权力,并将其赋予有关机构”(28)。这一进程的最终结果将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拥有的绝对统辖权的终结,以及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秩序的地区体系的形成。
区域一体化是拥有自主权和管治权的民族国家向超国家的区域共同体整合的过程。一体化进程使超国家共同体取代国家的部分功能,民族国家的权力和政治权威逐步向地区共同体转移。这种转移最终将使次国家层次行为者的认同发生外溢效应。由于各地区一体化发展程度的参差不齐,这一进程在现实层面的实现程度具有地区间非均衡性的特征。东南亚地区作为发展中世界的一部分,其权威转移的程度明显较欧盟落后,但从长时段视角来看,这一客观历史进程终将改变东南亚区域社会的认同结构。
(2)认同外溢形成效忠转移的内在机制
外溢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它用来描述驱动地区一体化的过程机制。(29)新功能主义将外溢概括为功能外溢、政治外溢和地理外溢三个方面。外溢承担了新功能主义理论对一体化的绝大多数解释功能。但新功能主义没有对一体化进程中的认同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如果将外溢视为一种过程机制,它同样可以借鉴来用于一体化中认同问题的考察。效忠转移的实现过程,从本质上可以视为一种认同外溢的过程,即在一体化进程中认同由较低层次社会共同体向较高层次社会共同体外溢。
认同的这种外溢进程是国家权威转移的后果。民族国家的权力流散和权威转移,将促进后民族结构的形成。在后民族结构之中,公众的认同观念将发生变化。以具有先天继承性的自然特征为基础的民族认同逐步开始弱化,外在于民族身份的多种社会认同也将会促使这些成员结成相对稳定的共同体,民族起源的不同将不再阻碍人们将自己视为同一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民族国家不再是唯一的认同归属对象,作为后民族认同具体形式的地区认同在一体化进程中不断孕育和发展。后民族结构对社会认同的功能性需求,将导致地区认同的生长。
就东南亚地区而言,认同外溢只能是东盟一体化长期扩展与深化的渐积性结果。一体化极大地促进各民族国家民众之间的相互交往、人员流动,并使人们日益认识并接受民族起源之外的其他集体性身份向度。(30)随着东盟地区内部公共交往与社会整合的深入发展,民族认同终将弱化至不复阻碍效忠转移的实现。当属于同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共同体(民族国家)的事实,不再构成公民身份的充分基础(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认同由民族国家向地区共同体的外溢便可启动。彼时,东南亚的认同冲突将会开始消解——正如一体化起步之初东南亚安全困境逐渐消解一样,效忠转移的困境亦将迎刃而解。
新功能主义的一体化理论忽视了认同因素的作用,因此,它对一体化进程中外溢机制与效忠转移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未能给出清晰的论证。事实上,由于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主导型认同归属的转换以及与此同步的效忠转移,并非像新功能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可以轻易实现。这一问题在东盟一体化中尤为突出。东南亚地区多为“二战”后方从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的新兴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影响尤重,民族认同与地区认同之间的冲突关系尤为明显,这也使得新功能主义所设想的一体化最终导致的效忠转移面临极为艰巨的困难。但从长时段的大历史视野来看,东南亚的一体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随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地区结构会不断演进,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也会逐渐开始转移,这种外在客观深刻的变化将会影响内在认知的变化,使认同之间的冲突逐渐弱化,进而使效忠转移在东盟未来的一体化进程中最终成为可能。
①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 Charter,http://www.aseansec.org/21861.htm.
②对于一体化的理解,学界一直存在广义与狭义两种观点的分歧。笔者采信广义的理解,即一体化是原本独立的单位整合成一个更大的单位的进程或状态,哈斯和多伊奇都是持此种观点的代表。狭义的一体化则特指“二战”后出现的地区一体化。
③另一主流范式是以穆拉维斯克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政府间主义。
④Ernst 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s,Social,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6.
⑤Ernst 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s,Social,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4.
⑥陈玉刚著:《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⑦Walter Veit ed.,The Idea of Europe,Problems of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Routledge,1992,p.1.
⑧[法]埃德加·莫兰著,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2页。
⑨刘兴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第18页。
⑩这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不同,民族认同更多地强调文化与社会属性的一面,国家认同则更多地强调法律与制度属性的一面。
(11)[美]迈尔威利·斯徒沃德著,周伟驰等译:《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93页。
(12)肖欢容著:《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13)张锡镇:“东盟共同体发展趋势及其主要推动者”,《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1期,第3页。
(14)耿协峰著:《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15)Ben Rosamond,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Macmillan Press,2000,p.14.
(16)[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138页。
(17)[德]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18)梁英明著:《东南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页。
(19)这一模式是由建构主义学者提出的。[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
(20)[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21)Otten S.Mummendey,"To Our Benefit or at Your Expense? Justice Considerations in Intergroup Allocatio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ources",Social Justice Research,Vol.12,No.1,1999,pp.19-38.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1期,第476页。
(22)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mett,Security Commun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7.袁正清:“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的解析”,《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41页。
(23)徐建军:“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和利益分配”,《世界经济》,2004年第8期,第17页。
(24)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http://www.aseansec.org/15159.htm.
(25)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The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Plan of Action,http://www.aseansec.org/16832.htm.
(26)[英]苏珊·斯特兰奇著,肖宏宇、耿协峰译:《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
(27)戴炳然:“欧洲一体化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第28页。
(28)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欧洲》,1999年第2期,第45页。
(29)肖欢容著:《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0)翟金秀:“一体化变量下的当代西欧民族主义——新功能主义的视角”,《世界民族》,2010年第1期,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