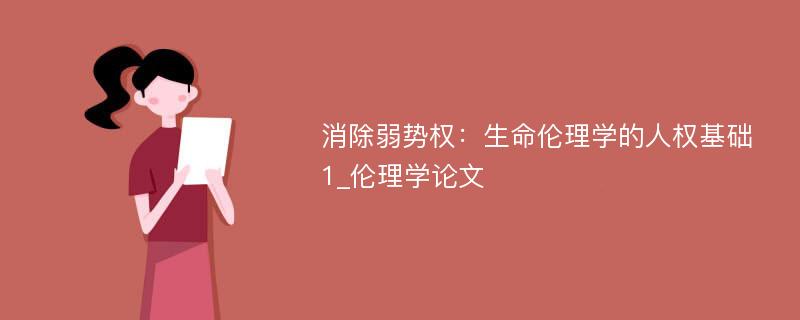
祛弱权:生命伦理学的人权基础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人权论文,生命论文,基础论文,祛弱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7.9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自古希腊以来,伦理学领域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争(如苏格拉底和智者关于德性的争论)一直绵延不绝。如今,作为道德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伦理学强调否定性、流动性、破坏性,执著于不确定化、多元化、相对化,推崇无立场、无原则的伦理学,甚至为此不惜离“家”出走,流浪荒野。后现代伦理学对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学的断然否定和全面解构,把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普遍主义之争推到空前尖锐的地步,其结果必然引发应用伦理学领域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争。生命伦理学就是激烈争论的主战场之一。
极为典型的是,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奠基者恩格尔哈特(H.Tristram Engelhardt)曾在《生命伦理学基础》(1986年)中提出了后现代伦理学境遇中的生命伦理学达成共识的基础原则:形式的允许原则和质料的行善原则②。20年之后,他在新近主编出版的《全球生命伦理学:共识的崩溃》(2006年)一书中却明确否定了后现代伦理学境遇中的生命伦理学达成共识的可能性③。恩格尔哈特前后矛盾的转变,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他何以由肯定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到宣称生命伦理学共识的溃败?生命伦理学是否可以达成共识?如果能,共识的基础又是什么?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和共识何以可能?
我们认为,脆弱性是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与脆弱性密切相关的祛弱权问题应当成为生命伦理学的核心理念和理论基础。关于脆弱性的伦理思考,正如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在《善的脆弱性》的修订版序言中所说:“即使脆弱性和运气对人类具有持久的重要性,但直到本书出版之前,当代道德哲学对它们的讨论却极其罕见。”④ 一般而言,人类社会主要推崇人类生活的乐观状态,相应地,伦理学主要推崇人的坚韧性而贬低人的脆弱性。建立在坚韧性基础上的理论形态主要是乐观主义伦理学,典型的如柏拉图以来的优生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德性论,边沁、密尔等古典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康德等古典义务论的德性和幸福一致的至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伦理学等。尤其是尼采的超人哲学过度夸大人类的坚韧性而蔑视人类的脆弱性,其推崇的必然是丛林法则而不是伦理法则,希特勒等带来的道德灾难和人权灾难就是铁证⑤。麦金太尔通过考察西方道德哲学史也指出,脆弱和不幸本应当置于理论思考的中心,遗憾的是,“自柏拉图一直到摩尔以来,人们通常只是偶然地才思考人的脆弱性和痛苦,只有极个别的例外。”⑥ 乐观主义伦理学在乐观地夸大人的坚韧性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人的脆弱性。
不可否认,对坚韧性的否定方面即脆弱性的思考也源远流长。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契约论伦理学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的国家起源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人的脆弱性。不过,脆弱性在坚韧性的遮蔽之下并未成为传统伦理学的主流。以坚韧性(理性、自由和无限性等)为基础的传统伦理学所追求的目的主要是乐观的美满和完善,即使探讨脆弱性也只是为了贬低它以便提高坚韧性的地位,如基督教道德哲学把身体的脆弱性作为罪恶之源以便为基督教伦理学做论证,或者主要是在把人分为弱者和强者的前提下对强者的关注,如尼采的超人道德哲学等。这和关注普遍脆弱性并基于此提出人权视阈的祛弱权还相去甚远。
二战以来,深重的苦难和上帝救赎希望的破灭激起了人们对自身不幸和脆弱性的深度反省,人们在反思传统乐观主义伦理学贬低脆弱性并基此夸大、追求人的无限性和完满性的基础上,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脆弱性在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这是以脆弱性同时进入当代德性论、功利论和义务论为典型标志的。当代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波普尔批判谋求幸福的种种方式都只是理想的、非现实的,认为苦难一直伴随着我们,处于痛苦或灾难之中的任何人都应该得到救助,应该以“最小痛苦原则”(尽力消除和预防痛苦、灾难、非正义等脆弱性)取代古典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⑦。如果说波普尔主要从消极的功利角度关注个体的脆弱性,麦金太尔的德性论则把思路集中到人类的各种地方性共同体,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人的生命的脆弱性和无能性为境遇的,因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靠着依赖性的德性和独立性的德性共同起作用才能维持下去的⑧。当代义务论者罗尔斯批判功利论,把麦金太尔式的个体德性提升为社会制度的德性,明确提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并把公正奠定在最少受惠者的基础上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已经把脆弱性引入了应用伦理学领域。
上述对脆弱性的理论研究和近年来新的天灾人祸和伦理问题(如恐怖事件、金融危机、环境危机、克隆人、人兽嵌合体等问题)一起,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把人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彻底摧毁了柏拉图以来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或超人的狂妄,祛弱性不可阻挡地走向前台,深入到应用伦理学各个领域,尤其是和脆弱性直接相关的生命伦理学领域。如今,在欧美乃至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法学的研究中,对脆弱性的关注和反思,业已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理论思潮。美国生命伦理专家卡拉汉(Daniel Callahan)说:“迄今为止,欧洲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法学认为其基本任务就是战胜人类的脆弱性,解除人类的威胁”,现代斗争已经成为一场降低人类脆弱性的战斗⑩。其中,丹麦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亚鲁德道弗(Jacob Dahl Rendtorff)教授、哥本哈根生命伦理学与法学中心执行主任凯姆博(Peter Kemp)教授等一批欧洲学者对脆弱性原则的追求和阐释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以自由为线索,把自主原则、脆弱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尊严原则作为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法学的基本原则,并广泛深入地探讨了其内涵和应用问题。他们不但把脆弱性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的生命伦理学原则,甚至还明确断言:“深刻的脆弱性是伦理学的基础。”(11) 这对恩格尔哈特否定生命伦理学共识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对此,智利大学的克奥拓(Michael H.Kottow)却不以为然。他特别撰文批评说,脆弱性和完整性不能作为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因为它们只“是对人之为人的特性的描述,它们自身不具有规范性”。不过,他也肯定脆弱性是人类的基本特性,认为它“足以激发生命伦理学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要求尊重和保护人权”。(12)
克奥拓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描述性的脆弱性本身的确并不等于规范性的伦理要求。他的批评引出了人权和脆弱性的关系问题:描述性的脆弱性可否转变为规范性的伦理要求的祛弱权?
克奥拓批评的理论根据源自英国著名分析哲学家黑尔(R.M.Hare)。黑尔在《道德语言》中主张,伦理学的主体内容是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具有可普遍化的规定性和描述性的双重意义,因为只有道德判断具有普遍的规定特性或命令力量时才能达到其调节行为的功能(13)。
他沿袭休谟与摩尔等区分事实与价值以及价值判断不同于、而且不可还原为事实判断的观点。他认为,价值判断是规定性的,具有规范、约束和指导行为的功能;事实判断作为对事物的描述,不具有规定性,事实描述本身在逻辑上不蕴含价值判断,因此单纯从事实判断推不出价值判断。但是,描述性的东西一般是评价性东西的基础,即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是对它做价值判断的基础(14)。道德哲学的任务就是证明普遍化和规定性是如何一致的(15)。我们认为黑尔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依据黑尔,要从描述性的脆弱性推出规范性的脆弱性,并提升为祛弱权,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脆弱性是否具有普遍性?从描述性的脆弱性能否推出价值范畴的规范性的祛弱权?如果能,祛弱权能否作为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回答了“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和共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二、脆弱性何以具有普遍性?
每个人都是无可争议的脆弱性存在,脆弱性在人的状况的有限性或界限的意义上具有普遍一致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基本层面:
其一、非人境遇中的脆弱性
每个人相对于时间、空间以及非同类存在物如动物植物等都具有脆弱性,甚至可以说“我们对外界的依赖丝毫也不少于对我们自身的依赖;在疑难情况下,我们宁肯舍弃我们自己自然体的一部分(如毛发或指甲,甚至肢体或器官),也不能舍弃外部自然界的某些部分(如氧气、水、食物)”(16)。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是生物学上的一个极为年轻的种类。赫胥黎认为,人类大约在不到50万年前产生的,直到新石器时代革命后即1万年左右,才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种类。人的自然体并非必然如今天的样式,也可以是其它模样。所有占统治地位的种类在其历程开始时都是不完善的,需要经过改造和进化,直到把它的全部可能性发挥殆尽,取得种系发展可能达到的完满结果。(17) 不过,种系发生学上的新构造越根本越彻底,其包含的弱点和不足的可能性就越大。据拜尔茨(Kurt Bayertz)说,意大利解剖学家皮特·莫斯卡蒂曾从比较解剖学的角度证明了直立行走在力学上的缺陷:皮特博士证明人直立行走是违反自然且迫不得已的。人的内部构造和所有四条腿的动物本没有区别,理性和模仿诱使人偏离最初的动物结构直立起来,于是其内脏和胎儿处于下垂和半翻转的状态,这成为畸形和疾病如动脉瘤、心悸、胸部狭窄、胸膜积水等的原因。雷姆也认为虽然能保存下来的种类都是理想的,但造化过于匆忙,给我们的机体带来了四条腿的祖先没有的缺陷,他们的骨盆无须承担内脏的负担,人则必须承担,故而韧带发达,导致分娩困难,致使人类陷入无数的病痛之中(18)。更何况,今人仅仅处在一个新的阶段,有待更长更久更完善的改进和进化。面对无限的时空和无穷的非人自然,每个人每时每地都处于脆弱性的不完善的状况之中。这种非人境遇综合造成的人类的脆弱性,甚至是当今人类不可逃匿的宿命。不过,我们的当下使命不是抱怨为何没有被造成另外的一种理想的样式,更不是无视自身的脆弱性而肆意夸大自身的坚韧性,而应当是勇敢地直面自身的脆弱性,把祛除脆弱性上升为普遍人权。
其二、同类境遇中的脆弱性
霍布斯曾描述过人对人是豺狼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暗示了任何人在面对他人时都有一种相对的脆弱性。其实,国家制度等形成的最初目的正是为了祛除个体面对他者的脆弱性。
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疾病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根本的脆弱性。患者相对于健康者尤其相对于掌握了医学技术和知识的医务人员来讲,是高度脆弱性的存在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健康之遮蔽》一书中认为,健康是一种在世的方式,疾病是对在世方式的扰乱,它表达了我们基本的脆弱性,“医学是对人类存在的脆弱性的一种补偿”(19) 医务人员相对于其他领域和专业如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也同样是脆弱者。任何强者包括科学家、国家元首、经济大亨、体育冠军等在其他领域相对于其他人或团体都可能是脆弱者。如果尼采的超人是人的话,也必然是相对于他者的弱者。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在今天,我们看不见英雄。……历史性的决定不再由孤立的个人作出,不再由那种能够抓住统治权并且孤立无援地为一个时代而奋斗的人作出。只有在个体的个人命运中才有绝对的决定,但这种决定似乎也总是与当代庞大的机器的命运相联系。”(20) 由于自我满足的不可能性,绝大多数人由于害怕毁谤和反对而被迫去做取悦于众人的事,“极少有人能够既不执拗又不软弱地去以自己的意愿行事,极少有人能够对于时下的种种谬见置若罔闻,极少有人能够在一旦决心形成之后即无倦无悔地坚持下去。”(21) 相对于他者,每个人任何时候都是弱者——既有身体方面的脆弱性,又有精神和意志方面的脆弱性,但每个人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强者。没有普遍性的坚韧,却有普遍性的脆弱。就是说,脆弱性体现着平等,强韧性则体现着差异。
其三、自我本身的脆弱性
人自身的脆弱性是自然实体(身体)的脆弱性和主体性的脆弱性的综合体。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人的存在的典型方式是身体的有限性和心灵或精神的欲求的无限性之间的脆弱的综合。”(22) 这种脆弱性显示为人类主体的有限性及其世俗的性格,我们必须面对生活世界中作恶的长久的可能性或者面对不幸、破坏和死亡。鉴此,拜尔茨说:“我们和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双重关系之中。一方面,不容置疑,人的自然体是我之存在和我们主观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思想感觉或者希望,甚至不可能有最原始的人的生命的表现。另一方面,同样不容怀疑,从我们主观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的自然体又是外界的一部分。尽管他也是我们的主观的自然基础,可同时又是与之分离的;按照它的‘本体’状态,与其说是我们主观的一部分,还不如说他是外部自然界的一部分。”(23)
我们作为个体都是身体的实体的有限性和主体性的综合存在,但个体的实体是具有主体性的实体。不但实体是有限的脆弱的,而且实体的主体性也是有限的脆弱的。康德曾阐释了人的本性中趋恶的三种倾向:“人的本性的脆弱”即人心在遵循以接受的准则方面的软弱无力;心灵的不纯正;人性的败坏如自欺、伪善、欺人等(24)。其实,这都是主体性本身的脆弱性的体现。另外,人的自然实体(身体)是主体性的基础,它本身的规律迫使主体服从,主体对自身实体的依赖并不亚于对外部自然界的依赖。就身体而言,遗传基因和生理结构形成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命运或宿命。人自婴儿起,就必须发挥其主体性去学会控制其自然实体、本能和欲望、疾病等。自然实体和主体性的对立,身体和精神的矛盾常常体现为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现象首先被看做是病态,它让我们最清楚、最痛苦不过地想到,有时候,我们的主观与我们的自然体相合之处是何等之少。”(25) 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普遍的脆弱性。
尽管脆弱性的程度会随着人生经历的不同和个体的差异而有所变化和不同,但基本的脆弱性是普遍一致的,如生理结构、死亡、疾病、生理欲求、无能等不会随着人生境遇的差异而消失,任何人都不可能逃匿自身的这种基本脆弱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被抛入到脆弱性之中的有限的自由存在,人生而平等(卢梭语)的实质就是人的脆弱性的平等。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脆弱的存在者,不论其地位、身份、天赋、修养等有何不同,概莫能外,自我和他人都是处于特定境遇之中的脆弱性主体。因此,普遍的脆弱性“或许能够成为多样化的社会中的道德陌生人之间的真正桥梁性理念。”(26) 不过,诚如克奥拓所言,身体生理、理性认识、主体性和道德实践的不足以及缺陷等脆弱性,都只是描述性的,如果它不具有价值和规范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价值范畴的人权。同时,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出现了:由于脆弱性不可能靠脆弱性自身得到克服,乐观主义伦理学有理由质疑,如果人类只有脆弱性,那么人们凭什么来保障其脆弱性不受侵害呢?
三、祛弱权何以可能?
传统乐观主义伦理学的功绩在于重视人的坚韧性(自由、理性、快乐、幸福等),其问题主要在于夸大坚韧性,忽视甚至贬低脆弱性。的确,人不仅是脆弱性的存在,而且也是坚韧性的存在。人主要靠坚韧性来保障脆弱性不受侵害。
我们认为,描述性的脆弱性或坚韧性不能形成规范性的权利的本真含义是:纯粹坚韧性或纯粹脆弱性都和价值无关,都不具备道德价值和规范性的要求。就是说,只有相对于坚韧性的脆弱性或者相对于脆弱性的坚韧性才具有价值可能性。因此,只有集脆弱性和坚韧性于一身的矛盾统一体(人),才具有产生价值的可能性。换言之,人自身的脆弱性和坚韧性都潜藏着善的可能性和恶的可能性。
其一、脆弱性既潜藏着善的可能性,也潜藏着恶的可能性。
脆弱性具有善的可能性在于它内在地赋予了人类生活世界以意义和价值。为了简明集中,我们以作为脆弱性标志的死亡或可朽作为考察对象。
尽管我们梦想不朽以及运用自己的能力完全掌握我们的身体存在而摆脱自然力的控制,但是我们总是被自身的身体条件所限制而使梦幻成空。实际上,如果生命不朽成为现实,它不但会突增烦恼、忧郁,而且必然导致朋友、家庭、工作,甚至道德本身都不必要而且无用,生活乃至整个人生就会毫无意义。因此,“不朽不可能是高贵的”(27)。康德曾经把道德作为上帝和不朽的基础,实际上应当把作为道德权利的普遍人权作为人生的基础。不朽和上帝的价值仅仅在于,它只能作为一个高悬的永远不可达到的理念,在与可朽以及其他世俗的有限的脆弱性的对比中衬托或对比出后者的价值和意义。
生命(生活)的所有的价值和意义都是以可朽(必死)为条件的。似乎矛盾的是,在生命科学领域,“一些生物医学科学家不把死亡、极限看做人类本性的根本,而宁可看做我们在未来可以战胜的偶然的生物学事件。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是否能够彻底消除所有脆弱性的问题,诸如来自我们自身的死亡、极限和心理痛苦等问题,以及这样一来会产生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因此,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各种形式的脆弱性对好生活的贡献是如此丰富和重要。”(28) 脆弱性和有限性使追求完美人生的价值和德性具有了可能性,“道德的美和崇高在于我们能够捐献自己的生命,不仅是为了好的理由而牺牲,也是为了把我们自己给予他人。如果没有脆弱性和可朽,所有德性如勇敢、韧性、伟大的心灵、献身正义等都是不可能的。”(29) 脆弱性不应当仅仅被看做恶,它应当被看做需要尊重的生命礼物和人类种群的福音。生命意义的根基就在于我们是在不断产生和毁灭的宇宙中生活的世俗存在。脆弱性基此使善和德性具有了可能性。
脆弱性使善具有可能性本身就意味着它使恶也具有了可能性。因为如果没有恶,也就没有必要(祛恶)求善。恶是善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奥古斯汀在晚年所写的《教义手册》中,曾从宗教伦理的角度阐释了脆弱性与恶的关系。他把恶分为三类:“物理的恶”、“认识的恶”和“伦理的恶”。“物理的恶”是由于自然万物(包括人)与上帝相比的不完善性所致,任何自然事物作为被创造物都“缺乏”创造者(上帝)本身所具有的完善性。“认识的恶”是由人的理性有限性(主体性)所决定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达到上帝那样的全知,从而难免会在认识过程中“缺乏”真理和确定性。“伦理的恶”则是由于意志选择了不应该选择的东西,放弃了不应该放弃的目标,主动背离崇高永恒者而趋向卑下世俗者。在这三种恶中,前两者都可以用受造物本身的有限性来解释,属于一种必然性的缺憾;但是“伦理的恶”却与人的自由意志(主体性)有关,它可以恰当地称为“罪恶”。奥古斯汀说:“事实上我们所谓恶,岂不就是缺乏善吗?在动物的身体中,所谓疾病和伤害,不过是指缺乏健康而已……同样,心灵中的罪恶,也无非是缺乏天然之善。”(30) 我们认为,如果祛除其上帝的神秘性,这三种恶其实就是人的脆弱性、有限性的(描述性的)较为完整的概括。如果说(对人来说的)“物理的恶”是自然实体即身体的脆弱性的话,“认识的恶”、“伦理的恶”则是主体性的脆弱性。由于脆弱性使人易受侵害,这就使它潜在地具有恶的可能性。奥古斯汀的错误在于他把描述性的脆弱性和其价值(恶)简单地等同起来,因为脆弱性只是具有恶的可能性,其本身并不就是恶,更何况它还同时具有善的可能性,且其本身也并不等于善。
脆弱性之所以潜藏着善恶的可能性,是相对于与之一体的坚韧性而言的,就是说:
其二、坚韧性既潜藏着善的可能性,也潜藏着恶的可能性。
1771年,康德对皮特·莫斯卡蒂反对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了哲学批判,并肯定了坚韧性(主要是理性)的善的可能性。他说,人的进化固然带来了诸多问题,“但这其中包含着理性的起因,这种状态发展下去并在社会面前确定下来,人便接受了两条腿的姿势。这样一来,一方面,他有无限的胜出动物之处,但另一方面,他也只好暂且将就这些艰辛和麻烦,并因此把他的头颅骄傲地扬起在他旧日的同伴之上。”(31) 我们同意康德的观点,即人直立行走等带来的脆弱性的代价赋予了人类独特的理性和自由等坚韧性。与脆弱性相应,坚韧性也体现在三个基本层面:非人境遇中的坚韧性、同类境遇中的坚韧性,以及集生理、心理和精神为一体的自我的坚韧性。坚韧性既有可能保障脆弱性(潜藏着善的可能性),也有可能践踏脆弱性(潜藏着恶的可能性)。
一方面,坚韧性潜藏着善的可能性。如果说“物理的善”的可能性是自然实体即身体的坚韧性,“认识的善”的可能性指理性具有追求无限的可能性,使人具有祛除认识不足的可能性,“伦理的善”的可能性则是主体坚强的自由意志使人具有克服脆弱性的可能性。就是说,个体的坚韧性使主体自身具有帮助扶持他者的能力,并构成整体的坚韧性如伦理实体、国家、法律制度等的基础。因此,个体的坚韧性使他者的帮助扶持和主体保障其自身的脆弱性不受侵害,以便扬弃克服其脆弱性的自我提升得以可能。因为如果主体自身丧失或缺乏足够的坚韧性,只靠外在的帮助,其脆弱性是难以根本克服的。不过,坚韧性的这三种善只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比如,生命科学本身就是人类坚韧性的产物,它使人具有有限地祛除脆弱性的可能性。不过,只有生命科学实现其作为治病救人、维持健康、保障人权、完善人生的目的和价值时,才具体体现出了坚韧性祛除脆弱性的善。
另一方面,坚韧性也潜藏着恶的可能性。坚韧性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同时意味着它有能力践踏和破坏脆弱性,即具有恶的可能性——具有“物理的恶”(利用身体控制他人身体或戕害自己的身体)、“认识的恶”(利用知识限制他者的知识、戕害自己或危害人类)和“伦理的恶”(自由地选择为恶)的可能性。这在医学领域特别突出。医学本身是人类坚韧性的产物,但作为纯粹实证科学的医学把各种器官、结构仅仅根据身体功能看做生理过程和因果性的机械装置,它把疾病仅仅规定为能够导致人体器官的生理过程的客观性错误或功能紊乱。这种观念植根于解剖学对尸体分析的基础上:解剖学易于把身体作为一个物件和有用的社会资源,“当身体作为科学和技术干预的客体时,它在医学科学领域中不再被看做一个完美的整体,而是常常被降格为一个仅仅由器官构成的集合体的客体。”(32) 实证的医学生命科学没有把人的身体看做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存在,亦没有把克服人体的脆弱性以实现人体的完美健康作为目的,从而丧失了人性关怀和哲学思考而陷入片面的物理分析,背离了其本真的目的和价值。这样一来,生命科学就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可能途径之一。
既然人的脆弱性和坚韧性都同时具有善与恶的可能性,那么,
其三、祛弱权何以具有人权资格?
如上所述,描述性的脆弱性是相对于坚韧性而言的,它本身就潜藏着价值(善恶)的可能性。因此,从包含着价值的脆弱性推出作为价值的祛弱权并不存在逻辑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既然每个人都是坚韧性和脆弱性的矛盾体,他就同时具有侵害坚韧性、提升坚韧性、侵害脆弱性和祛除脆弱性四种(价值)可能性。何者具有普遍人权的资格,必须接受严格的伦理法则的检验。
检验的标准是普遍性,因为人权是普遍性的道德权利,而且道德判断必须具有普遍的规定性(黑尔)。所谓道德普遍性,就是康德的普遍公式所要求的不自相矛盾。康德认为道德上的“绝对命令”的惟一原则就是实践理性本身,即理性的实践运用的逻辑一贯性。因此,“绝对命令”只有一条:“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而行动。”(33) 在这里,“意愿”的(主观)“准则”能够成为一条(客观的)“普遍法则”的根据在于,意志是按照逻辑上的“不矛盾律”而维持自身的始终一贯的,违背了它就会陷入完全的自相矛盾和自我取消。我们据此检验如下:
1.侵害坚韧性,必然导致无坚韧性可以侵害的自相矛盾。
2.提升坚韧性。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其坚韧性,尤其在后天的环境和个人机遇以及个人努力造就自我的生活世界中,人的坚韧性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多样性,且使人的差异越来越大。如果把提升坚韧性普遍化,结果就会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同时破坏坚韧性和脆弱性为终结,导致自相矛盾和自我取消。
值得重视的是,虽然提升坚韧性不具有普遍性,不可能成为人权,但可以成为(在人权优先条件下的)特殊权利。合道德性的特殊权利必须以不破坏人权平等为基准,以保障提升人权平等的价值为目的。否则,特殊权利就会导致而且事实上已经导致了人权平等的破坏。《世界人权宣言》等正是对这种破坏的抗议和抵制的经典表述。
3.侵害脆弱性。如果人们提出了侵害脆弱性的要求,这就会危害到每一个人,终将导致人权的全面丧失和人类的灭绝,这是违背人性的自相矛盾和自我取消。
4.祛除脆弱性。如前所述,没有任何一个人始终处在坚韧性状态,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时刻处在脆弱性状态,即都是脆弱性的并非全知全能全善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祛除普遍的脆弱性的价值诉求在道德实践中就转化为具有规范性意义的作为人权的祛弱权。就是说,描述性的脆弱性自身的价值决定了每个作为个体的人都内在地需要他者或某一主管对脆弱性的肯定、尊重、帮助和扶持或者通过某种方式得以保障,这种要求或主张为所有的人平等享有,不受当事人的国家归属、社会地位、行为能力与努力程度的限制,它就是作为人权的祛弱权。婴儿、重病人等尚没有或者丧失了行为能力的主体不因无能力表达要求权利而丧失祛弱权。相反,正因为他们处在非同一般的极度脆弱性状态而无条件地享有祛弱权。对于主体来讲,这是一种绝对优先的基本权利。其实质是出自人性并合乎人性的道德法则——因为人性应当是坚韧性扬弃脆弱性的过程。这合乎理性的实践运用的逻辑一贯性,因此,祛弱权是普遍有效的人权。
这就回应了克奥拓的批评,解决了亚柯比等人的描述性事实到规定性的人权的过渡问题。至此,祛弱权作为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何以可能?或者生命伦理学达成共识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祛弱权这里,恩格尔哈特所谓的“共识的崩溃”也就彻底崩溃了。这样一来,祛弱权就为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共识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结语
由于应用伦理学所直面的各种价值冲突从根本上说均体现为人权之间的冲突,因而对人权理论的深入探究,已经成为应用伦理学本身逾越其发展瓶颈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这一点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业已形成共识。然而,就具体的各个应用伦理学领域而言,各自应当以何种人权作为其价值基准尚远未达成共识——恩格尔哈特所谓生命伦理学视阈的“共识的崩溃”正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体现之一。
生命伦理学探讨的话题是以研究人的脆弱性、坚韧性为基点,确定“集脆弱性与坚韧性于一体”的人的地位和权利,最终辨明处于这一地位的人如何被置于治病救人、造福众生这一崇高的医疗事业的目标之下。这就决定了生命伦理学所直面的各种价值冲突如堕胎、安乐死、治疗性克隆、人兽嵌合体等引发的人权冲突问题,应当具体体现为(人权范畴的)祛弱权之间的冲突。因而,深入探究祛弱权,确立祛弱权在生命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从祛弱权的全新视角反思、审视、研究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人权冲突问题,将为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尝试、新的方法,为相关问题如人兽嵌合体、克隆人、医患冲突、医疗改革等方面的立法提供新的哲学论证和法理依据。
注释:
① H.Tristram Engelhardt,The Foundations of Bioeth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P.66,-103.
② H.Tristram Engelhardt edited, Global Bioethics: The Collapse of Consensus, Salem, Mass:M&M.Scrivener Press.2006,pp.2 - 15.
③ Martha C.Nussbaum,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reface.
④ Richard Weikart,From Darwin to Hitler:Evolutionary Ethics,Eugenics,and Racism in German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71-103.
⑤ Alasdair MacIntyre,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Why Human Beings Need Virtue,Chicago:Cams Publishing Company,1999,p.1.
⑥ See Karl Raimund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I,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237-239,pp.284-285.
⑦ Alasdair MacIntyre,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Why Human Beings Need Virtue, Chicago:Carus Publishing Company,1999,p.1.
⑧ See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3,pp.302 -303.
⑨ Jacob Dahl Rendtorff and Peter Kemp (ed) ,Basic Ethical Principles in European Bioethics and Biolaw,Vol.I.,Printed in Impremta Barnola,Guissona ( Catalunya - Spain),2000,p.46.
⑩ 同小注⑩,p.49。
(11) Michael H.Kottow,“Vulnerability :What Kind of Principle Is It?”,Medicine,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Volume7,Number3.2005,pp.281 -287.
(12) Richard Mervyn Hare,The Language of Mora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31.
(13) 同上,p.111。
(14) See Richard Mervyn Hare,Freedom and Reas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4,pp.16 - 18.
(15) 库尔特·拜尔茨:《基因伦理学》,马怀琪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16) 同上书,第217-218页。
(17) 同上书,第218-222页。
(18) Jacob Dahl Rendtorff and Peter Kemp (ed),Basic Ethical Principles in European Bioethics and Biolaw.Vol.I.,Printed in Impremta Barnola,Guissona ( Catalunya - Spain) ,2000,p.51.
(19) 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20) 同上书,第156页。
(21) Jacob Dahl Rendtorff and Peter Kemp (ed) ,Basic Ethical Principles in European Bioethics and Biolaw.Vol.I.,Printed in Impremta Barnola,Guissona ( Catalunya - Spain) ,2000,p.49.
(22) 库尔特·拜尔茨:《基因伦理学》,马怀琪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10-211页。
(23) 《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5-315页。
(24) 库尔特·拜尔茨:《基因伦理学》,马怀琪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25) Jacob Dahl Rendtorff and Peter Kemp (ed) ,Basic Ethical Principles in European Bioethics and Biolaw.Vol.I.,Printed in Impremta Barnola,Guissona ( Catalunya - Spain) ,2000,p.46.
(26) Jacob Dahl Rendtorff and Peter Kemp (ed) ,Basic Ethical Principles in European Bioethics and Biolaw.Vol.I.,Printed in Impremta Barnola,Guissona (Catalunya- Spain) ,2000,p.50。
(27) 同上书,p.48。
(28) 同上书,p.50。
(29)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0页。
(30) 库尔特·拜尔茨:《基因伦理学》,马怀琪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18-222页。
(31) Jacob Dahl Rendtorff and Peter Kemp (ed) ,Basic Ethical Principles in European Bioethics and Biolaw.Vol.I.,Printed in Impremta Barnola,Guissona ( Catalunya - Spain),2000,p.42.
(32)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