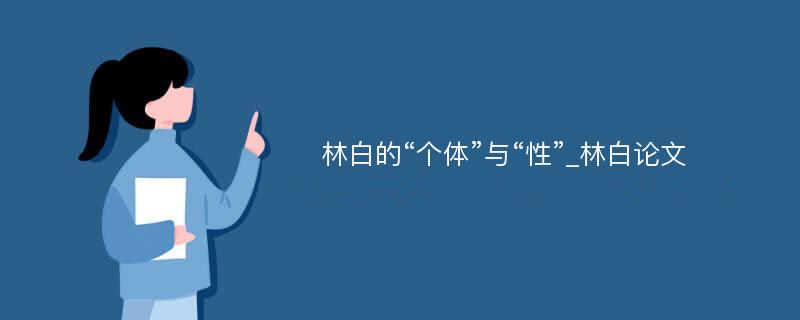
林白的“个人”和“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上总有一些作家,他们或她们生逢其时地与某个文学风尚相遇,成为这一风尚的核心,甚至旗帜,并最终被文学史所铭记。他们或她们与这一文学风尚互为表里,形成榫铆贴合、水乳交融的阐释关系;这种阐释关系,放大了他们或她们的文学意义,使其成为“经典化”道路上的醒目标记,甚至跻身“经典”之列。当然,这种阐释关系在将其文学意义推向极端的同时,也可能将其文学写作的其他向度进行了删削或遮蔽,使其文学意义在醒目的同时又不免显得扁平、狭窄。
可以肯定地说,林白就属于这样的作家。尤其是,她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与“女性写作”两个文学风尚交叠中的核心人物:她不仅在有关“个人化写作”的种种阐述中被频频提及,她同时也是近二十年来批评界在阐述“女性写作”时的“经典”人选。特别是后一类的阐释,使她的文学意义和她作为作家的个人形象逐渐在“性别写作”的论域中定型。
一、个人、历史与宏大叙事
“个人化”是个人主义的别称,它归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并在其时“新启蒙”的整体氛围中被暗中鼓励,被积极怂恿,直到泛滥。个人化或个人主义不仅将文学从所谓“大写的人”引向“小写的人”,也使始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从所谓的“共名”迈入“无名”。它虽是现代性的启蒙话语之一种,但其内部却潜藏了对于启蒙——尤其是以种种宏大叙事为元话语的启蒙——的深刻怀疑和逐渐拒斥,因此,它很容易地就发展成为一种解构力量,与“总体性”、“整体性”和“群体性”形成对峙。“个人”被单独剥离为一个价值范畴,它不再与“公众”、“群体”形成归属关系,相反,它与“公众”、“群体”之间的断裂被强调、被凸显,甚至它被强调为优先于“公众”、“群体”的价值前提。在文化上。“个人”意味着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解约;在文学上,“个人”意味着对“民族寓言”式写作传统的裂解。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也很自然地陷入了命名中的某种悖反:“个人”既是风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种写作风尚或写作群体的命名方式,它同时又是对风尚和群体命名进行抵抗的方式。这种悖反,深刻地影响了林白,并成为我们今天回头讨论林白这近二十年文学演进时的思路。
林白本人显然认同“个人化写作”的文学标签,并曾亲自释义:“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①林白的这段话贴合批评界对于“个人化”写作的基本定义,只不过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被提出并由她亲自确认:性经历。就这样,由于作家本人的“现身说法”,一直以来,“个人”与“性”,就成为用以解读林白的全部钥匙和全套密码。
但是,尽管有了这钥匙和密码,这么些年来对林白的讨论,真正深入、精微的却一直不多。比如,因为“性”的介入,在讨论林白这样的女性作家时,“个人化写作”就滑向了“私人写作”的另一端口,进一步成为与“宏大叙事”无限割裂、绝对无缘的文学,由此,林白的文学更多地被塞进“性别结构”内部进行讨论,并且,尽管对林白的“性”的讨论有着“身体政治”的学术修辞,但实际上基本都在生理主义的或是本质主义的泥淖里打滚。迄今为止,仍然只能在一些讨论中,零星地看到批评界对林白式的“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写作”所蕴涵的政治关系与“历史意义”的阐明。这里所谓“历史意义”,在我看来,是指林白的文学乃一种新的宏大叙事,一种积极地、创造性地改造世界的政治宣示,一种在重新刷出的起点上展开的历史叙事。当她的“个人写作”与“女性写作”相交叠的时候,她所谓的“一个人的战争”所体现的,是一个远比“个人”和内在的群体意志对于改写历史的更深广的剧烈冲动。
“个人化写作”虽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AI写作作风尚的命名,但实际上它早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文学大潮中派生、发轫,而且,女性作家——如张辛欣、张洁等则是其时重要的揭幕者、先驱者。王安忆在谈论八十年代文学时就认为,其时像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这样的作品就已然是“‘个人’终于上升为‘主义’”。②但是,此时张辛欣式的个人主义仍然属于“新启蒙”的宏大叙事,它表达的是与男性在同一地平线上共同成为历史主体的精神与文化诉求,并被轻易地整合进八十年代主流文化的建构。然而,林白式的“个人主义”则发展出了更为极端的意义。林白式的“个人写作”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个人写作”时所强调的“个人”与“历史”的解约,相反,因为林白对于性别立场的坚执,使得她写作上对于“历史”这一包含“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在内的公共、集体话语的有意疏离,变成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这种新的历史书写,起源于林白式的个人化/私人化的“性经历”的介入和参照——由于有这样的介入和参照,“历史”被放进性别政治的光谱试剂中鉴定,成为一个讨论政治压迫的分析范畴。在这样的历史辨析中,既有的“历史”被裁定为由男性/男权专有,因此,张辛欣式的试图与男性在同一地平线上共同成为历史主体的愿望,在林白这里被视为是一种错误和一种虚妄。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里,男性作家所坚持的“个人化写作”有终结“历史”的意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男性作家,历史确乎已经终结,因为历史的权杖在男性的手中从未易手过。但“历史”对于这些男性作家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即便是要确立“个人”的意义,仍然需要“历史”这一否定项的存在。在这个对峙关系中,“历史”越饱满、越强悍,“个人”就越锐利、越坚实。然而,对于女性作家来说,既有“历史”被否定之后,作为女性“个人”的意义仍然是虚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女性从来没有过“历史”,而“历史”是确立意义和价值的终极结构,存在的所有意义都是由历史给出的,一切意义皆植根于历史。也正因如此,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潮流里,男性作家的“性”或欲望叙事,被视为是针对道统或其他一切宏伟结构的批判性颠覆,通过这样的颠覆,最终确立了个人或自我的主体性,而林白式的“性”则总是被对象化、客体化,成为“文明”视野中的疯癫,成为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歇斯底里。如果检索一下当年对“个人化写作”的批评意见就不难发现,男女作家各自的“欲望叙事”所遭受的伦理驳难,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因此,林白的“性”必须被引渡到“女性写作”的立场上才能获得合法性的支持。由“个人化写作”提供给她的写作契机,必须在“女性写作”的意义域中发扬,而她最终在对“个人化写作”的评价中遭遇的困厄,也必须且只能在“女性写作”的意义域中得以化解。正是在这个意义域中,林白的“个人化写作”被理解为是一种新的历史书写,即通过一种建设性的历史书写,搭建那个可以为女性及其存在提供意义和价值的终极结构。
林白式的“个人化写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认为是“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③因此它很快被以“私人化写作”重新命名。这种“私人化写作”在内容上体现为与“性”紧密联结的个人经验史,是对自我个人“成长的故事”的讲述。换言之,《一个人的战争》这样的作品可称为自传体小说。而“私人化写作”命题中的“自传”则强调和表明了一种个人方式的纯粹性,即将个人经验从“主流历史”中分延,并拒绝个人的意义只能从“主流历史”中获得的历史意识。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这样的对比: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个人成长史,被认为只有植入到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与更为壮大的历史洪流中才是有意义的。就像一棵树苗必须植进土壤,才能获得水分、营养及其他生命之本。但在林白式的个人成长小说中,只剩下女性的“个人”或“私人”,作为土壤的“历史”被抹去了。这意味着,女性及其个人不需要参照男性及其历史(“历史”已被鉴定为是男性的)来获取意义并进行自我定义。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波伏娃曾这样说过:“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④而正是林白式对“历史”的拒绝,才使女性成为“绝对”,而个人成长中的女性个人经验才获得了“纯粹性”。
曾有论者指出,林白式的“个人写作”更加强化了“一种稗史写作的含义”。⑤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稗史”相对于“正史”而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通常表现为彼此消解和相互否定。如果说,“个人化写作”在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中还表达着一种试图作为历史主体参与“正史”的文化诉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则一并消解了历史“本体”及其“主体”的全部合法性,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则将女性写作彻底从“正史”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被引渡到“稗史”层面的、全新的历史书写。
与此同时,在女性主义看来,在“个人化写作”中发露的个人经验,同时也是无数未被讲述和未能讲述的女性经验中的一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个人也是女性群体的。因此,林白在叙事中展露的个人经验同时也被认为是性别(群体)经验。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看来,“讲述女性自己的经验即是为自己命名。让经验从话语层面浮现出来从而‘凝固’为意义,这正是今日女性的写作目标和进入历史的途径之一”。⑥也因此,在女性写作的视阈里,林白式的“个人化写作”恰恰是反个人的,她自传式的历史书写则恰恰是被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所质疑和放弃的宏大叙事。
二、性及其政治
林白的“性”,一度惊世骇俗。因此,大多数时候,林白的“性”都是被作为“震惊美学”来理解的,虽然这个理解程序并不推拒性别政治。
马尔库塞曾说,性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⑦这句话可以进一步被女性主义挪用来说明,今天的女性写作中有关爱欲的种种叙事,是色彩鲜明而浓郁的政治实践。埃莱娜·西苏也直接表明过这样的观点:“她的内驱力的机制是巨大非凡的……她的利比多将产生的对政治与社会变更的影响远比一些人所愿意想象的要彻底得多。”⑧也正是在这里,林白式的“个人化写作”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般而论的“个人化写作”分道扬镳: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中的欲望叙事通常被认为是反深度的,是不及物的,它既没有道德和理想的语义关联,也没有崇高或优美的美感形式,它只是“以肉身颠覆终极意义的欲望化叙述”,⑨因此,在那样的欲望叙事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接一个的色情化场景的描写,一个又一个勾引故事的上演,它们构成了从一个欲望到另一个欲望的能指链,构成了无深度的欲望化文本,并且,无论是作为写作主体的作家还是作为在文本中行动着的个体,都在欲望的裹挟、卷涌和冲蚀中丧失主体性。但对于林白来说,“欲望”不可以没有深度,不可以没有终极意义,尤其不可失却主体性,因为“欲望”或“性”在女性写作中有其政治上的深远意义:它是男权机制的解码器。
《一个人的战争》作为一部“成长小说”,被深刻地嵌入了有关身体、性经历的欲望叙事中。“成长”作为生命经验的形成与展示,其中的历史内涵越来越被抽空,欲望的气息却越来越浓郁。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多米五岁时就开始了对身体的充满色情质的体验,她在单调、无聊、郁闷的生活中学会了自慰,有了“没有人抚摸的皮肤是饥饿的皮肤”的欲望感受,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身体的秘密,掌握了快乐的节奏与强度。之后有初潮,曾热衷于偷窥,曾经历过被强暴与被诱奸,经历过怀孕和流产,最后陷于同性之恋而不能自拔。这样的身体或性经历的描写,尽管仍然存在被男性欲望重新对象化的危险,仍然存在被商业逻辑再度编码的现实,但它还是被视为女性写作中政治书写的有机部分,因为,很显然,在我们的写作传统中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性表达的主动/被动关系被有力地扭转了。正是基于对这样的一种关系扭转的价值考量,所以有论者会说:“使身体及性爱登场,便可能成为显露女性生命经验,呈现女性的主体性的历史机遇。”⑩《一个人的战争》与张洁在《祖母绿》中用让曾令儿“用一个晚上走完一个妇女一生的路”的压缩式的写法不同,林白放大了“一个晚上”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过程与每一个心理瞬间,让“一个晚上”变成无法终结的“在路上”。在漫长的叙述中,那些闪烁着欲念和幻想的性经验,那些源于个人情史与私密记忆的故事,都曾是主流叙事的禁忌,当它成为无法被男权“同一性”所整合、所融化、所阐释的文学形象时,它作为“差异”使自己获得了意义。与此同时,也是相当重要的,正如在女性主义视野中“女性个人”与“女性群体”常常交叠,女性写作中的性经验也常被当作性别经验加以对待。因此,这“差异”不仅被视为是“性经验”的,也被视为是“性别经验”的。这些经验的发掘、呈现、讲述和“凝固”,是重建主体性的前提条件。
林白之所以在其诸多小说中加大“欲望”的强度,很大的原因在于她对经典爱情中的权利关系的参透。在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的写作谱系中,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虽递交了一份有关男女之爱的纯净的精神盟约,但男性崇拜和禁欲主义显然是其叙事核心: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遥不可及的背影的一生仰望,毫无疑问地揭示了经典爱情中性别关系的隐形政治。因此,林白式的强力欲望叙事,旨在揭破那些借助爱情的神圣理由对女性进行的剥削与榨取。在林白看来,是与身体或性紧密相关的欲望(而不是爱情),才使男人女人真正地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因此,经典爱情叙事所固有的浪漫诗性,被林白所拒斥,她在《一个人的战争》中用“傻瓜爱情”来形容多米与男性的欲望关系,并大量地针对男性使用充满厌男症气息的躯体修辞。
毫无疑问,林白的“性”使她在同时代女性作家中走得更远、更激进。《一个人的战争》是从多米的自慰开始的;当她成年以后陷入“傻瓜爱情”时,她也毫不掩饰地表明,“我跟他做爱从来没有过高潮,从未有过快感,有时甚至还会有一种生理上的难受”。这个耽于自慰这一自体化欲望化解方式的女人,终于成为一个拒绝被男人洞穿的女人。她拒绝在欲望关系中被男性欲望所格式化,从此陷入了自我幽闭。实际上,自体化欲望就是在欲望关系中抹去男性这一维,让女性自己成为“一”,成为“绝对”。因此,自体化欲望虽然意味着对孤独的一种自我选择,但这种选择在林白那里是一种批判性的选择。林白声称:“也许孤独的人会在孤独中获得自由,他们的心灵是一片草地,对于这个世界日益堆积的混凝土、塑料、磁盘以及废水,没有通道也许会更好。”(11)因此,一些与幽闭、孤独相关的意象在林白的小说中频繁出现:房间、蚊帐、浴室或镜子,女性人物则通常在其间自闭、自恋、自语。这一倾向也导致林白的小说有一种内省式的独白风格。她自己就曾说:“我的许多小说……它们全都是来自我心灵深处的独自。独白是一种呼吸,一种结构,一种呻吟和呐喊。又是翅膀,又是舟楫。”(12)而这些独白又加强了她小说的幽闭气息。这种孤独、幽闭,其实未必如一般论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逃离”,相反,它更是一种拒绝。林白正是让她的小说女性人物通过这种“拒绝”来显示其主体性,并使自体化的欲望方式成为针对性别政治的反抗形式。用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题记中的话来说:“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
当然,也几乎是必然地,林白会进入对另一激进欲望关系——姐妹情谊,以及作为它的终端形式的女同性恋模式的书写。在西方,在经典女性主义立场上,姐妹情谊或女同性恋,“不只是作为一种‘性选择’或‘另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不是作为少数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对统治秩序的最根本的批评,是妇女的一种组织原则”。(13)林白在这方面的写作,贴近这样的定义。在她的《瓶中之水》里,服装设计师二帕在情感上有记者意萍依托时,她便灵感泉涌,而当意萍离她而去时,她便碌碌无为,灵感全失。当然,林白并不想把这种关系描绘成一种纯粹的精神同盟,而是让它在欲望的层面交织,并寄予婉丽而热烈的赞叹:在《致命的飞翔》中,李莴与北诺的激情交合使她们的身体熠熠生辉,而男人的触摸和侵入却只会让她们身体硬冷、欲望凝结;在《回廊之椅》中,朱凉与女仆对彼此身体的互相激赏,同样在林白的叙述中充满肉欲但芬芳的气息。凡此种种,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性别理念:如果连交媾都可以由同性代替,那么,男权世界还有什么不可取而代之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林白对同性恋模式的叙写展示了她对性别政治幽深腹地的挺进,即“对统治秩序的最根本的批评”,这也使她的写作呈现了完整的政治性。
三、语言、自传体及其他
林白的“性”或有关身体、欲望的叙事,很少被进行语言学上的解读。
有论者指出,不少女性作家为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设置了相当怪异的名字,“所有那些名字都包含一些寂寞的、幽暗的和优美的色彩,这和男性命名和书写的女性有很大的不同”。(14)若以林白为例,则有邸红、多米、七叶、二帕、嘟噜、北诺,等等。此外,林白还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笔法,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了一些特征鲜明的象喻系统,如“镜子”、“房间”、“血”、“飞翔”。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最初发表时题目为意味深长的“汁液”。这些语符与象喻系统,接近于克里思特娃(又译克莉斯蒂娃)所说的“符号”(又译“记号”)。它产生于语言的矛盾、无意义、混乱和空缺之处,联系着与“象征界”相对峙的“想象界”,是象征秩序之外的语言。特里·伊格尔顿说:“克里思特娃将这种记号‘语言’看作是破坏象征秩序的一种手段。”(15)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林白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讨论“身体”和“语言”的理路。林白的写作表明,身体写作不只是描写躯体,不只是在写作中将女性问题身体化、将女性身体对象化和客体化,相反,她一直努力寻找身体、语言和世界之间的秘密通道,强调“身体”与“语言”之间的等价关系,这使得对“身体写作”的讨论进入到将“身体”视为能指的语言学或叙事学价值层面。可以这么说,从林白式的身体写作开始,身体写作才被视为一种革命性的语言实践。
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里借助主人公多米对写作状态的描述而阐发过身体与写作(语言)之间互相打开、互相支持的关系:“这是我打算进入写作状态的惯用伎俩,我的身体太敏感,极薄的一层衣服都会使我感到重量和障碍,我的身体必须裸露在空气中,每一个毛孔都是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它们裸露在空气中,每一个毛孔的深处、沉睡的梦中那被层层的岁月所埋葬所阻隔的细微的声音。”(16)也就是说,在林白看来,语言和身体之间存在一种共振关系。依丽格瑞就曾表述过这样的共振关系:“女人却全身都是性器官。她几乎能随时随地体验快感……无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说她容易激动,说她不可理喻,说她心气浮躁,她说变幻莫测——当然还说她的语言东拉西扯,让‘他’摸不着头绪。对于理性逻辑而言,言辞矛盾似乎是疯话,使用预制好的符码的人是听不进这种语言的。女人至少敢于说出来,在自己的声明中重新不停地触摸自己。她几乎从不把自己与闲话分开,感叹、小秘密、吞吞吐吐,她返回来,恰是为了从另一快感或痛感点重新开始。”(17)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以及其他小说篇什中的许多段落中,那些絮叨的、复沓的、回环往复的、非线性、非逻辑的语体与叙述,似乎都能在依丽格瑞这里找到理论上的支撑与诠释。
但是,依丽格瑞虽然强调身体嵌入语言后可促使语言改变自身的结构形式,从而使“预制好的符码”失效,但她的这一说法仍然容易遭受“本质主义”的诟病。而林白的“共振”则更强调,改变后的语言要进一步使“身体”摆脱单纯的生理-生物的客观性状态的限制,从而向着更开放的意义层次的空间拓展。她说:“我一直想让性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性的快感。”(18)她的这一说法显然可以起到对依丽格瑞进行纠偏的作用。我们很容易在林白小说的各种性描写中获得印证:当密集的“身体意象”被形诸语言。语言便显得“毛茸茸、湿漉漉的,滑爽,通畅,是从她身上各个开口处流淌出来的”,(19)与此同时,“身体”和“语言”都僭越了成规而各有拓展,尤其是,林白总能以其精妙的修辞让语言提升身体的“意义”,并使这“意义”处于诗性的多义、开放状态。
由于语言这一“预制好的符码”被认为由男性发明或至少已被男权文化污染,从而是男权机制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主要部件,因此,女性写作被认为是“穿越布雷区的舞蹈”,危机四伏,语言的每一次使用都有可能陷女性自身于自我瓦解、自我湮灭的语义黑洞。如何抵抗和破解这一“预制好的符码”,是女性写作专注于语言革命的重要而内在的动因。就这样的“语言革命”而言,林白是少数为此贡献巨大的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之一。
此外,文体也是广义的语言形式。前述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代表的自传文体所具有的语言学或叙事学上的“政治”意义,一直以来也未被批评界充分地认识和重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从小说发生学的角度出发,认定“小说是伴随着十七世纪妇女所写的自传而开始的”,(20)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它成了女性作家在进行文体选择时的一种本能、一种自觉,因为,“为取得作者、人物、读者的契合,掩饰作品的虚构性,几乎总是女主角讲述自己的故事,沿用一种自传体的形式”。(21)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毫无疑问并非作家本人的自传,但一方面因为它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与林白本人的真实经历或真实传记(如林白的《流水林白》)构成一定的互文、互证、互释关系,另一方面则因为自传文体的运用,造成了作者、叙述者及小说人物之间关系界限的模糊,使得那些在小说中展开的、带有强烈自我体验色彩的成长秘密和私人经验显得权威、真实、可靠。华莱士·马丁在谈到自传的写作意义时说过:“一个人的故事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的故事少一点臆断性,因为后三者都是假定实体。在自传中我可以发现因与果的关系的第一手证据,而这种关系是历史学家必须推断而小说家们必须想象的:外界与内心、行动与意图。”(22)林白在其多部小说中展开的“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以它的“非假定实体”的仿真修辞,推进着关于女性个体或群体经验的真实性、可靠性的确证,而正是有了这样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的确证,方能使读者不致于对进入《一个人的战争》式的叙事文本后获得的震惊体验产生怀疑。
与此同时,所有的自传都将通过一系列成长故事来构建一个自我形象。对于自传体的女性小说来说,同样也要构建一个女性作家乐于认同的自我形象。正是在这个自我形象的构建上,林白的写作与此前的女性自传发生了悖离。在杨沫式的自传体小说里,女性自我形象都是按某种预设模式来构建的,经过意识形态的削减,其自我体验与个人意识都相对薄弱,甚至欠缺。而林白的自传体叙事,则以个人的性经历为核心内容,其中的自我形象完全逸出了传统性别话语的栅栏,成为时代与社会的“异类”。马丁说:“如果我的‘自我’是独特的,那么根据社会的或宗教的规范就无法充分地理解。”(23)林白就是用仿真性的自传体叙事构建了“独特的”、无法为“社会的或宗教的规范”所充分理解的“自我”。可以这么说,正是这种构建“独特自我”的自传体写作,林白设置了难以被男性作家所模仿或复制的叙事难度。正因为这种难度的存在,使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文本形态有了属于自己的结构、肌理和色泽,某种意义上,它也意味着女性长期由男性代言的历史被终结。
最后,我还想提及林白的近作《长江为何如此远》,以讨论长期以来对林白以及由她所代表的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批评所存在的某些偏误——如本文在开头时所说,正是这样的偏误,使林白的文学意义显得扁平和狭窄。
《长江为何如此远》让我感慨良多。“长江”对于林白来说,意味深长。在《一个人的战争》里,一个女孩在第一次出远门时。就在长江的航道上一步迈进了女人的命运轨迹。由此开始,这个女孩/女人开始了弃绝、背离整个世界的人生之路,开始了与世界的“战争”,并且是“一个人”独力而为。我以为,在林白那里,“长江”是女人真正人生的初始,是初次出门远行时所遭遇之“世界”的一个比喻。当她说“长江为什么如此远”时,她实际要问的是,现实世界为什么如此远。无论是作为作家的林白,还是作为小说叙述者的今红,都一直是生活在幽暗狭窄的个人记忆与个人体验中的女人。她们敏感于世界、人生对她们的伤害与折损。敏感于自我、个人的受伤体验,于是用硬茧一层一层地包裹自己,从此与世界渐行渐远。
在林白以往的小说中,“世界”是被拒斥的:只要它在一个不伤及自己的距离之外,管它是近是远呢?但小说《长江为何如此远》却表达了一种个人意识结构的转折。这部小说不只是在岁月回望时表达了“如此远”的感喟,更是抚今追昔地表达了“为何如此远”的自我究诘。小说主人公今红在并不起眼的个人生活挫伤中远离了人群,向世界彻底关上了心扉。但在三十年后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她才发现,这个世界一直有一个温暖的部分不离不弃地守候在她的心扉之外。她狭隘的个人记忆/个人主义瞬时露出了自私、冷漠和无情的底色。她在忏悔和自责中不禁要问:为什么,长江(世界)会变得如此远?
我把这部小说看成是中国女性写作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今的一个隐喻:它表明了中国女性写作曾经呈现过的批判姿态(与“世界”为敌的个人主义立场),并暗示了正在发生的话语流向(对个人主义尤其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省和逆袭)。
实际上。准确地说,《长江为何如此远》并非林白在写作上的一个转向,而是她写作中一直存在着但却被忽视了的方面在此得到了彰显,即林白式的“个人化”或“个人主义”其实是与“世界”、与“历史”紧相勾连的。她九十年代的中篇小说《米缸》,以及后来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都有着从“个人”出发的宏大关怀。这是她写作谱系中一直存在的一条脉络,但因为批评界有意无意的忽视,使之被挤向边缘,甚至完全潜隐。实际上,林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全面的抗辩关系,而非单纯的“逃离”。但一直以来,批评界对林白以及由她所代表的当代中国女性写作进行阐释时,阐释的理论框架总是被不断约减,所有批判性的结论都被限定在“性别结构”的话语空间里,而缺乏对“性别结构”之外的宏大社会结构的分析,仿佛越出“性别结构”这个语义框架后,林白的文学意义就失效。这实际上是批评界无形间形成的对女性写作的新的贬抑和歧视。
而我认为,林白的“个人”和“性”,包括她在语言和文体层面的贡献,都富于政治抱负。正是这样的政治抱负,使她的文学激烈、犀利和意义深远。也正是这样的抱负,她已诚如埃莱娜·西苏所言:“作为一名斗士,她是一切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4)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日于菩提苑
注释:
①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花城》1996年第5期。
②王安忆:《女作家的自我》,《王安忆自选集》第4卷,第41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③王干、戴锦华:《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大家》1996年第1期。
④[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第11页,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⑤尹昌龙、沈芸芸:《记忆与写作:我们时代的个人方式》,《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
⑥陈惠芬:《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第3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⑦[美]赫伯特·马尔库塞:《1966年政治序言》,见《爱欲与文明》,第11页,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⑧[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微笑》,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96-19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⑨程文超等:《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第30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⑩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第61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11)林白:《有一些孤独的人不谈孤独》,《死亡的遐想》,第21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2)林白:《静夜独自》,《德沃尔的月光》,第9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13)[英]玛丽·伊格尔顿:《引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14)蒋青林:《论中国当代女性小说语言范式的递嬗演进》,《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
(15)[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引》,《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37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16)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见《林白文集》卷二,第40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17)[法]露丝·依丽格瑞:《非“一”之性》,马海良译,《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21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18)林白:《选择的过程与记忆》,《致命的飞翔》,第35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19)徐坤:《双调夜行船》,第89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20)[法]朱丽叶·米切尔:《女性:记叙体与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180页。
(21)[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163页。
(22)(23)[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81-82、85-86页,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4)[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微笑》,《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97页。
标签:林白论文; 一个人的战争论文; 自传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个人自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