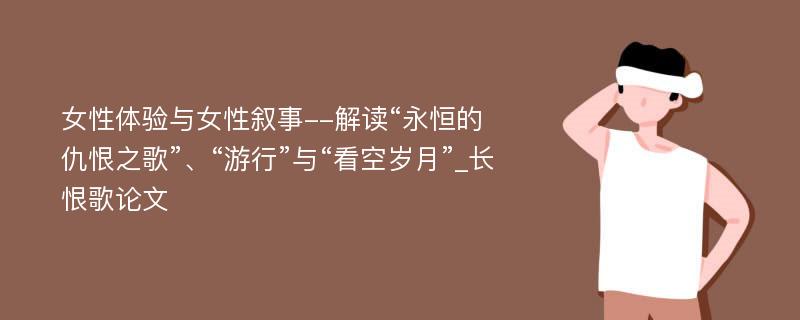
女性经验与女性叙事——解读《长恨歌》、《游行》、《守望空心岁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恨歌论文,女性论文,岁月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经验,对于女性来讲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作为女性自身,一方面非常熟悉它,因为它来自于女性的“身体体验”[①],来自于女性在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里所处的被动位置,来自于文化传统的承袭,以及这诸种因素在心理空间的折射。最终,它从女性的体验认识方式、表达方式中外射出来。另一方面,作为女性,对于自身的经验又是非常陌生的。女性很少能有意识地想到它,更少深究它,因为它与男性的“大气”、“大家风范”,是格格不入的,提起它,便令人想起“自叹自怜缠绵悱恻秋波潋滟嗲声嗲气忸怩作态等等”[②]。于是女性更多的是回避它。对于女性作家来讲,如果她“写的是妇女,她就有可能被戴上‘偏爱’‘狭隘!’‘妇女的书’等帽子”[③]。在当代文学的很长时间里,女作家们在涉足女性题材时,都尽量与男性的叙事风格靠近,而且很少从纯粹女性的角度关注女性的经验。人们在阅读女性作者的作品时,也很难从女性叙事的角度来接受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的经验世界是一个尚待发掘与展现的世界,女性叙事也尚需构建。
所幸的是,近期以来,一批年轻的女性作家毅然游离于“大家风范”的公认准则之外,开始了从女性经验出发构筑女性叙事的勇敢探索。近期面世的王安忆的《长恨歌》、徐坤的《游行》、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三部作品,如果从男性风格的“勇敢、有力、明晰、充满活力”的角度来阅读,或许会感到太具女人气,但从女性经验解读其叙事语码,会读出一些颇有意味的东西。
《长恨歌》:女红般的操作
读王安忆的《长恨歌》,感觉到进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繁复与罗嗦的女人世界。作者极有耐心地、絮絮叨叨地讲述着一个旧式女子王琦瑶的故事,也以平视而非俯视的角度体味着女性的人生。上海里弄里的陈谷子烂芝麻在作者笔下徐徐地搬弄出来,一直伴随着王琦瑶从选美时的倾国倾城到走完曲折坎坷的一生。
王琦瑶的一生是一个普通女性极不起眼的一生,是由无数的琐碎小事堆砌起来的女性人生图景。那些酸甜苦辣是从摆弄服饰,给人打针吃药,做饭烧菜,怀孕生子,一个个微妙的眼神,一颦一笑,举手抬足间透露出来的,女人生活的特有滋味也是从这些琐屑小事中流露出来的。王琦瑶凭着生的直觉与本能,女人天性的巧于安排日子,细小的心眼,小有滋味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她所遇到的困难有许多在那段禁锢的日子里是非同小可的,比如未婚生子,“上海小姐”的身份,李主任外室的背景,与几个男人的关系等等。她不是凭信念凭逻辑的步步为营,而是凭直觉凭女性的心眼走过来的。所以作者感叹说:“那就是一个女人的极其温婉的争取,绵里藏针的。”
作者直接呈露、渲染并勾划出王琦瑶由琐屑人生经验所堆砌而成的不同于男性生活的生命轨迹。这是女性生命的真实图景之一,这里没有回避,没有掩饰,没有曲解,没有忽略,没有“小中见大”的企图,有的是“绵里藏针”的女性的柔韧,女性的趣味,女性的灵巧,女性的敏感,女性的细腻。
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叙述应该是繁简得当的,精到的,动态的。《长恨歌》的叙述却是闲散的,繁复的,絮叨的,静态的。这是女人的讲述方式,不紧不慢,不温不火,罗罗嗦嗦的。这里随便拈出几个细小的场景:
流言——
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薰衣草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
打针——
她们早晨起来收拾干净房间,穿一身干净衣服,然后便点起酒精灯,煮一盒注射针头。阳光从前边人家的屋顶上照进窗口,在地板上划下一方一方的。她们熄了酒精灯,打开一本闲书,等着有人上门来打针。来人一般是上午一拨,下午一拨,也有晚上的一个两个。还有来请上门去打针的,那样的话,她们便提一个草包,装着针盒、药棉,白布帽和口罩,俨然一个护士的样子,去了。
做饭——
王琦瑶事先买好一只鸡,片下鸡脯肉留着热炒,然后半只炖汤,半只白斩,再做一个盐水虾,剥几个皮蛋,红烧烤夫,算四个冷盘。热菜是鸡片,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蝽子炒蛋。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菜,没有一点要盖过严家师母的意思,也没有一点怠慢的意思。
这种絮叨的叙述使我想到了女性的一种日常操作——女红:缝纫的无限的针脚与编织的无休止的缠与绕。这是纯女性的生活内容之一,重复,单调,与社会无缘,有的是女人编织的韧性与执著。女红的操作虽繁琐,单调,平淡,最后总能做成一件美丽的成品,就像女人的人生。可以说这种过于日常的操作方式也象征着妇女人生的一种特征和色彩。
与这样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相同一的女性的话语方式应该是容许絮叨、繁复、细密的,进而可以说,《长恨歌》的叙述与这样的女性经验与女性的生命色彩有着质的同一性。
《长恨歌》叙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环境描写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这从每小节的标题便可见一斑:弄堂、流言、闺阁、邬桥、外婆、阿二、平安里、熟客、牌友、下午茶……作品中的环境描写往往凝滞而冗长,这里略举两小段:
弄堂——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前边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客走动,贴了婚丧嫁娶的告示的。
邬桥——
邬桥吃的米,是一颗颗碾去壳,筛去糠,淘米箩里淘干净。邬桥用的柴,也是一根根斫细斫碎,晒干晒透,一根根烧净:烧不净的留作木炭,冬天烧脚炉和手炉。邬桥的石板路上,印着成串的赤脚板;邬桥的水边上,杵衣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邬桥的岁月,是点点滴滴,仔仔细细度着的,不偷懒,不浪费,也不贪求,挣一点花一点,再攒一点留给后人。
一景一物,都是与女性的人生相伴随的。这类静态的描写留给读者的映象不是变迁中的时代、政治与社会的内容,而是与女性日常生活经验和女性心理相对应的那些琐屑的细节,那些女性眼光所见的韵味。这样,故事环境便与具体的时代的动态变化拉开了距离。在日常的、限于生计的环境描写之中,王琦瑶虽是特定时代的人物,却又是游离于特定社会政治文化主题(主流话语)之外而存在的自在体。也可以说,这种静态的叙事方式将王琦瑶置于一种“私人的、非历史的、非政治”[④]的境地。女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游离于男性中心话语之外,因而她也有一套自己的生存价值观与生存的方式。这也是李主任等男性一个个从王琦瑶身边消失,而王琦瑶却能过得小有滋味的原因。作品就是这样将女性从男性中心话语的笼罩下剥离出来,展示出处于游离状态的女性的独特的生命景观。西蒙娜·波伏娃曾经这样描绘这种景观:“时间从来没有带给她新鲜的东西,时间对她来说不是创造之流;因为她命中注定过着重复性的生活,她看到的将来也只是过去的重现。”[⑤]
二《游行》:女性诗意之笔,戳穿penis的神话
“就让那支pen(笔)或penis(阴茎)把我击中,击成万道碎片,击得粉身碎骨罢!”这是《游行》中的女主人公林格的一句呼喊。
西方女学者曾细致分析过pen的深层特殊含意:“在西方文化中的父权制观念是,本文的作者是父亲、祖先、生殖者及美学之父,他的笔是一种像他一样具有生殖力的工具。”[⑥]pen即本文意义上的penis,二者同为父权的象征。对pen或penis的崇拜便是对父权的崇拜。从pen与penis二者的关系来讲,pen又是penis的一种工具,于是这支pen便为penis制造出了关于“爱情”的诗意的神话。
妇女被认为更执著于“爱情”的追求。这其中或许有社会学方面的原因:世界是男人的,男人可以是诗人、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这个家那个家,女人则什么也不是,所以女性只能望其项背,对“爱情”做“献身”运动。除了这层原因,这支pen对女性的引诱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古至今,“爱情”被这支pen抹上了一层又一层崇高而玄秘的光环。“爱情”必定是以女人对男人的仰视与倾慕为基础的。男性如果高大、俊美、有才、正派,便是爱情诗意的化身,便值得女性追随其后,甘于献身,万死不辞!如此,爱情便有了崇高的意味,女子的“献身运动”也便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了。“爱情”对女性意味着崇拜与牺牲,对男性则意味着宠爱与获取。
“爱情”是否真的玄秘?是否值得女性为之献身?作品以解构“爱情”为目标,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游行”。
《游行》里的女主人公林格的“爱情之旅”便从“崇拜”开始。林格对诗的喜爱与对诗人程甲的崇拜是二位一体的,她便是献身于千百年来男性话语对penis粉饰出的诗意。但林格毕竟是现代女性而不是秦香莲、孟姜女,当程甲“西装褪尽之后,便露出了里面的老式卡叽布大裤衩”,此时,爱的诗意也就轰然倒塌了。
林格的第二个献身对象是黑戍。黑戍是语言鸹噪的堆集体。如果说程甲式的诱惑是以古典诗意做诱饵,黑戍则是以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现代西方男权话语对性的阐释为幌子。“杀父娶母”、“里比多”等词语不间断地从他嘴里流出来,“他能够一刻不停地奔突交叉跳跃,从文艺批评转向社会政治学,又从文化民俗学转向后现代主义,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头顶背飞倒勾斜传,偶尔还能踢出一些莫名其妙十分出格的主义和动作。”黑戍就是这样口沫横飞地把持着说话的地盘,一边诱使林格对其“献身”,一边仔细地抹掉偷情的痕迹,以免妻子发现。
林格以行为与语言的对比,同样洞悉了黑戍的奥秘。黑戍一边享受着性的快乐,一边在口中重复着劳伦斯的话语,林格则在性体验的同时看出“劳伦斯总让他的男主角说野蛮粗鲁的话,又总是让康妮用诗意的语言回敬他,把他两腿中间的那玩艺赞美得跟什么似的”,这其实只是男性的“阳具自恋癖”,“跟手淫没什么区别”。
“颠覆一切伪善和虚妄的!”林格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要想戳穿一下已婚男人信誓旦旦的爱情谎言简直太容易了,只要不小心跟他怀上一次孕就可以完全试得出来。”林格怀孕了,黑戍的鸹噪在这个小小的事实面前突然变为失语,话语的堆砌物也突然隐遁、消解了。
程甲式的“才子佳人”的诗意也好,黑戍的弗洛伊德的“阉割情结”、劳伦斯的自恋也好,都不过是男权话语对“性”的刻意装饰。弗吉妮亚·伍尔夫曾说,“近几个世纪以来妇女成了镜子,这些镜子具有魔术般的、美妙的力量,按两倍于自然的尺度反映出男子的形象……如果(妇女)开始讲真实情况,那么镜中的形象便会萎缩。”[⑦]“按两倍于自然的尺度反映出”的男子的形象,便是男权制为粉饰自然而产生的虚幻的令女性为之迷恋而追求不已并勇于献身的高大、俊美、智慧、进取、大度等等等等的形象。林格游过了这些虚幻的镜像,也戳破了这些镜像,“待她重新游上水面,转身回头望时,这时映现在她的镜中,却不过是他两腿中间凸起的一个鲜红色脑袋罢了。”林格以对诗意的崇拜开始,以读遍男性,解构笼罩于性之上的神秘雾罩而结束,这是女性于爱的“乌托邦”的觉醒。
林格与伊克的关系喻示着女性戳破镜像之后所处位置的悬置。“颠覆,仅仅是为了颠覆。那以后重建的使命又留给了谁?”林格还来不及确定自身的位置,因为这种确定将是一个十分曲折、漫长、艰辛的重建过程。林格只好采取了一个疑惑的母性的姿态——“在身心两个方面同时帮助他成长”,“超度”伊克。
林格以纯粹女性体验的“游行”方式,对男权话语进行了解构。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把新时期初期张洁们作品中女主人公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林格的解构行动相比较,便可看出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有意味的是,作品写的是女主人公对“性”的探索,对性本身却采取了一种诗意的写法,这与男作家涉及这一题材时的直露是不相同的。男作家写性可以细致到“粘乎乎、湿渌渌”的程度,《游行》却通篇都采用了一种诗意的隐喻性的叙述方法。这里且引一段:
站着就义从来都是男人们的事情。女人只有倒下以后才能做出牺牲。林格现在就无比幸福地倒在诗意的砧板上,让那一行行长短不齐的诗文在腰下高高地垫着她,准备接受冥想中的那一支如椽巨笔的书写与点化。
这种隐喻的写法我想并非出于作者的不开化,而是缘自于某种根深蒂固的女性经验。在男权话语里,充斥着对性的淋漓尽致的描写,尤其是自话本以来的小说历史中,可以历数一本本登峰造极之作。这种直白的描写总是将女性置于一种被看被阅的位置,以女性的主动“献身”来满足男性的自恋心理。而女性意识却一直顽固地抵制着这种被看的位置,因此当她们有机会说话时,总是回避着这一位置,这也是从古至今女性说话方式的一个固有姿态。徐坤一方面解构男权话语对性的粉饰,一方面又采取了一种双重拒绝的方式,既拒绝传统意义上的“献身”,也拒绝了被看的位置。
三《守望空心岁月》:“猜想”的游戏
《守望空心岁月》也是一部充斥着女性经验的作品:对情敌、对两性关系的猜想;患病的感觉与幻觉等等。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作品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视角。
作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的有限视角。“我”的身份未作说明,也并不等同于其中的哪一个人物,在多数情况下,“我”便是书中的女主人公姚笠。在“艾影”一节里,有这样一段话:“在姚笠依偎在里安怀里的时刻若隐若现,它们通过我的眼睛,到达姚笠敏感的触角。”
“我”在叙述同子速、里安两位恋人的关系时,对两位恋人的妻子或其他情人都是以有限制的“我”的视角来“猜想”的,因为“我”从未与她们见过面。这是一种十分有限制的“窥视”视角。整部作品都使用这种视野十分狭窄的猜想的窥视视角。笔者认为这是为了传达出女性的一种独特的人身体验:在两性关系中的不自信和对自身位置的疑惑。这是由于女性的长期人生依附关系所形成的一个心理情结,我们姑且称之为“吕蓓卡”情结。
在“我”与子速的关系中,子速曾对“我”说“他爱我。”但当“我”在子速等待与妻子离婚的消沉日子里向他表白,“我”愿意同他在一起时,却受到了冷遇,可以说在与子速的关系里“我”是个失恋的女人。“我”因此而陷入了对子速的两个前妻的无休止的猜想之中。为何得不到子速的爱,成为“我”猜想两位同性的解不开的心理情结。
“我”在回忆与另一个恋人里安的情感纠葛时,里安的妻子艾影又“横亘在我和里安之间”,“她的身影时隐时现。”“艾影对于我就像电影《蝴蝶梦》里的吕蓓卡”一样无处不在。由此,“我”对艾影的猜想又不可遏止地流露出来。
“吕蓓卡”情结可以说是笼罩于女性心理上的一层阴影。《蝴蝶梦》里的“我”因社会地位的缺席而将生活的希望与价值维系在丈夫身上,对其丈夫在生活与情感方面都是仰视的,表现出极强的不自信心理。女人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着“身份危机”,在今天,她虽能就职就业,但仍遭受多种歧视,一遇风吹草动,她仍首先成为受到冲击的弱者。她需要得到丈夫或情人的认可,才能确立其身份。这就导致了她对情敌的猜想。这种“猜想”的心理游戏存在于古时的嫔妃、妻妾之间,也仍然若隐若现于当代女性的心理之中。这种“猜想”是女性所特有的一种心理体验。
“猜想”还涉及到对自我的定位问题,“我”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让她(姚笠)在男性面前担负什么角色呢?恋人?情妇?或者是为家庭所准备的未来的老婆?这是我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定位的问题也将是女性的一个长期的自我认知过程。
这就涉及到“猜想”视角的第二层含意:“我”除了猜想陈梅、甘颜、艾影,甚至父亲的情人之外,还猜想自身与自我。在“猜想”一章里,有这样一句话:“当姚笠爱上子速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女人才是我钟爱的对象。”这里明确提到了“我”对“姚笠”的钟爱,这可以理解为女性的自恋与自审。“我”猜想姚笠,这是一个对自我的审视过程,也可以说是在镜像中思索、寻找自我的过程。
姚笠在事业和爱情婚姻方面都是一个失败的女人。由于是女人,姚笠虽为一名有才华的卓尔不群的记者,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里仍然首先受到了冲击。她在社会关系中能够得到指认的“记者”职务得而复失;她与异性的关系也令人疑惑:她与子速的交往以失恋而告终,她在里安的眼里只是一个开放而性感的女人,她仅有的一次婚姻也是失败的。“我”对姚笠的女性角色充满了疑问:“在我对姚笠的观望中,我隐约觉得我的女主人公似乎不能胜任以上所列的三种角色,那么在我们现存的这个男性社会里,一个不能当恋人,不能当情妇,不能当老婆的人是谁呢?当恋人需要热情和浪漫,当情妇需要性感的外形和旺盛的性欲,当老婆则需要 贤惠和勤劳,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姚笠并不具备这三个方面的素质,她热爱写作和书本,喜欢自由、喜欢散漫,她缺乏讨好男人的热情与技巧。”
对于姚笠这位失去了传统女性品德的女人,她的位置当然只能是悬置了。她在现实处境里是受压抑和近于悲惨、又无法言说的:她受到排斥,她还处于流言的旋涡之中。她短暂的婚姻,被看作“一大奇观”,她离婚的原因,“在传说中有三种说法”,她甚至不被同类认同,“她无形之中被我们(女人)开除了。”从传统中挣扎出来的女性如何在两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中定位,“这是一个我感到痛心的问题”,也是《游行》中的林格在解构行动之后同样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当今女性的一种真实处境,表现出女性心理的深深的疑惑和彷徨。
这种猜想的视角甚至还具有第三层含意:喻示妇女的“私人的、非历史的、非政治”的处境。“我”(姚笠)无论是在社会关系还是在两性关系中都处于被动的位置,被控制与被摆布。主动权是由单位的那位领导、里安以及艾影的父亲等男人掌握的,他们不可捉摸、虚伪、善变、威严,事情的缘由及真象(如艾影身世之谜)都由他们掌握并竭力掩盖。所以,“我”不可能使用全知的视角正面叙述。当“我”能够说话时,“我”也只能是“猜想”。
上述三部作品都基于女性经验对女性叙事作了富有个性的建构。是否有必要存在有别于男性话语的女性叙事,这是值得探讨的。笔者以为,至少在女性声名被湮没许久的今天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倡导一种“阴阳合一”的境界,这应是包容并超越了男性与女性的境界。但在我国的当代时段,女性在走出家庭的同时被同化、被窒息了。在男作家的作品里,女性要么缺席,要么只是衬托男主人公的各类道具,完全拒绝了女性经验。女作家们则表现出困惑的心态:都尽量向男作家靠拢,尽量摈弃女性色彩,更不敢堂皇地展示女性体验。可以说在当代文学的时段里,女性的声名是极其微弱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女作家率先进入女性的经验世界,发掘建构那已经缺损的一极,于我国文学性别视角的矫正,并进而达到“阴阳合一”的境界,应该是极其有益的。
注释:
①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人民出版社,第22页。
②蒋子丹:《创作随想》,《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
③④玛丽·伊格尔顿,见《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72页,第163页。
⑤西蒙娜·波伏瓦《女人是什么》,第39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⑥桑德娜·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阁楼里的疯女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117页。
⑦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第43、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