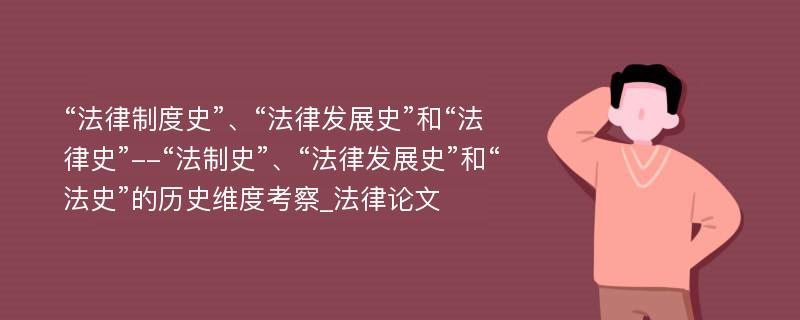
“法制史”、“法律发达史”、“法律史”———个历史维度的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律论文,维度论文,法制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48(2004)02-0042-03
自清末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法律史学科萌生以来,就已经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而言,有 “法制史”、“法律发达史”、“法律思想史”、“法律史”的分别,其中所映射的学 科内涵,除“法律思想史”无较大变动以外,余三者则经历了一个递次演变的过程。在 今天的条件下,重新审视其历史的轨迹,体会其内在的关联,对反思中国法律史学科的 建设与发展,或许不无裨益。
一
“法制史”之学科及名称的传播同日本的学术与近代法学教育的影响有关。日本学者 浅井虎夫的《支那法制史》、《中国法典编篡沿革史》以及东川德治的《支那法制史研 究》等对梁启超、程树德等人治中国法制史不无参考的作用。近代法学教育方面,1902 年清政府颁行的《大学堂章程》规定在四年制法律学科中开设《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 课程,“此时暂行摘讲近人所编《三通考辑要》,日本有《中国法制史》,可仿其义例 ,自行编篡教授”。[1]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章程》在法律门教学科目中正式确立了 《中国法制史》课程。由此,围绕着法学教育的需要,“法制史”渐次流行。但由于“ 史以法制为称,涵义极不确定,盖法制一语原无定释故耳”[2],所以“法制史”历来 也就有了广义、狭义之说。狭义的“法制史”基于对中国古代“法”的实质性意义和历 代法典均以刑事法为骨干的特点的认识。“采狭义之说者,认为法制即刑罚,法制史即 法律史,所涉范围,只以法律上制度为限,凡与讼狱律例无关之制度,皆在排除之列。 ”[3]“旧称法制以律与刑为主,刑事制度随而见之。程树德、董康、徐道邻、朱方诸 先生著中国法制史,采此例焉。”[4]广义的“法制史”的提出则是建立在现代法理观 念基础之上,研究的范围也逐步扩充到组织、人事、监察乃至民事、经济、社会等方面 。康宝忠、丁元普、陈顾远及其后的大多数学者著中国法制史,属于这种所谓的广义说 法。1934年陈顾远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法制史》一书中认为:“为社会生活 之轨范,经国家权力之认定,并具有强制之性质者,曰法;为社会生活之形象,经国家 公众之维持,并具有规律之基础者,曰制。条其本末,系其终始,阐明其因袭变革之关 系者,是为法制之史的观察,曰法制史。”又说:“则及现代之法理、政理而言,制度 之条文固可曰法;制度之见诸明令,为众所守,虽未定于律,入于刑者,又何尝非法? ”[5]据此,该书“除总论一编外,特就法之立场,为制之叙述,有政治制度、讼狱制 度及经济制度三编”[6]。林咏荣认为陈顾远关于“法”与“制”关系的解释非常透彻 ,“法与制虽各有其界限,但制度之形成,其具有强制力者,往往皆以法令为基础,仅 举‘法’而不及‘制’,不足于说明‘法’之效果;仅举‘制’而不及‘法’,不足于 说明‘制’之渊源”。依此,“中国法制史者,乃记述中国过去之法律及由法律所形成 之制度,考其沿革,衡其得失,并求其因果关系,卑资现代治其事者之考鉴也。”[7] 当然无论是狭义的“法制史”,还是广义的“法制史”,除认识上的原因外,其因袭援 用,学者的偏爱与使用上的习惯也是一重要因素。
二
1930年杨鸿烈为弥补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法系”不足于囊括其全体,“但只窥豹一斑 ”的缺憾,说明“中国法律之特点与其在世界文化的位置”,[8]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了《中国法律发达史》。为避免“专在零星的法律现象里头做白费的工夫”[9],以真 正表示出“中国民族产生法律的经过和中国历代法律思想家的学说影响司法的情况”, 这部著作的内容从“法律”“历史的演进及其与当时情势消长的关系”、“其立法意旨 之归宿或多数基本原理之哲学意蕴”的角度展开,综合运用了“外包”与“内容”、“ 纵”与“横”(“体”与“用”)、“历史”与“比较”等多种方法,(注:杨鸿烈.“… …其次便说到研究中国法律的方法,我先引日本、欧美的学者论研究一般法律史的方法 如下:鸠山和夫与阪本三郎合著的《法制一班》有说:‘……讨究法制沿革有两法:一 曰外包法制史,谓叙述法律全般之沿革,法律与国家之关系及法源等……二曰内容法制 史,谓叙述各种法律之性质及进化。……盖外包法制史者综合法制大纲而说明之,内容 法制史者解分法制经纬而说明之也。彼则脉络一贯易成绚烂之美,此则纷纠错杂易招索 默之欢……’。我这书就是兼用‘外包法制史’和‘内容法制史’两种方法。浅井虎夫 在《中国法制史》上又分为‘纵的研究法’和‘横的研究法’或‘体的研究法’与‘用 的研究法’。他说:‘凡研究支那法制有二方法:一纵的研究,一横的研究也。纵与横 之二方面均有不可相离之关系。法制上横的研究即所谓法典之研究也。盖法典常属于静 止的,一经编篡而即以不改正其成篇为限,使最富于静止状态。纵的研究则法制运用之 研究也。总之,纵与横之研究,所谓不离乎体、用之研究者近是。体的研究则为法典之 研究,在唐如唐令、律、疏、六典之类,在宋如敕令、格式、编敕、条法事类之类,在 明为会典、明律之类。用的研究则正式之志类、《九通会要》之类也。故单就体的研究 或单就用的研究,皆偏于一方而不完全,是以《文献通考》之类研究中国法制详且尽矣 ,然知其用未知其体也,体与用盖不可相离也。’我这书也是互用‘纵、横’、‘体、 用’的方法。再看司法部顾问法人耶士卡勒(Jean Escarra)教授讲演的一篇《中国法律 之(西方)研究法》(Western Methods of Researches into Chinese Law)有说:‘观察 (Observation)是第一个方法。建立每一制度的专门的结构(to build the technical
structure of an institution)是第二个方法。此外即是历史的方法和比较法学的方法 (history,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见《中国社会政治科学季刊》(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Ⅷ,January,1924))。’我这书是用‘历 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为多,其实这两种方法在我书里有极密切的关系……总之 ,我们研究中国法律实不能不综合以上三位学者所说的各种方法,然后方才不至挂一漏 万。”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之《导言》.)将法制的形式、内容的变化研究与 法律思想研究相结合。虽然从上下行文的语境和该书的内容上分析,杨鸿烈先生在这里 所使用的“法律”一词,主要有类似于狭义“法制史”的“法典”涵义(注:杨鸿烈先 生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导言》中也比较清楚地表达了此种意思:“ ……中国法制史是以中国历代法律制度的兴废与其演进的情形为研究的对象……本书既 命名为《中国法律思想史》,所以除叙述先秦仅少的法理学说的古籍而外,并以中国历 代法律制度的形成与进化中的思想为考察的对象。其着手之处即:(一)就个人的思想加 以考察,如学者的著述言论,以及法律家活动的遗迹;(二)就时代的思想加以考察,如 法典制度和历史文化等。可以考察时代背景和时代意识。这样即是本书的范围.”),如 他在“三项特殊的研究为主干”(注:杨先生的这“三项特殊的研究”是:“第一,沿 革的研究。这项即以研究中国法律演进的历史为目的……这样就使我们深信中国法典是 进步的,其内容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陈陈相因’,而却是各朝代有各朝代的特 色。”“第二,系统的研究。这项以研究中国法律的原理为目的……我这本书里所占去 大部分的篇幅也是在指摘中国法律所根据的原理显与其他如罗马、英美、印度、回回等 法系不同。”“第三,法理的研究。这项以研究中国历代法家的思想为目的。”参见杨 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之《导言》.)的第一“沿革的研究”部分列举了历代主要法 典的例子,[10]但他却未使用“法制史”一说,而采用了“法律发达史”的名称。何也 ?况且在“史”的内涵已包括了“演进”、“发展”、“发达”成分情况下,还有其画 蛇添足之嫌。究其原因,除饱含民族激情地突出说明中国法律自古至今一以贯之、不停 流变的目的以外,西洋人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可以从他在《中国法律发达史 》的《导言》篇的引文中反映出来。如:“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家论》(The
State)的第十四章《法律的性质和其发达》(Law,Its Nature and Development)”、 “都德龙”(Piere De Tourtoulon)《法律发达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w)”等。除称谓的差异外,杨鸿烈的“法律发达史”在体系与结构 上已大体上与后来的“法律史”相当。虽然就20世纪前半期学界著作的总体状况而言, “法律发达史”在数量上不占主导的地位,孤处于“法制史”的包围之中,但从“法制 史”到“法律发达史”的变化,却映照了学术的进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教授在《中 国科技史》中称赞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是法律史方面“ 最好的中文专著”[11]。杨鸿烈的研究方法也在实际中为治“法制史”的学者所借鉴。
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法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由于“文革”的破坏以及学界自身 的原因,在法学领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对前辈、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 的系统整理与总结,以至于不但不能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前进,反而在很大程度上 重走了过去的老路,造成了学术资源的浪费,阻碍了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因多方面情 况的限制,法史学科中,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法律思想史长期“截然分开”,“形成两张 皮,即使联系很密切的问题也各说各的,不越雷池一步”。“二者共同的纵向联系、横 向联系同样被人为地割裂,互不相通。”“不少学者已感到分工过细、过于机械的做法 并非上策。加之各自又只是在一个平面上来谈问题,毫无立体感;只谈静态,不谈动态 ;只谈论点,不讲实践,殊不合理。其实,仅就中国法律史而论,也是个多方位、多层 次的系统工程,不应当把思想史和法制史看成两个孤立的世袭领地。因此,有人索性主 张将两者结合起来改写成法律史或法律文化史,冶上下古今、立体平面、动静诸态以及 各种纵横联系于一炉。”[12]经过学者们艰苦努力,一批“中国法律史”著作相继出版 ,如张晋藩先生等人的《中国法律史》等。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法律史”著作没有机 械地将“两张皮”合二为一,而是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进行了积极的拓展。“法律史 ”的结构也绝非制度史与思想史的简单叠加,更多的则是站在“文明”或“文化”的高 度上而建筑的“以法律思想为核心,包容法律制度、法律设施和法律艺术诸方面”的“ 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13]。这其中透射的恢宏气魄,非单独的“法制史”或“思想史 ”学科所能够体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如何更好地把握传统,以及中华法律文明如何面对西方欧美法律 文明等问题的紧迫压力,也使得中国法律历史的进一步综合研究成为必要。学者们上下 求索,在着力对诸如中华法律文明的基本特点等宏观研究方面求突破的同时,在微观个 案的领域也取得较大的进展,以致于呈现了宏观与微观研究相互印证、相互说明的新局 面。但就学界的现状而言,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干“个体户”的多,搞“公司类规模 经营”的少等。因此,如何总结过去的经验,充分发挥法律史学会的感召与协调的作用 ,以运用学术队伍的大力量来尽力地克服目前学科在研究与教育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推动法律史学的繁荣,不妨可作为一尝试的设想。
收稿日期:2004-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