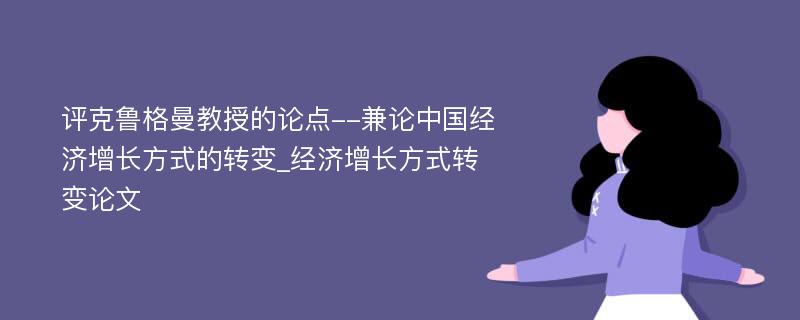
评克鲁格曼教授的一个论点——兼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鲁论文,论点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教授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鲁格曼教授关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投入,而不是靠“无形资本”的提高赢得的论点失之偏颇。东亚经济“奇迹”实际上是多种重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技术的提高。尽管克鲁格曼教授的论断难以成立,但是,从东亚发展中地区的经济整体素质看,集约化程度尚远远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这应当引起东亚发展中地区各经济体的重视。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应当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东亚经济“奇迹” 经济增长方式
美国斯坦福大学克鲁格曼教授1994年底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东亚经济“奇迹”只不过是一种“神话”的观点,至今在国际社会仍争论不休。根据他的研究,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不是靠“无形资本”(如技术)的提高赢得,照此下去将很快走到“尽头”,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多久,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只是“纸老虎”。除文中某些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辞句外,克鲁格曼教授的论点也失于全面,过于武断。然而,他所提出的这个增长方式问题,不能说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认真对待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
能不能说东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不断扩大“有形资本”的投入呢?不能。因为,东亚经济“奇迹”实际上是多种重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间荦荦大者有如:
1.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起飞依序相连,产业结构处于梯形层次,已确立一个互补性较强的区域性分工体系。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30年前由日本率先起步,并通过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带动起来的。日本早在60年代开始高增长;尔后,“四小龙”从70年代起加速发展,开始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70年代中后期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在较短时间内把自己建设成“新工业经济体”(NIES);80年代东盟国家和中国开始经济起飞,积极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开始建立起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从80年代后期起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大体形成了一个多层联系的产业分工体系:日本作为该地区的唯一超级经济大国,既是该地区的资金、技术和高新科技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能源、原材料及消费品的大市场;“四小龙”已成为该地区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重要供给者,也是能源、原材料的重要消费者;东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四小龙”的配套设备、元器件、零部件的加工生产基地,以及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中国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科技产业在内的工业生产体系,在技术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并已在不同技术层次上与东亚各国(地区)发展经济关系和技术合作。东亚的这个具有较大互补性的产业分工体系,对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2.在产业互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了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区域内的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近10年来东亚区域内的贸易迅速扩大,据美国“AMEX银行评论”(1993年3月号)报导,东亚9成员(中国、“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互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20.5%增加到1992年的29.6%,而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却下降了。如果把日本与东亚地区相互出口计算在内,则东亚地区内出口贸易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将更大,因为近几年来日本为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减少对美国的出口,相应扩大了对东亚的出口。据报导,东亚地区内,相互出口在该地区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估计已达42%。这表明,东亚地区的出口市场已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东亚地区越来越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正日益成为自己的重要出口市场。同时,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结构也有重要的变化,即“四小龙”对东亚地区的投资增长最快,从1982年的28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902亿美元,增长31倍;其规模已超过了日本(568亿美元)和美国(382亿美元),成为该地区的外资最大来源提供者。若加上日本在该地区的投资,则1993年东亚所用的外国直接投资2837亿美元总额中来自本地区的资金已达50%以上。正是上述贸易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使东亚经济具有了较强的内在支撑力量,免受9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和日本严重经济衰退的干扰和影响,保持了持续高增长的势头。
3.东亚地区长期保持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东亚地区人民素有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使他们长期保持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导,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在1983~1989年分别为29.8%和28.9%,而1990~1994年进一步提高到30.4%和30.9%(见《世界经济展望》,1995年5月出版)。至于东亚地区唯一经济大国日本,其储蓄率和投资率也比西方发达国家高出2~3倍。长时期的高储蓄和高投资支撑了持续的高增长。
4.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例如,日本战后以来一直致力于大办教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企业和家庭都把教育视为“智力投资”,不仅培养出大批精通业务的经营管理人才,而且还造就了一支素质很高的劳动力大军。日本的高级经理中拥有学位的占85%,与美国相当,高于法国(63%)、德国(62%)和英国(2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业把“终身教育制”跟“终身雇佣制”结合在一起,职工从入厂起到退休前,需接受企业安排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和再培训,通过“再培训”来适应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韩国从1962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一直大办教育,不仅各级政府,而且各企业也举办各种形式的大学、学校、职业学校、职工业余学校、专业培训或派送出国留学。目前,按人口平均计算,韩国拥有博士头衔数量居全世界之首。新加坡、我国的台湾地区等教育之发达对于经济高速增长也都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东亚国家(地区)在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时,大多看准上述4方面因素。既然如此,象克鲁格曼教授那样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主要靠的是增加“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的说法便有失片面。因为上述4方面因素之所以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动力,就在于它们带动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和人的素质提高,这一切都意味技术的提高,而决非仅仅是“投入”的增加。况且,像日本、新加坡、我国的台湾等地既缺劳动力资源,也缺天然资源,它们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技术提高,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实现高速增长。克鲁格曼教授关于东亚经济“奇迹”主要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提高技术的论断,未免过于片面、武断。
进一步讲,克鲁格曼教授忽略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发展中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处于不同阶段的事实,而简单地就其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比较也是不合适的。一般说,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是生产技术提高与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任何时候你想“转变”就可以“转变”得了的。西方工业国家工业化初始阶段其增长方式也是非常粗放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提高经济过程的集约化程度,通过机械化、自动化而发展到现在的电子化阶段,经历了一二百年的历程。用工业化刚起步或者仅仅进行了几十年的东亚发展中地区跟工业化进行了一二百年的西方国家相比较,就其增长方式的集约程度说三道四显然是十分不合适的。若拿现在的东亚发展中地区跟当年工业化初期阶段的西方国家相比较,则可断言前者的集约化程度定是大大高于后者,因为它们当时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动化或电子化,而后者则不仅可以利用前者已发展起来的先进科技成果,而且可以在自己的经济中建立个别高科技企业甚至高科技产业。这也许是东亚发展中地区的高速增长率可以比西方国家的增长率高出好几倍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克鲁格曼教授的论断有这样或那样的重大弱点,难以成立;但也决不容忽视。因为,东亚发展中地区就其经济整体素质言,其集约化程度目前尚远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靠国家投入而不靠提高技术的粗放型增长问题在该地区的各经济体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拒绝东亚经济主要靠增加投入赢得高增长的说法,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在东亚地区根本不存在或不重要。增长方式从靠“投入”转向靠“技术”,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这是任何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所必然面临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正是东亚发展中地区在自己的工业化实践中努力解决的问题。应该说,东亚经济“奇迹”正是该地区扩大经贸合作,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产业转移和技术升级,从而提高经济集约化程度的结果。克鲁格曼教授的论点虽不像是一个善意的忠告,但不失为一声令人惊心的警钟。东亚发展中地区必须继续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这尤为重要。
二
中国工业化经过近40多年,特别是近18年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拥有少数高科技产业在内、产业部门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仅管工业在GDP中已占到5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断有所提高,但就总体而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换取的。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区、各部门所热衷的增长方式,一是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忽视技术改造和科技开发,有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二是忽视规模经济,搞“大而全”或“小而全”;三是靠高投资、高积累,开工项目和在建项目多,完工项目少;四是靠资源的多占有、多投入、高消耗。凡此种种,虽可一时把速度提上去,却给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主要表现为:
1.投入多、产出少,边际资本产出率下降。“六五”期间每增加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平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3.2亿元,“八五”期间预计为2~3亿元。与此相联系,社会净产值(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逐年下降,扣除价格因素后,1992年比1978年下降了11.21个百分点。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1980年为25.6元,1994年下降到14.4元。
2.主要行业生产设备长期未能更新,技术水平落后。例如,机电工业的主要机械产品中只有5%达到目前世界水平,1/3只达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水平,该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15~20年;纺织工业的4100多万纺绽中早该淘汰的陈旧设备约有1/4,达到80年代先进水平的不到40%。
3.物耗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资源浪费严重。例如,中国每吨标准煤消耗所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为710美元,而美、日、法、德、英等发达国家每吨标准煤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165~6388美元。几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耗所占比例比发达国家高出5~10倍以上,最高达百倍,比印度也高出2~3倍。工业物耗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64.9%,1985年的67.4%增加到1989年的71.7%。
4.出口增长较快,但出口贸易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粗放型品质。中国出口贸易结构虽已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尚未实现从初级制成品为主向深加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级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出口贸易量的增长主要不是靠出口品的高品质、高档次、高技术含量,而是靠价格优势,导致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一直下降,仅1993年出口的63种初级产品和110种制成品中,就分别有49种和75种的价格下降,损失收入42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5%。
总之,尽管中国在推进工业化、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主要靠增加投入而不靠高技术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确实是妨碍经济增长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由于以下情况而显得格外严峻。(1)中国并不是一个自然资源富饶(除煤炭外)的国家,以石油为例,中国目前生产已不能满足需要,从1992年起已从石油输出国变为石油进口国,预计到2010年石油的需求量将是目前的好几倍。其它资源的供求情况也大抵如此。这就迫切要求把拼资源、高消耗的增长方式转变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增长方式。(2)中国国营企业连年亏损面大,如果继续重投入而不重技术和效率,势必进一步加大企业的成本负担,难以扭转亏损局面。(3)再加以西方大公司纷纷进入中国,迫使中国国营企业不能不在国内市场上迎接激烈的国际竞争。这一切无疑都加大了中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紧迫性。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1994年就向全国明确提出了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任务,并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与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一道作为今后15年全部经济建设工作的重大指导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说,克鲁格曼的论点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倒有其现实意义。
三
目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坚持摒弃过去那种靠增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其实,我国政府和经济学家早在60年代初就已注意到和讨论过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指出各地在经济发展中热衷于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争投资、搞外延型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社会资源大量浪费,结果是“少、慢、差、费”。当时人们也曾深感“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并探讨“转变”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再号召各地国有企业不应再靠争项目、争投资、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办法来加速增长,而要靠提高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扩大生产,要讲究效益。可是,言者谆谆,闻者渺渺。究竟原因何在呢?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结合在一起,国家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投资、经营的决策者,这种行政化了的企业缺乏资金成本与效益的概念,没有硬性财政约束,因而也就没有经济活力,加速增长的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向国家争投资、争项目、铺摊子。这就是从前热衷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体制性根源。改革10多年来,企业改革虽取得相当进展,但“政企分开”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只有通过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才能把国有企业建设成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独立生产者或经营者,国有企业才能拥有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生产率和竞争能力的激励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所以,实现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乃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是体制方面的前提条件。
最后,还有几点值得在这里提出。第一,尽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彻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条件,但并不是说只有等到完成企业改革之后才能着手转变增长方式。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跟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二者应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随着增长方式的转变日益向前推进,将越发迫切要求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经济体制的转变日益向前推进,将越发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开辟道路。只是任何时候别忘记: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为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体制方面的条件和保证。
然而,即使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也不是可以立即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会推动企业自发地转变其增长方式,而政府的积极干预(指导与鼓励)、人们的科技意识及管理意识的提高,都会大大加速这一转变。我国政府明确把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未来15年的基本任务之一,并采取了相应措施,这无疑会大大加速实现这个转变的进程。但应该认识到:如果说计划经济曾是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体制根源,那么,市场经济将通过竞争的压力为各企业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集约化经营程度提供一个内在的驱动机制。从这个意义来讲,和东亚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与地区相比较,我国还有一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任务,而且这项任务十分棘手、艰巨。
第二,决不应将增长的不同方式(如粗放型和集约型),跟产业的不同类型(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混淆起来。产业类型之所以分为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乃由各种产业自身不同的技术构成所决定,在当今发达国家里各类不同产业也都以不同的比重同时存在;至于增长方式问题即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靠扩大投入规模抑或靠不断更新技术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加速增长,则各类产业都经常面对这个问题。不仅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大力转变增长方式,提高集约化经营程度(如纺织服装业应致力于深加工,面料质量、印染技术,改进花色品种及设计,增加附加值),而且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同样必须走集约化经营道路。例如,我国汽车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依然在低水平上重复,遍地开发,搞“小而全”,形成不了规模,出不了名牌产品,长此下去,即使在国内市场也难有立足之地。可见,如果把产业的技术构成类型跟增长方式的不同模式混为一谈,以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集约型经营,从而忽视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或者以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只能是粗放型经营,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差别很大,因此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应由各企业根据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根据各自的经济与技术的实力以及市场的供求状况,来决定技术升级或技术更新的方向、步骤与规模。在这里,进行决策的应是企业而非政府;政府可对企业转变增长方式提供指导、咨询或鼓励,但不应越俎代疱,更不应利用行政力量搞“一刀切”。鉴于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政府在多数情况下仍是决策者,这需要格外谨慎从事。
标签: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论文; 粗放型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