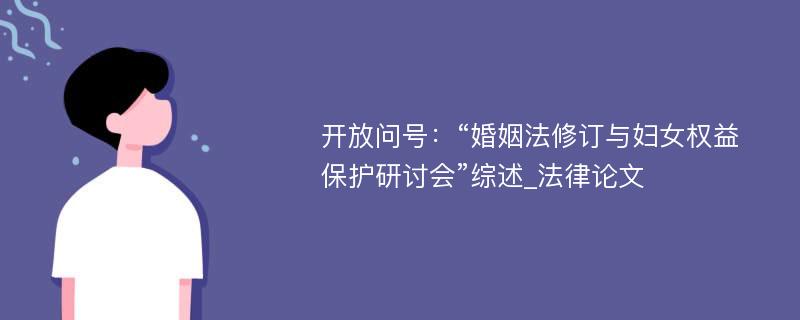
亟待打开的问号——婚姻法修改与妇女权益保障专题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婚姻法论文,问号论文,研讨会论文,权益保障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婚姻法的修改是近来社会各界颇为关注的问题,法学专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建议稿)在征求意见时,出现了多种不同意见。为了使新修改的婚姻法更切合实际并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有利于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近日,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婚姻法修改与妇女权益保障专题研讨会”,来自高校、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法院、妇联等部门的社会工作者对此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离婚自由等于先进文化?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邓伟志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婚姻观的基本点就是“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不论现实生活中婚姻的基础多么复杂,我们都要不懈地坚持“以爱情为基础”。“继续保持爱情”不外两种:一是珍惜已有的爱情;二是结束没爱情的婚姻。对离婚的卡压容易,引导则难。
中国80年代的婚姻法意味着中国人在社会文明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当时和事后都有人反对无过错离婚。不料,80年代反对无过错离婚的非主流观点,在21世纪之初正在成为主流。看来围绕婚姻自由问题的第三场辩论即将展开。辩论得越透彻,法律条文会写得越准确。人不可违法,法不可违规(规律)。理论不清晰,法律条文必然出错。“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亚洲性学联合会主席、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刘达临教授指出:千百年来,人们总认为“离婚无好人,好人不离婚”,其实,这需要作具体分析。法律不能解决感情问题,惩罚有时只能使矛盾激化。离婚率的增长、婚外情的增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一些现象。如何建立两性关系新的平衡?人们在爱情、婚姻和性的问题上,既要有自由,也要有控制。这种自由,是健康意义上的自由;这种控制,是合理的控制。合理的控制,不是压制,无论如何压制人性的时代应该过去了。
上海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安琪副研究员认为:把离婚率上升视作社会不稳定的信号,由此将限制离婚作为婚姻法修改主要目标的立法建议失之偏颇,离婚自由与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限制离婚或倒退到有过错离婚原则与先进文化相悖,也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方向不符。
其实,离婚率并非是婚姻稳定性的惟一测量指标,婚姻质量才是婚姻稳定最重要的前提和保障。去年全国有120.2万对夫妻离婚,但再婚人数高达100.5万。此外,与人们的料想相反,青年人轻率离婚的极少,把离婚率上升归咎于青年人将婚姻作儿戏并无实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金一虹研究员指出:婚姻是男女两性最全面的合作,是一个融合着经济、精神、文化功能的共同体,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经济契约,可以单凭物质利益的纽带强行连接。情感尽管不是两个人结合的惟一原因,但在情感的纽带断裂之后,婚姻却很难再维系下去。不能不考虑到婚姻这一特殊性。离婚,本身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它可以是女性反抗男权、摆脱不幸婚姻的一种解脱,也可以成为男人不负责任地抛弃女人和以便占有资源的手段,不能简单说限制有利还是放宽有利。所以,在婚姻法的修改过程中,既应该注意到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相符合——在人类生活的规范体系中,强制性规范应该越来越少,自律性规范越来越多,以及应更多地体现当事人的主体性原则,同时,也应使维护妇女,特别是妇女中的弱势群体的原则得到充分体现。
配偶权等于同居义务?
上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沈峻认为: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基于配偶身份而产生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配偶权中,同居是首要义务,没有它,婚姻实体的其他因素便难以存续,夫妻间亲密的程度也无法加强。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同居、贞操义务”的规定,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完善配偶权的内容,不仅可以更加明确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使双方增加一种责任感,而且加强对受害方情感上、健康上损害的补偿,也是体现对其人格尊严的维护。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讲师李红玲提出:强调同居义务对女性有利。首先,规定同居义务与束缚女性性权利没有必然联系。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同居义务,但实际生活中,丈夫违背妻子意愿用暴力等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情况并不少见。其次,不对同居义务作规定,反而会损害妻子的性权利。如果法律规定同居义务,并对其内涵及抗辩理由作出明确规定,则可以对婚内性行为作出合理的规范和正确的引导。既为认定夫妻间性虐待和婚内强暴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妇女维护婚内性自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从同居义务的内容看,规定同居义务对保护妇女权益有利。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例是丈夫长期在外寻欢作乐,或干脆寄宿他乡长年不归,对妻儿不闻不问。这实际是对妇女的遗弃。但由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同居义务,故对丈夫的这种行为难以认定和处理,致妇女求告无门。同居义务的规定虽然不能强迫那些一意孤行的男子回到家庭,回到妻子身边,但至少可以认定其行为违法,而要求其承担其他形式的法律责任。
徐安琪则认为:法学专家建议在新婚姻法中规定夫妻的配偶权,其实质是强调夫妻的同居义务,本意是为了限制由婚外恋的一方与第三者的非法同居。但配偶权的设立对于已一意孤行移情别恋的男子毫无威慑力和约束力,而且该立法建议没有明确规定何为“有不能同居生活的正当理由”,因此,在审判实践上也无法操作。况且,一夫一妻制本身就意味着婚姻当事人有同居和互相忠实的义务,刻意强调配偶权或同居权纯属多此一举。
财产分割等于保护弱者?
针对目前在离婚案中,往往出现男方有外遇后,将家中的财产转移、隐匿,使一些平时较为懦弱的女性在离婚时面临人财两空的困境,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高级律师缪林凤建议:1、各级妇联要加大对妇女自我保护的宣传力度,使她们增强在家庭生活中与丈夫共同掌管财产的意识;2、对平时在家庭中管理财产权的一方离婚时有转移或隐匿财产的情况,新修正的婚姻法要加强对违法一方的制裁力度,违法一方应承担责任;3、对转移或隐匿财产的一方,离婚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的超出本人收入的财产情况,允许另一方向法院提出诉讼,由法院进行审查,并要求其提供财产来源的相关证据,否则视为原夫妻共同财产。
徐安琪认为:法学专家虽提出无过错方有权要求对方赔偿损害,但既未解决如何赔偿的可操作性问题,也没有规定夫妻离婚在分割财产时应对无过错方的照顾。因各地的生活水平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差异很大,不宜作出统一的具体规定,但应确立赔偿数额的依据和原则。除了设立过错赔偿制,离婚时在财产分割、房屋租赁、居住权等方面也应照顾无过错方的权益。
怎样才算维护了妇女合法权益?金一虹认为,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面临两难选择,因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本身包含内在矛盾——在什么层面上对妇女有利?是生存的层面上,还是发展的层面上?是按照妇女自己的需求(比如无论如何也要“保全名分”),还是考虑到她的长远利益?妇女本身也是分层的,我们要保护的对象,是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相对独立的妇女,还是相对处于弱势,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依赖于男性的妇女?不同发展层次的妇女有不同的需要,没有办法制订一条法律可以使利益需求不同的人“皆大欢喜”。
对处于婚姻弱势妇女的最重要的保护,应该包括经济赔偿制、对无独立经济收入的妇女的赡养制以及提高子女赡养、教育费的标准;完善强制执行的制度;离婚后,财产关系、抚养关系变更中妇女利益的保护等。但是女性的精神补偿(特别是那些强烈不愿离婚的妇女,违背她的意愿离婚对她不是一种精神伤害吗?),共同投资家庭的未来收益等要不要考虑在内呢?这些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林荫茂副研究员认为:夫妻财产关系的恰当处理和分配,关系到家庭关系的稳定、夫妻纠纷的妥善处理和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婚姻法应当重视对子女财产的保护,不得将子女的财产混为夫妻财产来分割。另外,照顾无过失方原则还应体现在法院有权干预整个离婚财产的处理,使过失方实际所得财产不得高于无过失方。
徐安琪指出:有必要在婚姻法中重申实施家庭暴力的法律责任和司法机关的职责。具体条款为:“接受求助的公安机关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及时制止和为受害方进行伤残鉴定,并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求助不作为,因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其行政主管的法律责任。”还建议新婚姻法作出“有暴力倾向者不宜成为未成年子女监护人”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