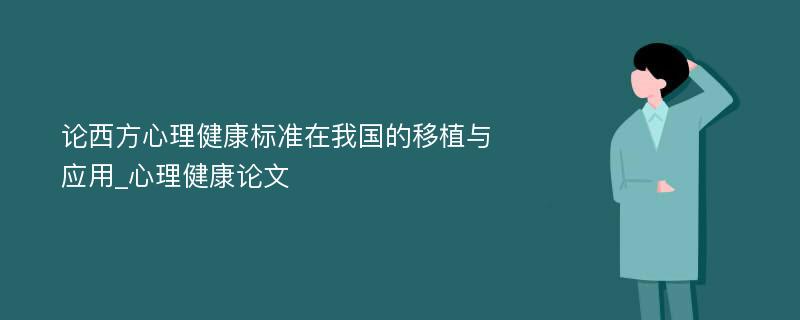
评西方心理健康标准在中国的移植与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健康论文,中国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3)09-0050-05
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迁之中,经济体制的转轨,生活节奏的加快,道德价值观的矛盾与模糊,行为模式的多元等等,增加了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紧张因素,致使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增多。心理健康教育——这一现代学校教育形式也应运而生。但是,由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较晚,目前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仍停留在引进和模仿西方理论、西方模式的水平上,缺乏本土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和方法。
西方心理健康及教育理论已形成众多流派,在不同的理论流派基础上又产生了多种辅导模式。本文无力一一详尽。在此,仅以心理健康标准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为个案,管窥西方(主要指美国)心理健康及教育理论在中国的移植与应用。
为此,我们选取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10本有代表性的相关学术著作,以及8种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注:10本学术著作为:王登峰,张伯源.大学生心理卫生与咨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王效道.心理卫生[M].杭州:浙江科技出版社,1990;马建青.心理卫生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陈安福.心理教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陈永胜.导引人生——心理卫生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孙少平.学生心理辅导[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朱敬先.健康心理学[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廖素菊.心理卫生与保健[M].台北:水牛出版社,1982;[美]鲍威尔,俞筱钧编译.适应心理学[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王友平,鲁克成.排忧解愁的艺术——当代心理卫生大观[M].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
8种学校刊物为:教育研究、心理学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心理科学、教育研究与实验、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等。)检索其对西方心理健康标准的引用与介绍情况(我们共搜集到30余种中西方学者对心理健康标准的界定),分析西方心理健康标准在中国的移植与应用之利弊得失,为今后引介西方心理健康及教育理论,以及当前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心理健康标准内涵的界定
综观我国学者所制定的心理健康标准,从中可抽象出下列六个要素,即正常的智力、适度的情绪、健全的意志、统一的人格、正确的自我概念、和谐的人际关系或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等,尽管在表述上用词很中国化,然而深究起来便可发现,智力、情绪、意志、人格、自我概念等的正常与否,仍是以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标准来判断的。从西方翻译过来的量表,即使经过修订,也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体现着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文化土壤中建立的许多理论、概念、方法和结论,即使在解释其自身的心理及行为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而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东方文化圈的国家中则有着更大的局限性,不是隔靴搔痒、解释无力,就是根本不符合当地实情。
西方关于智力的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智力概念。美国主流心理学认为,具有高智商的人应该知道很多事情,并且能迅速地回答问题。因而,在美国,一个人如果很灵巧,做事迅速,就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人。而在乌干达的Baganda人中,他们的智力概念往往与有学问、慢慢地深思熟虑以及能说出正确的事情有关。由此,缓慢与冗长的思维、符合社会规范等成为Baganda人所理解的智力标准。所以,Baganda社会的聪明人在美国社会里可能被视为笨蛋,反之亦然。[1]
在“人格”这一概念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港台学者曾使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MMPI)对中国人和其他文化群体中的人进行比较研究。[2]调查中发现中国人无论正常人还是心理疾病患者,在第二和第八项上得分都特别高。而这两个项目所描述的大多是人际反应、一般活动水平和人们的价值观问题,上述结果实际上是由不同社会对于这些方面的不同期望与评价造成的。它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差异,并不能表明中国人心理疾病的发生率更高。可以说,在我国学者制定的心理健康标准中,智力、人格、情绪、意志、自我概念、人际关系或社会适应能力等无一不是西方的概念,更具体来说,都是美国的概念。杨中芳在讨论社会心理学本土化问题时曾经正确地指出:“发掘及发展本土的、当地人常用的社会心理概念,而用他们来作研究对象,是本土研究定向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过去在过分依赖外国社会心理学的时期,我们在作研究时,选择什么概念,完全是‘照搬’,没有去考虑这些‘进口’概念到底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有没有?即使是有,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那个概念,与外国人脑海中的那个概念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时时犯了研究结果‘牛头不对马嘴’的毛病。”[3]她说过去几十年中国港台的社会科学研究结果支离破碎,变成围绕外国概念及研究的佐证。而对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同社会结构及价值体系下的完整的中国人,是怎么思想、怎么行动的了解缺乏一套完整的概念及理论。在中国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假思索地用西方概念来界定心理健康标准,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心理障碍只具有普遍性,各种心理障碍的原因和表现在不同社会都是相同的。事实上,大量的证据表明,心理健康标准乃是特定社会文化、历史空间交织下的产物。人格的发展是个体先天的资质禀赋与后天的物质及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都强调每个社会有不同的文化,而个人的人格特质常为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心理人类学的研究发现:不仅正常心理具有跨文化差异性,心理障碍也具有跨文化差异性。早期的一些心理人类学家认为心理变态是相对的,在一个社会中被认为是恰当和正常的行为,在另一个社会中则被认为是变态的,反之亦然。例如,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曾经比较了不同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她指出:“西方文明倾向于把一种甚至是温和的同性恋也视为异常行为。对同性恋的临床描绘侧重于它所产生的神经症和精神病,并且几乎象对待性倒错者一样突出他的行为功能的失调。然而,我们只要看看其他文化就会意识到,决不是任何社会情境中的同性恋者都普遍一致地出现功能障碍。他们并不总是软弱无能的。某些社会甚至特别地赞赏他们。自然,柏拉图的《理想国》最令人信服地陈述了同性恋者那令人尊敬的地位。同性恋被描述为一种达到美好生活的主要手段,而柏拉图对这种反应的高度评价则反映了当时希腊人风俗中的普遍行为。”[4](P248)她还指出,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中,同性恋者往往被看作是有非凡能力的人。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情形,而在今天的美国,同性恋已经开始被视为正常,并在有些州取得合法的地位。这一事实更加证明了本尼迪克特的观点。
另一个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e Mead)也强调心理障碍的跨文化差异性。在她之前,人们曾经普遍认为青春期的压抑与紧张是青春期所固有的,因而带有普遍性。但是米德通过对萨摩亚人的考察发现:“青春期并非必然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紧张时期,任何心理紧张都来自文化条件。”[5](P185)
“缩阳症”曾几度流行于东南亚和我国南部沿海地区,被国外精神医学界认为是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一种精神障碍。该症流行地区迷信较盛,在汉族居民中有“缩阳”致命的传说。又如多动症,我国父母和教师乃至医生往往容易夸大儿童的过动行为,许多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儿童,如果按照美国标准诊断都不够多动症的条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文化对儿童活动量的认定要低于美国文化。
尽管当代的心理人类学和跨文化精神医学已经不象早期那样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但心理障碍具有跨文化差异性这一点却是大家公认的。虽然有许多行为(尤其是严重的精神异常)在多数文化中都被视为异常,但也有不少行为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看待。心理健康标准既具有文化普适性,又具有文化相对性。在移植西方心理健康标准时尤其应注意后者。
二、个体还是群体——心理健康标准研究取向的抉择
就不同的研究领域而言,个体心理健康的标准可分为心理学的标准、社会学的标准和精神医学的标准。心理学标准注重对个体良好适应社会生活所应有的心理状态的描述。一般采用统计学的方法,找出正常行为的数值分布,即常态分配的平均数加(或减)一个标准差。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接近数值分布的平均状态,就被认为是健康的。如果其行为偏离平均状态,则被认为是不健康的;精神医学标准偏重心理疾病症状的描述。没有心理疾病症状者被认为是健康的,凡表现出心理疾病症状者被视为心理不健康;社会学标准则以个体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作为判断心理是否健康的标准。每个社会都有某些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行为标准。如果个体的行为符合这些社会规范,他就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明显偏离这些社会规范的人就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康的人。
如果分析一下西方(主要是美国)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界定,就可发现,他们的研究视角多以个体为取向。这些学者的学术背景以心理学家占绝大多数。心理学在美国开始建立之时就是朝向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的,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主观意识、内在心理活动、过程和状态。它只研究个体,并依据个体来看待和解释群体。如奥尔波特就提出,只有在个体之中才能够发现作为个体之间互动基础的行为机制和意识过程。那种不是以个体心理学作为自己全部基础的群体心理学是不存在的。[6]美国心理学的发展无疑严重影响着其对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致使美国心理学家在界定心理健康标准时局限于个体,而不包括群体、机构乃至社会,忽视个体与群体、机构、社会的联系,否定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作用。
美国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还深受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美国社会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的自由、自主和独立,追求个人自身内在价值的自我实现,注重个人的独特性。在对待个人与环境、社会之间关系时是个人取向的,强调个人的控制和能力。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促使心理学从注重个体走向了夸大个体,割裂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美国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是以个体为中心,注重个体内部的认识活动和过程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活动和过程,轻视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割裂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将个体置身其中的客观现实社会分解和简化为单独的、不含有历史和文化成分的个体。
显然,对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仅仅专注于心理学角度的探索难免会造成对心理健康标准的曲解和错误的认识。
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应该是以个体为本,着眼于个体自身内部的各种心理活动、过程及与外显行为之间的关系,着眼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相影响和制约,还是以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为起点,着眼于个体与其周围环境中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的过程及因素之间的联系,在个体与社会的联系中寻找关于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的科学解释?我们认为,心理健康标准是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产物,主张将其置于群体和社会之中来进行研究。精通社会学的心理分析家诺曼·秦伯(Norman Zimberg)曾很好地说明了社会学与精神病学之间的矛盾:“一个人在社会里能否表现自己,不仅取决于他的人格,也取决于他所在这个社会的指导准则。所以,某些在心理学上的问题,是主观的和文化性的,并不是客观的和天然的,这与躯体疾病明显不同。”[7](P332)换言之,心理健康标准是相对的和受价值支配的,它具有社会性,并随着文化的不同而变化。
以此反观我国学者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界定,便可发现美国主流心理学影响的深远。这首先表现在研究取向上的以个体为本。我国学者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探讨均局限于个体层面,对群体、机构乃至社会未予涉及。而事实上,心理健康不仅指个体,而且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已扩展到群体乃至机构的心理健康,也就是说,心理健康已涵盖个体、群体、机构等多个层面。例如,美国学者迈尔斯(M·Miles)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组织健康的十项指标和不健康学校组织的七项指标。[8]这一关于组织心理健康与不健康的标准在1989年已由我国学者李舒驰等人译介,[9]但在相关的著作和刊物中谈及心理健康标准时都未有反映。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的个体取向,已经带来诸多理论上及实践上的困惑。例如,在理论上,对社会适应论标准的质疑就是如此。[10]在现实中,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学校要培养出健康的学生也是难以想象的。根据社会学中冲突论的观点:个体所遵循或内化的社会规范来自于他所属的利益集团,尤其在个体所属团体规范与其他团体规范发生冲突时,个体往往选择前者加以适应。换句话说,就个体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而言,个体主要是与其所属的群体或机构发生直接的关系,因而群体或机构的心理健康对个体影响重大。如果不对个体所处的群体、机构、社会的心理健康作一明确界定,而孤立地研究个体心理健康标准,将很难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事实上,已有的许多心理健康标准中已经注意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取向上的局限(即只注意个体层面),从而导致了单方面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被动适应之片面性。
三、适应还是发展——心理健康标准的价值取向
就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性质而言,心理健康标准又可分为生存标准(也可称作社会适应标准)和发展标准。[11]生存标准立足于个人生命存在,目标是最有利于保存与延长生物学寿命,故强调无条件适应环境,绝对顺从社会世态(主流文化);而发展标准则着眼于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冀求最有价值地创造生活,强调能动地适应和改造环境,通过开掘个人最大身心潜力求得身心的满足,成为崇高、尊严、自豪的人。
与心理健康标准的个体研究取向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心理学的标准,还是社会学的标准都强调个体对社会的适应。“如果你没有能力给生活强加一种什么方式的话,你必须接受生活给你提供的方式”是这一标准的生动写照。社会适应标准是基于以下两个假设而建立的:(1)在任何时候,组成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永远是少数;(2)社会、群体、机构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永远是个体。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和哲学家弗罗姆曾批评道:社会就其整体而言并不十分健全这一观点,很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却拒绝接受。他们认为,社会的精神健康难题只涉及某些个别的“不适应者”,而不涉及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未调节的问题。他说:“大多数心理学家完全站在他们所在社会的立场,竟然认为:与社会不合拍的人就是无价值和不健康的人,反之,与社会意气相投的人就是健康和有价值的人。假如我们真正搞清楚了什么叫正常健康,什么叫患精神病,那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正常的人(指能适应社会)常常不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得健康(指实现人的价值)。正常的人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完全放弃了他的自我,明明是不健康还自以为是健康,他已完全丧失了其个性和自发性。”[12](P185)一个社会整个地在精神上不够健全的说法与当今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持的社会相对主义(sociological relativism)立场相反,这些社会学家提出,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它能运转,就是正常的,而所谓病态则只能从个人不能适应他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角度加以界定。由于大多数人都有某种思想或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就必定是正当的,这种想法实在十分幼稚。再也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千千万万的人都有同样的恶习,这并不能把恶习变成美德;千千万万的人都犯有同样的错误,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千千万万的人都有同类的精神病态,并不能使这些人变成健全的人。”[13](P11)事实上,并不是只有个人或少数人会发生心理变态,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条件本身可能就是异常的,压抑人性的,在此条件下大多数人都可能不能顺其本性发展,而他们对社会的适应就成为一种变态的心理反应,结果出现多数人心理不健康的情况,出现大量“适应良好的奴隶”(马斯洛语)。此时大多数人所代表的人格就不是健全的人格,相反,少数人的不适应倒是心理健康的表现。如果在某种病态的环境中生活感到十分“适应”,那才是真正的心理病态呢!正如马斯洛所说:那些对社会邪恶势力积极逢迎的人,即善于适应的人,可能比罪犯和精神病患者更不健康,因为前者的精神脊骨已经折断。[14]因此,适应并不等于健康,健康也未必都要适应。以个体是否适应社会作为心理健康的标准,可能会出现以下的情形:异化了的精神病学家以异化了的心理健康标准来判断个体的心理是否健康,从而强化了一些被异化了的心理品质。我们显然不能笼统地将社会适应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标准。“我们不能以个人是否‘适应’社会为前提来给精神健康下一个定义;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先看社会是否适应人的需要,社会功能是促进还是阻碍精神健康的发展,然后再根据这一情况来下定义。一个人是否精神健全,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的结构。”[13](P57)当社会及群体或机构的行为规范(或心理)是健康的时候,个体对社会及群体或机构的适应当然是一种健康的适应;而当社会及群体或机构的行为规范(或心理)是不健康的时候,个体对社会及群体或机构的适应也必然是一种病态的、不健康的适应;当社会的行为规范(或心理)与群体或机构的行为规范(或心理)发生矛盾时,个体若选择健康的社会行为规范(或心理),或者健康的群体或机构的行为规范(或心理)加以适应,则这种适应是健康的,反之,则是一种病态的、不健康的适应。
在西方心理学界,人本主义的心理健康观颇值得我们关注。他们认为,一个人仅仅免于神经症或精神疾病,还不能证明他是合格的健康者,而只能说是具备了心理健康的最低条件。真正的心理健康者,应该是其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精神生活无比充实,潜能得以充分发挥,人生价值能够完全体现的人。[15]基于这一基本的心理健康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提出了心理健康的人的各种模式,如奥尔波特的“成熟的人”模式、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模式、罗杰斯的“充分起作用的人”模式、弗洛姆的“创造性的人”模式、弗兰克的“超越自我的人”模式、皮尔斯的“此时此地的人”模式等。[16]人本主义的心理健康观的重心不是个人如何去适应社会,而是个人如何在新的“健全文化”条件下,充分挖掘自我潜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其中最引人注目、最有影响力的当首推马斯洛的心理健康标准。他在制定心理健康的生存标准的同时,也强调心理健康务必追求自我实现、丰满人性与高峰体验等发展标准。
尽管如此,就我国学术界的总体情况而言,似乎存在着这么一种倾向,即我国学者在借鉴西方学者的心理健康标准时,对马斯洛的发展标准未予应有的重视,而对生存标准却情有独钟。具体而言,迄今为止我国学界更倾向于心理健康的生存标准,而从维护人格尊严,有利于创造最大限度的个人生命价值出发,心理健康的发展标准是值得推崇的。当然,生存与发展两大标准应该协调,藐视生存标准将出现梵高式的悲剧。生存与发展始终是人类的两大课题,完美的心理健康标准是生存标准与发展标准的结合。
心理健康标准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亟待回答的实践问题。引进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理健康及教育理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推动我国这方面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西方心理健康标准在我国的移植与应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本文中所指出的内容上的西方文化倾向、研究取向上的局限于个体、价值取向上的偏重生存标准(社会适应标准)等,要使我国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并成为有效指导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宜着力克服上述研究中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