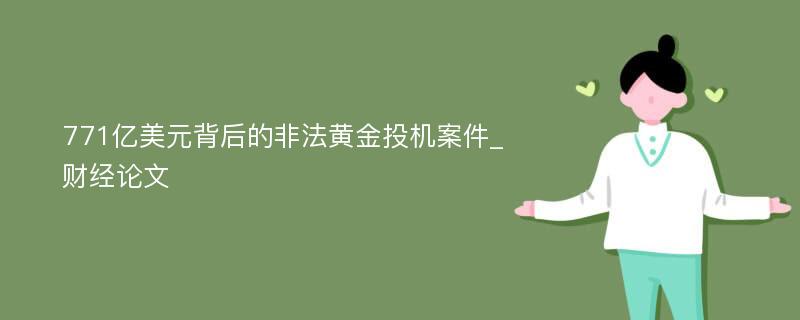
771亿非法炒金案幕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幕后论文,炒金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名香港商人,两家小公司,在两年时间里,通过网络平台运行的非法黄金期货交易,累计名义金额高达771亿元,涉及客户超过1100余人!
11月5日,这起中国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经营黄金期货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
这是一起典型的黑市交易案——没有资金托管,没有经纪公司,更没有任何监管力量的介入。
事实上,这并非孤案。就在此案开庭前一周,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刚刚于10月29日判决了一起涉案名义金额为583亿余元的非法经营黄金期货案,为此前国内同类案件的涉案数额之最。但时隔仅仅六天,纪录便被刷新。
“这类案子早有先例,且仍不断涌现新的案例,涉案的金额这么大,涉及的客户这么多,有关部门需要警醒了。”相关法律专家表示,案件频发的关键在于监管真空。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案情复杂,该案庭审持续了整整两天,至11月6日下午5时,审判长宣布休庭,将择日另行公开宣判。
粗放的骗局
非法期货交易在中国绝非新鲜事物,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在沿海地带泛滥。此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发文打击,但仍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根据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指控,伦亚领先(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伦亚)法人代表卢樱、前法人代表吴洪跃,上海凯斯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咨询分公司(下称凯斯顿)实际负责人雷建伟以及黄浩光、郭可然、郭秀蕙、黄理勇等七人涉嫌非法经营罪。
北京市检二分院审查查明,被告人卢樱、吴洪跃于2006年8月间,伙同香港人郭家强在北京成立了北京伦亚,郭家强为该公司的实际经营决策人。
自公司成立至2008年6月间,被告人卢樱、吴洪跃、黄浩光、黄理勇在郭家强的组织下,未经中国证监会等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分别先后利用北京伦亚的名义,通过非法网络平台,采用集中交易的方式,招揽社会公众客户进行所谓“伦敦金”等标准化合约的交易,在交易中采取了保证金制度、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双向交易、对冲交易等交易机制,非法从事黄金期货等交易行为,非法期货交易金额累计达563亿元。
被告人雷建伟、郭可然、郭秀蕙于2007年10月间,伙同郭家强在北京成立了凯斯顿北京公司,郭家强为该公司的实际经营决策人。
自公司成立至2008年6月间,被告人卢樱、雷建伟、郭可然、郭秀蕙、黄理勇在郭家强的组织下,未经中国证监会等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用与北京伦亚基本相同的手段,非法从事黄金期货等交易行为,非法期货交易金额累计208亿元。
据了解,凯斯顿名义上兜售的是一种理财产品——“金威尔”。在该公司提供的产品说明书上,公司将“金威尔”产品定性为“投资、投机两相宜”,并将黄金、白银买卖与外汇、期货、股票以及房地产交易进行了对比,突出黄金白银买卖费用低、流动性强、获利机会多、可靠、透明等“优点”,并强调,“虽然风险较大,但是控制完善,有限价止损等保障,交易量巨大,不受大户操纵”。
北京伦亚兜售的产品“领先实业”也完全类似。
这事实上是一种黄金衍生品交易,即盯住金价变动的对赌游戏,并无实物交割;再加上实施保证金交易制度,相当于将客户资金放大了50多倍的杠杆,进而渲染其盈利预期,客户就此落入陷阱。
“案发之初,我们曾经登陆北京伦亚的网站,上面有一个模拟交易平台,进入操作后,很容易就能赚很多钱,非常诱人。”相关办案人员介绍说。
事实上,这一私设的赌局全无风控保障。客户资金根本就没有进入公司账户,而是进入了几名被告及其亲属的个人账户。这些账户在案发后都被查封,冻结了700余万元人民币。
“这原本是个常识性问题:你做交易,怎么可能把资金汇入个人账户?但投资者都被所谓的赚钱效应迷住了眼睛。”一位期货公司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据办案人员介绍,客户完成汇款后,即可在该公司网站的交易系统中获得账号,进行无实物交割的黄金合约集中交易。
交易时,客户需要支付非常低的手续费,北京伦亚和凯斯顿与客户间采用人民币结算,并实施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当客户在炒金过程中亏损额达到所缴保证金的80%或者90%时,客户如果不补进保证金,即被强行平仓。
“这一套期货交易模式,确实吸引了不少不明就里的炒金客。但事实上,该公司的黄金交易并不与国际黄金市场接轨,只大致上按照国际即时金价的浮动报价,供客户进行参考。”北京市检二分院公诉处检察官符秋告诉《财经》记者,交易过程中,这两家公司同时充当买方和卖方,还按每笔交易向客户收取仓金。
“这类交易很可能就是那种‘黑箱’的对敲对赌,客户和公司之间对赌,公司方面可以通过随意变更交易头寸,牟取巨额非法利益,客户肯定要赔。”一位期货公司的人士分析指出。
据了解,北京伦亚和凯斯顿的黄金交易是每手100盎司,单边交易保证金为每手1万元,杠杆倍数高达50多倍,保证金比率不到2%。
“非法期货交易的卖点都是非常低的手续费,能够迎合投资者的心理,因为正常黄金期货交易的手续费远远高于这个水平。”符秋说。
至2008年6月案发,北京伦亚和凯斯顿网上交易平台上共有客户1143个,交易名义金额累计为771亿余元。两年间,北京伦亚和凯斯顿已向客户净收取交易保证金7951万余元,收取手续费和仓息合计3759万元。造成客户平仓损失3600万余元。
无人监管
在北京伦亚和凯斯顿案件中,香港人郭家强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先后创办两家公司从事黄金期货业务,亲自担任北京伦亚的技术总监,还把自己的儿子郭可然派入凯斯顿担任市场总监。案发后,郭家强人间蒸发,至今不知去向。
在11月5日的庭审中,多名被告人均辩称,自己对公司的实际运作不知情,只是按照郭家强设计的交易体系操作,他们认为,这套交易体系应该是合法的。
据多名被告人的供述,上述两家公司在这个市场中扮演着做市商的角色,每天把客户的交易进行内部对冲之后,轧出净头寸,由郭家强在香港甚至伦敦的场外黄金市场进行对冲。但这一辩称无证据支持。
不过,即便这一交易模式得到证实,其自身的合法性也相当模糊。
从国际黄金市场的发展轨迹看,场外市场的交易量占整个黄金市场交易量近90%。就伦敦黄金市场而言,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其交易是通过无形方式——五大金商及客户网络间的相互联系组成;苏黎世黄金市场也没有正式组织结构,主要通过瑞士三大银行为客户代为买卖并负责清算。
国际上的交易惯例,都是由代理公司在内部先进行对冲,轧出净头寸到外部找对手做对冲。这种基于信用基础的交易模式,往往存在着巨大的交易对手风险。事实上,在此次金融危机后,关于衍生品场外交易的规范一直在讨论中,诸如建立中央清算体系、将场外交易场内化等。
事实上,类似于北京伦亚、凯斯顿的黑市交易,较之国际上的场外市场更缺乏规范。作为做市商的这两家公司本身并无金融牌照,遑论内外部监管。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国内与北京伦亚和凯斯顿相类似的投资公司数目庞大,而真正被立案处理的案件并不多,原因就在于这类交易不属于任何一个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法律也对此没有明确的界定,是不折不扣的真空地带。
此案的第二被告人吴洪跃,其从业简历显示,在进入北京伦亚之前,曾供职于另一家从事相同业务的公司,而北京伦亚案发被查后,这个从事相同业务的公司却未受任何影响,至今尚在运作。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关来认定某一家公司是否属于从事非法期货交易,司法部门也很难办。”相关办案人员向《财经》记者透露,北京伦亚的案发,源于一名客户在损失上百万元资金后,感觉该公司交易平台有问题,遂于2007年6月向相关部门举报。
北京市相关部门收到这一举报线索后,先后汇报给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多个部门,线索在几个部门之间来回转手后,2008年1月北京市公安局立案。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在接手承办此案后,很快就将相关犯罪嫌疑人锁定,但迟迟不敢轻易实施抓捕,其原因就在于不能确定是否属于非法交易。
不得已之下,北京市公安机关通过公安部向证监会发函,最终获得证监会回应,出具函件确认北京伦亚与凯斯顿的行为属于期货交易行为。公安机关遂于2008年6月18日将涉案人一举抓获实施拘留。
在11月5日的庭审中,证监会出具的该函件,也成为公诉方指控被告人行为属于非法经营期货的重要证据。
但对于这一认定,多数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并不认可。据《财经》记者了解,多数被告的辩护律师,认为自己的当事人没有触犯法律,因而做了无罪辩护。
该案休庭期间,被告人黄理永的辩护人、北京市紫光达律师事务所王永俊律师向《财经》记者表示,此案的被告从事的交易不是期货,而是一种类似期货。对于这种类似期货,无论全国人大,还是最高法院,均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认定其为非法。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此案中被告的行为不应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王永俊还进一步表示,尤其是自己的当事人黄理永,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他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维护网络之类的日常工作。
不过,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两家公司提供的交易业务,实质上已经具备了期货交易中的放大交易和强行平仓两大特征,符合我国《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关于期货交易特征的管理。同时,作为监管部门的中国证监会已就本案两公司的行为作出了权威认定,所以应该构成非法经营罪。
亡羊何以补牢
“北京伦亚和凯斯顿案显然反映了我国现行法律的不足。”相关法律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对非法场外黄金交易惩处方面的法律依据不足。
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取缔自发黄金市场加强黄金产品管理的通知》,出台于黄金市场严格管制时期,主要针对黄金走私问题。而在1997年《刑法》出台后,对“非法集资”的界定中,也没有专门涉及黄金投资领域。因此,对于黄金市场违规者,目前多是按照非法经营定罪处理。
1999年《刑法修正案》在“非法经营罪”中增加了一款:“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但黄金无实物交易是否确定属于“非法经营罪”的期货范围,显然存在一定争议。
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监督管理黄金市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据《行政许可法》《金银管理条例》和国务院授权,管理黄金进出口;二是对上海黄金交易所进行监管;三是与中国银监会按职责分工,共同监管商业银行的黄金业务。
银监会则依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开办黄金业务进行准入性监管及有关内控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开办黄金业务均需得到中国银监会的审批或备案通过。
证监会则依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对黄金期货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监管。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黄金期货交易及相关活动。但场外市场并不在证监会的监管范围之内,境外的场外市场交易证监会也不负责监管。
正是由于法律不明确,造成监管真空,近几年来非法场外黄金交易层出不穷,很多不法分子通过设立交易平台,提供黄金交易服务,并要求投资者在其指定账户存入交易资金,并根据国内或国际黄金市场交易情况,提供黄金买卖报价,获取点差收入或交易手续费收入。由于其没有向任何监管部门进行业务和资质申请,从而使其游离于监管视野之外。
“这些非法交易多采用现金结算,具有预约性和随机性,连任何账务记录都没有,蕴藏着巨大的交易风险。”知情人士表示,“现在的监管真空导致好人举手也没人理,坏人则根本不必遮遮掩掩。”
在10月29日杭州刚刚判决的、涉案名义金额583亿元的浙江世纪黄金制品有限公司非法经营黄金期货案中,涉案公司曾经为了取得合法经营文件,奔走各地,走访了浙江省政府法制部门、证监会等多个监管部门,也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申请,但最终无一部门给出明确答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告诉《财经》记者,随着上述案件的曝光,相关监管部门必须反省。监管机构往往在理论上把境内和境外隔开,对于内外联动的跨境期货交易视而不见。
事实上,由于现代技术如此发达,境内居民对境外衍生品进行投资已比比皆是。比如一些代理商做的只是接受投资者的委托,帮助投资者在境外做期货交易,因而完全在现有监管框架之外。
同时,在通信科技发达的今天,界定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已经变得很困难。“我们很难说,某几个品种到底是场内交易,还是实际上在场外市场。”彭冰表示,在衍生品交易方面急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借以防止相关风险的再度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