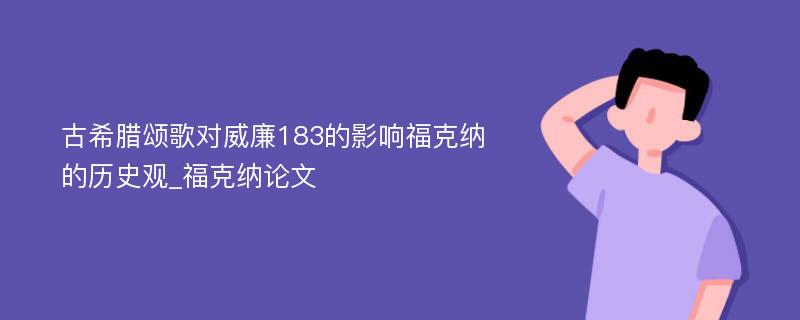
《希腊古瓮颂》对威廉#183;福克纳历史观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历史观论文,威廉论文,福克纳论文,古瓮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08)03-0085-05
1955年当威廉·福克纳被问起自己最喜欢的诗人时,他毫不犹豫讲到约翰·济慈,并承认《希腊古瓮颂》对自己影响深远(Grenier,1956:165)。除了这种坦率的表达外,福克纳在众多场合下还谈到对这首诗的喜爱,如1922年在读完约瑟夫·赫盖斯海麦的3部小说后他曾这样写道:“几个难以忘却的人物在悄无声息和无法阻挡的运动中,始终追赶不上时间的流逝”(Collins,1962:101)。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里的“悄无声息和无法阻挡的运动”意味着运动的永恒。他在1925年为《双面人》撰写的文章中又提到:“我读到‘你依然是寂静的贞洁新娘’,发现一片平静的水域,如此地强烈和有力,用自己的力量保持着平静,如同面包一样让人感到满意。”(Collins,1962:117)这里提到的“平静的水域”,如同对赫盖斯海麦小说的评论一样,展示了人们为暂时摆脱时间流动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愉快心情。分析一下福克纳的作品,人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从《萨多利斯》到《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还是从《下去,摩西》到《修女安魂曲》,都与《希腊古瓮颂》中所体现的“静”与“动”的统一相契合。这种“静”与“动”的统一以及所表现出的现实与历史的冲突与融合,从福克纳创作伊始就构成了其历史观最基本的部分。
1.《希腊古瓮颂》与《献给艾米莉的玫瑰》
《希腊古瓮颂》刻画了一群人或神在舞乐声中如醉如狂地追逐着一些少女,意景流动之美同古瓮浮雕之中静寂之美融合在一起:歌声、树叶和恋人的亲吻都被固于一瞬,通过瞬间表现让人们获得了最佳动态效果。同样,福克纳《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也体现了济慈《希腊古瓮颂》中这种“静”与“动”的关系。首先,从结构上来说二者都分为5个部分:《希腊古瓮颂》讲述了古瓮的历史和神秘涵义、诗人对古瓮上人物抛开时间束缚而表达的敬意、对永恒挚爱的庆祝和欢呼、一个因居民都到祭坛参加婚礼而使街道寂静的小镇、最后是对古瓮永恒的颂扬;《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讲述了艾米莉小姐的丧事及影响、同时间作斗争的信念、沉浸在爱情之中的易变性格、镇上的居民对其爱情的好奇与监视、最后为人们提供了其生活在一个“比爱情更长久的睡眠”图画。二者结构和场面的相似性以及“静”与“动”的对应性明显反映出《希腊古瓮颂》对福克纳的影响。
其次,从内容来看,《希腊古瓮颂》一开始,静态的古瓮被诗人拟化为寂静的新娘,因埋藏在地下年代久远,古瓮与寂静为伍并见证了历史,因此,堪称史学家。同样,《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艾米莉也是一个即将成为新娘,但同样在“静寂”环境下生活的女子:她是南方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南方历史的见证人。《希腊古瓮颂》第二节是近距离细节描写:吹奏乐器的歌手不知疲倦,少年的歌声在奔腾,热恋的情人在互诉衷肠,这一幅幅画面凝固在古瓮之上,抛开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展示了“静”与“动”的和谐之美。那对恋人即将接吻的嘴唇在接触前的一刹那间被固定下来,这个动作既包含了对过去的幸福回忆,也预示了对未来的希冀,给人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第二节也体现了这种完美的结合:艾米莉的父亲手持马鞭,在赶走她所有追求者的同时,也使她成为画中人,获得了暂时的“寂静”。当济慈通过期盼古瓮上人物在静止的图画中保持运动的永恒来结束全节的时候,福克纳也采用同样的方法结尾,让人们感受到艾米莉在其父亲去世短短的“静”中所表现出内心深处永恒的“动”。
《希腊古瓮颂》第三节直接描写了变化世界中的寂静,诗人连续用了5个“永远”,似乎强调在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幻想着一种亘古不变的静止。同样,《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第三部分也描写了一个建立在幻想和期盼之上的“幸福爱情故事”。为了和恋人永远厮守在一起,艾米莉用砒霜毒死了其男友。这种行为的后果与《希腊古瓮颂》的诗句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当人们享受爱情幸福的同时,爱情也常常会“留下悲痛的心和厌腻感/发烧的额头和焦干的口舌”(济慈,1998:401)。同样,艾米莉与恋人幻想在享受爱情永恒的同时,也遭受了现实生活的折磨与嘲笑。《希腊古瓮颂》第四节展现了祭祀、牧师和一群当地人见证两个恋人的婚礼的想象,这是一场注定不完美的婚礼,就好像新娘和新郎亲吻,却永远触不到对方的嘴唇一样;忙碌、操劳、幸福和喜悦带给人们的却是满城的“荒凉寂静”。《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第四部分也是如此。艾米莉不辞辛苦地准备着自己的婚礼,但最终并没有得到她真正的幸福。人们看到的是:在一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里,两个异性骷髅结合在一起的辛酸场景。艺术中感情可以永远不变,但现实生活中爱情需要代价。这样,静态的画面与动态的生命,永恒的历史和多变的现实社会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希腊古瓮颂》最后一节重新回到古瓮上,把静态的图像和济慈本人对同龄人的感情进行了比较。同样,《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结尾部分也回到故事伊始。把此时的故事同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进行对比:艾米莉静静地躺着,上方悬挂着她父亲的炭笔画像,这幅画正是多年前她本人亲手所作。济慈借助古瓮上的人物,联想到自己身边的同龄人,发出了“美就是真,真就是美”的感慨;当福克纳写道艾米莉“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煎熬的永恒的场面已经使他驯服”的句子时,谁又能怀疑他那“不变革的唯一出路是死亡”(Meriwether,1965; 95)的呐喊不是对战后南方人的警戒?
时间无法穿透古瓮上的婚礼,但可以把它变为永恒的空间;而济慈凭借自己的想象又把空间上的婚礼还原为时间上的现实生活,通过古瓮上瞬间浓缩的“静”和永恒完美的“动”,传达了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从古瓮的意象中找到了艺术永恒的真谛,即在变化的世界中把握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福克纳接受了济慈的思想,把时间上多变的南方传奇转变为空间上不变的文学形式,通过历史的“静”与现实生活的“动”的统一探讨了南方的辉煌过去与战后创伤,提醒南方人在崇尚过去荣耀的同时还要注重现在、面向未来。这体现了他在尊重历史的同时又不被历史所限制的辩证历史观。
2.《希腊古瓮颂》与《萨多利斯》、《喧哗与骚动》与《八月之光》
《萨多利斯》是福克纳第一部采用《希腊古瓮颂》意象的作品。对小说重要人物贺拉斯·班波来说,“和平的意义”存在于“昔日不变的岁月;或许没有翅膀,但也不是灾难”。(Faulkner,1953:19)在他看来,其妹妹纳西萨如同古瓮上的人物一样,代表寂静。为了反映贺拉斯对这种寂静的向往,福克纳再一次寻求“寂静水域”的意象来表现这个人物:“他迅速地看了她一眼,脸上的阴云如同来时一样迅速地退去了,他的神情,如同一个在平静海面上游泳者一样,迅速再次跌人到她那爱抚中的平静状态”。(Faulkner,1953:149)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加文·斯蒂文斯的塑造也是如此。这个杰佛逊的律师很像济慈的“大胆的恋人”,虽然接近了目标,却不能与自己相爱的女子接吻。他时刻幻想自己像骑士一样保护南方妇女,但遇到需要保护的女性时却逃之天天。加文的这种性格一方面代表了传统的人道主义,象征着对知识和生活的尊重;另一方面他又是知识和环境的牺牲品,被自己的思想所左右,即使在能够成功的情况下仍然退缩到过去的寂静之中,竭力幻想进入到青春期的姑娘不再变化。对生活在战后的南方人来说,南方历史上形成的荣耀和道德规范是静态的,而现实生活却是动态的,用静态的荣耀和妇道观约束动态中的南方女性,是贺拉斯和加文的悲剧所在。
同样,《喧哗与骚动》中昆丁也是如此。作为康普生家族的长子,昆丁被赋予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是不停地倾听手表走动的声音,还是到后来跳河自杀之前,都拼命地试图阻止时间,希望回到他与妹妹凯蒂在一起度过的“寂静”的童年时刻。对他来说,凯蒂是被凝固在古瓮上的人物,是绝对不变的化身,但现实生活却打乱了他的幻想,他抓住乱伦这个“暂时”性的字眼,希望能说服周围的人相信他和凯蒂发生了肉体关系,这样人们就会“暂时”从他们身边高傲地离开,把他们孤独地留在地狱,在地狱的烈火中保持纯洁与清白。
昆丁落入济慈“寂静”的陷阱,成了大胆的恋人,在永恒的岁月中试图珍藏着自己的爱,使之不受时间的侵蚀而发生改变。从这方面上看,济慈的诗句几乎是为昆丁所写:“她的红艳不会消退,你虽然永元这份福气。/你将永远爱下去,她也将永远美丽!”(济慈,1998:400)济慈劝告古瓮上的人不要悲伤——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激情永远不会被时间所侵蚀。然而,昆丁却是不幸的,为维护家族荣耀,他必须阻止时间的流逝,因此,当凯蒂告诉他自己会做他让她所做的一切时,昆丁并没有和她发生乱伦,他所需要的并不是乱伦本身,而是阻止凯蒂堕落的机会。这种欲望实质上是暂时的静止,既然时间不断地流逝,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永恒的静止,因此昆丁从自己手上摘下手表,试图掩盖影子来达到阻止或摆脱时间的束缚,他的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求助于最后的静止——死亡,并最终通过河水获得了济慈的永恒寂静。正如福克纳早期的小说所体现的一样,静止的河水象征了死亡,在昆丁看来,是摆脱时间的庇护所,而人们一旦进入到这个庇护所,就不用忍受因岁月流逝而带来的恐惧和压力。
贯穿昆丁这一节,我们始终感到福克纳对这个南方贵族子孙寄予了很大同情。昆丁无论是在面包店为陌生小姑娘买面包,还是把自己的衣服留给执事,都展现了他作为康普生家族长子的慷慨和大度,让我们不知不觉地站在他那边,接受和理解他因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巨大痛苦;另一方面,福克纳时刻提醒我们,他本人确实认识到昆丁由于沉湎于过去而产生的性格缺陷,对迪尔西的颂扬实质上是对昆丁的批评。当康普生家庭中的黑人保姆平静地看待时间,有效地对待生活和自己的尊严的时候,昆丁却选择了投河自尽,因为他没有像迪尔西那样正确理解暂时的“静”和永恒的“动”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是感受到南方的历史责任和日益变化的社会现实带给他无法摆脱的巨大痛苦,他只能通过死亡才能走向济慈诗歌中所幻想的永恒“寂静”。
《八月之光》中的希尔·海托华也像昆丁一样期盼生活在一个能够摆脱时间的庇护所中。这个从小陶醉在祖父辉煌过去之中的南方牧师认为自己正好出生在其祖父在高头大马上被枪杀的那一天,他选择牧师这个职业完全是出于对过去的怀念。在他看来,回到了其祖父牺牲的那一瞬间,也意味着他找到了躲避时间流逝的庇护所。昆丁把黄昏视为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刻,因为这时候太阳即将落下,无法将其身影投射到地面上;同样,对海托华来说,黄昏也具有相似的意义,他沉湎于过去,为每天黄昏时刻的到来而活着。因而,每天当下午最后的黄色的光线淡去的时候,他就坐在窗子旁聆听着其祖父急促的马蹄声,完全沉浸在过去的“寂静”之中。对妻子漠不关心导致了她对他的不忠,并最终因为无法忍受谣传而自杀;受到震惊的教民们希望他能辞去教会的工作并离开杰佛逊,但无论是恐吓还是肉体上的暴力都不能促使他离开,最终整个社区都对他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然而,当莱娜·格里夫出现以后,海托华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为莱娜接生了孩子,为拯救乔·克里斯默斯的生命而尽了最后努力。这种参与别人的生活,介入生命的极端——出生和死亡的行为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可以说,海托华寻找的永恒“静寂”在莱娜身上体现出来了。在对莱娜最初的描述中,福克纳就把她同古瓮上人物联系在一起,认为她“仿佛是拿古瓮上的绘画,老在前进却没有移动”(Faulkner,1950:7),象征了济慈永恒的“寂静”。她的生活目的,就连海托华也承认,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也就是满足自己自然的需要。莱娜很少考虑时间,也从不对时间的流逝感到失望,这样,那些缠绕在海托华头脑中的过去在她身上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正是从她对待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态度上,海托华最终迷途知返,回到了杰佛逊的现实生活中。
福克纳对海托华的塑造与对昆丁·康普生的艺术加工十分相似,既有批评的意味,又赋有同情心,表现为复杂的矛盾心态。福克纳十分清醒地看出海托华的悲剧所在,并把它清楚地呈现给读者,使人们看到了对过去的沉湎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巨大危害;另一方面,他又让人们从海托华的悲剧中理解南方人在内战结束后的内心仅存的自豪,“这是荣耀、自豪和生活最后的一点东西”(Faulkner,1950:431)。这一点,还可以从福克纳本人对海托华的评论中看到:“他本人失败了,但有一点他仍然拥有——他那勇敢的祖父飞驰进入到城镇……(海托华)必须忍受,必须生活,但他还有一件纯洁和美好的事情——一个对曾经勇敢的祖父的回忆。”(Gwynn & Blotner,1965:75)可以说,福克纳对自己作品中人物沉湎于过去的辉煌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但并没有表明他本人完全放弃了对南方辉煌过去的崇拜。他像自己作品中大多数的人物一样,虽然明明知道自己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却始终不断地重复这种行为。这种情感上的矛盾体现了他对待南方历史的态度,如同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所追求的“静”与“动”之间的关系一样辩证而统一。
3.《希腊古瓮颂》与《下去,摩西》
济慈诗歌中的意景虽然在福克纳上述作品中都有精彩的表现,但这些作品与古瓮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还是间接的,而《下去,摩西》直接提到或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与昆丁和海托华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中的艾克·麦卡斯林没有沉湎于祖先的辉煌过去,相反却躲避过去,因为过去带给他无限的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跑到自己童年向往的大自然中独自生活,因为在那里“死亡甚至不存在”,被枪杀的雄鹿“平静和永恒地跳跃着……是永恒的”。(Faulkner,1942:327、178)这是希腊古瓮上永恒的田园景象,福克纳通过这些景象的描写,提醒人们要正确对待南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福克纳常常认为自然是一个永恒和完美的王国,在他对自然充满敬意的同时,也感受到自然面临着消失的威胁。同样,艾克·麦卡斯林也是如此。他拒绝承认森林消亡的现状,但看到从身边经过的火车运送锯倒的树木直至消失在远处时感叹道:“那么,一切都过去了。不是过去的样子了。”(Faulkner,1942:322)接着,他又否定自己:“他们没有变化,并且永恒,不会是,但却是夏天的绿色、火焰、雨水、寒冷,甚至有时是雪。”(Faulkner,1942:323)在他看来,大自然是永恒的,因为他知道在这里死亡根本不存在,因此,当他不小心差点踩上致人死命的毒蛇时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惧,相反这条毒蛇的气息“唤起了所有的知识、过去的烦恼、流浪经历和死亡”(Faulkner,1942:329),一种久别的情感涌现在他心里。我们知道,虽然艾克不承认死亡,但他认为死亡在永恒的伊甸园中确实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他面对毒蛇的唯一反应是用他过去的手势,也就是重复了多年在公鹿面前同山姆老爹打招呼的动作。此时,他并没有意识到,由于时间变化了,该手势不是生命的象征,而是死亡的标志。
艾克期望自然能够永远像自己年轻时看到的一样永恒不变,福克纳不遗余力地通过引用《希腊古瓮颂》中的诗词帮助他实现幻想。艾克14岁拒绝射杀具有传奇色彩的熊“老笨”之际,福克纳借艾克表哥之口引用济慈的诗句来解释其不愿射杀这头熊的原因:“她的红艳不会消退,你虽然永无这份福气。/你将永远爱下去,她也将永远美丽!”福克纳通过济慈对永恒美的阐释,清楚地向读者展示了艾克始终坚持时间永恒的观点,并且认为完美的大自然是他摆脱复杂遗产和现实矛盾的庇护所。这种想法和昆丁的想法完全相同,其目的都是在变化的现实世界中保持自己童年时期的单纯和清白,希望能像古瓮上的图画人物一样,被赋予永恒的寂静与和平。
当然,福克纳对艾克的行为也发表过不同的看法,如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这样评论说:“唉!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仅是抛弃。他应该更加主动,而不是躲避众人。”(Grenier,1955:175)两年后当他被问起是否把艾克看作实现了自己的命运,他这样回答:
我认为,是的。他们没有使他成功但却给了他许多重要的东西,甚至在乡下。他们给了他寂静,给了他知识——我说的知识同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不同。他们教给了他这一切。(Gwynn & Blotner,1965:54)
福克纳上述两种评论并不矛盾,前者是针对艾克试图阻止时间和变革,把森林作为庇护所而逃避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而有所不满;后者是艾克作为旧时代和旧观念的代表人物,在南方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能保持自己的清白和纯朴,赢得了福克纳的尊敬。当然,当艾克拒绝家族遗产并声明山姆老爹给了他自由时,他表明自己已经摆脱了义务和时间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这可能是福克纳同情他的原因所在。但与艾克不同的是,福克纳并不认为这种声明在南方社会中能够实现,因为他知道,如同《希腊古瓮颂》展示的永恒艺术一样,虽然“寂静”中蕴藏着生命的活力,但现实世界是“寂静”存在的基础,缺少了动态的现实世界,当然也就无法谈论“寂静”的艺术之美。这种思想,如果运用到福克纳历史观的阐释方面,也就是南方辉煌的历史必须与动态的现实社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服务于南方的现实生活。这是福克纳历史观的核心部分。
4.结语
福克纳对自己作品中的众多人物的确带有一些矛盾的观点,他似乎十分谨慎而又充满激情地接近诸如艾米莉、昆丁、海托华和艾克等人物,因为这些人都希望阻止或减缓时间的流逝,以便回到或保持自己完美的过去。然而,就像济慈因羡慕古瓮上的人物画像使时间停滞而产生不快一样,福克纳也理性地发现自己情感对过去的依附以及对时间停滞的盼望而产生的复杂心情。作为一个20世纪的作家,他十分理解发展和变革的需要;作为一个南方人,他懂得十分关注过去的阴影所带来的危险。作为福克纳的代言人,《坟墓的入侵者》中的加文·斯蒂芬斯这样评论说:“一个人总是盲目地依赖祖先的罪恶,这是最大的悲哀。”(Faulkner,1948:23)福克纳也在不同的场合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时间必须是流动不止的,人类必须变革,反之,则走向死亡。
当然,福克纳从来没有解决好时间与变革之间的矛盾问题,他显而易见地尊重甚至羡慕迪尔西、莱娜等人,因为这些人能够按照时间的流动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能够接受流逝的时间带给他们的一切。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人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与福克纳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为他们的世界不属于福克纳本人,或者说福克纳作品中被时间所困扰的人物能够生活的世界只能是神话世界。像济慈古瓮的图画一样,福克纳崇尚时间的流动,但作为一个南方人,他又试图通过时间的变化来展现自己对南方传统的眷恋,而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恰好体现了他强烈的内心冲突,同时又成为影响其历史观最重要的因素。
收稿日期:2007-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