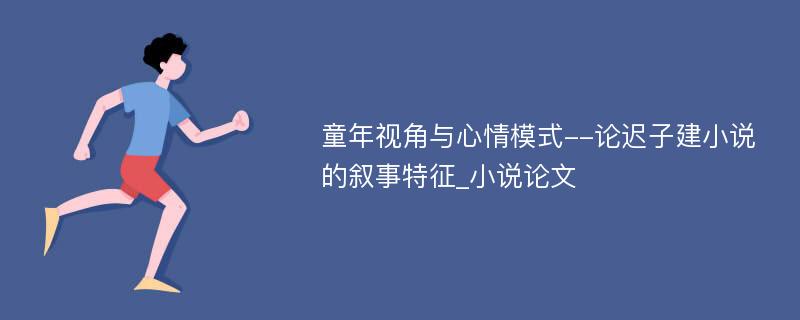
童年视角与情调模式——论迟子建小说的叙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调论文,视角论文,童年论文,特征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644(2001)01-0065-05 在当今颇具实力的作家中,迟子建的小说别具一格。创作题材的新鲜朴素、主题表现的深 刻博大,每每激活现代人那颗日渐疲惫和麻木的心灵,而在叙事上的着意经营,更使得她的 小说亲切而耐读。
进入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你首先就会看到叙述视角的丰赡和新异。所谓叙述视角,是指作 品 叙述人观看和讲述故事的角度,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亦即作家把自己体验到的现 实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因此叙述视角表现着作家的写作立场,甚至决定着 作品的价值取向。故迟子建小说对故土家园的钟情挚爱,对朴素生命和爱情的温婉表达,对 世道人心尤其是寻常百姓的独特解读,以及作品总体上“浪漫、空灵和忧郁”的美学格调, 可以说都与其叙述视角密切相关。然而在叙述层面上作家又是隐藏不露的。她让各种各样的 叙述人来完成这一切,由叙述人称来决定叙述视角的特征。在现今已发表的三百多万字的小 说作品中,从人称上看大致有这么三种:一种是第三人称,即全知视角叙述,这在迟子建小 说中占了多数,长篇《树下》,中篇《秧歌》、《香坊》、《旧时代的磨房》、《岸上的美 奴》、《洋铁铺叮当响》、《日落碗窑》、《逆行精灵》,短篇《沉睡的大固其固》、《葫 芦街头唱晚》、《罗索河瘟疫》、《挤奶员失业的日子》、《月光下的革命》、《盲人报摊 》、《亲亲土豆》、《腊月宰猪》、《逝川》、《银盘》、《雾月牛栏》等等都是;第二种 是第一人称,以作品中人物的视角叙述,《北极村童话》、《炉火依然》、《原始风景》、 《东窗》、《原野上的羊群》、《麦穗》、《向着白夜旅行》、《白雪的墓园》、《重温草 莓》、《从山上到山下的回忆》、《庙中的长信》、《朋友们来看雪吧》等等即是:第三种 是交叉使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即用两个以上叙述人的复合视角叙事,像长篇《晨钟 响彻黄昏》的第一章由“我”(宋加文)充当叙述人,第二章的“我”的叙述则改为刘天园来 完成,第三章和第五章(最后一章)则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第四章又以“我”——宋加文 的儿子宋飞扬担任叙述人;《遥渡相思》、《白银那》和《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也是两种 人称交互使用,双视角的参照,使故事内蕴更显得丰厚和幽微。
一般说来,第三人称叙事,最能见出作者的经历、学养、写作才能和文化立场。故透过全 知叙述的那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迟子建,一个深受祖国传统文化熏陶和黑龙江 水土滋养且对生活充满忧伤但并不绝望的知识女性,一个有着悲天悯人情怀、坚守民间立场 且注重“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的年轻作家。第一人称叙事,作家的写作姿态则不大好把 握,因为在不同的作品中,“我”像川剧中的变脸者那样,一会儿是一个天真活泼而又调皮 任性的小女孩(《北极村童话》),一会儿是一个深有涵养却不能生养的女画家(《原野上的 羊群》),有时是一个勇敢的男学生(《麦穗》),有时又成了热情尽责却有点儿好色的镇长( 《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但不管怎样,说到底作家塑造的众多人物中, 或多或少都有她的身影。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不论迟子建采用何种叙述视角,用哪一种人称 叙 事,她都不以启蒙精英或“精神领袖”的姿态居高临下,而是贴近底层,置身民间,带着热 切的人文关怀从事写作,因此她的作品总是洋溢着善意和良知,有着唯美的倾向。
在探讨迟子建小说叙述特征的时候,我觉得她对童年视角的运用特别富于美学意味。无庸 讳 言,迟子建的早期创作,像《北极村童话》、《沉睡的大固其固》等小说,在用童年视角叙 述的时候,确实有些稚嫩甚至表现出些许矫饰的痕迹,比如让7岁的学龄前小女孩告别北极 村亲人的时候,从心里迸发出“纯真”、“苦涩”、“自由之子”、“羡慕”、“思恋”、 “彼岸”等一连串文皱皱的词语来,就显得很不自然。看来初出茅庐的迟子建还没有驾轻就 熟地做到合理适度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感表达方式,故情不由衷地把成人的思想感情和行 为,硬加在童年的主人公身上了。尽管同后来对于童年心态的大多数成功描写相比,迟子建 这些违背一般情理的地方不过是白璧微瑕,但毕竟对她作品的完美性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不 过我们在批评作者童年视角有所不足的时候,千万别忽略了它的巨大的美学生成意义。因为 作为一个新手,叙述上的稚嫩是极自然的事儿,但在初始创作的童年视角中就包孕了诸如题 材、情调、结构、语言等多方面的、具有独创性的生成因子,可就有些不同寻常了。这些具 有独创性的生成因子,在《北极村童话》中,表现得尤为出彩。
《北极村童话》写小女孩迎灯六七岁时被留在北极村姥姥家的生活故事。这部散淡的中篇 几乎没有什么情节,通篇都是叙述一个孩童在北国乡村毫无羁勒地玩耍,以及和亲人、村邻 日常交往的事儿。相信这是作家童年生活的一段经历。和许多作家一样,迟子建在这里倾注 了全部情思,追忆和描写她的童年时光与经历。按照儿童心理学的观点,童年那些最深刻的 记忆往往能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的思维类型。因为7岁儿童的脑重量已能达到1280克,接近了 成年人的脑重量水平,由此脑结构、脑功能发生急剧变化,外部语言逐步向内部语言过渡, 于是最初的意识便开始产生了,生命在这时鲜亮得如清晨的露珠,最先进入的深刻印象会深 深附着并化合到思维结构和方式之中,而且必然会在今后的过程中一再地获得复现。尤其对 于作家来说,童年记忆不仅在情感上始终缠绕着他们,而且会成为他们创作思维定势的某种 定向路标,成为他们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的泉眼。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迟子建成名后的绝大 多数作品,都有《北极村童话》的影子,或者简直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进一步展开。《原始 风景》、《东窗》这样《童话》的成人版自不用说(和《北极村童话》的现在进行时的叙述 不一样,这两部小说故事时间和讲述时间是历时态的,因此虽说在大多情况下是用童年视角 叙事,但又明显的有一双成年人的眼光在打量着这一切),其它内容各异的作品,从《北国 一片苍茫》到《雾月牛栏》(短篇),从《树下》到《晨钟响彻黄昏》(长篇),从《逆行精灵 》到《观慧记》(中篇),都可以发现作家流溢在《童话》里的情愫、感觉、人生姿态和美学 追求。譬如对家园和亲情的依恋,对东北边陲原野风光的神秘与美丽的神往,以及小迎灯姥 姥的慈祥唠叨,姥爷的温厚沉默,姨娘和舅舅的亲切爽快,猴姥的热情和邋遢,都如旋律般 地一再回响在这些作品中;再如对死亡的描写,我们已经说过,迟子建有种浓得化不开的死 亡意识,好像在新时期青年作家中还没有见到哪一位像迟子建这样如此热衷频频地描写死亡 ,以至于像《日落碗窑》这样表现生命蓬勃的作品在迟子建笔下似乎成了特例。或许与大舅 的死对姥爷造成的哀痛、给姥姥带来的不幸有着深深的关联吧,而且“苏联老奶奶”的死, 这位把“我”带入文化之门,甚至可以说引向人生之路的慈爱而孤寂的老奶奶,在年节前夕 死 去,对“我”幼小心灵的刺激,一定会像童年海明威看到的因妻子难产而自杀的印第安丈夫 那样强烈,那样深深影响到一生的创作吧!还有在纯净感觉的叙述中,“我”流露出来的对 成人世界和习俗陈规的怀疑精神与反叛性格,也成了迟子建后来创作的一贯追求,成为她对 世界的一种独特认识。
从艺术经营方面来看,《童话》也可以说是迟子建一系列小说的生长点,譬如从这部中篇 开始,迟子建是那么钟情于童年视角,在迄今发表的所有作品中,对于童年生活的回忆和遐 想的该有半数上了吧?有论者说迟子建小说由此形成了叙述的追忆模式,当不为过。我们确 实在她的许多作品中读到了趣味盎然的童年生活情景,感受到大兴安岭山野迷人的风俗人情 。叙述人那浸润着温馨气息的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又雾一般地弥漫着惆怅、失落和忧郁, 使我们也和她一样担心那纯净和朴素的美逝去永不再来。与这种偏重于个人化的体验和情感 的抒发相关的,是《童话》这部小说没有传统文论所说的那种结构的完整性,只是些童年生 活的片段加上些个人化的感触,因此从结构上看它是由一段一段的生活场景拼接而成,而这 些生活场景彼此之间又未必有人事勾连,它们的有机结合主要靠叙述人的感触和情思来完成 ,故从文学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诗话了的情绪结构。这种貌似“太散文化”的结构方式—— 姑且叫做“板块拼合式”吧,一开始不少人可能因不习惯而不大欣赏,它的两次被退稿,就 表明了这一新颖的结构方式诞生初期的命运。随着小说观念的开放和人们视野的扩大,迟子 建是越来越有信心并越来越习惯地运用这种板块式结构了。不仅《原始风景》、《东窗》等 比《童话》在这方面走得更远,而且那些直觉表现和意识流动的作品如《炉火依然》、《遥 渡相思》和《重温草莓》等,甚至包括故事性强的一些小说,像中篇《秧歌》、《原野上的 羊群》、《白银那》,长篇《晨钟响彻黄昏》等等,也大都由零散的板快衔接而成,其用意 已不是追求情节的完整统一,而是重在人生形态和生命状态的表现。迟子建的这一不懈努力 ,使她的情绪结构小说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独创性,成为她作为一个出色作家的显著标志。还 有,迟子建小说总体上空灵与充实和谐融合的美学风格,也是很大程度上始于《童话》的。 《童话》中的山林、晚霞、干得裂了缝的田埂、回荡着歌声的大江、星星和淡淡的月牙、菜 园中的蚂蚱、蝴蝶、蜻蜓和蜜蜂,还有那梦中的项圈与屋外松软的雪地,实实在在又淡若岚 烟,那阔大、空明和梦幻色彩,是生活在逼仄的城市空间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而小说描写姥 姥带“我”去看孤独死去的苏联老奶奶,“我”轻轻地合上她眼睛的细节,却又真切地让人 落泪。在迟子建以后众多的小说中,大都具有这样在写实中弥漫着空灵的氤氲之气,在空灵 中又有着精细的写实之处的魅人特色。如在《重温草莓》中,“我”与父亲在酒店会面纯属 虚构,而父母日常生活中的温情嬉戏却又写得非常真实,给人亦真亦幻的感觉。这样的小说 感人之余,还能引领人们在精神的太空做自由的飞翔。
对于迟子建这样具有鲜明个性和风格的作家,通过讨论她的小说模式,来彰明她的小说主 导方面的叙述形态与特征,把握其题材内容和美学风貌,应该说会有所稗益的。我发现,就 收入四卷本《迟子建文集》中的一部长篇和几十部中短篇而言,凡具有童年叙述视角和情绪 化结构以及温情表达辛酸生活的作品,都与传统的情节模式明显有别,这些小说并不热衷于 故事的悲欢离合或惊险曲折,人物也不在聚焦镜头之中而是退居二线,因此故事在文本中不 仅显得散淡,人物的面貌也往往有些模糊,而且作家对人物心理活动及其行为特征的描写, 也不为刻画性格服务了。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迟子建不会讲故事,相反,我们一直认 为她在新时期青年作家群中是位讲故事的高手。因为能把金戈铁马、朝代更替讲得惊心动魄 并非真本事,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很诱人,而把平庸凡俗的日常琐事叙述得津津有味那才叫真 有才分,读《洋铁铺叮当响》、《逆行精灵》和《观慧记》这些小说,你不得不惊叹迟子建 何以能把我们身边常见到的人和事叙述的如此娓娓动听、情趣横生。然而迟子建又是很善于 节制故事的,她不屑于对现实生活的仅仅复原,而是执意寻找人物和生命的意义。故在她的 这一类型小说中,叙述人讲述一些事件,介绍一些人物,大都在于渲染一种气氛,营造一种 意境,借以反映一种生活状态,传达一种审美情调。我们把迟子建的这些作品命名为情调模 式小说,当是恰如其分的。“情调”作为人的一种情感特征,在心理学上一般指同感知觉相 联系的某种情绪体验。在小说中,作家总要或多或少地表现情感,因此情调并不单单是一种 叙述的功能模式,而是所有小说佳作共有的因素。但像迟子建这样的情调小说,和一般小说 中的情调因素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的情调已从从属性的地位一跃而为文本的核心与精髓,它 流贯在小说的每一场景之中,且将它们结构成一个诗意整体,从而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叙述风 貌。譬如发表在《山花》1998年第1期上的《朋友们来看雪吧》,迟子建也写了胡达老人与 他的孙子鱼纹,写了一位面目酷似已故父亲的电视人。虽然作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胡达老人 的衣着、相貌、身世和手艺,写出了小鱼纹的灵性,但与以塑造人物性格为旨归的情节小说 相比,这爷孙俩充其量也不过是“扁平”人物,更不用说那位不知姓名的、在晚上突然跑来 与“我”共同做菜、唱歌、吃饭、喝茶、聊天,过了一个温存的晚上就永远天各一方的中年 男子了。这篇从心底呼唤出来的小说也有些故事,像胡达在“我”来的当天晚上就来“看” 我 的栗色皮箱,鱼纹用他自己编的草编铜钱和“我”交换东西,胡达在正月十五死去,鱼纹点 礼花为爷爷守灵等等。然而这些描写,不仅与以故事的生动性和惊险性取胜的情节小说比起 来微不足道,而且在作品中,也让位并服务于对雪国小镇民情风俗以及“我”的感受的描写 。读这篇小说,我们和这位下乡采风的年轻女画家一样,印象最深刻的,是乌回镇忙年的景 象,胡达老人丧葬的气氛,这儿特有的松脂和烤土豆,是雪爬犁和狍皮靴子,画炕琴和 门神,还有“我”在这儿丧失可能诞生灵性儿童机会的深深遗憾。其间交织出的明朗热情和 忧郁伤感,真是撩人心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构成迟子建情调模式小说主体的,不是人物 ,不是事件,而是有滋有味的生活场景和人生体验。
如上所述,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情调的情绪体验性来自于具体的生活场景,而组合成这个 场景的便是那些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故注重生动的细节描写成为她的这类小说的又一审美 特点。当然,所有优秀的情调小说,都离不开对富有特征性的细节的发现和描写,某种情调 的产生,就是靠这些细节给出的情趣凝聚而成的。但是与一般情调小说中的细节大都轻松有 趣不同,迟子建的这些情调小说,由于多数是她“哭”出来的,故细节描写除《东窗》的末 尾,女人们让俊俏的小媳妇去勾引蹦苞米花的以把他赶走的描写有点儿发噱之外,一般都来 的沉重,就连其中的暖意也带着些许苦涩,别有一番情味。像《白雪的墓园》中“我”的一 家刚刚安葬好父亲,正陷于难以自拔的巨大悲痛之中,年猛然来了。小说不止一处地描写“ 我”握着炉钩子下意识地不停地烧火炉的细节,“炉火越来越旺了,我仿佛看见父亲正推开 走廊尽头的门,微笑着朝我走来。从他去世的那时起,这种幻觉就一直存在。他走到我面前 了,他伸出手抚了抚我的肩膀,我握着炉钩子的手就抖了一下,墓园的情景又锐利地再现” 。 而刚哭过的姐姐明知故问地说“我”老站在炉子这儿干吗,弟弟后来也走过来烧火,他们想 着这难过的年,想着被哀痛击倒在床上的母亲,更想着山上白雪的墓园,都希图用这旺旺的 炉火来驱除那发自内心的寒冷罢!又如《东窗》里写酒鬼倪满仓一醉就虐待妻子魏金枝,酒 鬼的两个儿子便思谋着替母亲报仇解忧:
……魏金枝醒来,见两个儿子正窃窃私语着,魏金枝过去一看,10岁的倪力和7岁的倪旭正 把一根尼龙绳系成活扣,倪力往弟弟倪旭的脖子上套上尼龙绳,试探性地拉了拉说:“这回 对了。”
弟弟对着哥哥说:“能勒死吗?”哥哥说:“咱俩合伙勒,准能勒死。”
魏金枝浑身哆嗦着训斥着儿子:“你们要去干什么?”
“勒死那个酒鬼,他一喝醉就欺负你,不能让他再活了。”倪力说。
作家捕捉的这个细节真令人哭笑不得,细想想又心酸不已。还有《亲亲土豆》中秦山得知 自己患的是晚期癌症后,从妻子李爱杰手里“骗”了300元钱,买了一条宝石蓝的软缎旗袍 ,秦山死后她穿上那件旗袍为丈夫守灵的细节,以及《树下》七斗和小日在船头撒面包屑引 来盘桓的飞鸟与七斗倾慕黑龙江两岸平阔绿野的描写,既伤感异常又使人温暖欲泪。
不少论者都注意到,契诃夫的中篇小说《草原》极浓的情调意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 家对俄罗斯草原的描绘。而我们发现迟子建的许多小说在这方面同契诃夫异曲同工。她是那 样钟情于景物描绘,使作品溢满了情调。欣赏迟子建笔下的景物,你会发现它们简直和人一 样有心情有神态有动作,这就形成了她的情调小说的第三个特点:拟人化。这兴许是情调模 式 在景物描写上与其它叙述模式的一个明显不同。我们看看迟子建对北国四季的描写:一开始 冬天的痕迹还在阻止春天的到来,“地上的雪坚强地存在了一个冬天,终于没能在春风的柔 情下再坚强下去,它坚强不住了,化做了春天的泥泞,任人踩着,也任人埋怨着”(《旧时 代的磨房》);而春天却傲得不能行,它“就在屋里屋外竖着或者躺着,它的身体绿得明滑 鲜艳。山丁子树芽中的那种绿让人牙痛,而草甸子上整整齐齐的像密密实实的丝绒地毯的绿 又给人一种抽筋断骨的感觉。在这种时候哪怕是一只羊走进草丛,你开始觉得羊是白的,但 它在草丛里活动久了,你就眼花缭乱了,羊仿佛也因沾染了满天春色而变成绿的了,你会心 惊肉跳地以为羊丢了呢”(《东窗》);北国的夏天是短暂的,“就像一只漂亮的梅花鹿从森 林中跑出来,再接近你房屋的时候又突然掉头而去一样的匆匆”(《东窗》),于是迟子建就 用这一句话带过;而秋天,北方的原野就像一个待孕的地母:“土地真是奇妙,只要是点了 种,到了秋天就能从它的怀里收获成果。别以为成果是千篇一律的,它们出土时姿态万千, 可见这土地是多么奇妙,让它生什么它就生什么。圆鼓鼓的白土豆出来了,它的皮嫩得一搓 即破。水灵灵的萝卜也出来了,它们有圆有长,圆的是红萝卜,长的是青萝卜。宛如荷花骨 朵一般的蒜出土时白白莹莹,而胡萝卜被刨出时个个颜色金红。每逢这种时刻,大地上人欢 马嘶,羊叫狗吠,一片沸腾”(《日落碗窑》);冬天呢,漫长的冬天可就是多种多样脾气多 变的了,内心孤独的夜晚,你觉得“寒风像小叫驴一样,一声比一声急,无边无际的茫茫林 海回响着这尖利的叫声,天上少了月亮,只有几颗孱弱的小星,在黑沉沉的天幕上打摆子” (《北国一片苍茫》);这时候你就会认为,漫天飞舞的“雪花拥挤在一起涌向地面是因为它 们自身无法承受寂寞,它们以寂寞来拥抱寂寞,所以才有胆量叛逆天庭,才有勇气接触尘土 ”;而冬天毕竟更多的是让你心境平和的日子,这时候你能看到,“上帝把寒冷季节中最温 柔最灿烂的景色播在这里,本身就造成了一种雄壮和神秘的气氛。雪的色彩极为绚丽,它时 而玫红,时而幽蓝,时而乳黄。雪光呈现玫红时是朝霞初升时分,那时炊烟在鸡啼之后升起 。雪光展现幽蓝时是在傍晚时刻,这时所有的恋人都在祈祷黄昏的消失。雪光隐现乳黄时星 月稠密,树林中所有的鸟都因眷恋美丽的景色而放弃歌唱。”(《原始风景》)。在这里,景 色与心境,人与物,都默契相通,抒情意味得以强化,情调感也油然而生。
耐心的读者至此会发现,我们讨论迟子建小说的情调模式,一直都是引证《北极村童话》 、《东窗》这样“太散文化”的作品加以阐释的。那么,在她的那些故事性强、动作紧凑且 人物命运令人牵肠挂肚的作品中,其情调意味是何以浓郁的?这就关涉到她的这类小说的第 四个特点了:用意象的穿插或抒情文字的诗意表述来营造情调氛围。像《逝川》、《洋铁铺 叮当响》等作品中如何捕捉意象来拆解故事线以强化情调的状况,我们将在意象叙述一节详 细分析,这里着重谈谈诗意文字表述。《观慧记》写“我”和记者、游客一同乘火车,搭汽 车,一路颠簸去漠河观望千年不遇的彗星和日食的大交合。小说写得热热闹闹,特生活化, 可读到其中这样一段文字,情调就在你的心里荡漾开了:
不过现在的松苑还有积雪,雪依然很干净,……直立而无绿意的松树给人一种孤寂的感觉 ,仿佛它们每天都想与上帝对话,而终无结果一样面目冰冷。我不知道树是否与人一样也有 五官?如果它没有耳朵,怎么会在风掠过它的枝桠间时制造出美妙绝伦的沙沙声?如果它没有 鼻子 ,又怎么会过滤出如此动人的清香气?我相信树还有舌头,它能品尝朝露细雨。那么树的眼 睛呢?它也一定在树身闪烁,领略着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既然树有眼睛,那么它们也将能看 到3月9日的日全食。当阳光突然把触角从它们身上收回,它们会有顿失温暖的忧伤吗?当太 阳完全被遮住,短暂的黑暗中有一颗彗星精灵般飞来,它们会感动的落泪吗?树如果落泪了 ,大地上空是否就会呈现出流星雨一样的气象?那肯定是一种达到极致而破碎的灿烂。
《亲亲土豆》的故事是近年少见的伤感小说,死神活活要把这对三十来岁的乡村恩爱夫妻 永远分开的描写,具有很强的下向性,即有种使你强烈地想一直看下去的吸引力。能干、爱 种土豆但有噬烟毛病的秦山,终于在咳嗽得受不了的情况下,由妻子陪着去县里省里看病, 诊断、看护、伤心、绝望,所有这些迟子建写得都很细致,再加上对病友王秋萍夫妇的陪衬 性描写,更能引发你的同情心和注意力了。然而迟子建并不满足于此,她还要在此基础上用 她那颗温婉的心,在一种温馨亲切的情调氛围中,去赞美寻常百姓中美好的人性。为此她不 惜在故事开头用了一大段文字写天上与人间的心灵对话:
如果你在银河遥望七月的礼镇,会看到一片盛开着的花朵。那花朵呈穗状,金钟般垂吊着 ,在星月下泛出迷幻的银白色。当你敛声屏气倾听风儿吹拂它的温存之声时,你的灵魂却首 先 闻到了来自大地的一股经久不衰的芳菲之气,一缕凡俗的土豆花的香气。你不由在灿烂的天 庭中落泪了,泪珠敲打着金钟般的花朵,发出错落有致的悦耳的回响,你为自己的前世曾悉 心培育过这种花朵而感到欣慰。
紧接着这段动情文字下面的,是晨曦中两个在土豆地劳作的礼镇人,互相诉说着先人托梦 想吃新土豆的事儿。土豆连接着亲情,连接着生与死。小说的结尾又写到,李爱杰将五袋土 豆倒在秦山的新坟上,阳光下秦山的坟豁然丰满充盈起来,“李爱杰欣慰地看着那座坟,想 着银河灿烂的时分,秦山在那里会一眼认出他家的土豆地吗?他还会闻到那股土豆花的香气 吗?”这天上人间的首尾呼应,这亲亲土豆的故事,审美重心依然是撩拨人心的情调。
[收稿日期]2001-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