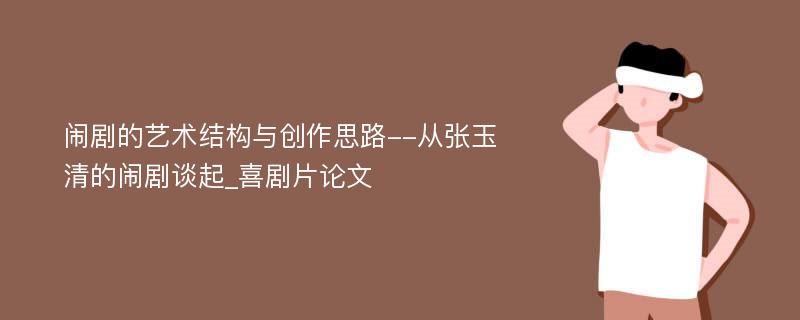
滑稽戏的艺术构造和创作思路问题——从张宇清的滑稽戏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滑稽戏论文,思路论文,艺术论文,张宇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宇清作品研讨会专辑
张宇清剧作的成功之处,诸如体现了时代性,保持了通俗性,坚持剧本的戏剧整体性,提高了滑稽戏的文学性,尤其是注重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肯定。面对这一切,张宇清的态度是,“我不要旧船票!”就是说,他关心的是新的航程。沿这一思路,本文的着眼点是关注张宇清创作实践中存在什么问题,怎样谋求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提高。而这些问题对滑稽戏而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一
滑稽戏的艺术构造可分两个角度考察。一是历时性构造,即作品按时间的推进,一段一段、一部分一部分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这也就是情节结构问题。一是共时态构造,即不是从剧情的推进来考察,而是从空间构成来考察,看滑稽戏的各部分如何组织起来,这实际上是研究一部作品各层面的关系,例如语言层面、情节层面、内涵层面的关系,对滑稽戏而言,这种层面关系最主要的是噱头与文学情节的关系。这方两面的问题对滑稽戏都是十分具体的实践问题。
张宇清的滑稽戏是怎样构造的呢?让我们举张的最新佳作《诸葛亮与小皮匠》为例来分析。该剧情节是:中学教师诸葛文热爱本职工作,他看不起邻居个体户小皮匠有点钱就飞扬跋扈的作风和见利忘义的思想,小皮匠则看不起诸葛的端方态和穷酸相,两家矛盾不断。小皮匠提出雇诸葛教师为他蹬黄鱼车运货,把诸葛气得当场发病。等到小皮匠为了把他的小店调到好市口而来找诸葛通关系,诸葛便躲出去避而不见。诸葛文穷到了老婆逼他卖茶叶蛋,女儿偷偷帮饭馆洗碗的地步,内心痛苦,但清贫自守,尽心教育事业,被评为优秀教师,获一笔奖金。小皮匠做生意被骗,财产赔尽,老婆又遇车祸住院,急难中得诸葛文全力救助,遂敬服诸葛的思想为人,痛悔前非,两家和好。这个故事给我们提供了艺术构造的信息。第一,故事具有文学性、完整性,诸葛与小皮匠的冲突也具有戏剧性,但无紧密的因果链条,没有贯彻始终地强调戏剧紧张感,因为冲突并没有聚焦到一个事件,按一个动作的进展来组织情节。因此,从戏剧的观点看,其情节结构属于较自由、松散一类。第二,这个故事并不滑稽,它之所以成为滑稽戏,是因为加上了噱头。有些噱头是将故事情节滑稽化(如卖茶叶蛋),有些噱头则是笑料的点缀(如诸葛接电话,误抓贾美丽的手当作话筒),但不管怎样,是一个能动的噱头层面和一个自足的文学情节层面构成滑稽戏,因而呈现出文学情节与噱头的两层次结构。张宇清的滑稽戏作品的构成不能说都和《诸葛亮与小皮匠》一样,有的戏戏剧动作组织更严谨些,有些戏的噱头体现为喜剧场面甚至场次,成为文学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在这些部分明确区分出文学情节层面和噱头层面。但总的说,情节结构并不是强调动作的严整性,文学情节与噱头的关系处理是先形成自足的文学情节,再考虑噱头的问题,则是明显的、普遍的现象。因此,情节结构的自由、松散,文学情节与噱头的二层次结构,可以当作一种滑稽戏艺术构成的状态来认识、分析。
这种状态是有普遍意义的,它实际上是滑稽戏由缺少整体性发展到具有完整的文学情节以后发生的构成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说有哪些优点和不足?我们难以判定,因为缺少必要的标准。于是我们失去了线索,我们陷入了窘境。
让我们看看蒋柏连的《滑稽戏结构艺术初探》①一文的探讨。蒋文指出,滑稽戏的结构最初不过是散漫的“噱头大会串”,至《三毛学生意》、《七十二家房客》,发展为场面连缀,尽量顾及整体性的状态;再后,在由成功的喜剧剧目移植改编的《活菩萨》、《拉郎配》、《钱笃笤求雨》、《苏州两公差》等一批作品中,滑稽戏有了贯通全剧的喜剧情节,滑稽特性也大为发挥,但与此同时,也有着在正剧、悲剧作品上点缀、硬贴滑稽噱头的扭曲现象;自《满意不满意》出,滑稽戏张扬自身特点而具整体情节结构的状态重行确立;新时期以来,这种具整体结构的滑稽戏作品已成批涌现,而喜剧情势不充分是致命伤,是质量提高的主要障碍。蒋文清晰地分析、总结了滑稽戏情节结构发展的历程,其“喜剧情势不充分”是当前具整体结构的滑稽戏的“致命伤”的观点十分中肯,并且给人启发。启发之处在于,蒋柏连是从实践的角度提问题的。这首先就避开了在寻找衡量滑稽戏标准时无所适从的困境,不是以话剧为标准指责它松散,不是以曲艺为标准指责它噱头和演员的表演魅力弱化,不是以戏曲为标准指责它缺程式,而是以文学上更完整、戏剧性更强、噱头发挥更淋漓尽致这种实际的追求为标准。其次,喜剧情势这一问题,虽然只是说情节结构,其实既关系历时性构成,也关系共时性的空间构成,因为喜剧情势的加强,必然改善戏剧情节结构的严谨性,也必然使噱头的创造更自然,噱头层面与文学情节层面的结合更贴切。
加强喜剧情势必然有助于滑稽戏质量的提高。然而,问题并没就此解决。我们需要知道:1,滑稽戏在具有完整的文学情节后,情节结构应否追求戏剧动作的严谨化?2,文学情节层面与噱头层面的二层次结构是否必然,能否做到使二者合一?3,提倡加强喜剧情势,那么学喜剧,向喜剧发展是滑稽戏提高的唯一途径吗?
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滑稽戏的本性。
滑稽戏是喜剧中独具特色的一种。而喜剧按其意味的不同而有讽刺喜剧、幽默喜剧(或曰抒情喜剧)和歌颂性喜剧之分。滑稽戏和它们都能沾边,但显然又不属其中之一,因为滑稽戏明显是承古代优人调弄滑稽的传统而来的。这种传统造就了中国古典戏曲的喜剧味,而其形态的直接传承则是中国戏曲中的插科打诨成分。通常以言论老生担纲的文明戏承此传统,发展起文明戏中滑稽表演的行当,滑稽戏就由此脱胎而生。那么,滑稽戏是否可作为与讽刺喜剧、幽默喜剧并列的一种喜剧呢?不能。因为滑稽并不是某一种喜剧意味,而是可以包括讽刺、幽默、诙谐、揶揄种种喜剧意味的,滑稽实为可笑的同义语。假如艺术实践推出以诙谐为主的喜剧,我们可以创出诙谐喜剧的名目,假如幽默喜剧被刻意细分为黑色、灰色、粉色的幽默喜剧,不管是否有此必要,逻辑上仍讲得通。而要说滑稽喜剧,就等于说有一种可笑喜剧,逻辑上是不通的。那么,分明存在的,被我们明显感到的滑稽戏的特点该怎样解说呢?滑稽戏和喜剧的区别是什么呢?
滑稽戏和一般概念所言的喜剧,就其都揭示事物的可笑性说,本质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具体形态的不同。滑稽性和喜剧性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揭露出事物之违反常规的不协调现象,使人发笑。在这一点上,滑稽与喜剧二词是通用的。但在表现形态上,滑稽和喜剧有所不同,滑稽把不协调表面化,例如卓别林的流浪汉造型,是帽子特小,鞋子特大,上衣极紧,裤子极肥,表情一派严肃,动作高度灵活,这种表面的、直观的违反常规,就造成滑稽效果;而喜剧却重视深层意义,要揭示出事物之存在的现象与本质的不协调,事物运动的手段与目的的不协调,让人识别出某些严肃的事物其实无价值,意识到某些有力的运动其实是时代的误会。因此,我们可以说,滑稽是表面化的喜剧,喜剧则是深刻的滑稽。
追求深刻的滑稽意义与把喜剧性诉诸表面化的形态,这二者应该是相联系的,所以喜剧情节通常伴随着机智的语言、夸张甚至变形的表演等等。但这二者不是不可分别发展的。例如马戏团的丑角演员就是不关心深层意义而创造表层滑稽的能手。而有的喜剧作品则可以只重深层喜剧性而不将这种喜剧性表面化,例如契诃夫的《樱桃园》就是不用表面化喜剧手段的一出喜剧。由于造就表面的可笑性与揭示深层的滑稽性可以各自具有独立性,因此二者也可以有各自的历史发展。我们面对着的滑稽戏和一般喜剧的不同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作为戏剧类型的喜剧,是以构成喜剧情势,通过喜剧冲突的进展,通过完整的剧情揭示事物的喜剧性为特征的;而作为一个剧种的滑稽戏,则是以拥有一套发达的表面化喜剧手段,即“噱头”技巧为特征的。
喜剧以喜剧性的戏剧情节为本,对表面化的喜剧手段的运用并无限制。滑稽戏以噱头为本,在全剧的喜剧情节上却一般地并不充分具备。依据这个区别,人们自然地会认为,滑稽戏未入戏剧殿堂,它是一种低级喜剧,所以其发展方向是向喜剧提高。八十年代在上海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并且进行了相应的艺术实践。但这种好心的努力没有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根本点在于,以喜剧为范本的改造与滑稽戏的本性有所不合。这种不合是人们清晰地感觉到的,但又是奇怪的,不易说清的。滑稽戏难道反对过喜剧情节吗?滑稽戏不是有过一批由喜剧移植的剧目大获成功吗?为什么会不合呢?对此,我们应尽力探究,因为正是在这里,滑稽戏的本性最具体地显露出来。
滑稽戏难以接受的,不是喜剧的喜剧性和情节整体性,而是戏剧的严整性和单纯性。戏剧是写冲突的,一切都为此而组织,它要求冲突的动作不断推进,排斥动作的停滞,不允许随处流连。戏剧还讲究始终保持冲突的张力,形成鲜明有力的节奏,这一切构成了严整性。喜剧以这种严整的冲突性动作去揭示某种喜剧性,它的审美姿态是专一的,或讽刺、或幽默、或调侃,全剧是统一的。这就造成了喜剧意味的单纯性。这种严整性和单纯性是滑稽戏不能完全接受的。滑稽戏所持的噱头,虽是表面化的喜剧手段,却不是专为这种严整性、单纯性服务,使之变得鲜明、强烈的外部手段,它经长期的发展,已具有独立的意义。噱头是一种小型的喜剧构造,它存在于戏剧中,不是模糊了,而是更清楚地显示出它造就笑的特点,一是直接性,二是多样性,三是旁观性。一般讲噱头的特点,多讲其描绘生活采取夸张、变形的形式,这固然不错,但这个特点与喜剧是共通的,不能将滑稽戏与一般喜剧区别开来。滑稽噱头不仅是夸张变形的,而且具有直接彰示喜剧性的特征。例如《多情的小和尚》中陈和尚与冷月眉的第一次接近,这二人向来是对头,现在冷由街道安排帮陈搞卫生,一走近陈,陈嗅到香气,看见女人的笑脸,忽然心驰神往,不能自持。按夸张变形的要求,这里只需夸张地表演一向横眉竖目的陈和尚此时如何心旌神摇、举措失态即可,但滑稽戏是不会仅指示观众去领略喜剧性的,它要的是喜剧性的直接展示,当场出彩。所以此一段不是如一般喜剧那样,在陈和尚失态的夸张表演上下功夫,而是在直接揭示喜剧性上下功夫。陈鼻子一嗅,有一点摇晃,冷便问:“做啥,发毛病啦?”陈竟然回答道:“对不起,我陈和尚已经十来年没有闻到女同志头上的香水了,今天给你一熏,啊会有点过敏反应?”于是滑稽立见,笑声骤发。这就是在揭示喜剧性上的直接性。滑稽噱头还具有多样性,就是说,全剧的制造笑料,以至在某一人物身上制造笑料,并不像喜剧那样,遵循某一种审美态度,而是随机生发,随时变换角度,一会讽刺,一会幽默,一会调侃,一会闹剧,与喜剧的单纯性相比,显出审美态度的多样性。而噱头之所以能保持这种直接性和多样性却不失表现生活的真实性,只因为它具有旁观性,即演员的表演既要认同角色,更要鲜明地保持一种超然旁观的地位,而且是以后者为重。这使滑稽戏表现生活采取一种喜剧评论的方式。这是滑稽戏所保持的曲艺特点。观众对此有着默契,因而容许和欣赏以调笑滑稽的态度来表现生活。以旁观的调笑态度多样化地直接地(表面化地)揭示生活现象的喜剧性,这就是滑稽戏的主要乐趣。于是喜剧好像军队,滑稽戏却像游艺场。犹如军队的力量在于步调一致,目标专一一样,喜剧依仗戏剧的严整性和单纯性而在冲突的推进中获取喜剧性。犹如游艺场的活力在于各种节目的丰富多彩和游戏态度一样,滑稽戏依仗噱头多样地对生活作喜剧观照取胜。要以喜剧为目标来改造滑稽戏,只能是尽量吸取喜剧的长处,要根本改造为喜剧,滑稽戏就会失去自身。
以上的思考使我们领悟到,滑稽戏向戏剧化、整体化发展,根本上存在着滑稽和戏的矛盾和统一问题。张宇清作品中艺术构成呈现的噱头层和文学情节层二层次结构的现象,正是这种矛盾和统一的表现。张宇清作品所取得的成就,给我们提供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启示。
第一,必须充分认识噱头的美学意义。张宇清的作品多明显分为两层次,如去除噱头层,则文学情节层情节较平直,内涵相当单薄,不足以成为一个好戏,加上了噱头,则成了一个好戏,这说明噱头有丰富的内涵。如《诸葛亮与小皮匠》中诸葛文的妻子逼他演习卖茶叶蛋的精彩段落;妻子要他用勺子敲三下锅子,然后喊“同学们,快来买诸葛老师的茶叶蛋。”诸葛文第一次敲罢三下,硬是喊不出口;第二次重来,精神紧张,敲了四下,忙说这回不行,多敲了一下;第三回鼓足勇气,三下敲过,张口喊出的却是“平安无事噢!”这一段观众笑三次,一次比一次强烈。第二番笑由自诸葛文迂腐地认为敲三下与敲四下有根本区别,第三番笑由自喊的话岔到了电影台词上而文不对题。但这些造笑手段有着中学教师叫卖喊不出口的心理根据,因而有力地展示了诸葛文的困窘尴尬,使观众领悟到教师要卖茶叶蛋是多么的荒唐,收到了喜剧性强烈、喜中含悲的效果。固然,要每一个噱头都如此内涵丰富是不易的,但正是噱头层所具的内涵与文学情节层共同撑起了滑稽戏的天地。噱头的内容更是滑稽戏的精华。噱头是滑稽戏的根本,它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二,噱头由于是使事物的喜剧性直截地呈现为不合理、乖讹形态的表面化手段,它只能成为剧中的片断、场面,而不能成为全剧的情节。若成为全剧情节,就成为喜剧,而失去了即时引人发笑的直接性。于是,全剧的文学情节和噱头必然形成两层次的关系。在这种两层次关系中,文学情节层面好比一篇文章正文,噱头层面好比评点。只不过这种评点是专门随时直截地对正文作喜剧性观照的评点,它不应象评点一样作为外加的东西存在,而应作为把正文部分滑稽化的形态存在。
第三,噱头具有广泛适应性。正如一篇文章的评点,可以随时变换角度,从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审美的、心理的等等角度发挥各种议论来点评一样,噱头可以随时变换喜剧审美心态,或热讽、或冷嘲、或揶揄、或幽默、或歌颂、或戏谑。于是,正像评点这种武器可以加于一切文章一样,噱头也有着广泛的适应性。没有理由断定噱头只能加之于喜剧。这就是说,噱头与文学情节这两个层面,噱头固然一定是喜剧性的,文学情节却不一定,可以是喜剧,可以是正剧,可以是悲喜剧,甚至也可以是悲剧。
第四,滑稽戏的文学情节不应过于强调冲突的紧张性、动作的整一性、组织的严整性。这是因为要给噱头留下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滑稽戏的审美价值来自其文学情节和噱头两个层面,但更多的来自噱头层面,因为在噱头引起的笑中,观众才更有力地领略文学情节层面不具有的,而因噱头作了喜剧性观照而评点出的意义。因此,文学情节一方面有其自足性,另一方面也是噱头的载体,是笑料起飞的跑道。如果文学情节具有戏剧的高度紧张性和严整性,一刻不停地奔向冲突的解决,就会使作者和观众都无暇他顾,尽管有些冲突的急剧发展也能产生噱头,但噱头的发挥总的说会受到限制。
从以上几点认识来看,张宇清的滑稽戏剧作中文学情节不具有喜剧性,戏剧情节有松散、自由的倾向,文学情节与噱头构成两层次的关系等特征,只有从传统的喜剧的标准来看,才会认为它们是不可容忍的缺点,而从滑稽戏艺术构成的规律来看,这些特征的存在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必然的。这些特征的存在并不一定影响滑稽戏质量的提高。
那么,影响张宇清滑稽戏质量进一步提高的因素是什么呢?回答是:文学情节。
从事理的角度说,当滑稽戏发展到讲求文学性、整体性的阶段后,就形成了噱头依附文学情节而生长的关系,文学情节必然是决定性的因素。尽管张宇清对滑稽戏追求文学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作品的文学情节仍然存在内涵单薄、生发噱头的势能不足的问题。
于是,我们的注意力集注到了如何加强文学情节的问题上。而这是个需要深入展开讨论的问题。
二
加强滑稽戏文学情节创作的关键何在呢?
当面对这个问题时,笔者还是首先想到蒋柏连的看法:喜剧情势不足是致命伤,是滑稽戏质量提高的主要障碍。这的确是个关键性问题。像《苏州两公差》、《钱笃笤求雨》、《拉郎配》、《满意不满意》这些作品,都是具有强烈的喜剧情势的。喜剧情势本身就造就情节的完整性、文学性、戏剧性,也具有强大的生发噱头的势能,因而使这些作品成为高峰性的佳作。它们相当程度上可说是样板。如果现今的滑稽戏创作能解决喜剧情势的问题,无疑质量就会上一个台阶,高水准的作品可以成批出现。然而问题在于怎么做到这一点。首先,喜剧情势这一问题,滑稽戏作者是不可能不注意、不重视的,是什么阻碍着他们在这方面长足发展呢?其次,求喜剧情势和完全学喜剧有何区别,要求喜剧情势和滑稽戏的文学情节不限于喜剧性的之间是否矛盾,能否统一?这些疑问引导我们去注意更多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把视线只盯住喜剧情势这一戏剧技巧问题,视之为全部症结所在。
我们首先得注意文学思路的问题。张宇清的创作是以追求文学性见长的。那么他的文学思路是什么呢?从其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模式:社会问题剧+歌颂性喜剧。这种模式,是从社会问题剧始,以歌颂性喜剧终,即从揭示社会问题着眼,接触生活中的矛盾,构成戏剧冲突,冲突展开后就纳入歌颂性喜剧的轨道,以歌颂某个正面人物的某种先进思想品质来对矛盾作正面解决。例如《多情的小和尚》,一开场似乎是父母反对子女自由恋爱的问题,但其实写的是老年男女寡妇鳏夫的再婚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由子女撮合,即歌颂新时代的年轻人的新思想新风尚解决的。再如《乐在其中》写的是住房紧张的问题,问题是通过歌颂房产科长克己奉公,感动了争房的小青年来解决的。《诸葛亮与小皮匠》揭示的是新形势下分配不公,体脑严重倒挂的问题,而矛盾是通过歌颂人民教师坚持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终得到社会的肯定和群众的理解来解决的。这种模式,不仅见于张宇清的作品,它已成了新时期江苏滑稽戏剧创作的主要文学思路。
对这种文学思路作何评价呢?从滑稽戏文学情节的要求来看,它既要有自足性,又要作噱头起飞的跑道,既要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对生活的见解,又要生发出大量笑料,给观众以笑的满足。兼顾文学性和滑稽性,是滑稽戏文学创作的思维空间。从这两点要求衡量,上述文学思路是一个既两面讨好,又两面不讨好的思路。
这个思路既从社会问题出发,它就能反映生活,反映时代,而且显示出思想的敏感性和尖锐性;但它又以写成歌颂性喜剧为归结,这就又能创造笑料,于是它兼顾了文学性和滑稽性。这就是两面讨好。另外,它还有一个显见的好处,就是它既及时提出问题,把握时代脉博,提出的问题又总是歌颂某种积极、正面的精神而加以解决,政治上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它两面不讨好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问题剧和歌颂性喜剧本性是相冲突的。社会问题剧的宗旨是批判性、揭露性的,它的目标是推出人们未尝注意的和现时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歌颂性喜剧的宗旨却是歌颂性的,它所创造的不谐调、乖讹,目的在于自违反常规的现象中显露出主人公的美好品质并加以赞颂。于是,社会问题剧的意旨贯彻充分些,歌颂性喜剧便应付不了,要写成歌颂性喜剧,提出社会问题便只能浅尝辄止或干脆虚晃一枪。两者的结合必然是此长彼消,相互制约,而不是相得益彰。这种现象在张宇清的创作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多情的小和尚》中陈和尚与冷月眉因做生意吵过架,这和老年人再婚问题并无关系,这两个人也没有老年人婚恋面临的房子问题、子女问题、地位问题,所以一接近就动心,一撮合即成功,在揭示老年人再婚的社会问题上,剧本实甚为空洞,不过以此给小和尚一个显示其热情和机智的机会罢了。《土裁缝和洋小姐》中,龙小林是个富有才华,跟上了世界时装潮流的时装设计师,对生活充满信心,毫无自卑感,所以轻易地便征服了女演员杨丽娟的心。作为老观念的代表,对龙小林管头管脚的爷叔——老裁缝王古板,则自己也正在与一个年老的女演员谈恋爱。所以该剧对关于城里人、乡下人的新旧观念的冲突问题的描写也是虚张声势的,不过给年轻人的恋爱经过设置一个有惊无险的幽默背景而已。《乐在其中》和《诸葛亮与小皮匠》则相反,因社会问题写得深入一些而无法呈现出歌颂性喜剧的面貌。前者真实地写出了缺房问题给工人群众造成的窘困和烦恼,而这个问题不是宣扬某种高贵品质所能解决的,尽管努力制造笑料,结尾用房产科长自己住得最挤最破来感动小青年,显得苍白无力,充满苦涩感。后者较深入地写出了体脑倒挂情况下,人民教师的生活清贫和精神困惑,最终安排诸葛文获奖和小皮匠一家遭到飞来横祸以解决问题,失之生硬和牵强。这种不足的存在,并不表现作者能力的失败,而是表现这种文学思路的窘境。我们从中强烈地体会到作者的苦恼。
显然,这种文学思路既因两面讨好而存活、立足,又因两面不讨好而限制着自身发展的水平。继续遵循这一思路,滑稽戏将只能是文学性上比较浮浅而笑的特征又被弱化了的滑稽戏,将不可能超越现今的创作水平。
那么这种文学思路是哪里来的呢?能不能断然抛弃呢?这种文学思路来自话剧,是可以而且必须抛弃的。“五四”时代,中国引进西方话剧,由于当时社会改造是人们面对全部生活的基本态度,所以独对社会问题剧最感兴趣,社会问题剧因而风行,这种创作思路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这种思路的长期统治,造就了剧作家的这种意识:及时地尖锐地描写社会问题,就是作家反映生活、干预生活之路,是作品的思想性所在,文学性所在。这种意识又反过来成为社会问题剧的创作思路长期保持的支持力量。然而社会问题剧在中国发展的时候也在蜕变。到了三十年代,受国际上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要求创作不能如批判现实主义那样只指出社会的病症而不开药方。要开药方,就意味着作品提出问题还得给予解决。这种方式的作品在解放以后一统了天下。由于提出了问题后总导向一个现成的而且是绝对正确的答案,剧作看来还是社会问题剧,其实已蜕变成了教化剧、宣传剧。而提出问题,再加解决,造成正剧形式,所以这种思路的统治也是造成悲剧、喜剧稀少的原因。滑稽戏创作不过是把这种历史形成的、统治性的创作思路接过来罢了。然而滑稽戏是必须得笑的,所以必须把这种思路喜剧化,而由于这种创作思路是宣扬正面的东西来解决,所以喜剧化便走了歌颂性喜剧之路。于是,社会问题剧与歌颂性喜剧结合的模式出现了,滑稽戏擅长的讽刺传统不知不觉丢掉了。在滑稽戏以这种文学思路(社会问题+歌颂性喜剧)进行创作的同时,话剧创作、戏曲创作却已适应着全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化而变迁了文学思路:由问题剧转向了社会剧。因此,滑稽戏创作抛弃了现有的思路不是一个谋求艺术上的改善问题,而是一个跟上时代步伐的问题。
由问题剧转向社会剧,不是说不再接触和提出社会问题,而是要把创作的注意力从关注社会问题转到关注人本身。问题剧也写人的命运,但它把人的命运当作载体以推出社会问题:社会剧也写社会问题,但它是把社会问题的存在当作背景,在其中探讨人的价值。
从问题剧向社会剧转变是一个深刻的转变。但实行起来并无困难,也无风险。并且滑稽戏实行这种转换更为容易。如果说话剧由此转换而卸脱了本就承担不起的对社会的政治责任,那么通俗的滑稽戏从来也不曾以写重大的政治性问题见长。如果说以往的问题剧虽写问题但总是已包含着探讨人的价值的成分,那么贴近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滑稽戏从来包含着较多的世态人情的成分。滑稽戏由关注社会问题向关注人的价值,不会减弱而会有利于发挥笑的特色。例如《多情的小和尚》如果按探讨老年人追求人生幸福的心态发展的路子写,是可以创造许多有趣的情节的。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是写人情而非写社会问题,作品喜剧化时不必再因要求正面引导而采取歌颂性喜剧的方式,即可以歌颂,也可以采取幽默、调侃、诙谐、讽刺等种种喜剧审美态度。因此,向社会剧的思路转换,对滑稽戏创作来说,无论在追求文学性方面还是在发挥滑稽性方面都是一种解放。
其次,我们还是须谈到喜剧情势问题。滑稽戏必须有喜剧情势,否则不能产生笑。但喜剧情势不一定非得是来自全剧的喜剧冲突结构。全剧的喜剧冲突结构是应当追求的,因为可以造成全剧性的喜剧情势。但在正剧、悲剧情节中,也可以随处造成局部的喜剧情势。关键在于喜剧意识,只要作者、演员有喜剧意识,随处可以创造出喜剧情势来。
在创造喜剧情势时,有个加强戏剧意识问题,又有个开阔思路问题。
张宇清的《难得糊涂》写科技发明家被安排干厂长这一行政工作的苦恼,作者写厂长徐小卫让其孪生哥哥徐大卫冒充厂长,自己偷跑几天去干科研,这十分高明,这是把生活戏剧化和喜剧化了,已经创造出了全剧性的喜剧情势。如果紧扣主题,正常发展戏剧冲突,可以发展出徐大卫这个假厂长胡乱应付,也处理了看似复杂实则一般的事务(真作假时假亦真)的一场,以及徐小卫去上级领导那里解释,却被当作假厂长徐大卫扣留追究(假作真时真亦假)一场。但作者由徐大卫代弟弟会女朋友的情节后,就完全陷入徐大卫的妻子、徐小卫的女友追究她们的丈夫、男友的情节去了,既偏离主题,也偏离了戏剧冲突情势的正常发展。这种偏离,无疑反映出加强戏剧意识的必要性。
所谓开阔思路,指创造喜剧情势应更放开手脚,更多样,更恣肆。英国式的幽默,法国式的机智诙谐都要吸纳,制造荒诞效果也应引入和大力发展,夸张变形则力度可以更大。其实这本来就是正宗传统。滑稽戏是承优人谈笑讥讽、戏曲插科打诨的美学传统而来的。在《窦娥冤》这样的悲剧中,我们看见昏官桃杌太守对来告状的大磕其头,旁人怪之,他解释道:“凡来告状的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在元杂剧《看钱奴》中,我们看见吝啬鬼临终嘱咐儿子待他死后应把他剁成两截装进喂马槽,以节省买棺材的费用,还交代一定借邻家的斧子,因为他的骨头硬,若用自家斧子剁缺了口,修修又得费好几文。传统尚且如此,今天造噱头时难道不能更放开手脚一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