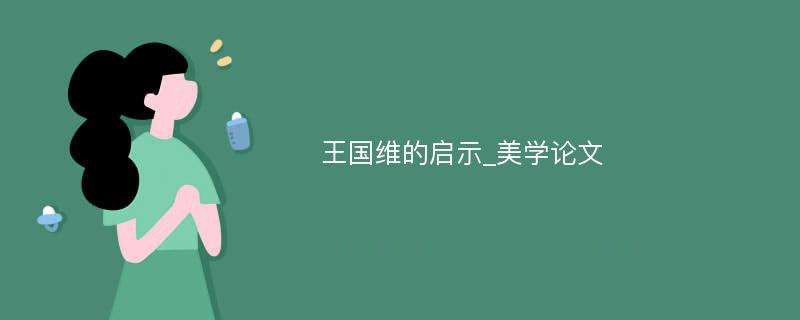
王国维美学启示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录论文,美学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在美学研究中,以文的自觉、人的觉醒和论的独立,推动了中国传统的“潜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型。当然,王氏美学的逻辑建构本身也带有转型期所难免的新旧互渗之特征。
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们的对王国维美学的比较研究却有着“平板化”的倾向,也鲜见对王氏美学的整体研究。其实,从文化术史的角度研究王国维的治学道路,对于人文学者在当代寻求自身的价值定位,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说王国维是中国唯一活到了20世纪的近代美学家?
以“境界说”为顶点的王国维人本—艺术美学与叔本华的思想血缘,可以说,既是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的第一命题,也是中国现代美学赖以发生的首要课题。下面,我想从学术史角度谈些看法。
第一,文的自觉。将文学作为纯语言艺术,并进而将艺术作为独立于政教人伦的审美性精神创造——若就其行为自觉而言,大约在魏晋便已发端;但就其理论自觉而言,即从人类精神活动方式之高度来界定艺术的非功利性,则此功非王国维莫属。从此,被“文以载道”压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坛,总算开了天窗,可以探出头去,吸一口新鲜空气了。王氏“无用说”关于艺术本性之雄辩及其“古雅说”对艺术程式的精细品味与珍爱心态,不仅为中国美学之首创,同时也使有所更新的中国美学找到了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共识,从而使中国美学成了与现代世界美学思潮遥相呼应的东方支流,而不再憋在古长城内墨守成规了。假如日后有人叙述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历史转折,那么,我要说,该转折的第一源头即在王氏,因为即使被视为惊世骇俗的新时期文论探索,就其基本观念而论,有些也可追溯到王氏,可见其理论的生命力或现代感之强。
第二,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实为“文的自觉”赖以发生的内在动因,这就是说,支撑“文的自觉”的理论支柱,恰恰是王氏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珍视与激扬,于是,人不再是被封建模具浇铸而只存天理却无个性的宗法零件,而出落为有血性、有灵气、不倦探询人生真髓的主体。大陆学界往往将近代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这没错,但却很少有人以比较的眼光,发现王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即人本主义沉思,或许比重在文化—政治批判的“五四”前驱,有更纯粹,更深挚,也更丰富的人学意蕴。可贵的是,王氏还将此思考贯穿于“天才说”和“境界说”,将作者有否深挚的生命感悟作为衡量艺术的文化品位的美学标尺,这就不仅将诱发艺术家的精神超越,同时也使公众通过接受高品位艺术,而使自己对人生愈益严肃或执着。
第三,论的独立。这不仅体现在,王氏美学已彻底摆脱了封建政教意识形态,而变成真正研究艺术的本性、规律、理想及其艺术化的人类生存意义——这么一门入文科学;更重要的是,与历代文论、诗论、画论相比,王氏美学在思维方面已获得传统美学所不曾有的理论形态。理论与思想,就其思维水平而论,确实不在同一层次;某一观念纵然表达得不系统,不严密,甚至失之散漫,零碎,但只要言之有物,发人深省,乃不失为“有思想”;但理论却非立论明确,论证严谨,条理缕析,自圆其说不可。思想可以仰赖灵感或直觉,只要有创意就行;理论却要靠逻辑来汇集、筛选与组织思想,去芜存菁,化零为整,以难以辩驳的明澈与浑然一体的凝重去打动人。因此,也可说思想是原料,理论才是成品。记得学界曾有人称中国传统美学为“潜美学”,而非真正理论意义上的“美学”,并非无理;或许,王氏的功绩之一,正在于他推动了中国“潜美学”向“美学”之转型。事实上,王氏美学的逻辑建构本身便带有转型期所难免的新旧互渗之特征。
先看方法基础。方法是任何理论建构的思辨法则或灵魂,它不仅预先规定了理论研究的对象范围,同时也是编织理论网络的操作性经纬。传统美学建构似很少讲究统辖全局,一以贯之的方法,故往往使真知灼见如断线珍珠,乍看局部不乏精妙,再看全体则未免堆砌,不见有机结构。不错,王氏生前未写过系统的美学专著,他那“天才说”、“无用说”、“古雅说”、“境界说”所构成的人本—艺术美学,也是靠后人才整合的;但这一整合所以成立,又恰巧证明王氏“四说”之间确有某种隐性结构,整合之成功不过是这隐性结构的外化或实现而已。这就像拼缝成衣所以顺利,无非是因为原先衣料裁片业已齐全,只差最后一道工序了。显然,王氏美学的隐性结构源自其方法,这方法便是叔氏“对人生苦痛的审美超越”。它像同一基因将王氏“四说”孕育孪生兄弟,虽风貌有别,却血缘归一;但毕竟还未将“四说”连为一体,即方法对美学结构之统辖尚未完全到位。从传统美学的无结构,经王氏美学的隐性结构到现代美学之结构,可见王氏在方法意识及其应用方面确是新旧参半,既继往又开来的。
再看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是理论系统的母题,系统内的所有定律或子概念,可以说都是从核心概念中推导出来的,故也可说,方法对结构的统辖最终是靠核心概念的内涵界定与外延展开才充分实现的。传统美学遗产可谓丰饶,却很少有环绕核心概念而有机展示的,有时也不是没有好见解,新观点,如“风骨”、“性灵”等,但几乎没有人能对类似术语作严格定义与演绎,往往满足于点到即止,结果便使好多不无灵气的观点由于得不到逻辑支撑,而最终萎缩为一个有意味的词。这是理论上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正是在这一点,王氏美学似明显地高于先贤,因为其非功利性“审美”作为核心概念,确像经络布遍了美学“四说”;假如说“天才”是“审美”力的艺术主体化身,“无用”是“审美”—艺术的本体特征,“古雅”是对艺术程式美的简称,那么,“境界”则是对高品位审美文化的诗性期待。这就是说,“对人生苦痛的审美超越”这一方法主线,正是靠非功利“审美”这一核心核念,才使王氏“四说”有可能趋向事实上的理论整合的。当然,王氏“审美”概念所以如此成熟,离不开叔氏的熏陶,因为说到底,“审美”概念毕竟是王氏从叔氏处拿来的,并非再创的。
《人间词话》中的“境界”概念倒是王氏的再创,也正因为是再创,故不免生糙,欠圆润丰满,譬如不仅不见对“境界”的确切定义,即使对“境界”的外延类别划分也大体流于纲目式的罗列与对照,而未作较细深的系统比较。维特根斯坦曾说,创造一个科学概念是艰苦的劳动,又说概念提炼不能拔苗助长。是的,王氏是诚实的,他在铸造“境界”这一核心概念时没有硬来,但也确乎证明“境界”概念其实还是胎儿,还未到分娩期,它却哇哇坠地,早产了。不错,比起沧浪“兴趣”、阮亭“神韵”,王氏用“境界”来指称诗词的高文化品位,无疑棋高一着;但若与王氏对“审美”概念之演绎相比,则“境界”还缺少一种行云流水、间无阻隔的气势即逻辑动力感。
所以,再从演绎系统来看,则《人间词话》确实离真正的理论整体尚有差距,这不仅因为其核心概念“境界”之内涵未见明晰亮相,更是因为从母概念到子概念(如从“境界”→“高格”→“气象”→“词品”)未见线性运演,似无迹可循,犹如散落湖泊的星状孤岛,岛与岛之间没有桥,只能让思维在其间作模糊性跳跃,于是整编《词话》也就称不上是整体,而更像是诗学断想与印象评点之联缀;我不否认若干条目间尚有有机感,但总体上仍处于半系统思维水准则无疑。所以;当王氏将《人间词话》题为“词话”而非“词学”,看来也不尽出自谦虚或沿袭俗成,而实在是与其思维形态相契也。
诚然,事物是需要比较的。当我对王氏《人间词话》评头品足时,我并未忘记若将它与中国第一部《六一词话》或近人梁启超《饮冰室札记》摆在一起,则王氏的现代思辨感又相形而见显著了。是的,不论王氏《人间词话》或王氏美学有何疵点,它终究比任何先贤更靠近现代美学。所以称王氏是中国唯一一位活到了20世纪的近代美学家,并不过分。这一“活”字当然不是指他的生理存在,而是指他对本世纪中国现代美学与中西美学关系走向的深远影响。这一世纪性影响或许到下一世纪将更强烈地显现。总之,王氏美学既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长子,又是中西美学关系的第一混血儿,它在草创世纪性学术奇观的同时也留下了累累斧痕。这与其说是开拓者无暇弥补的空白,毋宁说是历史特意空出的一段诱人回味的飞白,假如前驱将一切皆臻于完美,那么,还要我们这群子孙干什么呢?
怎样避免王国维美学比较研究的平板化倾向?
比较美学可能在如下方面被平板化:一、在方法论层面,不是将比较理解为一种对不同时空的思想传承何以发生之追究,也不是要探寻超越不同文化框架的艺术本性,相反,而是将比较日常词语化,望文生义地将它浅化为某种对若干形似对象的经济性罗列;这就势必导致二、在操作论层面,仅仅满足于对详尽资料作分门别类对照,而不是捅破单一平面作纵深掘进,细察某门类的内在关系及各门类间的有机关联,以达到对对象的整体逻辑还原。
平板化研究尚处在比较美学的“初级阶段”。所谓“初级阶段”也有两方面:一是对仓促引进的比较方法毕竟刚打交道,有个逐步熟识过程,从“外行凑热闹”姗姗走向“内行懂门道”;二是就操作程序而言,任何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起码有三部曲,从详尽占有资料→分门别类→某门类的内在关系及找出各门类间的互相联系,这落实到影响性比较一案,则就得着力揭示蕴结在显性形似背后的隐性神交,即活在彼此身上的那种必然亲和性。这才是学术思维的“高级阶段”。显然,平板化研究还够不上这台阶。
这就清楚了,对王氏与叔氏关系作影响性比较,若想避免平板化,关键全看你能否潜到发生学水平去展示两者势必作超时空传承之底蕴,这就不仅要求你说明两者的相似处,而且亟需你证明他俩何以心心相印,即究竟在哪一关节点上,两颗巨魂撞出了深深的共鸣。由此,你的比较研究也就逸出了路人皆知的经验平面,而获得另一描述两者的可逆互动关系的立体模式:“比较美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化学”。其中“比较美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化学”这一顺向程序,是标记研究者对两者关系的逐级沉思,因为,你首先是在美学层面发现王氏身上有叔氏影子的,而影子又直接源自叔氏哲学,但王氏对叔氏哲学并未全盘师承,这又取决于王氏对人的价值期待同叔氏不尽一致;相反,“比较美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化学”这一逆向程序,则是标记研究对象的发生本相,因为陷于灵魂之苦的王氏渴望人生探询,才使他钟情叔氏哲学,但由于其定势更倾向于对人的肯定,故又促成他对叔氏的人本主义解读或扬弃。也因此,看表面,王氏美学的思辨基点是从叔氏处拿来的,但由于拿来作为某种价值筛选过程,故也就成了方法重铸过程,这更使王氏有可能再创出既有中国气质,又有欧化光彩,风格独特的人本—艺术美学。
我发现,上述发生学模式虽是影响性比较的派生物,但其应用范围又不是影响性比较能限定的,事实上,它在驰骋影响性比较圈的同时,也涉及平行性比较。当然,你也可说,这是在影响性比较这棵大树上长出来的平行性比较,如对王氏与叔氏在美学、哲学、文化学方面的异同之分析,皆是在王氏为何接受且如何接受叔氏这一大前提下进行的。但这一个案,至少为影响性比较与平行性比较的可能合作提供了某种前景,而无需像以前那样,为了标榜各自对比较文学的合法继承权暨阐释权,而弄得老死不相往来。
多层面复合结构的发生学模式作为比较美学方法之一,较之平板化的经济性形态对照,无疑要复杂些,因为它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挺复杂。对象与方法的这一对关系,酷似音乐与高保真音响之关系,现代音响器材及其组合所以愈搞愈精致愈繁复,无非想更大限度地迫近原音之美,于是驱使一代代“发烧友”为配制理想音响效果而不惜一掷千金。我想,比较美学界在努力建构且完善研究方法方面,也应具备“发烧友”式的学术热情。
中国大陆学界为何鲜见王国维美学整体研究?
通观20世纪王国维美学研究史,有个问题:王学整体研究为何到80年代才在中国大陆学界初成气候?而在此前的半个世纪(即从20年代到70年代),学界却大多热衷其《人间词话》,对其前期著述(姑且从叶氏说)则较少关注,能打通王氏的前后期而作整体探讨如叶嘉莹者,诚属凤毛麟角。
对此,叶氏的解释是:资料不全。确实,较之学界对《人间词话》的搜辑之勤,版本之多《静庵文集》及其《续编》所载之前期著述却被湮于烟海,难见流传。照理说,前期著述“所表现的敢于突破旧传统勇于接受新观念的过人识见,在当时原当受到晚清思想界及文学界的普遍重视”,然而竟未能如此,何故?叶氏以为原因有三:A.《文集》、《续编》问世于1905-1907年间,时值革命激变前夜,激进者纷纷从政而无暇旁顾美学,保守派则忌叔、民“贱仁义,薄谦虚”而避之,致使流传不广;B.辛亥年后,时代转新,王国维反而倒退,1923年自编《观堂集林》时对前期著述竟一字不录,遂使吴文祺有“绝版”之叹;C.王国维死后,其门人亲友虽将前期著述编入《遗书》(1936年),但那时中国文坛已陷入非学术纷争,当无人留意王国维的美学之绝唱了。
如上注疏诚然不错,但我总觉得似还漏了什么,即前期著述所以暂未传世,除了王著——最初遗世独立,继而幡然悔悟,末了运离时尚——这三部曲外,是否还应补上一条:即深受传统浸染的中国大陆学界(特别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界),当它面对王氏的前后期著述时,其定势恐怕将使它倾向后者,而非前者吧。故从20年代俞平伯到80年代初刘恒、滕咸惠、靳德峻……对《人间词话》或重印,或修订,或校注,或笺证,乐此不疲,其间虽曾被“文革”中断,但噩梦过后,接踵继弦,可见其情切切。但对王国维的前期著述,则一直到1987年才由周锡山编校结集,重见天日。“爱有差等”矣。
这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一本书、一种学说的传播程度,表面看来是取决于媒体,但媒体是受制于人,受制于人所信奉的学术背景的(暂将非学术因素撇开),故,王氏前后期著述在大陆传播系统的境遇反差,恰如镜子折射出学界的阈限:即学界似历来将王氏美学视为近乎国粹的区域性学术现象,而不是自觉呼应世界潮流,经中西融汇向现代人文转型的精神再创;也因此,它可三世同堂地竞相咀嚼《人间词话》的世袭书香而漠视其更可贵的价值醒悟,至于对欧化痕迹明显的前期著述则就更加隔膜乃至不惜怠慢了。
耐人寻味的是,叶氏作为留洋多年的华裔学者,其笔下之厚此薄彼也俯拾皆是。譬如她将王氏圈入中国文学批评史范围,乍看是重在评估王氏与传统诗学之关系,但究其实质,则是叶氏从未自觉而强烈地感受到王氏的现代意味,于是也就势必将他尊为晚清为终端的、中间古典诗学及其批评性演绎之历史的最后一位大师,而未看到他同时还是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的开山祖兼中国现代美学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也因此,她对王氏的批评性文字之兴趣远胜过对其原理之兴趣,这从叶著的篇幅分配即可见出:其下编《王国维的文学批评》计190页,用于《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分析各为30页、130页,合计约10万字,但对前期原理之评述只占26页,仅1万7千字,可见亲疏之别。
叶氏对王氏美学中的传统成分之偏重,取决于她的学识格局。叶氏承认她所以研究王氏,首先是为了圆其少女梦。因为她天性纤敏,在北平上初中读《人间词话》便曾有“一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直觉的感动”,①这当属传统化的诗性感受;后为人妻,为人母,历尽沧桑,对王氏之“古雅、凝静”,“在含蓄收敛之中隐含有深挚激切之情,和一种虽在静敛中也仍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采”②便愈发敬崇。但同时,她对原理性“批评的批评”并无好感,仅仅是不愿割爱机遇,才“勉为其难”地走上诗学研究之路,③谁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这又表明她对王学整体研究之学术准备是不充分的。这就是说,王氏无愧为国学大匠,但其包含批评论在内的整个人本—艺术美学,又断不是靠国学二字所能涵盖,所能消化的;若没有近代西方哲学的素养,缺少现代世界文化演化之眼光以及中西美学关系之知识,单凭国学积累,哪怕再渊博,再正宗,也会在王氏美学前捉襟见肘的。因为说到底,王氏美学并不是“土生子”,而是“混血儿”,故王学整体研究绝非中国文学批评史界之专利;相反,若无影响性比较美学作先导,则任何探险都将走不远。
王国维美学研究史晚近以来为何成了一部误读兼误判的历史?
从纯学理角度看,我敢说,大陆建国后的王国维美学研究史,基本上是一部误读兼误判的历史。当然,这里有名实之分。假如说,在80年代前,王氏作为中间现代美学的奠基者兼饮誉世界的学术巨子,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与崇敬,反遭清算——这是名份问题;那么,80年代后,学界虽公认王氏是本世纪初对中国学术贡献最大者,但就王氏美学及其与叔氏关系的实际研究而言,则又可说是忧喜参半的。喜,是指王学界自“新时期”以来成果委实不少;忧,则是着眼于现有成果之质量,离巨子应得到的公正而科学的历史评价相距甚远。大凡天才皆难免这一宿命。
对此,叔氏是深有体会的。他说:“一个精神上真正伟大的人物,他的完美的杰作对于整个人类每每有着深入而直指人心的作用;这作用如此广远,以致无法计算它那启迪人心的影响能够及于此后的多少世纪和多少遥远的国家”。但或许天才太伟大了,故他又“好像一棵棕树一样”,“高高地矗立在它生根的土地上面”;而且,由于这一距离不会很快消失,即“人类的接受能力远赶不上天才的授予能力,所以不能立刻成为人类的则产”;这就亟待天才能沉得住气,“必须先经历无数次被人曲解和误用的曲折途径,必须战胜自己附和陈旧的谬论而与之合流的试探而在斗争中生活,直到有了一个新的、不受拘束的世代为这[新]的认识成长起来”,天才才能最终赢得世界的认同与敬重。④
不过,与叔氏的生前厄运相比,王氏的身后命运或许更糟。不妨让数字来说明问题。叔氏1818年完成名著,至1848年后声誉雀起,其间被埋没了30年;但王氏与叔氏的那段美学姻缘,虽始于1902年,止于1912年,然而直到90年代的今天,大陆学者仍未见有一本对上述美学关系进行系统影响比较的专著问世,其间竟长达80年!这与其说王氏美学太超前,毋宁说大陆学界太滞后了。
我所以说学界在建国后落伍了,是因为发现有两位前辈早在50年代前便对王氏—叔氏关系颇具卓识了。他们是胡征铸与缪钺。胡氏大概是中国大陆最早敏感王氏诗学的人本意蕴的学者之一,因为他在30年代末便清晰辨出《人间词话》“其立论多从哲学立场,而不从历史立场”,所谓“哲学立场”,即人本忧思也,“受叔本华影响处最多”也;⑤也因此,他深感《人间词话》中“若‘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诸条,最是发人深省。至其谓后主词以血书,此之于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则信为重光千古知己。词客有灵,定雀跃于地下也”。⑥惜作者执笔时身逢“丧乱中无叔氏书在手,不能一一列举也”,⑦否则,定能从文献学角度写成中国第一篇王氏诗学的影响比较论文。缪钺在大陆王学史上的地位更不容小觑,因为他在四十年AI写作的《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堪称中国第一篇从发生学角度揭示王氏为何接受叔氏的心理动因的影响比较专论。他指出:“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唯未能如叔氏所言之精邃详密,乃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其了解而欣赏之,远较读他家哲学书为易,……”⑧可以说,若无皓首究极王氏,叔氏原著精髓之功力,与潜心洞烛巨魂睿智,想必谁也道不出这番穿透力极强之高论。三十年后,海外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论及王氏性格,亦可见缪氏之遗响。这就是说,中国大陆学界早在50年代前对王氏—叔氏关系便有关注,并且,无论从文献学,还是发生学角度来说,皆有可观的起点,只是未打影响比较旗号罢了。但遗憾的是,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大陆对王氏美学的影响比较,于名实两方面皆奄奄一息了。
中国大陆王学史所出现的这一学术断裂,就人格中介而言,当与50年代前后两代学人风范迥异有关。这就是说,与胡氏、缪氏等前辈相比,建国后崭露头角的吴奔星、李泽厚们,似乎多了点什么,也不了点什么。本来么,学人应以清寂为怀,唯崇理性之尊与对象之真,不以政教成见杂之,从这一意义来说,吴氏、李氏为隐性政治语系所蔽,遂成误判王氏美学之心理障碍,确实是多了点前辈所不曾有的累赘。但同时,前辈所具备的,也是人文学者所应有的,不为时势所扰的清峻理智,对生命存在的深挚体悟,与对精神现象(包括艺术在内)的纤敏感知,却未见后者传承。记得李氏曾把50年代长大的“解放的一代”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五代”,说他们“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但长期处于从内心到外在的压抑环境下”,故“作为不大”。⑨不能不说其中含有李氏的自我反省成分。因为从当时李氏对王氏美学的误判来看,其学术人格委实被隐性政治语系单向度化了。
由此,不禁想起顾颉刚《古史辨》中的一个精彩思想,他说:“若将伪史置于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是绝对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只要把伪史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则“伪史的出现即真史的反映”。同理,若从纯学理角度看,50-60年代大陆对王氏美学之误判当无大价值,但换一视角呢,若从当代学术文化史角度来考察,则我发现,上述误判又确实是将当时学界的心理障碍与学术贫困文献化即“史料”化了,舍此将无以考证历史的真实。
王国维是超前演绎现代学人的价值跌宕的镜子吗?
掩卷默想,脑海上浮出一串硕大的问号:王氏究竟为本世纪中国学界留下了什么?仅仅是学术吗?还是他那用毕生来支付的价值探寻及其跌宕?或许,后一笔遗产比前者更沉重,更具文化神韵,故在你眼中,王氏又成了可能藏匿大陆人文学者的命运密码之预言和镜子?
是的,说王氏是超前演绎现代学人的价值困境之预言,并不过分。因为不论从胡适到瞿秋白,还是从冯友兰到何其芳,这些知识精英似皆未能找到十分恰当的价值定位。他们老在读书与做官,治学与宣传之间痛苦地迂回而迂回的结果又往往归一,即皆不像青年王氏那样执着于个性本位与学理纯正,倒皆像晚年王氏自觉不自觉地让时势牵着鼻子走,也不问自己是否真有从政才干。用瞿秋白的话说,这是“犬耕”;用我的话说,则是价值自虐。
价值自虐在观念上有如下特点:即惯于让“忧世”压倒“忧生”,让“经世致用“压例”无用之用”,让政治本位压例个性本位。价值自虐在行为上则形态有二:个体自虐与群体自虐。所谓个体自虐,是指学人硬让自己干他本不愿干,或日后思想虽通,却仍不宜干,也干不好的事(如何其芳,本是诗人,独钟艺术美,却让自己扮演“批判家”,晚年有所悔,欲重操尘封多年之锦瑟,无奈老矣,没时间了,只得遗恨于九泉)。所谓群体自虐,则是指学人阶层的“窝里斗”或自相攻讦,不仅自己不务正业,也不准他人务正业,近半个世纪来,几乎所有政治运动无一不拿学人开刀,但“操刀者”却又无一不是耍笔杆的秀才。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揪你,扭作一团,斗得昏天黑地。时过境迁,双方固然可捂着各自伤痕一笑泯恩怨,但彼此的韶华却俱付东流,只留下苍白的虚空。只有那真正耐得住寂寞,将生命托付给遗世静思者,才可能拥有心灵的充实与欣慰(如钱钟书,“抗战八年”他写《谈艺录》,“文革十年”又从二十四史啃出数卷《管锥篇》,构筑起周览通观人类文化的中国学术故宫)。
其实,人文学者在当代的价值定位,关键是要实事求是——既不像青年王氏纵情放大人文学科学之功能,仿佛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然此“书”非指儒教经学,而是指王氏曾酷爱的文哲之学);也不像晚年王氏羞于染指非功利之文哲,似乎既无“经世致用”,也就一钱不值,乃至自暴自弃。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什么都是”跌到“啥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假如真的将王氏的人生曲折作殷鉴,当代学人是可能认清自己本是什么,应干什么,即找到自己如何生存,及其为何如此生存之意义或理由的。
首先,文哲之学既是人文学者赖以谋生之职业,更是其事业或生命的第一需求。他们可以设想失去健康、爱情、地位与金钱,但不能设想失去他们曾为之呕心沥血之文哲。这是他们的人生寄托。尽管名利聒噪之世已很难安置平静之书桌,但一旦真的伏案笔耕,他们乃会因内心充实而弥散蔚蓝的安宁。文哲已内化为他们的脉搏、呼吸即生存方式。他们似乎只有这么活,才活得舒心,进而怨时间过得飞快,但又快得问心无愧。除此之外,他们几乎尚未想过世间竟还有其他活法,若有,想必也是属于人家,而不是属于自己的,这就像世上的路有千万条,但真正适合自己走的,大概只有一条。这是选择,也是权力。他们有权将自己的生命灌进文哲这一瓶子里,而不忌这是否给他们捎来清贫。因为与生存意义相比,钱袋是否鼓囊,毕竟是低一档次的。诚然,若联想到只要地求上还有人,只要人类中还有严肃者在探询生存意义,那么,人文学者所苦恋,所繁衍的文哲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价值的,虽不宁说前者是后者的灵魂工程匠,但若能为人类生存智慧宝库增添一份色泽或参照,这也足以证明学人对文哲的情恋未必纯属私人性质,同时也有益于人类。
其次,文哲之学既然可以作为学人的生存方式而存在,则,该学问的魅力也就可能通过如下两种形态来呈示:学理与人格。或许,借助坚贞人格形态来演绎的活的文哲,要比单纯的思辨推导更具高贵、灵动之气质。有人担忧,学者若唯求真理是非而不旁骛时势,是否将导致学者人格萎缩?但历史却提供了另一信息:当有的学者愿为其创新独白承受铁窗时,又有几个政治家敢为国为民“披逆鳞”并始终不媚不昧,不渝不悔呢?
进而,学者既然可通过其人格形态来辐射其文哲,那么,有出息、有抱负的学人应有如此自信,即他们不仅以文哲为生,同时他们也是文哲赖以发展的活力或能源,他们本身就是文化载体,文哲的未来是在他们身上。故,他们须有两种时空观念;现世与来世——而不屑将自己变成现炒现卖的时鲜,或能源,他们本身就是文化载体,文哲的未来是在他们身上。故,他们须有两种时空观念;现世与来世——而不屑将自己变成现炒现卖的时鲜,急吼吼地兜售。当然,我不是说文哲不必研究潮流,我是说学人写什么,怎么写,不应先迁就市场,而应先考察自己有否强烈的创作冲动,及其能否写好。好文章未必定有同时态轰动效应,而轰动一时的也未必定是好文章。若叔氏当时只为时势而撰,则其文也就不可能在另一时空感动青年王氏。同理,若青年王氏当时也盲从“经世致用”,则中西美学关系暨中国现代美学之发生在本世纪初就将出现空白。尽管当初王氏在建构人本—艺术美学时,其原动力还是出于自己喜欢,或情有所系。这叫“有意练功,无意成功”。若后世多能领悟于斯,则我敢说,王氏没有白死,因为他不仅活在中国学术史中,更活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意蕴幽邃的价值反省中。
注释:
①②③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3,472,477页。
④[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565-566页。
⑤⑥⑦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其评论汇编》第90,96,99页。
⑧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思想与时代》1946年第26期。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