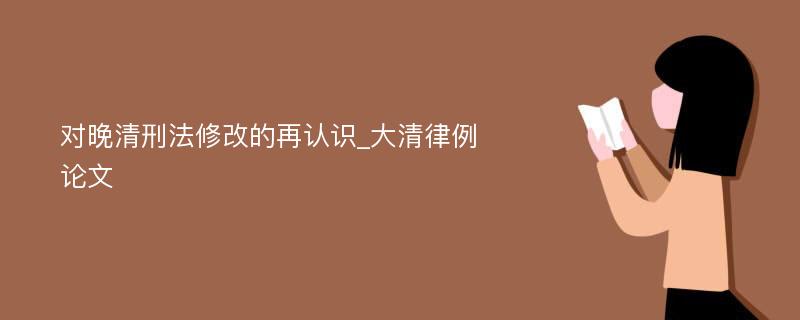
清末修刑律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刑律论文,清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传统的学术观念出发,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是以刑法为基础,而西方法律则是以民法为基础。这正是传统说法的所谓中华法系与西方罗马法系的重要区别所在(普遍认为罗马法系是以民法为基础)。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在19世纪,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早有十分精辟的论述:
古代社会的刑法不是“犯罪”法,这(宏按:原文如此,恐当作“而”字)是“不法行为”法,或用英国的术语,就是“侵权行为”法。被害人用一个普通民事诉讼对不法行为人提起诉讼,如果他胜诉,就可以取得金钱形式的损害补偿。
如果一种侵权行为或不法行为的标准是:被认为受到损害的是被损害的个人而不是“国家”,则可断言,在法律学的幼年时代,公民赖以保护使不受强暴或欺诈的,不是“犯罪法”,而是“侵权行为法”。(注:[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08—209页。)
所谓“侵权行为”是指因作为或不作为而不法侵害他人财产或人身权利的行为,法律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是采用民事手段,即经济赔偿的方式,让致害人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借以保护受害人,制裁致害人。梅因所说的是世界普遍的现象,在中国也不例外。如据历史传说在夏代就出现了“金作赎刑”,即用财产或金钱赎罪以代刑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蔡枢衡先生,他认为:
三皇时代只有扑柣和放逐,没有死刑和肉刑。《路史·前纪》卷八,祝诵氏:“刑罚未施而民化”;《路史·后纪》卷五,神农氏:“刑罚不施于人而俗善。”《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政,疑为罚之误),都是这一实际的反映。桓谭《新论》:“无刑罚谓之皇。”可见没有刑罚,正是三皇所以被称为皇的缘故。(注: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蔡先生还认为:“原始社会的制裁是教导,而不是惩罚。”对于人身及财产损害的补偿,大多是以“赎”的方式来赔付。夏有赎刑已有定论,但大多被后世学者曲解为“罪疑惟赎”。实际上是古人以类似“侵权行为”的方式来对待“犯罪行为”,这可从后世少数民族的史料来解析。如唐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其法:劫盗者二倍还赃,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头,乃得赎死,以纳死家。”(注:《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牂牁传》。)金之始祖定约:“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女真之俗,杀人偿马牛三十自此始。”(注:《金史》卷一,《世纪》。)这可以看出,在各民族早期的历史中,对本部族成员的保护,正如梅因所说,不是以“犯罪法”,而是“侵权行为法”。法律对致害人的制裁大多是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借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罗马法将这种侵害行为定性为“私犯”,是因为其认定受侵害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公权。
但中国较早地将侵权行为的损害对象确定为是“国家”而不是个人,认为任何侵害他人的行为都使国家秩序受到侵犯,较早地使用刑罚手段来打击各种损害国家及个人的犯罪行为,是以“犯罪法”来治理国家、社会及个人,故其刑事立法亦较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西方的刑事立法用梅因的话来说,“真正的犯罪法要到纪元前149年才开始产生。”(注:[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17页。)这一年是古罗马根据“坎布尔尼法”设立刑事审判委员会,开始进行刑事审判,是为西方刑事立法的开始,根据此法所定的罪名为“索贿罪”。(注:参见[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8页。)中国当时是西汉景帝时期,距离文帝的刑制改革已晚18年(公元前167年文帝废除肉刑)。这样看,所谓罗马法是以民法为基础,只是说明其一直在以“侵权行为法”作为解决刑事犯罪的手段,而中国则早已使用刑法手段处理“民事侵权”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刑事法律一直非常发达,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律文明,在近代以前始终名列世界之前茅。
二
西方国家进入近代史时期始于公元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四年后,中国的明王朝即灭亡,清朝建立。清政府刚一建立,就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修订《大清律》,并在第二年“命颁行中外”,是为《大清律集解附例》。这是清王朝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刑法典。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对清律进行了较大的修订,采取律、例合编的体例,更名为《大清律例》,此律的法律效力一直保持到清朝末年,引入“西法”,修订“新刑律”后才废止。在清前期,《大清律例》在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范围,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如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曾这样评价中国法律:“关于中国,只要听到这种法律,我不得不主张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注:原引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影响》,转引自王涛:《中国近代法律的变迁》,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 28页。王涛在同书同页中还引用了巴尔夫著《一个哲学家的旅行》说:“若是中国的法律变成各民族的法律, 地球上就成为光辉灿烂的世界。”)
但英国在革命后,其刑法仍以“普通法”为基础,变化不大,至今仍未制定刑法典,只限于制定单行的刑事法规来对旧的刑事法律制度进行某些改革。作为普通法系的美国,也同样在刑事立法方面直到20世纪才有所动作。
法国在1789年的大革命之后即开始着手制定资产阶级的刑法典,拿破仑在主持立法时,除吸收了17—18世纪进步的思想家和法学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贝卡利亚等人的先进思想外,特别参考了当时世界上仅有的仍在行用的刑法典《大清律例》,其立法参考附件为《十二表法》、《查士丁尼法典》和《大清律例》等法律文本,只有《大清律例》是仍在行用中的、活的刑法典。当时尚未发生“鸦片战争”,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国家,学习大清帝国的法律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1810年,《法兰西刑法典》正式完成公布实施,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部刑法典。法典由总则和四卷组成,共484条, 其总则规定了犯罪的分类和处刑的原则等,与中国传统刑律的《名例律》部分相当。我们还可从其“刑罚”部分看出《大清律例》的影子,如死刑规定为斩首,恢复了在大革命后已被废除的无期徒刑、终身苦役、终身流刑等,还保留了示众、刺字、烙印、枷颈和戴镣链等刑罚,这些都与清代的刑罚制度有着相似之处。这部刑法典的刑罚部分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去除了其野蛮残酷的内容,如1832年修改时,废除了死刑前砍手的酷刑等,至今仍是法国现行的刑法典。1810年可以说是西方世界制定刑法典的开始,欧洲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都以法国《刑法典》为楷模。
以下我们用列表的方式说明当时较先进的国家的刑事立法概况,并与中国清末修订刑律加以对照:
1810年 法国制定《刑法典》。
1813年 德国制定《巴伐利亚法典》。
1825年 英国颁布《犯罪法》,但其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犯罪概念,至今未制定刑法典。
1835年 俄国颁布《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其第15卷为刑法。
1851年 德国统一前颁布《普鲁士刑法典》,大量承袭法国《1810年刑法典》。
1860年 印度颁布《刑法典》,是印度传统法、伊斯兰法与英国普通法、判例法融合的产物。
1868年 日本开始制定《暂行刑律》,又称“假刑律”,是明治政府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仍仿中国明清律。
1870年 日本颁布《新律纲领》,仍以清律为基础,如刑罚为五刑体制,律目也与前律相当。
1871年 德国颁布《德意志联邦刑法典》,贯穿了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
1874年 日本颁布《改定律例》,取消“五刑”制度,将刑罚定为惩役和死刑,是向资产阶级刑法的过渡。
1878年 匈牙利颁布《刑法典》。
1880年 日本公布旧《刑法典》,以法国《刑法典》为蓝本。
1902年 挪威颁布《刑法典》。
中国清政府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
1903年 俄国《刑法典》实施。
1904年 中国修订律例馆成立。
1905年 中国开始修订新刑律草案。
1906年 中国设立法律学堂,并派员出国考察;清政府发布“仿行宪政令”;《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编成。
1907年 日本颁布新《刑法典》,参考德国《刑法典》。
中国《大清新刑律草案》完成,引起“礼法之争”。
1908年 沈家本上《奏请编定现行刑律以利推行新律基础折》。
瑞士颁布《刑法典》。
1909年 美国颁布《联邦刑法典》,至今仍有效。
奥地利颁布《刑法典》。
1910年 清政府于5月颁布《大清现行刑律》。
1911年 清政府于12月颁布《大清新刑律》。
1912年 北洋政府颁行《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
1928年 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刑法》(旧)。
1935年 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刑法》(新)。
1940年 巴西颁布《刑法典》。
1960年 苏联颁布《刑法典》。
1961年 蒙古、捷克斯洛伐克颁布《刑法典》。
1971年 美国法学会制定《模范刑法典》,又译作《标准刑法典》,各州依此为蓝本,结合本州情况制定新的州刑法。
1979年 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79年刑法)。
1997年 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97年刑法)。
从此对照表看,清末中国政府开始修订新刑律,是合乎世界范围的刑事立法潮流的。在清政府修订新刑律之前,全世界只有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匈牙利、挪威等少数几个国颁布了刑法典。法国情况如前所述。
德国于1813年颁布的《巴伐利亚法典》和1851年颁布的《普鲁士刑法典》是大量承袭法国的《1810年刑法典》,德国统一后,于1871年在此基础上略加修订,成为《德意志联邦刑法典》,是德国统一的刑法典,对日本、清政府的修律活动有着重大的直接影响。20世纪30年代后,德国法西斯化,1935年对1871年的刑法典作了修正,抛弃了“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用“意思刑法”代替了“结果刑法”,甚至恢复了中世纪的野蛮刑罚——宫刑,即去势。战后根据《波茨坦协议》,德国废除了法西斯的刑法,恢复了1871年刑法典,并开始对其进行修正。1975年才正式完成新刑法典的修订,标志德国进入刑法现代化。以后又陆续作了许多修订工作,其刑法改革至今仍在进行中。
1860年印度颁布《刑法典》,印度是东方国家中最早颁布现代刑法典的国家之一,该法是以传统印度法与外来法结合的产物,对东南亚、东非等原属英国殖民地国家的刑事立法具有重大影响。现被公认为是东方国家将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成功结合的典范。
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废除旧律,制定新的《暂行刑律》,该律分为12律,分别为:名例、贼盗、斗殴、人命、诉讼、捕亡、犯奸、受赃、诈伪、断狱、婚姻和杂犯等,都与中国刑律篇目相合,可以隐隐看出明、清律的影子。日本称之为“假刑律”。这是明治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典,因其封建性显而易见,遭到反对,未能实施。1870年,在《假刑律》的基础上,修订了《新律纲领》,共14律,律目比前者更接近清律,主刑仍为笞、杖、徒、流、死,又对世族和官僚另设了闰刑,对他们犯罪适用谨慎、闭门、禁锢、戍边、自尽,以代五刑。仍未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但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建立法政学堂和研究机构,翻译西方法律,培养法律人才,并聘请西方法学专家讲学,为按资本主义模式编纂刑法典做准备。1874年颁布了《改定律例》,废除了笞刑、杖刑、徒刑和流刑,缩小了死刑适用范围,明显带有资本主义的影响。1880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刑法典,该法由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保阿索那特起草,仿照《法兰西刑法典》体例,将犯罪分为重罪、轻罪、违警罪三种,引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在刑制上也采用西方主刑与附加刑结合的方式,排斥了依身份等级不同而处罚有差异的封建旧律的影响。在进入20世纪后,日本又开始参照德国刑法典,吸收新派刑法理论修改刑法,于1907年颁布《日本刑法典》。为区别起见,将前者称为“旧刑法”,后者即为“新刑法”。新刑法分总则与分则两编,总则取消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条款,刑罚有主刑:死刑、惩役、监禁、罚金、拘留、罚款,附加刑为没收。这部刑法典对清政府修改刑法具有直接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开始对此刑法典进行反思,1956年成立修改刑法预备会议,1974年法制审议会提出《刑法修正草案》,1980年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刑法的法律》。至此,历时百年,日本终于完成刑法现代化的改革历程。
美国在1909年制定的《联邦刑法典》,共14章,536条,没有总则部分,章与章之间有许多空白条文,犯罪种类繁多,概念不明确,条文杂乱琐碎,内容也比较陈旧,实际上是经过整理的法规汇编,但至今仍然有效。直到1962年,美国法学会编制了一部《模范刑法典》,让各州结合本州具体情况,制定各州的新刑法典。1971年联邦刑法改革委员会提出了《联邦刑法典草案》,虽经参议院通过,众议院却没获通过。所有可说美国至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典。
三
清末修订刑律,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被动地进行的。西方制定刑法典是从无到有,属创新;中国则早有二千年之久的修律传统,每朝每代,不断完善,到鸦片战争时仍堪称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刑法典。当代法史学家杨鸿烈先生曾论到:
中国法律虽说从现代法学眼光来看并不算完美,而其自身却是很有条例统系,绝无混乱矛盾的规定,就现存的法典而言,唐代《永徽律》(即《唐律疏议》)为《宋刑统》所根据,《大元通制》影响明太祖洪武三十年更定的《大明律》,又为《大清律》所本,《唐律》和《大明律》如此的领袖两种形式的法典,经我几年重新爬梳整理之后,更觉得中国法律在全人类的文化里实有它相当的——历史上的位置,不能说它不适用于近日个人主义民权主义的世界,便毫无价值;英国《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也极称赞《大清律》说:“这部法典最引我们注意事便是其规定的极近情理,明白而一致——条款简洁,意义显霍,文字平易。全不像别的使的人嫌怨的东方好自炫的专制君主那样文饰夸张,但每一规定都极冷静、简洁、清晰、层次分明,故浸贯充满极能使用的判断,并饶有西欧法律的精神……”(Vol.XVI[1820]P.476 English edition)这样就可见中国法律是为世界上过去数千年人类的一大部分极贵重的心力造诣的结晶。(注: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上海书店1990年,第6页。)
如果说中国人是出于对本土文化的迷恋,盛赞自己的法典,那么一些真正研究过中国法律的西方学者的评介,可能更加客观一些。《辛丑条约》后,英国又与清政府签定了《中英追加通商航海条约》,其第12条规定:“中国深欲整顿律例,期与各国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案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允弃其领事裁判权。”(注:转引自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下),上海书店1990年,第872页。)英国以放弃领事裁判权作为条件,诱使清廷修律。沈家本、伍廷芳等也是冀望于此,力主修律。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自裨治理。”(注:《大清法规大全》卷三,《法律部·修订法律大臣奏请便通现行律例内重法数端折》。)就在中国的大臣们忙于修订新刑律时,一位德国的法学教授赫善心,当时正在青岛的特别高等学堂任教,教授法学,对此曾发出不同声音,他说:
余到中国日浅,于中国立法一事,不敢妄生末议。惟余见今日中国,自置其本国古先哲良法美意弗顾,而专求之于外国,窃为惜之。夫学与时新,法随世易。余非谓外国之不可求也,要在以本国为主,必于本国有益,而后舍己以从人;以本国国民之道德为主,必与本国国民之道德不悖,而后可趋时而应变。
……且《大清律例》向为法学名家推为地球上法律之巨擘。昔英人司韬顿君,曾将此律翻译英文,于西历1811年印刷成书,并谓其中有许多规则,他国亟应仿效者。余虽于此所得不深,然已有确证。缘近今最新之瑞士(西历1908年)、奥地利(西历1909年)、德意志(西历1909年)诸国刑律草案,其主意亦见于大清律各条也。惟《大清律例》只须特加发达,以便中国得一极新而合乎时宜之律耳。
余意以为,中国修订法律,须以《大清律例》为本。他国之吕,不过用以参考而已。倘正修订法律不以《大清律例》为本,则真可为不知自爱者也。盖中国纵将《大清律例》废弛,不久必有势不得不再行启用之一日。
千八百十年时(距今百年),有法学大家谓人曰:“汝等笑大清律,不知中有极精处,将来泰西尚有当改而从之者。”云云。中国此时宜就大清律改订,与泰西不甚相违。泰西今年改律,亦有与中律相近者将来必有合龙之日,若全改,甚非所宜。(注:[德]赫善心:《中国新刑律论》,转引自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化》,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151页。)
现在回顾清末修律的历史,首先应当对《大清律例》有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所谓“客观公正”就是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照同时期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步骤,予以考察,得出结论。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得出当时中国的刑法在体例方面并不比世界上的所谓“先进国家”落后多少,只是在刑法理念方面,有许多值得引进的东西。
1906年,中国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帮同修订新刑律,当时日本也在制定新刑律。1907年,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完成新刑律的起草工作,日本及时颁行,从此走上刑法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中国的《新刑律草案》刚一提出,即由此引起一场“礼法之争”,只得先搞个《现行刑律》,再修改草案,结果却在1910年一年内搞出两部刑法典,却都没有来得及实行,清政府自己在颁布新刑律后仅仅一年就垮台了。客观说清朝覆灭与修订新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清亡后,北洋政府将《大清新刑律》稍加修改,于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1928年和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先后颁布了两部《中华民国刑法》,其第二部刑法一直用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现在台湾当局仍在使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清末修律时,从世界范围讲,中国的刑律并不比西方落后多少,起码与日本的刑律改革是同步进行的,真正的落伍是在1949年之后的停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并没有将刑事立法作为当务之急的工作,仅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念取代法学理论,30年没有制定出一部基本的刑法。我们不仅在刑法思想、理论方面倒退,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处处碰壁,教训惨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又重新开始从西方国家大量引进现代刑法理念,进行恶补,但在引进的同时,却又把忽视法制建设的责任归于自己的老祖宗,对祖国的法律文明传统一概抹煞,没有认真的总结,也没有将批判与继承相结合。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又修改重颁,这两部刑法典的共同特点是虽然一再强调“中国特色”,却体会不出中国味。可以说从清末到当前,我国先后颁布了七部较为重要的刑法典。这七部刑法典都是以借鉴西方的法学成就为主,很少顾及自己的历史传统,甚至对此不屑一顾。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清末修订新刑律历史,回顾百年来的刑事立法史,应该有所反省,对这段历史进行再认识。面对当前的社会现状,重读赫善心当年的忠告,难道没有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吗?
标签:大清律例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古代刑罚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论文; 法律论文; 古代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