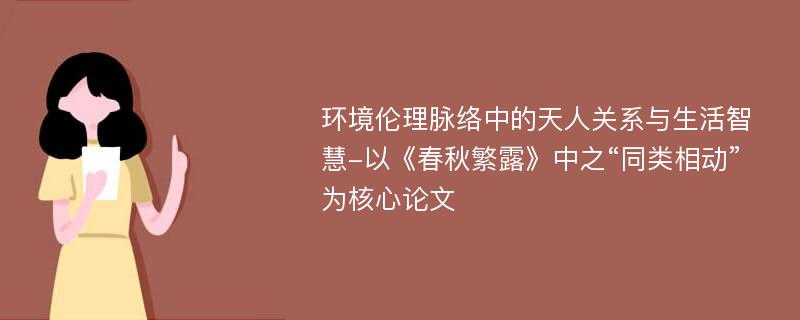
环境伦理脉络中的天人关系与生活智慧
——以《春秋繁露》中之“同类相动”为核心
王涵青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438000)
摘 要 :《春秋繁露》中由“同类相动”作为建构其天人感应系统的基本方法、驱动天人感应系统运作的律则,并赋予人参天的能力与责任。在当代环境伦理学层面,人类立基于“同类相动”,循序发展出“见端知本、贵微重始”的基本原则,“可节而不可止、当义而出”的主动积极参与原则,再以“类其进退”的方式响应天道秩序,而使整体存在界维持着自然律动,展现各种与天地参的实践生活智慧,并通过种种实践智慧,整体性地以一种天人感应特色之修正后的人类中心思维,指导人与他者(他人、他物、环境)的关系,拉紧人与他者的关联,回应过去西方环境伦理推展上的困境,找出环境伦理实践上可实际落实的进路。
关键词 :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天人关系;环境伦理
随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快速发展,短短数百年间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且其发展速度与变化的样貌于近几十年更是使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随着这些剧烈变化,就人类言,带来的是更便捷舒适与安稳的生活;就整个地球环境整体而言,相应的则是为了人类的各种需求,而产生的资源消耗与匮乏、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物种的灭绝与生物多样性的危机等等;而人类作为地球中的一员,其同样必须面临这些情况,并且意识到应对这些情况有所回应。因此,环境伦理的思考逐渐成为当代应用伦理学发展的重要议题。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以西方伦理学为主体,发展出人类中心、生命中心、生态中心等各种不同主张的环境伦理学内涵,其中生命中心与生态中心的环境伦理学,更将“内在价值”之范围,由人类自身扩展至生物或整个生态系统;响应于西方环境伦理的思考,中国哲学亦从儒释道不同角度提出许多环境伦理主张,其中不乏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西方环境伦理理论的对话或修正① 譬如朱建民《由儒家观点论西方环境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鹅湖学志》2000年总第25期,第6-7页)中提到:“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断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这两种立场究竟孰是孰非,而仅想简单地响应一个问题,亦即,如果我们对这两种立场都不满意,是否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呢?本文认为,儒家可以融入经由知性修改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可以用仁心之发用来说明自然中心主义者的关怀,而不必涉及内在价值说的困难。”又或者潘朝阳提出宋明理学家程明道的仁学,含藏了整全生机、人物一体的生态思想,其“以仁心为中轴,从它发出环境实践的动力,以诚敬来面对人、世界乃至一切生命和存有,必然顺应自然环境中的自然律,以此原则建立和发展人文”(潘朝阳《儒家的环境空间思想与实践》,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24页),以此种儒家环境伦理对比并回应西方生态中心的环境论。以及叶海烟言:“道家以物物共生为道的活动场域,而由于道遍在一切,人终究与物无对,因此道家乃由‘人本位’向着‘道本位’,全面发展天地间几无遮拦的本然动力,而‘道本位’其实已无任何‘本位主义’可言,道本无所本,而无所本乃以道为本,这也就是物物自然的‘去本位主义’或‘去中心主义’。……不外乎是一种超乎人类中心主义的豁达胸怀与广大气度。”(叶海烟《中国哲学的伦理观》,五南图书公司2002 版,第116页) ,而这些论述,最大宗者仍是以先秦儒道哲学,以及宋明理学为主体。此时,我们或许可提出一种思考,在先秦儒道与宋明理学外,如在汉代宇宙论系统亦或魏晋玄学中,是否可以找寻到其他可为环境伦理论域提供资源的观点或主张?在本文中,笔者即尝试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回应当代环境伦理中的某些议题。至于《春秋繁露》可回应当代环境伦理中的哪些议题?回到环境伦理议题本身。
首先,当代环境伦理所纠结的核心之一,即在于“内在价值”范围的问题,西方环境伦理就着存在物“内在价值”的设定范围而有人类中心、生命中心、生态中心等不同主张。但发展至今,其无法摆脱的是大多数人基本上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其价值观指导原则的稳固型态;因此无论是生命或生态中心,为不少对环境议题热切关怀的人所支持与推广,相较而言,其仍旧是少数人的价值信仰,无法说服享受现代便捷生活的多数人的认同。因此,如何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稳固型态中,如西方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进路般,建构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引导人类主体的行动,此为更实际与可能落实的进路。而在此思路上,儒家思想无论就先秦或宋明理学层面,都已有不少论述提供,在这些论述基础上,或许可进一步探讨,汉代宇宙论尚可提供哪些观点?
几个月后,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将美国卷入太空战。为了赶超苏联,美国重新对反馈计划进行规划,以便加入兰德的另一个想法——建造可以将监控图像以可回收方式返回地球的人造卫星,这对日冕计划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1960年至1972年间,日冕计划将121颗卫星送入太空。
次者,当代环境伦理从发展的进程上来看,是将西方伦理学所关涉的伦理范围,从人与人之关系,扩展到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然而就现代人而言,我们的生活方式相较于农业社会甚至早期的工业社会时期,早已有剧烈改变,人类对他物(无论非生物或生物)利用与支配的方式,胜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对他物的利用与支配的方式甚多,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亦是如此;并且,我们为自己构筑了一种“非自然”的生活世界,在城市高楼中,疏离了所谓的“自然”。在此情境中,我们如何再引导主体去“自然”地思考人与他者(无论他人、他物、环境)的关系,成为一重大挑战。相应于西方环境伦理,在中国哲学的世界观中,则以“天人合一”的主张顺势地对此挑战做出了直接回应,此即是指,中国哲学的思路中,从来都是就着人与自然与环境的关系为论的,如蒙培元认为中国哲学是所谓“生”的哲学,其基本问题是“究天人之际”,其主流哲学是“天人合一”,其所要解决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1]。同样地,除了先秦儒道或宋明理学的天人合一主张,汉代宇宙论就此观点上可提供什么样的思考,亦是值得探讨的。
式 (1)中:Y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A为技术水平,在各地区数据中,表现为各地区相对应的产出及投入;δ1、δ2为资本、劳动力投入的分配系数;这里m=1表示不变的规模报酬,假设行业规模报酬不变;ρ代表替代参数,各地区由于发展状况、技术条件各异,相对应要素替代弹性不同;e-μ为随机误差项。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春秋繁露·阴阳义》)
一、“类”与“同类相动”
“天人感应”是汉代宇宙论就天人合一议题之核心主张,余治平指出:“中国古代哲学里的感应,在对象、内容上尽管偶尔也涉及物与物、人与物,但主要还是指天与人之间的感通与应和。”[3]213从先秦到汉代,我们可在《诗经》《尚书》《管子》《易经》《吕氏春秋》《春秋繁露》等著作中看到感应思想的逐步发展,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则为中国古代感应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中,“同类相动”是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为建构天人感应系统的基本方法、驱动天人感应系统运作的律则。在《春秋繁露》中有《同类相动》一篇,且在许多篇章中,董仲舒亦对此概念有许多建构。
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冬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多胜少者倍入,入者损一,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动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势,以就同类,与之相报。故其气相侠,而以变化相输也。……故至春,少阳东出就木,与之俱生;至夏,太阳南出就火,与之俱暖;此非各就其类,而与之相起与!少阳就木,太阳就火,火木相称,各就其正,此非正其伦与!(《春秋繁露·阴阳终始》)
随着感应思想的发展,“类”亦逐渐成为建构感应思想的基础,如: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易·乾·文言》)
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
在特性上,风景园林行业相关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园林绿地建设的基本要求,不涉及技术细节。而各类标准则是法规标准体系的技术支撑,数量众多,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规范与各类标准相互融合、互不排斥、协调发展,构成和谐统一的体系。
“类”在这里,就着种类、类别与模拟、类似的字义,引申形成了万物各从其类、类固相召的理论。就《易传》与《吕氏春秋》在论述上文字的一致性而言,余治平认为《吕氏春秋》是对《易传》的直接继承,而且在深度与广度上并无超出《易传》[3]221-222。另外,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亦可见到类似描述:“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物故以类相召也。”只是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借着“类”概念的使用,形构了他的天人感应系统。
二、“同类相动”的宇宙生成感应系统
整体存在界的根基是“元”,“元”是万事万物之所以能发生发展的基础,在存有阶层与时间上具有先在性。然而,“元”是如何运作使得整体存在界万事万物得以发生发展?则必须通过“气”的运行,董仲舒言:“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元”与“气”是其宇宙论系统中的两大默认,气可概括为阴气、阳气两种作用形态,再扩展为四时、五行系统,因此,“元”与“气”作为基本预设,而“气”扩展为“阴阳、四时、五行”,则成为董仲舒宇宙结构论的基础[4]。但“气”又是如何由阴阳二气结合四时、五行而成为一宇宙论系统?此时,董仲舒循着《易传》与《吕氏春秋》中之“类”概念的基础,展开论述:
STS教育就是在STS思想指导下,为培养了解科学技术、能积极参与科学技术相关社会问题的决策、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公民而进行的一种教育,突出科学技术在个人和社会方面的应用以及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谓一元者,大始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春秋繁露·玉英》)
在“同类相动”作为驱动天人感应系统运作的律则得以展现其作用前,首先,董仲舒需要确立此感应系统中的根基,即整体存在界之根源为何?在此问题上,其以“元”的概念解释之,其言:
“同类相动”概念的出现如感应之说一样,可在许多先秦至汉代的文献中寻找到踪迹。“类”基本上有几个重要意思:一是种类、类别,即许多相似或相同事物的综合,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易·系辞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春秋繁露·十指》“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着矣”等等① 本文《春秋繁露》之原典引用以曾振宇、傅永聚注释版本《春秋繁露新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为依据,后续引用直接于引文后标明篇名,不再另行注释。 。二是法式、法则的意思,如《韩非子·说疑》“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春秋繁露·度制》“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等等。三是模拟、像、类似的意思,如《易·系辞下》“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荀子·不苟》“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端悫而法”,《春秋繁露·执贽》“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等等。当然,“类”字仍有其他意思,但以此三意为大宗,在各种文献中被普遍使用。
阴阳二气的实际运作是整体存在界得以循天道终始循环的要素,此二气运行会“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如冬天阴气向西方逐渐隐没减少而阳气由东方逐渐高仰出现,基本上春夏阳气多阴气少,秋冬阴气多阳气少,但此气的多少,不是完全固定的而是就着实际情况相损益、相溉济;另外,阴阳二气的运行还会“以就同类,与之相报。故其气相侠,而以变化相输”,即是就其共同属性而凝聚变化,如春天少阳之气由东方生出以就于木,夏天太阳之气由南方生出以就火。此时,董仲舒就着阴阳二气,融入了方位、四时(四季)、五行等范畴,对经验世界运行的基本样貌展开说明。但此所谓就着实际情况而产生的损益溉济、变化相输等,又是如何运作的?其云:
智能制造不是简单的自动化,而是制造业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让机器、生产流程和产品变得智能化、人性化。智能制造战略不是工业自动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需要引导和支持工业自动化和信息通信技术深度有机融合;实施智能制造战略支撑因素的缺失,将延缓制造业向智能制造升级。
进行产业风险评价有助于合理分配信贷资源,优化信贷资源结构。根据产业风险的不同,对不同产业的信贷投放权重进行更科学地制定:对于风险较小、新兴高科及政策扶持力度较大的产业可以加大信贷资源投放力度,对于风险较大、产能矛盾较大的产业则加以控制,并考虑到产业间的联动性风险,对风险较易传播的产业的信贷投放加强管理和后续跟踪追进。这样在进行授信时合理分配信贷资源,优化信贷投放结构,从而提高改善银行信贷业务的收益。
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
凡天地之物,乘于其泰而生,厌于其胜而死,四时之变是也。故冬之水气,东加于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厌于胜也;生于木者,至金而死;生于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过秋;秋之所生,不得过夏,天之数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即我们体育教师在课堂尾声中引导学生适当腾出一些“空白”,设法留下余味,促使学生去思考、去探究、去想象、去创新和消化、吸收。比如水平一:跑跳单元“龟兔赛跑”一课的结束部分中,教师可以这么设计:乌龟和兔子在赛跑中,虽说乌龟赢了比赛。但是,兔子如果不偷懒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最终谁会取得胜利呢?(生:乌龟。生:兔子。)最后的答案有待于同学们课后去揭晓吧。这样的留白式课堂尾声不露声色地将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完全激发了起来,使得课堂自然由课内延伸课外,拓展了学生学习的空间。
阴阳之气就着阴阳属性与其同类的事像、物像而有基本的运行规律,所以在季节上,阳至其位大暑且热、阴至其位大寒而动。而阴阳二气的生灭变化是交相影响的,因此经验世界中的事像、物像也是相互变化的,如春夏秋冬四季随着阴阳二气五行方位的更迭即是如此① 本文之写作目的不在于对董仲舒的宇宙论系统进行详尽研究,因此就阴阳二气本身的运行规律层面,便不再详尽分析。 。此外,存在界的所有事像、物像均循着此节律而运作,如: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军之所处以棘楚。……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明,皆鸣而相薄。其气益精;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阴阳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火者夏,成长,本朝也。……土者夏中,成熟百种。……金者秋,杀气之始也。……水者冬,藏至明也。(《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火干木,蛰虫蚤出,蚿雷蚤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春秋繁露·治乱五行》)
首先,就事物的存在方式上言,“以类相召”是其基本律则[3]227,因此阴阳二气与四时五行方位等核心范畴以类相召而成基本节律系统,阴阳二气落于万事万物中依循同类相召之律则,驱使各种事像、物像顺着阴阳二气与四时五行产生运动变化,因此“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次者,从感应的发生机制上看,阴阳二气会帮助各俱阴阳之性的事像、物像[3]227,所以说“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阴阳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此“以类相损益”一方面说明了“以类相益”,另一方面也提到了“以类相损”,如此,阴阳二气于事像、物像上的感应是双向与多维的[3]227-229,其互相的干扰会导致时节事物的失序,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此双向与多维的性质“类其进退”,而有所回应,譬如董仲舒在《同类相动》中所举致雨与止雨之例,在《春秋繁露》中更有《求雨》与《止雨》两篇,详尽说明如何依据此“类其进退”的律则进行实际操作,即通过以阳益阳、以阴益阴,与以阳克阴、以阴克阳等方式达到目标。
所以,董仲舒实际上将阴阳二气的交感运行汇入了五行相生相胜的概念,再配合四时,将整体存在界中的各种事物发生发展首先归类于阴阳二气的变化,再归类入四时、五行之中,以“同类相动”的各种细则形成一套宇宙生成论的感应系统,如冯达文所言,此种宇宙论的认知方式可称为“类归方式”,对整体存在界中的万事万物通过“把单个事物归入‘类’中,进而把‘小类’归入‘大类’中,通过归入来予以介说与把捉”,因此“宇宙论是通过把捉、还原大自然生化的过程与节律而建构起来的”[2],此分析可说十分精确。
三、“同类相动”与天人关系
通过“同类相动”所建构起的宇宙生成发生论体系,最重要的,还是要说明天人关系的问题。因此,在更多的论述中,董仲舒认为“同类相动”的“以类相召”“以类相益损”等律则,最终得以“类其进退”的,还是人类主体。虽然说“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春秋繁露·观德》),天地是万物本源而生成万物,但人类在万物之中有存在阶层上的重要位置,其言:
证明 对于G=PQ,考虑Q在P上的作用,则有P=CP(Q)×[P,Q](见文献[10]中定理8.2.7).若CP(Q)>1,则[P,Q]<P,从而G交换,矛盾.故CP(Q)=1,P是初等交换p群,取P中的p阶子群的生成元代表A={x1,x2,···,xt},其中t=又循环群Q非正规,由Sylow第三定理可知其Sylow q-子群的个数至少∪为q+1,取出这q+1个循环群的生成元代表B={y1,y2,···,ys},其中s=q+1,显然AB即构成了势为q+1的点独立集,不等式显然成立.下面考虑等号成立条件.
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伏。阳至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春秋繁露·阴阳位》)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目前,椎弓根螺钉已广泛应用脊柱骨折、椎间盘突出症、椎管狭窄及脊柱肿瘤中。椎弓根置钉方法有很多,而术中导航为最准确的[1],但导航系统价格高昂,难以短期内在更大范围内应用。基层医师因条件限制,术中往往凭经验、手感行椎弓根螺钉置入,其位置常常很难控制,甚至会将椎弓根穿破,其发生率为20~30%。我们在基层医院常常可以碰到椎弓根钉植入失当或误置,引起骨折复位不佳、固定不稳,甚至出现了许多诸如椎弓根螺钉穿破椎弓根、椎体,损伤血管、脊髓、神经根等并发症[2]。这些并发症的发生不仅与手术者水平有关,还与椎弓根解剖结构个体差异有关。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题直立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人本于天与万物一样,亦与万物一样循着“同类相动”的各种律则而生成变化,但人与万物不同则在于是“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因此人是与天相类的万事万物中联结最紧密者,董仲舒以“物旁折之/取天地少”与“人正当之/取天地多”区别了人与其他万物。所以在《人副天数》中详尽地描述了人体生理结构与天地结构的一致,凸显人的地位,其他篇章中董仲舒同样通过“同类相动”将前述的宇宙生成论感应系统与人链接,譬如:
喜怒之祸,哀乐之义,不独在人,亦在于天。而春夏之阳,秋冬之阴,不独在天,亦在于人。(《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就着上述两个面向,在中国哲学涉及环境伦理的主流论述中,如先秦儒道或宋明理学,都已有讨论,因此均不是新的课题,只是过去的讨论是从汉代儒学观点切入的,相较之下仍是少数。但如冯达文所言,是时候应对汉代宇宙论的发生、发展及其评价有重新的探索,“宇宙论作为追踪大自然的变迁节律的一套学问,它所体现的‘类归性’的认知方式,所开启的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政治哲学,及从‘赞天地之化育’的大气象中得以证成的价值体系,其含蕴、其呈现的,至今仍然有极其值得品味,值得借鉴的意义”[2]。这里提出汉代宇宙论具有的“类规性的认知方式”特点,笔者认为,就是回应上述环境伦理两议题很好的资源。而就整个汉代宇宙论体系发展而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所提供的“同类相动”,又是一最佳代表。因此,本文即以《春秋繁露》中的“同类相动”为核心,展开思考。
阴阳二气四时运行与喜怒哀乐同样地“以类合之”,因此,“同类相动”的“以类相召”“以类相益损”等律则在人身上同样发生作用,而人若不依循此律则便会导致因为“同类相动”原则而造成的“以类相损”。本来,天人之间其基本的节律是依循春夏秋冬、喜乐怒哀、生养杀藏而发生发展,又譬如我们可于《五行顺逆》篇中看到详列的四时配合五行,在每个节律上本都应有其秩序以及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该有的行事,但人君若“出入不时、惑于谗邪、好淫佚、好战、简宗庙”,则会打坏此节律,打坏节律则会因“同类相动”原则造成“以类相损”,最终便出现“自然之罚”: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其君枕块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春秋繁露·立元神》)
由此可见人类在此宇宙生成论感应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天地生养万物而人类成之,彼此通过“同类相动”原则互相影响而为一体。当然,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又将最高的在上位者的地位与责任提到最高,因之言“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春秋繁露·立元神》),此种对于最高在上位者的设定,回到董仲舒之时代,当然是可理解的,至于在当代社会,当然我们可以不再需要将绝对权力与威势的核心放在一人(最高的在上位者)身上,但如《春秋繁露》中所描述的各种复杂的社会运行规则与人事行为准则等,都须依靠着“同类相动”原则运行与操作,若没有一个在上的体制与机制参与执行,势必在运行过程上也难以推进。
因此,人类作为与天地“相参相得”(《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参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地之参”(《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者,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一方面可表述每一个人类主体通过此“同类相动”的宇宙律则而展现其生活方式与内涵,另一方面可表述整个体制如何通过制度与规范的建置与执行而产生符合节律的国家社会之发展。
四、从“同类相动”律则到主体工夫操作
从前述所描绘之天人关系中可知,董仲舒认为就着“同类相动”的“以类相召”“以类相益损”等整体存在界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律则,最终得以能“类其进退”者,仍须回到人类自身。因此,如何循着此律则而实际操作?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相关说明。
董仲舒很明确地指出“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春秋繁露·五行变救》),当存在界的事像、物像产生异变,除咎之法即在于人主之德,此“德”非单纯地指作为人之本身的德性表现,《春秋繁露》中更重视的是各种以“同类相动”为原则而有的操作,如曹迎春所言,董仲舒设定了人在宇宙中具有的独特地位,因此“人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人对自然万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充分发挥‘参’的作用”[5]。以下,便对人如何“参天”的细则进行扼要分述。
(一)见端知本、贵微重始——详查“同类相动”律则之始动
依照“同类相动”的律则,首先要把握的即为各种事像与物像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征兆,在其征兆显示异相之初即有所对应处置,董仲舒言所谓的灾异是“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并且由天之谴告的“灾”逐渐扩大为天之威吓的“异”,人若置之不理,终将导致“自然之罚”,而对治之基本原则,首先即是能做到“见端知本、贵微重始”: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圣人见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应万,类之治也。(《春秋繁露·天道施》)
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着也。……故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着也。……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着,虽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贵微重始是也。(《春秋繁露·二端》)
可节而不可止也。节之而顺,止之而乱。……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二)可节而不可止到当义而出——符应“同类相动”之律则
人类作为参天地的能动与主动者,除了“见端知本、贵微重始”,更重要的是能让“同类相动”的律则适当与准确地发生作用。如何让此律则适当与准确地发生作用?首先在于“可节而不可止”:
《春秋繁露》中对各种灾异的描述,包括许多自然界现象,就现代的角度而言或许是不科学的,因这些现象已可被科学地解释,譬如地震、陨石等。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自然与人文活动现象,其实则凸显的就是自然节律本身的失序,以及因为人类活动的不恰当,造成的人文或自然节律失序。所以,就天人间的关系而言,《春秋繁露》列举了许多天道施化整体存在界,而人类相应相感于天道却失其义,因此“以类相损”而造成的各种自然或人文灾害现象,譬如引文中所描述的“夏大雨水、冬大雨雹、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等异常气候现象。就现代“极端气候”的角度看,其可能产生的因素即在于过度的人文活动造成的自然循环的失调。所以,“见端知本、贵微重始”是基本的原则,此基本原则还是较为被动地提醒我们要谨慎地审视各种事像与物像发展变化的开始,才能作出正确的回应。
在适当的时节中让与此时节同类而相应之事物应时而动,天地人均应时而动即是“岁美”,而人若要主动地在各种政事制度上进行修订或增减,亦当顺应节律,绝非强硬地直接制止或执行,譬如在《度制》篇中论到对贫富之调节,董仲舒云:
其次,策划能力有待提高。军工企业质量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在于强化质量监管,在进行质量管理系统建设时,军工企业无论在引导方面还是管理方面亦或是策划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影响了质量管理系统建设效果,总得来说,军工企业策划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其遗秉,此有不敛穧,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春秋繁露·度制》)
一方面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中加强学习型组织机构的建立,不断提高党建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和管理能力,定期组织党建工作人员进行思想培训和学习交流,让其了解国家最新的教育政策理念,并对其在教学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地交流和探讨,结合大学生思想发展现状,制定今后的教学计划和方案,推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有效发展[4]。
在浮选钛精矿的烘干工序中,主要采用两种工艺流程,其一是以A公司为代表的直接烘干工艺,即采用高温烟气直接与浮选钛精矿接触进行烘干;其二是采用高温烟气加热管壁,管壁与浮选钛精矿接触,简称间接烘干,此种烘干方式以B公司为代表。两种工艺流程的优缺点如表1所示。
“调均”不是一味地平等,通过强硬手段将贫富差距消除,必然会导致原有秩序的失序而造成混乱。“调均”是要让富者贵而不骄、贫者养而不忧,社会各阶层有其稳定位置与发展,后面董仲舒接续提到的“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等等,亦都是此原则的遵循与运用。我们可再看以下两例:
凡养生者,莫精于气,是故春袭葛,夏居密阴,秋避杀风,冬避重漯,就其和也;……四时不同气,气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视代美而代养之,同时美者杂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荠以冬美,而荼以夏成,此可以见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气也。荠,甘味也,乘于水气而美者,甘胜寒也。……天无所言,而意以物。(《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第一例就人的各种生活面向言,譬如符应节律的穿着与居住环境的选择,注意各节律气候对人体的影响,对于物品与食品的选择同样依循阴阳二气与四时五行之节律变化而交错使用,此种种均为“循天之道以养其身”(《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的各种实践。第二例则就施政体制的层面论述四时(春夏秋冬)与四政(庆赏罚刑)的以类相应,各季节有其依类而适当与应当进行之政事,因此要注意彼此之“不可相干、不可异处”。如此,董仲舒云:
全国水文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3月27日,全国水文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水利部副部长刘宁充分肯定了2009年全国水文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分析了“大水文”发展理念下水文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水文工作的“三个夯实、五个强化”要求,即:夯实水文人才、水文法规、水文站网,强化水文管理、水文监测、水文服务、水文科技、水文文化建设。
是故人主之大守,在于谨藏而禁内,使好恶喜怒,必当义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春秋繁露·阴阳义》)
依循“同类相动”律则而应有的积极性作为,即在于人之能动且主动地使得万事万物“当义而出”,就施政层面言必须绝对地谨慎,了解“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的道理。如董仲舒认为阳气为德而阴气为刑,在自然律则上阳气多于阴气,因此回应于人身上,亦应当德厚于刑。又回应于当时之时代背景,董仲舒虽强调的是最高在上位者的作用,但实则也对其施政作出了严格的规范,非一味地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力,反而是要求君主谨慎严肃地循着“同类相动”的宇宙律则处理一切政事① 其实,回到每个人身上,董仲舒也提到“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然而“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春秋繁露·实性》),亦如“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一般,要通过实际的教化,逐步地使人得以更准确地在“以类相益”的一面发生发展。 。
(三)“类其进退”的操作
从可节而不可止到当义而出,《春秋繁露》已给予人积极参天的重大责任,但对于人的责任要求,其不仅只是机械化地顺应天道,天道阴阳二气运行自身之展现亦会各有“以类相益损”的情况,因此人之更甚者,是能通过“类其进退”的操作,更积极地处理因着“同类相动”而有可能形成的“以类相益损”的各种情况,其言:
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故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前文已提过的致雨与止雨,即为最好的例子,所以自然与人文世界的所有事像与物像彼此因相类而相应,产生各种好或坏之情状,阴阳之气与祥瑞祸福等,就宇宙论层面言均遵循着“同类相动”之律则而发生发展,就人类主体之工夫操作而言则可“类其进退”回应之。人通过对“同类相动”律则的把握与操作,可比喻为如我们使用同样宫调引发乐器之间的共鸣,当其他人未见此操作过程,便以为乐器相动无形而自鸣,因之谓自然,其实其中包含着人主动性的操作,但却是一种“使之无形”的操作,因为人并非破坏了宇宙律则,而是相应着此律则而有所作为,这是一种更确实的顺应天道的脉络。
五、环境伦理脉络中的天人关系与生活智慧
整体而言,如曹迎春所言:“董仲舒将天人进行了详细对比,找到了这个有机整体的结合点‘类’,即天人之间的相似结构和本质。”[5]这是就天人关系层面而言,展现出《春秋繁露》的天人合一径路,在此脉络上,“同类相动”不仅是《春秋繁露》中的一篇文章,更是其宇宙发生发展的核心律则,也是引领人类主体工夫操作的基本法则。至于“同类相动”的理论形构模式,则如冯达文所言,是一种“类归方式”的认知结构,此种主体的认知进路与方式,是人类通过对经验世界中多样丰富之万事万物的细微之俯观仰察而来,通过观察与归类找寻到存在界运作发展与变化的规律,此种认知模式有其合理性。当然不能否认的,在《春秋繁露》中有更多是根据此类归而引申的各种祥瑞灾异的联想,并且加入了天降灾异的视角,就此而言,我们说《春秋繁露》不免有迷信化或神灵性化的面向,且此面向影响了汉代谶纬之说的流行,甚至成为主导官方的意识形态[3]254;亦如刘国民之评论:“同类相应的关键是类的建立是否真确。……如果把不是同类的事物当作同类,而认为它们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这就不是类应类推,而是异类比附。……以同类相应为理论建立起来的阴阳五行架构,因为类之建立的不科学性,所以此架构本身及其与经验事实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6]或许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对于汉代宇宙论或天人感应思想的评价,相较于先秦或宋明理学,亦或中国佛教等,常是较低的。然而亦如本文前言所述,汉代宇宙论与天人感应之说,除了过往的批判视角,当然具有价值且值得继续发展之面向,譬如就上述之评论言,说同类相动的建立不具科学性并且与经验事实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是过于偏颇的,同类相动的理论建构首先必须立基于人类对经验世界的观察,以及观察后的统整归纳,此为理性思维的操作模式,只是往后延伸与扩展时混入了各种非理性的联想,因此我们仍可就其具有价值的面向延伸思考。譬如就当代环境伦理的视角而言,“同类相动”提供了具有意义的思考方向。
首先,就着本文前言所提的第一个议题,当代西方环境伦理一直有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命中心、生态中心主义间的拉扯,就中国哲学所提供的各种讨论资源,也有着关于人类中心主义或深层生态学之修正与回应的论述。然而,稳定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实则难以避免,从生物学的繁衍角度言,所有生物都以为了自身之繁衍为根本目的而活,都只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所有生物对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或无生物,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有所利用,把他者作为“资源”,为一种常态。当然,我们也都相信人类终究是“异于禽兽者”,西方从理性而中国往往从德行说明此“异于禽兽者”的所异之处何在?但大多数人则更能从人类的先进科技、异于地球上其他生命的繁荣生活模式来看到我们与他者之异。此种明显差异拉开了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存在物的差距,人类对地球上资源(他者)的使用方式相较于其他生物的使用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形成了“宰制”万物的模式,人类因此对地球整体环境的影响,相较于其他生物也有着天壤之别。此时,当代环境伦理中的各种环境问题,譬如自然资源消耗、空气污染、全球暖化、过度放牧、滥垦山林、大量渔捞等等,出现于人类急速发展之时。然而,在此之时,对于引导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得以被生命或生态中心的观点改善,我们是否愿意放弃从人类出发而如生态中心主义呼吁的“像一座山那样去思考”?如果这一步就目前而言仍是困难的,那么,董仲舒通过《春秋繁露》所建构的人类中心主义型态,或许即为另一条可供参考的思路。
在《春秋繁露》中,人类主体的地位在存在阶层上虽然是肯定的高于他者,但通过类归思维的结构,人类与他者的差距又非绝对的宰制的,我们当然可视地球上的他物为资源,但各种资源(其实也就是各种存在)与人类,即这些经验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与天道阴阳二气之运行是“同类相动”的,人类与他物都是这同类相动的其中之一,彼此互相影响。但人类与他者的差异在于人被赋予的“参天”的责任,在地球上人类是唯一的主动与能动者,能让这世界的万事万物循律而动,对于世界,人类有责任,也必须充满着爱,因此董仲舒言:“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着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春秋繁露·仁义法》)通过推恩的模式,人类的参天与爱物层层地由内而外扩展,对内反理正身,对外推恩广施。西方修正后之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出“非人类的物种及自然事物具有价值,端赖其能否满足‘省察过的喜好’,提供人类保护自然的理由”[7],仍显示出人类主体地位与他者的距离。回到《春秋繁露》之脉络,实则人类不是“保护自然”的角色,当我们意识到环境成为伦理问题时,自然环境已经成为必须被“保护”的状态,人类成为造成此状态的凶手,又成为审判凶手的法官,我们的价值观在对立的角色中更显混淆无依靠,而《春秋繁露》通过“同类相动”的律则建构的人与自然关系(天人关系),将人类的“参天”形塑为与天同感共应的一致节律,又确定了人类于天地间的责任与地位,此或许是另一条人类中心主义作为我们处理环境伦理议题,进行价值引领的可参考模式。
次者,当我们为自己构筑了一种“非自然”的生活世界,疏离了所谓的“自然”,如何再引导主体去“自然”地思考人与他者的关系?在此议题上,循着“同类相动”的宇宙论结构,回到人类身上,《春秋繁露》便提供了非常多的实际操作之例,也就是主体工夫操作的说明。无论对内反理正身或往外推恩广施的层面,本文上一节“从同类相动律则到主体工夫操作”中的三个层次与各种例子,都显示人处于经验世界中,有许多与天地参的实践生活智慧,不但能同类相应,更能“以类相益”,形成一种和谐的生态观。面对环境问题,我们或许已打破了此种和谐,造成了“以类相损”的情况,譬如空气污染问题造成的全球暖化,全球暖化造成的气候变迁,气候变迁中产生的极端气候,而各种大小范围的极端气候造成的各地区各种生命的失序与节律的破坏,又或者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药滥用造成的土地污染或地力过度消耗、单一作物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消失等,亦会影响环境中生命的失序与节律的破坏,反之,对人类自身而言,也会有极大的影响。人类作为地球环境的一员,如何重新通过这些“同类相动”的实践生活智慧,重新思考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方式,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
[1]蒙培元.中国哲学生态观的两个问题[J].鄱阳湖学刊,2009(1):96-101.
[2]冯达文.重评中国古典哲学的宇宙论[J].孔学堂,2015(4):68-77.
[3]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陈福滨.智与思——陈福滨哲学论文自选集[M].新北:辅大书坊,2016:255.
[5]曹迎春.董仲舒生态思想研究[J].衡水学院学报,2014(3):20-22,128.
[6]刘国民.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76-277.
[7]朱建民,叶保强,李瑞全.应用伦理与现代社会[M].台北:空中大学,2005:72.
Heaven-Man Relationship and Life Wisdom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Ethics:A Focus on“Telepathy of the Same Kind”in Chun Qiu Fan Lu
WANG Hanq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Huanggang,Hubei 438000,China)
Abstract :In Chun Qiu Fan Lu,“telepathy of the same kind”,a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whereby the telepathic system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s built and the law through which the telepath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s propelled,equips Man with the capac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understand Heaven.In terms of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ethics,on the basis of“telepathy of the same kind”,Man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foreseeing the end from beginning and valuing both the trivia and the beginning”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of active participation“with moderation and justice”.Then,based on the principles,Man can respond to the order of the heavenly way in the form of the telepathy of the same kind so as to make the whole world of being follow the rhythm of nature, show all kinds of practical life wisdom informed by “forming a triad with Heaven and Earth” gui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Others (other people, other creature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make Man and Others closer by means of all kinds of practical wisdom and anthropocentric thinking that is comprehensively corrected by the telepathy between Heaven and Man.In this way, we can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of promoting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find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Key Words : Dong Zhongshu; Chun Qiu Fan Lu; telepathy of the same kind;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environmental ethics
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19.03.003
作者简介 :王涵青(1978-),女,台湾高雄人,副教授,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9)03-0018-10
收稿日期: 2018-11-16
(责任编校 :卫立冬英文校对 :吴秀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