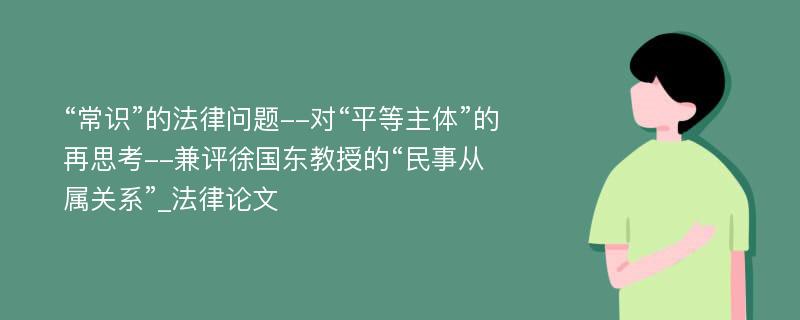
一个“常识性”问题的法学难题:对“平等主体”的再思考——兼评徐国栋教授的“民事屈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识性论文,法学论文,民事论文,难题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4)08-0155-08 一、平等主体:“常识性”问题的法学难题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法学界围绕着民法与经济法之界分的论争尽管最终经由《民法通则》对“平等主体”的立法确认而暂渐平息,然而,这一立法表达在当时是以正趋时尚的“商品经济”理论为支撑的,而且明显受到政治话语的影响。正如尹田教授所言,促成这一立法表述的“既不是佟柔等民法学者就平等主体关系说不遗余力的鼓吹,也不是《民法通则》就民法调整对象所作出的规定,而是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之社会实践本身。”[1](p13-20)因而这一所谓的“胜利”并非是学术讨论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话语作用于立法的产物,“平等主体”之于民法的真正意义及其内在意涵并未被充分地挖掘和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针对“平等主体”问题的疑问并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搁置了。 这一被搁置的问题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再一次暴露出来。并再次引起了法学界对“平等”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因巩献田教授在致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中批评《物权法(草案)》违宪而引发,其核心问题是在物权法领域应不应当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平等保护。对于这样一个被认为是民法的“常识性”问题,民法学者“不曾想到会有个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要对这一原则发难。他们对此等荒诞之举感到非常气愤,且又哭笑不得……不得不组织起来对这个‘常识性’问题进行重申。”[2](p121)然而,当民法学者们反过头来重申这一“常识性”问题时,却发现面临着难以言状的困难。回顾当时民法学者的反驳,似乎没有人能够从民法理论上清晰地界定“平等”的基础和内涵,而是被动地局限在“平等”是否违宪这一具体问题上而进行防御性的申辩。而且即使这种防御性的申辩,当时所采取的策略也大多是迂回的、游击的,甚至是妥协的、自相矛盾的。比如王利明教授立足于“平等”并不排除“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反驳,[3](p1-5)尹田教授则以“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已写入宪法,《物权法》没有必要重复为由来为《草案》申辩,①龙卫球教授甚至以《草案》已经体现了对公共财产的优先保护来妥协,②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证“平等主体”在民法上具有当然的正当性。以致尹田教授在回顾这场论争时,仍不无遗憾地称:“我们理不直且气不壮,没有能够从理论上真正击破他们的错误观点。”[1](p13-20) 因《物权法(草案)》而引发的争论是围绕“平等保护”问题而展开,但其更深层的问题仍然是对民法上的“平等主体”如何认识的问题,国家与个人能否以及在何种基础上可以作为平等的主体?应当如何认识国家在民法上尤其是《物权法》上的地位?《物权法》上的征收、登记等制度是否应视为一种不平等关系在民法领域的体现?在未就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进行解决的情况下,应否平等保护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澄清。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在讨论中仍未充分展开,甚至于基本上未被触及,最终《物权法》立法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问题再一次被搁置了。 从上述两次针对“平等”问题的大讨论看,政治话语多于理性思考,政治正确压倒了逻辑分析,其隐含的学术问题并未得到澄清,它必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再次浮出水面。随着对民法典立法问题讨论的深入,对“平等主体”的质疑声又开始渐次响起。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次质疑甚至批判的声音未夹杂政治话语,而是秉持着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对“平等主体”问题进行重新反思,物权法、家庭关系、劳动关系、消费合同关系等各个领域所体现出的诸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开始全方位地被纳入到质疑者的视野。 蔡立东教授立足于现实的观察视角对“平等主体说”提出了措词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逻辑上必然先于民法而存在,如果将民法调整对象界定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平等关系必然已经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然而,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表明,民法所谓的任何人皆是平等主体这种立法上的表达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因而“平等主体”的表述缺乏基本的现实根基。《民法通则》将“平等主体关系说”明确为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当“私法”还属于理论禁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而随着国家计划在经济生活中的逐渐淡出,对于当今中国的民事立法而言,“平等主体说”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赘语。[4](p81-89) 徐国栋教授从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大量存在不平等关系的角度也对“平等主体说”提出了批评。③在此基础上,他还试图寻求一种能够将“不平等关系”纳入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基础。他从十七世纪菲尔麦在亲子关系上提出的天然不平等命题出发,分析了“人人平等”原则得以被普遍接受的历史缘由。他得出结论说,针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人们为了能将人人生而平等的醉人口号继续喊下去,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民法同样成为了“一个长期被平等蒙汗药麻醉的领域”,以致对家庭关系、劳动关系、消费者合同关系、甚至物权登记征收制度、合同法中的格式合同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同样视而不见。在他看来,世界是“平等与不平等兼有的人间,民事屈从关系构成了不平等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将民法调整对象限定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容易被证伪的错误。对于各种不平等关系,他借用“屈从”的概念来概括,并试图通过“形成权”来统一规范。其基本理路和目标是“把亲子关系领域的屈从与形成权领域的屈从打通,甚至把屈从的概念运用于从属劳动关系等其他领域,形成一种规模性的屈从理论,打消天主教经院哲学家打造、近代重要宪法文件继受的平等幻觉,为一种新的民法理论张目。”[5](p159-175) 由此看来,所谓的“常识性”问题并未因《物权法》的论争而消除人们对它的质疑,尽管目前看来反对观点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平等主体”说的地位。然而反对者显然也并非是信口开河、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任何人无法回避的现实基础。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需要民法学人给予合理的解释。然而,不知是因对此“常识性”问题之不屑,还是因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理论难题,对反对者的质疑似乎仍未引起充分的关注,至今尚无人对此作出正面的回应,他们最多不过是在解释“平等主体”问题时,针对现实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一些附带性的说明。从这些附带性说明看,大致有三种解释:一是对不平等现象作例外解释,认为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关系,身份法领域的不平等、因对实质正义的强调对弱势群体进行的特殊保护以及民法上的登记征收等问题只是特定的例外。[6](p26)二是所谓的“整体解释”,认为尽管民法上也存在监护关系、社团内部关系等具有服从性质的关系,但面对公、私法之间在许多领域上的交错,不必强求像刀子切苹果一样清晰无误地切成两半,因而从整体上说,“平等主体”的表述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7](p67)三是从形式平等和事实平等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平等主体中的平等指的是法律地位的平等,而不是具体法律关系上的事实平等,雇佣关系、监护、消费者合同中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不影响在法律上将他们理解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可以通过法律的干预进行校正。[8](p4) 可以看出,上述解释均采取了一种含糊其辞的策略,难以令人信服。如果家庭法中的亲子关系、劳动法中的劳动关系、消费者权益问题上的消费合同关系、乃至物权法上的征收登记等问题均体现了一种不平等关系的话,显然已不能简单地用“例外”或“整体上看”这样的措词来敷衍了之。形式平等和事实平等的说法同样无法消除人们之于“平等”的疑虑,形式平等和事实平等之间是一种何种关系?它对解释并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到底能够带来哪些帮助?如果认可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平等主体”还能否成为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限制语?上述解释显然并没有就这些基础问题进行正面的回答。看来,“平等主体”这一“常识性”问题似乎已经成为我国民法上长期不能攻破的跨世纪难题。 二、“法律人格”之抽象:“平等主体”的立足点 如何认识民法上的“平等主体”首先需要确定一个适当的观察点。实际上,近代民法上作为主体的“人”并非是现实中的“人”,而是对现实中的“人”的抽象。用克尼佩尔的话说就是:现实中的“人”并非是法律上的主体,成为法律主体的是“法律人格”。④ “法律人格”的概念普遍认为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并非一切生物意义上的人均可成为法律上的主体,只有具备一定的身份条件的人才可以成为法律上的Person,即“法律人格”。⑤近代以降,每个人取得了同样的法律地位,身份不再成为区分“人”与“法律人格”的依据。但现实中的人无处不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不仅有地位高低、财产多寡等外在因素的界分,也有年龄、性别、体格、相貌等自身条件的差异,更有情感、智力、偏好等内在特质的区别。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民法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人的特殊情况,而只能依所谓“普通人标准”来作为规范制定的依据。这意味着立法者不再考虑个人的外在条件和自身特质,而是首先需要剥离掉上述因人而异的各种差别,这种被剥离掉一切外在条件和个体特质的个人由此成为“一个孤立的、褪掉个人历史特性和历史条件的个人,一个绝对的法定的我的图像。”。[9](p75)这种“法律人格”构成了普遍性规范获得的条件,没有这种抽象,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民法规范便失去了基本的参照。⑥ 然而,这样一个被剥离掉一切特质的“人”并不仅仅是一个空壳,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主体,它必须有思想,有意志,会思考,能行动。它必须保留着能够成为法律主体的那些东西,因此,在对个体外在条件和内在特质进行剥离的同时,还需要对“法律人格”进行法律上的基本预设。 首先是理性人预设。理性被视为是人与其他种类的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17世纪以来,理性被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思想家们相信,每个人经由理性能够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能够分辨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应当摒弃的。尽管通过理性达致正确认识的基础和具体途径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比如自然法学者可能会以某种先在的、不言自明的第一原理为基础,经验主义者会将理性的判断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历史法学派的法学家也许会认为理性无法脱离历史传统和民族的共同经验。但这些分歧不足以影响他们形成一个共同的认识,即理性能力是每一个人所固有的能力,它能够有效地压制个体的情感、欲望和偏好,从而形成正确的判断,为个体的行为提供正确的导向。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理性作为人所共同的东西被赋予了“法律人格”,通过理性的内在立法,这一“法律人格”能够约束自己的情感,涤净欲望和偏好,并且能够依据一条可以被视为普遍法则的最优化的方式而实施行为,由此实现个人的目的与普遍秩序的统一。[9](p77-79)理性人预设是近代民法上关于“人”的基本预设,因为人是理性人,所以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思为自己立法,可以实现法律上的“自治”;也因为人是理性人,所以人是可归责的,他必须对自己的承诺、自己的行为担负起责任;同样因为人都是理性人,所以不同的人才可以在相互关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能够形成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律秩序。可以说,这一预设是近代民法基本理念和原则的逻辑起点,构成了近代民法制度和体系构造的基础。 其次是自由人预设。“法律人格”仅有理性只说明个体有了自我判断、自我决定和自我归责的能力,理性能力能否成为自我判断和自我选择的决定因素,取决于这种理性判断是否会受到来自外在条件的干涉和强制。只有在排除了外在干扰和强制的情况下,人的行为才真正受自己理性的支配。排除外在因素的干涉和强制,最为有效的手段是赋予个体完全的意志自由,只有在个体摆脱了外在的干涉和限制,建立在自己自由意志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选择。 经过剥离和预设,“法律人格”也即民法上的主体就成为这样一种人:他是孤立的、被剥离掉个体一切特殊性的人,他享有独立而自由的意志,能够通过理性进行思考,并通过理性来判断事物的正当性,从而决定最终行为的选择。通过剥离,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无差别的法律主体地位,它是获得普遍适用性规范的条件;而通过预设,每个人成为了能够自我决定、自我归责的主体,它是主体平等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前提。 通过这种“法律人格”的设计可以看出,民法上的主体并非是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个人,而是对现实中的“人”的抽象。无论现实中的诸个体存在怎样的差别,从主体设计的这一前提意义上,它都不属于普遍性规范所应考虑的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任何人得以成为平等的法律主体。离开这一基础,法律主体的清晰图像便会混迹于芸芸众生而让人眼花缭乱,由此人们便无法再理解一个乞丐与一个百万富翁何以能够成为平等的主体,也无法理解一个婴儿基于何种法律设计能够与成年人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离开了这一基础,面对现实中的各色人等,面对任何一个人在不同侧面的优势和劣势,立法者便不可能制定出适用于每一个人的统一的法律规范。离开了这一基础,各种因景而生的解释便会纷至沓来,我们最终失去的或许是民法一切制度最为原初的根基。 三、“法律人格”的理性与自由:“不平等”问题的起点与归宿 “法律人格”通过对个体外在条件和内在特质的剥离,使得每一个人获得了同等的法律地位,但法律主体能否平等地行使权利,需以其理性能力和自由意志为前提。因而对现实中并不具有“法律人格”设计所要求的理性能力和自由意志的个体,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予以补救。 首先是理性能力的补救。对于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等不具备“法律人格”所要求的理性能力或不完全具有理性能力的个体而言,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理性来作出判断和选择。因而,他们所享有的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只不过是一个“平等”的形式,并不能保障他们“平等”地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来弥补其理性能力之不足,从而保障其平等主体地位在具体的法律关系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对于理性能力不足的自然人,其理性能力通过监护制度来补救,而对于法人则通过意思机关的设立作为理性能力的根据。 其次是自由意志的补救。“法律人格”的设计以主体的理性能力和自由意志为前提,理性能力为主体能够依靠自己的理性平等地行使权利提供了可能,然而这种可能还需依赖于个体的自由意志来保障。“平等主体”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法律人格”假设,在这种假设下,由于一切外在的因素都被剥离,每个人都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不仅有充分的理性能力,同时也拥有不受任何外在因素限制的意志自由。然而,“法律人格”一旦进入现实的世界,理想而纯粹的“人格世界”必然会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人的外在因素和个人特质便会一一出场,这些因素反过来会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表达构成限制或障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形成对个体意志的强制。这样一来,法律所设计的“法律人格”的基础就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以此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现实世界”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必须考虑现实世界对“人格世界”可能造成的威胁,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来弥消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对“人格世界”的影响。 因此,“平等主体”并非不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平等”问题,而关键在于民法所关注的是何种类型的“事实不平等”,为何要关注以及如何来关注这种“事实不平等”以及民法应立足于何种立场来关注,其意欲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由于“平等主体”以“法律人格”的前提设计为基础,而“法律人格”已剥去了人的身份地位、财产多寡等一切外在条件,民法没有将这些外在条件纳入视野,这意味着民法事实上默认了这些外在条件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民法无法解决基础分配上的不平等问题,而只能是以现实条件为基础,提供一种平等适用于所有主体的内在调节机制和矫正手段。事实上,民法也不可能解决基础分配上的事实平等问题,甚至它以现实的社会分配问题为前提,如果现实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分配上的不平等,从某种意义上民法恰恰是对这种现实不平等的维护。 也就是说,一切基于个体外在条件和个体特质意义上的“事实不平等”问题均不属于民法关注和力所能及的范畴。民法设计了一整套平等适用于所有主体的调节机制,这一机制依赖于个体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来运转,只有当“事实不平等”问题影响到这套机制的正常运转时,它才能够被纳入到民法的视野。而且这种纳入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关系双方不平等的基础,而在于通过对调节机制本身的矫正,来弥消不平等的基础对民法调节机制正常运转所带来的影响。 如一个乞丐和一个百万富翁,二者在经济条件和经济地位上显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然而在民法所设定的“法律人格世界”里,乞丐和百万富翁的经济状况作为个体的外在条件被剥离了,民法所看到的只是两个有着同样法律地位,有同样的理性和意志自由的、平等的个体。它并不关注,因而也不可能改变二人在经济条件上先在的不平等。在乞丐和百万富翁二人之间的买卖关系中,如果乞丐因自身的购买能力的限制不能够达到交易的目的,而非来自于另一方当事人——百万富翁的强制,这并没有改变民法所设定的“平等”的基础,因而这种情况并不属于民法矫正的范围。但在诸如劳动关系中,如果乞丐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接受百万富翁提出的严苛条件,则二人外在条件的“事实不平等”使乞丐的意志自由受到了来自这种外在条件的强制。在这种情况下,民法应赋予乞丐特定的权利来对抗百万富翁所施加的强制,或者对百万富翁施加特定的限制来消除其对乞丐自由意志的强制,由此使二人能够继续维持民法所设定的“平等关系”,从而保障民法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转。 民法通过“法律人格”的概念打造了一个“人格世界”,它与“现实世界”是异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现实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只存在于“现实世界”,并不存在于“法律人格”的世界。只要个体还停留在“法律人格”的世界里,民法所设定的调节机制便不会受到影响,一旦个体突破了“法律人格”世界的边界而进入到“现实世界”,民法的调节机制便不再有效。然而,“现实世界”的诸多因素常常会影响到个体在“人格世界”的存在,因而个体或出于优势而主动、或出于劣势而被迫回到“现实世界”中来,民法的任务就在于通过特定的机制和手段将个体维护在“法律人格”的世界里而不逾越“人格世界”的边界。在这一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民法对“不平等”的关注并非是单纯地对现实中“事实不平等”本身的关注,而是立足于“平等主体”的理性能力和意志自由的关注,它是以“法律人格”为起点,同时也是以“法律人格”为归宿的。 四、“不平等关系”作为民法调整对象之谬误 一些学者之所以反对民法上“平等主体”的表述,主要是认为民法所调整的下列社会关系并非是平等的关系。 一是亲子关系。徐国栋教授认为未成年子女由于缺乏理智的成熟和经济上的独立这两个平等的支点,所以必须与其双亲维持一种屈从关系。在这种屈从关系上,法律所体现的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而是保护原则。他还将亲子关系作为不平等关系的一种类型,并由此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保佐人与被保佐人之间的关系、医患关系等均纳入到这一类型的不平等关系中。[10](p44-45) 二是从属劳动关系。在徐国栋教授等人看来,从属劳动关系是权力财产(即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对非拥有者的支配,劳动者必须从属于雇主的意志,雇主拥有指挥权、控制权、甚至是惩戒权。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种屈从关系。这种类型的屈从关系还包括房屋租赁关系、附有随意条件的合同关系以及附随合同(主要是消费合同)关系等其他不平等关系。[5](p159-175) 三是民法中规定的,尤其是《物权法》中规定的征收、登记等制度,这些制度所体现的同样并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典型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11](p75) 可以看出,上述认识均是立足于现实,直接从现实的角度来观察民法规范,其观察视角和论证路径是:现实规范。既然现实中存在不平等,则法律规范就不应无视不平等,因而将民法限定为平等主体就是错误的。然而,这种观察视角和思维方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民法的规范设计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法律人格”设计,在此前提下民法规范的形成及思维的路径应当是:现实法律人格规范。首先通过对现实中的人的外在因素和自身特质的剥离,获得一个平等的、无差别的“法律人格”,这是民法“平等主体”的前提,在此基础上,立足于现实反过来对欠缺理性能力、影响意志表达之自由等威胁“法律人格”之基础设计的外在因素通过制度进行补救或平衡。在此过程中,“法律人格”是一个核心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它不仅是现实的过滤网,同时还是现实的调节器,通过这一过滤网过滤掉法律不应考虑的差异因素,通过这一调节器来调节现实中所谓不平等因素对前提设计所造成的威胁和障碍。 在上述意义上,亲子关系上的不平等现象并不与民法上的主体平等设计相抵牾,而恰恰是为维护主体之平等的必要前提。亲子关系的目的主要也不是为调整所谓的父与子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是在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确保无理性能力者能够平等地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而采取的填补性手段,并由此来调整“子”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父”与他人的关系。从当前的民法编排看,监护制度大多依托于家庭关系来规制——尽管同时也辅以其他补充性的法律手段,这种编排淡化了“法律人格”设计的基础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界对监护制度理性填补意义的忽略。 在所谓的“从属劳动关系”方面,劳动者并不缺乏理性能力,但是外在的条件却限制了其自由意志的自由表达,使“法律人格”的基础设计不再有效,因而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来回复弱势一方的自由意志,从而维护民法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转。从本质上看,劳动关系和消费关系所体现的仍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关系双方并不存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别,任何一方均无法律上的特权,与对方也不存在任何隶属或依附性关系。其法律关系的设定、变更和终止仍然依赖于个体理性的选择和自由意志的表达,而非是法律的前提性预设。也就是说,对劳动关系与消费关系的调整依然以平等关系为基础,以当事人的意思为前提。只不过是,“法律人格”所剥离掉的外在因素反过来影响了个体自由意志的表达,从而成为双方关系平等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任务只能是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来弥消外在因素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回复到“法律人格”最初设计的前提性状态。在这一意义上,当下就所谓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讨论中,学界一味强调形式平等所存在的问题,并以实质平等为目标,这一认识实际已偏离了民法上“平等主体”的基本意涵。实际上,形式平等仍是不可改变的基础,而实质平等问题只不过是为实现形式上的平等,或者说为消除形式平等的外在影响因素而进行的必要的制度性调节。只有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民法才能不失“平等”之前提,所谓的实质平等才能获得可供参照的标准。 至于征收和登记等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并不以个体的理性和自由意志为前提,的确体现的是国家和个体之间的管理关系,而非平等关系。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民法应调整这种不平等关系,征收的条件、程序等核心性的和具体性的内容均不由民法来规范。前文中已经讨论,民法在调整具体关系上并不考虑个体的外在条件,然而外在条件却常常构成个体权利的前提。比如,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拥有财产的权利,但财产权所依附的具体财产却有数量和种类上的差别。民法虽不解决这些基础分配问题,但却需以基础分配的结果为前提,而这种基础性分配的结果在民法上是通过权利来表达的,因而首先需要对主体的权利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确认。由此,征收制度只不过是为明确个体权利在特定条件下所受到的限制,登记制度也不过是权利确认的一种方式而已。它们所解决的是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前提性问题,而非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身。 因此,无论是家庭法上的亲子关系,还是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乃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消费关系和物权法的征收登记制度,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确认某种不平等的关系,更不在于维护这种现实中的不平等状态,而且也不在于——事实上也不可能——消除现实中关系双方外在因素上所存在的差异。这些关系的法律调整,仍然以“法律人格”意义上的平等为基础,以人的抽象为前提,以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平等行使为条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弥消自由意志行使之障碍,也不意味着这些制度的设计以“事实上的平等”——或“实质平等”为目标,而毋宁是对“法律人格”基础设计之回复,从而使个体能在“法律人格”的前提下自由地表达意志、平等地行使权利、自主地决定行为的选择。 将不平等关系或“屈从关系”视为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仅没有基本的法律理论来支撑,还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是民法与其他部门法——主要是行政法之间的划分问题,徐国栋教授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一旦取消(平等主体的限制语),人们本来以为已厘清的民法与行政法、税法的区分又将陷入混沌。”[12](p37-40)就此,他也未能寻求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因而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愁死人”的问题。[5](p159-175)其次,如果将不平等关系或“屈从关系”作为民法的调整范围,立法目标应当如何定位的问题也会陷入困惑,民法到底是要维护这种不平等关系呢,还是矫正这种不平等关系?如果针对不同的不平等关系应予区别对待的话,那么,哪些不平等关系应当维护,而哪些不平等关系需要矫正呢?同时,不管是维护还是矫正,应当以何为标准?维护或矫正到何种程度才是适当的呢?这些问题对民法基本理论无疑均是具有颠覆性的,同样也是难以解决的“愁死人”的问题。就此,徐国栋教授试图通过形成权来予以统一规制,然而形成权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为维护权利人的优势地位,相反却是因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权利人因处于某种不利地位而容易受到对方当事人的不当限制,因而需要赋予其某些特殊的权利用来实现双方关系上的平衡,这恰恰是从平等关系出发,并为维护平等关系而采取的矫正手段。因而形成权总是有明确而特定的前提,而且这种前提往往是基于对方当事人的某种不当行为,或者是在不损害对方当事人现实权益的情况下而设定的。将形成权作为“屈从关系”的规范基础,并不符合形成权的性质及宗旨。 总之,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劳动关系,民法规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平等”,而不在于“屈从”;其目的更不是为规范或维护一种支配性权利,而是为回复到“法律人格”的基础设计为已足,这一点从现代民法越来越多地削减和限制家长和用人单位权力的立法趋势中可以得到明显的体现。因此,民法上的“平等主体”中的“平等”并非是对现实的直接描画,而是基于“法律人格”的平等,这种平等也并非是对现实中的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而是只有当其威胁到“法律人格”意义上的平等基础的时候才被纳入民法的调整范围。这种对不平等现象的纳入,其目的也不在于不平等关系本身,而同样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平等”为目标、以“平等”为标准的。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亲子关系上的监护制度主要是对“法律人格”理性欠缺之弥补,而劳动关系上的强制性规范则是对“法律人格”意志自由之回复。至于征收制度和登记制度等,它们仅涉及民法的一些前提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而非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身。 由此,民法的调整对象仍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通过“法律人格”的抽象获得了同等的法律地位,因而身份、地位等外在因素不再成为对人进行区分的标志;在这种关系中,主体的理性判断和选择通过个体的自由意志来表达,因而法律需要为这种表达提供必要的前提性条件;在这种关系中,法律关系的设立和变更仍以个体意思为基础,因而得以与其他不以个人意志为基础,而以某种先定的隶属或管理关系为前提的法律部门相区分。 ①参见尹田教授在接受《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观点,该采访由吕娟、鲁楠整理为《法学界的“郎顾之争”——物权法叫停的背后》,载《法律与生活》2006年第2期。 ②参见龙卫球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座:《论物权法的合宪性问题》。http://www.baojian.gov.cn/bjsy/fxqy/2006-04/7392ae8c987b0ecc.html,访问日期:2014-1-18。 ③徐国栋教授对“平等主体”说提出的质疑和反对可参见其:《“平等主体”民法调整对象限制语研究综述》,载《北方法学》2009年第3期;《家庭法哲学两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3期;《论民事屈从关系》,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平等原则——宪法原则还是民法原则?》,载《法学》2009年第3期等文,还可参见其《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中关于“平等主体”问题的讨论。 ④参见[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59页。关于法律人格的讨论可参见尹田:《论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马俊驹:《人与人格分离技术的形成、发展与变迁》,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4期;马俊驹:《论民法个人人格构造中的伦理与技术》,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2期;秦伟、刘保玉:《略论法律人格的内涵变迁及立法评判》,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6期;[德]汉斯·哈腾鲍尔:《民法上的人》,孙宪忠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冬季号;尹田:《论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王森波:《人格——源流、涵义及功能》,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崔拴林:《论私法主体资格的分化与扩张》,法律出版社2009年;张翔:《自然人格的法律构造》,法律出版社2008年;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赵红梅:《私法与社会法——第三法域之社会法基本理论范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文章和著作。 ⑤在罗马法上,一个人要成为完全的法律主体,必须具有三种资格:自由权(status libertatis)、市民权(status civitatus)、家庭权(status familiae),只有同时具有这三种资格,才具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奴隶不享有任何自由权和市民权,因而不被视为是法律上的主体。参见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尹田:《论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马俊驹、张翔:《论民法个人人格构造中的伦理与技术》,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2期;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和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等。 ⑥康德对普遍性规范获得之前提进行了详细论证。他认为对于一个规则,如果主体认为这种规则只对他自己的意志有效,那么这种规则只能是主观的,譬如他将受辱必报作为准则,但这种准则倘使被当作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规则,它在同一个准则中就不能自相一致了,因而只能被视为是个人的准则。只有当这一规则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有效的,它才可以是普遍适用的实践法则。但是,这种普遍适用的实践法则却不能从个人的经验和禀好中去寻找,因为经验和禀好所欲求的对象对于“所有人的意志并不就有同一个对象,而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对象”,因而不能成为普遍实践法则的意志的决定根据,它不仅“不足以用作普遍法则,它在普遍法则的形式下反而必定会自行瓦解”。参见其《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一卷第一章中的讨论。标签:法律论文; 民法调整对象论文; 理性人论文; 民事法律事实论文; 法律主体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民法论文; 自由意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