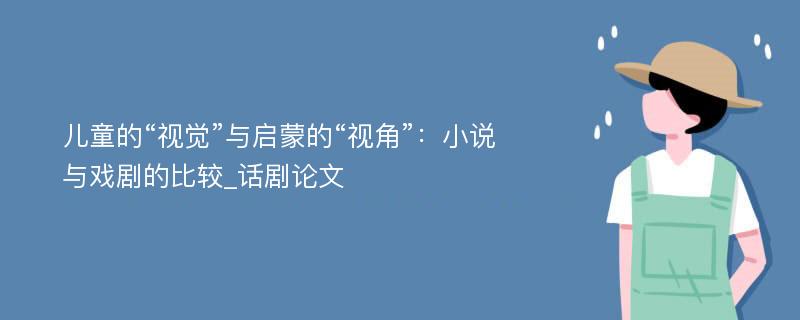
小孩子的“眼光”与启蒙者的“视角”——《生死场》:小说与话剧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视角论文,说与论文,小孩子论文,生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实验话剧院根据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代表作改编的同名话剧《生死场》,自从今年六月份在北京上演以来,受到了“圈内圈外”的一致好评。老实讲,这部话剧给笔者带来的感动与惊喜是不言而喻的。那浓郁的东北风味和演员扎实老到的表演自不必说,单是舞台灯光的起承转合、整个舞台动作所显示出来的造型意味,都让人激动不已。而编导者朝着“有戏”的角度对原著所做的大胆改动,更是极大地增添了戏剧效果。不过在感动和惊喜之余,笔者却又隐隐地感觉到了一丝莫名其妙的遗憾,总觉得相对于原著来说,话剧缺少了些什么。究竟缺少了什么,我也说不清楚。经过几天的思索之后才明白,那其实并不是什么“缺失”,确切地说只是不同——是话剧和小说之间的不同,是因为我对萧红的小说原著太过喜爱,于是不自觉地把对原著的改动当成了“缺失”。而令我最“触目”的则是田沁鑫(话剧《生死场》的编导)与萧红对这个世界的把握方式的不同。
笔者读《生死场》,读《呼兰河传》,读萧红的其它作品,总可以感受到作者那无处不在的小孩子般的眼光,也似乎总能看到她那一双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般的大眼睛,那双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困惑和疑虑,甚至还不无惊异和恐惧。萧红始终在用一双童稚的眼睛寂寞而孤独地注视着周围的“大人”世界,用一颗懵懂无知却灵气十足的童心感受着这个世界,并把这种观察与感受付诸于文字,传达给读者。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萧红为什么“叙事和写景,远胜于人物的描写”(鲁迅语),为什么她不能写出人物性格的丰满、复杂与深刻。这对萧红简直是太苛求了,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对他心目中的“大人”认识与把握得深邃全面呢?那是小孩子所力不能及的。萧红在谈到自己和鲁迅先生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区别时曾说到,鲁迅先生始终“站得比他笔下的人物高”,而萧红自己却做不到这样,起初她对笔下的人物还抱着一种怜悯与同情的“俯视”态度,但越到后来她越发现无法去怜悯与同情他们,因为“他们站得比我高”。萧红并不知道她其实被自己的儿童视角所“蒙蔽”了,小孩子对于大人,不论是好人坏人还是愚昧者和觉醒者,都会采取“仰视”的态度。
同样,我们也不能苛求一个小孩子能编织出线索明确中心突出又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那也是小孩子力所不及的。他也许对生活中的片段与场景有着特殊的洞察与记忆,但却做不到“综合与概括”。《生死场》更像是一个个场景与片段的组接,这一个个场景与片段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充满灵性和艺术动感的生活画卷。不仅如此,连《生死场》里的行文方式和语言也是小孩子式的,萧红总是贴近着女孩子的心灵,例如她描写成业摔死女儿的一段文字:“小金枝来到人间才够一月,就被爹爹摔死了!婴儿为什么来到这样的人间?……小小的孩子睡在死人中,她不觉得害怕吗?妈妈走远了!妈妈啜泣听不见了!天黑了,月亮也不来为孩子做伴。”这完全是小孩子的语言,小孩子的思维方式,一个成熟的大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话语?而作者写到王婆的服毒自杀,既没有喧染赵三的丧妻之痛,也没有过多地描写王婆的悲苦命运,而是站在王婆的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的角度,抒写着小女孩的孤苦与悲哀:“小女孩被爹爹抛弃,哥哥又被枪毙了,带来包袱和妈妈同住,妈妈又死了,让她和谁生活呢?”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担心”,和真正的小孩子又有什么差别吗?可以说,这正是《生死场》乃至萧红所有小说的最独特之处。
如果说萧红在小说中始终是用儿童的视角观察与感觉着那一片“忙着生,忙着死”的生死场,田沁鑫则自觉地认同于五四以来鲁迅所开创的启蒙话语,自觉地站到“高处”俯视着舞台上的角色。萧红的目光惊异而迷茫,田沁鑫的目光则深邃而冷峻,冷峻地照射出每一个人物灵魂深处的卑微与渺小。我们发现,小说文本里的世界是模糊而懵懂的(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对大人的世界了解得那么透那么深呢?);而编导者和演员们所合力创造的舞台世界则是清晰的,明朗的。因为清晰和明朗,每个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状态才那么鲜明,对比才那么强烈。无论是“二里半”的愚昧、懦弱,二爷的虚伤、自私和刚愎自用,王婆的烈性与麻面婆的“骚性”,还是赵三起初像“一块铁”、在传统报恩思想观念的作用下又变成了“一堆泥”,都在话剧中表现得那么“触目惊心”;小说中成业与金枝的“野合”几乎和多少年来祖辈们走过的足迹没有任何区别,那只是“懵懂的生,懵懂的死”的一部分;但话剧中成业与金枝的野合与私奔却自始自终被赋予了“反封建”的意义,他们为了“爱情”可以不顾父母的压力与村人的白眼,勇敢地追求着属于自己的幸福。而他们和周围无所不在的封建、落后氛围构成了激烈的冲突关系。——在这里,不仅人物“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被观众看得一清二楚,连人物实际的思想状态与他“应该如此”的距离有多远,我们似乎也能计算得出来。
萧红是悲哀的,她的悲哀把她的愤激掩藏起来了,她以含泪的微笑唱着一首首凄切哀婉的歌,表达着她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疑虑和生疏;田沁鑫则是愤激的,她的愤激使她不满足于小说文本中懵懂、模糊而灰暗的世界,她给这个“生死场”平添了许多亮色。成业便是其中最耀目的一个。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几乎无足轻重,他喜怒无常又暴躁残忍,对金枝“始乱终弃”不算,还亲手摔死了自己的女儿,不久他自己也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舞台上的成业却完全“面目一新”:他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后成了“生死场”上最早的觉醒者;他呼吁父老乡亲们去抗日,宁死不当亡国奴;他象征着“新生力量”的觉醒与壮大,也寄托着编导乃至观众的希望,他几乎成了整部话剧的灵魂与旗帜;面王婆的烈性也被编导者发挥到极至。小说中的王婆是因为儿子的惨死而绝望地自杀的,这种死法在一些落后愚昧的农村老太中可以说并没有特殊之处,也没有什么深层的意义所在,但在话剧中,王婆因为对自己男人懦弱的性格本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而自杀,就很是与众不同了。舞台上的王婆几乎成了自己丈夫赵三的精神导师和指引者。她一次次地激励丈夫说“你高高的,你高高的!”这当然也是编导和观众对赵三的一种期待,王婆在这里几乎成了编导和观众的代言人。
田沁鑫对舞台角色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二里半”羡慕而敬畏地称赞赵三“你胆子大”时;当他的妻子麻面婆即使被日本鬼子强奸杀死,他仍然麻木不仁不知反抗时;当他因为自己儿子成业的“败坏门风”而自觉抬不起头来时,当他一次次自言自语地说着“丢人呀,丢人呀,咋就这么丢人呢”的时候,观众自然也就在心里替舞台上的人物着急:“愚昧呀,愚昧呀,咋就这么愚昧呢?”于是,在话剧结尾处,当日本鬼子的野蛮暴行终于激起村民们的反抗,连“二里半”也昂起了头挺直了腰杆的时候,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当然自在情理之中,这也是编导所要达到的戏剧效果。不过,正如舞台上“石头发芽”一类的道具所显示的象征意义一样,村人们的觉醒与反抗更多地具备着象征的意义。尤其是像“二里半”这样的“落后”农民,连自己的老婆被残杀都表现得无动于衷,他怎么忽然就一下子“觉醒”了呢?这和小说中他在妻子惨死、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参加义勇军的行为完全不同。从全剧来看,前半部分刻画“生死场”上人们的愚昧麻木时,戏剧效果非常突出,但最后村人的觉醒与反抗多少有些牵强,似乎剧本被人为地分割成了风格不甚一致的两部分。
而剧本的改编也显示出田沁鑫的些许不自信,最明显的是她对王婆“死而复活”的情节处理,既然已经对王婆的“死法”做了很大改动,那就不应太拘泥于原著,再让她死而复活。话剧的前半场已经把王婆的“烈性”发挥到极至,她完全可以“放心”地离去。而“复活”后的她在精神上似乎伴随着那次未遂的自杀而死去了,她几乎没有任何出色的舞台表现。例如在前半场中,烈性的王婆不顾村人对金枝的流言蜚语,鼓励女儿尽管生下她和成业的“孽种”,并要替女儿抚养未出世的孩子;但在下半场中,赵三因为女儿生了个私生子而倍感“羞耻”,意残忍地摔死了刚刚出生的小生命的时候,“死而复生”的王婆竟然毫无反应,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当然我们要理解田沁鑫,她既要揣度小说原著的精神面貌,又要照顾观众的情绪,又要表现作为“主旋律”的抗日内容,也真够难为她的了。
标签:话剧论文; 生死场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萧红论文; 田沁鑫论文; 王婆论文; 戏剧论文; 剧情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