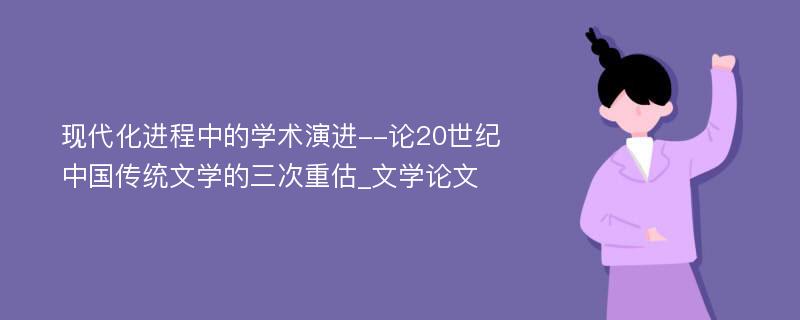
现代化过程中的学术演进——论二十世纪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三次价值重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过程中论文,学术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变革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完全建立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人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学有了不同于过去任何一个世纪的认识,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和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学术史的时候,这首先是留给我们的一个最强烈的印象。如果说,19世纪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以绍续传统为己任的话,那么,随着本世纪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如何对传统文学进行新的价值评估,就成为20世纪所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共同思考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传统文学的批判继承,抑或是新时期以来对文学传统的弘扬,都没有离开过这一核心问题,只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核心问题认识的一次次深化。因此,认清本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学术演进,就是我们从宏观上总结本世纪古典文学研究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从20世纪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三次价值重估入手,对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的现代批判
说起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自然从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我们知道,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是正统思想。受其影响,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言志载道为内容的诗、文一直被看做文学的正宗。但是自19世纪末开始,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封建文化的没落,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文学观念也出现变化。他们已经看到了传统诗文的落后性因素,开始重视戏曲小说这些在当时盛行于市民中间的通俗文学样式,认为它们有推动维新、改造思想的作用。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1897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狄葆贤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1903)等文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但真正认真地对古典文学进行新的价值评估,还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五四”运动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首先就从古今对立的角度比较尖锐地提出了变革古代文学的问题。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天朝大国一变而为受人欺侮的小国,于是,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就开始了为拯救民族命运的自强不息的斗争。但是,中国人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仍归于失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认为:“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反观西方的文明进步之所从来,虽然也是革命之赐,但西方人所进行的革命,并不与中土所谓的朝代鼎革相同,而是由革命带来文明的进化。因此,在陈独秀看来,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也同样不但要有政治革命,还要有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这是“五四”学人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得出的关于文学革命的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推动文学革命的最根本的动力。
那么,文学革命应该如何进行呢?很显然,那就首先应该对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一次新的价值评估。陈独秀认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本来是从“多里巷猥辞”的《国风》和“盛用土语方物”的《楚辞》开始,可是从两汉赋家以后,却逐渐脱离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变为“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这其中虽有韩昌黎之变法,宋元市民文学之兴起,但昌黎变法不彻底,一犹师古,二犹被“文以载道”的古训所牵,所以至明之前后七子和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出,此十八妖魔独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如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等几不被人所知。至清末民初,所谓桐城派、“骈体文”派、江西派之类,更是等而下之。此种文学,“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也正是“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因此,要改造中国,首先就应该打起“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只有如此,才会使文学革命取得成功。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是以宣传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为目的的,为此他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上自汉赋作家,下到明代前后七子和晚清时期被奉为正宗的桐城派,都在他的批判之列。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完全放弃了传统。他要有所建树,也必须借助历史,要对传统文学做出新的解释,从中寻找有生命活力的东西。他推重《国风》、《楚辞》、唐代传奇、元明剧本、明清小说,把这些看成是中国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这就等于把明清以来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价值评判来了一个大颠倒,标示着“五四”学人将要站在一个新的时代起点上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来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研究,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价值评判体系。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不久,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就成为“五四”学人所攻击的对象。
概括起来,“五四”学人这种由重新认识传统文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而引发的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革命,起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如果说,在19世纪以前,中国人传统的文学观念还是以经书为正宗,以雅颂为典范的话,那么,自“五四”以后,中国人就以平民文学为正宗,以白话文为典范了。倡导这种观念的,除陈独秀之外,最有代表性的当然还是胡适。胡适首倡文学改良,他和陈独秀一样,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也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是贵族文学的传统,一个是白话文学的传统。他认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文学改良刍议》)。这一观点自胡适提出后,就得到了“五四”进步学人的积极响应。用这种观点去看文学史,自然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其实,以胡适、陈独秀为首的“五四”学人把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并不是一个十分科学的论断,他们的观点在当时也曾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是,这种文学观点的提出,在当时的确具有震聋发聩的意义,它使那些沉湎于传统中的人清醒过来,用一副新的眼镜来看文学;它使一大批青年学人奋发,走上了批判封建的正统文学,研究白话文学的道路;它也使那些守旧的学者们不得不正视白话文学,再不敢以古文为正统而妄自尊大。所以,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提法并不十分科学,但是他们这种对于白话文学的张扬,这种新的价值评判,却被“五四”以后的学人们继承下来并得到发展。从此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改变了研究的格局并指引了新的方向。众所周知,“五四”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19世纪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直是以传统的诗文为主,而小说、戏曲以及平民文学,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五四”以前,以梁启超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看到了戏曲小说等的作用,才提出了“小说为维新之本”、“诗界革命”等口号,并开始了对戏曲小说的初步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毕竟尚处于较小的范围,不足以形成古典文学研究格局的大改变。是“五四”学人站在文学革命的立场上,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新的价值评估,由此才引发了一场研究革命,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古典文学研究格局,戏曲、小说等白话文学的研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作为一代学风的倡导者,胡适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鲜明的时代性。为了说明白话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就写了一部系统的《白话文学史》;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白话文学,他就费许多功夫整理和提倡中国古代民间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醒世姻缘》等。和胡适同时的一大批进步的“五四”学人,也与他抱着同样的研究态度,把重点放到了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之上,如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吴梅写《中国戏曲概论》,徐嘉瑞写《中古文学概论》,刘半农等人进行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等,这些学者的工作,填补了以往文学研究的空白,改变了以往文学研究的格局,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五四”时期之所以发生了文学研究格局的改变,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文学革命引起的文学观念的更新。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以至到“五四”以前的封建正统文人那里,文学一直没有独立的地位,只不过是宣扬文以载道的六经附庸而已。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下20世纪初黄人、林传甲等人所写的《中国文学史》就清楚了,在黄、林等人的观念中,所谓文学,仍是一个经史子集、音韵训诂、金石碑帖等无所不包的模糊概念。是“五四”学人以西方的文学观为参照,才给中国文学以独立的地位。这种文学观念,较之传统的文学观,似乎使文学的范围有所缩小,但是它却改变了以往的缺乏现代科学分类的状态,终于使文学成为一门系统的现代科学,并使“五四”以后的文学史家开始按照现代的科学分类法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新的文学观的确立,较之传统的文学观念,使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又有所扩大,把以往人们所不重视的戏曲小说、民间文学、白话文学等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正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不但彻底改变了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格局,而且引导了现代化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五四”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取得了那么突出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五四”学人站在了比以往任何时期的人都要高得多的现代立场上来看待中国文学。正是从这一立脚点出发,他们才比以往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思考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学进行新的价值评估,从而才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事实也说明,自“五四”以后,从20年代到40年代,尽管在当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学派,各学派也各自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在今天反观他们的研究,莫不和这种新的价值评估有关。例如,在“五四”时期,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激烈反传统,先有国粹派站在守旧的立场上对传统的极力维护,后有学衡派站在新人文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传统,相应的,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就有各自的特点和大小不同的建树。又如,自“五四”以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之后,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二三十年代曾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有的人主张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这实际上也是对传统文学的价值评估问题。由于这两派的观点大不相同,他们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也各持自己的观点并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再如,“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上的观点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文学革命”的大旗却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到了“五四”后期,胡适推崇西方文明,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他更多地带有改良精神,在“五四”时期他就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要用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去重新评估文化遗产,用西方文化来改造建设中国文化,做出了他的贡献;而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投身于革命运动,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古典文学研究上,但是他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介绍,却引导了后来的一大批学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派,并成为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方向。由此可见,站在现代化的角度对传统文学进行价值评估,不但是“五四”时期、而且也是“五四”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围绕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推动了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建国初期对传统文学的批判继承
在如何从现代化的角度对传统文学进行价值评估,从而指导古典文学研究的问题上,建国初期是另一个重要的时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和“五四”时期相比,这又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如果说,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相应的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要任务,也是反对封建旧文化,是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那么,建国以后的主要任务则是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了。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学的价值评估自然也不同于“五四”时期。这使得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去总结“五四”时期的经验,调整研究的方向,相应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必然出现一种新的局面。这种新的研究局面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变破坏为建设,变批判为批判地继承,标志着人们在传统文化的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
“五四”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批判。当然,“五四”学人在对古典文学进行批判时,也并没有完全抛弃它,他们为要建设通俗写实的平民文学,也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寻找进化论的根据,他们把民间文学、白话文学和通俗文学奉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推崇它们的价值并对它们进行前所未有的研究,这本身也是一场文学观念上的革命。但是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那样,“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民主和科学,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反对党八股》)。“五四”以后,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种思想方法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的偏颇,开始以分析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于是,至迟到3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口号。如以明在《读了萨著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以后》一文中,就提到了当时流行的“批判地接受过去文学遗产”口号的问题,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讨论,就是对“五四”时期文化论争的一次深化,也是对传统文化态度的一次变化。例如在这次讨论中,由王新命等十教授所写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这篇文章中十教授提出的建设中国文化的态度就是“不守旧,不盲从,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由此可见,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问题,乃是人们在当时的中国现代化问题探讨中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
然而,30年代虽然有人提出了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口号,但是,究竟如何正确地对待文学遗产的问题在当时还没有解决。真正地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理论的,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曾有过相关论述。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了这样一段精辟的话:“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的以上论述,虽然是在战争年代提出,但是却是建国后我们对古代文学遗产批判地继承的纲领。之所以如此,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运动经验的总结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得出的,同时也由于时代的变化,是为完成和“五四”时期不同的时代使命而提出的。在这里,我们只要把毛泽东同志的以上论述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略加比较就可以看出。首先,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要解决的是打倒封建文化的问题,而毛泽东同志所论述的则是如何建设民族新文化的问题;其二,陈独秀在文章中把除了戏曲小说之外的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几乎全部否定,认为那些传统文学就是和“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的东西,而毛泽东同志则明确指出中国古典文学中有着丰富的优秀遗产,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其三,陈独秀的文章评价古典文学作品的标准是看其与社会文明进化有无关系,而毛泽东同志评价古典文学的标准则是看它是否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显然,这已经是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正因为如此,建国以后,当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事业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当如何对待古代文化,如何认识古代文化在现代文化建设事业中作用等成为人们重新思考的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一系列论述就必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指导纲领。
第二,在如何批判地继承的问题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思想。
如果说,以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来对待古代文化,是建国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与“五四”时期相比较所显示的最大不同之处,那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为指导,在对几千年的古典文学进行新的价值评估时建立了一个新的价值评判体系,则是建国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和三四十年代相比较所显示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这一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在这方面,建国后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做了大量工作,也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对一些错误的观点进行批评和斗争,如“全盘西化论”,狭隘民族主义者或国粹主义者的主张,“经济唯物论者”或者“唯成分论者”等。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一系列论述,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武装自己的头脑,逐步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古典文学研究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和“五四”相比,起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充分承认中国文学遗产中有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如詹安泰的《中国文学史》在开头就说:“中国文学史是中国三千年来整部文学发展的过程,其内容是非常繁富的。这笔非常繁富的文学遗产,不仅成为祖国珍贵的库藏,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其卓越的地位。”将之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及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五四”学人倡导“文学革命”的主要理论之一就是把几千年的封建文学,尤其是文人文学看成是“落后的”、“没有价值的”、“死文学”,这种偏激的文学史观在当时的提出固然有它的现实意义,但是客观地讲这种提法显然是不科学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也是不利于中国的新文化建设的。因此,承认几千年的中国文学中有着丰富的优秀遗产,乃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也是批判地继承的基础。建国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首先承认这一点,正是和“五四”评价体系的一个根本不同点。
其次是建立了一个新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点不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形式,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古典文学的内容。它坚持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个标准在今天看来有些过于强调政治,但是在进行革命建设的解放初期却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承认古代作家和作品具有阶段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对不同的作家和作品却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不是一概肯定或否定,主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看哪些具有民主性的精华,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正因为坚持了这样的批评标准,所以建国后的古典文学研究才得以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学深度上展开,对于上自《诗经》、屈原、司马迁,下至明清近代的戏曲、小说、说唱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深刻地揭示古典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政治性、社会性和人民性的本质方面和文学所具有的巨大的社会认识价值、思想教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使古典文学的研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者是比较科学地描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国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历史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对它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古典文学的评价问题。建国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们遵照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学遗产批判地继承的原则,建立起了一套以社会政治变革为经,以文体发展流变为纬,结合各个时代的文化思潮,以揭示文学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揭示各个时期文学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性为中心的文学发展规律和文学史理论体系,并描述了一条与此相关的文学史发展线索。其中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标志着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的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新的价值评估所致。它继承“五四”传统而来,也多方吸收了“五四”时期的积极成果。但是,它毕竟发生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另一个重大阶段,有着和“五四”时期不同的历史使命,所以在更多的方面它是超越“五四”的。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成绩,我们是不能轻易低估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学进行价值评估这一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就自然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批判地继承”这一口号本身只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人们比“五四”时期的学者对古代文化的认识又有了巨大的进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历史的进展,就逐步显示出这一理论的局限。早在50年代,学者们用这种理论解释文学史中的许多现象,在具体确定究竟哪些遗产应该批判或继承和如何去批判与继承的问题时,就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按当时学者们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方面,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都应该继承,这就提出了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另一方面,一切统治阶级的文学又应该批判,还应该坚持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的党性。显然,这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为调和二者,当时又从苏联引进了“人民性”的概念。但是,文学的阶级性、民族性、人民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同样也是说不清的。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上,特别是面对那些既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又深受广大群众喜欢,没有明显的政治思想倾向性的作品,如山水诗、田园诗、爱情诗等,更让人无法评说。对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家,也无法予以评价。举凡50年代关于文学史问题的重要讨论,几乎都陷入了这种无法解决的困境,无奈,只好以人民性来限制民族性,以阶级性来限制人民性,最终的结局自然是以阶级性取代民族性。这实际上说明当时敏感的学者已经不自觉地触及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完满地解决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批判”和“继承”民族文学遗产的问题。事实说明,建国以来,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个重大失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是一个还在逐渐发展的开放的体系,而是当作教条来对待,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必然要犯错误。这种极左思想的极端发展,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时候已经不再讲对传统文学的继承,而是对民族文学遗产的彻底批判了。这又是这一时期在对传统文学进行价值评估时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训。
20世纪末叶对传统文学价值的全面弘扬
我们这里所说的20世纪末叶,是指本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这一段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如何对传统文学进行新的价值评估,之所以再一次成为人们理论思考的热点,显然是伴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开始的。那个号称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破坏”,本来,我们党在解放初就早已制定的对待传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的政策,所以,在粉粹“四人帮”之初,在古典文学研究中首先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就是重申党的“批判继承”的政策,批判“四人帮”反对继承文学遗产的一系列谬论。
到了80年代初,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逐渐深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也逐渐从一开始时的现象批判发展为深究“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历史文化原因。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十年浩劫,固然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犯了错误,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不能超越自身的历史阶段。所以早在50年代,当我们在执行党的“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政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早自5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左倾思潮的恶性发展。1980年,邓绍基在《文学遗产》复刊第一期上发表的《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就对自建国以来发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系列“左”的错误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到“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一些历史文化因素,有助于我们了解建国以来中国“左”的文化思想发展的轨迹。但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早在建国前就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可是到了后来,这“批判地继承”却变成了全面的批判了呢?为什么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最激烈批判的时候,恰恰又是落后的封建文化死灭复燃到最可怕的时候呢?显然,这要求我们不但要追溯自建国以来就已出现的一系列“左”的现象,而且还要追溯这些“左”的现象得以出现的历史文化原因;同时也要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以调整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由此可见,80年代以来人们之所以重提对传统文学的价值评估,实在是中国人在总结了“五四”和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之后的又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是这场革命才使我们认识到传统并不是我们的身外之物,而是已经复制在我们身上的原初基因;传统也不是和现代相对立的一堵高墙,而是培育现代化成长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既不应该是“五四”式的反对,也不应该是把我们自己置身于传统之外的“批判继承”,而应该是把传统和现代水乳交融,是立足于传统土壤中广泛吸收现代营养的新陈代谢。我以为,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也是我们在几十年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问题的探讨中得出的最深刻的认识。
表面看起来,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并不像“五四”时期和建国以来那样和政治结合得那么紧密,似乎也没有展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问题的大讨论,但是它的发展却是与此紧密相关的。回顾近十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看到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研究者摆脱了建国以来的庸俗社会学的模式,也不再仅仅以政治评判为标准,以“批判地继承”为口号来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或肯定或否定的简单批评。他们正在把文学的社会批评扩展为文学的文化批评,把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深入到哲学、美学、心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领域,把探讨文学的民族文化传统、把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任务。
也许,对于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些发生在自己周围的变化还没有看到,他们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近十几年来对传统文学的价值评估正在影响着自己的研究。但是,只要我们翻一下近十几年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就可以明了这种新的发展趋向。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87年齐鲁书社出版了一本卢兴基主编的名为《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的书,用编者的话说:“本书列入的二十五题,俱属范围较大的全国性讨论。时间上,从建国以后的50年代开始到目前为止;涉及的面,从根本理论性的探讨到历来有分歧的具体作家作品研究。”可以说,这本书带有一定的总结性,它总结了发生在50年代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讨论,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再留心一下这本书出版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就会发现,这本书中所列出的二十五个题目,几乎再没有人展开过讨论。那么,是不是这本书中所提到的问题已经都解决了呢?不是,里面的大部分问题,可以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为什么从此以后人们不再关注这些问题了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问题大抵上都是以50年代的庸俗社会学为理论基础、以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批判继承”为研究方法而提出的。正因为这种理论和方法存在着缺陷,所以其中的一些问题用这些种理论和方法也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在80年代的学者看来,文学并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消极反映,它本来就具有自身的特点;而我们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也不仅仅要从政治上判定其进步或落后,还要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上,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比较文化学等各个方面去分析和研究。有了这样的观点和态度,我们今天再看五六十年代提出的一些问题,自然就觉得没有继续讨论的意义,当然也不会有人再去争论它。事实也是如此,这些问题在五六十年代虽然并没有解决,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新一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却不再关心它,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研究转向了新的方面。即便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在80年代思想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当然,我们说80年代以后中国人在对传统文学进行新的价值评估问题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并不是说这一时期就完全否定了“文革”之前的“批判继承”的理论。正如“批判继承”的理论是人们在反思“五四”精神后的一个进步的扬弃一样,80年代以来人们对待古代文学的态度也是对“批判继承”理论的一个进步的扬弃。它批判了五六十年代的庸俗社会学,也批判了当时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同时,它又吸收了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追求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时期的人比我们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有着更多的理解,也没有哪一个时期的人比我们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更清楚的认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知道,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换句话说,20世纪各个阶段之所以对传统文学的价值评估不一致,并不是由于人们在纯粹的思辨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而是因为人们在不同时期得出的认识都来自于对前一个阶段的实践的总结。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看20世纪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我们才能对各个不同阶段的研究给以客观的历史的评价,肯定它们在完成不同的历史使命时所做出的贡献;我们才能对它们做出客观的分析而不是主观的批判,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合理的扬弃。同样,也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才会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了自豪,同时也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把盲目的研究变成自觉的研究。一方面使我们的研究服务于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的研究提供我们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但是我们宏观把握本世纪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发展动向的根本,也是调整我们将来研究发展方向的思想主导。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古典文学论文; 陈独秀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 白话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