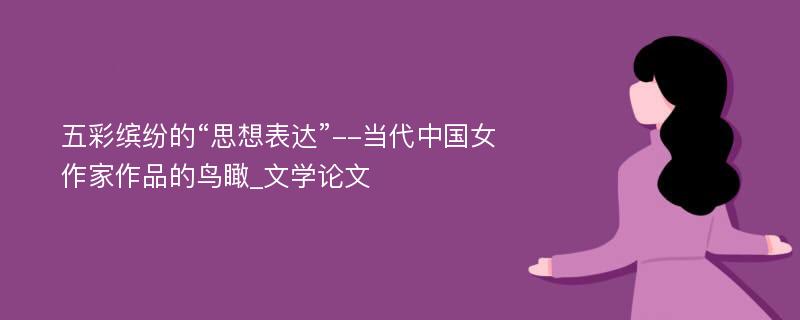
多姿多彩的“思想表情”——关于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的一次鸟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鸟瞰论文,女作家论文,多姿多彩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表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女作家的创作一直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正是这个时期繁荣的女性文学的一个侧面。它们不仅题材广阔,艺术探索也较活跃,所呈现的文学图象,色彩斑斓,煞是好看。
方敏《大拼搏》是篇动物小说,在整个集子里它是很独特的。方敏大学毕业后,曾在《小说家》杂志社当文学编辑,80年代后期去《中国林业报》任记者,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她把自己的创作视界,由反映知青生活转向对大自然的探索。90年代前期,当她在《新闻出版报》供职时,动物三部曲《大迁徙》、《大毁灭》和《大拼搏》就陆续问世了,并蜚声文坛。方敏写动物世界,不像有的作家那样,习惯于让动物体现人的意志和习性,把动物小说铺陈为关于人的命运的故事。恰恰相反,她善于客观地反映动物自身的生存原貌,呈现宇宙界的搏动和叹息;她还总是深情地弘扬生物界固有的生命情调,以表达她“以宇宙万物为友”的美好情怀。《大拼搏》写了中国历史上早有记载的鸟类——褐马鸡。这是一种高寒地带的野生动物,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山区林间,以寻觅野果、蚂蚁等为生。它们不仅要抵御恶劣的气候和缺食的饥饿;还要抵御许多异类——乌鸦、狐狸、豹猫、腹蛇和金雕的偷袭、侵犯和强暴。它们正处于频临灭绝的危险之中。方敏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指导下,按照褐马鸡原有的本性和行为方式编织它们求生存、抗毁亡的故事,结果,褐马鸡的“类”形象栩栩如生地挺立在我们眼前。《大拼搏》以褐马鸡两代头鸡——雄鸡长角、雄鸡长脖及其家属的命运遭际展开情节,其间,对褐马鸡在特定处境下的特定情态,刻写得尤为精彩。无论是摹写雄鸡长角带伤猛啄金雕的战斗场面,还是彩绘雄鸡长脖毅然呵护两族小鸡的义举;无论是呈现雌鸡凤尾失子后疯狂、昏死的图象,还是叙描雌鸡花翎啄食霉菌孵化后代的煎熬情景,作者笔触极富灵性,饱蕴着母性的对生命的礼赞和情思,使褐马鸡这个“类”形象富于诗意,给人以很多联想和思索。褐马鸡这个赢弱的动物种族,凭着对生命传承的强烈渴求,凭着对下一代的有效呵护,凭着不畏强暴的拼死精神,它们到底战胜了无穷无尽的劫难,适应了自然意志而幸存下来。无疑它们的生存意志对于我们人类,自有一股启发和催促的力量。方敏认为,许多野生动物对于“物竞天择”的体验要比人类多得多。她说:“假如文学不是站在人本身和人类文明史的角度,而是站在世间万物以及无穷时空的角度,去反映生命存在的意志,人类是否会得到更多的启示呢?”(见《红蟹的启示》)方敏站在大自然和人类的交叉口看取生命的新生和毁亡,《大拼搏》所呈现的生命景观,竟然是那样地辉煌和残酷,那样地坚韧和脆弱,那样刚强和颤栗,颇富悲剧的崇高感。方敏动物小说的视角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是令人赞叹和感佩的。
方方是位颇具创作实力的作家。她自从成名作《风景》发表后,总能不断地给读者带来新的惊喜。人们不会忘记,《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和《桃花灿烂》等小说在读书界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她的小说由于对社会生活能作出穿透性的逼视,在凡俗人生里赋予文化蕴含,同时对人性本真刻上复杂的印记,因而,读者从来不冷落她。晚近,她的《埋伏》受到欢迎,各选刊杂志转载,影视界为它拍片,反响又非同一般。《埋伏》的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迥异于她以往作品。这是部公安小说,叙述了两位民间治安人员——钢厂的保卫科长和干事叶民主,协助警方完成对罪犯侦察和破案任务的故事。在《埋伏》里,方方的叙述变得有点像通俗小说。她运用大量的直叙、闲笔和侧写手法,烘染这场“埋伏”的兴味、无聊和疲惫;她又不动声色地采取铺垫、悬念和奇峰突起等戏剧性手法,制造这场“埋伏”的悲喜剧效果。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又回味无穷的破案故事。科长和叶民主所在的埋伏点——鹤立山,是警方重案组组长杨高,凭一时的直觉冲动才设立的,过后,他对它并不重视,有关警方人员也都认为,在七个埋伏点中,鹤立山是“最不重要的”;21天后,当杨高让所有埋伏点撤离时,又是唯独没有通知到鹤立山,结果科长和叶民主在那里多埋伏了半个月时间。然而,正是这个被警方忽略,不屑的埋伏点,这个莫名其妙地被移长了坚守时间的埋伏点,使犯罪团伙首领——智者感到不解、困惑、起疑,最终导致他行动部署错位而落入法网。当然,方方没有把故事驻留于此,只作“形而下”的叙述,她聪敏地寓“形而上”意味于通俗故事之中,通过整体构思,使小说具有一种寓言的味道。有一些点睛之笔富有深意:如对忠于职守的科长之死的设计,如叶民主拒绝参加庆功会,拒戴破案功臣桂冠情节的铺叙,如叶民主女友在埋伏点铺撒野花的场面描写,都无不在唤起人们对生活中的愚弄的醒悟。《埋伏》将一种哲理意味和生活态度,暗藏在庸常琐碎的叙描之中,使雅与俗、形而上和形而下自然平易地融合在一起,它是方方进行艺术探索的新成果,值得重视。
90年代以来,毕淑敏佳作迭出,已成为当今文坛一位出色的后起之秀。也许因为她曾是个守卫在中国西部边疆的军人,又有过较长时间当医生的经历,在家还是位好妻子、好母亲的缘故,她的性格和作品都给人以刚柔相济的感觉,既豪迈开阔,又亲切温存。毕淑敏像许多作家一样,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写到死亡。晚近的《预约死亡》就是一篇集中摹写死亡和思考死亡的小说。之前,毕淑敏在名篇《阿里》、《女人之约》、《生生不已》里写几位女人公的死亡时,是让她们自觉地走向生命的结束,满怀深情地将人的尊严,人格力量,生命意识和母爱力量注入其间,使她们的死笼罩在人文精神的光环里,显得格外壮丽、肃穆和神圣。《预约死亡》却与它们有很多不同。该小说是作者采访临终关怀医院的医生和病人后的文学实录,展露的是普通人的正常死亡,艺术形式倾于散文化、散点式,而沉思的生死问题也广泛得多。当小说叙述人“我”(实际上也正是作者自己)带着我们走进北京一家临终医院采访的时候,我们很快被那里一个个干瘪枯萎的老人所震骇。中国人是忌讳谈论死亡的,她究竟想向我们说些什么呢?随着叙述人的引导,我们首先看到了对待将逝者的两种人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尔后,我们又发现了东西方民族相异的死亡观念。临终关怀医院确实是“文明世界的象征”,在它观照下,崇高、善良、文明的字样会变得分外夺目耀眼;卑鄙而虚伪、愚昧的行径也会显得格外地触目惊心。然而,该小说最动人心魄的地方,却是作者主动请求住进病房,以对“死亡”作真切体验的行动。病房的阴气、光线、墙壁、床垫、病友,无不在猛烈地敲击着毕淑敏的神经,她预约死亡的行动实在勇敢,倘若没有一点超凡入圣的殉道者的劲头,是很难以想像的。当毕淑敏径直走进那些将逝者最后心灵的时候,她的感受更加深切。她领悟了将逝者视“死亡”为一个过程的睿智,她看到了将逝者对生命达观的态度,她还注意到将逝者对死后的希望,实际上正是关于生命的延续和永恒的期盼。假如说,一个人通过回顾灾难(包括他人的灾难),能够提高接受命运挑战的勇气和力量的话;那么,像毕淑敏那样地去体验死亡,就会获得更多更深刻的有关生命的哲学。毕淑敏在创作谈《炼蜜为丸》中写道:“我已经超然。是死亡教会了我勇敢,教会了我快乐,教会了我珍惜生命,教会了我热爱老人”。毕淑敏创作的经常性主题是,对人的深度的关怀和对生老病死生命现象的深入思索,《预约死亡》把这个主题引入了一个新境界。
《棉花垛》、《浪漫的黄昏》、《爱又如何》和《红羚》等四篇小说与上述小说不同,都是表现或涉及爱情生活的,属另一类题材,另一派风光。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爱情题材的创作发展较快,而女作家的先锋作用也尤为突出。是女作家率先使爱情小说从以往政治文化模式中走将出来,而具独立意义,是女作家成功地突破“五四”以来爱情创作的圣洁模式,注“性”因素于婚恋题材之中;又是女作家站在女性本位立场,伸张女性在爱情中的权利和自由,呼出了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抗争之声。然而,80年代后期以来,爱情题材创作出现了某种曲折。过分的肉欲、官能、性刺激的物质性描写,使这美好题材存在向性本能滑落的危险;而个别女作家过分的私人化写作,也存有使女性文学成为男性社会窥视对象而被物化、商品化的危险。本集收入的四篇婚恋小说都创作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成熟的背景之下,女作家们对爱情问题的思考日趋沉着,未跌入非理性主义怪圈,因而,她们的爱情篇章有益于认识社会、人生和人性,影响积极。
《棉花垛》是铁凝的作品。铁凝是位优秀小说家,擅长摹写女性世界。80年代中期以来,她改变了创作初始单色纯情的笔触,使女性视角和思考日益丰满和成熟起来。《棉花垛》正是她铺写女性生存及其命运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棉花垛》所展开的三个农村妇女——米子、乔和小臭子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之前和之中。这些故事似乎离我们很远,但它们毕竟真实而催人深思。米子的故事,折射了某些传统妇女的生存方式和命运。她青年时代美丽诱人,但从不下棉田劳动,专靠秋日“钻窝棚”同男人睡觉,以换取棉花养活自己。后来,她只得同一个鳏夫成亲。她没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只有对男人的取悦和依附。小臭子是米子的女儿,乔是小臭子的女友。她俩的故事自始至终不宜分开。俩人后来虽非属同一个政治营垒,但俩人最终竟遭遇相同方式的毁灭。她俩的毁灭呈现了男权文化所酿制的女性命运的永恒困境。乔和小臭子在少年时代一起玩耍,甚至一起同男孩子做性游戏。长大后,俩人一起上抗日夜校,行抗日打扮。但乔成为了抗日干部,恋上抗日队伍里的同志——国。而小臭子抵挡不住物质诱惑,同汉奸鬼混,并出卖了乔。后来,乔被日本鬼子轮奸后惨遭杀害;小臭子呢?她在被国押送到县里听审的路上,先被国所占有,后再被国所枪毙。一个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鬼子先奸后杀,一个非正义的小臭子被正义的国又是先奸后杀,这实在太令人震惊了。然而正是这一笔,铁凝揭开了男性世界对女性强暴式的占有欲和征服欲,呈露了他们对女性残酷蹂躏的性文化态势。原来世界上男权文化都一样地视女人为肉欲对象,而要任意地拥有和享用她们。铁凝是当今中国文坛上敏于女性性心理,谙于人类性文化的一位作家。她的《棉花朵》不仅驾轻就熟地铺衍了三个女性的性心理对其行为的驱动关系,更为成功的是,她把男性霸权主义文化放在战争背景下予以揭示、突现,对男权文化的针砭机智而有力。我以为,将它置于女性文学经典之列,是不为过的。
叶文玲也是位富女性意识的作家,以探索人性美、人情美著称。她创作初始的爱情小说也惯于作至情纯美的吟唱,倾于温情主义。然而,《浪漫的黄昏》不同。该作通过社会转型初期两代人爱情观的冲突,呈现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性信息,环顾女性存在发生变化的文化景观,内涵变得丰腴和深沉起来。《浪漫的黄昏》里的母亲尹如婵,是位在旧中国历尽沧桑的老艺人,然而,她到底在改革开放年代得到心上人的爱情,黄昏岁月,让爱情之舟荡漾在轻波上。作者对这个人物,倾注了很多爱意,写起来也轻车熟路,在融融乡情和款款河水里,烘染了她苦难的身世和黄昏的恋情。于优美意境中突现出来的尹如婵具典雅之美,令人钟爱。女儿尹卉,可是位时髦的女商人,一家公司副经理。她有过糟糕的婚恋史,也痛恨那些欺辱过自己的男人;但她毕竟识得商场上的事务,不惜利用自己单身女人的性别优势,赢得生意场上的胜局。在她看来,单身女人在生意场上才能发挥其魅力和光彩,倘若结婚,反会贬值。尹卉关于婚恋观的大胆表白,展示了当今商品社会的爱情生意经。作者对尹卉这样的人物,于80年代中期尚属陌生,但她如实地描摹她,并注入自己的思考。小说结尾,作者安排尹卉为她母亲办寿宴的情节,通过母女俩人对寿宴的不同态度和做法,透露了商品社会对人情美、人性美的消蚀和异化作用。这样的写法,表明了叶文玲对现实生活变迁的贴近和敏感,是难能可贵的。
最近几年,张欣因为成功地刻写城市爱情和城市女性而得到文坛和读者的青睐。她常常以爱情为支点,揭示城市的物化世界、世俗利益对人的灵魂的影响和对情感关系的耗损;又总是以女性为主角,披露她们被围困、被扭曲、被牺牲的状况,从而期待都市的人们灵魂得到安顿、都市的女性生存价值得到重建。《爱又如何》是她很有影响的一个作品。《爱又如何》中的女主人公可馨原本是个幸运儿,是商品大潮把她的生活颠簸得乱作一团,家庭和事业的风帆全被撕破,她活得比在她家当过保姆的菊花都不如。可馨是按照传统的道德规范,是非原则去处事待人的,但事事败北、未获好果。爱情是她最后的停泊地,但同样被物化世界挤压得疲软、蹋陷,她不能不哀叹“爱又如何”。至于可馨的好友爱宛,从表面看,她比较适应工商社会,是商界瞩目的一颗新星。她荣任一家大商厦的经理,风月场上也不示弱,投入了两个男人的怀抱。但实际上,爱宛是带着孤苦的身世和创伤,生活在繁华世界的。寂寞使她渴望得到异性的关爱,孤独逼她独自去舔平自己的伤口。结果,她既无法抵住那品味低俗的“诗人”的诱惑,也舍不下那个在财力上给过她支持的烟老板的旧情。她过的是并不“纯粹”的生活,她没有家庭,没有亲人,谈何幸福?张欣并不在意自己的小说是否能成为人们人生的教材,而乐于以自己的城市人的故事,去为奔逐在生活兢技场上的人们“透透气”(张欣语),给他(她)们以精神上的松驰和抚慰。因而,她的小说在艺术上尤为舒展,人物性格复杂但保持适度,故事情节曲折但情调温馨,语言流光溢彩但自然流畅,能把深刻的道理明白化,通俗化。《爱又如何》正是这样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得很得体的小说,给人以舒心缓意的惬意感。
杨泥的《红羚》是这本集子里唯一的短篇小说。它虽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但红羚这个人物塑造得奇特诡秘,给人留下颇耐咀嚼的印象。红羚的少女时代被一桩同男孩毛哥“幽会”的谣言所追逐,她一直背着“坏女孩”名声随母亲四处搬家,备受冷遇。在大学里,她与男同学周乔发生了一次性关系,周乔对此事持漫不经心的态度,红羚对此事也没有留下太多的刺激和感觉。后来,她办起一家小公司,一位雇员李一,在走进她办公室的同时走进了她的家门,俩人随遇而结成夫妻。成婚后,李一对红羚顺从、照料,甚至对所有发生在红羚身上的事情,都持“没有意见”的容忍态度,什么毛哥、周乔、总经理,他全不理会。他常沉默,但这沉默就是真正的理解吗?他常“付出”服务,但这“付出”就是真正的爱情吗?俩人没有激起过真实的感情火花。红羚感到同李一生活在一起,有一种茫然的感觉。爱情的不幸,在于它不曾存在。婚后,伤痕累累的红羚对爱有过朦胧的期待,但李一没有醋意,没有愤怒,没有激情的姿态,让她如何处之?她陷入的是真正的不幸。杨泥对红羚这个人物心理发展的处理,没有在她阵痛痉挛的时候戛然而至,而是继续披露她人格深层失落,人性深度弱化的趋势。不是吗?当红羚领悟到与李一的关系已经“彻底完了”的时候,她的心反而轻松下来,感到眼前敞亮,她还预感到未来不会有什么变化,一切会照旧下去。作者采用冷调子但却具有张力的叙述,以及通过环境烘染人物的手法,来写红羚的心理传奇,沉着而含蓄地展示红羚这类人(包括周乔、李一等)什么都无所谓,都不经心的生态和心态,相当令人回味。红羚和她伙伴们的悲剧根源,不全在于他(她)们无奈的命运,而更在于他(她)已经或正在丧失生存的意义和目标。红羚是当今文坛上尚不多见的艺术形象,而小说《红羚》则是杨泥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标界。
我很欣赏铁凝关于小说的一种说法。她认为,小说表达的思想圈是有限的,但小说家创造“思想的表情”可以很有力度、很丰富(见《优待的虐待及其他》)。七位女作家的心灵气象万千,她们在小说里对生命、爱情、世俗、人性、人文精神的思考和表达,却是那样地多姿多彩而具中国特色和情调。我愿为她们祝福,祝愿她们的小说能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祝愿她们创造出更多更精湛的“思想的表情”,在文学这个永恒事业中取得更大进步。
注:本文是作者为《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六)》所写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