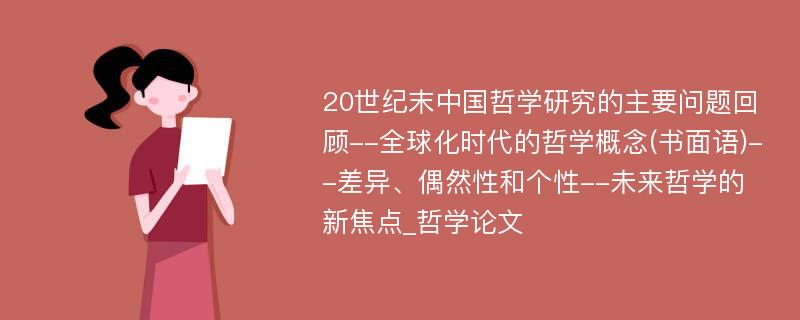
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十——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笔谈)——差异性、偶然性和个体性——未来哲学的新的聚焦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体性论文,笔谈论文,偶然性论文,差异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观念和以“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新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对传统哲学的主导性观念的颠覆,近年来大家都在关心和讨论一个问题:未来哲学的发展趋向是什么?无庸讳言,替未来哲学画像,就像替未来社会画像一样,是一项风险很大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画得越具体,被证伪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以比较抽象的方式来谈论未来哲学的发展趋向也许是比较明智的。本文无意对未来哲学的总体走向做出全面的预断,只是就未来哲学可能关注的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求正于方家。
本文认为,在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同一性、必然性和总体性一直是主导性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未来哲学的发展中却可能被边缘化,而在传统哲学的研究中本来处于边缘化地位的一些原则,特别是差异性、偶然性和个体性却可能在未来哲学的发展中再度上升为受宠的主题。之所以说是“再度”,因为这些主题在哲学史上早已得到某些哲学家的关注。然而,由于时代条件、理论视域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这些主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或许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些主题引起普遍重视的机会才真正来临了。下面,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些主题,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差异性
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中,智者派起着思想启蒙的作用。他们强调的是差异性、多样性和感觉的可靠性。苏格拉底起来驳斥智者派,他的学生柏拉图则从哲学上总结了他的老师与智者派之间的争论。在柏拉图的晚期著作中,特别探讨了“一”与“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里的“多”也就是差异性、多样性。黑格尔指出:“这种相异者、‘有’与‘非有’、‘一’与‘多’等等的结合,因而并不仅仅是由‘一’过渡到对方,——这乃是柏拉图哲学最内在的实质。”[1]
在智者派和柏拉图之后,莱布尼茨也是一个十分重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学者。据说他在宫庭中提出了著名的相异律,即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见解时,宫庭中的卫士和宫女们纷纷走入御花园中,试图找出两片完全没有差异的树叶,以驳斥他的相异律。黑格尔嘲笑了卫士和宫女们的浅薄,在他看来,相异律是无法加以否认的,甚至人们在强调事物的同一性时,也蕴含着对相异律的认可。
黑格尔这样写道:“当知性对于同一加以考察时,事实上它已经超出了同一,而它所看见的,只不过是在单纯差异或多样性形式下的差别。假如我们依照同一律来说,海是海、风是风、月是月等等,那么,这些对象在我们看来,只是彼此毫不相干的,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同一,而是差别。”[2]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人们说“海是海、风是风、月是月”时,也就等于说,海不是风,风不是月,月不是海。换言之,海、风、月之间是有差异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强调同一性也就是强调差异性。当然,黑格尔注重的不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外在差异,而是同一事物之中的内在差异,即矛盾。所以他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2]黑格尔还辛辣地嘲讽了以谢林为代表的、排斥差异性的“同一哲学”,认为在这种哲学中,就像黑夜看牛一样,什么也看不见。
尽管黑格尔高度重视差异性,强调“同中有异”,但在他的哲学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在其“绝对精神”的概念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在哲学史研究中,黑格尔坚决反对哲学史家们只看到历史上不同的哲学流派和人物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相互推翻的现象,他指出:“这样的哲学史家有点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和谐和性,却没有透进它们的头脑。”[3]诚然,黑格尔也主张要看到不同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差异性,但他更注重的则是这些有差异的思想的“一致性和谐和性”。所以,归根到底,黑格尔哲学仍然属于“同一哲学”的范围,他和谢林的区别是:谢林不承认同一包含着差异,而他则强调同一蕴含着差异,但他们的共同之点都是对同一性的倚重。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西方哲学对同一性的倚重在当代世界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从其“此在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揭示出传统哲学崇拜同一性的起因:“从其基本音调来听,同一律所说出的东西正是整个西方-欧洲思想所思的东西,这就是:同一性的统一性构成了存在者之存在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无论我们在何处和如何对待哪一类型的存在者,我们都感到自己已被同一性所呼求(angesprochen)。倘若这一呼求(Anspruch)不说话,那么存在者就决不能在其存在中显现。”[4]海德格尔敏锐地发现,传统哲学向同一性的呼求,实际上就是向存在的呼求。但在他看来,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性弊病却是对“本体论差异”的遗忘。所谓“本体论差异”也就是“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差异。由于传统哲学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把“存在者”误认为是“存在”,从而导致了对“存在的意义”的遮蔽和遗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德格尔正是通过对差异性的强调,走出了传统哲学的藩篱,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也高度重视对差异性问题的研究。众所周知,在法文中,名词différence解释“差异”,为了赋予这个词以更多的含义并使之与黑格尔所强调的差异区分开来,德里达把这个词改写为différance(中文通常译为“延异”,以示与différence之区别),并解释道:“我将力图区别延异(différance中'a'表示它的生产性和冲突性的特征)和黑格尔的差异,因为黑格尔在《大逻辑》中将差异规定为矛盾,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要解决它、内化它并将它上升(按照思维辩证法的三段论过程)到本体-神学,或本体-目的论的综合的自身在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确切地加以区分。延异(在绝对接近黑格尔的某点上,像我在讲演中的其他地方所强调的那样:在此,最关键的东西在胡塞尔称为‘细微差异’或马克思的‘显微学’中变得毫无用处)必须表示出与‘扬弃’系统和思辨辩证法决裂的那一点。”[5]在德里达看来,他和黑格尔虽然都强调差异性,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在黑格尔那里,差异乃是矛盾的一种别称,黑格尔总是通过其思辨辩证法,尤其是“扬弃”的方式,消解掉差异性,使它回归到绝对精神这一包罗万象的总体性中去。而德里达则反对这种同一性和目的性,认为延异就是一切存在者的原初的存在方式,它是既不能被消解,也不能被扬弃的。德里达也把自己的“延异”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区分开来。他写道:“延异不是本体论的差异的一个‘种类’。”[6]
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主要有如下三层含义:第一,差异;第二,时空上的延缓或间隔;第三,“'différance'(延异)中的'a'所包含的积极性或生产性在差异游戏中指涉生成运动”[6]。这就是说,延异使事物不会停留在一个封闭的结构或系统中,它本身蕴含着一种解构系统的破坏力量和生成能力。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十分强调“他者”(the other)的作用,而对于“自我”(self)来说,“他者”也就是一个异在,即一个异己的存在者。所以,“他者”这个词本身就是差异性的一种体现,它表明自己就是一种原初的存在物,不可能被“自我”吸纳和同化。这个“他者”概念在政治文化上的含义是:如果把西方文化理解为“自我”的话,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就是“他者”,“他者”有自己存在的权利,不可能被还原和同化到西方文化中。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西方出现了“差异政治学”(politics of difference),强调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容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传统哲学的同一性原则将为未来哲学的差异性原则所取代。当然,同一性仍然有它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没有同一性,差异性也无法存在,但它的作用和意义必定会被边缘化。
偶然性
关于偶然性问题的思考同样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那里。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著名哲学家》一书中介绍古希腊原子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思想时,这样写道:“一切都由必然而产生,涡旋运动既然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这在他就被称为必然性。”[7]不用说,德谟克利特的这种观点必定会导致宿命论或决定论。他的学生伊璧鸠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写道:“被某些人当作万物的主宰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宁肯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性。”又说:“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短而易走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而对必然性本身加以制约倒是许可的。”[8]伊璧鸠鲁坚决地驳斥了他的老师所主张的必然性的理论,他通过对原子偏斜运动的强调,阐明了偶然性的重要地位,从而在古代必然性理论的铁笼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伊璧鸠鲁的研究成果引起了青年马克思的高度重视。他在《博士论文》中力排众议,明确地指出:“德谟克利特注重必然性,伊璧鸠鲁注重偶然性。”[8]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偶然性构成伊璧鸠鲁哲学的主导性原则,这一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肯定了自我意识和自由的重要性。然而,青年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的思想却没有引起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的充分重视。下面这段话就是一个明证:“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对立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一般说来,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9]按照这样的说法,在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始终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偶然性的作用则始终是边缘性的。
我们发现,在这里有一种向德谟克利特式的必然性理论返回的趋势。这或许可以说是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最经典的表现。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就说过:“一切宗教,差不多一切哲学,甚至一部分科学,都是人类孜孜不倦地作出努力以坚决否认自身出现的偶然性的明证。”[10]莫诺通过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只有偶然性才是生物界中每一次革新和所有创造的源泉。进化这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是绝对自由的、但又是盲目的纯粹偶然性。”[10]莫诺还举了下面的例子来说明生活中偶然性的作用:假定勃朗医生到一位危急的病人那里出诊去了。与此同时,承包工琼斯已出发去紧急修理附近一座大楼的屋顶。当勃朗医生走过大楼的时候,琼斯正好一个不小心把他的榔头掉了下来。榔头落下的“弹道”正好同医生走的路线相交,于是医生的脑袋就被砸碎而死于非命。“我们说,他是偶然性的牺牲品。难道还能有别的说法适用于这种无法预见的事件吗?在这里,偶然性显然是本质的东西,是完全独立的两条事物因果链所固有的,而在它们的交叉点上造成了意外事故。”[10]在莫诺看来,偶然性不仅常常在自然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实质性的、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个概念从根本上摧毁了人类中心论,尤其是人类在目的论方面所做的种种设定。在某种意义上,莫诺的研究成果复兴了伊璧鸠鲁和青年马克思提出的哲学主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无论是休谟还是莱布尼茨都早已对感觉经验知识的或然性做出了论证。莱布尼茨说过:“感觉对于我们的一切现实认识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足以向我们提供全部认识,因为感觉永远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例子,也就是特殊的或个别的真理。然而印证一个一般真理的全部例子,不管数目怎样多,也不足以建立这个真理的普遍必然性,因为不能得出结论说,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将来也永远会同样发生。”[11]比如,许多民族的人都认为昼和夜是在24小时内相互更替的,并认为这条规律适应于所有的地方,但在北极圈内这个规律就完全不能适用,因为它在夏天是有昼无夜,在冬天则是有夜无昼。莱布尼茨由此而发挥道:“诚然理性也告诉我们,凡是与过去长时期的经验相符的事,通常可以期望在未来发生;但是这并不因此就是一条必然的、万无一失的真理,当支持它的那些理由改变了的时候,即令我们对它作最小的期望,也可能不再成功。”[11]事实上,莱布尼茨明确地告诉我们,与经验有关的任何知识都缺乏必然性。而休谟则从归纳的局限性上阐明了同样的道理,因为任何经验知识都是在归纳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归纳的实例不管如何多,也不可能使经验性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
正如当代哲学家波普尔告诉我们的:“从逻辑的观点看,我们从单称陈述(无论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来,显然是不能得到证明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到的任何结论,结果可能总是假的。不管我们已经看到多少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12]在波普尔看来,不管经验中的实例如何增加,都不能使经验命题成为全称命题,即成为必然性的陈述或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除了演绎逻辑和数学外,人们根本就不能在经验生活中使用“必然性”这一概念。如果他们一定要保留使用“必然性”这个提法的话,那么这个提法所表示的不过是“高概率的偶然性”,即出现频度较高的偶然性而已。这就启示我们,取代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新观念应该是:在经验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存在的只是偶然性,或至多不过是“高概率的偶然性”而已。谁能向我们证明,1968年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是必然的呢?谁又能向我们证明,1989年苏联和东欧的“政治风暴”是必然的呢?正如莫诺告诫我们的:“人类至少知道他在宇宙的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是孤独的,他的出现是偶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王国在上,地狱在下,人类必然作出自己的选择。”[10]
总之,只有走出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必然性”理论的铁笼,返回到伊璧鸠鲁、莱布尼茨、休谟、青年马克思、波普尔和莫诺等思想家那里,重视对偶然性的思考和研究,生活世界的真理才会向我们涌现出来。我们确信,未来哲学将会把偶然性的问题放到自己的王座上。
个体性
人所共知,个体性问题是和经验生活中的人的存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从外观上,即从身体上看,每个人是以个别的方式存在在世界上的,但真正的个体性指的并不是人在身体上的独立性和个别性,而是指人在政治法律上的权利和精神世界的、普遍的独立性。每一个熟悉人类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直到近代西方社会,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性才产生,并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得到了初步的表现。莱布尼茨在《单子论》中写道:“如果我们愿意把一切具有刚才所说明的一般意义下的知觉和欲望的东西都通统称为灵魂的话,那么,一切单纯的实体和被创造出来的单子就都可以称为灵魂。”[13]莱布尼茨认为一切单子都是有灵魂的这一思想,一方面暴露出他的泛神论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的看法始终是以近代社会中的、真正个体化了的人作为范本的。所以黑格尔指出:“莱布尼茨的基本原则却是个体。他所重视的与斯宾诺莎相反,是个体性,是自为的存在,是单子。”[14]
在莱布尼茨之后,对个体性的原则大力加以弘扬的是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对群众抱着天然的敌意,他认为真理不仅是主观的,而且唯有孤独的个人才能加以体悟,他甚至在生前给自己写下了墓志铭“这个个人”(the individual),所以宾克莱评论道:“尤其重要的是,克尔凯郭尔强调个人,强调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存在的关注,强调以狂热的献身精神使自己委身于一种生活道路,这一切都是他对那些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而寻求指导的人所作的伟大贡献。”[15]事实上,马克思作为克尔凯郭尔的同时代人,也对个人和个体性予以高度的重视。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阐述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时曾经这样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die universelle Entwicklung der Individuen)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freie Individualitaet),是第三个阶段。”[16]马克思这里使用的Individuen(个人)和Individualitaet(个性或个体性)表明,他始终把独立的个人和个体性理解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然而,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那里,马克思对个人和个体性的重视却被掩蔽起来了。这些教科书通常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设立一章——“人民群众与历史人物”来讨论个人问题。正如有的教科书所说的:“在个人中,按其对历史影响的大小,可以分为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9]在这里,“普通个人”是从属于“人民群众”的,他不过是“人民群众”的一个片断、一个因子,仅此而已,而“历史人物”作为伟大的个体,则是与整个“人民群众”相对峙的。换言之,唯有“历史人物”才是真正受重视的个人,而“普通个人”则是微不足道的,他只是通过“人民群众”这个集合性的概念获得了抽象的、似是而非的意义。说得刻薄一点,人们通常以为自己在谈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
所以,当代法国哲学家萨特强调,在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已经出现了人学的空场,他试图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以恢复“普通个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等都充分肯定了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和不可取代性。比如,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到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如果能做些事情的话)。”[17]正是基于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诺齐克提出了“最弱意义上的政府”(a minimal state)的新概念,主张政府的权力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有限的功能。在当代哲学中,不仅个人的政治、法律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甚至连知识的个人化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迈克尔·波兰尼的《个人知识》一书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就是一个明证。总之,按照笔者的看法,未来哲学对个人和个体性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而与这种个体性相对峙的、在传统哲学中备受崇敬的总体性原则则将退出舞台的中心。
综上所述,随着耗散结构理论、非线性科学、混沌学、大爆炸宇宙学等新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现和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解构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发展,未来哲学将进一步脱离传统哲学重同一性、必然性和总体性的思维轨迹,过渡到对差异性、偶然性和个体性的倚重上。事实上,正如同一性、必然性和总体性相互支持、相互贯通一样,差异性、偶然性和个体性也是相互支持、相互贯通的。无数事实表明,能以宽大的胸怀容纳差异性的人,一般说来,其思想也不会屈从必然性的铁笼,心甘情愿地在这一铁笼中枯萎下去;与此同时,他们也不会俯首听命于总体性的专横的话语,而会以盖着生命和鲜血的印章的个体性冲决总体性撒下来的罗网。在笔者看来,这些原则一旦成为未来哲学的主导性原则,整个未来哲学将会改弦更辙。
标签:哲学论文; 莱布尼茨论文; 同一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必然性与偶然性论文; 哲学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