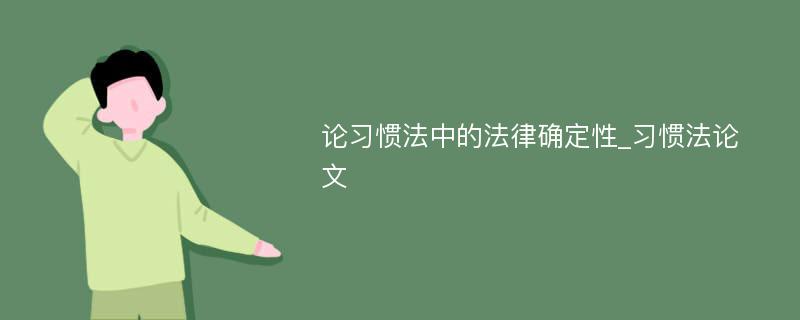
论习惯法中的“法的确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习惯法论文,确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11)01-0023-06
民国二年,大理院发布判例规定:“凡习惯法成立要件有四:(1)要有内部要素,即人人有法之确认心。(2)要有外部要素,即于一定期间内就同一事项为同一行为。(3)要系法令所未规定之事项。(4)要无悖于公共秩序、利益。”[1]该司法判例所确立的习惯法的成立要件的第一项即“人人有法之确认心”,在民法理论中简称为“法的确信”。“法的确信”在民法和国际法中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那么,究竟何谓“法的确信”、其实质意义是什么,以及法官在司法中如何发现“法的确信”?这些问题牵涉到“法的确信”理论的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大陆法传统中的“法的确信”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上述大理院判例起源于大陆法传统。在大陆法的“习惯→习惯法”的跨越中,“法的确信”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以英格兰为代表的普通法系,“法的确信”理论在法官、律师或者法学家中根本没有被审慎关注过。[2]在大陆法系传统中,习惯通常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人们的普遍惯行或者惯例,以及法律所要求的人们对此惯例的普遍确信。后一种因素即“法的确信”,离开“法的确信”,惯例只可以作为考察当事人意图的线索。[3]所以,“法的确信”理论主要是大陆法系判断习惯的司法适用性的标准,而普通法法官则主要适用另外一套由一系列要素构成的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
从根源上讲,“法的确信”理论源自西欧历史上的“人民创制法律”的观念。在《优士丁尼学说汇纂》中有这样的记载:“根深蒂固的习惯应当被当作制定法遵循,这就是所谓的经由惯例确立的法律。因为,既然制定法约束我们的唯一原因乃是因为其被人民的一致意见接受,所以,理所当然的是,那些人民经过非书面同意的东西也约束所有人。因为,人民通过投票还是通过实际行为和行动表达自己的意愿并无实质不同,因此,下述结论也是公认的:法律不仅可以由拥有提案权的人通过投票废除,而且可以通过众人的一致同意不运用而废除。”①很显然,习惯之所以变成法律乃是因为人民接受其为法律。[4]这种理论倾向经过罗马法的复兴而被学者重新诠释和继受,成为大陆法系习惯法构成要件的通说。
现代德国学者拉伦茨认为:“认定存在习惯法与否,关键不是看实践,而是看它是否具备了‘必要的确信’,即人们是否普遍认为它是正确的。”[5]17根据“法的确信”理论,当习惯被共有同一法律制度的人们确信为法律、接受为法律并践行为法律时,习惯就成为法律。如果人们通过一系列持续重复的行为接受了惯例,那么“法的确信”与惯例这两个要素就结合在一起,法律在此时间点上就被创造出来。[3]从纯粹推理的角度来看,上述论述似乎很圆满,我们看不出“法的确信”理论内涵的历史变化。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现代学者讨论“法的确信”问题的前提变了:拉伦茨是在判例的基础上探讨(作为实证法的)习惯法的形成基础,也就是说,他所谓的习惯法在实质上乃是法官借助习惯规范创造出来的“法官法”,而这种法官法与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中创造的习惯法有很大不同。[6]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面临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习惯规范的司法适用性基础。即,在并不存在判例的情况下,法官如何判断人们对某个习惯规则具有“法的确信”,从而该习惯具有正当性并具有司法适用性,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显然,上述民国时期的判例中,法官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形。当判例积累起来以后,再判断是否存在习惯法时,才涉及到拉伦茨等人所论及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影响“法的确信”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改变,从而在当下,能够称为“习惯法”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在法制史中,习惯乃是法律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渊源,前现代的法官可以径直援引习惯判案,因为当时的法官有权这么做,故而经由“人民的默示同意”所形成的习惯规范在历史上可以直接称为法律,这在当时不会产出任何疑问;而在现代分权学说影响下的欧洲,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取消了此种特权,立法权专属于立法机构,而民间的习惯则需要经过认可才能成为法律。我们现在的困难在于,民法理论将历史上存在的习惯法和当下经判例确立的习惯法统称为“习惯法”,从而在概念和术语上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事物,这造成论述和理解上的困难。
所以,在现代法律实证主义观念影响下以及立法和司法分权的前提下,使习惯成为规范的因素与使习惯成为法律的因素是不同的,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之间的区分非常重要。我们首先分析“法的确信”蕴含的义务观念对形成习惯规范的意义。
二、“法的确信”与习惯的规范性
民间习惯作为客观存在,只是一种社会事实,从这种社会事实中是如何推导出规范性的?从客观存在的作为社会事实的行为模式中如何产生“应当”?其内在的机制是怎样的?如果裁判需要说理的话,那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就成为法官运用习惯规范进行裁判时说明裁判理由的一个重点和核心。“法的确信”理论充当的便是法官的说理工具。“法的确信”理论涉及到习惯的规范性,即人们遵守习惯规范的义务感的来源[7],“某人可以说,惯行必然是共同体的‘法的正当性信念’或者‘法的普遍确信’的表达,只有假定他很清楚这种‘法的正当性信念’或者‘法的普遍确信’并非一种‘纯粹的心理事实’而是(一种法律命令的行为的)‘履行某种规范的意识’,发展自或扎根于共有同一法律的人们基于自身的判断而进行的个体行为中。”②当相关共同体的人们就某问题上存在义务观念时,法官可以据此判断存在某种习惯规范。
按照凯尔森的界定,所谓规范就是“应当”,即按照一定的标准,社会主体应该做的事情。“规范”这个词的意思是:某些事情应当(ought)存在或者应当(ought)发生,特别是某个人应当以某种方式行为。此处的“应当”应作广义理解。按照习惯用法,“应当”这个词仅对应着一个命令,“可以”意味着允许,而“能”是指一项授权。但此处的“应当”用来表达指引他人行为的某些人的特定行为的规范意义。这个“应当”包括“可以”、“能”。[8]4-5规范是一种应当(ought),但表达意志的行为则是一种事实(is)。“应当”是每一个针对他人的行为表达意志的行为的主观方面;但并非每个此类行为都具有客观意义;只有当这种表达意志的行为具有客观意义时,这个“应当”才是一个规范。如果“应当”也是该指示行为(act)的客观方面的意义时,则该指示行为(act)所指向的行为(behavior)就被视为应当做的事情,不仅在做出指示的人看来是如此,而且指示所指向的人也认为如此,甚至与二者无关的第三人看来也是如此。[8]7-8“应当”代表着义务观念,对习惯的“法的确信”即意味着习惯规范中的“当为”观念的产生。
习惯形成和变迁的历史证据已经不可追寻了,但是,理论上的重述还是可能的。“法的确信”理论便是在面对一种社会既定事实的基础上给出的一种假定;这种理论并不是要重述历史,而是对既定事实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与“法的确信”理论密切相关的是“模仿”理论。“模仿”因素在“已为”向“当为”的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曾被严重忽视。“模仿在任何个体或者社会的生活中都是最为普通并且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我们的行动更多的是纯粹模仿性的,而纯粹理性的行为则比较少……在普通事务中不特立独行——遵循既定的行为模式——至少是一种安全方面的保证。因此,通过自身的循规蹈矩,我们往往会轻易地相信背离老套路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反社会的。这种信念多数不是建立在对终极的对错的确信上,而仅仅是建立在惯习的基础上。”[9]所以,这种行为的重复性毋宁是一种人类惰性的产物而不是理性的结果。这就是所谓从众心理,即“随大流”。上述分析中已经包含了一种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而对他人行为的评判,即如果别人不遵循既定的模式,则自己对此人的评价就是否定性的——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反社会的——因此,就会给其贴上一个标签:“异端”。这种贴标签的倾向意味着在常态和异端之间划定界限,划定界限的过程同时就是对作为常态的行为模式形成“确信”的过程。
社区共同体的公共舆论和公共裁判机构对“应当”的产生和维护起了决定性作用。社区公共舆论事实上就是一种交叉的评价:自己对他人的评价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习惯的产生是一个同义反复,因为习惯的规范性的含义即社会舆论将其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因此,我们是在探究一个“点”,这个点既是“法的确信”产生的时间点,也是行为的模仿累计的量的点。这个过程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循环解释。当我们切入到这个循环解释中寻找习惯的规范性产生的起点时,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认为:社区舆论乃是产生习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社区舆论是“法的确信”的外在表现。舆论是产生习惯的催化剂。在社区舆论中,有一种特殊的机制即第三方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这种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在小社区中、在较为落后的部落社会中,乃至一些小国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某种纠纷出现得足够频繁,而同一裁断者通常达成相同的处理结果,那么一项习惯可能就产生了。③这是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来看习惯产生的原因,这种第三方裁断者的裁决意见往往会促进社区共识的形成,所以,这可以视为产生“法的确信”的一个环节。“应当如此行为”,当公共舆论的话语结构中包含着一种清晰可辨的行为模式时,“法的确信”进而习惯的规范性事实上就产生了。
三、从公众的确信到法官的确信
公众对习惯规范的“法的确信”对于法官识别和适用习惯规范具有核心意义。但在现代语境下,将习惯变成习惯法的,绝不是公众对习惯的“法的确信”。艾伦·沃森认为:“在西方私法中,要将习惯视为法律就需要比惯例更多的东西,即使该惯例已经是普遍的和盛行已久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能从是中得出应当。连续一致的行为符合某种特定的隐含的规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当如此行为,或者相反,如果他们不如此这般的行为就会面临某种制裁。”[10]公众的“法的确信”只是使习惯成为规范的心理要素,这种心理要素只是习惯的规范性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心理要素,习惯就不成其为习惯,而仅仅是一种惯例。使习惯变成习惯法的,是法官对习惯的适用。即,法官的权力是习惯变成法律的核心要素,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司法判决。沃森认为,习惯法的基础经常被视为习惯而不是司法先例,对待该问题的这种方法引发了司法判决在习惯法的创制中的作用问题。他进而提出了澄清此问题的具体方案,该方案包括如下九个命题:
(1)要想成为法律,习惯需要“行为方式”之外的一些东西;(2)“法的确信”理论难以提供这种必需的特别要素;(3)法庭宣告习惯法,甚至在习惯并不确定时(即不存在法的确信)以及并不存在习惯时,也是如此;(4)在很多法律制度中,即使法庭判决并不创造法律,命题(3)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并不能说法庭裁决是习惯法的全部基础;(5)官方作为法律记载的习惯与制定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是,官方记载本身并不能证明该习惯并非是既存法律。这是不证自明的;(6)法庭判决并非法律,因此不能成为习惯转变为法律的基础。但是,如果这些判决宣告习惯为法律,甚至并不存在必需的惯行(例如命题(3)中的情形),那么,官方把一条规则宣告为习惯法就使其成为法律,不管其背后的行为是不是习惯性的;(7)在裁决者将习惯行为视为法律的社会中,同时也是视人民在通过默示而造法;(8)但是,这种法律只有在裁决者以官方的形式承认和适用它的时候才被创制;正如主权者的意见在以制定法的形式表达之前并非法律一样,人民的意志在得到法庭判决对它的制度化表达之前也不是法律;(9)因此,必然的结论是,如果习惯没有在司法判决中得到清晰的阐释,那么它就不是法律;但如果在官方的编纂中得到记载,那么该习惯成为法律,但是作为制定法而不是习惯法。[11]
从沃森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法律实证主义者。他甚至认为,法官以习惯判案所依据的习惯并不一定是本地习惯,依据外来习惯照样可以形成习惯法。④其进路已经不是习惯的司法适用或者不纯粹是习惯转变成法律的问题了,重点已经成为法官的造法权力问题。因为很明显,不存在本地习惯而借助于辖区以外的习惯判案实际上是法官造法问题——本地习惯自身都不存在,更遑论习惯的司法适用问题。但是,沃森的其他论点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从结果来看,他所借助的事实是成立的,正是法官的判决、法官在个案中将习惯作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解决纠纷,才使得习惯向法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判决并不被视为有司法拘束力的国家,如我国,该项习惯只能作为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而存在,并不能一般化而成为习惯法,只能继续作为“适法习惯”而存在。当纠纷再次发生时,法官或者是当事人只不过是简化了习惯的查明程序而已。所以,在沃森的理论(以及拉伦茨等民法学者的理论)当中,缺乏“适法习惯”这个概念环节。也因此,我们理解他的命题要点时可能会感到生硬和跳跃。在司法判决没有拘束力的国家,沃森也认为法官的判决宣告了习惯法的存在,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法的作用是面向未来的,而在上述情形中,判决中的习惯只是起了一次作用,仅仅溯及既往地适用了一次,限于判决书自身的功能而不能自动向未来生效。这种判决只是宣告了一个“适法习惯”,并且增加了公众对该习惯的“法的确信”。基于该判决,公共交往中的当事人相信,法官在未来的纠纷中会再次适用该习惯判决案件。此时的“法的确信”的重点,已经从公众身上转移到了法官或者司法判决身上。卡尔·拉伦茨“习惯法”概念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他所谓的“习惯法”是在长期判例的基础上形成的。
拉伦茨认为,《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后,在民法领域,迄今为止适用的习惯法,似乎没有再继续适用的余地,产生新习惯法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存在了,因为如果要产生习惯法,那么整个帝国(整个联邦)范围内的人们都必须确信这是一种“法”,并且遵守这种习惯法的规范。而通说认为,虽然制定了成文法典,但是习惯法依然在很重要的范围内形成和发展。它是通过所谓的法院实践,尤其是通过各个最高法院的长期判例产生的。如果我们同意通说,认为习惯法是有约束力的规范,并以同成文法相同的方式“适用”,那么,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时应该十分谨慎。只有在某个判例是切合实际的解释以及无懈可击的推理结果,亦即它是“正确”的范围内,它才会具有约束力以及规范性效力。如果将一个在交易中已广为遵守的判例作为习惯法,那么,法院就必须像受到法律拘束一样受该判例的拘束。即使法院发现了该判例的不正确性,也不能抛弃它。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将每一个在交易中已广为遵守的长期判例都认定为“习惯法”,法院对其自身作出的先例进行解释或变更的自由就会受到难以承受的限制。尽管如此,一项长期判例(有时甚至是最高法院的某项一次性裁判)还是可能促使某种习惯法的形成或使之明确化。条件是:该判例中表明的某项规则被交易实践所接受,并且它符合一般的法律意识,为人们所普遍遵循;而它之所以被遵循,并不是因为人们担忧会败诉,而是人们认为这条规则是一项毋庸置疑的法律要求。认定存在习惯法与否,关键并不仅仅是它的实践,而是要看它是否具备了法的确信,(整个联邦)范围内的人们都必须确信这是一种“法”,并且遵守这种习惯法的规范。如果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即可认定该项判例是习惯法。否则,判例的时间再长,实践的时间再长,也产生不了有约束力的规范。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裁判准则,不能仅仅因为它们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争议而认定其为习惯法。[5]14-17
如果拉伦茨对习惯法的论述是对德国情形的准确描述,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公众的法的确信的基础已经发生转移,其重心已经不再是社会实践中的当事人的行为模式,而是法院的判决。“法的确信”建立的基础是法官对某种习惯规则的确认,甚至“法的确信”的对象只是法庭判决所建立的规则,而这种规则不一定是对现实中存在的习惯的确认。因此,“法官的确信”成为“公众的确信”的风向标和指示器。如果进行总结,我们可以认为,在现代法律制度中,使习惯成为法律的毋宁是两种因素:一是习惯自身的规范性,二是法官对这种规范性的确认,并且“法官的确信”已经成为主导因素。
四、法官对“法的确信”的捕捉
就习惯的司法适用而言,关键的问题是,“法的确信”理论的可操作性何在?理论上的说明毕竟不能直接作为司法实践的根据,法官要将习惯规范纳入司法判决需要进行正当性论证,“法的确信”理论如何提供这种正当性支撑?法官的确信与公众的确信如何对接?
对大陆法国家的法官而言,判断“法的确信”时至少涉及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地域范围问题,即在多大范围内人人具有法的确认心,相应的习惯规范才可以被视为习惯法?民国时期的实践显然专注于一个小区域,比如一个县⑤;而在德国,拉伦茨认为,必须是全帝国(现在是全联邦)的人们均具有法之确信,相应的习惯规则才会成为习惯法。[5]14由于习惯均具有地方性,“全国性”的习惯在一些小国家中尚有可能存在,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显然不太可能存在。并且,中国司法中的民间习惯的司法识别基本上是地方习惯的司法识别,因此,地域范围方面应当是地方性的。第二,如何判断人们是否具有法的确认心?这一点必须结合实例才能更好的说明,空对空的抽象推理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请看如下案例:
金马公司接受中行上饶分行委托整体拍卖上饶市“正大商厦”总建筑面积约6289.6平方米的房产。拍卖会由拍卖师叶青主持。在叶青询问至2050万元并宣布“2050万元第一次”后,曾意龙举牌应价2100万元。叶青在2100万元价位报价三次无人响应,遂告知曾意龙其应价未达到保留价2670万元,并询问曾意龙是否接受保留价。曾意龙举牌应价,叶青随即落槌并宣布成交。有竞买人对拍卖师的操作方法提出质疑,认为其应就2670万元的价位主持全场竞价;其他人也指责叶青在2670万元价位上没有叫三次,没有询问是否有人加价。此后,叶青由2670万元开始继续拍卖,曾意龙起初摔牌表示抗议,但在叶青报价2715万元时举牌应价。最后,叶青在17号举牌应价2740万元时询问了三次后,落槌并宣布竞拍结束。曾意龙与其合伙人与金马公司就拍卖事宜产生纠纷,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法院判决确认金马公司拍卖标的物第二次落槌成交无效;确认金马公司拍卖标的物第一次落槌成交有效等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审查本案拍卖师第一次落槌行为是否得当,首先应确认拍卖师对保留价的报价是否属于竞价报价,是否需要报价三次。曾意龙所出2100万元的应价虽为拍卖会当时的最高报价,但根据拍卖法的规定,该应价因没有达到保留价而不发生效力。拍卖师对保留价的报价属于竞价报价,应当征询各位竞买人是否有更高应价。对于是否需要报价三次的问题,经查明,拍卖现场采用的“三声报价法”,是目前我国拍卖市场约定俗成的一种技术措施,对此有关法律并无具体规定。本次拍卖中,金马公司的《拍卖规则》和拍卖师强调注意事项时虽然未提及报价方式,但拍卖师在该次拍卖的前一阶段采用了“三声报价法”,表明其认同这一技术措施,并与各竞买人就此问题达成约定,故拍卖师在随后的拍卖活动中,仍应报价三次。拍卖师单独询问曾意龙且仅报价一次即落槌宣布拍卖成交,这一落槌行为明显不当。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曾意龙的诉讼请求。曾意龙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前后都应三声报价”没有法律依据,不能作为认定拍卖行为效力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三声报价法”是拍卖行业的传统报价方式之一,目前仍为我国众多拍卖公司与竞买人所认可。对于此次拍卖活动是否必须采取“三声报价法”,拍卖法没有规定,金马公司的《拍卖规则》也没有规定,但金马公司拍卖师在2670万元以前的报价采取了“三声报价法”,现场的竞买人也接受了这一报价方式。虽然法律、拍卖规则对此种报价方式没有规定,但行业惯例在具体的民事活动中被各方当事人所认同,即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本案拍卖活动的当事人必须遵守。金马公司拍卖师在2670万元价位上没有经过三次报价,即落槌宣布成交的做法是无效的。曾意龙主张一声报价即落槌有效没有法律依据。⑥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法的确信”与其说是习惯自身具有的一种属性,不如说是法官对这种属性的一个捕捉、抽象和表达。我们所寻求的可操作性毋宁是法官经过长期实践以及对民间习惯的体验而形成的一种感觉——一种捕捉习惯的法律感,而法官只是借助于“法的确信”这个观念为适用自己捕捉到的习惯规范判决案件寻找正当性借口。如此一来,问题就转化成为:法官如何说明某项习惯具备“法的确信”。事实上,习惯规则的识别过程本身已经包含了法官对习惯的“法的确信”的发现和把握,问题只在于法官如何对待和说明这种“法的确信”。
“人人具有法的确认心”是一种心理因素,更进一步而言是一种大众心理。法官对这种大众心理的捕捉必须站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上才有可能,并且,法官是站在一个外部视角,他只能通过对现象的描述间接地说明人们对某项习惯是否具有“法的确信”。上述案例中,法官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法的确信”,但在判决书中“法的确信”呼之欲出。“三声报价法”显然是拍卖行业中普遍遵循的习惯,虽然法律并没有对其效力做出规定,但它却是确认拍卖效力的重要依据。事实上,本案中的当事人主张一次报价就成交,既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也没有习惯方面的支持。假如法官亲临拍卖现场,就会发现“三次报价法”在拍卖这个特定的场域中的效力。它是拍卖组织者、主持者和竞拍者等各方参与人的共同准则。拍卖参与各方是以“默示”的方式,即以自己的行为接受了三声报价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明确指出这样的习惯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虽然法院并没有采用类似“法的确信”的字眼,但在事实上确认了拍卖参与各方对该拍卖习惯的“法的确信”。
若法官直接以人们对某习惯具有“法的确信”为由而说明习惯的规范性,乍看上去似乎法官什么也没有说,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同义反复,⑦而且这种说法无异于使“法的确信”神秘化。但笔者认为,法官是否明确使用“法的确信”这样的字眼并非问题的要害。制定法或者判例规定某习惯需具备“法的确信”,目的是通过法官的判断在习惯和法律之间建立起某种勾连,给该习惯以更高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其内在的逻辑是:“法的确信”理论赋予法官一种自由裁量权,令其在对公众的“法的确信”有所认知和把握后。通过法官之口确认存在“法的确信”,从而在相关的民间规范和援引该习惯规范的制定法规则之间建立链接,赋予该习惯以合法性。因此,潜在地,公众的“法的确信”作为公众共享的一种经验必须转化为法官对民间习惯的“法的确信”,该民间习惯才可能具有司法适用性,法官可以借此进一步为习惯打上法律的烙印,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注释:
①D.1.1.32.1(Julian,Digest84).
②这是拉伦茨的观点,转引自Alan Watson,An Approach to Customary Law,U.Ill.L.Rev.,(1984),vol.1984,No.3,p.563.沃森译自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二版。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的中文译本相关内容与沃森的英译有所不同,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1页。
③司法对习惯形成的促进作用,参见T.W.Bennett and T.Vermeulen,Codification of Customary Law,Journal of African Law,Vol.24,No.2(Autumn,1980),p.216;司法与人民一道创造习惯,参见William Thomas Tete,Code,Custom and the Courts:Notes Toward a Louisiana Theory of Precedent,Tul.L.Rev.vol.48(1973-1974),pp.9—10;Gray认为,习惯经常从判决中产生,参见John Chipman Gray,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the Law,New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1,pp.297—299.
④在Watson的命题3中,并不存在习惯而法庭又宣告习惯,他指的是法庭借助辖区之外的甚至是国外的习惯解决纠纷。参见Alan Watson,An Approach to Customary Law,vol.1984 No.3,U.Ill.L.Rev.,(1984),p.570.
⑤黄源盛在探讨民国初年的法源问题时提出疑问:习惯法应否更具有地理区域的要件?(参见黄源盛:《民初大理院民事审判法源问题再探》,载李贵连主编:《近代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根据民国初年提出上述习惯法的构成要件的背景,以及民国初年所进行的习惯调查情况,可以推测出习惯(法)的地域范围应为县一级的司法管辖区域。
⑥“曾意龙与江西金马拍卖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市分行、徐声炬拍卖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本文只关注法院对拍卖习惯的认定,关于本案的其他细节,可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
⑦惹尼对法的确信的论证也被视为一种同义反复。参见Peter E.Benson,Francois Genys Doctrine of Customary Law,20 Can.Y.B.Intl L,P.275.
标签:习惯法论文; 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拍卖程序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司法拍卖论文; 法学方法论论文; 拍卖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