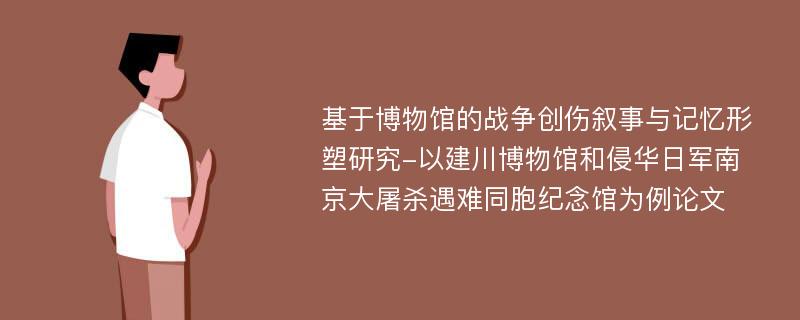
基于博物馆的战争创伤叙事与记忆形塑研究
——以建川博物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
刘美辰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225)
摘要: 博物馆是凝聚历史记忆的场域,同时也是文化再现的场所。博物馆利用其独特的藏品、丰富的展示手法,以及特殊的建筑结构叙事空间,将一段段鲜活的历史、文化、记忆向我们娓娓道来。作为承载人类历史记忆的媒介,博物馆通过展示“物”,再现“物”之主的个体记忆;营造“场”,借由其特殊的“场”,塑造并建构社会乃至国家之集体记忆。文章主要以建川博物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纪录国家、民族之创伤记忆的战争纪念型博物馆,叙写建构创伤与形塑记忆的手法与意义。
关键词: 战争纪念型博物馆 创伤 叙事 个体记忆 集体记忆
2017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也就是指某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蛰伏或潜伏在社会常态甚至光明面下的那些“难以言说”的血色历史乃至人们深埋心底的暗黑记忆。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发生过说不尽数不清的“天灾”和“人祸”,其中既包括:地震、海啸、泥石流、火山爆发等自然因素引起的“天灾”,又包括:战争屠杀、殖民、性侵害、恐怖袭击等“人祸”。在这些“有争议的历史记忆”中,一部分被史学家们记录于册、束之高阁,绝大部分被时间所消融,只有很少的部分被人们所铭记。阿维夏伊·玛格丽特(Avishai Margalit)提出,人类应该记住根本之恶和反人类罪行。[1]20世纪后期,随着新博物馆学的兴起和发展,博物馆越来越被视为保存人类历史记忆的机构与场所。在一场场灾难,特别是人祸之后,我们更应该铭记历史记忆,以警醒世人,而不是忘却,这就需要博物馆、纪念馆等,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作者将“有争议的历史记忆”范围缩小至“战争”语境,对国内反映二战战争创伤记忆的建川博物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开了调查研究,基于此两座博物馆分析战争纪念型博物馆叙写创伤与形塑记忆的过程与手段。
一、博物馆、战争创伤与记忆
博物馆是收藏与展陈人类历史记忆,构筑文化认同的重要场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逐渐由最初以收藏与展示珍贵、珍稀物品为主要功用的单一存在模式,向新的领域探索,现代博物馆的存在形式也逐渐趋于多样化。20世纪80至90年代,战争纪念性博物馆、纪念馆在世界各地被不断修建。
市场需求一旦发生变化,订货量会随之变动,即q>q*或q
对于“战争博物馆”,学界对其并没有一个确切翔实的概念定义,段书晓指出“针对不同的研究视角,海外及国内学者对有关博物馆、纪念馆有多种称呼方法”[2],例如:伤痛博物馆、灾难纪念馆、纪念性博物馆、另类记忆博物馆等。然而,战争纪念型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关键不同在于其对“创伤”的着重叙事与描写上。在战争博物馆这一特殊记忆实践场所中,收藏并展示着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创伤记忆,不断重塑并建构着属于集体同时贴合人类所处时代主题的文化认同,熔铸历史并构筑着新的文化认知体系。
爱尿床的宝宝在晚上7点以后就不要饮水了,晚饭也不宜过甜、过咸。宝宝饮水最好控制在白天,以减少夜间膀胱贮尿量。
战争纪念性博物馆能够将受害个体的创伤经验熔铸成集体性的创伤记忆,并与当代社会体系链接,从而建构出一个城市、地区甚至民族、国家的共同情感和集体认同。本文接下来将分别以建川博物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两座博物馆为例,探讨战争创伤纪念型博物馆,究竟是如何进行创伤的叙事与建构,并成为表征创伤记忆的重要文化记忆实践场域的。
(5)成本:PPS无基布滤料不受基布尺寸及其稳定性的影响,分切尺寸可以更加灵活,且分切的毛边可直接进行开松作为其他材料使用,有效降低损耗,节约成本;
塑料排水板伸出级配砂砾垫层不小于0.5m,施工完成后可将排水板露出端弯折埋置于砂垫层中,同时在砂垫层中埋设盲沟和集水井,井壁随着土层的填高而随之砌高,确保软土地基中空隙水由塑料排水板排到级配砂砾垫层中,再由盲沟汇总到集水井,从而达到加速软基固结的目的。
经历战争、灾难等事件,往往对人们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当受害者体验过严重心理创伤后,往往会出现一系列生理与心理反应,例如:心跳加快、噩梦、焦躁、失眠、记忆衰退、精神恍惚、注意力下降等,甚至在思维角度,可能会产生有如电影回放般的“闪回”(flash back),这样的记忆重现经历体验。并且,由于创伤会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内心记忆之中,故其是很难完全被治愈的。著名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一套完善的心理分析治疗法应该包括:宣泄、解释、教育、转化这四个过程。而由于战争创伤面向受害者数量巨大,不同的战争受害个体所受创伤具有差异化和难以言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的创伤治愈造成了难度。而战争博物馆、纪念馆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创伤治愈的新空间。
创伤(trauma),学者Mc Nally将其定义为:一个客观的事件、个人对其主观之意义诠释性之反应。[3]此外,沈志中指出,创伤对于受害者的恐怖之处,并非在于其所引起的身心伤害,而在于它的意外性与突发性。受害主体对于突如其来的创伤损害不能及时作出自我防御与保护。基于这点,他认为,创伤应同时囊括体验、诠释与重复这三个过程。另外,也有学者定义心理创伤是,人们听闻、目睹乃至亲身经历威胁自身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非常规事件后引起的心理伤害。
参观战争叙事型博物馆,可以帮助受害者回忆自身经历的创伤事件,并且展示与再现其他受害者乃至遇难者的创伤、灾难经历,可以使他们产生强烈的群体性身份认同甚至归属感,这有助于他们对自身创伤的宣泄与解释。同时,博物馆自身具有强大的教育、教化功能,置身战争创伤叙事类博物馆,观众能体验到强烈的真实在场之感,产生巨大的共情影响。在战争创伤博物馆这样一个特殊的赛博空间之中,受害者能够再现伤痛历史记忆,并通过记忆重塑来实现对创伤经历的和解和自我的释怀。
博物馆作为以观众为导向的社会公共机构,它所面向、接纳、服务的群体是广泛的。博物馆观众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博物馆环境直接体验行为的所有人。这就意味着它的展示内容不是个人主义的,而一定是具有集体性的。同样,战争创伤博物馆也不是以展现孤立的创伤受害个体的个人记忆为主要目的的,它的更大意图在于通过展示、再现一个个鲜活个体的记忆,来谱写、建构甚至引导社会、国家之集体记忆,而往往集体记忆的型构需要通过个体记忆的诠释、重塑来完成。台湾学者陈佳利指出,创伤纪念性博物馆作为记忆保存机构,一方面,重新构建诠释了灾难与创伤事件本身;另一方面,也给大众提供了回溯反思历史、凝聚民族情感,构建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的空间。[4]
二、战争纪念型博物馆的创伤叙事与记忆形塑分析
而不屈战俘馆的战争叙事,则以建筑场馆的气氛烘托与密集的遇难者照片墙的交织展示为主,使用实物资料非常少。馆内光线黑暗,窗户呈现割裂状,象征着战争带给人们的撕裂感。整个建筑结构模拟了战俘所处的幽闭、阴森环境,墙壁为仿监狱样式,结合牢笼、刑场及各式刑具的复原,制造了一种恐怖惊惧的空间氛围,对战俘的战争创伤记忆进行了形象表征,战俘当年所遭受之痛苦无需文字描述,观众亦能轻易真切体会。
博物馆与难以言说的历史,是如今博物馆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由于纪录、展陈灾难性的特殊创伤记忆,创伤叙事型博物馆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学界最关注的新兴博物馆之一。历史纪念型博物馆,包括战争纪念性博物馆、纪念馆在内,从叙事手法与展示策略的角度来看,以历史叙事为主,通过编年式的展现手法,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具体经过进行描述;运用大量的照片与实物资料等为佐证,加强博物馆叙事的真实与可信性,并建构所发生之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通过营造渲染其展示的空间氛围,引起观众的共情体验,使他们由内心升腾出对展示之事件的各种情绪反应,有如身历其境。
以聚氯乙烯和煤焦油为主要原材料,掺入适量的外加剂,以水为分散介质而制成的水乳型防水涂料,称为聚氯乙烯防水涂料。聚氯乙烯防水涂料在施工应用中,也需要铺设玻璃纤维布或聚酯无纺布等材料进行增强处理,以达到增强的效果。
在国外,Foote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人们经常会选择通过博物馆、纪念馆及纪念碑等形式与机制,来保存他们想要记忆的创伤与悲痛,并借由这些纪念性之事物,消减甚至抹除那些人们不愿再回忆的事件。[7]美国斯蒂文·里普则以中国文学作品《一个地主的死》为着眼点,研究了中国战争叙事类博物馆对创伤记忆的叙事。他认为,这本书批判地讲述了战争的目的及其本质,并且强调了在战争语境下个人更甚于集体,并且他还认为,战争带来的创伤与伤疤解构了战争的史诗性叙事。[8]同时Violi认为,战争纪念性博物馆与纪念馆等的重点在于保藏与转化创伤,与其他形式的记忆遗址相比,战争创伤遗址是暴力事件存在的物质证明,且在道德与美学层面扮演着重要角色。[9]
目前,我国对北极的研究相对滞后,更多还关注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国1999年才启动北极考察,比南极考察晚了整整14年,随着北极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对北极的研究短板凸显。
在人类社会由战争破坏力较小的“冷兵器”时代进入到“长枪火炮”使用重型武器的“热兵器”时代后,经历了两次灾难深重的世界级战争,这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各国的人力、物力乃至经济、文化发展都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与破坏。一次大战役就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屠杀,在战争影响下各地饥荒四起、民不聊生,更别说还有“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灭绝人性的有意识地屠戮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灾难性行为。战争里种种反人类行径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更给亲历者们留下了永不可磨灭且难以诉说的无尽创伤。战争语境下,“创伤”是人们绕不开、躲不过,更不可否认其存在的永恒话题。
(一)建川博物馆
位于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民营博物馆。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内共建有30多座场馆,主要由抗战、抗震救灾、民俗和红色年代四个主题系列构成,其拥有馆藏文物达1000多万件,博物馆聚落收藏内容丰富,建设规模与展览面积巨大。而在所有主题场馆中,抗战主题场馆是让馆长樊建川最为费心的场馆,同时也是作者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落脚点。基于对战争纪念性博物馆的创伤叙事与记忆表征方法进行研究的主题,作者所在小组对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的部分场馆及区域进行了研究与观察,发现其中日本侵华罪行馆和不屈战俘馆对战争创伤的叙写与记忆表征最具代表性。
建川博物馆中的抗战主题场馆,通过各个展馆诉说着战争的不同视角,并经由视角集合叙述了战争的残酷及带给无辜群众的深重灾难。通过战争纪念物对个体创伤记忆的建构与表征,引导博物馆观众反思战争,沉淀出浓厚的爱国情愫,升华出强烈的集体认同。
同时,辅助以鲜活的场景复原与声音、影像展示,例如日军“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复原场景,和战火中孩子无助的哭喊声的声音背景的使用,以及战争纪录片的播放等,渲染了一种暗黑肃杀的气氛,增强了场馆带给观众的沉浸感,使观众产生“真实在场”的感官经验,置身于其中人们仿佛真实回溯、经历了惨痛的战争,体验并理解了战争受害者的创伤。战争受害者的个体创伤记忆,经由场馆特殊的赛博空间、各种纪念物的展示与各种辅助铺陈手法的应用,被参观观众所逐渐吸纳、理解乃至认同,个人记忆在此过程中被转化、重塑为属于集体共同的记忆。
针对战争纪念性叙事类博物馆、纪念馆内,各种呈现战争、灾难的纪念物和纪念行为以及它们所承载的记忆,国内外学者亦展开过相关探索。在国内,周海玲将战争博物馆、纪念馆,理解为承载战争记忆的物化遗存,并发现此类博物馆在传统急剧消减的今天,反而能够产生新的文化模式,从而参与到当下的文化与生活之中。[5]古骐瑛则进一步认为此类博物馆是,经由文物及各种影像资料来纪录人类历史,并为社会、国家回溯、传承乃至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场所。她关注到,战争纪念型博物馆常借助各种纪念物来对创伤记忆进行叙事铺陈,比如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中的遇难者姓名展示,和美国犹太浩劫纪念馆中展示的人像塔等。[6]同时,她还注意到了战争纪念性博物馆内,对战争历史进行口述的相关纪念物,包括:报刊、书信、录像、日记、历史见证人证言等,这些都是战争博物馆进行创伤叙事的重要工具。
博物馆存在的主要价值之一,就是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通过展示具象的实物资料和应用一系列辅助展陈手法来塑造抽象价值概念,向人们叙写表达其想要让人们理解的主题。而战争博物馆存在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在博物馆这一特殊纪念空间场所内,通过对体现战争的各类实物资料,包括:遇难者日常用品、侵略者使用的实物、幸存者口述资料等的展示,和应用一系列辅助展陈手法,例如:文字说明、数字标识、图像、照片、互动参与装置、灯光效果、声音及多媒体的使用、模型与场景复原搭建、特殊参观路线的设计与引导、虚拟成像技术的应用乃至建筑空间的氛围营造等,来呈现、解释和反省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伤害,并塑造“珍爱和平,远离战争”的主题,在叙述个体的创伤记忆的同时,构建属于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的共同记忆。
在日本侵华罪行馆场馆入口处,摆放着成排的日军钢盔,结合墙壁上“1931年日军蜂拥”的字样,一下子就把观众带入到场馆的展陈叙事场景中去,同时也十分巧妙地交代了馆内展示的主题与内容。展厅设置有如光线灰暗的老式照相馆,采用了大量的历史照片与实物资料结合展示的手法,展馆内以历史大事纪年为主,对战争历史、事实进行了大量的文字说明与铺陈,引领观众走进这段惨痛的历史记忆。按照时间线索进行了路线的设计与展示,各个展厅之间由栏杆廊道连接保证观众参观的连续性,使观众对战争历史的理解逐步深化而不被顺序性扰乱。
本次研究的90例患者均经过手术病理进行确诊,其中C组诊断准确率高于A组,但是和B组对比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2。
(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设于1985年,其建立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拾“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记忆,使中华民族铭记国耻,缅怀战争中逝去的同胞,倡导以史为鉴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由史料陈列馆、集会广场、万人坑、和平公园等几个重点部分组成。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馆中,建筑结构空间、实物资料展示、数字标识、照片影像、场景复原、光影使用、交互式证言等各种展陈叙事手法充分融合,共同塑造了一个回溯创伤、形塑记忆的文化记忆场域。王明珂指出,不论是个体记忆还是社会集体的记忆,都是借由具体的实物资料或者文字载体乃至各种图像唤起的。因此他认为,无论是读历史书,还是翻看照片或是参观博物馆、纪念馆,都是唤起甚至重塑集体记忆的重要仪式活动。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一文化记忆空间中,“物”与“场”完美交织,通过对个体遇难者创伤记忆的叙事,帮助观众回顾战争历史,完善对战争破坏的认知,唤醒内心深处的责任意识,完成集体记忆的形塑。
场馆内收集了大量有关大屠杀记忆与纪念馆发展的历史档案,既体现了对战争创伤记忆的珍视,同时亦是塑造社会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再深刻的历史记忆往往也难敌自然的记忆曲线规律,这段发生在1937年冬天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创伤记忆,在战后的恢复过程中逐渐被人们弱化甚至开始模糊。而历史档案是记忆承运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联结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纽带。随着近年来对社会记忆的呼吁与重申,“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战争创伤记忆,已经被重塑为神圣的国家、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记忆并保藏历史档案是保证记忆存续而不至于记忆断裂的关键性行动保障。
然而,与其他同类型博物馆不同的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突出强调了战争中受害者的个体创伤记忆。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史资料,包括说明牌与展示墙上的历史证言、口述历史影像多媒体放映厅的应用、口述证言墙的实物密集展示以及以幸存者夏淑琴为人物投影背景的交互式证言互动参与装置的设置等,来叙述受害者的个体创伤记忆。在所有展陈叙事手法中,口述史的应用展示是对观众产生“移情”效果最显著的方式,观众只要一读出那些锥心的话语,就能立马被拉回历史,有如身历其境。
集体记忆常常寓于个人记忆之中,并借由个人记忆进一步外化形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借由对个体记忆的强调,顺其自然地重塑了观众对历史集体的认同,熔炼了社会集体之记忆。同时,通过对战争创伤个体之集合记忆的叙事与表征,使观众在博物馆记忆实践空间内完成了集体记忆的构筑。
三、结语
作为承载人类战争历史记忆的媒介,战争纪念型博物馆、纪念馆通过各种纪念物与特殊纪念空间,对战争之创伤进行叙事铺陈,回溯了“物”之主的个体记忆,在赛博空间中营建“场”,借由其特殊文化记忆场域,熔铸并形塑了社会、民族乃至国家之集体记忆。然而,在战争创伤叙事博物馆逐渐拥有更多集体话语权的今天,我们也应关注战争受害个体的立场与视角,避免造成二次创伤,平衡好集体记忆建构与个体记忆呈现的关系,以更好地发挥其自身的社会功用。
参考文献:
[1]阿维夏伊.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78-79.
[2]段书晓.创伤记忆的话语建构: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D].复旦大学,2012.
[3]Mc Nally,R.J.Remembering Trauma[M].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4]陈佳利.创伤、博物馆与集体记忆之建构[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7(66):105-143.
[5]周海玲.群体记忆、审美仪式与治理性——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渡江战役纪念馆新馆为例[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13(1):252-264.
[6]古骐瑛.论纪念类博物馆展示策略[J].中国博物馆,2008(1):60-64.
[7]Foote,K.E.Object as memory: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of human semiosis[M].Semiotica,1988,69(3/4):243-268.
[8]斯蒂文·里普.创伤之战:残疾、伤疤与战争的反英雄叙事——以余华《一个地主的死》为例[J].南方文坛,2017(2):79-83.
[9]Violi,P.:Trauma site museums and politics of memory Tuol Sleng[M].Villa Grimaldi and the Bologna Ustica Museum.Theory,Culture&Society,2012(29):136-175.
中图分类号: TU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05-0071-04
作者简介: 刘美辰,西南民族大学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
责任编辑:张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