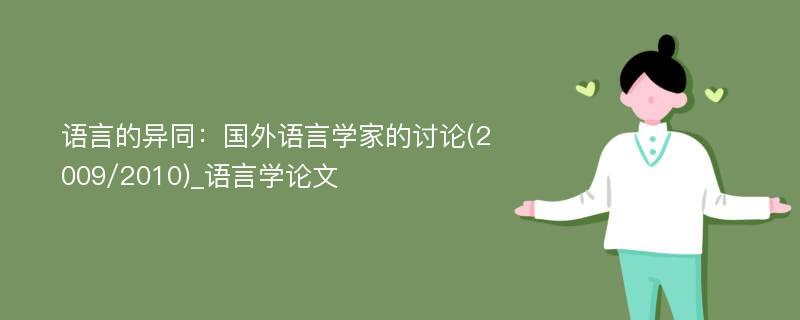
语言的共性与差异性:国外语言学界的一场讨论(2009—201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差异性论文,共性论文,学界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关于语言共性的讨论一直是国外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且不说不计其数的单篇论文、专著和论文集,各专业期刊纷纷发起讨论、集中发表讨论文章就有五次之多,分别是:《语言研究》Studies in Language 2004年28卷第3期)、《行为和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2009年32卷第5期,后简作BBS)、《语言》(Languae 2010年86卷第3期)、Lingua(2010年第120期)、《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 2010年2762期)。其中以BBS和Lingua的讨论参与人数最多,话题最为集中,讨论也更广泛、深入,影响最大(参见姚岚2013)。 这两次讨论始于埃文斯和莱文森(Evans and Levinson,简作“埃-莱”)发表于BBS 2009年第5期的一篇名为“语言共性的神话:语言的多样性及其对认知科学的重要性”(The myth of language universals:Language diversit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cognitive science)。该刊将其作为一篇标靶论文(target article),邀请学者参与讨论。文章一经发表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先后有50多位学者参与讨论。此后,Lingua杂志又接过话题,于2010年(第120期)设专栏讨论,两刊都在讨论的最后安排埃-莱作一次回应,有来有往,精彩纷呈。本文就标靶论文和讨论文章的主要观点作简要综述和评论。 2.埃-莱的主要观点 生成语法认为语言间的差异是表面的,如果作形式上的抽象,个别语言间的差异就会消失。埃-莱称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对心理语言学、语言进化研究、语言习得、神经认知、话语分析和识别以及认知科学的各个分支都有极大的消极影响。这种误解的产生可归咎于以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为中心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在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交叉和对话中,生成语言学成为代表语言学界的观点,该理论在认知科学领域深入人心,以至UG(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成为关于人类语言共同点的代名词。语言共性不是来自于空对空的假设或基于个别语言的抽象,只有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才能证明是否存在语言共性。当类型学家面对大量的跨语言事实时,共性归纳绝非易事。埃-莱认为语言类型学家有责任通过对话让认知科学领域的学者知道语言的多样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UG。埃-莱的文章发表于认知科学的专业期刊BBS,这也体现了他们撰文的目的。 2.1 语言的差异性 埃-莱从语音、音系、句法、语义等层面以及若干概念入手说明共性其实不存在,多样性才是语言的真实面目。在语音层面上,有的语言有十几个音素,有的有一百多个,而手势语则没有任何音素。单是手势语就可以颠覆“所有的语言都有口腔元音”的共性。各语言中的发音方式、发音部位也变化多端,应有尽有,并且传统的描述音素的方法以及CVC音节结构①并不适合所有语言(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33)。形态上的差异性更明显,英语中用一个句子表达的意思在有些语言(如卡尤加语Cayuga)中可能一个黏着的词就可以表达,这意味着对词和句子的重新定义。就词类而言,通常所说的四大开放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并不具普遍性。另一方面,传统词类的划分无法涵盖一些语言中出现的新词类,如状貌词(ideophones)、位置词、副动词(coverbs)、量词等(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34-5)。 语义上的共性同样在跨语言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语法和词汇中编码出来的概念在各语言中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如有的语言没有逻辑连接词if、or等,有些语言没有表示“蓝色、绿色、手、大腿”的词,有些语言中没有时、体、数词、第三人称代词等。另一方面,很多语言中的语义区分在印欧语言中闻所未闻。例如在中波莫语(Central Pomo)中,任何判断都必须说明言据来源;夸夸嘉夸语(Kwakwala)中必须标明所指之物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澳大利亚土著语必须注意参与者之间的亲属关系。这足以说明,人们用各语言特有的系统表示不同的意义,而不存在固定的、先天赋予的思维语(mentalese,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35-6)。 埃-莱进而说明无论是生成语言学意义上的普遍语法,还是语言类型学意义上的语言共性都是不存在的(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36-7)。埃-莱又以主语、成分组合关系(constituency)和递归性为例说明通常所用的语法概念都表现出很大的跨语言差异性(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40-2)。 2.2 协同进化模式: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框架 语言的差异性既挑战了生成语言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同时呼唤新理论的诞生。新理论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如何解决人类语言共同的生物基础和语言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埃-莱提出认知和文化的协同进化(coevolution模式,认为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是两个不同的轨迹,彼此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这种双轨模式为适应文化环境特征的生物进化提供机制。语言的差异性通过文化轨迹的多样化来解释,在此轨迹中语言特征的进化过程与人口遗传学的进化过程类似。这些过程导致人口条件的产生,而后者为新的人口变体的产生提供环境,若干选择因素及限制条件导致出现不同的变体(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44)。语言的多样化和杂交过程同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且遵循人口生物学的规律。 运用协同进化模式可以帮助重建语言谱系树,明确其中每个枝节的结构特征,并且追溯至最初的源语言。语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相对稳定的状态不断取代相对不稳定的状态。语言共性大都表现为倾向性。共性倾向是交际、认知以及语言处理等方面的限制及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文化因素影响语言变化的方向。反过来,我们可以借助上述因素来解释不同变化状态之间的差异。进化论和人口生物学的研究视角,可以更好地解释语言参项的典型特征和非典型特征,这种解释诉诸语言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大脑中某种先天的装置(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44)。 总结起来,埃-莱(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45-7)的主要观点包括:(1)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语言的差异性是一种特别的属性,因为其他动物的交际系统都不表现出这样的差异性。(2)语言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中演变而成的。此外,人脑、语言器官以及对交际系统的功能和认知限制等诸多因素在语言演变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选择器(selectors)的作用。(3)语言的多样性表现为原型、特征的集合以及家族相似性,而不是表现为绝对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语言类型。(4)类型变化分布表现出具有倾向性的进化模式,这些倾向性特征像吸盘一样,吸引各语言向该特征进化。(5)在漫长的生物史中,语言的生物基础只在最近才进化而成。人类的语言器官在负责语言功能的同时还负责别的功能,如大脑、口腔、舌头等都是如此。(6)语言学家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的认知能力,研究相同或相近的生物基础如何产生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3.生成语言学者的反应与批评及埃-莱的回应 由于标靶论文涉及到各语言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同语言学流派的学者都对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回应的学者主要来自三种背景:(1)生成语言学、(2)语言类型学以及(3)认知语言学及其他学科。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就标靶文章的观点、理论、列举的语言事实、推理方法等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讨论的切入点包括语言习得、语言处理、神经认知、跨物种比较等。 3.1 生成语言学者的批评 由于标靶文章对生成语言学的核心假设提出了挑战,生成语言学者大都不同意埃-莱的观点。第一种批评意见是埃-莱只停留在语言差异性的表面,对语言结构的浅层变化关注有余,而对其背后的规律挖掘不足。Baker(2009:448-9)认为各语言在描述层面上表现出差异性,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表现出共性。归纳共性时,适当的抽象是有必要的。某一共性受到跨语言事实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共性不存在,只说明对共性的抽象和表述还不够准确。Pesetsky(2009:463)认为埃-莱只是列举了一些现象;他们描述的事实未必准确,在理论上也经不住推敲;透过现象看本质,不难发现共性是存在的。Tallerman(2009:469)认为埃-莱过于强调各语言琐碎的细节而忽略共同的区别性特征以及普遍共享的策略。差异是表面的,共性是更高层面的、抽象的。各语言经常采取不同的语法手段达到类似的效果,这种效果构成共性;采取的手段甚至是相同的,更证明了共性的广泛存在。Rizzi(2009:467-8)认为埃-莱的讨论局限于贫乏的、未经任何提炼的描述机制,注定不会上升到形式上的共性。在形式语法的框架下,尽管各语言在不同层面表现出差异,但差异不是没有限制的、不是无穷无尽的。经过一定的抽象和理论提炼,不难发现具有普遍性的结构。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不能因为语言的差异性而放弃对语言共性的追求。 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埃-莱缺乏理论。Smolensky和Dupoux(2009:468-9)从生成语言学的立场阐述“共性对语言认知理论的重要性”。认知理论应该是可证伪的、高度形式化的理论,而埃-莱的观点是思辨性的而不是系统的可以形式化的理论。 另外,一些学者从事实上反驳埃-莱。Berent(2009:450-1)通过分析一条音系共性证明UG的存在。共性的限制作用尽管不一定体现在实际语言结构中,但在所有说话人的语法中存在。埃-莱以Kiowa语中数的系统为例说明不存在UG和语言共性,而Harbour(2009:457)认为相反,Kiowa的语言事实恰好说明存在语义基本元素,从而证明UG是存在的。Pullum和Scholz(2009:466)认为埃-莱关于灵长类动物句法学习结果的论断是错误的。事实是猿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没有学习语言的能力。语言一方面表现出不可预料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可能的差异都实际存在。与其说埃-莱的结论否定了普遍语言共性的存在,不如说他们从生物学的角度表明差异性是语言的突出特性。 还有学者批评埃-莱方法上的缺陷。Freidin(2009:454)认为埃-莱只提供了一些粗略的描述,而没有明晰的分析,他们对UG的挑战建立在未经证实、甚至没有明确表述的假设之上,这导致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未经分析的语言材料不足以证明或颠覆语法假设。Harbour(2009:456-7)认为语言学家应该像化学家那样透过物质的表面去发现构成物质的元素及其特征,这正是共性所在。Nevins(2009:461)认为,认识人类语言结构的共性需要对语言作多层面的比较分析。埃-莱关注语言的实体变异,而忽略了形式共性,后者对于研究语言同样重要。 3.2 埃-莱的回应 埃-莱坚持协同进化模式,认为接近表面(而不是深层)的描述不会扭曲语言事实。文化进化对于理解语言差异性有着重要意义。儿童的语言习得不需要借助于任何先天的UG,和一般动物不同,儿童学习语言是发声学习,即他们能够学习并发出听到的声音。人类语言进化具有其它动物没有的环境和基础。埃莱主张在人类的遗传、神经认知、心理语言过程的广阔图景中理解人类语言的多样性(Evans and Levinson 2009b:473)。 埃-莱认为抽象是有代价的,越是不可证实的、不可观察的抽象,解释力越强,但理论越是艰深,就可能离实证基础越远(Evans and Levinson 2009b:475)。越是具体的表征,越忠实于语言事实,保存的信息越多。采取渐变的随机模拟模式(而不是离散的方法)研究语言,直接呈现语言的差异,对于认识语言的演变过程、解释语言的差异性非常重要。所有科学都是在寻求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好的科学既能高度概括,又不失实证基础(Evans and Levinson 2009b:475)。生成语言学者认为共性存在于语言的结构表征上,功能类型学认为共性存在于语言演变的过程中,只有充分认识到进化结果和过程的多样性,才能真正意识到进化机制的统一性(Evans and Levinson 2009b:475)。 针对缺乏理论、表征不准确等批评,埃-莱回应道,标靶论文的初衷不是提出理论,而是让人们注意到语言的多样性及其对认知科学的启示意义,并勾画出未来研究的方向,旨在推动语言研究从封闭的个人思辨到实验科学的方向转变。况且语言学理论多种多样,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类型学等都是语言学理论,生成语言学理论只是诸多理论中的一种,该理论置语言外部因素于不顾,不考虑功能、实用、心理、神经等诸多因素,语言进化理论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Pesetsky(2009:464)、Tallerman(2009:469)等批评埃-莱说,他们只罗列奇异的事实而不加分析,稍加分析不难发现,这些语言事实还是符合语言共性的。反对者以Tlingit语为例,说明成分组合关系就是一条语言共性。埃-莱认为任何自由语序的语言足可以颠覆这条共性——哪怕是一个反例就足以证伪一条共性。 Pinker和Jackendoff(2009:465)批评说,埃-莱夸大了差异性的范围而忽略了语言可能存在的设计空间(design space),人类语言只占据这个空间的一隅。埃-莱反问道,(1)这个可能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语言进化有其生物基础,这是语言文化进化的平台,同时又是限制语言存在的设计空间,人们可以通过语言的输入/输出系统以及语言交际中的实际互动反观语言的生物基础。这种功能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限制设计空间的动因,可以解释语言如何演变为一个精妙的运作系统(而不是一团乱麻)。(2)人类语言为什么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Pinker和Jackendoff的回答是因为内在的先天的限制。但如果考虑到语言进化的时间跨度,这就不难解释语言的多样性。在协同进化的模式中,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解决。 4.语言类型学及其他领域学者的反应和批评 语言类型学者广泛接受语言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进化语言学已经出场(Croft 2009:453)。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修正或补充埃-莱的观点,或是针对生成语法的某一概念或观点进行批评。 Haspelmath(2009:458)同意埃-莱的观点,认为对语言学家而言,更有意义的是蕴涵共性,这种共性可表述为级差的形式,如关系从句的位置级差:主语>宾语>旁接宾语>领有者②。Goldberg(2009:455)认为绝对的、有实在意义的语言共性几乎没有。但不能否认有动因的语言模式是存在的,并且可以解释。这些语言模式是相互作用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制约因素(包括文化的、历史的和认知的)之间协调的结果。这种解释没有预测功能(UG的解释是预测性的,但往往站不住脚)。语言研究诉诸动因分析而不是预测性的解释。Croft(2009:453)认为埃-莱对UG理论的批评过于遮遮掩掩。例如他们没有放弃词类、语法关系之类的术语,生成语法宣称的语言结构的共性根本不存在,任何语言共性的研究首先必须跨过语言差异性这道坎。进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正在兴起,它可以取代生成语言学理论成为认知科学重要的理论支撑,这对于认知科学发展极具意义。Christiansen和Chater(2009:452-3)认为语言是文化进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这种进化受生物、认知、思维、社会语用、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不同社会间,这些制约因素可能相似,因而不同语言可能表现出相似之处,但这只是家族相似,即没有一种特征是所有语言共有的。儿童之所以较快习得语言不是因为UG,而是因为通过一代一代学习者的文化选择,语言表现出的模式便于儿童自然习得。 实验心理学、跨物种比较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等领域学者的批评大都是正面的,他们佐证、完善、修正或补充埃-莱的观点。这类讨论关系到语言变异以及认知科学的研究方向,值得重视。Waterfall和Edelman(2009:471)提供证据说明人类语言体系中存在的共同模式是由认知限制和文化因素导致的。他们建议将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不同物种之间的比较研究纳入语言进化研究。Margoliash和Nusbaum(2009:459)也认为跨物种比较研究对人类语言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在研究生物体所具有的某项能力时,应结合该能力所对应的功能以及生物体的社会需要等外部因素。语言是一种动物行为,人类语言的机制和使用模式与语言的实际使用密切相关,语言研究应建立在实验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的基础上,动物交际系统的研究对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Penn等(2009:463)指出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其他动物的认知能力有着本质的不同,人脑和其他动物大脑的差别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语言的差异性表明,人类的语言官能并不局限于大脑的某一区域而是依赖整个认知系统,这个系统由其自身应对各种不同的功能和目的进化而来。人脑和语言都是生物-文化杂交的产物。埃-莱(Evans and Levinson 2009b:479)认为这类观点是正确的,也是对标靶论文的重要补充,他们提供的关于学习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回答了人类如何学习千差万别的语言这一问题。 Merker(2009:461)认为埃-莱呈现出的语言差异符合文化传递的生物学原理。通过文化传递,任意的符号串变成有效的、共享的语法,语言是符号串间物竞天择、代代相传的结果。更有效、更具概括力的语言形式更具竞争力。语言的原始状态与鸟类的歌唱并无本质不同,语言是人类适应社会环境,适应表达和交际意义需要的产物。人类拥有一种特有的进化了的学习能力,即发声学习的能力,这是人类语言的生物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学习能力,语言的形式经过文化传递这一历史过滤器,并适应语言的使用、可学性、神经资源、文化常规等方面的限制,代代相传。 Waterfall和Edelman(2009:471)提供证据证明人类语言体系中存在的共同模式是由认知限制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的。类似的研究勾画出语言和认知在生物变异中的地位以及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方向。认知神经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确立,人们注意到个体生物变异的研究价值,并发现了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与基因标记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大脑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进化的体系。这不仅意味着脑科学的革命,而且将带来语言学的革命。 McMurray和Wasserman(2009:460)从语言学习的侧面补充埃-莱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某一行为是固定不变的,则可以在生物体内解释;灵活多变的行为,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语言是一种高度灵活、极富变化的行为,是通过对环境高度敏感的学习过程习得的。语言的差异性意味着语言学习是一个复杂过程,正如不存在普遍通用的语言结构,也不存在通用的语言学习机制。人类通过各种不同的学习机制和信息来源习得语言,各语言的特性决定不同语言的学习是各自不同的、独特的过程。语言不是内化的结构,而是高度复杂的行为集合,语言学习就是发展这种行为能力的过程。 Bavin(2009:450)从语言输入是否为儿童习得语言提供足够的信息这一问题入手,说明UG理论不足以解释语言习得的过程,不足以证明语言输入贫乏论的假设,也不能证明儿童习得不同语言时经历的过程是一样的。研究语言习得应结合其机制、步骤、策略等;语言能力的发展与儿童大脑的发展、社会能力及认知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语言能力的获得和提高与认知能力及其发展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语言学家应充分认识到语言的差异性,认识到这种差异性对语言习得过程的影响,以推进人类关于语言制约的理解。 Catania(2009:451-2)认为三轨模式能更好地解释语言的差异性,即除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这两条轨迹外,还有发育的过程中个体语言全能(individual language repertories)的进化轨迹,三者各自遵循自身的规律,各自有着不同的选择机制,生物机制帮助选择语言的生理属性(如声道结构、神经组织),个体发生机制负责保持个体习得语言的特征,文化机制帮助实现语言代代相传。这三条轨迹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共同导致语言差异的产生。 5.讨论的延续(Lingua期刊) Lingua首先安排了一个编者前言(Editors 2010)。前言指出,埃-莱将差异性置于核心位置,强调“每一种新的语言都表现出始料未及的新特征”(Evans and Levinson 2009b:432),但没有注意到每一种新的语言都表现出似曾相识的现象。从语言内部观察这些现象是必须的,向内的概括往往更加抽象,“解释性的理论必然是抽象的”(Editors 2010:2654)。对事实的分析(而不是事实本身)才能证伪某一假设。此外,埃-莱没有回答语言习得、可学性、语言处理、历史演变等基本问题。他们强调语言作为一种技巧以及语言作为一种交际系统的一面,但这些都不是语言知识的核心特征。与语言的使用相比,语言的本质特征更值得研究(Editors 2010:2655)。解释语言先要有理论,语言知识的理论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在逻辑上优先(Editors 2010:2556)。 与BBS的讨论相似,反对的意见主要来自生成语法学者,讨论的问题包括反例能否推翻UG的理论假设,如何看待表面的差异性等。由于后一种意见在上文讨论过,限于篇幅,这里综述第一种批评意见。 5.1 生成语言学者的批评及埃-莱的回应 Abels和Neeleman(2010:2657)认为生成语言学的任务是发现自然语言的限制。理论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共性是对语言事实进行概括的结果,假设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共性。反例的意义不在于否定语言共性,而在于反例与理论之间的联系,理论如何解释共性以及反例。对反例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完善共性的表述,而不是放弃对共性的追求。埃-莱③回应道,Abels和Neeleman将语言学理论等同于自然语言的限制条件。这种限制只能根据现有的、大家熟悉的语言设立,未知的、已经消失的、将来可能出现的语言极有可能超出这种限制。语言学理论既可以是心理能力的理论,也可以是文化进化的理论,即使是心理的理论,也不一定是语言官能的理论,语言的输出和理解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素(Levinson and Evans 2010:2751)。 Bolender(2010:2661-2)的批评意见是,埃-莱无法否定所有的语言共性,当某些共性被否定时,剩下的共性反而突显了出来,在语言差异性的背景下,语言共性显得尤为重要。共性极有可能反映人类的共有思维和认知特性。而来自认知科学领域的实验证据表明人脑中的某些组织与语言结构密切联系,这给共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埃-莱(Levinson and Evans 2010:2751)认为,认知和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但这里存在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是认知造就语言能力,还是语言环境促进认知能力的提高,这个问题尚无确切答案。 Crain等(2010:2669-71)提出UG是关于人的语言官能的起始状态的理论。它决定儿童初始的语言假设,定义可能的人类语言,预测不可能出现的语言现象,等等。世界诸语言都有UG的印迹,但像埃-莱那样通过统计跨语言结构类型不能发现语言共性。因为在描述特定语言的时候,该语言的特殊之处往往比语言共性更引人注意,语言共性并不企图解释语言中的例外和不规则的情形,因此通过各语言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来反驳语言共性不能说明问题。埃-莱(Levinson and Evans 2010:2750)反驳说,照这样说,UG只是儿童学习语言的初始状态,它对语言的差异性无能为力,刚好说明UG不合理。 Duffield(2010:2674-5)指出埃-莱对UG与终点状态语法(end-state grammar)之间的关系有误解,前者是关于起始状态语法(或称作语言官能)的理论,它为具体语言的语法提供抽象的框架,但它本身不足以决定后者。语言共性的缺失并不意味着UG不存在。此外,埃-莱对语言表面差异性的理论意义也存在误解。他们似乎认为各语言表面的差异性越大,对UG构成的挑战就越大。相反,语言的差异性正是UG立身之本,差异性需借助UG来解释,因而显示出UG的巨大力量。埃-莱针锋相对,认为这刚好说明UG的不可证伪性,这也是其他学者对生成语法摸不着头脑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初始状态的具体情形。到目前为止,人脑中是否存在专司语言功能的区域还没有得到证明,因此UG(或语言官能)的解释力大打折扣(Levinson and Evans 2010:2750)。 O'Grady(2010)认为无论语言类型学中的语言共性,还是原则参数下的语言共性都经不住事实的考验。真正的共性不是对个别语言表面特点的归纳,而是对语言的产生、理解以及习得机制有关的基本事实的概括,这些共性是非语言的,O'Grady(2010:2708)称之为“基本语言共性”。埃-莱基本认可这样的观点,但补充说,这些限制的根源在语言系统之外,却对语言特征起作用,语言无法规定这些限制,但可以对其作一定的变通(Levinson and Evans 2010:2752)。 Reuland和Everaert(2010:2713-5)认为埃-莱反对在跨语言差异中寻求规律性的语言学理论(如生成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如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将一些奇异的事实呈现在读者面前,不能增进人们对语言的了解。他们又以约束理论为例,说明白19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一直注意参照跨语言的事实,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约束理论,使之更具跨语言有效性。但埃-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而他们对这一理论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埃-莱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应该在语言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寻找共性,而不是在语言结构中寻找,Reuland和Everaert有为了迁就约束理论而不惜扭曲语言事实的嫌疑,不能说服人(Levinson and Evans 2010:2750)。 5.2 赞同、补充和引申 Kemmerer和Eggleston(2010)从名词和动词这两个基本的语法范畴入手,考察它们在语义和形态/分布上表现出的跨语言共性和跨语言差异性。近年来的认知科学研究表明,名词和动词分别对应大脑中的不同区域(Kemmerer and Eggleston 2010:2688),但这类研究都没有吸收语言类型学有关语法范畴的最新研究成果。试问,如果当今世界主流语言不是英语而是Makah、Lango、Jaminjung(这几种语言中名词和动词之分与英语迥然不同),认知科学关于语法范畴的研究会有怎样的不同(Kemmerer and Eggleston 2010:2689)?Koschmann(2010:2694)针对埃-莱关于递归性的讨论,对其作进一步阐发。生成语法认为递归性是语言本质的、普遍的属性,与思维有密切联系,这是人类先天就具备的能力,而且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是人类交际能力的一部分。 Rothstein和Treves(2010:2717)认为共性论者和类型学者的争论陷入一种怪圈:前者提出的共性被后者提供的反例推翻;前者不以为然,认为后者的反例未经分析,不足为证;如此循环往复,谁也不能说服谁。讨论不应纠缠于此,鉴于负责语言功能的神经机制与认知功能背后的神经机制并无不同,认知神经科学家和语言学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神经机制如何相互作用,以及为什么只是小范围的神经机制负责语言功能。解决这类问题有两种路径:其一是语言学途径,其二是统计的方法。这两种途径都说明共性存在于语言处理的计算过程中,而不是计算结果中。 此外,来自手势语研究领域的讨论大多佐证了埃-莱的观点,这类讨论角度新颖,值得注意。 Cormier等(2010:2664)的讨论表明多样性在口头语和手势语中都有体现。Sandler(2010:2727)说明,手势语和口头语一样,是一个具有共性特征的连贯系统。各语言间不但有着惊人的差异,也有着惊人的共性,这些共性和差异很多可以借助语言的外部因素来解释,而不是像生成语法那样局限于语言内部。Malaia和Wilbur(2010:2704)同意埃-莱的立场,只有在不同模态下(包括手势语和口头语)跨语言事实描述的基础上才可以提出科学的、可验证的假设。同时,他们认为,可以在这种描述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提出理论模式。他们以手势语为例说明,对语言事实的描述以及对语言形式的抽象都有助于通过语言神经基元研究人类语言在大脑中是如何实现的。 6.埃-莱总的回应与结论 最后埃-莱对这场争论做了一个总的回应。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讲,争论反映出C-语言学(乔姆斯基语言学,Chomskyan-linguistics)和D-语言学(多样性语言学,diversity-linguistics)在语言事实、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根本不同(Levinson and Evans 2010:2735-2736): 就语料而言,C-语言学一般凭直觉获得语料,使用的语料极为有限。D-语言学借助语料库、类型学数据库、多媒体材料等,广泛占有语言事实。在理论模式上,前者在UG假设的基础上断定对一种语言的结构分析可以直接运用到另外一种语言上。后者主张先单独对一种语言进行分析,然后再作跨语言比较。前者将研究某一语言的元语言等同于用作跨语言比较的元语言,后者则不然。前者认为存在一套先天的专用于语言的原则,后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前者寻求内在的基于结构的解释(外界对这种解释有循环论证的批评);后者多诉诸功能的、使用的因素以及历史的因素解释语言。 尽管双方争论的话题没有大的改变,但近年来外界环境有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二者间的平衡。这些变化包括:(1)可供描述语言学家使用的语料在数量、质量、类型上都有极大的改变。(2)借鉴生物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大规模语料表现出的规律。而且计算机技术可以非常逼真地模拟语言的进化和变化过程,也可以模拟出认知因素在此过程中的作用。(3)文化-生物协同进化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机体中哪些特征是先天的,哪些是在文化的基础上进化而来的。在语言进化过程中,历史进化和生物基础的作用同等重要,人们对前者的作用认识不足。(4)上述方法和语料的出现使得语言学和其他学科可以更紧密、更有成效地合作。例如,可以借鉴人口生物学的方法研究语言现象的分布规律,从语言变异入手发现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没有表型变异(phenotypic variation)就不可能发现基因;同理,不通过语言比较就不可能发现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 语言科学正在面临一场大变革。C语言学企图维持30年来的现状,通过使用凭直觉得来的语料演绎出抽象的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一直变化着,前后不一致,人们难免莫衷一是。D语言学关注语言的差异性以及丰富、真实的语料,尽管他们注意到新的进展,但却缺少统一的理论框架。埃-莱勾画出了协同进化模式的理论框架,变异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这一模式对上述变革做出“正确的”反应(Levinson and Evans 2010:2733)。这一模式对什么是事实、形式表征处于什么位置、如何进行语言比较、什么是解释、语言设计的源头是什么等问题都有自己的全新的回答。这场大的变革已经来临。对这场变革的反应将决定语言学的未来(Levinson and Evans 2010:2733):要么重复老路,裹足不前;要么投入到这场变革。这不仅关系到语言学的未来,还关系到所有研究人类本质特点的学科的前途。 这场讨论关系到生成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背景的学者都参与进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标靶论文本身,呈现出不同学者对语言学理论、事实和方法的不同观点,因而讨论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也将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在这场讨论的启发下,在更多跨语言事实、更多新的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面前,各语言学流派必将反思自己的理论。纵观讨论的全过程,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争论双方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各自对语言共性的认识和定义不同。Chomsky(1965:27-30)认为有实体共性和形式共性之分,Smolensky和Dupoux(2009:468)区分描述共性和认知共性以及特定共性和整体共性(Pinker和Jackendoff称之为区别性共性),Longobardi和Roberts(2010:2700)将共性分为归纳共性和演绎共性等等。类型学中的共性属于实体共性、描述共性、特定共性、归纳共性;生成语言学的共性属于形式共性、认知共性、整体共性、演绎共性。前者的反例未必构成后者的反例。这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也是双方分歧无法消除的直接原因所在。双方发现共性的方法也不一样:生成语言学认为语言共性可以从现有的、甚至是单一的语言中推导出来,并且可以通过跨语言事实的验证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类型学家认为,发现共性的唯一方法是在跨语言事实中归纳。后者的结论认为经得起检验的、有意义的共性几乎没有。因此Editors(2010:2651)认为类型学的研究过程就是推翻共性的过程。另外,在生成语言学内部,有些学者对UG和语言共性不做严格区分,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他们认为UG处于更高的理论层面,语言共性被推翻并不意味着UG不存在。如果UG是一种理论假设,不能用反例推翻,埃-莱关于UG不可证伪的批评值得生成语言学者认真思考。如此等等。争论的问题本身没有统一的定义,难免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一定意义上讲,生成语言学和协同进化模式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参见Hawkins 1988; Editors 2010:2651)。首先埃-莱承认语言的生物基础,生物进化是他们提出的双轨协同进化模式中的一条轨迹。Chomsky早就认为语言学和生物学、心理学密不可分,提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语言研究(Abels and Neeleman 2010:2657)。语言是生物文化杂交的产物(bio-cultural hybrid,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46),这是大家都认可的。生成语言学者更注重“生物”的部分;埃-莱等更注重“文化”的部分(Editors 2010:2653)。前者在机体内部寻求解释语言,后者则倾向于通过机体外部的因素解释语言。尽管类型学的发现对理论构成挑战,但类型学式的细致分类是走向理论的第一步。类型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记录语言事实,理论家解释语言事实,二者对语言研究都很重要。如果说生成语言学和协同进化论都企图解决语言何以如此这一核心问题,前者从语言计算/进化的结果(即语言的现状)中寻求答案;后者关注语言进化的历史过程,即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如何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相互作用、彼此协调,共同导致语言差异性的产生(Hawkins 1988; 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44,445-7,473,475; 2010:2740,2750;参见Catania 2009:451-2; Rothstein and Treves 2010:2717)。结果和过程是相对而言的,现状是过程中的一个状态,是重现过程的确切的参照点。与其说语言类型学的目的是寻求语言共性,不如说是寻求语言进化的规律。生成语言学寻求差异性现象背后的原因,往往诉诸对事实的抽象,协同进化论为再现过程往往更真实于事实本身,这种不同是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路径决定的。 其次,语言科学的发展与相关科学的发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长期以来,生成语言学为心理语言学、神经认知科学提供理论指导,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生成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或是少数通用语言的事实基础上,这些假设有待更多的跨语言事实的检验,有待脑科学、神经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去验证。比如,人脑中是否存在专司语言功能的区域、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是否分开,儿童出生时是否就获得了语言习得机制,如果存在这样的机制,它和语言功能如何联系,等等。随着这些学科的发展,新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的出现,这些问题可望解决,语言学的假设可以得到科学验证,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理论。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语言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更多的语言事实可能在原来的理论框架下不能得到很好的描述和解释,这就要求对理论做出调整,使之更具跨语言有效性。当代语言学家有责任也有条件走出书斋语言学(armchair linguistics)的窘境,吸收各学科的成果,以事实为基础,使之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最后,国外学界学术至上、求真务实的态度和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不同学派的学者能够直接交流自己的观点,不回避,真正据理力争,将讨论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顾及人脉关系等非学术因素,尤其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借鉴。即使持赞成观点,也不是一味随声附和,而是修正、补充,或作进一步发展,真正坚持真理、尊重事实,以理服人。可以肯定,这是一场重要的争论,必将给语言学界带来新的空气,引导人们对双方的理论、事实和方法作深入的思考,对语言学和其他相关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可以断言,争论尚无定论,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类似的讨论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 ①即辅音(consonant)+元音(vowel)+辅音(consonant)的音节结构。 ②该等级构成一系列蕴含关系:右边的蕴涵左边的。举例说,如果某语言中宾语能提取出来被关系化,则该语言中主语也能提取出来被关系化,反之不定然。由此类推。 ③Lingua,上回应文章作者的署名顺序是Levinson and Evans,为保持前后文一致,此处仍略作“埃-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