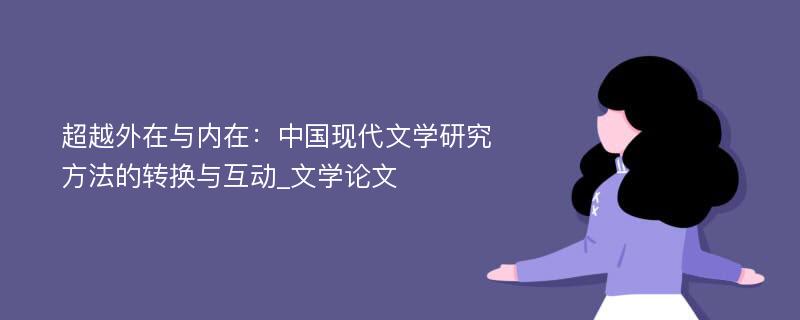
超越外部与内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转换与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07)05—054—059
文学研究有不同的方法,关于方法的选择和流行就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成为一种时代话语。在它的背后有对象、时代的不同和研究主体的选择。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之所以能在中国被接受和流行开来,也有它自己的命运。应该说,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概念的区分及其使用早已存在,盛行于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就隐含了内外的差别。但作为方法论的自觉,或者是说作为一种话语的反思和传播,则主要来自于1984年由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共同翻译,三联书店出版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2005年,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修订本”。
韦勒克、沃伦抱着“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文学的’”[1] (P19)目的写作了《文学理论》,他们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认为文学的外部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学与时代、社会和历史的关系研究,具体体现为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他艺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的内部研究是指“以文学为中心”,对文学存在方式的研究。它把文学作品分为四个层面:声音、意义、意象与隐喻、诗的神话等,文学的内部研究是对四个层面的研究,同时还有对文学类型、文学评价与文学史的研究。一本书并不能改变一个时代,但它可以促进时代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作为新时期“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第一辑四本之一种的《文学理论》的翻译和出版,也推动了中国新时期文论话语的转换和变革。该丛书主编之一的王春元在1984年汉译初版本的“中译本前言”里对作者韦勒克和沃伦的著作的基本理论做了概括和介绍,并不忘提醒读者注意作者的“形式主义立场”与当时的“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存在“根本的差异”,“特别是当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范畴时,作者不惟评价甚低,而且往往做出很武断的错误解释”,但它还是可以作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鉴之用。[2] (P2)不知为什么,在初版本里,没有译者的“后记”对翻译的过程做些说明,只有“翻译说明”而已,且只是说到了翻译的分工情况。一下到了2005年的“修订本”时,又取消了原来的“中译本前言”,而由译者刘象愚写了《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代译序)》,他把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看作是《文学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3] (P8)。时代语境不同了,对事物认识的眼光也有了不同。应该说,《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主要还不是它的“外部研究”,而是“内部研究”。事实上,韦勒克、沃伦自己也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持了反思和批判的眼光,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1] (P145)那么,文学的外部研究是“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研究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1] (P65)。这种研究对理解作品的价值、探讨文学活动的特点、规律是有价值的。但它的“研究起因显然绝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起因和结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那些外在原因不能产生的具体结果——即对文学艺术作品——往往是无法预料的”[1] (P65)。并且,它对文学起因的解释也被“过高地估计”了,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问题。[1] (P66)显然,作为美国新批评理论家,他们宣扬的是文学的内部研究,是文学的形式研究,而不是文学的原因、作家和背景的研究。
这契合并融入了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文学研究对传统社会历史研究的反叛和超越,推动了形式主义文论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两条发展线索,一是从文学的社会历史阶级论向文学的人性论转变,经过了从文学的“人性论”到“主体论”的发展;二是从文学的“人论”到文学的形式主义的“文”论的发展。前者是启蒙主义和人本主义文论,后者是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文论。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提出就是中国新时期文论发生分化和转变的标志。它对内部研究的推崇就为形式主义文论和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对文学性的维护和坚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后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重视对西方以文本为核心的形式主义文论的系统翻译和介绍,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原型理论、结构主义诗学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均有翻译,其代表人物也有详细的介绍。这些翻译介绍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也就是文学本体的关注。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森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文学术语,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文学性主要是指文学文本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独特性,也就是对日常语言进行变形、强化、甚至歪曲所产生的新的语言形式。其他形式主义批评家如巴赫金、热奈特也曾使用过文学性概念,稍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也同样致力于诗歌语言的描述与研究。如克林斯·布鲁克斯的“悖论”和“反讽”、阿兰·泰特的“张力”、兰色姆的“肌质”、沃伦的“语像”、瑞恰慈的“情感语言”、燕卜逊的“含混”等等诗学概念,实际上都是从语言和修辞的角度描述文学性的构成。
文学性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把文学性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它与文学史上关于文学的形式整体性、情感表现性、艺术形象性、语言表现性等说法一样,都不过是对文学特征的种种描述,文学的定义都只是文学在不同时代所呈现的不同话语而已,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无论怎么变化,它都与文学在时代中所面临的不同境遇有关,如文学的历史传统、社会遭际和其他学科知识等等。把文学理解为形式本体,这实际上是新时期中国文论和文学研究对文学的政治话语的极端厌恶以及采取的革命行动。把文学的声音、意象、隐喻和文体等形式看作文学的本质,与把文学看作是政治、革命、阶级和人民的文学,甚至是启蒙、人性的文学,都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对抗。对前者的坚守和维护无疑就会引爆文学研究的方法革命。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论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时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提出不但带来了文学研究的观念变革,而且还带来了思维方法的革命。20世纪西方文论经历了由作者到文本、由文本到读者的两次转移,80年代再次又转移向了文化。它在近一个世纪完成了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再到外部研究的循环。而中国文学研究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较早做出回应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经长期引领中国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成了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生长基地,曾经拥有过令人十分自豪的辉煌历史,也是当下在边缘化过程中而不断被唤起的怀念和梦想。
根据笔者的判断,在《文学理论》出版的一年后,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里,便提出了“从‘内部’来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其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个文学进程中的辨证发展”,他们从语言与文体角度阐释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形式演变和特点。并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打破‘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的割裂。”[4] 他们首次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的“内部”有机性,并把文学研究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维度,这种分法显然借鉴了《文学理论》的看法。他们还从五个方面具体讨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其中在“艺术思维”部分,明确提出文学语言学研究,“把握住文学‘语言’这一关键性的中介,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同时也揭示了文学与社会、与心理、与哲学、与历史等诸种复杂的关系,从而沟通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两个原先被割裂的领域。”[5] 这里,就明确提出了以“语言”为中介实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问题。
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问题,从一开始就以开放的眼光去拿来和借鉴,同时又有所校正和超越,提出了以语言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方法论的统一,而不是机械地照搬。此思路同样显示了研究者的“世界眼光”,同时也有自身的“民族意识”。他们注意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对象的特殊性和方法论的局限性,追求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统一。研究方法应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而选择。研究方法既与对象有相关性,又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有着紧密联系。
近20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审美阐释、形式批评和文化研究等阶段,从研究视野和研究观念看,出现了“走向世界”、“方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和“全球性”等不同时期的不同观念。它充分吸收并运用了当代中国在改革和开放背景下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资源,尤其是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输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出现了蓬勃生机,总体上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从疏离到独立,再到重新融合的过程。所有方法的运用都要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达到高度的契合,否则的话,方法只是一把锋利的刀,如果一顿劈砍后,见到的就不可能是鲜活的生命,而是一具具死尸。在什么样的方法之下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对象,反之,有什么样的对象就应该有不同的方法。中国现代文学是发生在“中国”的文学,有中国的本土性和历史性,如出现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启蒙、革命、政党、阶级等历史现象是不可能完全绕开的,不但不能绕开,而且还要重新面对和思考,特别是在超越政党利益的基础上重建现代中国的历史观、政治观、革命观和社会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运动也应有新的认识和思考,并在这样的背景上思考它们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其次,就是它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是80年代以来重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股学术思潮。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对象与价值相关性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的现代性研究过多地纠缠在现代性的有无和多少上,而忽略了它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笔者以为不可把现代性绝对化、本质化,也不宜将现代性作为裁剪中国现代文学独特性和丰富性的标尺,它应成为激活我们反思和批判的一种精神,由此体验到被历史或现实遮蔽了的生命的真实。现代性一旦转变为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和思考的对象,就已经成为中国的现代性了,即便有所谓的中国与西方、本土与殖民等问题,也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意义发生的一部分,绝对不可能是西方意义的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有中国的现代性。在方法论上,也就不存在内部与外部的所谓区分和差异。现代性既是外部研究,也属于内部研究。有关现代性中的传统与西方问题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它“不是中国和外国的传统决定着中国现代作家,而是现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把握中国和外国的传统,现代作家的主动性在于他们在不同于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条件下进行着仅仅属于自己的追求,不论其成果如何,他们都是为自己和自己的时代而创作。”[6] 第三,它是中国现代的“文学”,那么,这里就牵涉到什么是文学的概念,对于这一点,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学观和方法论,最后都要能够达到充分揭示文学历史本身的丰富性的目的。如果完全采用内部研究方法,就会失去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意义,这也不是恰当的研究视角。如果单单是外部研究,也将带来对文学本身的遮蔽,而把现代文学混同于现代历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没有单一、至尊的研究方法。只有以揭示对象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为中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主体之间,实现方法的超越与互动,才能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同时又面临着新的起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意在实现对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超越。随着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被大量翻译和介绍进来,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80年代开始就对文化问题有很强的依赖性和方法借鉴传统,这促使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转变。80年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哲学、美学和心理学,90年代则变成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从哲学、美学和文化学角度进入文学带有明显的抽象性和理想性倾向,如哲学中的个人、启蒙和自由,文化中的传统和民族国家,美学中的诗意与自由,它们都是世界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建构的一套大概念,适用于阐释追求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则以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意识形态作为考察视角,讨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如何具体制约着观念意识的发生。西方的文化研究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主要探讨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力量的操纵和控制,或者是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采用哪些方式可以使文化力量为其他意识目的服务。它追求研究的跨学科性、大众化、族群、阶级和性别分析,文学成为了它研究的一种材料和对象,文学的界限和特性却容易被泯灭,所有文学文本都被一视同仁看待,并被赋予相同等级的价值意义。这样,由知识分子所厘定的精英文化和文化经典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套价值秩序就被拉入到一个相同的价值平台。它提出走出文本、面对社会的研究思路,极大地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增强了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量,但同时也造成了文学文本整体性的碎片化和意义的零散化,剥蚀了文学文本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应该说,文学中的文化是有文学性和审美性的文化,它区别于其他社会形式中的文化内容;文化性是文学的一种本质属性,文学本身就是从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的,在中国魏晋和西方18世纪以前,文学通常是被作为文化看待的。乔纳森·卡勒就认为:“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7]。即便是作为审美形态的文学,其生产、传播和接受虽具有丰富的文化特性,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应与文学的语言、形式、文体和意义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以避免陷入文化决定论和一一对应的庸俗社会学方法。
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只是韦勒克、沃伦等西方形式主义者为了凸显文学作品的中心性、文学形式的独立性而采用的表达策略。它是对文学人本主义的反拨和批判,开创了现代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文论。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文学研究对它的移植和运用,却体现了反文学的意识形态分析的目的,体现为对文学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多样性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它的进入强化了中国新时期兴起的审美主义思潮,成为人本主义文学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在中国新时期,乃至现代,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形式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截然分离和对立,西方的科学主义在现代中国依然具有人文主义内涵,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也具有人本主义内涵,这一点也不奇怪,反而是现代中国思想和思维方式的特点,以现实需要为目标,不求其名实相符,不以“名”伤“实”,将名实相分,只求其“实”的作用和意义。如果从名与实一致的原则考查,就很容易在现代中国文论中得出传统文论的“失语症”和西方的“伪现代”的看法,的确,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没有变形的传统,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没有变化的西方,只有中国现代意义上真实的复杂的“对象”和“问题”。
文学研究应以对象为基础,以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目的。文学研究的方法是由于对象和问题的存在而存在的。实际上,文学的外部与内部很难分开,从文本的外部也可以分析文学的内在特质,如语言、形式和文体的选择,同样,从文本的内部也可以抵达文学的外部世界,如文化、政治、历史等问题。文学内部研究不应该是完全脱离社会、历史的形式主义研究,文学的外部研究也不应是背弃语言、形式和文体的外围背景研究。就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内部研究,也应通向外在世界,通向文学的社会、时代和文化意义,语言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声音、意象、隐喻、象征的世界,还是一个文化、生命的意义世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也有不同的意象,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隐喻方式。语言本身有先在的历史性和时代性,这种历史性就是人类的文化,时代性就是社会性,对语言的言说和表达不能不成为文化和社会的表述。研究文学文本的语言问题一样应达到对文化、社会、时代的分析。比如郭沫若诗歌中的“大海”、“太阳”意象就不纯粹是语言形式问题,而是时代的文化的精神的符号;同样,鲁迅小说中的“夜”意象也不是自然的语言符号的“夜晚”,而有时代、社会和个人生命的独特感知和体验。鲁迅的杂文文体也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关系到现代思想、都市文化和文人集团的复杂意义。
因此,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都是文学研究的相对概念,没有根本的实质性的差别。看重或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对不同文学的一种建构和想象,文学是被人们按照不同的目的建构和塑造起来的,表面上有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学意图的差异,文学意图是介于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性存在,是对文学与社会、时代、文化关系的不同表述。文学观念就成了对文学的不同解释而已。因此,所谓的文学外部和内部的研究不过是文学研究的两个不同视点而已,二者之间并非是完全矛盾的对立关系。文学是用语言、结构、形式、文体来表达对社会、人生、文化的思考,那么对文学的研究就必然会出现外和内的两个不同视点。如果站在文学立场或以文学研究为目的,即使研究文学的外部,发现和分析出来也是文学问题;站在非文学立场或非文学目的,研究文学的内部所发现的也是非文学的问题。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研究的关系不能被简单理解,也不能被机械化,被庸俗化,被二元对立地看待,而应该综合、全面地看待它们的关系。
之所以有文学研究内部和外部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文论和当代文论的非文学研究倾向的存在,他们逼迫文学内部与外部研究概念和知识的提出和实践,无论是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式说”,还是亚理斯多德的模仿说,还是中国儒家文论的“诗教”主张,道家美学的“无言之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它们都是把文学研究纳入一个更大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立场,从而忽略了文学的独立性。到20世纪,所出现的种种形式主义文论不过是对它们的抵制和批判,是对回到文学自身的呼唤和批评的重建,他们认为从作者、社会、历史、思想角度讨论文学都可能导致对文学的遮蔽,并不是对文学自身的研究,文学的本质不在于表达了社会、文化和生活本质,而在于它有了自己的“文学性”,他们所提出的“文学本体论”和“文学语言论”都是为了把文学从其他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有自己独立存在的形式本体。在此思路和背景下,文学的外部研究就常被判定为是非文学研究的性质。对文学外部研究的贬抑,高扬的就自然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了。内部研究暂时撇开文学与作者、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将文学看作一个虽由其作者创作出来,但却具有了自己的地位,不再受制于社会和作者的存在;文学成为了独立的文本的语言世界,而不是文化世界、社会世界,甚至是人的世界。“内部研究”本身在后来也受到了来自内部的挑战。它也只是一个假定,即关于文学的作者、文学与社会和文化在本文面前只是一个条件,真正意义是由文字组成的“本文”,本文具有超越作者、超越历史关系和影响的独立价值。本文就作为一种能指,成为了新的膜拜对象。但本文概念本身也是不确定的。不同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本文也有不同的看法。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来自与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概念,他给能指赋予了十分实在的意义。所指也是“滑动的”、变化的,能指同所指有密切的关系,能指也就具有滑动的特性,文学的本文作为一种能指的存在就缺乏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出现了对内部与外部研究的反思,问题也出在近年来的文化研究的泛滥和使用的机械化上,从审美文化学角度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思潮、文化冲突和文化意义,包括传统与西方、城市与乡村、世俗与宗教的矛盾,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形态,包括媒介文化、宗教文化、地域文化、道德文化、审美文化、政治文化之间的观念价值和思维方式的复杂关系,都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视野,无论是对文学思潮,还是作家的精神心理、作品的文化内涵都有比较深入而开阔的阐释;在研究方法上,超越了单一的社会政治、审美批评和形式分析,它从整体上综合地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在社会效果方面,它积极配合和支持了8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想启蒙思潮,通过对“文化”这一更广泛存在的社会范畴的分析阐释,文学重新获得把握和参与社会的可能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话语的显著特点。但同时又出现了把文化当作一个垃圾桶,成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箩筐的现象。这反而带来了文化研究的表层化和结论的预定倾向。文化研究逐渐走入死胡同。而诞生于现代传媒、大众文化基础上的文化研究也主要是文论的领地,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基本上还是边缘的观望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方法问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化研究的意义,也不能走向把它们又割裂开来的老路,而应该坚持只有文学,没有内外,只有对象和问题中心,没有方法的本体的立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方法只是进入方式,条条道路都可以通罗马,没有从正门进入才算是到了罗马宫廷的说法。方法是对对象的打开和研究者的解放,不能打开对象的方法,取消研究主体的方法都是机械的方法。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形式主义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