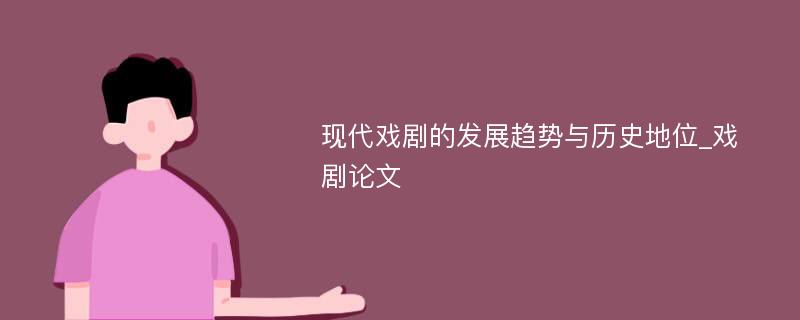
近代戏剧的发展走势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戏剧论文,走势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戏剧包括传奇杂剧、地方戏和早期话剧这样三种不同的戏剧样式。其中话剧出现甚晚,且未成熟,因此当我们试图探讨整个近代戏剧的发展走势及其历史地位时,理所当然地应以传奇杂剧和地方戏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对象。
应该说明,研究者对近代传奇杂剧和地方戏各自相对独立的演变过程及历史命运,已经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论述。但这些论述或许都太“板块式”了,它们所关注的只是传奇杂剧或地方戏(即某一“板块”)独自的演变事实,而不是整个近代戏剧的发展走势。其实,无论是传奇杂剧还是地方戏,都只是近代戏剧的一个子系统而已。它们各自的演变过程及历史命运,总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近代戏剧的总体发展走势,而一旦我们把握住这种发展走势,我们就可能对近代戏剧的历史地位、成就、不足乃至当代戏曲的发展,获得一些较有价值的认识。
1
近代传奇杂剧的命运是最富于悲剧意味的。一方面,为了反映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这种古老的戏剧样式曾经顽强地进行过自我改革;另一方面,这种改革终究未能使这种古老的戏剧样式枯木逢春,随着近代历史的终结它不得不凄然地退出了它曾经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剧坛。
近代传奇杂剧的自我改革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就逐渐迈开步履,并以庚子(1900)为界形成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庚子之前,传奇杂剧作者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始复苏,剧作的内容开始面向现实,传奇杂剧的固有形式也开始自我解放。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原本是传奇杂剧最值得称道的优秀传统之一。但是自清代中叶以后传奇杂剧的创作就逐渐归于平庸和卑俗,其基本特征是“偏得曲词的欣赏,忽视作品的社会内容”。①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深重的国难和民族危机第一次严峻地摆在了国人面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愤激情绪在爱国的知识分子中迅速地弥漫开来。于是一些敏感的剧作家便陆续改弦易辙,用传奇杂剧谱写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了。黄燮清对自己创作于鸦片战争之前的约五部传奇深以为非,竟至“自悔少作,忏其绮语,毁版不存”。②并及时地创作了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新传奇《居官鉴》。李文翰的《银汉槎》隐喻了中国当时内忧外患交相迫拶的严酷现实。③钟祖芬的《招隐居》④和范元亨的《空山梦》也都反映出了鸦片战争时期国人的某种切肤之痛。⑤显然,庚子之前传奇杂剧领域虽未形成带有普遍性的现实主义剧潮。但作为这种剧潮的先导迹象是出现了。与剧作内容的转换相联系的,是剧作形式的自我解放也有剧作家主动实践,在这方面最为自觉的可能是范元亨。他的《空山梦》不用宫调,不遵曲牌,唱词均为相对自由的长短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越出了传奇律曲、制曲的正轨。钟祖芬的《招隐居》传奇更别出心裁地创用了荒诞剧的手法。自然,上述纯属形式范畴的自我解放在当时还只是个别作家的个别尝试,因而还未形成传奇杂剧曲律、体制、语言乃至表演路数的大面积、大幅度改革的时代潮流。
庚子之后,在戏曲改良运动的推动下传奇杂剧的自我改革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传奇杂剧的创作群体也由庚子之前那些大体上都属传统型的知识分子转换为维新运动或革命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比其前辈更为炽烈。而且和对社会政治变革的关注紧密地粘合在一起。因此这一时期传奇杂剧创作无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直接取材,如表现维新理想、鼓吹妇女解放、反映辛亥革命、歌颂革命志士等,还是从历史记载中取材,如表彰文天祥、瞿式耜、郑成功的民族气节等;也无论是以外国事件入剧,还是作家新创神话寓言故事剧,都有一个极为明确的创作动机:用传奇杂剧这一戏剧样式来揭示现实的黑暗腐朽,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因而剧作普遍呈现出极为鲜明的时代性、政治性、现实性、宣传性和战斗性。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⑥收录了此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剧作近三十种,郑振铎认为这些剧作“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⑦此一时期的传奇杂剧从形式看也有了更大的解放,其表现是:在语言上对白增多,且逐步向通俗化、口语化方向演进。在动作上由于所演多为今人今事或西人西事,生活化的动作提示大量增多。在角色安排上不再遵守传奇一定生旦两全的成规及其登场次序。总之,庚子之后的传奇杂剧除曲牌联套这一点仍基本保持不变外(但也相对减少其所占篇幅),其他方面对传统的形式几乎都有相当的突破。
按照文艺社会学和艺术进化学的观点来审视,近代传奇杂剧自我改革的两大取向——内容上贴近现实、形式上突破束缚——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改革的力度也是较大的。然而正确的改革还是未能挽救传奇杂剧最终消亡的命运,原因何在?传奇杂剧的最终消亡不能用晚清传奇杂剧由于过分注重宣传效应而忽视了艺术上的精雕细刻来解释,因为某种文体一个时期的艺术粗糙完全可以期待来日予以改进,文学史、艺术史上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传奇杂剧的最终消亡也不能简单化地套用旧文学必将让位于新文学的规律来解释,因为同样属于旧形式、同样必须按谱填词的古典诗词,不是至今未消亡且已蜕变成新文学的一员了吗?显然,传奇杂剧最终消亡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改革的失误和不力,也不是其艺术生产过程中暂时的偏颇倾向或某些不起决定作用的制作手段,而是决定着其基本样式或形态的曲牌联套体制。
众所周知,曲牌联套体制是传奇杂剧区别于其他任何戏剧样式的根本之处。这种体制是以被称作“词余”的“曲”作其本位的。“词”的填写方法,“曲”的结构形态被植入“戏”的文体创作之中,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它使“戏”由杂耍、献艺而进入文学之林,自元代以降那么多文人一往情深地醉心于传奇杂剧的制作,这不能说不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曲牌联套体制在强化戏曲的文学性时却又派生出“重曲轻戏”的弊端,于是曲词越来越典丽,结构越来越冗长,格律越来越严密、体式越来越板滞,戏曲理应具备的艺术综合性和舞台实践性原则被不断地压抑和弱化。正由于此,传奇杂剧的最终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自清代中叶传奇杂剧的创作普遍向案头化移位开始,它作为“戏剧”的生命力就日渐衰老了。近代传奇杂剧的自我改革不过是给一个濒于消亡的戏剧样式注入一些延缓生命的强心剂而已。唯此,它在那个变动不居、焦躁噪动的时代里着实亢奋了一阵,但亢奋过后则是迅即的死灭。
那么,结论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说近代传奇杂剧内容层面的自我改革竟使传奇杂剧能获得暂时的亢奋活力,可以说明近代戏剧的发展走势这一是面向现实、服务现实,那么传奇杂剧的最终消亡以及导致这种消亡的根本原因则可以从反面说明:追求艺术的高度综合性和舞台实践性同样是近代戏剧发展的走势之一。对于戏剧这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而言,后一发展走势无疑是最不可逆转的。
2
和典雅高贵的传奇杂剧相比,地方戏是所谓“托体既卑”的俗剧。然而近代地方戏的舞台生命力却最为旺盛,这同样是一个颇堪重视的近代戏剧现象。
“托体既卑”当然是正统文人、正统曲家对地方戏的歧视性评价。但是如果我们剔除“托体既卑”这个断语中的封建贵族文化意识和态度,应该承认它还是反映了地方戏的某些弱点或缺欠的,正是这些弱点或缺欠,使地方戏的总体文化品位和传奇杂剧乃至新生的话剧相比显得有些卑下和低俗。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其一,地方戏的作者队伍和演员队伍一般地说文化素养较低,因此他们少有传奇杂剧作者和新生话剧作者们那种较为清醒的时代敏感和改造现实的巨大热情,这使得地方戏直到“庚子”前后戏曲改良运动兴起之前在反映现实、促进时代变革方面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为。即便是戏曲改良运动兴起之后,地方戏虽也取得一定成就,但就新剧作的数量、新剧作的时代性、政治性而言也无法与传奇杂剧和话剧相抗衡;其二,由于地方戏的作者队伍和演员队伍文化素养较低,地方戏的剧本总起来说文学质量不高。“庚子”之前的近代地方戏剧本虽也有少量的文人专门之作,如余治的《庶几堂今乐》,⑧但绝大部分则是由传奇杂剧或古典小说改编而成的。这些剧本多数不仅在内容和人物塑造上无新的建树,而且文词质白无味,章法冗散失检随处可见。“庚子”以后固然出现了汪笑侬、黄吉安等人创作的具有较高文学水准的优秀剧作,但地方戏剧本着遍缺少文学性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改观。其三,由于相同的原因,近代地方戏的戏剧理论建树更为薄弱。
但是,近代地方戏又确乎是近代戏剧舞台上真正的宠儿。到光绪年间,上海的昆班基本上解体,各地的皮黄戏班也基本上不再夹演昆曲小戏,“昆乱同台”演出的现象逐渐消失,以搬演传奇杂剧为能事之“雅部”昆曲在舞台上就几无立锥之地了。和昆曲的黯淡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属于“花部”或“乱弹”的各种地方戏的迅猛发展,其中尤以皮黄和梆子两大声腔系统的地方剧种发展惊人。皮黄腔中的汉剧、徽剧和粤剧基本上控制着当地的舞台,成为著名的地方大戏,而皮黄剧(京剧)则作为中国地方戏之翘楚,先是称雄于北京,后又发展到全国,成为举国认同的剧坛新盟主。梆子腔则覆盖了北方诸多省份,产生了一系列梆子剧种,如陕西的秦腔、同州梆子、汉调梆子,山西的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河南的河南梆子、南阳梆子,山东的曹州梆子、莱芜梆子,河北的河北梆子、老调梆子等。近代地方戏除上述两大声腔系统的剧种外,另一支劲旅是与高腔(弋阳腔)关系更为密切的川剧、赣剧和湘剧等,它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常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此外,近代还产生了一系列在曲艺和地方小调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地方剧种,如评剧、沪剧、越剧、花鼓戏、黄梅戏等。总之,不论近代地方戏存在多少弱点和欠缺,它的发展之快、舞台生命力之旺盛,是无可怀疑的现实。
研究者都注意到近代地方戏迅猛发展这一现实,并对其繁荣的原因作出过多方面的解释。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近代地方戏繁荣的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什么?近代地方戏繁荣的根本原因不是所谓近代都市的繁荣为地方戏的发展提供了种种方便,不是所谓地方戏作为民间艺术深受民众喜爱,不是所谓地方戏的内容和题材无单调贫乏之弊,不是所谓地方戏善于向兄弟剧种学习。因为人们很容易提出下列疑问:近代都市的繁荣不也同样为昆曲的演出提供各种方便吗?何以昆曲沉落而地方戏单单兴盛?地方戏固然深受民众喜爱,但昆曲作为“雅音”不也受到许多知识分子喜爱吗?何以最终竟至几无立足之地?而且喜爱地方戏的难道仅仅是民众吗?清宫内廷不是也嗜演皮黄,并把百余出传奇杂剧《昭代箫韶》翻改成皮黄剧本了吗?地方戏的剧目确实丰富,但其主要剧目基本上都是由昆曲改编而来的,所谓三国戏、水浒戏、杨家将戏,包公戏再加上《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等传统剧目,事实上昆乱皆演,何以单单地方戏内容无单调贫乏之弊?地方戏确实善于向兄弟剧种学习,京剧的定型和成熟原因之一就是能“镕昆弋声于皮黄中”,但昆曲不也向皮黄学习吗?昆曲艺术大师俞振飞不就回忆过他与杨小楼、梅兰芳等京剧泰斗同台演出时受到的教益吗?显然,近代地方戏繁荣的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不是上述数端大体都属于戏剧体制自身之外的原因,而是地方戏的戏剧体制特点及其艺术优长,对此,我们应该作出深入的探讨和把握。
任何事物总首先存在于与它的对立物的对立之中。从清代乾、嘉年间的“花雅争胜”到近年咸、同年间的“昆乱之争”,地方戏一直处在与昆曲及其文学体制传奇杂剧的对立之中。正是在这种对立之中地方戏逐步突破了传奇杂剧曲牌联套体制的限制,创造并成熟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板式体戏剧体制。这是一种全新的戏剧体制,其特点和艺术优长反映在戏曲唱词上,是不再依照一定的曲牌按谱填词,不再象“曲”那样过分追求文采的华丽典雅和抒情意味,而是依照板式(节拍形式)编成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的排偶句,用叙述的口吻道出,因而浅近质朴,易为观众听清听懂;反映在戏曲的音乐结构单位上,是不再以曲牌套数作为基本单位,而是以可长可短的唱段为基本单位,这样戏曲的布局摆脱了曲牌完整性及套数的限制,情节的安排和进展获得自由伸缩的余地;反映在戏曲情绪和气氛的创造上,是不再靠选用不同宫调的套曲来表现,而是主要靠歌唱的长短及板式的变化来调节。⑨显然,板式变化体制首先使戏曲中的“曲”脱下了古典华贵、繁缛呆板的衣装,变得较为通俗和灵活。惟其通俗。它较之已经贵族化的昆曲更易于观众接受;惟其灵活,它使戏曲更易于强化“戏”的机能,使戏曲的艺术综合性特质和凭借舞台表演展示其生命存在的方式得到充分发展。实际上,通俗性、艺术综合性、舞台实践性正是近代地方戏的最光彩照人之处,正是它最终占胜昆曲及其文学体制传奇杂剧的杀手锏。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近代地方戏的兴盛和近代传奇杂剧及其音乐体制昆曲的沉落,反映的是近代戏剧同一个发展走势,即走向通俗、走向艺术高度综合、走向舞台实践。如前所述,对戏曲艺术而言这一发展走势是最不可逆转的,相对高雅的传奇杂剧及昆曲不得不逐步沉落,相对卑俗的地方戏却处处走红,其起决定作用的根本性原因皆在于此。
近代地方戏的兴盛诚然深深得益于它的板式体现戏剧体制,但如果它始终只是陈述或表演那些古老的内容和题材,如果它始终触摸不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它同样是很难得到时代认可,很难具有持久生机的。近代地方戏发展中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它在戏曲改良运动中及时把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时代敏感的知识分子吸纳到自己的阵容中来,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品位,而且为自己的创作和演出注入了原本较为欠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时代性。其中成效较著的是京剧、川剧和秦腔的改良。京剧著名的改革家是汪笑侬,他不仅编演了一批借古讽今,有极强现实批判指向的历史剧,如《党人碑》愤慨于戊戌六君子之被害,《哭祖庙》影射清廷之畏敌卖国等,而且编写了演述波兰亡国惨史的《瓜种兰因》,并亲自身着西装出演,开地方戏编演时事剧、洋装剧之先河。⑩川剧改良则有蜀中名儒黄吉安的参与,黄氏编创的许多改良戏本不仅文辞精美,而且多数也具有现实意义,如《断双枪》宣传禁烟,《凌云步》宣传放足,《邺水投巫》宣传破除迷信,《闹齐廷》抨击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私欲。(11)秦腔也于1911年成立了新式演出团体易俗社,明确宣示其演剧宗旨是“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显然,正是上述改良活动使近代地方戏开始焕发出那种富有时代特征的活力,使近代地方戏开始具有人文意义上的“近代”性质。因此,近代地方戏的发展同样反映出近代戏剧努力面向现实,服务现实,改良现实这一发展走势。
3
明确了近代戏剧的总体发展走势,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评估近代戏剧的历史地位及其不足,这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戏曲的命运也不无某种启示意义。但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在近代三大戏剧样式中,由于话剧还是刚刚出土的幼芽,它的辉煌时代是在现代而非近代,由于传奇杂剧最终归于消亡,它在近代只是作为历史的陈迹而存在着,因此当我们评估近代戏剧的历史地位及其不足时,我们的目光将主要投放在地方戏这一“板块”上,因为只有地方戏才是近代中国戏剧的辉煌存在,并且它毕竟也延存到当代,依然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者。
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近代文学是最受漠视的。因此近代戏剧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的研讨和足够的肯定。其实,只要我们切实认识到走向通俗、走向艺术高度综合、走向舞台实践是近代戏剧最基本的一个发展走势,只要我们不是过分地强调戏剧的文学层面而是全面地把握戏剧的特点,我们将会发现:近代戏剧不仅在近代文学中不容轻视,而且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中国戏曲史上,元杂剧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其基本的依据之一便是它奠定了歌、舞、剧三者合一,唱、念、做、打四样俱全的综合性艺术形式。但是元杂剧和继它之后兴盛起来的明清传奇,都存在着“曲本位”的缺陷。王国维尽管称颂元杂剧为可与唐诗宋词相比肩的“一代之文学”,但他也曾尖锐地指出:“夫以元剧之精髓,全在曲辞;以科白取元剧,其智去买椟还珠者几!”(12)王国维还认为无论是元杂剧还是明代传奇,其“结构”直可称为“至幼稚至拙劣”。(13)曲辞胜便是文学性强,科白弱便必然削弱戏剧的艺术综合性,艺术综合性弱便殃及舞台演出效果,舞台演出效果差便必然影响戏剧的舞台生命。显然,元杂剧及其以后的明清传奇虽然奠定了中国戏曲的综合性艺术特征,但所谓综合性是并非完美和高度有机的。因此中国古典戏曲固然因为杂剧传奇而成熟,却也因为传奇杂剧的“曲本位”特征而逐走向危机,清代中叶以后的绝大多数传奇杂剧只配做“纸上戏剧”,正是报导古典戏剧秋之将至的片片落叶。近代地方戏以其独具的板式体戏剧体制为增强戏曲的艺术综合性带来了极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使中国戏曲终于告别了“曲本位”的传统,在完善戏曲的艺术综合性和强化戏曲的舞台实践性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戏曲也因此而克服了自身的危机,步入了一个新的充满生机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地方戏的繁荣和发展为主要实绩的近代戏剧,是中国戏剧史上戏剧本质更为明显、戏剧艺术更为完善的新阶段。(14)
按照西方接受美学的有关原理,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存在物,只能存在于作者、演员(剧本的活体)和观众三者之间的交互运动之中。以此来审视近代地方戏,演员这一极最强,而作者这一极明显的偏弱。传奇杂剧的“曲本位”实际上是“作者本位”,而地方戏的演员这一极特强实际上是“演员本位”。因此古典传奇杂剧光照后人的是一位位伟大的剧作家而不是戏剧表演艺术家,而近代地方戏光照后人的是一位位戏剧表演艺术家而不是剧作家。应该承认,演员地位的升高是戏剧走向艺术高度综合、走向舞台实践的必然现象,它充分肯定了演员在戏剧创造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较之“作者本位”自有进步之处。但对“演员本位”也不可全然肯定,因为任何时代的戏剧如果缺少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如果产生不出能感受时代脉搏、贴近观众心理、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戏剧精品,这个时代的戏剧成就是不能高估的,这种戏剧的前程也不能是无虑的。不幸,近代地方戏和地方戏的今天,不足之处恰恰在此。
在近代那个特定年代里许多知识分子的深层意识里地方戏显然仍不及传奇杂剧更正统、更正宗。因此地方戏作者队伍偏弱有某种必然性。近代地方戏的这一历史性的缺欠按理在“五四”以后的现代应该得到弥补,但事实却不如此。传奇杂剧此时是消亡了,但话剧却步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一批批才华四溢的剧作家竟相把自己的热情和创造投向了话剧,地方戏依然带着演员强而作者弱的隐性偏枯在舞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着。面对着崛起的话剧,地方戏往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延至当代,由于受影视等艺术的冲击,话剧尚且自感危急,更遑论戏曲。于是人们频频疾呼:“振兴戏曲!”但是怎样振兴?集中海内名角,上演一批脍炙人口的传统剧目,或者定期搞汇演,搞大奖赛,当然不失为一策,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如下两点:第一,继续加强戏曲的艺术综合性和舞台实践性。不必过分强调京剧姓京,川剧姓川,梆子必须是梆子,在维持各个剧种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不妨多吸收一些别的艺术形式的表现方法和技巧;第二,切实加强戏曲反映现实生活,促进历史前进的意识和功能,在这方面认真思考一下现当代话剧名作如《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屈原》、《升官图》、《茶馆》的题材、内容和价值取向,是会有教益的,因为如果话剧也只是无休无止地改编搬演《西厢记》、《群英会》、《白蛇传》、《秦香莲》,它不会象目前这样几乎是独占现代文学史上戏剧一编的地位的。自然,这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舍此别无他途。
注释:
①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213页,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 冯肇曾:《居官鉴·跋》。《居官鉴》系黄燮清《倚晴楼七种曲》之一。
③ 《银汉槎》系李文瀚《味尘轩四种曲》之一,约作于1844-1845年间。
④ 《招隐居》有1894年刊本。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收有此剧,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⑤ 《空山梦》作于1841年,有1891年刻本,附范元亨《问园遗集》后。
⑥ 《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全二册,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社。本节引述的“庚子”后的传奇杂剧之作,均见此书,不另注。
⑦ 见《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叙例”。
⑧ 《庶几堂今乐》是一部皮黄剧本集,收余治创作的皮黄剧28种,有1880年刻本。
⑨ 本文此处参考了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⑩ 汪笑侬剧作可参阅《汪笑侬戏曲集》,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1) 黄吉安剧本可参阅《黄吉安剧本选》,196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2) 王国维:《译本琵琶记序》。
(13) 王国维《三十自序》。
(14) 本文此节参考了康保成著《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但见解与康保成博士同中有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