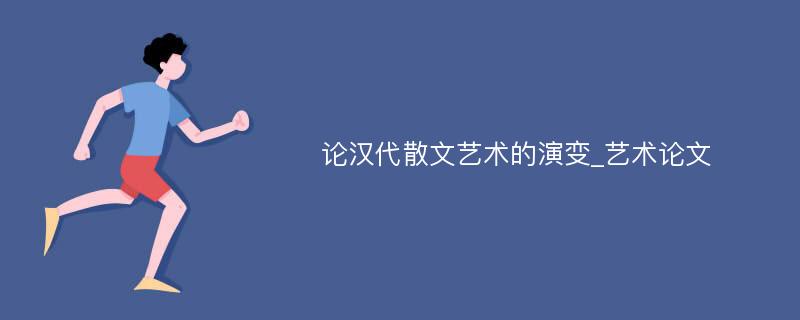
两汉散文艺术嬗变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散文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两汉 散文艺术嬗变 新儒家散文
提要 两汉散文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汉初到宣帝时期。其散文艺术,主要是在继承先秦散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自出变化,显现出逸气纵横、个性突出的特点。二是从宣帝以后到桓帝时期。这是汉代新儒家散文艺术的发展期,成熟期,诸多散文都有依经立义、典雅深厚、茂密阐缓的特点。三是从桓帝时期到汉末。其散文艺术的发展,主要是在继承先秦散文艺术传统和吸纳前二阶段散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自出变化。抽心作论、清峻通脱为其突出特征。两汉散文艺术的嬗变,与两汉思想文化和辞赋艺术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撇开这一点,简单地以朝代为界区别两汉文风,用盛、衰二字分辨其特点,并不能正确地揭示两汉散方艺术嬗变的规律和评论其艺术价值。
在古代散文史上,两汉散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在充分吸纳先秦散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使古代散文艺术的发展跨入全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它在发展中又有新的艺术积累,和先秦散文一起为构建古代散文艺术传统起了奠基作用。不但下启魏晋文风,而且长时期影响到我国古代散文艺术发展的进程。
两汉400余年,散文艺术总在变化。魏晋以降,论两汉散文,多以朝代为界。唐以后,古文家更是持西汉文盛、东汉文衰之说。其实,简单地把两汉散文的发展分为西汉、东汉两个阶段,用盛、衰二字概括其特点,并不能揭示两汉散文艺术嬗变的规律和准确地把握其艺术精神。如果把两汉散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会发现它有不少突出的特点。至少其艺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各阶段的散文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貌。
一
大抵昭、宣以前,为两汉散文艺术发展的第一阶段。历时约一个半世纪。这一阶段的散文,可以说是战代散文的延续,也可以说是在先秦散文艺术经验累积基础上产生飞跃的产物。它集先秦散文艺术之大成,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柳宗元说“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1]。其实只有这一阶段的散文足当其论。
和先秦不同,这时除少数人致力于著述之文的写作外,大量出现的是单篇散文。而著述之文和单篇散文,大都具有雄丽刚劲、逸气纵横的特点。
就单篇散文言,其作者可以分为四组。一以贾谊、贾山、邹阳等为代表;二以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等为代表;三以路温舒、杨恽为代表;四以刘恒、刘启、刘彻为代表。
第一组作者主要活动在武帝即位以前。他们是受战代多元文化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人物,因而思想活跃,文风活泼。本来此时大汉始兴,国家统一,政治、经济发展势头看好,大家对前途充满信心。但是,由于去秦未远,君臣都能牢记秦朝速亡的教训,故其为文,多具忧患意识。喜直言尽言,并且说得激情澎湃;或作夸张之论,以耸人听闻。
如贾谊作论,无论从总结秦亡教训入手,还是从指陈现实问题入手,都是“铺陈帝王之道”[2],为文帝治政出谋划策。而指摘时弊,总是情感激荡,言之深切。文中有大声疾呼语,有太息悲叹语,有痛哭流涕语。均是率性直言,而语语急迫,能以声势、情感动人心魄。可谓奇传雄肆、气盛辞壮。
贾山也好论时政,而“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3]。其代表作《至言》,文中雄肆之气,喷薄横厉,句句有崩云坠石之势。
晁错言事切于实用。其文言政、言兵、言农,疏直激切与贾谊散文相同,而特别显得沉实、峻厉、瘦硬。外具森严之貌,内含凛然之气。
枚乘、邹阳都曾先后做过吴王、梁王的门客,有策士之风而巧于言事。枚乘在吴王反迹未大露时劝其勿反,行文长譬远喻,曲尽利害。看似信笔挥洒,却用语恰到好处。所用譬喻百态横生,又饶有理趣。邹阳在狱中上书梁王为自己辨冤,不直言己冤,而借对众多古人古事的评议以见意。句多排比,语多复笔。气盛词壮,慷慨激昂。把一腔悲愤倾泄无遗。
这一组作者的散文,直接取用先秦儒、法、道、纵横家散文的艺术经验,而受纵横家散文影响最深。同时还取用了辞赋的表现艺术。贾谊《过秦论》即“作论而似赋”[4],枚乘、邹阳即“用辞赋之骈丽而以为文者”[5]。这两种艺术倾向也表现在第二组作者的散文创作中。
第二组作者主要活动在武帝在位的半个世纪内。这时汉代综合国力空前强大,但也潜伏着危机;思想界百家并存的局面仍未改变,但独尊儒术的建议已被武帝接受;在文学领域,由于武帝喜好,辞赋艺术技巧成为文士最为娴熟的作文之道。所以这一组作者的散文艺术特点,受辞赋艺术影响最深,其次才是纵横家文。
受辞赋艺术影响最深的是司马相如和东方朔。司马相如为著名赋家,惯于“以赋为文”[6]。举凡赋的艺术特点,都被他移植到散文中。比如他的《难蜀父老》即取辞赋主客问答方式结构其文,而《谏猎书》变怪百出,多想象之词。出句突兀,说得奇险无比。设句造境,分明得益于赋中奇崛、瑰异境界的创造。
东方朔好诙谐之谈,却敢于谏诤。方孝孺说他“谏诤似汲黯,文辞似司马相如,肆意轻世,旷然有麾斥八极之意”[7],东方朔虽也“以赋为文”,但文章气格高健、情词恳切,却胜过相如之作许多。其《谏起上林疏》,用语激切明快,文气昌盛,与贾、晁文风相近。若论其敢于斥君为非,和行文的言简义丰,似乎贾、晁之作亦稍逊一筹。无怪乎徐中行称其“乃西京谏书第一”[8]。其《答客难》更是借用辞赋艺术,首创一种士人抒发牢骚的散文体式。故其出现后,各代都有仿效之作。
受纵横家散文艺术影响较深,而能加以变化的是司马迁、严安、主父偃等人。司马迁《报任安书》,叙写悲愤,风格沉郁。其为愤发之文。看似任意写去,直言尽言,不加检束,却是潜气于粗豪之中,寓情于字句之内。用字力沉气猛,不避险峭。故其奇矫雄肆,风神横溢。其恣肆雄放,纵横骋词,自是从《战国策》中来。而以气运词,妙传风神,则得《左传》“文章从容委曲而意独至”之妙[9]。
严安、主父偃、徐乐本为纵横家人物,其文自受策士之词的影响。但如严安数落武帝治政之非,徐乐论“土崩瓦解”之祸,都切于实际,绝非战代游谈之上揣摩之词可比。而尽言之词文气紧健,也与纵横家言铺张扬厉、散而不收有别。
和这一组作者生同其时的还有刘安、吾丘寿王。前者尚黄老,后者尚儒学。立论所依有异,文辞详略不同。但在直言其事、径陈其理、固执己见和句求整齐方面,并无二致。
第三组作者活动在昭、宣之时。此时儒学尚未取得事实上的独尊地位,士人心态仍然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故散文艺术的发展能保持上一时期的势头。如路温舒《论上德缓刑书》,说当今刑狱之弊为秦政“十失”之一,实在有耸人听闻之意。又文章博引史实作论,引俗语作证,作断语以斥,亦可视为骋词之作。杨恽所作《报孙会宗书》,受前期文风影响尤为明显。吴汝纶即谓“此文亦脱胎《报任安书》而悍厉过之”[10]。
第四组作者实为几位帝王。汉代诏令多为精心之作,颇能映现一时文风。刘勰说:“观文、景以前,诏休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11]几代帝王,诏各有体,但都语近于质。高帝用语浅近,文帝出语优柔,武帝选言弘奥,宣帝发言峻厉,但都有自然、通脱、实话实说、言简义明的一面。刘恒之作,尤能以情生文。刘熙载即谓“西京之文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彼(指《周书·吕型》)文至而实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12]。显然,刘恒以情生文和这一时期文士作文不掩个性、发愤修书、挟气作论的风气是一致的。
第一阶段的单篇散文有几个特点:一是大都围绕“秦所以亡,汉所以兴”做文章,立论阔大,识见深远。二是尚气善辩,多见先秦遗意。如贾谊、贾山文自儒、法、名、道、纵横各家文中来,晁错文自兵、法、农家文中来,严安、主父偃、徐氏之文自纵横家文中来,司马迁文自楚骚、纵横家文中来。而诸家之文几乎都受到纵横家文的影响。三是将辞赋的某些文体特征移入散文文体之中,把作赋常用的艺术技巧用到散文写作中。四是论自己出,用自家话说自家观点,即使引用成语、故事,也是以论带事,或借事佐证而已。五是句式灵活,以奇句单行为主。较之先秦散文,语助词明显增多。篇法、章法无一定之规。
这一阶段的著述散文,与单篇散文在艺术精神和艺术风貌上也很相似。《淮南子》论述帝王之道,为武帝兴汉提供方略,《史记》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表现作者对“秦所以亡,汉所以兴”的看法。《淮南子》有《易》、骚之奇,得《庄》、《列》之放,指事述意,略近《吕览》。行文则有策士恣肆高谈之风、赋家铺陈张扬之习。故其文奇妙瑰玮,气雄藻丽。《史记》写人、记事,则有《左传》神韵,《老》、《庄》意兴,楚骚情怀。行文则学纵横家言,出语恣肆,尽而有余。刘熙载说“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13],虽论三家文,实则道出这一阶段单篇散文、著述散文和先秦散文在艺术上紧相承传的关系。即如《盐铁论》极写大夫、文学论难之词,有博丽之美。“或有却击如骂,侮弄如嘲”[14],分明也有策士论辩的特点。
当然,这一阶段散文艺术的发展,并非众壑归于一流。其中最突出的,是以董仲舒之作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家散文艺术的崛起。刘熙载即谓“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15]。其《举贤良对策》,首开两汉散文醇厚、典雅、和缓之风。这种文风,在两汉散文艺术发展的第二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二
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约两个世纪,为两汉散文艺术发展的第二阶段。和前一阶段相比,散文艺术精神和艺术风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大多数散文言事说理,持论都以儒学为宗。其次,作家在散文中的主体意识不断减弱,个性色彩日渐淡化。再次,以气运词为敷衍经义所代替,恣肆激切为沉稳从容所代替,言简意明为语赡思靡所代替。第四是纵横家文的影响消退,辞赋艺术的影响更加增强。句式则由上一阶段的不拘长短,而以奇句散行为主,变为渐有定式,而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奇偶相生而以四言成句者居多。
西汉后期,元帝即位,儒学独尊渐成事实。赋作骨力渐衰,由气雄词壮转为气和词平。体物言事,尤好铺陈、形容。受此影响,散文艺术风貌则变夭矫雄健为雍容典雅,变逸气纵横为词茂力缓。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匡衡、刘向、谷永、贡禹、梅福、王嘉等人。
匡、刘均为西汉鸿儒,其文实承董仲舒文风而来。二家文依经立义,好援引经文托为议论,喜称引先古之事以作论证,爱借灾异之事以作发挥。文气阐缓,体貌温厚,有阴柔之美。
元、成之时,匡、刘文风占主导地位。即如贡禹,文风虽形成于昭、宣之时,写出过絮絮如道家常的《上书乞骸骨》,但他上书元帝作抗直之论,却也略引经文,以从时好。元、成之后,书疏本经立义,已成定则。行文却有变化,即经书语录的出现,不再像匡、刘之文那样频繁,而说古称先、讲论灾异愈来愈多。谷永对策文即以经术为缘饰,而其《讼陈汤疏》是引古事作论。楼昉说“西汉末文字,惟梅福、王嘉书最好”[16]。梅、王之书,说理深切、明白,虽也偶引经文,但大量文字是称引古人古事。鲍宣本为名儒,其上哀帝二疏,少文多实,说民亡之祸、进治政之术,直言尽言,可谓激切。但文中无一经辞,都从议论灾异入题。
扬雄是生活在西汉后期、文风异于时尚的人物。所谓“扬雄欻焉,刷翼孤翔”[17]。他作文有复古倾向。虽于前人之作好“放依而驰骋”[18],却“能自树立,不因循”[19]。其文既有先秦散文的平易顺畅,也有其简古奥峭,还有他辞赋的丽辞瑰气。虽不及贾谊、相如之文雄放、恣肆,终不入匡、刘阐缓一路。其《解嘲》虽仿东方朔《答客难》而作,却纵横驰说,锋颖锐利。“气苍劲而词精瘦,恣态横溢”[20]。可谓青胜于蓝。句法历落,不入排偶,也是其文有先秦遗迹的一大表现。扬雄为文,纵然意思平常,语必求新。由于嗜古崇古,深谙字学,故用字不避古奥怪异。以至苏轼说他“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21]。
东汉前期的著述文很多。史书《汉书》独尊儒学,多记灾异。其文虽袭用《史记》者不少,总的艺术风貌却与《史记》大不相同。概言之,则如刘熙载所言:“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22]细言之,叙事则“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23]。“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24]风格则“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之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无余,情意俱尽。此班、马之分也”[25]。“《史记》以风神胜,《汉书》以矩矱胜。”[26]“《史记》宏放,《汉书》详整。”[27]“太史公之文以愤而奇,而孟坚之文以整而奇。”[28]句式则《史记》长短句错综而出,间或有偶句,总以寓骈于散为主。《汉书》则“毗于用偶”[29]。总之,《汉书》以宏赡、典雅、严密、笃实、显明著称。其特点对汉代新儒家散文艺术传统的形成深有影响。
东汉前期,对东汉散文艺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著述之文,还有桓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和王符的《潜夫论》。三部子书的共同特点是:一、指讦时短,意由己出;二,明快严密,句式多变。《新论》反对假托谶纬以言政事,否定神仙之说,既立论独到,又言之得当。王充即谓“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30]。又谓其“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词,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31]。
王充作《论衡》也是独抒己见,破往古之妖妄,订时俗之忌讳;作怀疑之论,正虚妄之说;敢于问孔刺孟,唾弃谶纬神学。其书内容宏洽,立论新奇,辩析有术。或旁引博证,解释同异,纠正嫌疑;或出以锋利之语,摧陷谬异之论;或反复诘难,以骋其说。持理不主一家,儒、法、道、墨,乍出乍入。在艺术上则兼得众家散文之长。其取臂连类,雄辩、宏博,接近道家之文,故刘熙载言“《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32];其峻厉峭拔,接近法家之文,故章学诚言“其文有似韩非矣”[33];其平实、谨严,接近儒者之文,故恽敬言“其为文以荀卿子为途轨”[34]。具体特点是:一、立义创意,无复依傍;放言作论,起结自如。二、辩驳论析,义洽理备,既中肯綮,又言之周严;各篇各章,前后条委深密,矩矱精笃。三、行文单句散行,出语明快、流利;不务深覆典雅,唯求浅露易晓;既作庄语,亦多谐趣。显然,《论衡》的这些特点,是由作者敢于怀疑、敢于批判,立论、行文不循俗迹的艺术精神所决定的。
王符《潜夫论》立论兼用儒、法。揭露时弊、论述治政之术,多切于实际。文风则远受《荀子》、《韩非子》、《战国策》的影响,而近得董仲舒散文之“醇厚”和王充散文之宏博、善辩。
总之,东汉前期子书之作,多能取法先秦诸子,论自己出,“多有个自家在内”[35]。思想、艺术的演变,和此时单篇散文的趋向有所不同。
此时由于儒学极盛,经术地位崇高,臣下奏对,言必引经为据,见诸文字,遂捃摭经文。即刘勰说的“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36]。“中兴之后,群臣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37]。又因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故东汉前期单篇散文,多是侈言谶纬、称说怪异。而文风典雅、和缓、渐多排偶之句。汉代新儒家散文的艺术特点,主要是在这时形成的。
首开东汉散文阐缓、排偶之风的是冯衍。但其文自言其理,自显其志,纵横驰说,逞性叙事,并不援引经辞。对汉代新儒家散文艺术发展贡献很大的是班、张、崔、蔡,而以班、蔡为最。
班固单篇散文的艺术风貌,多与《汉书》中的赞、序相似。溯其源流,则如刘熙载所说:“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味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38]班文虽属董、刘一路,并不博引经辞,只是依经立义。议事论理,温柔敦厚,和雅舂容。不作钩深之论而意无不尽。词茂意密,重章法而尚规矩;句多排偶,用语不贵绮错。
张衡能文,兼擅持、赋。张溥说“东汉之有班、张,犹西汉两司马也”[39],即就其总体文学创作而言。大抵其赋词丽体宏,远胜于文。他是自然科学家,故当图谶流行时,能“发愤陈论,务矫时枉”[40]。其文卓有见识,思虑详细,据事说理而论证严密。
崔骃少与班固齐名。所作杂文《达旨》,既不像《解嘲》任气骋词,也无《答宾戏》之闳丽。或连类举事,或反复形容;迭用譬况,词密意浮;排比时出,偶句络绎。
蔡邕实已跨入汉季。但其文风远绍班固,近接张、崔,既集汉代新儒家散文艺术之大成,同时还受到其他散文艺术精神和艺术技巧的影响。因而他又是汉代散文艺术发展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代表性人物。其文冲和、雅澹。行文坦迤,似不经意,能像班文娓娓而谈,不大声色。而舒详安雅,少警切语,不如班文雅壮多风。较之班、张,蔡邕短于立论,疏于炼句,故钱钟书讥其文“识卑词芜”[41]。要指出的是,蔡邕虽为儒家学者,但他后期对《论衡》极为喜好,“尚其新奇”[42],“常秘玩以为谈助”[43]。另外,论蔡邕之文,既要注意其碑文“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辞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44],还要顾及其《被收时上书自陈》一类文字。它们用语朴质,不务偶俪,时作愤激之词,又是一种文风。后来,他的学生(如阮瑀、路粹等)、朋友(如孔融)、他所赏识的人(如王粲)以及喜好他文章的人(如曹操),于典雅、冲和之外另创文风,不能说与受蔡邕多种散文艺术风格的影响全无关系。
总的看,东汉前期的班、张、崔、蔡和西汉后期的匡、刘等人,沿着董仲舒开创的路子,培育出两汉新儒家散文的文风,形成所谓“汉文本色”[45]。完成了汉代散文艺术发展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由于转变是在儒术独尊的思想、政治背景中完成的,所以这时的散文多是本经立义。或敷衍经义,或博引经辞,持论鲜有创意而多“腐谈”[46]。又由于这次转变是在辞赋艺术充分发展的时期完成的,而许多散文家都是赋家。赋的“以色相寄精神,以铺排藏议论”[47],赋的“依类托寓”、“离辞连类”[48],赋的体物“显亮”[49]、“极声貌以穷文”[50],以及行文的“纷至沓来,气猛势恶”[51],都对散文艺术发展深有影响。故文多博引经传,罗列故事;说尽说透,意少词繁;持论欠严密,短于攻守。如章炳麟所言:“汉世之论,自贾谊已繁穰,其次渐与辞赋同流,千言之论,略其意不过百名。”[52]“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53]而当两汉散文艺术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后,这种依经立义、典雅深厚、茂密阐缓的“汉文本色”便迅速消退,而代之以新的艺术特色。
三
东汉后期70余年为两汉散文艺术发展的第三阶段。从前一阶段到这一阶段,散文艺术的发展,显现出由典雅到质朴、由和缓到激切、由谨严到通脱、由茂密到清峻的变化趋势。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
一、与经学中衰有关。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权的崩坏,依据儒学制订的种种原则、规矩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儒术已不能疗救社会弊病。用引经立义之文论政言事已没有多大力量。这便使散文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不能不跳出汉代新儒家散文的窠臼。
二、与士人心态转变有关。和帝以后,外戚、宦官迭互专权,士人不断反抗,不断遭到打击以至镇压。打击愈狠,反抗愈烈。士人的儒雅风度不见了,代之以刚烈、激愤。《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这种“婞直之风”的流行,自然不利于典雅、阐缓文风的发展。而两次党锢之祸,使士人“有一种忠而见弃的深沉悲哀”。“这种悲哀心绪,和对于朝政的疾视与批评,伴随着他们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54]。所谓“走向自我”,即抛掉对君主的愚忠,挣脱儒学的束缚。对现实政治敢于抗愤、横议。蔑视俗论,高自标置,既“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又在实际政治活动中重义尚气,追求带有独立意识、富有个性特征的人格精神。用这种心态作文,岂能温柔敦厚!
三、与治经学风变化有关。东汉后期,儒生治经已不严遵家法、师法和死守章句。像郑玄说经就能自有见识,而沟通今、古文,兼取其长。释经之文也由繁琐支离趋于明快简洁,并且“在简洁明快的释经中出现了义理化的倾向”[55]。这种新学风,对文风由深厚、茂密趋于清峻,由雍容、典雅趋于通脱,自有促进作用。
四、与道、法、名、纵横家思想复兴有关。经学衰退,道、法诸家思想便乘虚而入。非儒思想的复兴,不但会影响士人的政治见解、文化心态,也必然会影响文风。诸家文风的扇扬,既丰富了东汉后期的散文艺术,也带动了新儒家散文艺术风格的嬗变。
东汉后期文风之变,安、顺时期已露端倪,桓、灵时期已十分明显。这时除少数作者论理言事还详引经辞以作论断、保留上一时期的习惯作法外,多数作者作文都论由己出,径遂直陈,不引或极少引用经辞。而急言竭论,辞锋锐利,意切气盛,以至悲愤淋漓,不掩情性。像黄琼、李固、朱穆、皇甫规、陈蕃、张奂、刘陶、李云等人的散文,无不如此。即如经学家郑玄、延笃所作之书,虽持论不违儒学之理,行文亦抽心而谈,信笔而就。显然,这些人的散文的艺术特色,正是前一时期新儒学散文艺术在东汉后期出现新变的结果。
深受汉末新儒学散文新变文风影响,而作论独持己见,指事类情剽剥儒、墨,学得道家散文跌荡放言、恣肆淋漓之风的是孔融。孔融论人之作,往往重人意气、精神,行文亦气扬采飞;驳难之作更具悍厉之势,或直言其非,或嘻笑诋诮,挟怒气以作攻讦,而出语通脱。刘熙载谓其“遒文壮节”,称其文气骨甚高,“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56]。甚是。同样以气运词、奋笔直书的还有祢衡。应该说,孔、祢都是这一时期将典雅、阐缓文风转变为慷慨多气、清峻、通脱的重要作家。
陈琳、阮瑀的文风深受纵横家文影响。陈琳先后依附何进、袁绍、曹操,人生态度本与战代策士相似。其文亦如纵横家言,敷张形容,气势凌厉。移檄之作,尤善自扬其威,揭敌之短。阮瑀,“简书如雨,强力敏成”[57],也是词随气生,有翩翩之美。二人都是这一阶段行文由简趋繁、崇尚骋词之风的先行者。
曹操也是深受桓、灵时期新儒家散文新变文风影响,而“能自树立”的作家。其文得益于他的尚法术、贵刑名和政治上的务实精神。曹操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但他主张作切实之论。刘勰说“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58]。深忌浮华,正是曹操作文的一大原则。故其文清峻、通脱,却与孔、祢之文逞性作论、用词典丽有别。
此外,像王粲作论善于校练名理,实受名家散文艺术的影响。臧洪作书气骨凛然,固因其遒节壮志所致,也不能排除桓、灵以来儒家散文新文风对他的影响。赵壹之文兼具儒、道散文的艺术精神。而潘勖《册魏公九锡文》铺张典丽,卫觊《为汉帝册魏王诏》文采炳耀,则是对上一阶段新儒家散文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些都反映出第三阶段的单篇散文,随着作者思想解放、论无定检,艺术风格趋于多样化的特点。
这种倾向也表现在著述之文中。崔实《政论》明言治政必用霸道之术,故范晔称其“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不能过矣”[59]。荀悦《申鉴》亦非醇儒之文。仲长统《昌言》论政,也是兼取儒、道、法诸家观点,而“笔致骏发腾踔,在桓宽、王符之上”[60],而“略近贾长沙”[61]。
不过,就句式说,这一阶段的单篇散文,除曹操等少数作家的作品多以奇句散行为主外,大量作品都保留了上一阶段句尚偶俪的倾向。著述之文则继承了上一阶段子书句法自由的特点。这应该是后一阶段较之前一阶段,散文艺术大变之中的不变之处。
四
两汉散文艺术的发展,中经三变,总体艺术风貌依次显现为雄健激切、典雅阐缓、清峻通脱。大抵前期之作,兼用先秦儒、道、名、法、阴阳、纵横家散文艺术经验,主要是在吸纳纵横家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自出变化。中期之作(子书除外),主要是在继承先秦儒家散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自出变化。后期之作,兼用先秦儒、道、名、法、阴阳、纵横诸家散文艺术经验,主要是在吸纳名家、法家散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自出变化。无论何期散文,都有依采前代经典的特点,都受到同期辞赋艺术的影响。
和先秦散文相比,两汉篇各一事、自具首尾的单篇散文明显增多,而且文体大备。虽然汉代出现过像司马迁《报任安书》那样的抒愤之作,像马援、张奂、郑玄、王修所写的诫子弟书,像马第伯《封禅仪记》那样日记体的游记文,像秦嘉、徐淑夫妇所写的“两地书”,像王褒《僮约》、黄香《责髯奴辞》那样的游戏文字,但出现最多的是属于告语体的书疏之作。但比较而言,汉代散文抒情者少,而以说理、论辩居多。两汉散文的审美特征,便是由它以理为主的特性所决定的。两汉散文艺术的嬗变,主要是论辩艺术的嬗变。
两汉散文文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气盛词雄、排宕纵横,到深厚含蓄、温醇儒雅,到简约明朗、峻厉多风的过程。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立论从“由意而出”[63],新颖、深刻,到“假取于外”[64],平实、稳当,到跌宕放言,出人意外。二是说理言事从恣言激切、铺张扬厉、耸人听闻,到称引先古、缘饰经术、含蓄不尽,到纯尚真实、径遂直陈、以气运词。三是句式从参差不齐,贵用短句;以奇句散行为主,不杂骈俪之词;即使对偶也是大体相对,并不要求句法相同,到句多长句、偶句,且对偶要求语词相对、句式相同,但仍以奇句推动偶句运行,到句尚整齐,多作排比。四是语词从疏荡雄丽,到茂密典丽,到简约清丽。用字则从多用古文奇字,到务求雅洁,到不避浅近。
以上说的是单篇散文的情况。两汉著述之文基本上保留了先秦诸子之文理论自成体系、文风自成一家的特点。就其艺术特色的形成来看,虽也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的艺术传统,但似乎主要是在借鉴、吸纳汉代著述和单篇散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而自出变化。比如《论衡》取用《新语》之说,而奇创近于《淮南子》;《潜夫论》辨别是非近于《论衡》,而文风又与董仲舒文相似。他如《昌言》俊发如贾谊文,《政论》有晁错文风,《申鉴》中的“杂言”颇似扬雄《法言》,都能说明这一点。大抵两汉著述文,除了书《淮南子》、史书《汉书》(主要是赞、序)外,都以奇句散行为主。语词简约、质朴、明畅为其共同特点。
注释:
[1] 柳宗元:《柳宗直西汉文类序》
[2] 裴度:《寄李翱书》
[3][18] 依次见《汉书》、《贾山传》、《扬雄传赞》。
[4][41][60] 依次见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第十四则、六十则、六十五则。
[5][9][12][13][15][22][32][35][38][45][56][61] 刘熙载:《艺概·文概》
[6] 王世贞:《艺苑卮言》
[7][8][28] 依次见《汉书评林》引方孝孺语、徐中行语、王维桢语。
[10] 高步瀛:《两汉文举要》引文
[11][36][37][44][50][58] 依次见《文心雕龙》中“诏策”、“才略”、“时序”、“诔碑”、“诠赋”、“章表”。
[14][46][52][53] 章炳麟:《国故论衡·论式》
[16] 楼昉:《崇古文诀》
[17] 孙何:《文箴》,见《宋代文论选》。
[19] 韩愈:《答刘正夫书》
[20] 《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
[21] 苏轼:《答谢民师书》
[23][59] 《后汉书》《班固传赞》、《崔实传论》。
[24] 朱熹:《朱子语类》
[25] 焦竑:《焦氏笔乘》引程颐语
[26] 茅坤:《刻汉书评林序》
[27] 王鏊:《震泽长语》,《借月山房汇抄本》。
[29] 曾国藩:《送周荇农南归序》
[30] 王充:《论衡·案书》
[31][63][64] 王充:《论衡·超奇》
[33] 章学诚:《文史通义·匡谬》
[34] 恽敬:《读论衡》,《大云山房文稿》。
[39][40] 张溥:《张河间集题辞》
[4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43] 《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
[47][48][49][51] 刘熙载:《艺概·赋概》
[54][55]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第一章。
[57] 王杰:《阮元瑜诔》,《全三国文》。
标签:艺术论文; 散文论文; 文化论文; 史记论文; 汉书论文; 读书论文; 论衡论文; 报任安书论文; 先秦散文论文; 淮南子论文; 儒家论文; 纵横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