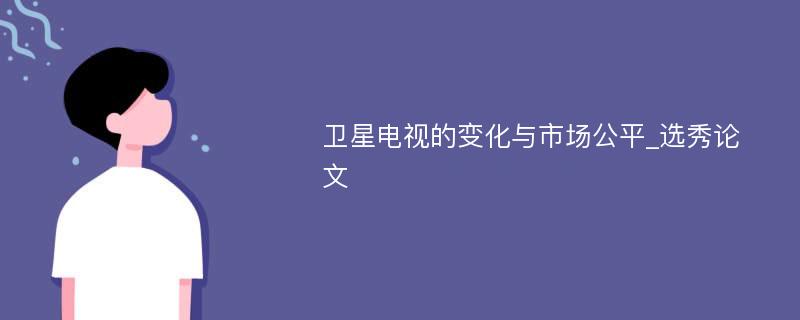
卫视变局与市场公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局论文,卫视论文,公平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国内电视市场的宏观性研究中,往往很难借用成熟的经济理论对研究对象给予较为妥帖的解析,因为时常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对这个市场施加着影响,改变了经济模型的存在基础,那就是行政指令。近半年来全国卫视格局变动,原因固然很多,但行政指令的影响,不应忽视。
2012年第一季度,湖南、江苏、浙江前三甲的排位还相当稳固,二线卫视中开始出现“黑马”,山东卫视收视率跃居第四,偶尔还能挺进前三,其重金打造的《歌声传奇》对频道的人气拉升功不可没;去年排名靠后的湖北卫视,创新力度空前,挤进前十;进入第二季度后,收视排位加剧动荡,卫视前五位座次频繁更替。湖南卫视“龙头地位”开始动摇,于四月第二周跌至第三,其后在第四至第六位之间徘徊;江苏、浙江占据头两把交椅;天津卫视冲进了前三。
本文主要关注近期卫视竞争格局变动的“外因”,尤其是政策因素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影响。经过现象分析和逻辑推演,笔者的思维落点集中到了一个看似不相关、却又实际存在的问题——市场公平。
诚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从本轮卫视格局的变动中,我们看到卫视个体的积极创新与奋进,以及各大卫视对竞争策略认识的趋同。
“限娱”,打开了机会窗
“限娱”与近期的市场“洗牌”,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从内在逻辑上看,也能找到千丝万缕的关联性。一年之计在于春,在市场的耕耘上,卫视同样遵循着这条古训。每逢岁末年初,我们的电视荧幕都会迎来一个节目创新的高峰期。而一纸“限娱”由上而至,对时段、形态、总量的控制,左右了本轮卫视节目的创新方向。据CSM媒介研究统计,以2012年第一季度晚间时段501个进入常态播出序列的新节目为观察对象,与2011年全年水平相比,卫视频道综艺类新节目的数量比例降至27.6%,新闻类新节目的数量比例增至7.6%,专题类新节目的数量比例达到33%。从这一变化,我们看到了“限娱”的正效果,“过度娱乐化”的趋势得到遏制,节目形态更加多样。
但卫视的机会窗口,仍在于娱乐节目。面对“限娱”,娱乐节目总量受到控制,让一线卫视不得不对娱乐类节目做减法,将节目创新集中于新闻及道德类节目;于是“敌退我进”,机会来了,“后进”卫视乘势“反扑”,重金打造娱乐节目。调查表明,晚间时段501个进入常态播出序列的新节目中,播出当月能带动时段收视率提升的仅有66个,其中有30个是综艺节目。这30个新出炉的娱乐节目中,“后进”卫视无疑占大多数;而超过三分之二的新节目播出后,所在时段收视均出现下滑。此消彼长,在创新节目的表现上,“后进”卫视要明显优于排名靠前的强势卫视,这种局部的“胜出”,部分竟得益于“限娱”让“后进”卫视有了“敌退我进”的机会。
卫视竞争格局变动与“限娱”的关联性有多大,还难下定论,对创新节目的研究,可作为一条线索。由于每档新节目都经历过严格筛选和详细论证,被卫视寄予厚望,某些节目甚至是集全台之力打造,对频道整体形象及人气的提振意义更大于收视率本身;另外,各大卫视原有品牌娱乐节目的收视基本稳定,在此情况下,研究新节目更具有典型性。
但由于创新节目的时长毕竟在全台整体节目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对整体的收视贡献仍然有限,因此,不妨将研究范围扩大。
“完全竞争”,收视变动呈偶然性
“限娱令”对娱乐节目形态及总量的控制,从新一轮节目创新的倾向上,我们看到了积极效果。但是我们并没能看到国内学者黄匡宇所预期的——“黄金时段的王牌转移到非黄金时段,这意味着黄金时段必须要做出更有价值的自制节目”①。前面提到,三分之二的创新节目(主要是非娱乐节目)播出后,所在时段收视均出现下滑。因此,在卫视间不存在“合谋”的情况下,单个卫视绝不敢冒风险把收视低迷的新闻和道德建设类节目放在黄金时段,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的现状——黄金时段完全被电视剧占据。
如今电视黄金时段的状态,像极了市场结构中的“完全竞争”状态。“市场结构”是描述市场竞争程度和集中度的概念。“完全竞争”是一种高竞争度、低集中度的状态:每个企业都出售完全同质的产品;厂商众多但都不强势,竞争激烈;每个企业只能按既有价格出售产品;如果单个企业私自涨价,则产品会完全滞销;如果单方面降价,虽赢得销量的大幅飙升,但是利润微薄,且破坏了市场秩序,容易引起恶性竞争。当前电视的黄金时段,与这样的状态高度一致:卫视众多,同时播出电视剧,并且某些剧因常常是多台“联播”会同时出现在多个频道,如果单个卫视采取提前播出或变相提高播出进度抑或压缩广告时间等变相“促销”手段,则会带来收视提升。
把电视剧看作完全同质的产品,似乎缺乏严谨。但是通过对受众收视习惯的分析,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央视市场研究”早期(2004年)做过有关调查,85%的观众的电视收看习惯属于“随便搜索,发现好的就看”②,这个比例在当前新媒体的冲击下,恐怕还会升高。电视剧对于“随便搜索”的观众来说,或可看作是同质的,除非对某部剧有事先了解。
电视剧收视本身带有偶然性,我们常常看到所谓的“大剧”收视惨败,观众口味永远处于不确定之中;再加上观众观看习惯的不确定性,当前黄金时段成为一个拼运气的博弈场。这些不可把控的因素,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大家获得一个“平均收视率”(既有价格)。对于某些联合购买、同步播出的电视剧,由于“积聚”效应,会提升该剧的关注度;而一部剧的胜出,会带动一批卫视的收视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的“后进”卫视就搭了一轮“便车”。例如浙江、安徽、天津、上海抱团同播的电视剧《心术》,各台收视率接近,并长期处在黄金时段收视前五位;《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五号特工组之偷天换月》《独刺》等联播剧均表现不俗。
湖南卫视因响应“限娱”之令,以“金芒果独播剧场”取代19:30-22:00自制节目带,加上22:00“金鹰独播剧场”,湖南卫视周日至周四整个黄金档完全交给电视剧,成为了“完全竞争”市场中无差异化的一员,收视下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仅仅是遵循概率分布的结果;同时,由于自制能力的过剩,人才和节目创意大量外流,带动了一批“后进”卫视的节目创新。卫视收视有可能因此再一次“此消彼长”。目前,湖南卫视已着手改版,首先动刀的就是“金鹰独播剧场”,原22:00档电视剧将由十档全新自制节目取代,相当于将“限娱”前19:30-22:00档和22:00-0:00档的节目安排做了对调。
选秀,或将收视进一步拉平
新办娱乐节目提升了卫视的人气,原有品牌娱乐节目依然坚挺,新闻类节目扛不起收视重担,道德建设类节目遭到冷遇,电视剧收视充满不确定性,以上分析基本可以反映当下卫视竞争状态的全貌,并可隐约看到一种“外力”对整个格局的影响。
由于选秀节目的特殊性,在此单独拿来研究。清华大学赵曙光归纳了常见的受众诉求要素:重要性、显著性、利益相关性、情感体验、信息量、悬念冲突、转折与戏剧性、互动及参与等③。满足越多的诉求要素,节目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这一归纳基本能解释娱乐节目能赢得更高收视率的原因,尤以“选秀”为甚。《超级女声》的成功对于湖南卫视乃至整个卫视市场,都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山东卫视总监闫爱华将深藏在卫视思维中模糊的、尚未成型的观念一语点破:“从几个一线卫视走过的道路来看,选秀是二线卫视冲击一线卫视的必由之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更合适、更有利的捷径。可以说,办好一档选秀不见得能从二线冲到一线,但想冲到一线必须要成功地办一场选秀节目。”在这个市场浸淫多年的电视人,触角是敏感的。今年,走上这条“必由之路”的卫视,已不下十家。目前已正式启动的栏目有:《花儿朵朵》(青海)、《激情唱响》(辽宁)、《中国红歌会》(江西)、《中国藏歌会》(四川)、《天籁之声》(山东)、《完美声音》(云南)、《THE SING-OFF》(深圳)、《一声所爱·大地飞歌》,湖北卫视《盖世英雄》还在酝酿,以上选秀全是歌唱类,并且定位雷同。值得注意的是,这当中未见传统一线卫视的身影;只有长期屈居第三的浙江卫视《非同凡响》“疑似参战”④。
在越位晋级的策略上,各大卫视不约而同选择了“选秀”。前面提到,选秀类,尤其带有很强竞技性的歌唱类选秀,在满足受众诉求上具有先天优势;在经济投入、获取广告商支持、受众的“接触点”数量以及整合营销的力度上,歌唱类“选秀”都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节目。可以想见,未“参战”的一线卫视还将面临更大的冲击;今年的卫视收视格局,在一片嘈杂声中,还将处于长久的动荡中。
竞争,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环境?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近期卫视收视格局的频繁变动,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与“限娱”有关联。电视研究者是否应该反思这种“关联”的合理性,或者说行政指令带来的效果是否理想?
从娱乐节目的总量,以及娱乐化倾向上看,“过度”的问题得到了较为有效的遏制,容易滋生低俗化的土壤“铲除”了,低俗化自然减少了;同质化的问题,在节目形态的抄袭和复制上得到控制,但由于电视剧的充斥,使同质化换了一种形式存在甚至加剧;文化品位,因新闻、科教、公益类节目尤其是纪录片的比例提高有所提升,而用电视剧替代娱乐节目是否意味着文化品位的提升,还需做个案分析和比较研究。总体而言,“限娱”的监管目标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但是,任何一项针对产业的调控政策,即便是出于政治和社会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一项经济政策,会对整个市场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因此,对于政策调控只做政治考量,是不全面的,还需对经济后果进行考量:“限娱”对“量”和时段的限制,降低了卫视间的差异,使原本良性的差异化竞争转变为粗放的“完全竞争”,使市场结构陷入“亚健康状态”;不加区分地以节目形态划线,将所有卫视拉回到同一起跑线,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规则,也有违市场公平。笔者想起了作家王小波谈过的平等问题——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另一种是向下拉平,实行容易,只需对“冒尖者”施以“闷棍”⑤。此番政令“一刀切”的做法,颇有“向下拉平”之意。
市场公平不是市场份额的拉平,而在于健全法制下,主体地位与外部机会的均等。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基础,为了社会和政治目的,损害市场公平,是否值得?这考验政策研究者的智慧。尤其在中国广电产业化刚刚起步、屡遭挫折、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难以形成的特殊背景下,对市场的干预更需慎重。
是否一定要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做出取舍?有没有两者兼得的做法?回到“限娱”问题,能否在“反低俗”、“反同质”的同时,不伤及市场公平?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要基于对娱乐节目及受众的重新认识。
娱乐类节目在满足受众诉求点和“接触点”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注定会形成大的影响力。正因如此,也容易进入学者的视野,形成舆论。可以预计,今年的“选秀乱战”,必将引来新一轮的口诛笔伐。于是出现了一幅自相矛盾的图景:学界业界一面大力鼓吹满足受众需求,大力提倡通过整合营销传播应对新媒体的冲击,一面又要对身体力行者用力挥舞道德大棒,矛头直指“低俗”和“娱乐过度”。难道娱乐节目因“低俗”才受热捧?如上文,娱乐节目由于天然的形态优势,其高“热度”具有必然性,与低不低俗无关。那么,是否“过度”了呢?
在早期电视可以垄断观众注意力的年代,传播学研究者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忧:现代媒介“既调节公众生活,又控制私人方式,不仅灌输思想,而且还渗透进了人的心理结构,把确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强加给人们,使人失去内在的自由和独立的决断能力”⑥。这个理论基础一致左右着传媒监管者和研究者的思维,直到今日。对于“度”把握,一直受到格外关注。但是对于受众的认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向,尤其是在新媒体出现后,电视地位开始动摇。人们开始从“看”电视,转变为“用”电视;人们开始从遭受“这种使人上瘾的、致幻性的物质(指电视)的麻醉作用”,转变为“随便看看”⑦。
受众的使用习惯已经改变,电视媒介的影响力在下降,对于是否“过度”的问题,不能仅凭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所营造的反对舆论和对电视娱乐氛围的感性体验就做出判断,而需结合新的行业背景,用更为科学的定量手段加以考量。
“反低俗”本身隐含公平意义——防止电视媒体以低俗内容博得收视率,但如果将矛头指向节目形态,则有可能“错杀”好节目,反而有违市场公平⑧。只有针对内容品质(而不是节目形态)来反低俗,才是政治与经济的“双赢”之策。“低俗化”解决了,“过度”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针对内容品质制定反低俗政策,国外已有成熟经验:首先,重点在于明确“低俗”的判定标准,以及违规的惩罚措施。例如,美国的低俗节目是指那些尚未达到淫秽色情等级,但是又明显带有猥亵、不敬、脏话等下流内容或者公然冒犯社会基本道德水准的电视节目。其中“猥亵”、“不敬”等关键词都有详尽的解释和评判标准。我国的判定标准可酌情从严提高尺度。其次,要建立公民投诉渠道及处理投诉的专门机构,一旦判定触犯禁令,则上报总局,着手调查。另外,可通过行业协会的职业规范以及各电视媒体的专职把关部门,对区域内从业人员进行行为约束。这些法例,在香港也有着确实的体现和实施。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引入节目过滤硬件设备和电视分级制度,实现自我约束和监督。⑨
由于电视产品特有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国内外的电视行业大都处于“高监管、低自由”的状态。“低自由”是相对于一般的产品和产业而言,如果监管措施细致而明确,各个市场主体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公平与自由,正是当下卫视最为需要的外部政策环境。
注释:
①李青:《一纸限娱令能治道德病?》,《羊城晚报》,2011年10月30日A3版.
②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电视观众生活形态调查报告(2004年),2004年版.
③赵曙光:《媒介经济学》,2007年版,P39.
④刘亚娟:《选秀“乱战”:近10档歌唱类选秀节目征战暑期档》,《综艺报》,2012年11期.
⑤王小波:《椰子树与平等》.
⑥⑦赵曙光:《媒介经济学》,2007年版,P36.
⑧谢江林:《“限娱”:倒掉“脏水”,还会倒掉什么?》,《南方电视学刊》,2011年第6期.
⑨李世成、黄伟、张许敏:《美国低俗电视节目的监管与启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