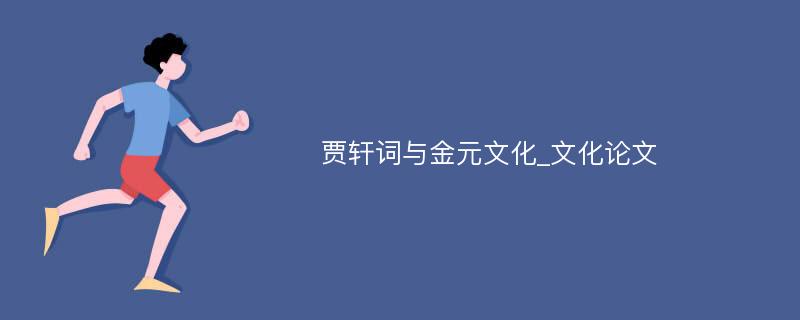
稼轩词与金源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稼轩词论文,金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稼轩词一直是词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辛弃疾被作为南宋最重要的爱国词人,受到词学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对其主体精神和词体风格等方面的探讨,多是在南宋或两宋的范围内寻求解答,忽略了当时的中国词坛,北方还有半壁江山,而作为词人的辛弃疾正是生于斯,学于斯,投宋后其思想情感仍留在了这块土地上。所以离开了对金源社会,特别是对其文化形态的考察,当无法真正地理解稼轩词。
由金源文化性质看稼轩词爱国主义精神
稼轩词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
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稼轩词表达了“挽救国家民族的伟大志愿”,对“国家和民族存亡”及“华夏文化沦亡”的深切忧虑(注:见夏承焘、游止水《辛弃疾》(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等。)。很显然,这些论点都是从以南宋为“国”、北金为“敌”的角度立论的,其“国家”、“民族”的概念,并不包括北方的金国。也就是说,辛词的爱国主义性质是定位在抗击“外国”、“异族”侵略这一层次之上的。还有一点也很明确,论者所使用的“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与“中国”、“中华民族”的一般意义完全相同。
对于稼轩词爱国主义内涵的这种规定,实际上忽略了当时金源社会的文化性质。宋、金分立与历史上一般的分裂状态(如东汉后的三国)固有不同,它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对立,亦即“夏”、“夷”之间的对峙。但中国历史上的“夷”、“夏”,实质上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外”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如钱穆先生所论,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在这种海内一家、天下一体的观念中,四夷与诸夏分别的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3页、41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在地理观念处于封闭状态的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中国,应该承认钱氏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自周秦以来天下一体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历史上分裂的南北双方(包括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历来都被包括在大中国的概念之中。实际上,宋人包括辛弃疾本人也没有认为宋、金对立与历史上的南北朝局面有什么本质不同(注:见辛弃疾《美芹十论·自治第四》。)。此外,稼轩词产生的12世纪下半叶,女真族实际已经完成了由“夷”到“华”的“文化”转变,正如《金史·文艺传序》所述: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钦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金统治者一系列汉化政策的实施,使这个起步于落后游牧社会的政权性质逐步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特别是金统治者对“德运”问题的重视和科举制的恢复,作为明显的标志,表明了金源文化成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和一部分的性质。可以说除了皇帝的种姓不同之外,金政权与南宋政权在本质上已无大的差别。这一阶段的女真族统治已与其初入中原时以破坏为主的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此时宋金关系也进入了力量均衡、双方都不具备统一条件的相峙阶段,从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南、北朝时代。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双方和东汉之后的三国一样,宋、金之争实质上是中国内部两个政权争夺正统地位和完成统一基业的斗争。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稼轩词产生的12世纪下半叶,并不存在“中华民族”的存灭问题,更不存在“华夏文化”沦亡的危险。如果将稼轩词以抗金恢复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精神,定位在抗击外国入侵,或者称为挽救民族文化精神衰亡的层次上,显然,客观上并不存在其立论的前提。
我们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否认稼轩词爱国主义精神的存在,而是予之以更准确的科学定位。从上述金源社会的文化性质看,只有从恢复统一消除分裂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精神,才符合历史客观实际。事实上,辛弃疾反金恢复思想的现实基础,正是祖国分裂的局面及其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在稼轩词中,我们不难发现词人有着一个顽强的“补天”情结,“西北有神州”、“西北望长安”、“举头西北浮云”一类语句不时见于其笔端,分裂的神州已成为他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以至于在残阳、残月、残花、残山、残水一类自然物象和睽离、分别之类社会现象的描写中,往往都融入了他忧国忧民渴望统一的情怀;而“补天裂”、“补天西北”、“整顿乾坤”等语更是直接表达了其反分裂主统一的强烈愿望。这一由现实激起的愿望,同时又是与民族文化心理中生于“天下一家”思想的“大一统”观念相契合的。大一统的实现是历代政治家最基本的目标,“分而必合”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辛弃疾的恢复主张也正是基于对这一“天下大势”的清醒认识,这在其《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可清楚地看到。可见,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文化传统,都决定了稼轩词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内涵,只能是对消除分裂、恢复统一的渴望与追求。
客观地讲,在12世纪后半叶,金源对南宋的征伐也带有完成统一、正统天下的意义,既然如此,辛弃疾为什么一定要弃金投宋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邓广铭先生曾以“对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深切忧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对沦陷在金人铁骑下中原地区的乡土和人民的缅怀和同情”(注: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几点来概括辛弃疾反金投宋的动机,如果将第一点中的“国家和民族”限制在南宋范围的话,邓氏所论显然揭示了稼轩及其词作反金恢复思想赖以生成的某些本质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把稼轩词视为包括金源文化在内的特定时代的文化载体的话,便会看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诸原因下面,还有着更深层的复杂的文化心理动因,而上文谈到的“夷夏之辨”观念则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前所述,金源社会虽然在文化上已成为华夏民族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在“道统”上可以取得广大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同。但是非汉族人为君主的事实仍难以被纳入封建“正统”体系之中。在这一统系中,周边地区的“夷狄”如同大家族中的小宗庶出之子,只有臣服的义务,而没有为君的权利,故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而在汉族帝王的统治被少数民族种姓所取代时,这种“正统”观便成为一种拒绝认同新政权的强大心理情结。汉族政权南宋存在的事实,无疑又使金朝汉士心中的这种“正统”观更难消释。无庸讳言,这种“尊夏攘夷”观念当是辛弃疾走上反金道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这在稼轩词中有十分明显的表现,而在其奏议中表现得更直接,如他《美芹十论》中曾以“晚妾之御嫡子”之语来比喻女真人对汉人的统治关系,即为一明显例证。
就辛弃疾的人生道路而言,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古代士人传统的“功名”意识,具体地说辛弃疾两次举进士而落第的事实,对于他举兵反金有着不可忽略的关系。辛弃疾作为汉士,尽管他从“正统”上难以完全接受女真族的统治,感情上有着亲近南宋的天然倾向,但他仍然可从理智上说服自己为金政权服务。因为“华”、“夷”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区分,“进于中国”的金统治者已取得了“据天下之正”资格,这对于以“治国平天下”为价值目标的士子已不存在拒绝合作的基本理由。他两“随计吏”之事,已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如果没有出现山东农民大起义这样的契机,如果辛弃疾科场得意,中第授官,凭其才华,如其同学党怀英和后辈赵秉文等人,功业有成,名显金廷,也未可知。南宋末谢枋得《祭辛稼轩先生墓记》中的一段记载是值得注意的:
辛弃疾……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
此事有无且不论,但至少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宋金时代的人们(包括辛的崇拜者)并不像今人那样认为辛、党的去留有着明暗抉择的意义,而只是将其看成一种对成就功名途径的选取。由此看,寄希望在南宋实现包括获取个人功名在内的理想抱负,当是辛弃疾反金投宋动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稼轩词所表现的强烈的功名意识,即是很好的说明。辛弃疾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个人的功名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指出稼轩词反金恢复思想的深层文化心理动因,丝毫无损于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而是使其显示出了更为真实更为深刻也更富于个性的具体内容。
苏学北行与稼轩词的文化特质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反金恢复是稼轩词最基本的主题,但是稼轩词在金源词坛却备受推崇。作为金源文坛“一代宗主”的元好问给予稼轩词以极高的评价,他说:
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注:元好问《遗山自题乐府引》、《新轩乐府引》。)
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注:元好问《遗山自题乐府引》、《新轩乐府引》。)
以上所论有两点应予注意,一是旗帜鲜明地以苏、辛并列于冠首,就今见资料看,在词学史上尚属创论。终南宋之世,关于稼轩词“非雅词”、“粗豪”、“非词家本色”之讥从未休歇。可以说,直到元好问之论出,稼轩词的词史地位才得到真正的确立。二是明确地指出从苏轼到辛弃疾,词坛上存在着一个“皆自坡发之”派系,并以“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来概括其共同的词体特征,其中“清壮顿挫”言其风格,实启后世“豪放”之论。
为什么稼轩词在南宋被视为别体而在金源却位居正宗呢?就遗山所论可看出,稼轩词之被看重与其“自坡发之”密切相关,因此了解东坡与金源文化的关系,当是揭示遗山推崇稼轩原因的关键。
东坡豪放体词的出现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且有“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辈继踵,但并未被当时词坛普遍接受。宋廷南渡,词风始变,东坡影响渐著,出现了一批接近东坡体词风的慷慨激昂的爱国词和超逸绝尘的隐逸词,其中朱敦儒和张孝祥的创作最引人注目,但影响有限,远未改变词坛风气。也正因如此,稼轩词出于南宋犹如异类突入,而难为习俗接受。也就是说,稼轩词并非南宋词“本色”,其词体根脉不在南宋文化土壤中。这就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辛弃疾成长与就学的北方金源社会。
事实上,在稼轩同时和稍后,已有人注意到辛词的北方文化特质,如曾为《辛稼轩集》和《辛稼轩词》写过序文的刘克庄和刘辰翁在其文中皆论及稼轩词的“英伟磊落”、“淋漓慷慨”之气与“斯人北来”、身为“北方骁勇”之间的关系。元人赵文《青山集》中的论述对我们更具有启发性:
渡江后,康伯可未离宣和间一种风气,君子以是知宋不能复中原也。近世辛幼安跌宕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而已。
稼轩词“跌宕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所显示的正是一种北方文化特有的刚健豪爽的精神气质。清人况周颐对稼轩词所禀承的这种北方文化精神看得十分清楚,其《蕙风词话》云:
金源之于南宋,时代政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曷与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尝不可南;如吴彦高先在南,何尝不可北。细审其词,南北确乎有辨……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
值得注意的是,辛词和吴词虽被公认为代表了当时南北词坛的最高水平,但况氏却没有将二人列为南北词风的典范。显然他意识到二人所作与南“秀”北“清”的风格不相类似,其原因又与辛“先在北”和吴“先在南”的身世有关。基于对其词作美感特质的“细审”,况氏认定“南北确乎有辨”。
靖康之变,南北分治,文学创作也因之而各呈异貌。北方金源统治者出于“正统天下”的需要,有意识地学习和引入汉文化,促使了传统儒学的复兴,由此重道务实的“苏学”适得其所,被文人士大夫广泛接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清人翁方纲所称“程学盛南苏学北”(注:翁方纲《书元遗山先生集后》。)。金源文人对于东坡的仰慕,包括了对其政治主张、哲学理论乃至整个人格理想的欣赏与推尊,更体现为对其诗词、文章、书法等艺术创作的崇拜与追摹。赵秉文《东坡真赞》诗“裹粮问道往从之”句,正是金源文人这种尊苏心态的形象表达。苏学之于金源学术,最大的影响当在文学上,尤其是词的创作,直接禀承苏轼所创立的言志之体及其所特有的刚健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北宗风范。词的“应歌”功能在北方的迅速衰微,北方民族崇尚豪爽之气和刚健之美的文化心理,都促使金源词坛对以“豪放”为基本风格特征且具有明显诗化倾向的东坡词的认同。作为文坛领袖的赵秉文和金源最重要的批评家王若虚均有以东坡词“为古今第一”之论,而在一般文人士子中,尊苏学苏更是蔚然成风,元好问《续夷坚志》中的一段记载颇可说明问题:
承庆字昌叔,襄城人。父文仲,承安中进士,以孝友淳直称乡里,官至文登令,年七十余卒。沐浴易衣冠,与家人诀,怡然安坐,诵东坡《赤壁》乐府,又歌“人间如梦”以下二句,歌阕而逝。
此为一极端的例子,但有金一代文人对东坡词赏爱至极的心理与风气由此可见一斑,而其于词坛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遗山《自题中州集后》诗称“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气尽豪”的中州文学自然是包括词在内的,以“气”为主,以豪放刚健为尚正是东坡体词的基本特征。事实正是如此,从金初“吴蔡体”到金末遗山词,其总体精神与格调可谓均出东坡一脉。
辛弃疾在北方金源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就其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看,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其艺术观念和创作功力的基础,金源文坛的宗苏风尚对年轻辛弃疾产生深刻影响,当是必然之事。稼轩词“自坡发之”,准确地说,应是自遗传有“苏学”基因的金源文化“发之”。如果没有金源文化的熏陶,很难想象稼轩词于南宋词坛一出手,便能以相当成熟的形式,在根本艺术精神上显示了与东坡的相通与契合。遗山极赏稼轩词,辛作在文化气质、审美祈向、风格流派上与金词的一致,或者说稼轩词对东坡词本质上的继承与发展,当是最根本的原因。
吴蔡体对稼轩体的直接影响
有金一代词坛“苏体”大盛与立国初所出现的“吴蔡体”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而“吴蔡体”对于辛稼轩词学思想和词体特质的形成,则起了直接的启发和导向作用。元好问《中州集》卷一云:
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
伯坚即蔡松年,有词《明秀集》,吴彦高名激,有《东山集》。金初吴、蔡齐名,所作词“脍炙艺林”,由于其词体的某些共同特征和相当的词坛声誉,故被称为“吴蔡体”。“吴蔡体”对“稼轩体”形成的影响非同一般,辛弃疾居金时曾有拜师蔡松年事,《宋史·辛弃疾传》载:
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
元代虞集《题李溉之学士湖上诸亭》诗有“受业萧闲老,令人忆稼轩”句,即咏辛弃疾拜师蔡松年一事。稼轩体导源于吴蔡体最好的证明当是二者词体本质上的内在联系。从东坡到稼轩是以言志抒怀为本质特征的豪放词体由初生到大成的发展过程,而吴蔡则是其间递传薪火者。
东坡“以诗为词”的词体革新意义在于使酒边游戏的“小词”,像诗一样有了言志抒怀、全面表现作者人格理想的功用,但苏轼做的并不彻底,至金源“吴蔡体”出现,言志化才真正成为乐府词创作的主流。这个过程的完成实质上是随着词乐的衰微,词体功能逐渐由应歌娱人向交际自娱转变的结果。
女真入主中原后,由于战乱而造成的词乐资料的散佚、音乐人才的缺乏以及新兴北曲的繁盛等原因,词体应歌功能迅速衰微,脱离了歌场的词,不必再考虑如何代人言情和取媚世俗,而以自我情性的畅抒和快适为追求,这无疑会促使词体言志化的发展,此意不难理解。而关于交际功用对于词体言志抒怀的影响,论者历来多持否定态度,如周济、王国维就强烈反对以词“应社”和“美赠投刺”(注:见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王国维《人间词话》。),但实际上交际活动如果不抱过强的个人功利性目的,而是以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为主要内容,特别是亲人知友之间的交游,往往是彼此敞开心扉的机会,反映在作品中的情思自然应是自我主体意识的真实表现。词介入作者的交际,也就是介入了作者的现实生活,也因之有了与作者主体意识发生联系的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定词体功能从应歌向交际的迁移作为一个条件和标志,来论述词的内容由客体化向主体化转变过程。事实正是如此,东坡体的主体精神在吴蔡体中的主流化、本质化,以及在稼轩体中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正是通过词体功能的转变来实现的。
社会交际,是传统诗歌的一个基本功能,而大量地将词用于社会交际则是从具有明显诗化倾向的东坡词开始的,其豪放词代表作多为这种交际活动的产物。在发挥词体的交际功能方面,较之东坡后至南宋初的词人,吴蔡词更为全面,也更为彻底,蔡松年所存词86首中大约有60%以上的作品与词人的交际有关。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交际成为其词体基本功能的同时,吴蔡体在词史上第一次将表现内容从总体上定位于作者自身的雅志豪情。从题材上讲它已经彻底摒弃了淫靡香艳之气,即使个别艳情之作,也不失蕴藉风流之致。总之,在吴蔡词中,交际功用已成为词体实现充分言志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从词体交际功用这个角度看,稼轩体与吴蔡体是一脉相承的。南宋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云:“稼轩胸中今古,止用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此说虽嫌绝对,但辛弃疾确实全力“为词”,实际上他是将诗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地位和功用转让给了词,因而其创作与其社交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据统计,《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江、淮、两湖之什”共词88首,而确切标明关涉社交的有44首。其中难免有一些言不由衷之辞,但从总体上讲,其英雄之怀和恢复之志借助词体的这种交际功能而得到了充分展示。与吴蔡体相比,稼轩体所涉及的社交面更为广泛,所表现的内容也更为深刻。词往往成为辛弃疾在交际中陈述政见的工具,甚至寿词也是如此,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渡江天马南来),《寥园词选》评道:“辞似颂美,实句句是规励,岂可以寻常寿词例之。”当然,在南宋中后期以词为交际工具已成为一种词坛风气,这里只是想强调稼轩体更为突出,所产生的言志效应也更为明显,而且由此所体现出的词体观念也表明了它对吴蔡体的直接承继。
词体功能的转化使词人摆脱了由应歌带来的种种束缚,这不仅为自我主体精神的表现开辟了广阔的领域,也为体现着新的审美理想的豪放词风的确立及其相应的表现手法的创造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如果我们进一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吴蔡体之于稼轩体形成的词体革新意义。
吴蔡体与稼轩体虽各具面目,但对东坡豪放体所体现的阔大词境和刚劲之气的认同与追求,则是一致的。吴激词气格上略近婉约体,但就其词境而言,则又与那些剪红刻翠之作不可同日而语。如《木兰花慢·中秋》(敞千门万户)词中所写中秋月夜思乡之情虽为传统题材,但那种“瞰沧海”、“眺河汉”的广阔视野及去国离乡的悲壮情怀,则为传统词境所缺少。伯坚词追步眉山,其词境也多有“大江东去”之神韵。如《水调歌头》(星河淡城阙)、《念奴娇》(倦游老眼)等名篇莫不如是。吴蔡词中虽不乏一些造境“小而好”之作,但其词境的基本类型之于“宝帘闲挂小银钩”这样的传统词境已有了本质的不同。稼轩词对词境开拓的气魄与规模自胜于吴蔡,但吴蔡能于前代遗留下来的满目红翠之中,直寻东坡,标倡雄阔,并使之具有词体属性的意义,无疑有其开创之功,对于稼轩再造佳境,其导向与铺垫的作用也当不容忽视。
基于阔大之词境的清爽刚劲之气,构成了稼轩体与吴蔡体不可分割的又一内在联系。如《蕙风词话》所云“金源佳词近刚方”,承绪东坡风范的“刚方”之质可谓吴蔡与稼轩共同的风格特征。不过吴蔡更多地继承了东坡豪放体清爽旷逸的一面,而稼轩则主要发展了东坡词中未得以充分展现的豪雄精神。蕙风所谓“以冰雪为清”颇能说明吴蔡体,特别是伯坚词所体现的清刚之气。在传统的婉约体作品中,人们所熟视的是春风秋雨、疏柳落花这类香艳软媚的意象,而在《明秀集》中,我们则看到词人对于冰霜风雪这类冷峻清寒意象及其感受格外垂青。其例俯拾皆是,仅卷一开首8篇《水调歌头》即多达20余处,如“东垣步秋水,几曲冷玻璃”、“沙鸥一点晴雪,知我老无机”、“十年流落冰雪”、“空凉万家月”、“手捻冷香碎”、“晓猎冷貂裘”、“好在西山寒碧”、“忽有冷泉高竹”、“冰雪做生涯”、“醉玉嚼冰雪,樽酒玉浆寒”等等。冰雪之物、冷寒之感成为词中的审美意象固然与北国的自然环境有关,但它更是词人审美情趣的偏好所致。冰雪冷寒只是一种外在的自然现象,词人之所以反复歌咏之,是因其体现了他所追求的清爽之气和刚烈之风。这种清刚之质的确构成了吴蔡体最显著的艺术特色,即如那些传统题材的作品也与旧日风貌有别。如吴激《满庭芳》(柳引青烟)一词所写思乡之情与柳耆卿笔下的羁旅之思颇有相似处,但彦高生逢末世,国亡人留、有家难回的巨大悲慨,则是盛世不遇的柳永不可能体会到的。词人将此常情之外的强烈愁思压缩于细腻婉曲的词句之中,磨折为柳青花红间的春梦莺语,故艳辞丽句终难掩其悲壮刚大之气。实质上,这种风格已为稼轩体颇为人称赏的“摧刚为柔”之境导夫先路。
吴蔡体意境、意象上的这种清爽刚大之质并非其个人的偶然喜好,它实际上是一个时代审美观念嬗变的体现。吴蔡体所体现的审美理想可谓是对宋人“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张,喜深微而不喜广阔”(注:缪钺《宋诗鉴赏辞典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审美观的一种反拨,而稼轩体则又将此一理想引入南宋,开辟一片新天地,周济称“稼轩由北开南”,“是词家转境”(注:清周济《宋四家词选》。),即为此意。辛弃疾于南宋词坛开拓词境,转变词风,从根本上讲是“北宗”精神的南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