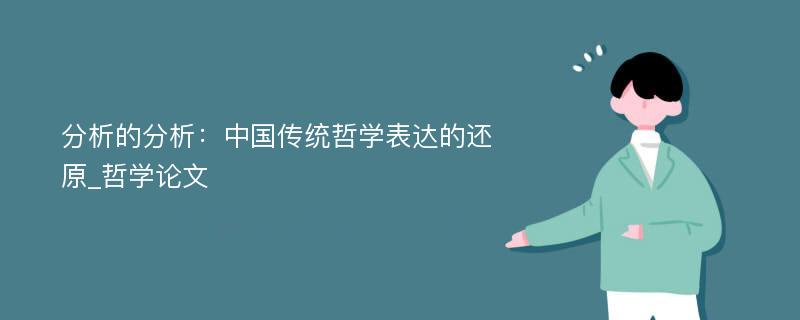
分析的分析:中国传统哲学表达方式的还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表达方式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传统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的分析是中国哲学走向现代的第一步。在30年代前后冯友兰等学者已走出了这一步,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下去。本文通过分析的分析,可望对中国哲学进行适当的还原。
对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的分析,无疑应当从传统哲学本身开始,但在本文中我的分析对象主要集中在冯友兰等老一辈学者对传统哲学表达方式的分析,所以我实际要作的乃是对传统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的分析的分析,评价的评价,但显然不完全是冯友兰“接着写”的接着写。
我们可否以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分析的分析工作呢?我认为即使作为中国哲学重建的一项基础性准备工作,哲学表达中国方式的分析也是必要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中国哲学的重新释义,也才谈得上用最民族也是最世界的语言(表达方式)来书写真正的中国哲学。我的基本思路是尽量避免零打碎敲式的分式,集中从符号学所谓语词的三维关系着眼,通过与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的比较,来对哲学表达的中国方式进行逻辑和语言分析,从而在世界哲学或文化发展大背景中为传统中国哲学定位。当然第一步只能从老一辈哲学家或学者的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从分析的分析开始。
从语法、语义、语用三维关系看,老一辈学者对哲学表达中国方式的分析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哲学表达的形式特点、哲学背景及中国哲学主要功用的分析三个方面。
关于中国哲学表达的形式特点,前辈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简短。无西方古典哲学鸿篇巨制的边想边写或边写边想的逻辑演绎而成的专门哲学著作,多是成熟的凝练的名言隽语。
前辈学人主要以先秦哲学为例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简短。但何以简短的解释却不相同,钱穆认为是因为深思熟虑;梁启超则认为简短是由于书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二百多年中这方面的条件变化并不大,何以会前后有较大的差别呢?何况古希腊也存在同样的“传写甚难”的问题,然而古希腊哲学却无此特征呢?与梁启超强调客观原因不同,冯友兰认为简短是刻意追求的结果,并可以解释以下几个特征。
无表面的系统性。虽然没有象西方古典哲学那样严密推演而成的公理化体系(如黑格尔哲学),但并非无思想的一以贯之的联系或连续性。
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1〕“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大都是简短的、论纲式的, 没有详尽的论证。然而言简意深,其中含有丰富的义蕴。”〔2〕冯友兰先生也有相同观点。
含蓄。所用譬喻例证往往不说尽不说白总是留有余地充满暗示,不似恩格斯曾讽刺的德国当时一个刚毕业的哲学系学生就想建立一个终极真理的完满的哲学体系。
冯友兰正是从含蓄充满暗示这一特征引伸他的形上学的负方法的,实际上这种方法更主要的还是一种形上学的表达方式,直到晚年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还说:“《新知言》说,有一种叫作负的方法,那就是,不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什么,而只说它不是什么。这就是佛学中所说的‘想入非非’。‘非非’,就是不是什么(非)而又不是不是什么(非非)。”并且再次以烘云托月为例。〔3〕可见超越前人的努力他始终没忘,不过正象胡伟希分析的那样,他确实是以神秘主义的方法来作这种尝试的。
主要从殊相到共相。中国哲学重直觉的了悟,总离不开具体殊相,用列宁的话讲也可说成经由感性具体——理性抽象而达到的某种理性具体(如寓言等),不一定非要假抽象思辨的曲径。
从上面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把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归结为一种什么样的表达式呢?或者什么样的表达式具有以上四种特征呢?冯友兰虽没有明说,但是认为正符合诗的表达特点,并且是刻意追求的结果:
“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4〕并认为中国哲学家也象诗人一样有刻意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暗示的倾向,发展到极端则是相见而不言,“目击而道存矣”,和禅家的拈花微笑似乎无异了。
此一段文字面向西方对中国文化完全陌生的初学者,确实说出了中国哲学表达形式上的特点,并且说得那么富有魅力,对弘扬中国文化和哲学,其功不可没,但他的分析主观色彩甚至神秘主义色彩未免强了些,也看不到象他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主要范畴的那种分析哲学的方法。所以这些表达的特征怎么形成的,还要看从语用关系及语义关系即他所谓中国表达方式的哲学背景方面他是怎么说的。
关于哲学表达中国方式的哲学背景,冯先生们的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是中国哲学的致思倾向或关注的对象及要达到的目标,二是对言——哲学表达式与意——哲学的内容及目标两者的关系所取的态度,亦可看作从语用和语义两个视角来分析其哲学背景的。
从语用视角看,这个时期的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更注意社会人生的反思。从梁漱溟的中西印文化三路向思考,到钱穆认为孔子以降皆循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传统,直到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对中国哲学的定义,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中国哲学的功用在人生的实践方面,在于教人成为圣人而不是某种具体技能的人,这与苏格拉底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的生活从而引出抽象的人生价值体系,从目标上看是一致的,但具体的途径则显然不同,一个是通过追问而引出普遍的道德价值,另一个则是直接给出一个道德的榜样。
从语义的视角看,冯友兰们的分析并不多,冯友兰认为主要表现在古代哲学的言意之辨上,认为庄子“得意忘言”不仅是哲学表达而且也是一切中国艺术表达所取的一种基本态度。这很容易联想到维特根施坦把哲学研究比作梯子,一旦我们爬上一定的高度就应把梯子踢开。
冯先生认为传统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方法,即负的方法,而“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5〕并认为正的方法用得极好的拍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里系统的顶点都有神秘性质。由此他认为“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6〕与维特根施坦的著名警句“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静默。”〔7〕两者联系是明显的,但区别也同样明显,冯先生就是要超越前者,甚至不忌讳用神秘主义作跳板:“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无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8〕冯先生确实超出了分析哲学澄清哲学的任务目标, 并试图重建中国的形上学,与维也纳学派否定形上学的初衷也异趣,是耶?非耶?也许有不同的回答。但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表达方式本质上是超越理性的,是神秘主义的,我们不敢苟同。
我们仍借三维关系作参照来进行我们的分析的分析。
从语言与其表达对象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哲学家与西方古典哲学家都感到了语言的无力,表达的不易。拍拉图曾说“如果真的有人以为重大的事情是可以被描述的,那他肯定是丧失了理智”,《老子》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即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据传孔子所作的《易·系辞》亦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一书中对语言表达真理的能力的质疑比比皆是,以致于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但并不完全象冯友兰所说主要是暗示的方法或负的方法。
中国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没有形成西方古典哲学那种以数学以逻辑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公理化哲学体系,但在语义关系上与西方一样,也存在语词本质认识上的自然派和约成派;也许我们可以说,在哲学表达上,中国传统哲学更倾向于自然派,即认为在每个词的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关系。许慎的观点继承了《易·系辞传》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有代表性的语言观,他就认为作为哲学表达的《易》与中国的语言文字都来自对所指世界的摹仿:
“古者庖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书写文字)”。〔9〕并归纳汉字的造字用字的原则“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中国哲学家象《易·系辞》所说,不仅“圣人象之”,“象其物宜”,也在不断地为“圣人象之”作着始终不懈的解释和阐发。虽然庄子之后又有王弼的“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但真正主张不立文字,言不言之言的似乎只有禅宗中个别时期的个别人。王弼倒提醒我们中国哲学的表达不止有象,而且有言。老子孔子庄子正是以他们的哲学表达(言)为人所知并影响中国及世界的文化的。所以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表达的主流是负的方法的观点与历史是不相符合的,首先不能解释文澜阁里一套四库全书经部、子部巨大的藏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冯友兰们只重“经”而轻“传”。这也影响了他们对哲学表达中国方式形式特点的归纳。
在语义方面对中国哲学表达方式值得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以“六书”为特征的中国文字对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究竟有哪些影响?基于这样的文字的汉语言是否真的由于先天不足而不能表达一种纯粹的哲学或者相反更适合于表达一种超越现有哲学的更高的哲学?但从易象与最早文字的同源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两者相互作用的研究线索。
从语用的视角,也许更能解释或说明哲学表达中国方式的特点。与西方古典哲学追问逻各斯(赫拉克利特:世界的普遍规律性)不同,中国哲学的目的在于求道。故为了把握逻各斯(斯多葛派:命运),西方古典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都有一个理想,即将哲学作为无所不包的对现实的系统描述和解释,“哲学被认为是一种更基本的、包罗更广泛的知识形式,这不仅是因为它企图把各门科学的结果结合在一起并将它们各种不同的方法相互比较,相互关联,同时也因为它企图根据科学所确定的事实和从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价值,来创造一种统一的世界观。”〔10〕这种为现实提供全景图式的理想源远流长,影响迤于当代各综合哲学之中,也曾是科学的一个梦。普里高津曾说:“牛顿科学的雄心是要提供一个自然图景,该图景将是普适的,决定论的,并且是客观的(因为它不涉及观察者),完备的(因为它达到摆脱了时间束缚的描术水平)。”〔11〕直到一九00年的国际数学会上,希尔伯特还在呼吁实现这个梦:“在致力研究一门科学的基础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公理系统,对该科学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作出精确而完全的描述。……在该科学领域内,要是不能靠有穷个合逻辑的步骤把一个陈述从那些公理推出来,就不能认为它是对的。”〔12〕这个共同理想恰是西方科学与哲学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中国的哲学和科学明显没有这样的野心和魄力。中国科学的发展以技术成果见长于世界,中国科学重技术因而重应用、重直接间接经验加之口耳相传的传播习惯,很可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带有极为明显的某种技术特征。从技术的观点看,中国哲学的求道,如从儒学出发,小学之道是礼、乐、射、御、书、数和洒扫应对进退这样的生存技能,大学之道乃内圣外王之道,是“提高心灵境界”的生存技术(用林语堂的话也许好听些:“生活的艺术”),道本身即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的意思。《说文》云:“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管子》也谓之“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岱年先生以为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轨道,或以为孔子之道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我以为极是,只是道有方向性或导向性,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必须遵循的轨道或原则,即所谓途径或门径。当然与工匠的方技强调制作的工艺程序细节不一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方技只能让人成为某一种人,而中国哲学教人成为成人或通人,或象冯友兰说教成内圣外王的素王。哲学就成了圣王之道,就成了生存技术臻于圣境或出神入化之境的要领(原则)。成为匠人是容易的,成为大师大家则极为困难。如何达到这一境界呢?钱穆以为最好是圣人日常相处以为教,这样可以学到圣人不仅为学而且为人之全。如果孔子是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集大成者的话,尽管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然而登堂入室者是极有限的,为了间接学习,这就有了记(《论语》《孟子》),就有了寓言,就有了所谓名言隽语比喻例证。道是达到某种目的途径也可以解释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如果是必然规律,又何必再法自然,又同谁来法呢?解释《易大传》形而上者之谓道,臻于至境的要领,又怎是有形的抟之可得的东西。也可以解释中国哲学执着的致用传统,当然也可以解释哲学表达中国方式的形式特点。
从语法的视角看,一种技术的表达,出于应用可操作性的需要,自然必须简明、扼要、具体,并由于传授的需要,亦必须易于理解、记忆和传诵。中国哲学不仅本身作为生存技术须满足上述要求,即使作为传道解惑文化传播的术业,也须满足上述要求。吕思勉说:“又古人之传一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兼传其词者,则其学本有口诀可诵,师以是传徒,徒又以是传之其徒,如今瞽人业算命者,以命理之书,口授其徒然。此等可传之千百年,词名仍无大变。但传其意者,则如今教师之讲授,听者但求明其意即止,迨其传之其徒,则出以自己之言。”〔13〕这种多由口耳相传的学术满足上述要求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又由于不是一般的技术而是一种“提高心灵境界”的途径和要领,所以不可能特别详细周密,难免有时含蓄,不过这并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暗示,象冯友兰的负的方法那种神秘法门,而是以代有人出的大量注释加以支撑和辅助的,含蓄不说尽不说白留有余地也可能是出于启发创造力的考虑,也可能出于类似当今技术保守的考虑。
这样来解释哲学表达中国方式的特点,似乎中国哲学就更不成其为哲学了,弄不好真有挨骂的可能,把冯友兰视为艺术甚至诗一样的表达方式(并且也广为国际上所接受),突然一下说成是不过象《朝阳沟》里“前脚弓,后脚松…”一样的技术要领的口诀,确实不易为人接受。但是所谓上智从事的哲学或道学与下愚从事的方技(科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绝不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相反如果我们重视两者俱荣俱损的相互缠绕,对于揭开中国哲学神秘的面纱,摆脱被视为屠龙之术的偏见,客观公正给予评价,倒可能是一条正道。下面我们将看到这样定位的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把哲学作为科学的基础及作为一切认识的依据恰恰是一致的。
我一直感到困感,为什么中国哲学在表达方式上与分析哲学一样拒斥形上学?看来两者对哲学的基本界定的相似,应该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因。不过,分析哲学明确意识到自己作为认识的依据从而作为谈论具体科学的谈论,思考具体科学的思考,只是开了一个头,而中国哲学与文史政经军事科技等等始终不分,其所积累的成果较之分析哲学真所谓汪洋之与坎井,虽滴水可以知大海,但中国哲学的丰富与深厚正是其至今仍能对现代物理学对现代思维颇多启发的原因之所在。
对于这种求道之学的表达方式,如果要归纳其特点是非常困难的,如上所述,可以是记(包括哲学家的传记和学说思想,所谓道德文章的统一),可以是寓言,可以是名言隽语比喻例证,也可以是逐字逐句的注疏阐释(既有我注六经,又有六经注我),往往这种注疏也并不缺乏名辨的详实,甚至也倡言“无征不信”(《中庸》),也可以篇佚浩繁;当然也可以是暗示,是机锋,是棒喝或其他形体语言,甚至我们也可以证明“史即六经”(不独“六经皆史”),诗言志文载道,文史哲不分,象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自序所讲老妈子黄妈,厨子的妻子,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的话语里皆可表达一种“道”。归纳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回答什么是哲学表达的中国方式,即没有专门的哲学表达方式。如果说这种表达方式有什么特点,那么就是以不全应不全。《西游记》99回写三藏师徒西天取经归来,不曾想那宝贝疙瘩在流沙河边被水淹石粘风卷,弄了个残缺不全了,正当三藏痛惜不已时,却听那猴子说道:“不在此,不在此,盖天地不全,这经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不是应不全之奥妙也。岂人力所能与耶?”与西方古典哲学相比,在形式上中国哲学确实是不完全,不完美的,但与分析哲学零打碎敲的支离琐屑比起来,中国哲学还不能算太残缺。关键在于中国哲学从人类生存着眼,更注重对纷繁复杂的、随机的、不可逆的对象世界作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毛泽东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恰恰道出了中国哲学的灵魂。正是这个灵魂所系,决定了中华学术包括中国哲学的博大宏厚的积淀,不是一句东方神秘主义或原始思维或思辨哲学一点也没有就可以否定得了的,也正由于此,在“自然用一千个声音讲话,而我们仅是刚开始去听”的全新认识论背景下,中国哲学有可能为人类重新认识和表达世界提供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经典科学的新思路和新的表达方式。
注释: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发微》第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72—273页,三联书店1989年。
〔4〕、〔5〕、〔6〕、〔7〕、〔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6—17页、394页、395页、395页、3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9〕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廿九第1—7页,上海书局。
〔10〕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第2页,商务印书馆1988 年。
〔11〕《从混沌到有序》,第26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12〕《可能世界的逻辑》第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13〕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