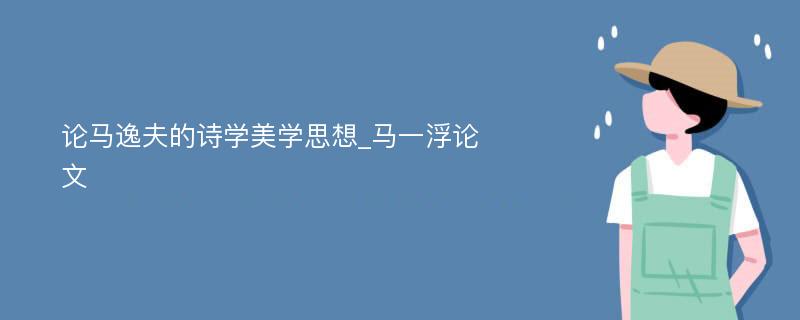
论马一浮的诗歌美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诗歌论文,思想论文,论马一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9)06-0034-05
马一浮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学者,于旧学有极其深厚的功底,因此,也公认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有精湛的西学功底,但治学主要是国学。在国学中,他于诗学研究最深,也最有创见。试粗略地清理他的诗歌美学思想。
一、“六艺之教,莫先于诗”
马一浮治国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六艺一体,他不仅认为“六艺统诸子”[1](P12),而且“六艺统四部”[1](P14),而六艺又“统摄于一心”。[1](P17)
《春秋繁露·玉杯》关于六艺有一个重要的说法,那就是:“《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马一浮根据这一观点,将今日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划入六艺:
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不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此最易知。宗教虽信仰不同,亦统于《礼》,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也。哲学思想派别虽殊,浅深小大亦皆各有所见。大抵,本体论近于《易》,认识论近于《乐》,经验论近于《礼》。唯心者,《乐》之遗。唯物者,《礼》之失。凡言《春秋》之意。……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外乎六艺也,故曰“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1](P21)
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很精辟的。中国古代学术分类意识不强烈,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法,是不科学的。马一浮先生根据今日科学分类法,将中国古代的学术分别派属于六艺,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里面,他强调六艺之教,不仅是中国至高的特殊的文化,而且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创见,可谓闻之未闻。在这个基础上,马一浮先生进一步指出:
西方哲人所说的真美善,皆包括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诗》教主仁,《书》教主智,合仁与智,岂不是至善么?《礼》是大序,《乐》是大和,合序与和,岂不是至美么?[1](P12)
真善美是西方文化提出的价值标准,马一浮将六艺如此套进去,是不乏创见的。这里,可以商榷的是:
第一,《诗》至善,诚然。按儒家的《诗》教说,《诗》是对全民进行教化的重要手段,《毛诗序》说诗有“风”的功能,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意思是,诗教像风一样感动全社会,影响全社会,这点没有疑义,有疑义的是,《诗》不只是至善,也至美。诗的美,一是在于它有形象,而且是一种审美的形象。诗用比兴的手法喻理,有鲜明的意象,有浓郁的情感。诗的意象是诗人从生活、自然中加以概括、提炼的形象,诗中的情感是诗人经过提炼、升华的情感,这象、情、理三者融为一体,因此,诗的意象不仅是美的,而且是至善的。
第二,《礼》,作为儒家的一套社会制度与行为规范,无疑是至善的,但是,儒家的礼,非常注重形式,而且形式与内容做到了高度的统一,因此,它不仅是至善的,而且是至美的。
第三,《春秋》是史书,固然是至真的,但是,春秋强调“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因而使乱臣贼子惧,可见,其实,它也是至善的。
按笔者的看法,六艺虽然有些重真,有些重善,有些重美,但是,总体来说,真善美都是看重的,似不宜太过细。值得注意的是,马一浮先生提出“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于此感发兴起,乃可识仁。故曰兴于诗。又曰诗可以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一切言教皆摄于诗。”[2](P239)这话包涵有两个重要的思想:
第一,中国古代的学术即六艺其源头是诗。言为心声,诗用美好的语言形式抒发人们的心声,它包括早期人类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社会的种种现象的记载,也包括早期人类最早的对形象的感受与把握,还有情感生活的自我回味与交流。后世所说的各种门类的学术均可以从《诗》中找到源头。
第二,中国人真善美的价值评价尺度也在《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另外,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马一浮非常重视乐,乐与诗在古代是一体的,乐即诗,诗即乐。马一浮说《乐》为至美,这美,又是与快乐联系在一起的。其实,主张快乐,不只是《乐》教的主旨,也是中国儒家一切经典的主旨。马一浮谈《论语》首章说:
首章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悦乐都是自心的受用,时习是功夫,朋来是效验。悦是自受用,乐是他受用。自他一体,善与人同,故悦意深微而乐意宽广,此即兼有《礼》、《乐》二教义也。[1](P26)
马一浮认为《论语》中的“悦乐”观兼有《礼》《乐》二教义,《礼》《乐》二教,马一浮认为是“至美”,那无异是说,《论语》品格也是兼有至美的。而《论语》众所周知,其主旨是谈仁,仁属于伦理学范畴,这也就是说,即使散文体的《论语》也具有《乐》和《诗》的品格。这又回到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于此感发兴起,乃可识仁。”马一浮的美学的基本思想是真善美相统一的,这在他的关于诗歌的理论中最为突出。
二、“心能描境,境不自生”
马一浮对诗的审美特征有足够的认识,这认识主要表现在他提出“诗以感为体”。他说:“诗以道志,志之所至者感也。自感为体,感人为用。故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言乎其感。”[3](P692)
这话非常深刻,虽然,在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中,对诗歌“感性”特征不是没有认识,但没有谁将“感”提到诗之“体”的高度。
“感”为诗之体包含了马一浮哪些重要的美学思想呢?
第一,诗的产生,是因事所感,这事可以是自然风物,也可以是社会人事,总之,是具体的实际的生活场景、自然场景触动了诗人的心弦,于是产生了兴,进而激发了情,于是发乎歌吟,成为诗。
第二,诗的本体,是感性的意象,它不是概念,不是教条。所谓感性的意象,包括两“感”:一是活生生的自然、人文景象,二是活泼泼的情感意蕴,这两种又是不可分割的,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两者妙合无垠,巧者情中景,景中情。中国古曲诗学谓之意象,兴象,我称之为情象。
诗之意象,虽然象是载体,却不是灵魂,灵魂是情感。马一浮重情,说“感愈深者言愈挚”[3](P694)。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诗人,不同的遭际,不同的境遇,自然会生出不同的情感。马一浮先生受儒家诗教的影响,因此,比较多地注重哀怨之情。他说:“中土自汉魏以来,德衰政失,郊庙而乐章不复可观。于是诗人多穷而在下,往往羁旅忧伤,行吟山泽,哀时念乱之音纷乎盈耳。或独谣孤叹,蝉蜕尘埃之外,自适其适。”[3](P693)而他自己,因为主要生活在旧社会,为社会的悲惨现实所感发,化为歌吟,自然也多伤痛之语了。他说:“余弱岁治经,获少窥六艺之指。壮更世变,颇涉玄言。其于篇什,未数数然也。老而播越,亲见乱离,无遗世之智,有同民之患。于是触缘遇境,稍稍有作。哀民之困以写我忧,匪欲喻诸行路。感之在己者犹虑其未至,焉能感人哉!”[3](P693)
第三,诗之审美效应,谓“感人”。所谓感人,就是以鲜明的形象作用于人的感官,同时,激动人的情感。这就是诗。在马一浮看来,就一般功能来说,诗与礼、乐、易、春秋等没有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这“感”。它将这称之为诗之体。从美学的观点来看,“感”是审美的本质。美学创始人,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鲍姆嘉通说: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马一浮说,诗以感为体,无异于是说,审美是诗的本质。
马一浮较之别的理学家,似更重视感性,他著文谈《论语》中的“视听言动”。他注意到,儒家很重视视听言动这些感性活动,领悟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他说:
学者当知,人与物接,皆由视听。见色闻声,有外境观。心能描境,境不自生。色尽声消,而见闻之理自在。常人只是逐色寻声,将谓为物,而不知离此见闻,物于何在?此见闻者从何而来,不见不闻不时,复是何物?当名何等?须知有不见之见,不闻之闻。声色乃是无常,而见闻则非断灭。此是何理?人心本寂而常照,照用之发乃有变化。云为形起名兴,随感斯应。故曰言行者,君子之枢机。虚而不穷,动而愈出,运之者谁邪?或默或语,或出或处,法本从缘,莫非道也。[4](P65)
视、听、言、动,属于人的感性生活方式。人的见闻,即认识,源于感性,但绝不止于感性,它要进一步抽象,化实为虚,从而进入“境”。境,接于外物,故有“外境观”,但境的本质乃是心,境为心生。一方面,“心能描境”,强调心的功能,另一方面,“境不自生”,强调物的功能。总起来,境乃心物相互作用的产物。“声色”这些感性之物变灭万千,为无常,而“境”作为感性之物的心理升华,它“常照”,为有恒。儒家一方面重视感性,主张以感性接物;另一方面重视理性,主张以心造境。所以,儒家的人生观,最高层次为境界,境界是生气勃勃的,充满着鸢飞鱼跃的生命乐趣,境界又是深邃浩冥的,充满着无穷无尽的难以把握的神秘。如果将老子的学说引进来,感性是实,是有,理性则是虚,是无。老子强调实与虚的统有,有与无的统一。这种观点也可以用到儒家的人生哲学上来。儒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实与虚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这种人生境界既是真的,又是善的,同时也是美的。
关于境界,马一浮强调构成境界的诸多因素的“化”。他是从孟子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谈起的。他认为,这个“化”很重要,标志着境界的最高层次,是谓“化境”。说到颜渊,他达到了“充实而有光辉”的层次,但是未达到“大而化之”的层次。
儒家这种人生境界观在诗歌中得到更为集中的体现。中国诗歌的审美本体就其最高层面言之为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境界是实与虚的统一,有与无的统一。较之意象,境界重虚,重无。马一浮论国学,重视“三无”:“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衰”。“三无”精神是重虚,重无限。境界也是这样的,它灵动,变化,难以把握。中国美学,其基本点,可以归结为美在境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儒家学说其实是富有美学色彩的,儒家的人生境界观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境界观虽然不能等同,却是相通的。
关于诗歌内在因素的构成,马一浮在强调诗以感为体之后,又说:“玄者诗之本,史者诗之迹”[3](P693)。玄具体指什么,马一浮没有说,联系到魏晋玄学的三玄《老子》《庄子》《易经》,我们可以说它指中国的古典哲学,但玄学整合名教与自然,应该说也涉及到伦理学,具体来说,涉及到儒家的经学。从价值论来说,它属于真,善。
中国古代诗学中有诗与理关系的讨论,唐诗尚情,宋诗尚理。关于唐诗、宋诗孰优劣,自明以来争论不休,主流的观点是肯定唐诗,批评宋诗,这种情况直到当代钱钟书都是如此。其实,宋诗也有宋诗的价值。诗未必不能言理,只是不能直说,如果寓理于象,如苏轼的《咏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也是好诗么?马一浮强调诗以玄为本,真实意图是强调诗要有兴寄,有内涵,这是正确的,也是深刻的。其实,这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只是没有像马先生说得如此明确。
至于“史者诗之迹”,这是说诗与史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重要问题。自杜甫在诗中寓史事后,“诗史”说甚为流行。明代的杨慎曾提出过异议,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更是提出批评,说诗与史各有其功能,以诗为史,则诗的特质可能会消泯。这个问题看来不能绝对。一方面,诗中未必不能记史,但另一方面,诗主要是表达时代精神,不一定记具体的史实。
如果不是史诗这种体裁,诗之记史就有限。马一浮重申中国古典诗学的“诗史”说,其真实含意可能还不是强调诗的记史功能,而是诗的讽谕功能,他说:“史以通讽谕,玄以极幽深。凡涉于境者,皆谓之史。”[3](P693)那么,这史重要的不是史实,而是史识了。而史识又联系到讽谕,则真与善相通了。另外,他讲的史迹,还不只是人文事迹,还有自然事物,他说:“山川、草木、风土、气候之应,皆达于政事而不滞于迹,斯谓能史矣。”而且,它还可能称之为玄,因为上句话后,他接着说:“造乎智者,皆谓之玄。”[3](P693)
马一浮先生论诗,其基本的观点与论六艺的看法一致,也是主真善美统一。
三、“《诗》教主仁”
中国儒家的诗歌传统是强调教化,从孔子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文学艺术都非常看重教化。
《毛诗序》,目前学界认为是儒家“诗教”说的渊薮,让人感到有些不解的是,《毛诗序》的教化说,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仁”这个概念。而马一浮的诗教说紧随孔子,明确地提出诗可以识仁,也就是说,《诗》教主于仁。马一浮说:
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于此感发兴起,乃可识仁。故曰兴于诗。又曰诗可以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一切言教皆摄于诗。苟志于仁无恶也,心之所之莫不仁,则其形于言者亦莫不仁。故曰不学诗无以言也。[2](P239)
这里,马一浮提出一系列与诗教相关的概念。主概念是“仁”。那么,首要的问题,何谓仁?马一浮说:“仁者,心之全德。人心须是无一毫私念时,斯能感而遂通,无不得其正。即此便是天理之发现流行,无乎不在全体是仁。若一有私系,则所感者狭而失其正,触处滞碍,与天地万物皆成睽隔,而流为不仁矣。故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2](PP.239-240)
这里,马一浮对“仁”做了一种新的解释。它的要点是:(一)仁是大公,无私念;(二)仁是天理,流行天下; (三)仁是天地万物无不得其正,即各自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四)仁是天地万物感而遂通,天人合一。显然,这种理解,已超出孔子了,它吸取了宋明理学家的观点,自成体系。马一浮对仁的理解特别强调天地万物感通,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于此会得,乃可以言诗教。”[2](P240)因此,这仁,不是伦理学的范畴,而是宇宙本体论的范畴。
作为宇宙本体的仁,既在天地万物之中,也在人的心中,是心之本体。诗歌的作用,就是通过特殊的手法,让宇宙本体转化成人心本体。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按马一浮的观点,主要通过“兴”、“志”、“言”等。马一浮没有解释“兴”,他采取的是通常义。“兴”,一般来说,它具有这样三个要素:象、情、理。朱熹说,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因而它具有比喻、引发的意味。诗的主要手法之一是兴,兴具有强烈的感发力,能逗发人们的审美情趣,但兴并不只是如此,兴的背后有理,有寄托,通常说的是“兴寄”。这“兴寄”寄的是什么呢?不是一己之悲欢,而是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感受与理解。这就是“志”了。儒家诗教强调“诗言志”,马一浮完全接受这个观点,他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兴”起,到“志”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它意味着“仁”已经进入诗人的心胸了。下一步,则是“言”,诗人需要将心胸中的“志”,用诗的言语表达出来。仁是可以言说的,不同的言说方式,它具有不同的效果。诗的言说,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言说,这是一种美学的言说,自然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当然不是说,不学诗不会说话,而是说,不学诗不会说仁话,而且是美好的仁话。
如我们在上面所言,马一浮是主张六艺一体化的,他谈《诗》教也同样将它与六艺中的其他五艺联系起来。在这方面,他也有许多深刻的观点。我们略作分析:
如,《诗》教与《易》教的关系,他说:“《易·乾·文言》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知仁包四德,即知诗统四教。”[2](PP.242-243)这方面的例子,马一浮举了不少,比如,《周易·系辞传》中说,“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他引孟子的话:“天子不仁,不保四海。”然后得出结论:“仁者,心无私系,以百姓为心。”[2](P243)
再,《诗》教与《礼》教、《乐》教、《书》教的关系,他引《礼记》中的话“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说“是以知诗书礼乐参互言之”[2](P243)。“诗乐必与书礼通。”[2](P243)马一浮同样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九》有吴国公子季札观乐一段记载,这是说诗最古者,马一浮说,这段记载充分说明,“闻其乐,而知其德也。”[2](P244)
《孔子闲居》有一段重要的话:“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马一浮对《诗》教的“五至”说十分重视。他详尽地做了分析,其实,这也是他的六艺一体论或者说真善美统一论的发挥。他将《诗》教的“五至”最后归结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内圣外王”。马一浮说:
总显一心之妙。约之则为礼乐之原。散之则为六艺之用。当以内圣外王合释,二者互为其根。前至为圣,后至为王。如志至即内圣,诗至则外王。诗至即内圣,礼至即外王。礼至即内圣,乐至即外王。乐至即内圣,哀至即外王。此以礼乐并摄于诗,则诗是内圣,礼乐是外王。[2](P247)
说得极为透辟!
内圣外王,内圣是人心的修炼,外王是事功的成就。二者相互联系,互为其根,总为一体。而《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均有内圣外王的功用,如要区分,只能看“前至”和“后至”了。如仅就《诗》教与《礼》教《乐》教的一般关系来说,诗是内圣,礼乐是外王。
马一浮是现代国学大师,他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理解达到了当代的最高峰。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马一浮先生本人是诗人,他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诗学的实践,而他的诗学,也是他自身的诗歌创作体会的提炼和升华。这说明,中国古典诗学在今天诗歌创作中仍然有生命力,马一浮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收稿日期]2009-04-27
标签:马一浮论文; 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文化论文; 论语论文; 春秋论文; 读书论文; 毛诗序论文; 六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