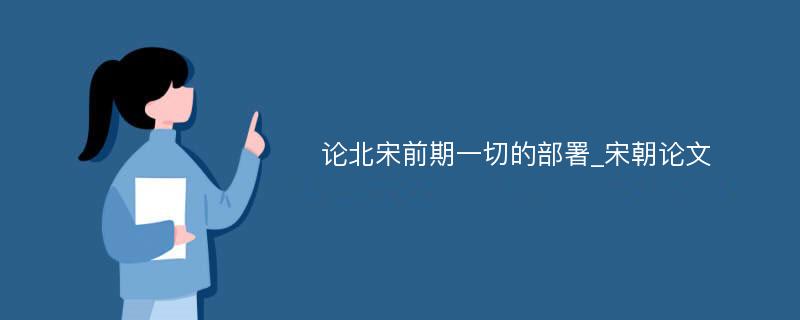
论北宋前期的都部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人孙何说:“今之都部署,昔之大总管。”“盖元戎之任,无不统摄也。”[1](卷64《上真宗乞参用儒将》)可见,都部署一职在北宋初期的地位何等重要。经查,都部署虽然仅存在于北宋前期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但在《宋史》中竟出现355次,且不包括其简称、别称。在《宋史》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本纪中,枢密使、都指挥使、都部署分别出现62、36、78次。都部署的出现频率高于研究者一向注重的枢密使、都指挥使,这一查询结果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所谓都部署,系马步军都部署的省称,其简称还有部署、兵马都部署、步军都部署等。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四月,宋英宗赵曙刚即位便下诏:“天下官名、地名、人姓名与御名同者改之。”[2](卷198,嘉祐八年四月乙亥)此后,部署更名总管。结合史料研习有关论著(注:参看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65页;李昌宪《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陈峰《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在深受教益的同时,不免产生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问。现陈述于下,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都部署之设始于何年
都部署是辽宋金时期特有的官职(注:都部署一词在《辽史》、《金史》中分别出现174次和5次。辽、金时期的都部署另当别论。)。此职始见于五代时期,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阅读有关史料,却遇到两个或许细微但又不得不略加辨析的问题。
其一,都部署之设究竟始于何年?北宋前期李上交将其绝对年代确定为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他认为:张景达这年“充西北番汉马步都部署”,都部署“始此也”[3](卷2《都部署》)。然而,查阅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即发现,都部署此前已有之。都部署首见于《资治通鉴》卷269,梁末帝贞明元年(公元915年)七月条:“晋王(即后来的唐庄宗李存勖)爱元行钦骁健,从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献之,以为散员都部署,赐姓名曰李绍荣。”此事,《旧五代史》卷70《元行钦传》、《新五代史》卷25《元行钦传》均有记载。此后至清泰三年以前,《资治通鉴》有关都部署的记载有四条:1.卷277,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九月癸亥,虽然尚未称帝、但已盘据四川的孟知祥,“以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副之”;2.同卷,长兴三年二月辛巳,“以(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3.卷279,清泰元年(公元934年)二月辛卯,唐闵帝李从厚“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副之”;4.同卷,五月庚戌,“初,(唐)明宗(即李嗣源)为北面招讨使,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副都部署”。有必要说明的是,最后一条系追述,在这四条记载中,年代应当最早。房知温任副都部署,至迟不会晚于唐庄宗同光年间(公元923—926年)。此外,李肃、石敬瑭在贞明元年至清泰三年之间,曾任都部署。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三月,唐闵帝李从厚“以前金吾大将军李肃为左卫上将军,充山陵修奉上下宫都部署”[4](卷45《唐闵帝纪》);同年五月,唐末帝李从珂“以成德军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都部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都部署如故”[4](卷46《唐末帝纪上》)。这两件事为《资治通鉴》所未载。可见,元行钦、房知温、李仁罕、赵廷隐、王思同、李肃、石敬瑭等人担任都部署均早于张敬达,李上交之说并不确当。
其二,总管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五代部分分别出现57、17、23次,都部署分别出现101、33、39次。前面已经讲到,在《资治通鉴》中,都部署首见于卷269梁末帝贞明元年(公元915年)七月,而总管则首见于卷267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十一月辛巳:“赵王(王)镕复告急于晋,晋王以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晋阳,自将兵自赞皇(今属河北)东下,王处直遣将将兵五千以从。”总管、都部署为什么在五代时期同时并存,原因何在?对此,只能作以下两种推测。一种可能是都部署系总管的更名,此后这两种官职名称又多次对换,只是更改官职名称的敕令,有关史籍全部失载。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因史籍成书于宋英宗以后,都部署已更名为总管,史籍中某些地方的都部署被编者按照当时的习惯改称为总管。对于《资治通鉴》来说,因其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十二月,这种可能确实存在,并有例证。如前引《旧五代史》载石敬瑭任都部署;而《资治通鉴》则载石敬瑭任总管:“以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但薛居正《旧五代史》成书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欧阳修《新五代史》基本完稿于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则无这种可能。如有问题,应出现在刊行、流传过程中。其实,史籍在记述北宋前期的史实时,这种情况同样时有发生。如《宋史·仁宗本纪》中,“都部署”一词仅出现3次,“总管”一词竟出现28次。对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可知,所有这些“总管”均应作“都部署”。应当指出,在《资治通鉴》中,总管之称最后一次出现于清泰二年七月,唐末帝李从珂“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权”[5](卷279,清泰二年七月乙巳)。《资治通鉴》从卷280开始,即清泰三年以后,不见总管职衔,只见都部署官称。李上交《近事会元》“成于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6](卷118《杂家类二》),早于《资治通鉴》。司马光或许是受李上交都部署之设始于清泰三年这一观点的影响,也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史籍中,后周时一概不见总管职衔,只见都部署官称。《旧五代史》卷123《高行周传》中虽有“总管”一词,但系追述后唐年间的事情。可见,后周时都部署已完全取代总管而成为定制,北宋初年所沿袭的正是后周之制。此外,五代时期无论都部署与总管是两种官职还是一种官职的两种称谓,两者的职责几乎完全相同,大致都是为执行某一特定重大军事任务而临时委派的。如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因“契丹、吐浑、突厥皆入寇”,唐明宗李嗣源任命石敬瑭为蕃汉马军总管,率军抵御。天福六年(公元942年)十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反”,晋高祖石敬瑭任命“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以讨之”[7](卷8《晋高祖本纪》)。仅此两例也可看出,都部署与总管官职虽异,职责大体相似。不仅五代,而且十国也设有都部署一职。如南唐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二月,南唐元宗李璟“以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帅师三万,赴寿州(治今安徽凤台)”[8](卷2《元宗本纪》),以抵御后周。从前面所引孟知祥以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可知,后蜀设有都部署一职。
二 都部署由谁担任
五代北宋前期,都部署一职经历了由武将担任到由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的前后变化,并生动地体现了朝廷国策从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前后演变。宋人孙逢吉《职官分纪》卷35《马步军总管副总管》称:“国朝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副总管以观察使充,有止一州者,有数州为一路者,有带两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则管勾军马,旧相重臣亦为都总管。有禁兵驻泊其地者,冠以驻泊之名。”这段简洁的概述又见于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47《都总管副总管》、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75《都总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9《都总管》,或许是由于过份简洁,不仅未能如实地反映这一变化过程,而且容易造成误解。王曾瑜先生指出:北宋初,都部署“专用武将。宋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9](63页)。陈峰先生《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一文说得对:“都部署的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北宋武将地位变迁的一个缩影。”下面以已有研究为基础,作些补充和讨论。
早在五代时期,都部署一职经历了主要由地方节度使到由中央禁军长官担任的变化。起初,几乎一概由地方节度使担任。《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本纪》载:“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己卯,陷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庚辰,归德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二年二月,“横海军节度使田武为东北面行营都部署,以备契丹”。三年六月,“丙寅,契丹寇边。己丑,(泰宁军节度使)李守贞为行营都部署,义成军节度使皇甫遇为副”。都部署一职虽然只具有临时性,特定战事一旦结束,节度使即返回原来镇守之地。但是,这一职务对于节度使来说,仍然很重要,否则他们则无权带兵出镇作战。后来,特别是后周时期,节度使担任都部署者减少。《新五代史》卷12《周世宗本纪》载: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十一月乙未,朔,李榖为淮南道行营都部署,以伐唐”。李榖系唐明宗长兴元年(公元930年)进士,后周开国,官拜平章事,有“周朝名相”之称,是一个读书人出身的标准文臣。应当指出,李榖任都部署,实属特例。当时的都部署多由两司即中央禁军长官担任。如《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四月乙未,周世宗北征契丹,“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太祖皇帝为水路都部署”。这时,韩通系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其副职石守信也是中央禁军将领。《宋史》卷484《周三臣传·韩通传》称:韩通“为陆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焉。”赵匡胤这时身为殿前都指挥使,其前线职务,据《宋史》卷1《太祖本纪一》记载:“(显德)六年,世宗北征,为水陆都部署。”“水陆”,《资治通鉴》卷294作“水路”。《资治通鉴》同卷又载:显德六年五月“辛亥,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治今河北霸县)都部署”。可见,朝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大多不再由节度使率领地方军出战,而由禁军将领率领禁军为主的中央军征伐。这表明与唐朝末年、五代前期不同,五代晚期中央禁军实力增强,节度使地位呈下降趋势。而中央禁军实力的增强与枢密院权力的加重、三司使的设立、学士地位的提高,都意味着中央集权开始强化。
宋太祖时,行营都部署一概由武将担任。如果说后周时期尚有文臣担任行营都部署之职,如宰相李榖出任淮南道行营都部署,那么宋太祖时绝无此例,行营都部署非由三衙长官即由节度使担任。宋太祖确实施行了一些削弱藩镇的措施,但对武将并非一概猜忌。《宋史》卷250《论曰》:“石守信而下,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特别是对御边将领,更是相当信任。如慕容延钊“握重兵,屯真定(即今河北正定),太祖谕旨,听以便宜从事”[10](卷20《慕容延钊传》)。宋太祖对通远军使董遵诲“委遇始终不替,许以便宜制军事”,他在“通远军(治今甘肃环县)凡十四年,安抚一方,夏人悦服”[11](卷273《董遵诲传》)。何谓“便宜从事”?宋人有解释:“主将之从权行事,谓之便宜黜陟。”[12](卷4《便宜》)对于宋太祖优待边将,《宋史》卷250《论曰》有较为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宋太祖给与边将当地财赋支配权、商业贸易权、免征商税权、不经请示自行处置权等多种特权。清人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序》称:“太祖一朝,制沿五代,方镇仍旧”,不无一定道理。宋太祖信任边将,的确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正如北宋后期人任伯雨所说:“本朝太祖、太宗时,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时势所系,不得不然。”[1](卷65《上徽宗论西北不可用武人》)人们多半认为,宋太祖重文轻武。其实,宋太祖时正值战争年代,很难重文轻武。他生长于五代,又是出身武将,但注重文治,并作出过“作相须用读书人”[2](卷7,乾德四年五月乙亥)一类的许诺,也属不易。然而,宋太祖难免对知识及读书人仍带有行业性偏见,发表过“之乎者也,助得甚事”[13](卷中)的言论。从上述史实看来,恐怕应当说宋太祖文武并重,一概任用武将出任“事权甚重”的都部署[14](甲集卷11《马步军都总管》),即是其虽然重文但并不轻武的例证。
与任伯雨的太祖、太宗“乃用武臣分主要地”之说不同,《太宗皇帝实录》称,“上欲兼用文士,渐复旧制”[15](卷41,雍熙四年五月甲子)。熙宁年间,范百禄甚至将“用文吏领兵,以辖边界”称为“至道故事”[11](卷337《范镇传附百禄传》)。至道是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于是,研究者们通常认为:“宋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其实,雍熙三年五月北伐失败以前,并无文臣出任都部署之例。即使在此后,例证也极少。人们经常引用的三个例证,均有可斟酌之处。
例一:张齐贤知代州。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七月,张齐贤“授给事中、知代州,与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16](下编卷2《张文定公齐贤传(太史)》)。但有两点应当指出:第一,张齐贤出任此职是触犯宋太宗的结果,甚至可以视为降职使用,并非受到宋太宗信用,用他以文制武。史称:“左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言事颇忤上意,于是上问近臣以御戎计策,齐贤请自出守边。”第二,张齐贤在代州虽非有职无权,但不仅对部署潘美,甚至对副部署卢汉赟,都不得不谦让三分。如当年冬季的代州城下之战,“卢汉赟畏懦,保壁自固”。张齐贤非但不予谴责,反而将自己的战绩“悉归功于汉赟”[2](卷27,雍熙三年七月壬午、十二月己未)。足见,他也未能做到以文制武。
例二:柴禹锡任部署。《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载:端拱二年正月(公元988年),“以涪州(治今重庆涪陵)观察使柴禹锡为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兵马部署”,此后又任镇州(治今河北正定)驻泊部署。然而,柴禹锡系宋太宗做晋王时的“藩府旧僚”,“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11](卷268《王显传·论曰》),历授翰林副使、如京使、观察使等武臣官阶,可见他并非文臣,当属近臣。后来曾任镇、定、高阳关(即关南)三路都部署、枢密使等要职的王显上奏宋真宗称:“祖、宗以来,多命近臣统领军旅。”[17](卷230《征伐》)他本人及柴禹锡便是近臣统兵之例。
例三:赵昌言任都部署。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赵昌言中进士,确实是个标准的文臣。史称: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八月,宋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自(王)继恩以下并受节度”。宋太宗“御札数幅,授以方略”[2](卷36,淳化五年八月癸卯)。值得注意的是,赵昌言并未入川赴任,而是留驻凤翔(今属陕西)或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关于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由于赵昌言“貌有反相”,宋太宗赓即反悔。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载:“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折额,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遂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诸将,留少兵,令昌言驻凤州为后援。”另一说为,宋太宗稍后即认为不必小题大做。太宗称:“贼,小寇。昌言,大臣,未易令前,且宜军于凤翔屯驻,止令卫绍钦赍朕手书指挥军事,亦可济矣。”[18](卷35《兵马总管副总管》)然而,赵昌言毕竟被任命为都部署,虽然仅此一例,也可证明与宋太祖时稍有不同,宋太宗时都部署并非一概由武将担任。
宋真宗即位后,右司谏孙何仍上疏“乞参用儒将”[1](卷64《上真宗乞参用儒将》)。这又是宋太宗时都部署通常由武将担任的佐证。或许由于这类呼声日渐高涨,宋真宗时文臣都部署逐渐增多,张齐贤、钱若水、王钦若、向敏中等宰执大臣相继出任都部署。《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编卷2《张文定公齐贤传》载: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闰十二月,张齐贤“拜右仆射、判邠州兼经略使”,其目的在于以文制武,“令环庆、泾原两路及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驻泊兵并受齐贤节度”[2](卷51,咸平五年正月甲辰),以制约西面行营都部署王超。可是,经略司判官曾致尧则认为,职权不明晰,目的难实现。他说:“兵数十万,王超既已部署矣,今丞相徒领一二朝士往临之,(王)超用吾进退乎?吾能以谋付与(王)超而有不能自将乎?不并将而西,无补也。”[19](卷87《曾公墓志铭》)咸平五年正月,张齐贤改判永兴军府兼马步军部署,其职权更加明确。同年四月,曾任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出任“知天雄军府(治今河北大名)兼兵马部署”[20](卷9《钱公墓志铭》)。他“分布军伍,咸有节制,深为戎将所伏”。宋真宗称赞:“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并派遣他“巡抚陕西沿边诸州,听便宜制置边事”[2](卷51,咸平五年四月辛未)。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七月,契丹入寇,宋真宗“欲择大臣,使镇大名(即天雄军)”[21](卷3,景德二年“王钦若罢参知政事”)。曾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愿意前往,宋真宗深感欣慰,“特加工部尚书,判天雄军,兼兵马都总管(应作都部署),并参豫如故”[22](卷28《王公行状》)。景德二年九月,咸平年间曾任宰相的向敏中出任延鄜路都部署兼知延州。上述文臣都部署,均兼知、判州郡,实为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统辖军队之始。他们就任前,张齐贤、向敏中曾拜相,钱若水、王钦若官至执政;卸任后,向敏中曾复相,王钦若则拜相。此时确如孙逢吉所说:“旧相重臣亦为都总管(应作都部署)。”宋徽宗时,任伯雨说:“及至太宗以后,迤逦悉用儒将。至于并边小郡,始用武人。”[1](卷65《上徽宗论西北不可用武人》)其实,宋太宗乃至宋真宗时都够不上一个“悉”字。
到宋仁宗时,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兼任都部署才逐渐成为制度。尤其是在仍处于战争状态的西北地区,曾“析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秦、渭、庆、延知州分领本路马步军”[11](卷196《兵志十·屯戍之制》)。如文臣夏竦知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范雍知延州、陈执中知永兴军、庞籍知延州、范仲淹知庆州、王沿知渭州(治今甘肃平凉)、韩琦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文彦博知秦州、滕宗谅知庆州,并一概兼任本路都部署。如果说宋真宗时某些武将都部署仍然权力不小,如咸平年间,“王超兼总北面三路兵,诸将皆受节度”[2](卷54,咸平六年五月辛卯),那么宋仁宗时这种权力一般属于兼任都部署的文臣知州。如《宋史》卷196《兵志十·屯戍之制》称:“赵元昊反,以夏竦、陈执中知永兴军,节度陕西诸军。”《宋史》卷283《夏竦传》云:“赵元昊反,(夏竦)拜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听便宜行事。”夏竦等文臣知州,此前已是朝廷要员,如夏竦曾任枢密副使。稍后,更是权位显赫,如陈执中、庞籍、韩琦、文彦博拜相,夏竦、范仲淹官至执政。定州(今属河北)“实天下要重之最”,韩琦在宋仁宗时曾知定州。如果说“自国初已来,专以武臣帅诸路”,那么时移世易,按照这时的制度,“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马都部署,居则治民,出则治兵”[23](卷7《韩琦》)。
而在宋仁宗时,武将通常仅任副都部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马步军都总管》称:“旧名都部署”,“以武臣为之副”。宋真宗以前不是这样,宋仁宗时期大体如此。如武将刘平任鄜延、环庆两路副都部署、石元孙任鄜延副都部署、任福任环庆路马步军副都部署、葛怀敏任泾原路副都部署等等,均是其例。名将狄青“有狄万人之称”,并被宋仁宗誉为“朕之关、张也”[18](卷35《兵马总管副总管》。但他仅任泾原路、真定路副都部署,并无任正都部署的经历。王铚《默记》卷上称:“韩魏公(琦)帅定,狄青为总管(应作都部署)。”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8之2《枢密使狄武襄公(青)》则云:“狄青作真定副帅。”两相对读可知,狄青仅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正都部署则由文臣知州韩琦兼任。宋真宗时,武将都部署尚可与文臣知州抗衡。如咸平年间,知环州张从古“领兵离州,袭杀蕃寇,官军有死伤者。”环庆路都部署张凝上报朝廷,宋真宗当即指责张从古“不曾谋于主帅(指张凝)”,“贪功失机,罪不宜赦”,并“遣使按问”[2](卷52,咸平五年八月丙寅),张从古被贬官。宋仁宗时,武将副都部署对文臣知州只能俯首贴耳,如知渭州兼泾原路都部署王素命原州都监蒋偕出战。狄青有异议:“(蒋)偕往益败,不可遣。”王素很不高兴地说:“(蒋)偕败则总管(指狄青)行,总管败,素即行矣。”狄青唯唯诺诺,“不敢复言”[11](卷320《王素传》)。对读《宋史·狄青传》便知,狄青这时的确职务不是总管,而是泾原路副都部署。狄青任真定路副都部署时,韩琦知定州兼真定府、定州、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狄青“每至韩忠献(即韩琦)家,必拜于庙廷之下”[24](卷8),每见韩琦,“甚战灼”。甚至妓女公然称狄青为“斑儿”,“讥其面有涅文也”[25](卷上);优人更称狄青为“黥卒”,“如此诟詈武襄(即狄青)不绝口”,狄青竟“笑语益温”[26](卷8之2《枢密使狄武襄公(青)》)。狄青身为一代名将,境遇尚且如此,足见当时武将都部署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以文制武的原则已成为固定制度,重文轻武的气氛已笼罩整个社会。这与时代的变迁有关。宋仁宗时虽然并非无战事,但就全国来说,宋人往往将它视为所谓“承平”时期,宋仁宗有“太平天子”[27](卷4《遵尧录四·仁宗》)之称。
起初,令人不解的是,武将夏守恩、夏守赟兄弟在宋仁宗时居然出任部署,乃兄历任并代路、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乃弟历任并、代二州、定州路、陕西、真定府、定州等路、高阳关都部署。稍加考察之后,即发现夏氏兄弟与宋真宗关系很特殊,并非普通武将。《宋史》卷290《夏守恩传》载:“父遇,为武骑军校,与契丹战,殁。时守恩纔六岁,补下班殿侍,给事襄王(即后来的宋真宗)宫,累迁西头供奉官。”《东都事略》卷62《夏守赟传》称:“父遇,以军校死王事,守赟幼孤,真宗在襄邸,怜之。及即位,授右侍禁,迁供奉官。”他们幼年入宫,被授予西头供奉官一类的内侍官阶。夏守赟曾任多半由宦官充当的走马承受公事,“帝甚亲信之”。夏守恩更是深受宋真宗刘皇后宠信:“帝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知谏院富弼甚至将夏守赟与宦官王守忠相提并论。其《神道碑》载: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公言:‘用守赟既为天下笑,而守忠钤辖,乃与唐中官监军无异,将吏必怨惧。’”[28](卷37《富郑公神道碑》)富弼还指责道:“夏守赟早事先朝,尝参储吏,既缘攀附,渐致显荣。惟事贵骄,罔思畏谨,每更剧任,颇乏清名,才术无闻,公忠弗有。”[1](卷131《上仁宗论西夏八事》)从种种迹象看,夏氏兄弟即令并非身体被阉割的宦者,也是精神被阉割的佞幸。一言以蔽之,他们当属特例。
三 驻泊都部署首见于何时
都部署不止一种,有大内都部署、山陵都部署、仪仗都部署等,从军事史的角度看,其中以行营与驻泊两种最重要。王曾瑜先生曾精当地指出:都部署“有‘行营’与‘驻泊’之别。‘行营’往往用于征讨,‘驻泊’往往用于防卫”[9](62页)。从五代到宋代,都部署经历了从以行营为主到取消行营、仅存驻泊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如实地反映了从战争年代到和平环境的时代变迁,也具体地体现了朝廷国策从积极进攻到消极防御的前后演变。
都部署原本是五代战争时期的产物,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都部署无疑是行营。在《旧五代史》中,“都部署”一词出现101次,其中“都部署”与“行营”两词在句内组合中出现达86次之多。五代时期的某些都部署虽无行营之称,而有行营之实。如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五月戊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唐末帝李从珂于当月“壬寅,削夺石敬瑭官爵,便令张敬达进军攻讨。乙卯,以晋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4](卷48《唐末帝纪下》)。张敬达所任之职,虽无行营一词,但其性质无疑属于行营都部署。其官称虽有太原二字,但他显然并非太原一地的地方统兵官,只不过是临时奉命在太原执行特殊军事任务而已。又如开运元年(公元944年)五月,平卢节度使杨光远联络契丹,起兵反晋。晋出帝石重贵令张从恩、李守贞率军进讨,其官职分别为“贝州行营都部署”、“青州行营都部署”[7](卷9《晋出帝本纪》)。张、李二人肯定不是贝州、青州(治今山东益都)的地方统兵官。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时期仅有行营都部署之称,而无驻泊都部署之名。在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中均未出现“驻泊都部署”或“驻泊部署”这一词汇。都部署在五代时期出现频率逐渐增高。特别是周世宗“锐于亲征”[4](卷114《周世宗纪》),立志统一全国,以率军攻战为主要特点的行营都部署在显德年间尤其活跃并屡立战功,预示着分裂割据即将告终,全国统一指日可待。
宋太祖时,都部署仍无驻泊之名。当时所谓都部署,其性质多属行营。诸如石守信曾任扬州行营都部署、慕容延钊曾任湖南道行营都部署、王全斌曾任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潘美所曾任贺州(治今广西贺县东南)行营兵马都部署、李继勋曾任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之类。其职务是某州、某道、某路都部署,但他们并非长期驻守某地的地方统兵官或地方军政长官,而是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这反映了宋太祖的战略总方针是以积极进攻、主动出击为主。经查,在《宋史·太祖本纪》中,“驻泊”一词仅出现一次: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十一月“癸亥,定州驻泊都监田钦祚败契丹于遂城(在今河北徐水西)”[11](卷2《太祖本纪二》)。且系“驻泊都监”,并设置于与契丹接壤地区。此外,如前面所说,韩仲赟为北面都部署,以防契丹;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三月,“以雄武节度使、守太保、兼中书令、太原郡王王景为凤翔节度使,充西面沿边都部署”[2](卷2,建隆二年三月辛亥),其任务是防御党项。韩仲赟所任北面都部署、王景所任西面沿边都部署均带有驻泊的意味,这反映了宋太祖对契丹、党项的方针与对十国有别,并非以积极进攻,而是以积极防御为主。
“驻泊部署”一词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首见于卷20,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上以郑州防御史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癸巳,命(杨)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此后在《宋史》中,雍熙北伐以前仅有1例,见卷260《米信传》,(太平兴国)“六年秋,(米信)迁定州驻泊部署”。雍熙北伐以后则有7例。卷260《田重进传》,雍熙年间,田重进“迁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卷268《柴禹锡传》:柴禹锡“改涪州(治今重庆涪陵)观察使,徙澶(治今河南濮阳南)、镇(治今河北正定)二州驻泊部署”;卷260《刘廷翰传》:端拱年间,郭守文、刘廷翰先后出任“镇州驻泊马步军都部署”;卷275《安守忠传》,安守忠“知沧州,改瀛州,兼高阳关驻泊部署”;卷275《尹继伦传》,淳化五年,尹继伦“以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团练使领本州驻泊兵马部署”;卷275《郭密传》,淳化年间,郭密“凡八迁,移贝州驻泊兵马部署”。此外,如《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载:雍熙四年六月,“以右骁卫大将军刘廷让为雄州都部署”,“以彰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王承衍为贝、冀(治今河北冀县)都部署”,“定国军节度使崔翰复为高阳关兵马都部署”;端拱二年三月,“命高琼为并(治今山西太原)、代都部署”;淳化元年四月,“以殿前副都指挥使戴兴为镇州都部署”;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三月,“田绍斌为灵州兵马都部署”。上述都部署虽无驻泊之名,均具有驻泊的性质。
驻泊都部署可视为战略方针转换的产物,其数量的逐渐增多反映了宋太宗的战略方针从以进攻为主逐渐转换为以防御为主。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宋太宗对待辽军的基本方针已是“来则御之,去则勿追”,“坚壁清野勿与战”[2](卷28,雍熙四年四月己亥;卷29,端拱元年十一月己丑)。如郭守文在出任镇州都部署时,宋太宗“面命之”,“朝廷以镇、定、高阳,控扼往来咽喉。敌若敢逾镇、定,汝但勿与战”[29](卷4,端拱元年四月)。
四 都部署是否一概属于地方统兵官
都部署往往被一概视为地方统兵官或地方军政长官。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将都部署定性为:“北宋前期临时委任的大军区统帅。”[30](2377页)这一定性不确切之处有二。一是“临时委任”四字仅适用于行营。龚延明先生的解释相当确切:“凡行营,事毕即罢,驻泊即常任。”[31](441页)二是“大军区统帅”一词又至多仅适用于驻泊。无可否认,都部署的确在澶渊之盟以后特别是宋仁宗时演变成为地方统兵官,下面两点即是其标志。
其一,取消所有行营都部署。宋真宗逐渐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行营逐渐失去意义,与驻泊混淆,于是在宋真宗前期出现了所谓“驻泊行营都部署”。如咸平五年六月,“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继忠副之”。其任务不是征讨,而是防御。宋真宗叮嘱王超:“不须力战,但控扼备御,不失机,便可也。”[2](卷52,咸平五年六月乙亥)宋真宗早有“厌兵之意”[11](卷8《真宗本纪·赞曰》),一再强调“以和戎为利”。澶渊之盟刚达成,他立即在景德二年正月,裁减河北地区的兵力,河北诸州强壮“并遣归农”,“以河北诸州禁军分隶镇、定、高阳关都部署,合镇、定两路为一。天雄军、沧、邢(治今河北邢台)、贝州留步卒六指挥,其余营在河阳(在今河南孟县南)及京城者并放还,行营之号悉罢”[2](卷58,景德二年正月癸丑)。对于“行营之号悉罢”措施,章如愚《群书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马端临《文献通考》均有记述。其中,谢维新如是说:“景德诏镇、定两路并为一路,诸路并去行营之名,止为驻泊总管(应作‘部署’)。”[32](后集卷75《都总管》)取消所有行营都部署,仅保留驻泊都部署,表明宋真宗在军事上已无攻取之心,只有防守之意。
其二,路分部署的出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诏近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总管、钤辖以上,许与都总管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总管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2](卷135,庆历二年正月庚戌)。所谓“路分总管”,这时应称“路分部署”。“路分部署”或“路分总管”一词为此前所无,此后则较多,既见于《宋史》卷169《职官志九·叙迁之制》,又见于《宋史》卷198《兵志十二·马政》。路分部署出现于宋仁宗时,表明都部署性质已演变为地方统兵官。这是宋朝国策由以进攻为主转化为以防御为主的必然结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五代到北宋初期乃至澶渊之盟以前,都部署的主要性质为中央统兵大员或前线总指挥,不可一概视为长期驻守一地的地方统兵官或“军区统帅”。通过前面所述即可看出,宋人对都部署的比喻又是其佐证。宋人往往将都部署的渊源追溯到魏晋两朝的都督、北周隋唐的总管。如梁颢说:“驻泊、行营都部管(‘管’字系‘署’字之误),古之将军、大总管之任也。”[17](卷322《御边》)高承称:“晋有都督诸军事,后周(指北周)改为总管。”“宋朝初有兵马都部署,治平初避英宗嫌名,改为总管,亦法古号也。”[34](卷6《总管》)这虽然只是一种比喻,但为我们判定都部署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曹真、司马懿、司马昭在曹魏时,杨坚在北周时,曾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或都督诸州军事,其职责是“总统内外诸军”[35](卷59《都督》),其性质显系中央统兵大员。西晋初年,晋武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羊)祜为都督荆州(治今湖北江陵)诸军事”[36](卷34《羊祜传》)。唐朝初年,唐高祖为平定盘据江陵的萧铣,将李孝恭任命为荆湘道行军总管。羊祜、李孝恭官衔虽有“荆州”、“荆湘道”字样,本人又身处江陵前线,但他们并非地方军政长官,而是统率中央大军攻打东吴、萧铣的前敌总指挥。唐代初期以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都督的性质逐渐变化。《新唐书·百官志四下·大都督府》称:“盖汉刺史之任。”然而,从曹魏到初唐的都督、总管并非均为所谓“汉刺史之任”。历史上的都督、总管,有的是地方军政长官或地方统兵官,有的则是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赵昌言一度被任命为川、峡两路都部署,司马光干脆称之为“元帅”,“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37](卷2)。这一比喻道破了北宋初期都部署的主要性质。赵昌言与晋初的羊祜、唐初的李孝恭相似,绝非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或军区统帅,而是出于征伐的需要,临时负责执行重大军事使命,担任前敌总指挥。
何以会将都部署笼统地误认为地方统兵官,或许与王曾瑜先生《宋朝兵制初探》一书在探讨地方统兵体制时论述都部署有关。然而,稍加留心,即可发现王先生并无此意。他有关行营与驻泊的区分及其论述,即是证明。问题还是出在前面所引宋人孙逢吉的那段概述:都部署“有止一州者,有数州为一路者,有带两路、三路者”。而《宋史》卷167《职官志七》又无都部署职责的记述,仅称:总管“掌总治军旅屯戍、营防守御之政令”。于是,平淮南李重进,石守信任扬州行营都部署;平南汉,潘美任贺州行营都部署;平南唐,曹彬任昇州(治今江苏南京)行营都部署,被作为“有止一州者”之例。伐后蜀,王全斌充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刘光义充归州(治今湖北秭归)路副都部署,被作为“为一路者”之例;讨李顺,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被作为“带两路者”之例。其实,石守信等人均非地方统兵官,而是中央特派的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北宋初期,即使是以防守为主的都部署,其性质也有别于后来的安抚使。前者仅设于缘边地区,后者遍及全国各地;前者有明确的作战任务,后者则不一定。岂止防守性都部署,即使是缘边巡检也如此。宋真宗时,钱若水说:太祖“止以郭进在邢州,李汉超在关南,何继筠在镇定(即今河北正定),贺惟忠在易州,李谦溥在隰州,姚内斌在庆州,董遵诲在通远军,王彦昇在原州,然但得沿边巡检之名,不授行营部署之号,皆十余年不易其任,立功者厚加赏赉,其位皆不至观察使。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1](卷130《上真宗答诏论边事》)。从“但得沿边巡检之名,不授行营部署之号”一语可以看出,钱若水认为,不仅缘边都署,而且缘边巡检,职责与性质均与行营部署无多大差别。
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陈峰先生《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一文并未将都部署的性质一概而论。他较准确地指出:五代宋初的都部署通常“为方面军统帅”,“为临时性军职”;“之后,这一职务逐渐固定,成为某一区域的军队统帅”。如雍熙北伐失败以后的驻泊部署,尤其是宋仁宗时出现的路分部署,其性质确属“某一区域的军队统帅”。另如宋太宗雍熙北伐,兵分三路,曹彬、田重进、潘美分别出任幽州道、定州路、云(治今山西大同)、应(治今山西应县)、朔(治今山西朔县)等州都部署,曹、田、潘三人则属“方面军统帅”。然而,前面讲到周世宗时征南唐的李榖、宋太祖时平淮南的石守信、伐南汉的潘美、攻南唐的曹彬,乃至宋太宗时一度被任命为川、峡两路都部署的赵昌言等等,则不是方面军统帅,而是前敌总指挥。
北宋初期的统兵体制通常被概括为“枢密院—三衙体制”,将都部署排除在外。这种兵权一分为二之说源于范祖禹,他在宋哲宗时指出:“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38](卷26《论曹诵札子》)此说的精辟之处在于点明了枢密与三帅既相互配合,更相互牵制的关系,但不免忽视了帅臣统兵的作用。另有兵权一分为三之说,则源于李纲。他在北宋末年指出:“在祖宗之时,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39](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据此,金毓黻先生认为:“宋分统兵之责为三,枢密司调遣,二司司训练,帅臣司统率,三者不相统属,此宋代立法之精义所在也。”[40](第1册16页)张其凡先生进一步论定:“握兵权、调兵权和统兵权三者分开,是宋代兵制的主要特点之一。”[41](110页)北宋初期的都部署作为帅臣的一种,非一般帅臣即后来的安抚使可比,与同样被称为大帅、大将的南宋初年的“武臣为宣抚”[42](卷132《庆历宣抚使》)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等相似,握有不可忽视的统兵权。在宋人看来,“中书、枢密院,朝廷政令所出,治乱根本,系之于兹”[27](卷2《太宗》)。都部署的权力固然难以同枢密使相比,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绝不在三衙长官之下。何况北宋初期的不少将领本身便是都部署与三衙长官一身而二任。我们认为,似可将北宋初期的统兵体制概括为“枢密院—三衙—都部署体制”。
注释:
③ 关南指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以南地区。
标签:宋朝论文; 宋真宗论文; 宋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旧五代史论文; 新五代史论文; 狄青论文; 宋太宗论文; 赵匡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