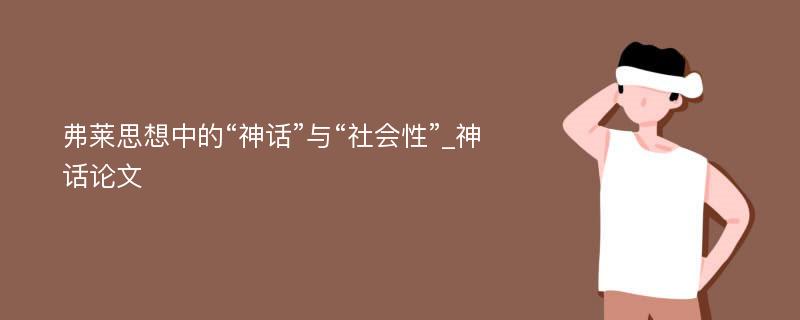
诺思洛普#183;弗莱思想中的“神话性”和“社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性论文,弗莱论文,神话论文,思想论文,诺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燕红译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析弗莱的代表性著作《批评的解剖》入手,指出弗莱思想中的二重性,也即“神话性”和“社会性”,并且集中探讨了三个方面:(1)弗莱思想中不断出现的“关怀的神话”;(2)弗莱的社会批评及社会责任感;(3)弗莱思想遗产中的积极方面。作者认为,弗莱的遗产不仅体现在他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而且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或思想家。
关键词 诺思洛普 弗莱 神话性 社会性 关怀的神话 社会责任感
《批评的解剖》一书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和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角度气势非凡地确立了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弗莱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其目的是将文学作品视为一自身内部有序的并最终构成一完整的文学体系的语言结构。这一观点,尽管在捷克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中已初见端倪,但对于加拿大读者来说仍不失其开拓性;弗莱谨慎地预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文学在人类活动中能否发挥社会功能——我们能否称之为自律性(autonomy)。通过仔细阅读“导论”我们发现,这不仅是关注社会倾向的读者提出的,更重要的是,也是弗莱自己的问题。的确,批评家囿于“他自己设制的概念世界里”①。弗莱的目的并不是将自己孤立于其余的人和人文主义事业之外:假如他的观点“文学是人文科学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学科,历史和哲学在其左右两侧”②是正确的话,那么他的目的仅仅是描述批评家所作所为的特殊性。而这一点主要体现于清除所有的把文学作品与社会因素的联系视为偶然的决定论因素。在全书的结尾,弗莱回归到文学作品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一话题,他指出,文学作品倾向于失去它本来在社会中具有的功能。他之所以这样讲,并非是否认文学与社会的固有联系,而是断言批评能够在新的语境下重建这一联系。换句话说,《批评的解剖》所强调的并不是创立一种文学/社会二分法,而是极大地扩大文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文学批评在人类生活进而在社会中的作用。
然而,文学与社会这一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含的;就其研究的本质来说,它只能是隐含的。《批评的解剖》结尾处明确指出,知识语言是多元的,众多的语言中无一能成为超语言(superlanguage)——有朝一日,我们或许能够同意弗莱对近几年来将符号学视作超语言的尝试的反拨——而且“我们同时拥有语言的多元性”③,这样“如果批评家继续他们自己的事业,那么这”——他这里指的是修复创作与知识,艺术与科学,神话与概念之间已经断裂的联系,即幻想与现实的联系——“将愈加明显地显示出他们的工作所具有的社会的实际的结果”④。笔者的目的旨在挖掘并简短地分析弗莱的文学和文化哲学中未能明确表达的那些方面,而这恰恰与其社会联系有关。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与其同时代的法国和瑞士新批评家一样,着重强调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特殊性,他甚至认为它们应当显示出自律性;尽管这里笔者不能确定弗莱本人是否经常使用“自律性”这一术语,因为在文化范畴中,也像在生活中一样,没有一项活动能被视为完全自律的。然而,弗莱为其论点的必要目的性所予以自律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说来,都外在于与批评家和理论家的社会责任感相关的任何思潮。笔者认为,通过探索想象世界,以及文化中想象的功能和产物,来揭示硬币那不发光的一面,也即批评家所行使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弗莱,同时也对于我们的学科,都是尤为重要的。假如这里允许发表个人意见的话,我可以说所有的文学和文化理论都是在人群中,并且为了人而发展的,无论这些人总体上被当作社会或被强调为个体。难道弗莱本人没有指出他的著述无不出自对社会的关怀吗?
理论是补充实践的理论思辨的一个阶段。这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惯于指责某些比较文学专业专注于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则未必清楚,好象理论化在某种程度上与研究文学文本截然对立似的。在纽约宾汉姆顿召开的一次文学理论会议上,笔者曾出于直觉地感受到周围气氛,为什么理论是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时我周围是一群年轻的美国理论家,他们正忙于破除等级制,变边缘为中心或变中心为边缘。这是他们激进的方式。当然这也应当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笔者却从未如此清楚地认识到理论是如何成为社会抗争的一种形式。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一点,即他们属于弗莱的后一代人,而且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主要反对的,即使不是弗莱的观点,至少也是他所提倡的这种整体性社会。然而,弗莱在50年代完全可能一直在全力支撑《批评的解剖》中的观点。我想论证的是,弗莱以坚定的信念确实是这样做的,尤其包括对社会决定论的破除,这具体体现在他担负社会责任的方式。让我们再次想起上文所引用到的《批评的解剖》的结束部分,这一视角一旦得到人们许可,弗莱的形象便在其复杂性中显得更为统一了。
人们时常耳闻弗莱曾是新民主党的党员,甚至对加拿大联合教派始终忠贞不渝,好象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与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哲学家的弗莱毫不相容。笔者认为,这些事实是一个连续体的一部分。在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已经接触和探讨了另一些悖论,诸如文化中主体的自我完善等等。对神话的关注始终贯穿弗莱的思想,作为他的文学神话的一个平行的层面。下面我们集中探讨三点:关怀的神话(the myth of concern)的不断出现;作为其观点的一部分而非偶然现象的弗莱的社会批评;弗莱思想遗产中的一些并不一定属说教性的积极方面。
在提出这些论点时,笔者留意到,与此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中的美学的令人困惑之处。这种令人困惑之处通常是由于无法将美学思辨与真正的美感在社会思想体系内相结合所致,这样做的同时又不能破坏美感。从美学意义上说,摩尔的《乌托邦》是一个丑陋的地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反映论”以及在各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继续,促使我们将20年代的苏联小说视为美学上的罪恶。相反地,弗莱却使得文艺以及对文艺的研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暂且不讨论它是不是高雅文化,先回过头来探讨审美体验的功能性,以及我们可称之为的文化反思。前者,按今日被人们广泛认可的巴赫金的观点,或许比后者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
在一篇题为《扩大的眼睛》(“Expanding eyes”)⑤的论文中,弗莱对人文学科的可能的社会影响作了一番思考:“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真正功能鲜为人知,即使那些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也难免认为,文学研究与批评是一项‘亚创造性’(subcreative)的活动,与诗歌和小说的‘创造性’写作相比,似乎创造性是属于文体而非使用这些文体的人的。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学术结构的狭隘性。不妨从哲学中取一类比:没有人怀疑有必要对以往的伟大哲学家的理论进行注释、阐述和再理解,也没有人怀疑有必要去研究哲学史,但是,假如在哲学学术部门除此以外其它任何东西也见不到,人们或许会问,真正的哲学研究在哪里?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同样的问题是:塞缪尔·约翰逊、柯勒律治和马修·阿诺德所关注的真正活动是什么?被问及我们时代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是哪些,文学批评家可能不仅难以提出一位他认为其影响超出了自身领域而能称为杰出思想家的文学研究者,而且很难想象任何一位文学批评家能在现代思想中占据如此中心的位置”。
这里我们至少有衡量批评的社会功能的两个不相上下的标准。第一个涉及创造性。“有创造性的”这一形容词加上引号是为了表明弗莱并不认为诗人比批评家或哲学家更具有创造性;这两种创造性只是不同而已。另一个准则则并非直接的——至少我认为是一哲学意义上的迂迥,但是在弗莱看来,都有理由认为它是至关重要的。这里弗莱以流行来看待杰出,实际上考虑到了这一点,即任何一位文学批评家,也许包括他自己,要在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留下印迹进而产生社会影响是多么地难啊。渐渐地,弗莱摆脱了将自己视作主要批评家的羞怯。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本笔记里,也即在1988年8月30日,他记下了一段话:“我被其他批评家引用多少次数倒无关紧要:我倒是成了值得每位批评家去阅读的亚文本。”⑥同样地,另外两篇在他逝世后发现的文章也不仅表明了他本人在批评家中的首要地位,而且也表明了他作为一位天才的与众不同的地位。
至少可以认为弗莱关于社会责任的观点与社会影响有关;而且,一位批评家或思想家越伟大,他或她的社会影响就越深远。有一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即这种社会影响究竟会导向何处。笔者觉得,伟大的思想家,正如伟大的作家一样,是存在的,无论对他们有何种道德上的评判。弗莱并非不关心道德准则;对于他而言,思想体系,诚如科学体系一样,主要是服务于综合知识和阐释;使用它们的人可以依据具体情况对之进行合乎道德的或不合乎道德的处理。
艺术本身,由于其在读者或观众身上产生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一首诗,我们说,是“由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材料构成的:无意识部分指的是任何缺少大彻大悟的人都无法控制的东西,但在某些精神部位它却能找到其表达方式。当它表达出来时,便构成一种心智力量的传导器,不时地给读者充电,直到,正如布莱克所言,“人们睁大的双眼明察奇异世界的深邃”⑦。这也许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也即从蒙昧中豁然开朗的一个阶段;而且它就存在于布莱克与弗莱之间。然而,从总体上讲,它在人类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位置(同样的证据几乎自动说明艺术教师和阐释者也占有一个位置)。弗莱继续指出:“将艺术视作像锻炼身体一样的一种人类基本必需品,而这一必需品都一直被压抑在一些虚假的东西之下。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任何将生活水准降低到维持生存的基本的需求程度的文化,比如爱斯基摩人的文化⑧,我们便发现诗歌是如何跃入那些生存的最基本必需品的行列的[…]。这里人们可能开始汲取教训,探讨我们应该重建的或回归的是何种社会,以达到上述的质朴纯真,但是这些教训中许多是相当幼稚的。我只想强调对艺术的反应的可能性、重要性和真实性,而我们却不再能够将这种对艺术的反应孤立于社会背景和个人专致之外。”⑨如此说来,诗歌,作为艺术形式的一种,特别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在人类生活中占有即使对非文学读者来说也值得恢复的一个位置(然后又回过头来含有一方面教育大众,另一方面扩大诗歌领域的作用)。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即弗莱提到了对重建和转变社会进行思考的可能性,但却止步于真正地设计那个社会。这是他的社会关怀的独特表达方式:描述以往的文明和文化,对现存的文化进行广泛的批判分析,而很少涉及为未来描绘蓝图。在此意义上,弗莱知道他为何人,我们也知道:一位分析家,综合家,文化变革的哲学家,而远非社会改革家。尽管如此,考虑到弗莱对于在一个动荡的世界进行社会变革的潜在贡献,比如现在在中国,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分析的有益价值,因为它们常常指明了未来的可能方向同时也指明了需要回避的方向。例如上文所述,诗歌和生活中的质朴本质可能一方面是一个被代替了的田园梦想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与关于人类生活更好地与自然环境协调一致的新思潮相一致。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有助于理解支撑弗莱思想中文化主导性的社会哲学的三个方面。首先,关怀的神话(the myth of concern)。笔者相信,《批评的道路》一书描绘的关怀的神话是弗莱关注神话的正面。这是一个意识形态怪物,占据了一个特定社会里它的进程中的每样东西,包括文化中渴求自由和公正的那些东西,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文学主题。“关怀的神话之存在是要社会保持为一个整体,因为语言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了它,真理与现实并不直接地与推理或证据相关联,而是在社会上确立的。所谓关怀,是社会所相信的并且对权威的一种回应;信念,在其可被语言描述的范围内,实际上表达了是否愿意参与一种关怀的神话。”⑩关怀的神话尤为典型地说出了信念的语言,因而逐渐地发展了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学的积淀,并且趋向于生成一种对于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学来说尤为重要的完满的宗教,这种宗教对其信仰者获取最终的安全感是大有裨益的。同样,关怀的神话是焦虑的、防卫性的和保守的。一种托胎于关怀的神话的文学充满了保守气息并以重复为特征。从这一点来看,人们可能会把弗莱理解成把关怀的神话彻底魔鬼化的人物。但是,请记住,他并不赞成价值判断,至少不赞成一种先验的价值判断。他往往描述功能,以及关怀的神话的内在的危险。在与口头文化相反的写作中,个体往往表明他/她对于信仰的坚持,但是也可以反对流行的信念并且最终反对社会,退避一旁,傲然于世;这样,文化圈中便存在一些远离文化主流的小岛,也存在着被解放了的判断以及被弗莱称之为自由神话(the myth of freedom)的东西,但这种神话只能在与关怀的神话之中相对立而产生,而且只能在个体的社会良知中产生,因为个体的真理观和真实观与关怀的神话是背道而驰的。
以下这段引文不仅应该被认为是有系统的重复陈述,或甚至是弗莱清楚表明的一个法则,它可以很好地适用于加拿大和中国的情况,而且也是个人爱好的回音:“社会批评态度,可以洞察虚伪、腐败、无法达到标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等等。这是反仪式的态度,如没有理性与实证中所揭示的真理的一致性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盟友的支持,是无法引起社会关注的。因为自由神话构成社会的‘自由’因素,恰如同关怀的神话构成社会的保守因素那样。那些拥有它的人不可能组成一个比持批评态度的,通常是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更大的群体。组成这样一个完整社群并非自由神话的功能:它必须在自身存在于其中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与之和睦相处。”(12)下面这一点是最根本的:尽管自由神话与关怀的神话同样具有功能,但它的功能只存在于昙花一现的、脆弱的、甚至有点杂乱无章的、通常是寄生的处所。人们或许在此可以发现弗莱对于自由运动的同情心,因为这种运动的特点与通常受到鼓励的个人思想及其构成因素的独立相符合。最后,拥有抗议自由的愿望实际上是无数的可能性之一,假如它不是对弗莱至关重要的话语的真正暗示的话:“真理使人自由”。然而,关怀的神话却与社会秩序密不可分;如果笔者对弗莱的学说诠释得对的话,那么自由神话也能够改变人性,却不能根除它。至于将关怀的神话的社会需求与自由神话的社会美德重新调和起来的社会群体,这只是一种实质。弗莱并没有给它下一个正面的定义,免得它会复制关怀的神话。
弗莱社会哲学的第二个方面可能要从他作为社会批评家的观点中去寻觅。他的任何一篇论文都未罗列出这些观点或者综合了这些观点的共同点,因为弗莱的社会和政治评论常常与他的文化见解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带有指示性的例子,比如《现代世纪》(The Modern Century)第一章“事物的终极之城市”(“city of the end of things”),写于加拿大联邦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在这样一个恰当的机会,弗莱思考了国家的涵意,断言:“[…]我们正走向一个后国家的世界,而加拿大则比大多数较小的民族向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些”。(12)他赞扬加拿大避开了两种紧张感:一种是那些新兴的国家过于急遽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分裂主义,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排外并与外国世界协调;另一种是“诸如美国苏联这样庞大的帝国在发展中伴随着的某种混乱和暴力。”(13)我们不要忘记这段话写于1967年,迄今为止,加拿大已经能够避免这两种极端,保持适合于即将来临的后国家世界的“均衡感”。弗莱从未停止过相信加联邦将以某种方式存在而且继续挫败其内部的过时的民族主义。加拿大人(与其它西方国家一起)享有的另一个机会是文化的自我意识:他们能够“为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与他们时代的联系而奋斗”(14),并且相应地建设自己的生活;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沦为媒介的被动消费者。这两种态度的区别奠定了该文中弗莱关于文化发展的见解之基础。他对人积极地和有意识地参与自身的文化的赞赏不容赘言。我们的目的是研究作为社会批评家的弗莱,有必要集中探讨他不同意的广泛流行的消极态度的本质、原因和结果。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注意文化中使个人反应钝化的部分和被影响的个人这两方面;但尤其最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两者的联系。因为,尽管文化——或人类学家——独立于任何主体之外生活着,而且在许多方面组成了这一主体,但以同样的特征它需要主体去体验它并使它成为现实。在现代世纪,心理隔阂介入人的生活,为被动的反应扫清了道路,因而不再阻碍个体抵抗强加于他们的广告、宣传或大批量生产的文学等带来的现成的说法。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不落伍于时代,将自己视为世界发展进程的批判性参与者;然而,根据弗莱的分析,这仅仅是蒙蔽他们的另外一例幻象。
谈到这点,弗莱在此文中使用的中心意象是反典型,按照他自己的术语,与柏拉图的洞穴之比喻颇为相似:“借用加拿大人都熟悉的无终止的火车旅程,我来描述一下一个人最终将发生的事。当一个人的双眼被动地划过飞逝的景物时,天色渐渐变暗,那人开始意识到那些看起来在外部的诸多景物实际上是车厢内景物的反映。当天整个黑下来后,他便进入一个自恋的世界,除了这里那里的一两盏灯火外,我们仅能看见我们自身所在地的反射。”(15)这表明弗莱认为没有人能逃脱幻象的力量,人所能做的只是意识到这种力量。在极限上,或许很难将上述两种态度截然孤立起来,因为即使有自我意识的个人也必须为远离幻象而永远抗争。
已成为只是行进的进步,即进程的加速,其实是一种幻象;持有此观点的远非弗莱一人。至于城市的堕落,最终媒介的非个人性,这些观点亦非弗莱独有。弗莱与多数流行的文化人类学观点的区别在于,他所持有的关于社会动因的观点是批判的和解放的。例如,他赞同伊尼斯(Innis)的见解,认为人最终能够并且的确能左右传媒的导向;并且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人类境遇的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类想要进步的愿望而独立发生”,以及“相信自动的或与人无关的进步是错误的。”(16)文化的自我意识清除了幻象,但是非神秘化并非它唯一的目的。更确切地说,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然而在一个如此趋向于同一性的社会,自由又有何用处?对问题的回答提供了关于弗莱坚信文化无处不在的部分解释,即自由只能来自主体对文化中倾向于强加同一性和窒息想象力的部分进行创造性抵抗。这样一来,想象远远不止是文化批评家的保留领地,它已成为每个人通向有价值的人生的必经之路。
在这一点上,我们正在跨越一条不明确的分界线——把我们讨论的第二点,即弗莱的一些社会批评要素,和第三点相分开的界限,即弗莱是否阐释了他自己的社会哲学这样一个问题。在笔者看来,他没有阐释他的社会哲学,假如社会哲学指的是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明确建构的、标准的学说的话。在他一方,积极地见解少于批判性的见解:而且前者紧随后者。此结论恰适用于弗莱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也即题为《加拿大文化发展》的讲座。(17)他迅速地审视了加拿大的历史情境,坚持认为,1867年危害联邦的也正是毁灭蜜切湖的东西:缺乏文化交流,缺乏理解和考虑相互的期望。愈来愈多的各种加拿大团体,不仅讲法语和英语的加拿大人,还有最早进入的民族和移民种族团体,都更加清楚而非更加模糊地意识到他们自身及其身份。“再建联邦”仅仅是一个政治行为;仅仅只有文化能作为分享生活方式、历史、遗产和创造性艺术的处所。如果教育使人开放思想,多元文化能作为补充被经历被尝试的话,那么重建联邦也能够实现。弗莱从批判分析到提出正面概念的思想轨迹将伴随我们进入一个没有幻象的现实世界。
(作者附志:本文的写作以及作者能够出席北京会议,完全得助于加拿大外交部和商务部的资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②③④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第12、354页,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⑤⑦⑨弗莱:《世俗精神:论文学、神话和社会》(Spiritus Mundis:Essays on Literatare.Myth.and Society)第105、121、122、121页,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⑥弗莱的笔记,1993年版。
⑧显然,这写于“Inuit”这一词语取代“Eskitno”一词之前。
⑩(11)弗莱:《批评的道路》(The Critical Path),第36、45页,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12)(13)(14)(15)(16)弗莱:《现代世纪》(The Modern Century),第17、18、27-28、41页,多伦多: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17)这是一篇发表于1990年10月17日的演讲,地点是多伦多大学哈特会议厅,对象是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会会员其及相关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