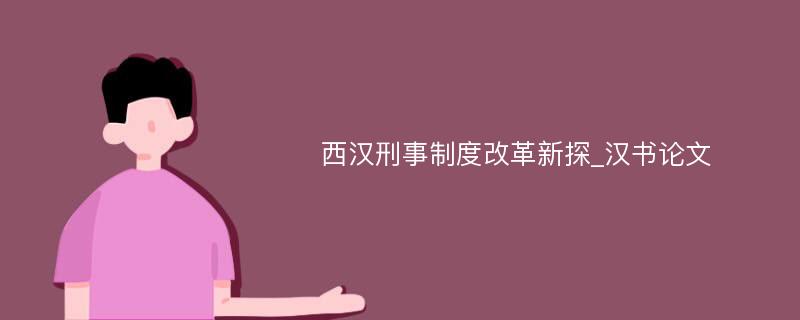
西汉刑制改革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刑制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日本滋贺秀三先生曾论及汉文帝改革刑制以后的劳役刑的刑期问题[①a],作为问题的背景,谈到了秦及汉文帝改革以前的刑制,将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来有关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的研究做了一个高度的概括。滋贺先生认为,高恒首先论述的秦的刑徒没有刑期的论文具有重要意义[②a];富谷至对秦刑徒无期说的补充说法“不定期说”更贴近实际情况[③a]。我赞同滋贺先生的看法。当滋贺先生把分散的各家无期说的精粹总合在一起加以评析和新的阐发之后,似乎使无期说主张的说服力陡然大增,以致于使人觉得有一锤定音之感。
种种迹象表明,文帝在废除肉刑的同时也废止了终身劳役刑,即规定了劳役刑的刑期。如高恒先生和滋贺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从《汉书·刑法志》所载文帝诏令下述文字中已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1.“其除肉刑,有以易之。”2.“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这里包含两大内容,一件事是废除肉刑,以其他刑罚代替;另一件事是设定刑期。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按照文帝的诏令拟定的改革方案对应地也分为两部分:1.“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2.“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
接着滋贺先生就上述方案的第二部分论述了有关新法规定的刑期问题。他指出《汉旧仪》中的刑罚制度与《汉书·刑法志》的记载有不合之处。的确像滋贺先生所说,这是问题的关键。在此也将卫宏《汉旧仪》的有关部分抄录如下:秦制,“有罪各尽其刑。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岁。完四岁。鬼薪三岁,鬼薪者男当为祠祀鬼神伐山之薪蒸也;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米也;皆作三岁。罪为司寇,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到三月。”日本学术界已经指出卫宏所说的刑制并非秦制,这些实际是卫宏所生活的时期即前汉末后汉初的汉制。我想,如果从刑期上看,以及从卫宏没有提到秦和西汉前期存在的隶臣妾的刑名这一点来看,这一见解颇有道理。因此,《汉旧仪》所说刑期与《刑法志》文帝时所定刑期应同为汉代的刑制。但经过仔细比较,滋贺先生指出,《汉旧仪》所说的髡钳五岁、完四岁、鬼薪三岁、司寇二岁等刑期,与《刑法志》所说有诸多不合。具体来讲包括以下一些难解之处:1.完为城旦舂的刑期,《汉旧仪》说是四岁;《刑法志》说是五岁(完为城旦舂,服本刑三年,加服鬼薪白粲一年,再加服隶臣妾一年后才可获释)。滋贺先生据此认为:“文帝以后直到西汉末,除了减轻笞刑以外,没有再度刑制改革的记录,所以,以上情况很难解释。”2.接着滋贺先生指出,更难以解释的是:“《刑法志》中,男子的司寇服刑一年即可获释,而女子的作如司寇却要两年。所以,有人认为:‘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之‘二’,实为‘一’之误。”3.滋贺先生最后提出:“在《刑法志》文字中没有出现鬼薪白粲的刑期。虽然知道在完城旦舂三年以后转为鬼薪白粲,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在最初的判决中即被判处鬼薪白粲的,他们的刑期却完全无从知晓。”
与过去我们或根据《汉旧仪》,或根据《刑法志》,或二者杂糅,或仅凭猜测而提出的有关汉代劳役刑的刑期的各种说法相比,滋贺先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并提出以上问题,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问题使我们必须对此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不去正视《汉旧仪》和《刑法志》的矛盾,仅是单纯地引用资料而各执己见。因为今本《刑法志》肯定存在我们过去忽略了的文字记载上有错误的问题,而且不解决班固《刑法志》和卫宏《汉旧仪》的矛盾,不论提出多少种有关汉代劳役徒刑的刑期的说法,从总体来说必然不够准确或全面。
比如,现有的论著、教材关于汉代劳役刑的刑期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完全采用《汉旧仪》的说法,即由秦到汉都是同样的刑期。2.有条件地采用《汉旧仪》的说法,与《汉旧仪》不同之点,是认为秦基本是无期刑,从汉文帝改革以后刑徒才有刑期。3.沈家本的说法。此说除了采用《汉旧仪》的说法,还对《汉旧仪》中没提到的“隶臣妾”,根据《汉书·刑法志》的内容推定为是三岁刑。4.程树德的说法。亦基本采用《汉旧仪》的说法,但对“隶臣妾”则认为是一岁刑,同时认为带有“耐”字的“耐为隶臣妾”是两岁刑。5.钱大群的说法。提出两种“城旦”都有五岁刑期,“鬼薪白粲”是四岁刑期。6.范明辛的说法。此说并列了两说。其中对髡钳城旦舂似乎没有加以说明。
各说有关汉代的刑名和刑期关系请看下表[①b]:
《汉旧仪》 沈说程说
钱说 范说一范说二
髡钳城旦舂五岁 五岁五岁
五岁
完城旦舂 四岁 四岁四岁
五岁 五岁 四岁
鬼薪白粲 三岁 三岁三岁
四岁 四岁 三岁
隶臣妾 三岁一岁(耐二岁) 三岁 三岁 二岁
司寇 二岁 二岁二岁
二岁 二岁
至于滋贺先生的新说,在指出《汉书·刑法志》文字有错误的同时,提出了《刑法志》有脱文的假说,而假说的核心部分,是在《刑法志》中的两处补进推定的脱文总计13个字。但最后得出的各种刑罚的刑期,和沈家本说仍是相同,而且基本是以《汉旧仪》作为参照系来寻找和修正《汉书·刑法志》的错误。那么,《汉书·刑法志》的错误之处是脱漏文字吗?大约东汉初才写成的《汉旧仪》中所述的刑制,是否就是西汉文帝改革中所确立的刑制?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查阅和研究了相关文献资料,希望能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案。我研究的结果,是找出了与滋贺先生所说完全不同的《汉书·刑法志》的错误之处并提出处理方案,同时对《汉旧仪》中的刑期规定从何时开始的问题,作出新解释,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心得。现在一并发表出来,供同仁参考。
二、有关《汉书·刑法志》正文和诸家注释之抉隐
今本《汉书·刑法志》除了本文外,还有一些后人的注文,在分析正文的时候,同时分析一下部分注文也是有益的。
我们先分析张苍等所拟的改法方案的第一段,根据张苍等人上奏有“臣谨议请定律曰”的文字,我想称它为“定律之段”。今本《刑法志》在这一段的结尾,有颜师古的注文:“(前略)杀人先自告,谓杀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赇枉法,谓曲公法而受赂者也。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者也。杀人害重,受赇盗物,赃污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论名而又犯笞,亦皆弃市也。今流俗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复有笞罪亦云‘复有籍笞罪’,皆后人妄加耳,旧本无也。”我们先按师古注文的后半段把流俗本《刑法志》正文部分复原。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如果仔细分析师古所说和《刑法志》原文,实际只在“劓者”之下插入“籍笞”(而且这处籍笞可能和三百之上的籍笞是同一个,对流俗本显然有成见的师古或许没看仔细多说了一个),其他三处仅插入一个“籍”字便可(“籍笞”二字全用亦不影响理解)。“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籍笞〕,〔籍〕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籍〕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籍〕笞罪者,皆弃市。”
关于《刑法志》本文和师古注,我想提出以下两点:
1.关于“籍笞”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师古用的“旧本”权威到什么程度,但流俗本有这样的原文,不会是凭空添加的。“籍笞”见于本段全部共四处,显然也不是一种笔误。“籍”在此处是何意?经反复研究,我觉得没有必要到古字书中去寻找答案,如果联系《刑法志》的其他部分,在随后不久汉景帝的诏令中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景帝元年(前156年)针对文帝时制定的刑制造成受笞的罪人“率多死”的问题进行改革,他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结果犹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景帝诏两次都提到“加笞”的词语,《三国志·陈群传》谈到议复肉刑时陈群说:“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其中的“增加笞”三字,“增”为动词,“加笞”为名词。此处说的一除一增,表示汉文帝时是用“加笞”代替了部分“肉刑”。根据以上资料,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张苍等人上奏文中“籍笞”的含义就是“加笞”,“籍”等于“加”。无论《汉书》的版本到底如何,由此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张苍等人当初的这篇奏文中,这个字是存在的。“籍”字恰好说明这里的“笞”不是一般作为独立刑罚的笞,而是附着于髡钳城旦之上的附加刑,它可能比加笞的“加”,更能体现出“附加”的含义。过去的理解,把这里的“笞”误认为是汉代的“笞刑”,完全是因为少了一个“籍”字的缘故,结果造成从师古开始就说它是笞刑,这很不准确,不合张苍所拟令文的原意。师古不明其义,斥责流俗本是妄加,其实这正是流俗本不同于师古手头的所谓“旧本”的一个优点,应该说流俗本更忠实法令的原貌(至于是否忠于班固的《汉书》,我们不知道),在上奏文中需要表示刑罚内在特点时,此字实不可少。
2.师古的误注。
在师古看来,新的改动为:杀人自首、受赇枉法、主守自盗等三罪,都是论名后又犯笞将被处以弃市。我认为他的这一理解是错误的。“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籍〕笞罪者,皆弃市”。是一个复杂的复句。文中由“及”字(请务必注意这个“及”字)先列举了并列关系的三个主语,然后共用“者”字以下的“皆弃市”三个字为谓语,构成全句的主谓关系。我们设三个主语为A、B、C,那么A=当斩右止,B=杀人先自告,C=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籍〕笞罪。因此原文可简化成如下的句子,“A及B及C者,皆弃市”。所以原文真正的意思是:
B.杀人先自告,弃市。
即过去对杀人后自首者不处死刑,可能有减刑的措施;新法不再考虑自首情节,只要杀人(应指故杀)一律弃市。这一项不包括在复犯籍笞的一类中,师古的说法有误。真正需要再犯籍笞才处死刑的只是指下面两种,它们是C主语内部的又一并列和条件关系,意思为:
C1.吏坐受赇枉法、已论命复有籍笞罪者,弃市。
C2.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籍笞罪者,弃市。
笔者的看法是,B作为主语和C主语全部文字并列(由“及”字构成这一并列关系),但不和C主语中的两个分句C1、C2中的受赇枉法、监守自盗并列。
“论命”的含义有些不好理解,根据晋灼的注文“命者,名也,成其罪也”,似乎可以推测,论命是指经过审判,罪名成立。为什么用这样的词句呢?我想它可能包含的意思较多,比如审判后已经论罪,一种是受到刑罚处罚进入服刑期;另一种则可能是在囚系时因恰逢大赦,虽罪名已成,却未及判决或执行,这些也许都属于“已论命”。“复有籍笞罪”是指在曾有受赇枉法和监守自盗这两种犯赃罪行之一已论命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结果又犯了“籍笞”罪,即又犯了“髡钳城旦籍笞五百”(相当以前的当斩左止者)或是“髡钳城旦籍笞三百”(相当以前的当劓者)这样等级的罪行。因为后犯的是比较严重的重罪,结合前科曾犯过赃罪,对这种特定累犯,以前处肉刑,现在则改为处以弃市这样的死刑。
如果按原来的理解,仅是在犯了“笞”罪后就弃市,很不合情理。比照一下睡虎地秦墓竹简(以下简称睡简)的相关内容,一般来说,笞在笞数最少的时候,可能只笞十或二十,完全是小过薄罚,如果再犯这样的小过就要被弃市而丢掉性命,那简直让人无所措手足,再谨慎的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不会复有“笞罪”而是复有“籍笞罪”才被判处弃市。
根据令文和睡简中见到的刑名之例,文帝时对肉刑所作的改革应当如下:“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例如‘黥为城旦’变成‘髡钳城旦’)。”“当劓者,籍笞三百(例如‘黥劓为城旦’变成‘髡钳城旦籍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籍笞五百(例如‘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变成‘髡钳城旦籍笞五百’)。”“当斩右止者,弃市。”“籍”字因笔画太多,法律条文用字时可能很快便用“加”代替了,比如后来的汉景帝减少加笞的数量,在景帝元年,像上面例子中的髡钳城旦籍笞三百改为髡钳城旦加笞二百;髡钳城旦籍笞五百改为髡钳城旦加笞三百。在景帝中六年,又再次减笞,前例中的髡钳城旦加笞二百被改成髡钳城旦加笞一百;髡钳城旦加笞三百改成髡钳城旦加笞二百,也就是说,作为髡钳刑,连不加笞的一种合计在内,其内部以是否加笞、加笞多少分为三级(在稍后的叙述中可以得知,在这次改革时它们的刑期规定的年限相同)。后来大概觉得不用“加”字也不影响理解,干脆省略了。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师古也许可以称为注释《汉书》的大家,但他肯定不是明了汉代刑制的行家。
张苍等的上奏文的第二段是有关刑期的规定,我想称其为“定令之段”,估计汉代对刑罚的细节规定都在律外以令的形式补充。以下分析这一段第一小节。为了以后的论证能够展开,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师古的注文选出,放在原来的位置上。为了便于区别,注文比正文小一号字:“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师古曰: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鬼薪白粲满三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隶妾亦然也。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滋贺先生“假说”的一个理由,是考虑到现有版本的文字(指正文)里,没有关于最初判处鬼薪白粲以后如何确定刑期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今本《汉书》上所有的文字考虑进去,即使不采取补进字句的方式,而只是在现有版本的文字范围内适当调整本文和注文,也会发现文意突然通顺起来。在作这种调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汉书》版本方面曾经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作为可以进行调整的正当理由。兹举例如下:
例一:《汉书》的有些注文有脱漏注释者姓名的情况,如《卫青传》提到卫青麾下为特将者十五人,其中一位是李沮,《汉书》的正文是:“李沮,云中人。”此句下的注释只写有:“沮音俎。”没有通常注前应有的注释者名,而且现存的各种版本都在这里脱注者名,王先谦认为是脱了“师古曰”三个字。
例二:除了上述一类的问题,《汉书》还存在正文与注文舛乱的情况。如《地理志》谈到京兆尹管辖下的各县,其中有:“南陵,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蓝田谷,北入渭。师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沂音先历反。视读曰示。”按这里的文本,“师古曰”以后应是注文。钱大昕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认为“师”字是后人妄加,应删去;“古”字以下是班氏本文(即《汉书》的正文),“沂音”上则当有“师古曰”三个字。我觉得钱氏的考证是正确的,如果依其意改过,这后一段为:“霸水……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师古曰〕:沂音先历反,视读曰示。”[①c]
我想,今本《汉书·刑法志》也有出现上面这样的版本错误的可能。在仔细地分析正文和注文之后,我考虑出另外一种修正方案。即认为“鬼薪白粲满三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不是师古的注文而是《刑法志》正文,而且这一句正文后的注文仅出现脱漏注释人名,那不过是今本《汉书》中常有的现象,只需要增加“某某曰”三字,全文即可通顺,甚至可以不加注释者名而保持原样也行。这样,基本不用增添字词,问题同样也能得到解决。以下是我推定的复原文,其中增字也用〔〕括起来,为了便于区别,注文比正文小一号字。重点是下加横线的部分,这是原为师古注文,而我认为是《汉书》正文的地方。为了分析司寇的问题,将如淳的注也一并录出:“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师古曰: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鬼薪白粲满三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师古曰〕:隶妾亦然也。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如淳曰:罪降为司寇,故一岁;正司寇,故二岁也。”这样调整以后,原来被认为令文中没有出现的鬼薪白粲的刑期便显露了出来,它的刑期是四岁。如果为了看的更清晰些,不妨把注文再去掉,把四种刑罚的刑期规定一一列举,问题可以说圆满解决了。《刑法志》的文字可以用如下方式表示:
罪人狱已决:1.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
2.鬼薪白粲‖满三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
3.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免为庶人。
4.作如司寇二岁,免为庶人。我们可以看到,前三种刑罚的新规定所使用的句式,一律写成为:“××刑、满×岁,为××刑……”;最后,四种刑罚一致都是写“××刑×岁,免为庶人”。我们所复原的正文即第2项有关鬼薪白粲的刑期规定,完全符合这一句式。根据上面所说《汉书》版本所存在的问题(例二),可以认为传世的《汉书》在这里是误将《刑法志》正文当做师古(或他人)的注文了,至于从什么时期变成现在的样子,我想,大概是在西晋以后,以下有四点需要详细说明:
(一)为《汉书》作注的人,有东汉、三国、晋等时期的不少人,仅以《刑法志》部分来看就有十余人,具体到我们研究的文帝改制部分,也有三国时的李奇、孟康、如淳,晋时的晋灼、臣瓒。这些人去汉不远,如果正文没有鬼薪白粲这个在文帝改革前后一直存在于汉代刑制中的刑名的刑期,他们首钊菀追⑾终*
样不正常情况的人,但却没有一个人讲到,说明当时的写本是不存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问题的。估计是在后来某个时期把分别流传的《汉书》和诸家注合在一起编成注本的时候,造成正文和注文的舛乱。不少人据敦煌写本《汉书》残卷,指出颜师古往往把前人的注当做自己的[①d],如真是这样,我想,作为一个唐代人,他对汉代的刑制并不精通,所以可能按他人注释照录了这段已混乱的注文。另一种情况,也可能是在师古以后出现正文和注文的混乱。
(二)经过复原的正文“鬼薪白粲满三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讲到鬼薪白粲降罪后只提到降为隶臣,少了一个“妾”字,这可能是张苍所定令文的原文,也可能是班固摘录时的省减,就和我们上面提到的“籍笞”的问题相仿。在秦汉一直到文帝时,“隶臣妾”只简称为隶臣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后来隶臣妾的刑名消失了,特别是三国以后劳役刑名一律改成按刑期的岁数称呼,对于这以后的《汉书》读者来说,解释一下是必要的,因此后人加注“隶妾亦然也”一句,说明女徒也是一样,免得人们发生疑问。其实,即便张苍等人原来就是这样写的,当时的汉人也不会误解,因为从女徒“白粲”减下来,比照男徒“鬼薪”减至“隶臣”,谁都知道是指减到与“隶臣”相同的“隶妾”。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班固有意删去了“妾”字。可是,在《汉书》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当把正文和注文合编的时候,这一句下的注文与前述例一相同,也没有注释者的名字,因而容易被后世不懂汉代制度的人在传抄中把前面的正文同化,于是所有文字就接到前一注文后变成了一长段注文。仔细读一下,会发现这一长段注文使人感到不得要领。以致王先谦在他的《汉书补注》中说这里“三岁”误,当为“一岁”,以便衔接上下文。他看到这一句最大的问题是注释和正文前后不能照应,因为在《刑法志》的上句中,明明说的是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到师古解释时怎么会变成“鬼薪白粲满三岁为隶臣”了呢?但是王先谦没有由此发现上面提到的正文与注文舛乱的问题,他的疑问也就变成了主张改动的理由。照他的改法,看上去似乎通顺了,却经不起推敲,因为改后的结果,将使这所谓的师古注变成了一句还不如正文简明扼要的多余的话,我们将正文和按其说法改过的“注文”来对照一下:《刑法志》的正文:“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改后师古“注文”:“鬼薪白粲满一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隶妾亦然也。”如果说师古本会作这样的注,我想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相信。因此可以说,版本出现的错乱把对《汉书》已烂熟于心、功底非常人可比的王先谦也搞糊涂了。当然,《刑法志》有关刑制的这一段是最难读懂的一段,加上版本中的文字已经出了问题,所以谁都可能读错,这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其实“三”字并不误,这句话本来不是师古注文而是令文中有关鬼薪白粲的刑期规定,被后人错羼入注释之文中了。真正的注文只是在它前后的各一小句。
(三)关于“司寇”的问题。根据如淳“罪降为司寇,故一岁;正司寇,故二岁也”的解释,从“隶臣妾”罪降下来的“司寇”,应当代表了男女两性,它似乎和睡简中的“城旦司寇”、“舂司寇”相仿佛,本罪不是司寇,由于是从较高刑种降下来,所以降后刑期较短(这里我只是说明本罪和降罪的区别,不涉及秦汉刑罚的其他同异)。至于“作如司寇”则是指“正司寇”。我的理解,这里是在说本刑(即判处刑罚的当时)就明确判处“作如司寇”,它的名称应该包括男女徒,刑期二年。在这方面,似乎不必拘泥于《汉旧仪》的说法,因为卫宏是在追溯秦制,在他非秦非汉的解说里面不一定全面照顾到汉制,而汉代的“作如司寇”未必专指女徒。在此仅举一例,《后汉书·章帝纪》讲章帝在建初七年九月下减罪诏书,除了对死罪以及亡命各有赦减外,还对囚系的罪人做了如下处理:“系囚鬼薪白粲已上,皆减本罪各一等,输司寇作。”我想,这里所谓的“输司寇作”,正是指西汉文帝以后司寇本名的劳役性质就是“作如司寇”,从章帝诏书的意思来看,鬼薪、城旦可以“输司寇作”,白粲、舂也可以“输司寇作”,表明司寇是没有男女徒名称上的区别的。
(四)本段段首的“罪人狱已决”的含义,本文采用滋贺先生的解释。他认为这一段规定的刑期和废止无期刑,是面向未来的和当时的刑徒两方面,即不仅包括新令颁布前已经判决正在服刑期中的现役刑徒,他们的刑期“从原判决之日”起算的含义,也包括有“今后,凡被判决者从被判决之时”起算刑期的含义。本文下面谈论关于刑期的问题,也以滋贺先生“双重意义说”为前提[①e]。
综合以上分析,文帝改革时完城旦到司寇的刑期结构分别如下:
1.完城旦舂,服本刑三年后,转服鬼薪白粲刑一年,再服隶臣妾刑一年,然后释放,合计刑期为五年。
2.鬼薪白粲,服本刑三年后,转服隶臣妾刑一年,然后释放,合计刑期为四年。
3.隶臣妾,服本刑二年后,转服司寇刑(男女同名)一年,然后释放,合计刑期为三年。
4.作如司寇(男女同名,实际使用时简称司寇),服本刑二年后,释放。
接下来我们看《刑法志》第二段的最后部分,原文是:“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这可能是目前最难懂的一部分,从中可以提出许多不易解答的问题。后一句滋贺先生已经指出“刑城旦舂”的“刑”字是“黥”的代称,解决了我们理解上的一个大困难,但是这里只提“刑城旦舂”,那么原有的“刑为鬼薪”、“刑为隶臣”等类似的带“刑”字的刑名,为何没有提起呢?这也是个问题。让我们且把一系列问题搁置一旁,目前只能知道的是,根据滋贺先生论文中确认“岁”是“一岁”之意,可以推测新法里髡钳城旦舂的刑期,是从判决之日始服劳役满一年后,再按完城旦舂的岁数(五年)服满刑期,其刑期总计为六年。
但是,这与《汉旧仪》的说法真是除了司寇一项之外,没有相同之处了,难道是《汉旧仪》又错了吗?不是的。我认为《汉旧仪》的记载,是基于西汉还有一次刑期改革后的制度所撰述,然而这后一次重要的改革没有被史籍记录下来,因此不为人所知。可以说,连距西汉时间最近的东汉的人们至少是卫宏也不知道。
三、对于历史上一次没有文献记载的刑制改革之发微
滋贺先生在文中提到:“文帝以后直到西汉末,除了减轻笞刑以外,没有再度刑制改革的记录”,但他在文末还提到:“关于隶臣妾,正如滨口重国氏所说,因为它在文帝以后不久便废绝了,所以未被记载在西汉末东汉初所著的《汉旧仪》中,这一观点很有说服力。至于复杂的劳役结构的消失,也许可以解释为,这是刑罚名称由表示劳役的种类向表示刑期长短转化的结果。”滋贺先生这些看法给人以极大的启发:首先,史籍确实找不到文帝后到西汉末何时有再度改革刑制的记录文字。其次,从隶臣妾的废绝和复杂的劳役结构的消失,又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肯定在西汉历史的某一时刻,必然至少有一次针对废除隶臣妾以及将刑名由表示复杂的劳役刑结构改为表示刑期长短的改革(而且这一改革还涉及到刑期方面的新变化)。可是,在提出前述富有卓见的看法之后,滋贺先生却被先入为主的《汉书》存在脱文的思路遮住了视线,忽略了由其本人看法能够引申出来的上述的西汉必有再次改革的结论。
为了把这没有记录的再次刑制改革的历史事件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梳理出来,有必要把一些看上去不相关的人和事,如五行说、秦始皇、刘邦、张苍、汉武帝以及刑制问题做一次综合研究,以便逐步分析他们之间的联系。
《史记·秦始皇本纪》讲到秦初并天下后,“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在这段文字后有注文,张晏曰:“水,北方,黑,终数六,故以六寸为符,六尺为步。”瓒曰:“水数六,故以六为名。”
五德是据阴阳五行学说而来,它在实际运用时,其中包括有关正朔、颜色和数字的内容。刘邦起事反秦时为了让属下对他产生神一样的崇拜,曾经剑斩白蛇,杜撰出自己是赤帝子,所以颜色尚赤。但以他当时的身份,还无资格考虑正朔、数字和使用五行中的哪一德。灭秦后,刘邦当了汉王,后来还当了皇帝,需要使用某一德时,又完全改回到和秦一样了。据《史记·张丞相列传》载:“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汉用水德,仍是十月朔、尚黑,自然也是数用“六”。张苍是水德的坚定主张者,《史记》谈到他用水德“以比定律令”,这句话很重要,说明他在定律令时也是坚决贯彻水德主张的。如果联想到文帝刑制改革时正是由身为丞相的张苍作为第一主持人,这也是唯一有关他定律令的记载,那么这次定律令中在确定刑期的问题上,张苍绝不会忘记水德之终数是“六”,法律作为最重要的制度理应受水德支配,刑期的最高刑必然是“六岁”。张苍的立场、水德及其相应所用之“终数”,可以为我们上节分析文帝改革各种刑期梯次年限的问题,特别是最高刑期的年限为“六”提供重要的旁证。
在文帝十三年这次刑制改革前,贾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①f]但是以后不久,张苍的“汉为水德说”正式遇到了挑战。据《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十四年,“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文帝让丞相张苍等议此事,结果“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认为不应改变。可是到十五年,成纪地区见了“黄龙”,所以文帝又召来公孙臣,任为博士,商讨改土德的事,这次张苍被冷落并被免官。只是改土德的事正在进行中,由于乘机参与进来的新垣平的欺诈行为暴露被诛,文帝感觉很没趣,便停止了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可以想见,此后的“数”自然还是维持为“六”。
变化应当是开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据《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记载:“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这一段下有张晏注:“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武帝时“数”用“五”的情况,有些早已开始。如儒家经典原来提出的是“六艺”,包括《乐》,公元前136年则只设《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经”博士;又如武帝先是将货币从“三铢钱”改为“半两钱”,后来到公元前118年又改成“五铢钱”。至于到太初元年五月,可以推想,是进行一次总的清算,数都用“五”了。刑罚这样重要的制度也不会例外,原来的劳役刑刑期最高的是六岁刑的髡钳城旦舂,现在必须压缩最高年限,才与用数相符。如果它改成五岁,其它刑罚又是以年限为主要梯次等级依次改下来,原来的刑罚就没有相应的年限上的位置。我想,可能正是此时,隶臣妾被挤出劳役刑的序列,从刑罚中最终消失了。
据富谷氏检索史籍资料,确认文献最晚见到“隶臣妾”,是在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原史料见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李信成)元狩五年,坐为太常纵丞相侵神道,为隶臣”,因此他指出,从大的范围来说,隶臣妾是在武帝中期消失的[①g]。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断。不过他据此认为就在元狩年间隶臣妾这一刑名不再使用的看法也许不确。现在既然推测出上述武帝改制的具体时间,因此我想对富谷氏的研究做一补充修改。元狩五年距离太初元年只有短短的14年,考虑到王侯将相总的人数不多,不一定每年都有人犯罪,就算犯罪,也不一定被判处隶臣妾;《汉书》只是记载王侯将相的历史,有不能反映普通百姓犯罪情况的局限。所以我认为,这条资料虽说有很重要的价值,但不能将隶臣妾刑罚的消失定在元狩年间,而应具体定在“数用五”的太初元年夏五月。从此以后,劳役刑的刑名和刑期有了变化。我们将文帝改革后的刑名和刑期年限与武帝改革后的作一对照:
文帝十三年五月始(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初)
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始
髡钳城旦舂 六岁刑 髡钳城旦舂五岁刑
完城旦舂
五岁刑 完城旦舂 四岁刑
鬼薪白粲
四岁刑 鬼薪白粲 三岁刑
录臣妾 三岁刑 司寇 二岁刑
司寇 二岁刑
武帝时将髡钳、完城旦、鬼薪等分别从六、五、四岁降为五、四、三岁,这样降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让吏民百姓感到大多数劳役刑都减轻了一等,由此使民众了解和赞同五德的改革。沈家本在《赦考》卷二改元条下列举武帝时的情况后说:“武帝即位无赦而改元赦,其后十改元三无赦”。这三次改元不赦,其中就包括太初元年[②g]。作为五德、正朔、服色等这样重大的改制之年如无赦是不正常的,不过现在有了一个释疑的好答案:如果按上面所说的,在此次数用“五”的时候,法律制度上把大部分的劳役刑都永远地减轻一等即减少刑期一年(当然也包括对正在服劳役徒刑的已决犯减少刑期),这和一般的赦只惠及当年已决或未决罪人的情况相比,更显恩泽流远,以致武帝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下其他的赦令了。关于改元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以“太初”元年为界,此前的六次(包括太初)都是在前元满六年后开始改元;此后的几次改元则变成了满四年一改元。这也是直至太初前,武帝朝仍使用终数“六”的一个旁证。
此外,估计这次刑制的改革也同时改变了复杂的逐级降等的劳役结构,以此为界,大概刑罚名称也从表示劳役的种类和刑期的混合状态,转化为基本表示劳役刑期的长短。到这个时候,已经和后来西汉末东汉初卫宏所著的《汉旧仪》叙述的刑期完全一致了。可见,卫宏所说的虽然可以作为汉代刑制的参考,但其说代表的只是他所处的西汉末东汉初时的情况,几种刑名的刑期既不是秦代的,也不是汉文帝时期的,而是汉武帝以后的产物。也就是说,这本来从秦到西汉时期存在的一系列发展过程,在卫宏《汉旧仪》的叙述里几乎都不见了。
现在可以根据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和本文以上的分析,将秦汉时期劳役刑的刑期问题作一个总结。有关这方面的刑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以前,从秦继承下来的劳役刑是不定期刑(特定意义上的无期苦役),这一时期的各种劳役刑的轻重(除去肉刑等附加刑造成的区别外),是以刑名所代表的劳役的苦累程度来加以区别的。
2.汉文帝十三年开始,至汉武帝太初元年为止,即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04年,各种劳役刑基本成为有期刑,最高刑期是六年,以下依次递减。其轻重的区分,是以刑期的长短和劳役的苦累程度(较高的几种有定期递减,形成较复杂的结构)这二者的混合形式为标准(附加刑造成的区别除外)。
3.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刑罚制度进一步做了调整,从秦继承过来的隶臣妾这一刑名被取消,刑罚等级在其上的各劳役刑的刑期顺序减少一年,也就是最高刑期是五年,以下依次递减。经过整合后的各劳役刑内部不再存在复杂的劳役结构,从此劳役刑的刑名基本用来表示刑期的长短(附加刑造成的区别除外),从这时开始,才和《汉旧仪》中说的刑期一致起来。
注释:
[①a] 滋贺秀三:《西汉文帝的刑制改革》,原载《东方学》第79辑,1990年,第1—8页。中文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6—82页。
[②a] 参见高恒《秦律中“隶臣妾”问题的探讨》,《文物》1977年第7期。
[③a] 滋贺先生归纳了富谷至提出的观点并说道:“富谷氏认为,虽然秦律未规定劳役刑的刑期,但服刑者可以因临时的赦免令而获释;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那么称其为‘无期刑’(即终身刑)不如称其为‘不定期刑’更接近实际情况。这也许是对当时(至少是战国末期)刑期问题的最贴切的说明了。”
[①b] 所举各说的来源分别为:沈说,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版,第1536页以下。程说,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3页以下。钱说,见钱大群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173页。范说,见范明辛、曾宪义、张希坡编著《中国法制史教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目前各种论著教材基本在上述几种说法的范围内。
[①c] 本文所引《汉书》及注释,均取自中华书局标点本。
[①d] 参见堀毅《汉书刑法志考证》,《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7页。
[①e] 我原来的看法,同意富谷氏的解释,即《刑法志》中记载的新法是对当时正在服役的已决犯的“处理规定”。后来曾与滋贺先生通信商讨,滋贺先生在来信中又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也有道理。不过,我还有些疑问:有无另一种可能,即“罪人狱已决”仅为对当时正在服刑的已决犯的处理方案,而针对以后犯罪者的方案可能是比照已决犯的解决方式另行制定,它没有被班固抄录在《刑法志》内。因为,令文中“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的语句,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在制定“此令”时,是否还制定了不止一个的“它令”呢?另外,“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的句子,在按完城旦舂岁数服刑以前的那一岁,究竟服的是哪一种刑,从文意上也不清。由于目前还研究不出结果,为了避免横生枝节,这个问题只好存疑。
[①f] 《汉书·贾谊传》。
[①g] 参见富谷至《两群刑徒墓——秦至后汉的刑役和刑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1987年,第569页。
[②g]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赦考》,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版,第5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