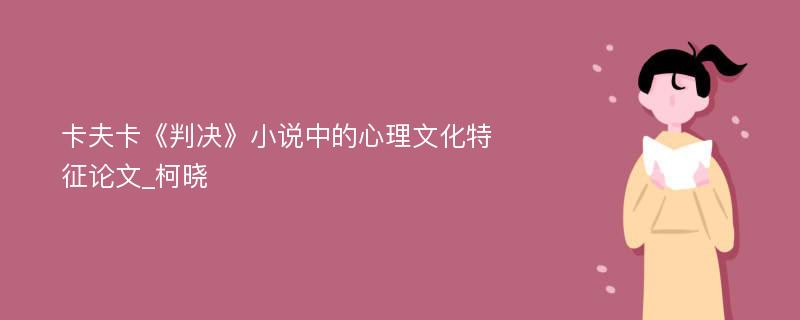
柯晓 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
【摘要】本文在介绍卡夫卡短篇小说《判决》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小说的文本和内容特点,解释了卡夫卡的创作意图和小说中显意识和潜意识转化中的父子冲突处理,笔者认为卡夫卡正是通过现代的镜头感和创作的“效果论”,达到了小说中独树一帜的心理文化特征。
【关键词】文本翻转 意识错位 心理文化 效果论
一、小说《判决》介绍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写于1912年9月22日的晚间,也就是他即将三十岁的时候。卡夫卡说这个小说是一个“夜晚的幽灵”(它写于夜间而且是通宵),他说“我写下它把它固定下来,因而完成对幽灵的抵御。”
这篇小说全文9000字不到的篇幅,开始时以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不管是德文还是中文译本)都在介绍格奥尔格对彼得堡朋友和他们之间关系的“想”,从小说第二段“他在想他的这位朋友”开始,一直到最后“事实上他在这个礼拜天上午写的那封信中把他已经订婚的消息告诉了他的朋友。”④离开父子关系主题的漫长的开头是这篇小说文本的最大特点,而小说结尾儿子突然被父亲判决投水淹死并且他真的投水自杀表现出的父子冲突,是这篇小说内容的最大特点。
二、显意识和潜意识心理文化中的父子冲突
解读《判决》的关键问题是父子冲突的理解,不管从“儿子心理学”还是“父权”、卡夫卡亲身经历等角度解读都有点隔靴搔痒,笔者从黄燎宇先生的《卡夫卡的弦外之音——论卡夫卡的叙事风格》⑤一文得到很大启发,黄先生从卡夫卡的《平常的困惑》一个小故事出发,得出卡夫卡叙事是“投影式写作”,“卡夫卡是一个写自我、写内心的作家,把内心世界投射到外部世界,使虚幻朦胧的下意识形象化、客体化、打破了心灵与外界、幻觉与真实的界限。”⑥
体现在这篇小说中,那就是关于主人公格奥尔格心理的潜意识和显意识表达是错位的,《判决》开始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让读者看到的格奥尔格悠哉的玩耍信件、惦记着彼得堡的朋友,自己经营的公司出人意料的飞速发展、一个月前刚刚和富家姑娘订婚等等,都是他“在想他的这位朋友”自我认知的潜意识,他和父亲的冲突首次出现在到底有没有这位彼得堡的朋友,父亲刚开始认定他没有这位朋友,后来直挺挺的站立在床上,大声责骂的时候明确指出“我当然熟悉你的朋友,他本应是合我心意的儿子。”这是对前面两者就是否在彼得堡真的有这么个朋友争执的交代,更意味着开始三分之一篇幅可能全是格奥尔格自己臆想的“客观事实”,意味着和父亲眼中的“现实”完全相反。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判决》中无所谓父子表达的谁是真正的事实,所以卡夫卡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他在开始就对读者做了误导性的虚构,造成了后面阅读体验中的荒诞感,就像先给读者带了有色眼镜,从格奥尔格的自我心理认知去感受这个人,如果我们反过来从父亲角度重新理解开始的三分之一篇幅,解读为什么父亲要发疯一样辱骂格奥尔格,那就要从父亲后来的大段责备中提炼线索,彻底翻转这开始三分之一篇幅的格奥尔格的“自我感觉良好”和读者对格奥尔格的感觉良好。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如父亲所责骂的格奥尔格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把亲兄弟逼走俄罗斯,一直拒绝和富家姑娘订婚,甚至亲兄弟在“俄国垮了”也不妥协,觉得“他应该容忍我这个人,我可无法把我变成另一个人,变得和现在不一样,更适合保持友谊的人”,导致亲兄弟甚至母亲在两年前去世也无法返回家里,利用父亲的客户资源发展了公司,把父亲在公司由“照着自己看法办事”变得“比以往审慎了”,然后对年迈的父亲不管不问,甚至好几个月没到过父亲房间,从不关心共同坐着的父亲看的是什么报纸,不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只是嘴上殷勤和自己以为的关心着父亲的健康。
注意对父亲有句描述是“他因能洞察一切而十分得意。”,他判定格奥尔格“这个人太残忍”,所以他把顾客名单都装在自己口袋,格奥尔格都认为“他父亲单用这一点就能让他在全世界无法立足了”,经济无法独立后,父亲说“看你还敢不敢挽起未婚妻的手,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把她从你身边赶跑了”,击碎了格奥尔格的婚姻美梦。最后父亲明确告诉格奥尔格,他一直在监视他,格奥尔格远在彼得堡的“朋友”,“一切都知道了,他知道的事比你自己还多一百倍,一千倍!”宣告了格奥尔格在家庭关系中的破产。在彻底剥夺了格奥尔格的经济关系、感情关系和家庭关系后,判决了他去死。
胡志明在《一部现代的“儿子心理学”》⑦中解读格奥尔格“父亲情节”,笔者认为这恰是卡夫卡为读者设下的阅读体验“陷阱”,如果翻转文本,从父亲角度解读开头三分之一的篇幅,也可以表现为一部父亲的“儿子情节”,父子冲突被卡夫卡消磨在两位主人公的臆想中。
三、卡夫卡小说的心理文化特征分析
卡夫卡小说的难解之处也是高明之处,在于他采用的叙事者讲诉放弃了传统小说的全知和旁知视角,采用单一人物的内部视角和严重局限性,让读者像跟随电影镜头一样猜测下一步剧情,必须由读者开动脑筋去补充信息,不管是《审判》中的约瑟夫·K还是《判决》中的格奥尔格,卡夫卡都会有意标注“他是不考虑明天的”、“他总是忘掉一切的。”,让主人公带着读者接二连三的陷入意外和惊骇,这种叙事者越是心不在焉、稀里糊涂,越让读者感到恐怖的滑稽和叙事者的思维吸引力。然后逐渐被叙事者的思考方式和心理感受同化,无法兼顾对立人物和其他人物的感受。
正如爱伦.坡认为小说创作的关键在于作品中先确认某种效果,具体创作和思考围绕这种预期效果,小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苦心经营”实现的“效果论”。⑧卡夫卡在小说创作前已经有了推理和误导读者以达到阅读快感的效果目的。笔者认为在《判决》这篇经典小说中,文本和内容的最大特点在显意识和潜意识中实现了完整的统一。
注释:
《卡夫卡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
④《审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231—242页,下面文本内容引用不再一一注释。
⑤⑥黄燎宇,《思想者的语言》,三联书店,2013年11月,第130页
⑦胡志明,《一部现代的“儿子心理学” ──解读卡夫卡《判决》的“父亲情结”》,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6月
⑧董衡巽,《一本书搞懂美国文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
论文作者:柯晓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5年10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6/30
标签:父亲论文; 卡夫卡论文; 彼得堡论文; 判决论文; 格奥尔论文; 小说论文; 读者论文; 《文化研究》2015年10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