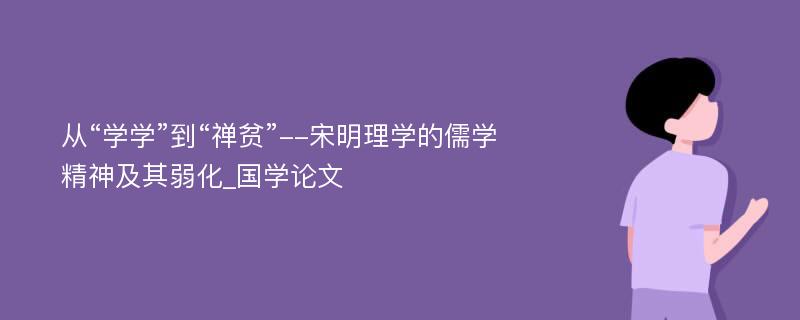
从“学而时习”到“静坐穷理”——儒学的笃行精神及其在宋明理学中的弱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理学论文,学而论文,精神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1)04-0023-08
一、“学而时习”与儒学的笃行精神
孔子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①常有人释曰:“时常复习已学过的知识,不也令人愉快吗?”这种基于现代汉语语境的诠释,既曲解了孔子之言,也使儒学的笃行精神隐而不彰。杜维明先生则云:
儒家文化传统是一个学习文明。儒家能从曲阜、中原、东亚走向世界是“学而时习之”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学习,儒家文明就不可能延续。儒家学习的方式以对话为主。对话是倾听也是参与,是沟通也是反省,是尊重他人也是自尊自重,是广结善缘也是独立自主。②
杜先生对于儒家文明学习传统的强调和赞扬,可谓善也。问题是:杜先生似将“学而时习之”中的“学”、“习”混而为一,且亦将“学习”一词作现代汉语式的理解。相应的,“儒家学习的方式”又被理解为“以对话为主”。此种诠释虽有别于前者,思想后果却是相同的。且就孔子此言所蕴含的笃行精神之被遮蔽而言,杜说似有过之。
事实上,“学”与“习”本有分别,且“习”特别是“时习”的意义问题与儒学的笃行精神关联深刻。若对此视而不见,儒学的这一精神将有遗失之虞,空谈义理之弊亦不可避免。那么,“学”、“习”者何谓?其间有何意义差别?“学而时习之”何以会使人“悦”?
关于“学”。《说文》谓“学(學)”乃“篆文斅省”,本义为“觉悟”。段玉裁释云:
斅觉叠韵。《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按知不足所谓觉悟也。《记》又曰:“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按《兑命》上学字谓教,言教人乃益己之学半。教人谓之学者。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故统谓之学也。……详古之制字,作斅从教,主于觉人。秦以来去攴作学,主于自觉。《学记》之文,学、教分列,已与《兑命》统名为学者殊矣。③
据段氏,作为“觉悟”之“学”(“斅”),本涵“教”(“上之施也”)、“学”(“下之效也”)之义于一体。其中,“学”固然可使学者“觉悟”,以“觉人”为务之“教”亦可反益教者之“觉悟”,此即《兑命》所谓“学学半”。段氏谓“学、教分列”,各主其义,春秋时已然,如孔子论“教”云:“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并以“文、行、忠、信”四者立教(《述而》);至于论“学”,孔子也主要是从“下之效也”的角度而发,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战国之世,诸子言“学”皆已取“下之效”义,如《礼记·大学》云:“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孟子云:“乃所愿,则学孔子也。”④庄子云:“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⑤荀子则更是直以“效”论“学”:“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颜色、出辞气效。”⑥
以“效”解“学”,虽与“学”之“觉悟”本义有差,然“效”毕竟是导向“觉悟”的,故不害文义,朱熹亦云:“学字为言效也。……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⑦
关于“习”。《说文》云:“習,数飞也。”本义为小鸟在太阳下(太阳之明为“白”)反复试飞。“试飞”即是练习或践习,或曰“习行”。现实中,“习行”可谓各种实践活动的统称,如技能之训练、观念之落实、道德之践履、事物之应对、社会之治理和政治之推行等,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是皆习民数者也”⑧、“不习于诵”⑨、“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⑩等,其中的“习”皆是“行”义,不可以“学”释之。
《说文》所谓“数飞”,是指小鸟的反复试飞,此种“反复”即“时习”,朱熹云:“习,鸟数飞也。……谢氏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斋,立时习也。’”(11)一个行为若被反复,易成惯性,此即习惯。习惯的力量很大,就常人而言,它可改变人的性情:“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甚至决定人之善恶:“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12)对于一个族群来说,行为的习惯可化为习俗,成为规矩,影响政教,荀子云:“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13)
当然,作为“觉悟”之“学”已包含了相应的修习实践,真正的觉悟也必在行为中得以体现。同样,“习”也必须以“学”作为其“头脑”,不是盲目乱行,更不是胡作非为。“学”、“习”之间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相互涵摄的。然而二者的内涵毕竟又各有所重,不可混淆,故古人常“学”、“习”并举,以各彰其义,如《礼记·月令》云:“鹰乃学习。”其中的“学习”,非今之“学习”。
关于“学习”的内容和目的。《大学》谓儒者的使命为“修齐治平”。其中,修身是为根本,其目标为仁人君子。仁人君子即是德才兼备者,而以德为要,孔子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修身之要,在于“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古代积淀、承传下来的礼乐文化和典章制度,尤以大、小“六艺”为核心。大“六艺”即六经,它们是人文精神之载体。关于六经涵养教化之功,《礼记·经解》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小“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多为时人借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技能,不过,它们亦有益于修身进德。礼、乐二艺自不必说,即便表面上属于纯粹技能的射艺,也蕴含深厚的道德和政治意蕴,《礼记·射义》云:“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对于射艺的政教功能,《礼记·乐记》指出:“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朱熹举例云:“《记》曰:‘武王克商,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待到周衰礼废,“列国兵争,复尚贯革,故孔子叹之”(14)。
要了悟或掌握大、小“六艺”,仅有慎思与明辨还不行,尚需“时习”之。“时习”“六艺”之学,或可验证所悟之道,或可涵养性情,或可修身进德,或可臻熟所学之艺。无论如何,皆是令人愉悦之事,故朱熹云:“既学而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悦,其进自不能已矣。程子曰:‘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故说。’又曰:‘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15)
“时习”即笃行。在《中庸》中,孔子所说的“学”、“习”进一步演化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其中,“学”、“问”、“思”、“辨”皆可视为“觉悟”之“学”的具体展开。笃行则不然,其内涵自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与“学”一起构成了儒家修道的主要途径。若阙行失笃,儒家之道自无落实的可能。因此,所谓“儒家学习的方式以对话为主”之说,不仅有以偏概全之嫌,且对于儒学的笃行精神或有损伤。
二、笃行精神与儒学的实学性
“学”、“习”或“知”、“行”虽相辅相成,共为修道或弘道之要,然总体而言,先秦诸儒论学时往往更重“习行”。孔子云:“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学文”的前提是“行有余力”:“行”既可使所受之教如孝悌仁信等儒家伦常得以践履与落实,也为学者体认更为“高明”的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若“行”无余力或“行”之粗疏乃至知而不“行”,不仅所受之教不得落实,将“学”之“文”也可能流于虚浮妄诞,所谓“觉悟”自亦无从谈起。孔子在答哀公“弟子孰为好学”之问时还指出:“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孔门弟子学有所成者众多,孔子却独标颜回“好学”,可见其“好学”之甚。然对于颜回如何“好学”,孔子仅概括为“不迁怒,不贰过”。二者似极平易,人人皆可为之,孔子何以独许颜回?其实,孔子以此方式论“好学”,既强调了“行”之于“学”的目的性,也指出了“行”的艰难。
因为重“行”,孔子似乎便有些轻“言”,主张君子应“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甚至“欲无言”,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皆“行”于不言中,人之所为,亦当以笃行为重。在《乡党》中,孔子言慎行笃的风范得到集中的展现:对于所行之事,无论大小抑或内外,他皆真诚待之,不为苟且。即使是饮食坐卧,孔子也严格以礼束身,将修道落实于每一个细小的言行,真可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朱熹因而赞曰:“《乡党》记圣人动容周旋,无不中礼。”(16)《乡党》也表明:仁人君子的生命情怀与人格境界固然彰显于宏大叙事式的道德文章,同样也体现于人伦日用中的琐屑之事。而且,当君子身处卑贱或困顿之境时,其卓尔不群的人性光辉还主要是通过他的平凡行止得以展现的。那些以苟且之心应对细微之事者,又怎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把握好自己的生命方向呢?故欲破常人易患的好高骛远之心和坐而论道之弊,重“行”自为当然。
孔子之所以重“行”,还在于“行”在个体自我完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之论,即是因此而发。这表明:人总是在实践中成长和完善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道德和才能的巨大差异,主要在于其各自所行之道的本质不同。人之或为高尚或为卑劣,皆有相应的“习行”以为支撑。
基于孔子的教化和感召,孔门弟子也多务实不虚,深于践履。比如,“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公冶长》)。曾子则日三省其身:“为人谋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至于颜回,则尤为他人所不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故“贤哉,回也”(《雍也》)。
笃行精神深刻关联着儒学特别是先秦儒学的实学性。所谓“实学”,是指“充实之学”。儒学之所以“充实”而不虚,主要在于“习”、“行”。在儒家看来,“习”、“行”不仅使“学”、“知”得以切己落实,还可充实学者身心,协和平治天下。对此,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儒学首先是“为己之学”(《宪问》)。“为己”者,谓“学习”首先充实和完善的是学者自身的人文生命。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道之“凝聚”于一身,是为德;德得之于心而见之于行,实有诸己,可谓“实”。此“实”能润泽身心,而显人格之美与气象之大,孟子云:“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17)对于这种充实之美,荀子尝不无夸张地指出: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18)
欲达此种充实,固须问道以自觉,成败之关键则在于能否践道而行。《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强调了“行”之于“自得”的重要性。孟、荀则分别从“集义”(19)和“积善”(20)的角度予以说明,二子关于人性善恶之设定虽然相背,然对于何以能希圣成贤,皆以“集”/“积”善为根本,皆突出了“行”之笃实性。只不过,孟子之“集”强调的是不断扩充善端与善行,荀子之“积”则意在以善行之凝聚而化性之恶质。其中,“行”相对于“知”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个人成圣中的关键作用,荀子理之甚清,曰: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21)
杨倞注“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云:“行之则通明于事也,通明于事则为圣人。”又云:“言圣人无他,在止于行其所学也。”(22)在荀子看来,成圣是以“学”止于“行”为前提的,而圣之为圣,不过是“行”之“通明”(即通达)而已。所以,儒者的精神和气象,皆在于其学之充实,而此充实,又在于其行之笃实和通达。
另一方面,儒学亦是“事功”之学。“事功”意味着儒者的修身进德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自知自觉,也并不是为了一己之富贵通达,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他既应“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又须以其先知先觉来“觉悟”后知后觉者(23)。一言以蔽之,对于庶民,儒者的使命是既“富之”,又“教之”(《子路》)。否则,即为自私和褊小,非为真儒。无论“富之”抑或“教之”,儒者皆需率先垂范、切实治事,精进不已,从而“充实”其学,光大其道。孔子的立身处世即是如此,其行政教、游列国、治《六经》,皆为斯道。即便是面对“以费畔”的公山弗扰之召时,他也心怀理想,欲往救世,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孟子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此则“治天下可运之掌上”(24)。荀子亦云:“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儒者)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25),所谓“其道一”,“谓皆归于治也。故禹、汤、文、武事迹不同,其于为治一也”(26)。可见,对于儒者而言,王者尽管有异,时势可以有变,所谓“天下”之观念,治世之理想却是始终如一的。
儒学的这一“实学”品格将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贯通起来,诚如孟子所云:“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7)个体生命不是孤独封闭的,其充实和完美是与他者的生命存在血脉相通的。离开了对于他者的切己关怀,个体生命的伦理指向和意义支撑将会因此而有亏欠,从而制约着其自身的充实与饱满,儒学的实学品性亦将无从谈起。所谓“修齐治平”,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28),即此之谓也。
当然,笃行并非意味着愚行,亦非乡愿之行;笃行以道为指引,以“学”为辅助,它既践履着道,又印证着“学”(29);笃行立足于中正(30),以礼为经,以变易为权(31),注重制度建设(32);笃行也意味着坚毅与果敢(33)。以此行道,儒学何得而不“实”哉?
三、宋明理学论学重心的“逻辑性”转移与笃行精神之弱化
“学”、“习”不分以至消“习”入“学”,将会有伤儒学的笃行精神,进而伤其实学品格。在儒学发展史上,宋明理学通过“穷理”、“复性”之说以及对于“行”之意义的重新定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弱化了先秦儒学开创的笃行精神。儒学由是而显背实蹈虚之弊,流荡之风亦势不可免。
本来,宋明诸子如程、张、朱、王等人亦皆重笃行,皆主“学”、“习”或“知”、“行”之统一,并视此统一为修身进德、希圣成贤之根本。如朱熹云:“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34)“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35)。王阳明亦曰:“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某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曾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36)对于那种隔膜修己之“学”与“簿书讼狱”之“事”(即“习行”)的做法,阳明斥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37)强调“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38)。
念念不忘“践行”、反对“著空”的宋明理学最后却“著”了“空”,实在是悖论。从思想理路上看,这一结果与宋明理学论学重点的“逻辑性转移”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笃行精神之弱化不无关系。
首先,从弘道之学到穷理之学。道之本义为“行”,因“行”而引申出“路”义,较之于“路”,道之“行”义更为根本。以“行”、“路”之义为基础,道进而引申出引导(疏导)、方法(途径、手段)、理(原理、原则、规律)和言说等义(39)。与“行”之本义相应,道之于世界,即是“生生”之本身。此“生生”之人文化,被赋予相应的价值与意义诉求,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儒学以弘道为己任,《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地生物(即道之生生)博厚高明、悠久无疆。相应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40),人之“受命”过程也是深远无尽的。故“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直至其生命之尽时。只有“尽其道而死”,方为“正命也”(41)。
对于天地万物来说,“生生”之道即是其本根,且“生生”中自有其条理,是为“道理”。所以,有道方有理,无道则无理。先儒论学,重在明道和践道,而罕言“理”字,主要原因即在于此。然至宋明理学,随着二程“体贴”出“天理”二字,“生生”的本根性(即基础性地位)遂被抽离,道与理的内涵及其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理升格为道(或曰道降格为理),为太极,三者内涵已无区别,皆谓生之所以然者:“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42)、“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另一方面,相对于道和太极,诸儒论学,皆着重从“理”或“天理”入手,以求简明、直接。如论世界之本,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43)论事物之源,曰:“万事皆出于理。”(44)论理与诸德之关系,曰:“理,只是一个理。理举着,全无欠阙。且如言着仁,则都在仁上;言着诚,则都在诚上;言着忠恕,则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则都在忠信上。只为只是这个道理,自然血脉贯通。”(45)论立志,曰:“只念念要存天理,便是立志。”(46)由是论为学次第,曰:“学者须是穷理为先,如此则方有学。”(47)如此一来,儒学的内容和精神遂发生重要变化,由弘道之学一转而为穷理之学。
其次,从穷理之学到复性之学。天理如何可穷?途径有二:一是从具体物理入手,格物致知。物理是天理的展现,格物致知,一旦贯通,亦可悟得天理。然万物纷纭,其理如何可致?且若处置不当,学者还易为外物所诱,随其流转。如此物理尚且难究,何能穷得天理!二是“尽性”以彰显天理。《中庸》云:“天命之谓性。”在理学家看来,此性乃义理之性,为天之所命,同物理一样,也是天理的呈现。就此而言,性与理是统一的:“缘这道理,不是外来物事,只是自家本来合有底。”(48)“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49)。对于此性,理学家又称之为“本体”:“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50)它既体现天理,故先天善良。学者若能“尽性”,将其本性纯粹、“通透”地展现出来,即是天理呈现,“穷理尽性至命,只是一事”(51)。相对于向外格致物理,反身“尽性”直指本心,方便明达,从而成为理学论学之重心。
至于现实中为何罕有人能尽其性,以达天理,实为私欲昏乱和遮蔽所致,“人于天理昏者,是只为嗜欲乱著佗”(52)。“人性本善,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53)。若祛除私欲的昏乱,还人性以本来面目(此即“尽性”),自然就能彰显天理。故穷理其实在于“复性”,在于“返回”人性或人心的本来状态(“复其初”)(54):“圣人所由惟一理,人须要复其初”(55)、“圣贤千言万语,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56)、“圣人……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57)。于是,穷理之学一转而又为复性之学。
最后,从复性之学到“静坐”工夫。复性明理之要在于祛除私欲,“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讲学”(58)。这就不能不做工夫。工夫有二:小学与大学,“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59)。小学工夫是践行各种人伦日用之事,并在实事实行中涵养性情;大学工夫则是穷究事情之所以然。实际上,作为工夫的大学与小学说的就是“学”、“习”或“知”、“行”问题。关于“学”、“知”与“习”、“行”,理学虽主张统一,却又有先后和轻重之判:“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60)若究其根本,“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学”、“知”优先于“习”、“行”,因是而彰。伊川还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61)朱熹对此颇多赞赏,在与弟子论学时常常提及,如:“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62)可见,“习”、“行”固然是指实事实行,其意义指向却已非切实地“做事”,而在于“涵养”。其所涵养者,乃是作为“本原”的心体或性体。故理学虽亦主张“致知”和“力行”不可偏废,然“力行”的独立意义已被弱化或消解。借助于工夫论,复性明理思想一转成了“思索义理,涵养本原”(63)之说。
不仅如此,无论是“思索”还是“涵养”,皆须心之恭敬。“敬”强调的是执守“心体”不为物欲或外物所动,以保证“心”中之“理”存而不失。“居敬”与“穷理”本为一事,朱熹云:“主敬、穷理虽二端,其实一本。”(64)阳明则直云:“居敬即是穷理。”(65)至于如何“居敬”,朱熹云:“持敬以静为主。”(66)又云:“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明道、延平皆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67)阳明亦指出:“人于平旦时起坐,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68)“静坐”可直达本原。其间,不仅要摈除喜怒哀乐之情,甚至连思虑都不能有:“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若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69)此时(即心之“未发”时),物欲尚无,心性朗朗,天理昭昭自然呈现:“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存乎天理而无人欲。”(70)既然“静坐”之于“思索”和“涵养”有如此功用,所谓“力行”自然愈加“边缘化”了。
显然,宋明理学致思理路的上述展开,引导、“推动”了其论学重点的逐步转移。在此过程中,“习”、“行”的思想地位因此而被弱化,所谓静坐养心、独冥天理为主要内涵的工夫论便成为宋明理学的关注重心所在,“本体工夫之辨”亦成为其主导性的问题意识。笃行精神削弱的直接后果便是宋明理学与现实生活的逐渐疏离,损伤了儒学的实学品格。待到其学之末流,或空谈义理,或固执僵化,或狂禅放荡,或寂坐操存,诸种流弊越发严重,势不可止。
对于宋明理学的上述表现,历来学者多有批评。南宋时,叶适就曾指出,涵养应有其着力处,不可悬空进行,他以修仁为例,曰:“体孔子之言仁,要须有用力处。‘克己复礼’,‘为仁由己’,其具体也。‘出门如宾,使民如祭’,其操术也。‘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又术之降杀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无不在仁,庶可矣。”(71)他还对时儒修道工夫的寂灭倾向批评道:“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默视危拱,不能有论诘,猥曰‘道已存矣’。”(72)清代,王夫之、颜元和戴震等皆对宋明理学的工夫论及其后果多有指责,如颜元辟云:
是以当日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但仿佛口角,各自以为孔、颜复出矣。至于靖康之际,户比肩踵皆主敬习静之人,而朝陛疆场无片筹寸绩之土。……丧此不迫,乾坤尚安赖哉!(73)
近儒对于宋明理学亦有相似的批评。熊十力尝谓宋儒的工夫论“功力深时,必走入寂灭,将有反人生的倾向”(74)。牟宗三则辟阳明后学云:“王学的发展,何以会成狂禅,成为空谈心性?这在他的弟子应该负责的。”认为王龙溪只把握了阳明“良知”“灵明”的一面,而遗失了“良知”的天理性,致使其学“未免荡矣”(75)。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不如说,龙溪之学之所以“荡”,正是阳明思想乃至整个宋明理学自身所蕴涵的。在思想逻辑上,自有其必然性。
注释:
①《论语·学而》。以下引《论语》,仅注篇名。
②庞朴主编:《儒林》(第1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7页。
④《孟子·公孙丑上》。
⑤《庄子·德充符》。
⑥《荀子·大略》。
⑦朱熹:《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1页。
⑧《国语·周语》。
⑨《战国策·秦策》。
⑩《易传·象传·坎》。
(11)朱熹:《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
(12)王充:《论衡》卷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5页。
(13)《荀子·大略》。
(14)朱熹:《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第25页。
(15)朱熹:《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
(1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38,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97页。
(17)《孟子·尽心下》。《荀子·劝学》亦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18)《荀子·儒效》。
(19)《孟子·公孙丑上》。
(20)《荀子·性恶》。荀子亦言“积德”,如《儒效》又云:“遵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道。”
(21)《荀子·儒效》。
(22)杨倞:《荀子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23)《孟子·万章上》。
(24)《孟子·公孙丑上》。
(25)《荀子·儒效》。
(26)杨倞:《荀子注》,第65页。
(27)《孟子·尽心上》。
(28)《孟子·梁惠王下》。
(29)《荀子》对于“陋儒”(《劝学》)、“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非十二子》)以及“俗儒”、“雅儒”(《儒效》)的鉴别与批判,对于“大儒”与圣人的推崇,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现实之行。
(30)孔子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子路》)中正之道乃儒学的基本内容之一。
(31)如孔子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孟子亦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又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32)以礼导行,是儒家的基本态度,荀子云:“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荀子·礼论》)但礼又非凝固不变、僵化执著的,而是可以“义起”的,如《礼记·礼运》云:“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
(33)《中庸》云:“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3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第149页。
(3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第148页。
(3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页。
(3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3,第94~95页。
(3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1,第12页。
(39)关于道的内涵及其意义演变,详见陈徽《儒家“道”、“德”观之寻根阐释及其“形上化”后果》,《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第45~50页。
(40)《诗·周颂·维天之命》。
(41)《孟子·尽心上》。
(4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编》(宋元明之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5页。
(4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第2页。
(44)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2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4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第100页。
(4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1,第11页。
(47)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0,第163页。
(4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第153页。
(4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第82页。
(5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1,第24页。
(51)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8,第242页。
(52)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2上,第93页。
(5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第133页。
(54)先儒论学,皆不云复性或返其初,如孟子云“扩充”、“集义”,荀子曰“化性起伪”、“积学”等。所谓“复”、“返”,皆老、庄之言。如《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六章》)、“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十六章》)《庄子》亦频曰“归根”(《秋水》)、“反其真”(《大宗师》)、“复其初”(《缮性》)等。
(55)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6,第133页。
(5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第133页。
(5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2,第54页。
(5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第207页。
(5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第124页。
(6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第148页。
(61)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8,第236页。
(6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第148页。
(6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第149页。
(6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第150页。
(6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1,第33页。
(6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第151页。
(6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第210页。
(6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1,第21页。
(69)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8,第250页。
(7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7,第259页。
(71)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65页。
(72)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55,第1801页。
(73)颜元:《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0页。
(74)高瑞泉编选:《返本开新——熊十力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326页。
(75)牟宗三:《人文讲习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标签: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学而论文; 理学论文; 四书章句集注论文; 孔子论文; 朱熹论文; 论语集注论文; 乡党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