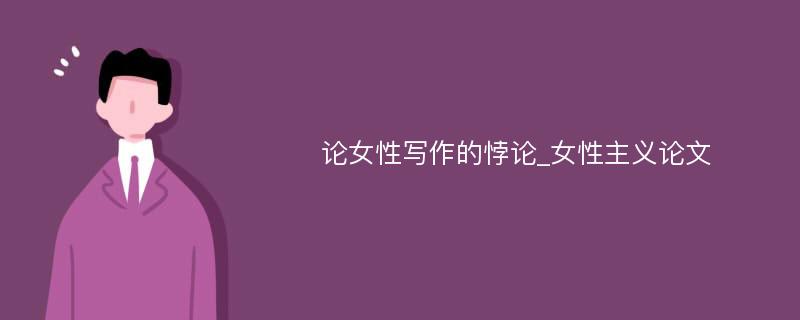
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话题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下五个话题也就是女性写作的五个悖论,是我们在女性文学批评中经常遇到的,有时候论者倡扬一端而排弃另一端,思维呈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状态。我个人有一度也陷于这样的思维状态中。后来我认识到,二元对立的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在丰富复杂的客观事物面前是远远不够用的,而且很容易使我们误入歧途;必须对这种思维状态进行整合,在此端和彼端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走出线性思维的怪圈。我对以下五个话题的思考即是基于这样的寻求,如果在寻求过程中还依然在线性思维的怪圈中徘徊,那么我将继续寻求!
其一、性别意识和超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既指女性意识,也指男性意识。但我这里所说的性别意识主要是指女性意识,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男性意识是显在的,而女性意识却是被压抑的,因而不存在需要张扬男性意识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性别意识主要是指女性意识的原因。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不干脆说是女性意识而说性别意识呢?那是为了便于与所谓的超性别意识相对应。
女性写作之所以区别于男性写作,是由于它是一种具有性别意识即具有女性性别意识的写作,我想这恐怕不至于有太大的歧义。事实上这正是八、九十年代女性写作较之以往的一大跨越。长期以来,我们的女性写作基本上是缺少性别意识的写作,“中性化”和“无性化”是普遍的倾向。从丁玲在延安时期所写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到草明在建国以后所写的《乘风破浪》,一直到新时期初期谌容所写的《光明与黑暗》,都是这样的作品。我这样说并没有否定这些作品的意思,“中性化”或“无性化”的写作也会产生一些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们的女性写作长期缺乏性别意识的觉醒。这当然有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恕我略而不谈。
性别意识的觉醒应该是新时期以后的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人的问题的重新被提出,人道主义的声浪日高,性别意识也随之苏醒了。八十年代初期,张洁和张辛欣的一些作品率先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张洁的《方舟》已经被公认为是女性主义写作的典型的文本,三个同病相怜的女性在“诺亚方舟”里的境遇,喻示着当代女性生存的困境,以及她们对男性的失望和排弃。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在展现女性的焦灼和生存困境的同时,还表现了女性与男性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竞争,女性企图从“诺亚方舟”突围出去的愿望,也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在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和铁凝的《麦秸垛》、《玫瑰门》等作品中,也表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但却没有张洁式的偏执。至此,中国的女性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主义倾向,其资源背景主要是中国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和文化变革。
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前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性别意识的大面积的苏醒,许多女作家、特别是一些年轻女作家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意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被命名为“女性狂欢节”和“女性高潮体验”的局面。一种被指称为“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女性写作堂堂正正地走进了文坛。对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命体验(包括性体验)的书写、对个体欲望的书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许多女作家都寻找到了书写这种体验和欲望的个人化的话语方式。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以及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名字频频在媒体曝光。此时性别意识苏醒的资源背景显然与七、八十年代已有所不同,一方面是对世妇会的呼应,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借鉴。
所谓超性别意识,似乎与性别意识是对立的,然而实际上,这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悖论。超性别意识是以有性别意识为前提的,它是性别意识的一种提升,但并不以抛弃性别意识为代价。按照陈染《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的观点,超性别意识应该有三层意思:一层是指爱情,“我的想法是: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异性爱霸权地位终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一种同性爱或同性恋,是为她的作品写的“姐妹情谊”所做的一个注脚;另一层是指“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洽地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情感和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地完整”,这里指的是把两性融合起来的一种写作姿态;三是指“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人,往往首先是脱离了性别来看待他人的本质的,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超出性别的。单纯地看到那是一个女性或那是一个男性,未免肤浅”,这里指的是要以超性别意识来看待人、欣赏人。其实,类似的话其他女作家和女评论家也曾说过,比如铁凝讲过“双向视角”、“第三性视角”(《铁凝文集·玫瑰门·写在卷首》),王绯讲过女性文学批评的“两种眼光(女性的眼光和中性的眼光)”(《女性与阅读期待》),等等,不过都不像陈染说得这么尖锐、这么明确,并且直接使用了“超性别意识”这一语汇。
无论是陈染还是铁凝、王绯,她们都没有否定性别意识。恰恰相反,她们自身的写作都是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的写作,但又是超越了性别意识的写作。女性主义批评家崔卫平甚至在她的文章中宣称自己是“男性主义者”,她说:“我所说的‘男性主义’,是经过了女性主义的男性主义,是分享了女性主义话语的男性主义;作为一名新的男性主义者,不管其是女人还是男人,都要走完女性主义的全部历程,并始终同女性主义并驾齐驱。”(《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重要的立场》)
我曾经认为提出所谓超性别意识,这是女性主义者的一种策略。现在看来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它是一种策略,但又不完全是一种策略,实际上是性别意识的一种升华,是性别意识与人的意识的一种融合。
其二、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
私人空间的开拓是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过去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比较强调的是开拓公共空间,不太重视开拓私人空间,甚至写私人空间的东西还要受到非议。如今大量写私人空间的作品出现了,其中尤以女性写作为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陈染、林白、海男诸人。写私人空间的作品受到媒体和评论界的极大的关注。
所谓私人空间,对于女性写作来说,主要是指与女性的个体生存经验、情感经验和生命经验有关的东西,特别是女性的身体经验和性经验。对女性身体经验和性经验的书写,在以往的女性写作中是很少见的,它几乎被视为一个禁区。在八十年代上半期张洁和张辛欣的作品中都还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八十年代下半期,王安忆、铁凝和残雪的某些作品首先突破了这一禁区,但在当时的整个女性写作语境中,这毕竟还是一种局部的现象。到了九十年代,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女性写作者显然是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者关于“身体写作”或“躯体写作”的理论的影响,“躯体写作”和“躯体语言”遂成为女性写作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私人生活》(陈染)、《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我的情人们》(海男)等作品的相继问世,“个人化写作”、“私语化写作”、对女性的身体经验和性经验的书写也就蔚然成风。
阅读这些主要书写女性私人空间(特别是书写女性身体经验和性经验)的作品,是对传统的阅读经验的挑战,因为它提供了传统阅读经验所没有或很少提供的东西,从而也是对我们原有阅读经验的补充和开拓。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活动,它的表现对象也应该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对个体的私人空间的书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本不应该有什么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书写私人空间的作品,是使我们的文学回到了它原本应有的地方。从女性写作自身来看,私人空间的开拓还是对男性话语中心的一种颠覆和消解,因为男性话语中心曾经对女性话语形成了种种限制,以宏大叙事抵消个体叙事、以公共空间取代私人空间,就属于这样的限制。因而,西方女性主义者(如法国的埃莱娜·西苏)甚至认为,妇女在通常意义上进行写作是无济于事的,要想摧毁菲勒斯中心语言体系,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躯体)来写作。(《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无疑是对女性写作、乃至对整个文学创作活动的一个开拓。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关于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关系问题。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两个概念,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无数个私人空间的组合,可以反映出公共空间的若干状貌,但它无论如何也难以替代公共空间,这就跟个体可以反映整体,但个体永远难以替代整体的道理是一样的。当然,文学创作总是通过个体来反映整体的,因而写个体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这里所说的“个体”与私人空间并不是一个概念。私人空间带有某种私密性,大多是指个体生存经验、情感经验、生命经验中比较隐蔽的部分,与公共空间未必有必然的联系,而“个体”所包含的东西显然要多得多,它既有私密性又有公开性,它的公开性部分则与公共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女性写作重视私人空间的开拓,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仅仅停留在私人空间中又是很不够的。如果像有些女性论者所说的那样,女性写作者只有回到“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们能够用来书写自身的只有自身的躯体,那就未免太狭窄了。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这样一种极端的意见,恐怕不应当是我们中国女性主义者所必需效法的。外面的世界毕竟很精采!放弃对公共空间的书写,也会使女性写作陷于褊枯。1995年,我曾在不同场合提出过“一己的感情波澜毕竟不能代替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的意见;1996年,女作家马瑞芳在南京的女性文学研讨会上,也提出过女性写作者要“走出闺阁”的主张;新近,还有一些论者提出了女性写作者有必要开拓写作的精神资源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是对女性写作者的非分的要求。当然,究竟是坚执于私人空间,还是突围到广阔的公共空间,每一个女性写作者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别人无权也不应对其横加干涉、指东划西。
对于理论批评工作者来说,由于他面对的是整个创作实际,因而就不能顾此失彼,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一个时期以来,新闻媒体和理论批评界比较关注和重视写私人空间的女性作家作品,对其津津乐道,连篇累牍地发文评价,而对一些一直坚持写公共空间并取得了不凡成绩的女性作家却重视得不够,是不是新闻媒体和理论批评也犯了“窥私癖”——如有人所批评的那样?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
其三、内视角和外视角
这是与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相对应的一个话题。由于一些女性写作者比较注重对私人空间的书写,因而很自然地更多运用一种内视角的写作,即更注重于个体的内在空间的开拓,更注重于表现人物的心灵世界、情感经验和生命经验,更注重于启用个体的倾诉和个体的记忆。这里至关重要的,可能是个体的体验和个体的记忆。正如林白所说:“对我来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和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被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记忆与个人化写作》)
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源远流长的男性中心机制,客观上阻滞了女性对世界的参与和体验,使女性的视野受到极大的限制。现代社会虽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女性有了较以往更多的参与和体验世界的机会,但女性的性别处境,仍然使她们难以与男性站在世界的同一地平线上。女性的天性也使她更关注个体内在的一些东西。这就形成了女性写作不同于男性写作的一些特点,更注重于运用内视角即是其一。
但女性写作并非注定就只能运用内视角,而不能运用外视角。把女性写作圈定在内视角的写作,这也是对女性写作的人为的约制。事实上,我们的很多女性写作者在实践中早就突破了这种约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和萧红,就是既具有强烈鲜明的性别意识,又要极力冲破性别的约制的作家,她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既运用内视角又运用外视角,女性个体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和时代感、空间感在她们那里是融为一体的。萧红曾经慨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但她却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冲出了这个低矮的天空。在当代,也有既成功地运用内视角又成功地运用外视角写作的女作家。比如张洁,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如《拾麦穗》和《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就主要是运用内视角的写作,但到《沉重的翅膀》和《方舟》之后,则更多的是运用外视角的写作,或内外视角相接合的写作,于是她的作品的视界不断扩大,作品的信息量和内涵也就不断加重。
视角问题的确不应作为评判作品的标准,但视角问题确实也关系到写作者视界的宽窄和大小,视界窄小者必然难以面对纷纭变幻的大千世界,那就只好退回到封闭狭窄的私人空间了。因此我想,为了不对女性写作的发展造成一种人为的约制,我们应当更多地提倡内视角和外视角相接合的写作,提倡从单视角过渡到多视角的写作,而不是只对一种(内视角或外视角)的写作投以青睐,那样就必然造成女性写作的褊枯。女性作者既要关注女性个体生活、个体情感和个体生命领域里的问题,也要关注社会生活、社会心理和全人类所面临着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
其四、自恋和自省、自强
在1996年的南京女性文学研讨会上,我曾经提出过女性写作应该克服“自恋癖”和“自闭症”的问题。当时,我之对“自恋癖”和“自闭症”置疑,是寄希望于女性写作能够冲破封闭的、狭隘的空间,而走向开放的、广阔的天地。但新闻媒体却把我推向了极端,在报导中把我划入了反对“私人化”写作的论者的行列。这当然是误解。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女性写作的“私人化”与价值目标》一文的发表。但是当时我对“自恋癖”和“自闭症”置疑的确是事实。经过这两年,面对着女性“私人化”写作给予我们的文学写作所提供的一些新鲜的经验,它在文学阅读和欣赏领域所形成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使我对这个问题有所反思。我觉得,女性写作中的有一点“自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凡事都得有个度,如果一味地耽于自恋,就会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我这里所说的自恋,是指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癖好、对自己的习性、对自己的情感、对自己意识深处比较隐蔽的角落……诸如此类的东西的迷恋、偏爱、抚摸,应该从诸如此类的迷恋、偏爱、抚摸中突围出去,才是女性写作的广阔的天地。有的女性论者用“纠缠”这个词是很形象的,即女性写作者要突破女性话语的纠缠,实现女性话语的“位移”,才能实现女性写作的自我超越。否则就只能在狭小的私人空间里徘徊,不断地重复自我,不断地被自我所纠缠,从而也就不可能再给读者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
同样是自恋,我想还有一个境界问题。例如以“躯体写作”来说,有的对女性躯体的书写的确很美,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而有的却只是单纯的躯体的裸露,是一种迎合卖点的“裸露癖”,实际上并不是对菲勒斯话语中心的颠覆,而是对它的变相的迎合。当然,公平地说,“裸露癖”并不仅在某些女性写作者那里,更多的是表现在某些男性写作者身上。这属于另一个问题了,恕我略而不论。
因此我想提出女性写作者应该具有自省和自强的精神气度这样的问题。所谓自省,就是对自身的反思、对自身优劣的沉思,换一句话说,就是“认识你自己”。如果认为女性身上的一切都是好的,女性就是真善美的化身,那就未免简单化了。就跟男性的劣根性一样,女性的劣根性也应该是我们拷问和鞭挞的对象。在这方面,我想特别提一下铁凝的《玫瑰门》,这部写于八十年代末的作品,不仅是铁凝创作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而且也是一部以犀利、老辣的笔触来透视人性的优秀长篇,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对女主人公司猗纹人性恶的揭露和拷问。能够以如此之勇气来揭示女性的人性恶,这是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这也使人们对铁凝的创作实力刮目相看!我这里无意于提倡女性写作者都要去审丑,都要去揭示女性的人性恶,我只是在说明一个事实:一个有深度的女性写作者,应该对女性自身的优劣有所沉思,这样,你的写作就有可能出现新的转机。
所谓自强,就是女性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其他的力量)站立在社会上,站立在男性面前,使社会尤其是男性对你刮目相看,甚至对你仰视。前此,我以《自强的女性》为题为女作家胡辛撰文,正是有感于她十五年来正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气度站立于文坛,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自己的强者品格。十五年前她闯进文坛时已38岁,以一名“高龄初产妇”在文坛上左冲右突,扮演各种角色,操作多种文体。如今,她又以“知天命”之龄和一个教授作家的身份到北京大学当“访问学者”,为的是“圆一个北大的梦”。这种年轻的、进取的心态是极其难得、极其可贵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再一次引用了来自新疆的一位女性批评家的话并表示认同:“女性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获得尊严和平等,要谋求事业的发展,实现其社会价值,既不能靠天赐,也不能指望别人给予,不仅必需靠自我奋斗来实现,还必需靠自我批判、自我整合来激励。只有首先认识自己,尤其认识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方能真正做到以行动求平等,以作为求地位,以奉献求发展……”(《任一鸣:《女性:认识你自己》)我以为,这当是当代女性应有的风范。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从自恋到自省再到自强,这是一个女性独立人格完善的过程,也是女性写作的攀升的过程。
其五、双性对峙和双性和谐
一些女性论者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颠覆或者消解菲勒斯中心机制即男性中心机制。这是可以理解的。自父权制社会以来,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国封建社会为妇女所规定的“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律条,更宣判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命运,导致女性独立人格的缺失。应该承认,这种观念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因而颠覆或者消解男性中心机制的确是妇女完全获取解放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但是颠覆或者消解男性中心的机制,是不是解决两性关系问题的终极目标呢?我认为并不是。解决两性关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两性的和谐。显而易见,社会要发展、要前进,不能倚仗两性的对立,而是倚仗两性的和谐。或者说既对立又和谐,在对立中寻求和谐。即令要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也需要借助男性的力量,把男性当成假想的敌手,在当今的世界上是绝对不现实的。倡导两性的平等,承认两性的差异,强调女性的特点和权力、甚至女性比男性优越的方面,等等,并不是要以别一种权力(女权)代替这一种权力(男权)、以别一种(女性)偏执代替这一种(男性)偏执。女性的偏执有时候比起男性的偏执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其实,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也已经走出了双性对峙的阶段。因而,在现时代,真正的女性论者,又往往是以超女性(超性别)的姿态出现的。如法国的“第三代”女性主义者朱莉亚·克利思多娃,她的基本策略之一就是从来不宣称自己是女性论者,而且认为不存在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妇女”或“女性”。她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男人与女人之间对立的二分法只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两性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但两性之间的截然对立或“死战”已明显降温,而让位给通过个体内部的运作而达到对“核心”的瓦解。(《妇女的时间》,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朱莉亚·克利思多娃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女性主义者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许多女性主义者之所以不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也许是与受到这种影响有关?
当然,在现时依然存在着男权中心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坚持自己的立场,开掘被男性文化遮蔽的女性文化部分,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系统和文学谱系,但这与双性和谐的终极目标是并不矛盾的。我想,这也许正是当今的大多数女作家和男作家都赞成双性和谐的缘故。最后,我想引用一位青年女作家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转换可以看做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它们紧相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指望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致于倾斜,才能维系平衡状态。”(迟子建:《我的女性观》)这话说得是何等的好啊!它既充满了睿智,也说出了多数人包括我个人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