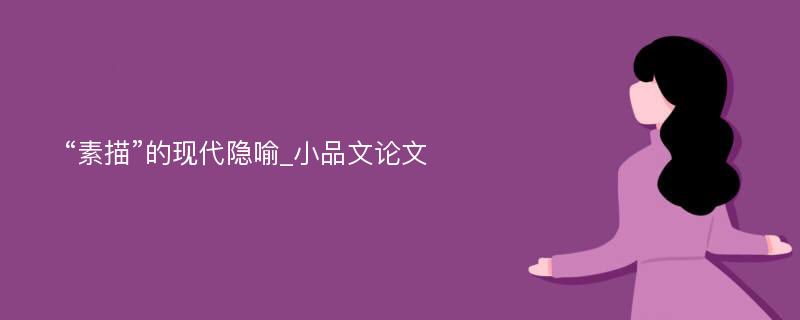
“小品文”的现代性隐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品文论文,现代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6)04-072-06
胡适1922年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新文学》时,就有为新文学溯源之意,他将富有变革精神的白话文学称作“活文学”,以其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源头;在《白话文学史》中,他进一步确立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为新文学的白话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胡适后来更愿意将文学革命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1](P259),显示出倚重传统的价值取向。周作人1932年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亦提出“要说明这次的新文学运动,必须先看看以前的文学是什么样”的论点[2](P19),指出必须为文学的发生寻找“根据”和“来源”,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方法”:横向与纵向的双向探询,使历史与当下融会。同时,由于从发现模拟到独创是日本文学赶上现代世界思潮的有效路径,因此对本国文学,他希望以此为榜样:“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3](P148)这样周作人提出了“创造的模拟”的文学思路。梁实秋则认为传统儒家的文学观念不能令我们满意,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参考西洋文学。不过“我们尽管借助西洋文学的思想,仿效西洋文学的艺术,但是新文学的建设仍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创造”[4](P155),这和周作人的观点有一致之处,“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5](P13)。“中西之辨”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视界,也是散文理论现代性构想的基本精神。五四之后散文源流辨析的本意,或许含有寻找合法性依据的意图,但其最终祈向是一种更具独创性的新文学,个性的创作所能倚赖的不只是欧化的外援,自身血液中流淌的传统更是决定的要素,所谓合法性其实就是基本的可能性,文学的自性特质不可偏废,这就必须苦心孤诣地维护本国文学的个性-主体性,唯此,传统的价值得到肯认。
将公安派小品文和英国essay确立为散文的源流,是现代性散文理论的重要部分。基于中西之辨的现代性取向,周作人于1928年在《燕知草跋》提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6](P124),这种确立其实含有为散文文体内质作界定之意,取两者之共性,更希望在融合中互补,进而形成周作人所谓“创造的模拟”,即最终自我生成为具有独特自性的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对“合成”如何成为一种可能,周作人更具体说过:“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7](P10)。找到外援之后,周作人开始寻找自身传统的“内应”,他发现:“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实在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6](P115);林语堂也认为追踪小品文遗绪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应寻出中国祖宗来,这样才可使一种文体得以“生根”。他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散文中有可以与现代散文接续的潜力,在《论文》中说公安竟陵派之文“甚近西文之familiar essay(小品文)”,其提倡“性灵”,而使文学由载道转入言志,足以启现代散文源流之处在于“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能“抓住近代文的命脉”。其《还是讲小品文之遗绪》重复上述见解,强调其擅用个人笔调、细致体察人生都体现出现代散文的特征。
散文源流辨析最终要提挈的是现代散文文体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包容着的文体特质,周作人说:
法国的蒙田,英国的阑姆与亨德,密伦与林特等,所作的文章据我看来都可归在一类,古今中外全没有关系。他的特色是要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去办差……英法曰essay,日本曰随笔,中国曰小品文皆可也。[8](P116)
他说就是称为“新的俳谐文”也未尝不可,这样,作为源流之一的英国essay渐渐也被翻译为中国式的“小品文”。而林语堂也总是将小品文和familiar essay对照着谈,不论公安派,包括了李笠翁、金圣叹的明末小品,还是乔叟一脉散逸自然而极尽个人闲谈文风的英文散文,他看重的是其中共同的笔调:抒发性灵,以及闲谈自然的笔调所包含的“解放作用”,即打破桎梏、排斥格套的现代文学见解,以现代人生观体会人情、观察人性幽微的现代散文特征。林语堂所谓评价和选取“亦不尽以古时所谓小品为标准,而当纯以文笔之闲散自在,有闲谈意味为准”[9](P179),即为此意。这里他们提挈出的现代性散文理论指向为:转向内心的自我表现,质疑传统、挑战文学成规的勇气,个性的充分张扬,在亲切絮语中的闲适美学。
一
散文源流辨析中,使essay和小品文之间得以沟通的桥梁是逐步确立的散文理念,这一理念获益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甚多,德国狂飙运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均对五四文学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在早期浪漫派的艺术认识理论中,“反思”具有绝对的意义,他们把艺术确定为反思媒介,很大原因是艺术及一切精神领域中的一切因素都表现出反思的特性,包括幽默。也就是说“反思是原本的、建设性的”[10](P80),因而它是作品的本质,是艺术的基础、艺术的理念,这就是浪漫派理论极力推崇反思的根由。他们认为小说是文学中的最高反思形式,不过这一点却基于小说中的散文因素,也就是说散文才是确定文学个性的基础。一方面是因为散文因素使文学 (小说)表露出它有弹性的、不受限制的特点,显示出全面能力,而使文学成为扩展的文学、无限的文学;另一方面,艺术家是充满激情的,但当写作时却基于冷静的理性,所以本雅明说:“当浪漫主义者表达真正的艺术创作物的不可毁灭性这一定理时,他们想到的是经过创作的、充满散文精神的作品”[10](P120)。散文精神是作品的核心,是冷静的——理念就是冷静的——和反思的,所以他认为荷尔德林“艺术的冷静”,“是浪漫派艺术哲学的基本思想”,“冷静”表明它与哲学的方法和反思的方法之间的联系,这种观点认为冷静决定着艺术的本质:
作为艺术原则,反思最强烈地表现在散文中,散文在语用上恰恰是冷静的比喻名称。作为思维的、谨慎的态度,反思是极度兴奋之反,是柏拉图的心醉身迷之反。[10](P118)
反思的冷静特性被作为散文的精神而体现于文学理念中,本雅明举荷尔德林的诗句“你在哪里?在时间中总要离去的——沉思!你在哪里,光明?”和A.W.施雷格尔说的“思索是人追求修养的最早艺术”,进一步说明作为文学理念的散文的精神特性;“冷静的反思”标志着现代文学的哲学倾向,它既是浪漫派的理论主张,又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的余绪,都旨在将沉思方式赋予文学。思、语言和诗,是海德格尔为现代文学的特征做出的归纳,所谓诗意的沉思指明文学中的哲学意义,沉思是散文原本的方式,虽然这种论说并非出于对散文文体本身的思考,但它足以暗示我们更深入领会作为独立文体的散文的基本特性,散文对于文学及其自身的价值都值得更多关注,尤其是“无限的文学”之说揭示出散文的无限可能。
将反思纳入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由反思,艺术的批评这一概念进入了文学创作,这里的批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评判,而是对自身的反思,本雅明引述将反思比喻为“照耀在最早的文学之上的一束光”的浪漫派理论家诺瓦利斯之语来说明其中的关联:“难道反思不是……一种向内的歌唱:内心世界。话语—散文—批评”[10](P119)。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内涵,一是它指明的内向性,二是暗示了作为文学理念的散文其反思的冷静特性是如何通往批评。批评由此作为对自身的反思——对散文核心的表现而成为文学的必然特征,奥·帕兹说:“这种倾向始于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开始突出,但只是到了现代时期诗人们才感受到这种观点那令人眩晕的、矛盾的一面:写作一首诗就是建构一个单独、自足的现实世界。批评这一概念因此便进入诗歌创作的本身”[11](P133-134)。林语堂逐以为现代文化就是批评的文化,只有批评家才能成为“思想界的先锋”、“精神界的领袖”,他以为今日中国,亟待一种批评的力量以使思想复兴、“创出一种新的,健全的,富有充实的新文化”,他认定批评是现代文明的唯一促动力[12](P1-9)。这些理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关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确定。散文的这种承担,是它本然的功能,其应然性则来自于散文对教育因素的倚重,也可以说是对其现代批评精神的确定。这一点同样来自散文的沉思带来的哲学意义,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就对散文教育读者的功能产生绝对信赖,这种信赖早在通过报刊与阅读达到启蒙目的的18世纪初就已开始,(最广义上的)批评——教育通过文学的写作——阅读获得实现,中国五四的文化启蒙运动演绎了相似的一幕,对国民性的批判成为散文必然的选择,散文的启蒙作用来自它内在的反思性。
五四之后,散文现代性理论对初期激进的反传统方式的反思与批评,及其后的理论转向,都体现出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它是散文自身内蕴的精神维度,这种自我否定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示,应把它看作一种内在于现代性的精神表征。虽然利奥塔认为散文恰恰是后现代的,他说,正是在表现里面召唤不可表现的事物、拒绝有关品味的共识、作家处于哲学家的位置、对新的规则的探索等方面,蒙田的散文显示出后现代特征[13](P140-141),由于,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是与现代性有相似性的时代,“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13](P165),那么,他说的散文是后现代的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现代的。这无疑提醒我们,散文具有的无限可能,它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文体概念,具有难以穷尽的魅力。而我们认知五四时期的散文现代性理论,应对其内蕴的不同维度做出开放而深入的理解。
二
而散文的批评性真正成为“向内的歌唱”,却必须是从肯定的批评向着否定的批评转化才可能最终完成的,至少中国现代散文在其现代性设计中是如此。肯定的批评与否定的批评之区别在于基于此前提时,肯定的意味落在对自身的反思和对这一散文核心的展示上,这种展示由于对文学中这一绝对物的信赖而信心十足,所以充满教育的热忱,这使它有可能介入时代和表现出对这种参与的肯定——五四初期散文对文化启蒙的承担就是这种肯定的确认。而否定的批评则是对自我洞察后的超越,这自我洞察包含了对文学本身和创作主体本身的双重洞察,对自身反思的洞悉因超越的企图却常常表现出一种无力感,一种出于深刻却反而产生的对自身能力的质疑,周作人所谓文学无用论可为说明。保罗·德曼对蒙田——一位由于对essay影响至深而同样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阐释,生动地说明了否定的批评:
由于对自身才智活动的过分信任使得他根本无法容忍其毁灭……清晰的头脑能够意识到其自身的主观性的认识功能的自我毁灭。它意识到它的整个生命就是这样一种一连串的失败的延续,而且它知道自己仍然拥有对这些失败进行估价的权利。得益于正负符号的惊人变化,这种权利被确立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就在思想对自身的软弱深感绝望之时,它因为认识到了这种软弱而重获新生。[14](88)
对于现代性认知主体而言,这种软弱的感觉意味着认知功能的某种涣散,即不再是那种充满自信的确定,“无用”和“聊以自宽慰”的陈述中,包含了德曼所言的“失败感”。但对此种失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都和蒙田一样保留了清晰的认识和自我评价的权利,诸多相关论述乃至与左翼文坛的不懈论争都是对这种权利的维护;通过自我评价他们最终将这种看似失败的体认,转化或者说确认为是对中国文学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将文学比作“无用的游戏与享乐”,是为了突出它是以“生命的余情”去创造比现在更自由的、更美的、更好的生活,这样的文学精神至今依然是中国文学的祈向。
也正由于这种“软弱”的感觉所滋生出的对文学教育因素的漠视,而体现出与“时代”的疏离,也使它的异端性彰显出来,这恰是“否定的批评”的基本内涵。所谓从肯定的批评向着否定的批评转化,在中国散文中即使从文化启蒙的宏大叙事到基于旁观者姿态的闲适美学的认取——“小品文”的确认,这个转折绝非随意选取,它体现出重新设计现代性散文理论图式的用意。
“小品文”所认取的或许并不在名称本身,小品文作家们着意强化的是自己与文学的政治化和功利化取向的疏离。在文学对政治和时代的参与几成主流的时期,他们说“文学不革命,但却是反抗的”,这种否定的姿态是否意味着对时代和国家民族的冷漠,一直是他们与左翼文坛论争的焦点,他们强调“小品文意虽闲适,却时时含有对时代与人生的批评”(《人间世》第2期编辑室语),所以不论是当初对传统的质疑、否定,还是此时对革命文学主张的否弃,对他们而言,始终是一种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极度关切而非冷漠。事实上,以文学为政治的解释,表面上看来于时代有益实则在集体性的附和中逃避了个人的思想,终归是虚假和欺瞒性的;意欲使文学为其服务的政治家或许目标明确,但为其效命的热忱文人往往并不自知自己所追捧的观念其实充满了一种可怕的对世界的冷漠:作为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双重冷漠。“使思想定于一尊”在文学上就是使审美体验屈服于专制压力,在更深刻的文化建设上就是使知识分子放弃和隐藏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深入。这就是周作人为什么说“集团的艺术”常借启蒙和民众的名义压制“真的自己的表现”的原因。所谓接着吻的嘴不能同时再唱歌,吁求的是散文家应专注于文学本身,文学的神圣承诺是一种类似于爱情的情感表达,这种体验被充分信赖正因为它来自个人对自身内在性的直接把握,这一类比也可以用来说明文学也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承诺,一种神情涣散的专注的幻象,一切都将取决于写作者个人的文学信念和姿态。而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对国民性的批评,都朝向民族文化和国民精神的时代重建,对政治文学的否定更是为了使之朝着真正有益于文化重建的方向发展,梁实秋说“文学家没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使命”[5](P8)。我们不可只断章取义地对前半句加以抨击,而忽略了后面那充满了文学理想的美好祈想,这里的否定可以更充分地说明否定的深邃寓意,那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世界中的否定渗透了一切思想,但否定并不摧毁一切联系而只是对其进行置疑。这种始终不渝的质疑,如果没有一种本真的理想或信念的支撑将是难以支撑的。胡适曾说:“(五四)整个运动,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以价值重估为特征的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要推翻一切,要尝试,要判断;要批评,要怀疑,根据新标准去评价旧事物。……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怀疑、批评、反抗的时代。”现代性散文理论的创设者秉承了五四的核心精神,从对传统的否定批评到对既存现实及其准则的质疑和批评,更加推崇内在性原则,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正如德曼在有关蒙田的文章中所说,“否定使对于主体结构的理解成为至关重要的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一种从内在性的角度认识世界的职责”。在1966年关于马拉美的博士论文里,德曼对于作家与时代问题有过阐析: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的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与”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应该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小说的问题……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一旦获得这一自我洞察,相应的行动便会接踵而至:
因此,到场但并不参与。
就在生命不断孕育之时,诗歌,作出神圣的牺牲,经受着创造的危机,处于孤寂中。[14](P99-100)
这就是内在性的同时反抗的文学精神的深邃意义,而这种关切个人(内心)的自我意识,正是散文现代性理论极力提倡的,所谓自我意识的优先权,就是认定人所能获得的最确切和直接的把握是对自身的精神意识——即个人内在世界的感受,罗伯特·布兰登说:“我们只能对(我们自己的)精神事件产生直接的意识,……这种直接意识包括我们每个人拥有的、对于我们自身内部活动的、有限的、但却是真正优先的把握,它无须受制于‘赐予神话’”,[14](P237)。自我意识所努力的返回内在的体验使写作显得非常个人化,五四现代性散文理论呼吁要充分承认这种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力量,而不应过分强调写作的政治倾向。
三
或许,今天我们对现代性散文理论的创设者的理解依然是肤浅的,把内在化的姿态仅仅理解为对自由写作的呼吁也是不够的,自由主体的自我选取问题较自由写作的外在化要求才是文学现代性的真谛,也就是说只有乞灵于独立的心灵,散文才能以更加沉入内在世界的方式,在批评和反对的精神维度上获得克服由具体处境所触发的绝望与悲哀的勇气。这也正是阿多诺所倡导的独自抵抗的精神:
艺术的功能并非宣扬选择的自由,而是以自身的形式独自抵抗这个时刻以死亡威胁着人类的世界进程。[15](P101)
内在性作为文学现代性的祈想时,“抵抗”和“否定”,在本体论意义上就是散文(文学)成其为文学的生成之地,即散文获得文学本质之处。对于散文,它赖以区别于非文学的本质毋庸置疑是其文学性。文学的基础虽然“植根在社会现实”中,总是在现实的重负之下,但文学只有在“超越于现实的即时性和克制对现实的直接反应”时获得“美”,“美”是作为一种使文学作品获得超越性力量而被期待的,这就是现代美学所高标的“分离的力量”,也被称为“否定力量”,是质疑既存现实的力量也是激发思想的力量[16](P256),它使文学家在独立的思考中获得精神性和主体性的表征。这一可以赋予文学以独特性、超越性、异在性的维度通常被称为“审美之维”。这是“一个其他经验不可企及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人类、自然界和其他事物不再受制于现存的现实原则的法则”[16](P190-202)。对散文否定的精神及其审美的维度,伍尔夫表达为:“散文必须把我们包围起来,并在现实面前拉起一道帷幕”[17](P110)。蒙田则说自由、隐逸和清静,是散文的必要前提:
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18](P11)
在这帷幕之后或者店铺后间,散文家才有望经由自由的隐逸和冷静的思索而实现自己真正内在的要求使命。得益于这种提示,周作人、林语堂所描摹的喝茶、吃不求饱的点心、看夕阳、躺在床上摹想人生之美、与友人围炉闲话,都意在为散文打开一个能够超越经验现实需要的维度。这种用生命的余裕絮语人生的方式,正因其充满余裕的从容和心灵的放松,而更可能超越外在压力实现个人思想的表达。这也是周作人所谓从“无用的优游与享乐”而来的“闲适”所包容的基本精神。“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9](P403),同样在内在性的精神需求和超远旷达地观照人生的双重向度上提示着散文的文学精神。人生的美永远是“人的文学”要不断絮语的内容,伍尔夫说“生活的很大而且很重要的一部分,包含在我们对于玫瑰、夜莺、晨曦、夕阳、生命、死亡和命运这一类事物的各种情绪之中……我们渴望着理想、梦幻、想象和诗意”[19](P441)。而这些都是谦逊而又无限忍耐的散文能够曲尽其妙地处理的,理解了这一点,即将这样的方式看作是回到文学本身的努力,才能理解为什么现代性散文理论执拗地将闲适设定为现代性散文美学。
收稿日期:2005-09-11
标签:小品文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周作人论文; 散文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反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