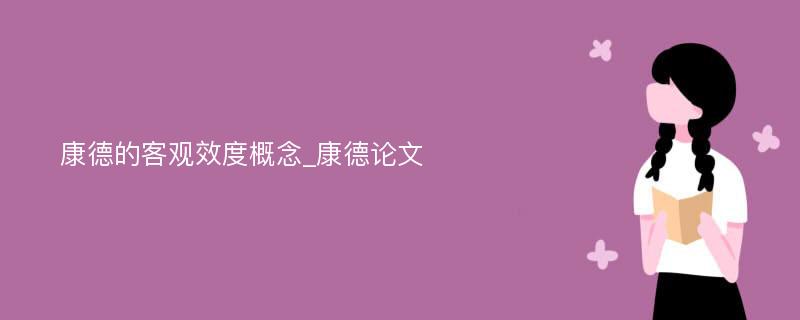
康德的客观有效性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客观论文,有效性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0)06-0081-05
在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客观有效性,以及与之同义因而可以互换的普遍必然性,是贯穿全局且极具关键性的核心概念,确实非同小可,岂容轻易放却;某种程度上,我们视这组概念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或支柱,也应该不算过甚其辞。弄清这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的内蕴,照本文的斗胆臆说,则对把握康德思想的宗旨和脉胳,可谓思过半矣。下面拟围绕这一缠夹的概念,并就相关诸问题,不揣鄙陋,略陈管见。
一
初涉康德,我们发现专家们每将客观有效性解作真理性、正确性和可靠性等等。(注:这是康德学界极其普遍的现象,可以以李泽厚先生《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再修订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为这种主张的代表。当然,也有些学者已经看出,康德的客观性概念,与日常用法大异其趣,譬如杨祖陶、邓晓芒两先生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即属之;奇怪的是他们仍以此责难康德,着实令人困惑不解:这就好比有人读一部儿科医学专著,却大骂作者没有给他提供治香港脚的秘传偏方,更有甚者则大骂作者没有提供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在这方面,据我们所知,唯一的例外是谢遐龄先生的一些作品,如《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从宇宙本体论到理性本体论的转折》(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砍去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谢先生明确主张,康德的客观有效性概念绝不可以等同于正确性;但是他似乎并没有对此做详细的论证,所以有些学者对他颇有微辞,甚至斥为武断,也不无原因。本文的目标,即在谢先生大胆假设的基础上,小心求索,步步为营,顺藤摸瓜,找到如山铁证,替康德鸣冤白谤。)但对这类流行的阐释,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约而言之,其端如次。首先,从使用这一概念的具体语境来看,康德往往有两种提法,一是感性直观、知性范畴的客观有效性等,一是经验判断的客观有效性等。后者后边再加详谈,姑且暂时撇开不论;至于前者,我们知道,感性直观、知性范畴所指的乃是知识的纯粹形式,是做成知识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先验根据,其本身无所谓正确与否,而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怎么能等同于真理?
其次,照康德的基本思路,知性范畴的客观有效性,跟范畴使经验判断成为可能,说的是一回事情。换言之,只要我们把知性范畴加诸感性知觉,那么就可做成客观有效的经验判断,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困惑重重。经验判断多半由归纳得到,因而总是偶然的、可错的;康德似乎并不否认这一点,而且一再强调。那么,经验判断的这种特征,与他声称的经验判断的普遍有效性和客观必然性,如何协调自治?我们完全可以随便地下一明知错误的虚假判断,或者我们已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某一判断缺乏可接受性,而作为经验判断,它又显然是运用某一范畴做成的,因而是合法的;这时我们还能坚持认为它是普遍有效和客观必然的吗?
还有,康德主张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是两个可以相互换用的概念,耐人寻味。他曾就此有一段相对集中的论证,殊为难懂:
我们的一切判断首先都仅仅是知觉判断,这些判断仅仅对我们——也就是对我们的主体——有效,而仅仅在这以后,我们才给它们一个新的关系,即对一个客体的关系,并且愿意它们在任何时候对我们都有效,同样对任何人都有效;因为当一个判断符合一个对象时,关于这同一对象的一切判断也一定彼此互相符合。这样,经验判断的客观有效性就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意味着经验判断的必然的普遍有效性。反过来,如果我们找出理由把一个判断当作必然的、普遍有效的(这不取决于知觉,而取决于包摄知觉的纯粹理智概念),那么我们也必须把它当作客观的,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不仅仅表示知觉对一个主体的关系,同时也表示对象的一种性质;因为没有理由要求别人的判断一定符合我的判断,除非别人的判断同我的判断所涉及的对象是同一的,它们都同这个对象符合一致,因而它们彼此也一定符合一致。(注: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64页。)
这段话粗读之下,其字面意思简直荒谬之极:如果真像这里所说的,关于同一对象的所有判断皆彼此符合一致,那么在任何问题上人们都不谋而合、百虑一致,不会发生任何争议,科学因而也就无所谓进步和发展。这分明是睁眼说瞎话。作为睥睨古贤、下开百世的超一流哲学大师,康德会犯这种低级可笑的错误吗?
另外,康德的范畴表的得来,很讨巧地直接对应于传统的形式逻辑中判断的各种形式。如果说全称判断还可以说它是普遍必然的话,那么对特称判断而言呢?特称判断普的哪个遍,必的什么然?再有,康德列出的范畴表中的模态样式,赫然有可能性一目;那么,据可能性范畴做出的判断如何又是普遍必然的?
凡此种种,均令我们苦思莫解,不知康德何以自圆。问题遂归结为,普遍有效性概念如果不能阐释为正确性,那么它究作何解?
二
涵泳往复,渐有所悟。本文认为,这一问题的满意答案,在1794年7月1日康德的一封信中,透露了若干消息;这封信如此着要,为求便于进窥其中的玄奥,这里不妨详加征引:
1.……此外,人们本来就不能说,一个表象归属于另一物,而只能说,如果表象应成为知识的一部分,那么,只有与某种他物(除了表象所内在的主体)的关系才归属于表象,因此,对于他人来说,表象是可以言传的。若不然,表象就将仅仅属于感觉(快乐或不快),而感觉本来是不可言传的。但是,我们只能够理解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并把它转告他人,前提是:我们直观某物,以便表象这种东西或那种东西,这种直观方式在所有人那里都可以被看作是同样的。这样,这种东西就是对一个复合物的表象,因为:
2.我们不能把复合物当作给予的来感知,而是说,我们必须自己制造复合。如果我们要把某种东西当作是复合的(包括时间和空间),我们就必须进行复合。就这种复合来说,我们可以相互转告。如果我的表象在理解中的综合,与对表象(假如它是概念)的分析,提供了同一个表象(互相产生),那么,对被给予的杂多的把握(apprehensio)以及把它纳入意识的统一之中(apperceotio〔统觉〕),就与对复合物(即只有通过复合才可能的东西)的表象是一回事。这种一致,由于它既不单独存在于表象中,也不单独存在于意识中,虽然如此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效的(可言传的),因此,就被与某种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效的东西,和主体相互区别的东西,也就是说,被与一个客体联系起来了。(注: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211页。)
这里最宜注意的,是康德将我们始终莫明其妙的“有效的”这一术语,作“可以言传交流、可以相互转告的”解。诸主体间可以相互传达的,当然是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意义理论是现代分析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康德固然赶不上这个时髦,但从意义的传达这个角度来解答何谓有效性概念,却可能是一个新颖而富启发性的思路。
我们将康德此信跟前引《导论》那段内容参照起来,仔细品玩,结果惊喜地发现,二者之间有无相通,若合符节,恰好能够互为发明;而那些粗读之下难懂之处,也变得文从字顺,依理成章。按本文的领会,这里需倍加留神的关键,也就是康德全部学说的要义之一,即对象、客体是做成的,而绝非直接被给予的。易言之,经验判断中合乎法则地建构出来的对象,方算人类知识的成员,否则不过一团杂多而已;对象一旦做成,就客观化了,其中既定的诸表象的必然的统一不允许随便更改,而主体赋予它的这些关系,也就表示一种客观的性质。紧紧抓住这一根本大旨,本文认为,康德试图表达的思想无非是说:某人做成一个判断,想转告他人;他人通过核对象和判断中必然蕴含的意识的统一,也即知识的纯粹形式,将有关的杂多,重新整理组合一番,再造、复制出一个判断;这两个判断必然相互符合一致,它们所涉及的必然是同一对象。这里康德所谓的符合一致,目标在于交流的成功,即他人可以准确无讹地把握某人做出的经验判断中的诸表象及其既定的复合关系;通俗地说,即他人可以完全明白某人做出的判断的意思。这里的他人,也逻辑地包括相对于最初做出该对象和判断、异时异地的某人自己;譬如我现在回忆、重阅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时,就可以看作是以他人的身分来进行的。而交流的成功,则有赖于经验判断的先验前提,即知识的纯粹形式;因为对象和判断一旦做成,其中相关的质料即杂多就已定型,这种秩序不容破坏。这样,交流双方的判断,都可以遵循作为纯粹形式的框架结构,不影响真值的确定地相互还原。打个简单而形象的比方,就拿炒菜来说,如果严格地遵循某一美食学家探索出来的菜谱上的配料和程序操作,从理论上讲,无论在什么地方起火,也不管由谁来掌勺,味道应该是一样的;但须注意比喻仅仅是方便说法的权宜之计,不可过于拘执,因为菜谱仍然是经验性的,而知识形式则是空灵的纯粹概念,不沾染丝毫的烟火气息。某人所做的菜肴固然可能正宗地道、原汁原味,但未必可口并富有营养;同理,某人做一判断未必一定正确,他人也不必一定认同。显然,经验判断的有效性较之正确性,更为基础;一个正确的判断首先必得是普遍有效的,但一个普遍有效的经验判断却不必是正确的。质言之,判断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岂能等同视之?
天机一泄,上文提到的诸多疑疑惑惑,顿时涣然冰释,迎刃而解;回头再读康德,也就豁然开朗,无往不适。欣慰之余,下文决定步步为营,乘胜追击,就与有效性相关的其他概念,如普遍性、必然性等,探幽索隐,彻底盘查,以阐明其中的堂奥。先说普遍性。我们注意到,康德曾经多次明确地区分了两种普遍性概念:一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性,一是比较上的普遍性。这两个层次上的普遍性概念各司其职,并行不悖,不能混淆。前者是就经验判断的合法性而言的,意指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具有有效性。这种普遍性是绝对的无限的;它是经验判断性命攸关的立身之本,须臾不能脱离。缺乏这种普遍性,经验判断立即自动丧失作为人类公共知识成员的资格。这种普遍性的品质,是由知识形式决定和保证的;在康德,对人类知识来说,其纯粹形式就是这样,不多不少,别无选择余地。而后者则是相应于经验判断具体内容上的可靠程度而言的。譬如由归纳得来的知识的普遍性即是此类。这种普遍性当然是相对的有限的,跟前者不可同日而语。康德郑重地指出:“普遍的同意并不能证明一个判断的客观有效性。”(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页。)这里的“普遍的同意”只可能是就判断的具体内容而言的。可以设想,这种同意所覆盖的范围,包括数量可观的一批人,或者几代人,甚至迄今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所有文明人,但谁能担保今后人们仍然赞成现在被普遍接受的判断?总之,这两种普遍性分属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两个领域。
相应地,康德也在两个层次上谈到必然性概念。关于这一点,康德有一段义蕴丰厚的话说:“判断不过是所予的各种知识借以达到统觉的客观统一性的一种样式而已,这就是系词‘是’的原意,系词乃是用来区别所予表象的客观统一性与主观统一性的。它指出那些表象对于本源统觉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必然统一性,即令判断的本身是经验性的,从而可能是不必然的。”(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160页。可以参看蓝公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新1版)第105-106页。)其中指涉判断中诸表象的客观统一性的,乃是第一层次上的必然性;而判断本身的经验内容可能不必然的必然,则是第二层次上的必然性。前者出自本源统觉,乃是纯粹概念本性之所在;这是我们得以做成知识的先验条件。在判断做出前,通俗地说,它是驱使我们寻找、探索事物间具体关系的推动者;我们得出的结果可能是或然的,但我们必须抱定事物间一定有必然关系这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出自纯粹概念。在判断做出后,它是体现其为公共可传达的知识成员的标志;我们可以把这种必然性比作判断中诸表象相互隶属、联系的关系的牢固性,因为正是它使得对象中诸表象的那些关系确定下来不可游移。没有这种必然性,主体做出的判断只能是一盘散沙的杂多,根本不能传达给他人。这种意义上的必然性,当然跟模态逻辑所讨论的必然性,无论从言还是从物,泾渭分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最后再略微提一下客观性。在康德,客观的意即把直观中给予的杂多联结到一个客体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干脆也可以说,杂多的联结本身就是那客体。因而客体概念不过是意识的必然的综合统一性的代称而已;或者说,它就是那必然的统一本身的表象。这种统一是绝对必然的、普遍有效的,通过它一个判断中相关杂多可以在他人那里得以完整地再现,即传达给他人。
综上所述,康德所谓有效性意即可传达性,由此得证。值得一提的是,康德本人在创作《纯粹理性批判》时期,对这条线索也很可能并无明确的认识。本文的证据是,康德在前引信末就坦率而遗憾地承认:“通过写下这些东西,我发觉,甚至连我自己也理解得不够。……对于我来说,过分精细地分解这条线索已经不再可能了。”(注: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因而本文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并没有妄下断语,信口雌黄,强作解人。
三
但是,有些康德专家囿于“客观”一词的日常意义和用法,在这一问题上对康德横加指责,批评他的学说矛盾含混。(注:行文至此,颇感犹豫。陈嘉明师在其不可多得的专著《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中极力主张,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还试图从外在客体方面(日常意义上的)为客观有效性寻求保障,尚未建立彻底的现象学,而中经《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到《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则痛改前非。本文于此疑虑颇多。一,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两版之间的康德根本判若两人;这种转变显得太过突兀。康德在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对第一版的〕命题本身及其证明,〔结构的〕计划的形式及其完整性,我都没有发现要改正的。”又说:“〔第二版的〕这种修正,虽然在提出命题的基本要义上,或者在其证明上,丝毫没有任何变动,但是在这里和那里却和以前的叙述方式有很大的出入,不是只用一些插补就可了事。”倘若不仅仅是叙述方式的更改,而是思想上发生质的飞跃,而康德本人居然未尝注意及此,不禁令人惊异。二,据陈先生的意见,像先验对象、亲和性诸概念都是和康德的立论主旨冲突的,因此在第二版中大义灭亲,一律削除。可是陈先生对康德删削之余,仍有漏网之鱼的解释,即康德不胜其烦,我们总觉牵强。以本文的理解,先验对象、亲和性诸概念与康德哲学的要义恰恰融贯自洽,初无不协,起码不会大相径庭。如果这种理解不错,那么陈先生的领悟,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三,何况,康德在第二版序言中同样明确提出:“然而〔第二版〕这些修正是含有一点损失的,那就是我不得不删去或节略的一些段落对许多读者可能还有些帮助,因而他们觉得还是需要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就是说,仅仅为了避免本书变得繁重不堪,这种删节方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康德还指出,这些删节的内容是那些“可能由于我的过失而引起的、乃至精明的思想家在批评我这本书时而陷入误解的那些困难和晦涩之处”。某些措辞遭到误解,并不表明这些措辞本身本来的意思即是如此;将误解后的意思强加康德,有失公允。)这种驳难,就笔者读过的材料,主要有三条他们看来有力的证据,但本文皆殊不以为然。这里我们也顺带地逐点澄清,目的无他,使康德免遭不白之冤而已。
论者们认为最能使康德进退维谷、处境尴尬的证据是,康德提出以现象的亲和性来强迫主体不能由自己的主观意志随便地裁断客体。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按,现象的亲和性乃是保证想象力的综合活动产生的表象联结具有必然性的客观的根据,换言之即给予的杂多在一个客体概念里的联想的客观依据,其要点在于自我意识,因而只能在先验统觉的统一原理中去发现。现象的亲和性依据先验的亲和性。在想象力的活动中,由自我意识的同一性而来的、把一切现象按照必然的法则做成一贯的联结的,就是先验的亲和性。就是说,先验亲和性的作用在于制约想象力,防止想象力过于(盲目的)活跃。而所以能赖先验的亲和性,由想象力产生的图象,最终做成客观有效的知识,端在于所谓自然界乃一切表象之总和,属于自我意识。这些论述与日常意义的“客观”根本了不相干。一念之差,概念错位,结果谬以千里,让人感慨。
论者们自认为抓住的另一个把柄是康德提出的先验对象概念。本文主张康德曾在两种意义上谈及先验对象,虽然他本人并未区分清楚。其一指涉作为现象的原因的先验基质。它完全不可被规定,就是说,不可用范畴来框架它思维它。这里它等同于物自体概念;或者确切地说,物自体的多重意义之一即先验对象。而且,就像康德说的(注:参考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译本第239页,韦译本第306页。),只要高兴,称它为本体也不致犯根本上的错误(康德在其他地方又说,先验对象不能称作本体;但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这里限于篇幅和主题不便展开)。就这个意义而言,说先验对象为客体的客观性提供基础云云,实在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因为在康德,客体指的是知性产生的纯粹概念,或者说它是纯粹思维的表象,其意义在于统一机能,而诸范畴乃是它具体执行统一机能的化身。形象地说,它乃是对象中诸表象被联结在一起的粘合剂。而康德所谓客观的,即具备合乎知性的形式。这跟日常所谓客观,风牛马不相及。
先验对象的另一种意义是康德在讲先验统觉时连带提出的。它是纯粹概念,其表象就是使直观中的杂多必然地综合的意识的形式的统一性。不妨说,它不过是综合统一的代词,或者说是综合统一中含有的必然性的代词。这里的先验对象当然不是物自体,也不可称作本体。它与康德哲学的一般对象概念相当。一切经验的概念,均以这个纯粹概念为先验的根据;就是说,它的作用在于唯一给予我们的一般经验概念以与对象的关系,即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说,先验对象先天地为人们做成知识确定一个标准,即诸表象必须同一个对象相关;而所谓相关,所说的无非是综合表象杂多中的意识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能说它为客观性提供保障吗?唯唯,否否;这要看怎么界定客观性。
康德还有一种说法,即经验判断、知识必须与对象符合一致,也容易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表面上看,它所带的浓烈的符合论气味与康德提出的哥白尼式革命南辕北辙,其实却是貌合神离。关键在于符合、一致的意思;这一点前文业已详论,兹不再赘。
那么,康德是否否认外在的物质呢?也不然。康德的学说是先验观念论和经验实在论的统一。经验实在论并不否认外物的实际存在性,但根本否认了外物对主体做出判断、进行知识创造活动的制约性。主张康德(曾经)向外寻求客观性保障的学者,问题出在对经验实在论的内涵体会不深。在康德看来,外物充其量只能提供杂多,而无法提供公共可传达交通的知识所蕴含的必然性。但是,康德立论主旨不是探讨认识发生学,即如何做出正确的、普遍同意的、合理的知识。所以,康德的逻辑是,尽管由于天赋的判断力上的缺陷,某主体做出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不可靠的,但它仍然具有客观有效性。
四
临末,本文仍围绕普遍有效性概念,简略地提出两点主张;进一步的发挥论证,则请俟异日。
一、康德的客观有效性概念,在其整个学说中一以贯之地都着眼于形式的普遍必然性。本文上面的阐释,主要依据的是《纯粹理性批判》,强调经验判断的客观有效性、普遍必然性是从知识形式来讲的,而不可与经验判断内容的可靠性、正确性等量齐观。与此相应地,在实践理性领域,客观有效性、普遍必然性也不是在质料内容层次上谈论的概念。这就是说,在康德,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与其合理性也不是一回事情。
我们知道,康德用以发现诸给予的东西的先验前提的,乃是先验方法;经验知识的纯粹形式的发现,就是运用先验方法的结果;这种方法运用于实践理性领域,则导致自由的发现。我们可以直接把握的,只是具体的一时一地的道德法则和伦理规范;但这些法则、规范都体现了自由,或者说,它们都以自由概念作为其逻辑前提。所谓自由,强调的是人具有克制各种自然欲望和感性冲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可以不必遵循自然必然性,因而人可以有所不为。总之,任何道德规范都预设和假定了人是自由的,而非自然的奴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者说正是在作为形式的自由这个层面上,康德对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展开详细而深刻的讨论。康德当然十分清楚伦理实践会随着时代、社会、民族、集团等等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某种具体的规范可以是相对的即具有历史性和区域性,因而不见得是四海皆准、百世不惑,但就其都是自由的体现即假定人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言,则是普遍有效的。一句话,像经验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跟其可靠性不一样一样,伦理规范的普遍有效性跟其内容上的合理性也不一样。
二、如果本文对康德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概念的阐释不错,那么康德和休谟在因果问题上的关系这段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公案,就可结算明白。(注:在这个问题上,分析哲学家张志林先生的新著《因果观念和休谟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立论谨严,充分展示了他的哲学才能,绝非一般拾人牙慧者可比,因而足觇当代汉语哲学界的研究水平,很值得重视。他试图以康德的学说为基础,重解休谟的因果问题;但他在普遍必然性概念上囿于流俗主张,始终未窥先验逻辑之堂奥,不免功亏一篑,实在可惜。)大体上我们可以说,休谟始终囿于形式逻辑来讨论问题,虽然他的学说离先验逻辑仅一步之遥。这一点,可以由归纳问题作为他讨论因果观念的副产品派生出来,清楚地看到。(事实上,休谟的宗旨始终在于因果问题;他甚至根本没提过归纳一词,虽然后来的哲学家围绕他的讨论,发挥整理出一个归纳问题,也不是空穴来风。)而在康德,因果性原理是说,一切变化都依据原因和结果的联结法则而发生;也即是说,为了使事物状态和知觉前后彼此相随的时间关系具有必然性,就必须把它们置于因果性的法则之下。所以如此,原由端在于,具有必然和综合统一性的概念是纯粹知性概念,并不存在于知觉之中;或者说,如果有所谓公共可交流的知识,就必须有这种客观有效的联系,否则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既成的知识,譬如某一具体的特定的因果判断。因果律作为纯粹知性的先验原理,乃是先验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的客观统一以其诸范畴通过时间图型实现于经验对象之上的结果。
关于这个道理,康德在揭露休谟何以失足时,明确扼要地说:
所以,如果蜜蜡以前是硬的,而现在融化了,虽然在验前,不依靠经验,我们不能在任何特定的方式上从结果确定其原因,或者从原因确定其结果,但是我验前却能知道,在前面必定有某东西(例如日光),而融化则是按照固定的规律跟在它的后面而来的。所以休谟在从我们按照规律而确定的不必然性推论到这条规律本身的不必然性时,是犯了错误的。他把“超出一种事物的概念而达到可能的经验”这件事(这种事是验前发生而构成这个概念的客观实在性的)和现实经验中总是属于经验的对象的综合混淆起来了。所以他所混淆的,乃是亲和性原理(这条原理的位置是在知性里面并肯定必然的联系的)和联想的规则,而这规则只存在于想象力的模仿能力里面,它所能表示出来的只是不必然的联系,而不是客观的联系。(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译本第642页。)
所有这一切均在先验逻辑层面上予以论证;这是整个哲学史上先验论证策略的首次运用,也是当代(分析)哲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总之,以先验逻辑的观点看(注:近读钱捷的《判断力的功效——论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答》(收入《德国哲学论丛(199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94页),发现该文的主旨跟本文这里讨论的要领,大体上是不谋而合的。该文的贡献在于,就康德如何回答休谟问题,做出细致的梳理。而本文则直探根本,因而可以说给该文的主张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吾道不孤当然值得欣慰;不过该文的发表说明,尽管本文仍然有独立的价值,但看样子它已不全是什么独得之秘了。促使我把好几年前写的这篇旧稿拿出来原封不动地发表,部分原因就在这里。),一个经验判断中具体的因果关系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当然太可怀疑,但对因果律本身的怀疑,其荒唐就好比一个人暴跳如雷,咆哮着吼道:“他妈的,凭什么证明我脾气坏,没修养?”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怀疑这种(语言)游戏要玩得转,毕竟先得有不容怀疑的东西作为前提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