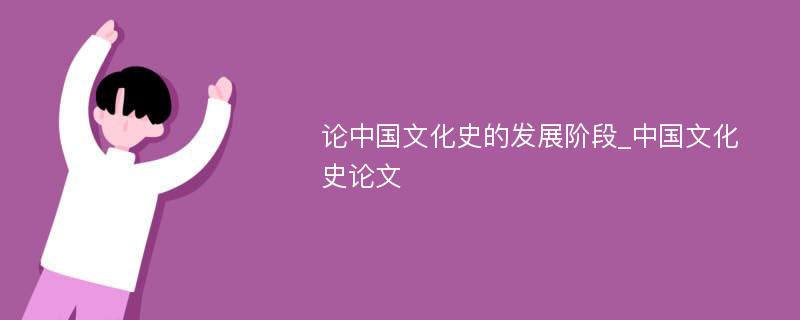
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462X (2000)03—0134—06
随着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学界同仁发表了不少的文章来探讨此问题,提出各自的见解,读后获益良多。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也发表一孔之见。
一
中国文化史的分期问题,涉及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诸多领域,比较复杂,因此,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难点问题之一。我们认为,在讨论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文化问题入手,即我们要从对“文化”的含义之诠释入手,然后以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去展开,用以观察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符合文化自身演生、发展规律的结论。因为“在我们的科学中,没有严格的定义就没有了明晰和准确。”那么,该怎样解释文化呢?笔者以为:“文化是从古至今人类在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全部知识的各种系统的总和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它的物化结果,以及受这些知识体系所指导而形成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在人类行为中的体现,它包括静态的积累和动态的创造两个方面。人类要进步、发展,就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和传承,因此,文化又表现为一种过程,积累和创造是这个过程的两端,居于中间的是人们对已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即各种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学习、掌握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也就是受教育的过程,这正是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文化的过程就是把上一代人所创造并积累起来的各种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传授给下一代人,并由下一代人用自己的创造去充实它、丰富它,再传给下一代人,如此而不断地累积、创造、传承下去,构成人类文化发展的川流不息的动态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难以理解文化的深刻涵义。”[1]在这里, 文化的实质或核心可以概括为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两大体系及其积累、运用、创造和传承的过程。只有把握住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才能使文化史免于泛论,克服其广至漫无边际、狭至局限于精神领域,令人均不能满意的弊端。把文化聚焦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就使文化成为有形的、可以具体把握的东西,而文化的发展历程也就可以用具体的界标进行揭示。
此外,人们在谈论文化这一问题时,往往还同时使用“文明”一词,经常是文化和文明交互使用,使人感到文化和文明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如泰勒就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 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是如此使用的,如他们谈道:“西晋以来,整个东亚文明的基本主题——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冲突和融合——导致中原农耕文化的中心向东南转移。”这里的农耕文明与农耕文化,也并未得到具体的解说,想来在内涵上当无多大区别。我们认为,为了使我们探讨的问题明晰和准确,文化和文明应该加以区分。对于文明的内涵应该这样理解:“文明是由文化的成果凝聚而成,它是人类文化在各个时期所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社会体系和行为规范的外在显示。第一,它必须有客观的物质实在物为标志,如村落、城镇、民族、国家、宗教实体、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第二,它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生产工具体系没有发生重大变革和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质变以前,它不会产生质的飞跃;第三,它必须有为社会所公认的行为准则,并通过语言、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各种社会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加以规范。”[3]
文化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文化的核心是掌握了一定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人,没有了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运用,也就没有了文化。但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生存的文化背景,人们一出生就已生活在自己祖先所创造的特定文化氛围之中,通过对前人所创造的全部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学习和把握,人们具备了生存、生活所必备的各种素质(从物质生产到社会行为到思想活动),并用自己的生命活动去发现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领域,进而丰富人类文化的内容,推动社会的前进。由于知识的内在联系使其本身具有凝聚力和驱动力,所以文化也就具有内在的驱动性,由于一代一代人的传承、累积和创造,促使文化的发展变化迅速而又频繁;文明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实体,它是文化的对象化及其结果,是文化所创造成果的物化或外在显示。如由物质文化成果凝聚成的各种器物、工具体系,由制度文化成果凝聚成的各种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由精神文化成果凝聚成的各种文学、艺术成品,由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凝聚成的道德观念、道德范式和行为准则,等等。文明在一定时期内作为社会实体的相对稳定,使人类能够享受自己所创造的各种文化成果,并用新创造的文化成果去丰富它,由此而标志着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类开化的程度。当人类的文化成果发生了突破性的质变(其中以物质文化成果为代表)时,就会将人类的文明程度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
在对文化与文明的内涵及其关系进行了诠释之后,我们以此来观察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发展时便可发现,以文明进程而论,中华文明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原始文明时期,这一时期大致是从远古直到夏王朝的建立为止;二、农耕文明时期,这一时期的产生当可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原始农业的出现,但作为界标当以夏王朝的建立为其开端,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为其结束,在此期间中华文化有许多发展与变化,但农业生产方式则是整个社会生存的基础,并无质的改变;三、工业文明,这一时期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实则洋务运动是其真正的起始,一直发展到现在仍在继续。以文化发展而论,作为中华文化演进基础的物质文化始终处于农耕文明的制约之下,即使是向工业文明过渡也不能摆脱其影响,在这种历时久远的农耕文明制约之下的中华文化之演进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1.酝酿成型期,2.梳理完备期,3.发展高潮期,4.成熟裂变期,5.冲击转型期。
第一,酝酿成型期:从远古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为止。这一时期有以下特点:
1.中华文化的多元起源。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表明,不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中华文化的起源都是多元的。由于文化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中华文化的摇篮和文明发祥地。正因如此,考古学上才对中华文化起源问题提出了区系类型研究的划分。
2.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并存,而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农业,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由此而规定了中华主导文化的发展方向,但在这一时期,中华大地基本上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的状态。而此时由于骑马术尚未发明,故游牧文化尚未构成对农业文化的严重威胁,且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文化的区域不断扩大,构成中华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
3.以中原为中心的统一趋势的形成。从新石器时代70多处遗址到进入原始社会末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趋同性,至江汉、河洛、海岱(见蒙文通《古史甄微》)或曰华夏、东夷、苗蛮(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三大集团的形成,到夏商周三朝的迭主中原,正是这种统一趋势的实际表现。这种趋势的形成既有经济上农业开发的驱动,也有强悍部族武力的征服,更有杰出人物的活动在其中,既有文德的感化,也有武力的威慑,还有地理环境的因素在其中,但更主要的应是农业文化逐步发展造成的向心凝聚力。这种统一趋势乃是后世大一统的思想产生的根源,也使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之形成成为必然。
4.西周王朝建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是中华文化体系成型的主要标志。在农耕文化和血缘关系网络的笼罩下,周人对夏商以来的文化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提炼。一则通过兴建洛邑作为划分天下四方的中心并以此制定了畿服制、分封制、宗法制、朝聘盟会制度等,由此而形成了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制度文化的雏形;二则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创立了注重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并以“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为特点的礼乐制度,其中“‘德’与‘孝’是西周伦理价值观的核心”,而其“外在表现形式是‘礼’”。[4] 这一礼乐制度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基础工程,规定了以后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
第二,梳理完备期:从周公制礼作乐以后,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止。这一时期有以下特点:
1.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整理与继承、弘扬。西周后期,开始出现了王室衰微、王权下移、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的局面,周公所创建的礼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面对这种形势,有孔子挺身而出,以继承和弘扬礼乐文化为己任,兴学任教,搜求、整理古代典籍,创立了以民为本、以仁为核心、以礼作为行为规范的一套阐述礼乐制度的系统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由此开创了儒家学派。这是一个与社会政治、身心性命紧密相连的文化体系,经后世儒学传人的不断阐释、发挥和改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此,“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5]
2.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使中国文化中的各种思想流派得以形成,中华文化体系得以充实和完备。西周以前是学在官府的时代,所有的古典文献皆由王的史官世代掌守,但至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周室既微,载籍残缺”,结果导致文献图籍散向四方,知识文化流布于民间,由此而有诸子百家“私学”的产生。这兴起于春秋中后期以迄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思想解放,活跃有生气,涉及面广,丰富而多彩”的时代,因而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到汉代开始又转变成儒家定于一尊的局面”。[6]
3.中国行政体制的奠定。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巩固,是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系统化的最重要成就。从春秋到战国数百年间的诸侯兼并,使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发生了根本变革,诸侯们在争战中为加强实力而建立的国君专制是以县制和官僚制为根基的,到战国时期形成中央集权政体和郡县制,最后由秦始皇的统一中国而推广到全国,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其后经西汉前期吴楚七国之乱的冲击,到汉武帝时期正式确定下来,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延续二千多年的主要制度文化。郡县制乃是中央集权政体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得以稳定发展、整个社会得以实现稳固的大一统的基础。
4.儒学独尊的文化主体框架的构建。孔子继承周公礼乐文化体系并创立儒学体系,在战国时期虽经孟、荀的继承与发展,但也只是诸子中的一派,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是对儒学的极大冲击。直到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新的改造、阐释和完善,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为主的一整套新的学说理论体系,被汉武帝定于一尊,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儒学的提倡和尊奉,才真正使其成为封建王朝实用的政治学说,才使儒家思想所派生的伦理规范深入人心,以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7]这样, 汉武帝时期就完成了中国文化体系主体框架的梳理和建构,中央集权统辖的郡县制和定于一尊的儒学思想体系是它的两个车轮,道、法、阴阳五行等其他思想流派与之相互为用,从此使中国文化走向稳定的发展并在唐宋时期达到高潮,后世虽迭经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却无法改变它的发展轨迹。
第三,发展高潮期:从汉武帝以后直到唐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时理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基本完成。从汉武帝以后至南宋灭亡,中国历史又经历了两次分裂混战的民族融合时期。其中五胡十六国以至南北朝的对峙,正是两汉以及西晋强盛之时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吸纳所造成的,如果中央王朝统治力量强大而稳定,那么这种民族融合就可能在和平环境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一旦中央统治集团陷入内乱,则被吸纳进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便乘时而起,使民族融合变成以血与火的方式进行。五代十国以及宋辽、宋金的对峙大体上也是这样两种途径,只不过其斗争、融合的范围更大、舞台更广阔而已。这是中原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吸纳、涵化的过程,我们不同意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农耕文化同化力减弱的说法,当这一过程完结之时,那些被吸纳进来的少数民族也就完全融入汉族之中。
2.制度文化的完备。这一点首先表现于中枢政治体制的演变,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削弱相权,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演化,形成了隋唐宋时期更加完备的三省六部制;其次是以科举制为代表的选官制度及一应的任用、监察、考核、升迁、罢免、奖惩制度的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相互制约而又有明确分工的官僚体系,使得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更加完备,也使这一集权政体更具弹性,统治基础更加扩大和稳固。
3.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涵摄。从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到唐宋时期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佛教为了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和传播,自传入之后就不断改变、调整自己以适合于中国的社会传统,它首先依附于两汉时特别盛行的黄老道术及神仙方术而得以流传,继而依附于魏晋玄学以打入中国思想界,经南北朝统治者的提倡,到隋唐时期形成了许多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而以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传入、普及与发展,不仅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佛教最终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外文化相互涵摄的结果。
4.理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学便居于中华文化体系之主导地位,但由于佛教的传入、玄学的兴起、道教的产生,一度使儒学的体系受到冲击,以至有隋唐佛学之称谓,并将儒、释、道并称三教,直到“宋代而理学兴起,对于佛老进行了理论的批判,从而恢复了儒学的权威。”[8] 理学的正式诞生是在北宋中叶,但其渊源却很久远,远者乃汉魏以来的经学、佛学和道教之互相激荡、长期各自发展并互相涵摄,由此而构成理学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近者乃中唐以后新禅宗的盛行、新文学运动(即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开展与新儒家的兴起,“三者的发展持续到北宋,并形成了主导宋以后文化的主要形态”[9](P16);而北宋时期兴文教、抑武事的政治方略、“三教并用,尤重儒学”的文化政策等乃其形成之“缘”,这样经过周、程、张、朱等几代人的努力,建构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到“南宋理宗时,由于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的积极倡导,理学确立了思想统治地位。”[10]由于理学的创立以及儒家经典十三经的形成,影响了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因而理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高峰阶段。
第四,高度成熟的发展与裂变时期:这主要指元、明至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这段时期,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大一统疆域规模的底定,这是中华民族融合完成的标志。元王朝以蒙古族而入主中原,实现了稳定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明清以来中国疆域的基本规模;明兴以后虽将蒙古族逐回漠北,但蒙古高原与内地已形成血肉一体的联系;满族兴起以后所建立的清王朝,由于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的问题,又抵御沙俄入侵、收复台湾以及实行满蒙联姻与盟旗制、金瓶掣签制、改土归流、平定准部和回部等,使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局面最终完成,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2.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成熟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皇权专制的高度发展及其绝对化,如明代洪武时期废丞相、升六部及永乐时期的设内阁,尤其是清代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设立,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它是由内廷官扩展为中枢官的最后压轴,是君主独裁专制进入顶峰的产物。”[11]二是科举取士在内容上的僵化,自元朝开始确立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地位,至明创八股文,此制一直沿用到清末。由于内容上的陈腐与僵化,因而限制了知识界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士子只知四书五经、纲常名教、子曰诗云、忠孝节义之类,而于发明创造、国计民生、科学技术则茫无所知,或视为奇技淫巧,由此而造成“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
3.理学的裂变与新思潮的出现。南宋时确立了理学的统治地位,在其后数百年的发展中,由于统治者冒充为“理”的化身,片面强调被统治者的义务而抹杀其权利,“片面地借用道德准则体系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抹杀准则的相互制约性而造成对被统治者压迫”[9](P7), 因而理学成为僵死的教条,对中国社会起着严重的束缚作用,于是有阳明心学的出现,“冲击了长期被朱熹思想所控制的局面,起到了活跃学术空气,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而当阳明心学走入末路时,“一些启蒙思想家或者利用并发挥王学反传统倾向,或者利用并修正阳明学的某些命题而创立自己的学说。”[12]于是有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对封建君主制度的批判,是谓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出现;有唐甄对理学的批判;有实学思潮的发展。而当清朝统治者竭力倡导理学时,乾嘉学者则埋首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清理与总结,遂使“儒学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志。”[13]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裂变的思想仍未脱离传统儒学的窠臼。
4.中国社会的发展态势由开放转向封闭。中国社会在唐代由于统治者的恢弘大度,从而创造了唐文化的廓大气象,这一势头一直保持到元代。自明代前期郑和下西洋之后,逐步转向了内敛,至清代而转向了封闭。明代在对外贸易上实行的勘合贸易、清代从海禁到闭关政策的实施是其主要表现,而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熙朝纪政·纪英夷入贡》,卷六),则是这种内敛、封闭社会态势的最好注脚,它对中国发展之限制、阻碍是有目共睹的。
第五,冲击转型期:这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当代仍在继续。对这一转型时期的特点,一些研究概括很有见地,笔者在这里只想强调以下几点:
1.中国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才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在此过程中,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冲击造成了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由此而影响到中国社会进程的方方面面,而中国对西方工业文明由学习、引进到自觉的发展,则构成了这段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
2.从文化本身的转型来看,中国文化对西方已经创造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采取的是积极吸收并且自己也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以其为实现工业化及增强综合国力之所必须;对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则是进行了比较和筛选,最后选中的是马克思主义,但在制度文化方面却是移植了经列宁、斯大林改造后的社会主义体制;如果从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层面看,则这种转型所造成的中西文化碰撞远未结束,新的适合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价值体系尚未建构完成,因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仍在继续。
3.大力发展教育是推动中华文化转型及早完成的根本手段。作为文化的主体,只有掌握了知识才有文化,理性的启迪是人类文化的开端,知识的系统化及其积累、运用、传承和创造,是文化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各种知识体系应用、普及的程度,对知识追求、崇尚的社会氛围,决定、制约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而实现知识普及、造成追求知识的社会风气、推动文化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的过程,其中价值观念、价值体系的建构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才能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扬弃,才能建构起适应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收稿日期:2000—01—06
标签:中国文化史论文; 文化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知识体系论文; 汉朝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汉武帝论文; 理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